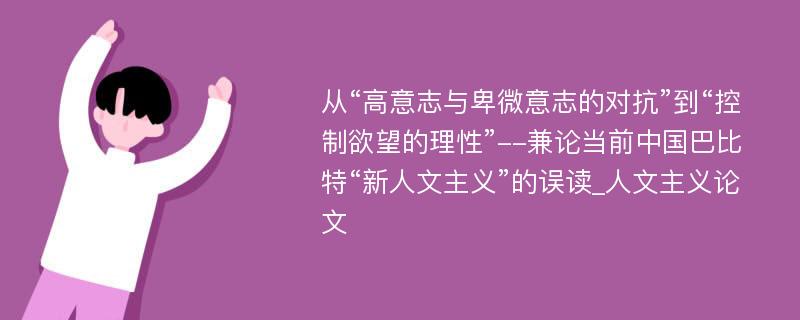
从“高上意志及卑下意志之对峙”到“以理制欲”——试论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在当前中国的一例误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志论文,卑下论文,人文主义论文,误读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375(2004)04-0035-07
白璧德(Irving Babbitt)的“新人文主义”思想针对当时美国“物质之律”(Law for thing)横行于世的情况,提出人们应转而研究“人事之律”(Law for man),以求通过“中庸之道”(the doctrine of the mean)在“一”(the One)与“多”(the Many)之间保持最佳的平衡;而实现这一“最佳平衡”的途径就是:以个人“高上意志”(the higher will)制约“卑下意志”(the lower will),不求诸于外在制约力量,而力求在人的内心达于“内在制约”(inner-check)。“‘高上意志’对‘卑下意志’的‘内在制约’”在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考察这一概念在当前中国的接受情况,或许可以反映出整个“新人文主义”思想体系在中国目前的接受与误读。
一、“以理制欲”抑或“以‘礼’治欲”?
1924年8月第32期《学衡》中有一篇题为“白璧德论民治与领袖”的译介文章,译自白璧德新作《民治与领袖》(Democracy and Leadership,1924)的绪论(Introduction)部分,译者为吴宓。在这篇文章中,“高上意志”及“卑下意志”作为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核心概念首次出现在《学衡》杂志,并第一次为国人所知。(注:在白璧德系列著作中,“the higher will”一词本身系在Democracy and Leadership一书里第一次出现。《学衡》在当时是中国宣传白璧德思想的唯一阵地,参阅吴学昭 译,“欧文·白璧德与吴宓的六封通信”,《跨文化对话》,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0期。吴宓在Democracy and Leadership一书出版后第一时间选译了该书的绪论部分,因此“白璧德论民治与领袖”一文即是Democracy and Leadership在中国的第一个摘译文,从而在《学衡》首次出现的“the higher will”及“the lower will”二词,亦属首次在中国为人所知。该词在《学衡》中还有其它中文译名,如此后1931年3月第74期《学衡》“白璧德论班达与法国思想”一文中,译者张荫麟将其译作“更高意志”、或“更高的意志”。)吴宓在文中“高上意志及卑下意志之对峙。”一句下面作了两行夹批:“吾国先儒常言‘以理治欲’。所谓理者。并非理性或理智。而实为高上之意志。所谓欲者即卑下之意志也。”吴宓用中国古已有之的成说“以理治欲”来比附白璧德的“内在制约”概念,就当时的时代语境而言,是非常接近白璧德原意的。
值得注意的是,新时期研究者的论著中也不乏“以理治欲”的提法。目前研究“学衡派”的专著中,近至2001年出版的《在欧化与国粹之间——学衡派文化思想研究》是最有代表性的一部,书中将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概括为“‘一、多’融合的认识论,‘善恶二元’的人性论,以理制欲的实践道德论”,[1](P44~47)然而,在此“以理治欲”一词的出现却显得颇为突兀,似乎吴宓将“新人文主义“思想比附为”以理治欲”是顺理成章的,而新时期研究者将这一发挥一旦坐实就会令人感到于义未安。这其中原因何在?我们注意到,《欧化》一书中关于白璧德及其思想的讨论,引文大多来自《学衡》杂志以及吴宓主编的《大公报·文学副刊》,因而不免会部分承袭“学衡派”惯用的套语(如称白璧德为当时文学批评界的“泰斗”,“学问博大精深”等等,其中包括“以理制欲”一词也成为引述资源之一),那么,在现当代中国对白璧德思想的接受过程中,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们不妨首先将问题回溯到吴宓那里。
吴宓是“新人文主义”思想在中国最有力的宣传者,是白璧德的得意门生,通读过本师所有的文章,堪称深悉“新人文主义”的精义,因此吴宓对“新人文主义”核心概念的理解本应不会偏离原意。但是,就在“白璧德论欧亚两洲文化”一文中(该文译自《民治与领袖》一书的第五章,载于1925年2月第38期《学衡》,译者也是吴宓。即与吴宓作“以理制欲”注脚的文章取自同一本专著,译者相同,且刊载时间前后间隔不过六个月),我们看到了白璧德本人根据孔子的学说对“高上意志与卑下意志之对峙”所作的阐释:
“诚以亚里士多德者学问知识之泰斗。而孔子则道德意志之完人也。……孔子尝欲以礼(即内心管束之原理)制止放纵之情欲。其所谓礼。显系意志之一端也。孔子固非神秘派之轻视理智者。然由孔子观之。理智仅附属於意志而供其驱使。二者之关系。如是而已。”(注:英文原文为:"He(Confucius)was not,like Aristotle,a master of them that know,but a master of them that will....The decorum of principle of inner control that he would impose upon the expansive desires is plainly a quality of will.He is no obscurantist,yet ther?le of reason in its relation to will is,as he views it,second ary and instrumental."etc.见:Irving Babbitt,Democracy and Leadership.第165页。比照原文来看,最末“二者之关系。如是而已。”一句系由译者吴宓添加。)
可见在白璧德看来,儒家学说与自己的“内在制约”说相通之处恰恰在于“以‘礼’治欲”。其实,一般论者也都倾向于用先秦儒学来阐释、沟通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其中见出白璧德“内在制约”说通于儒家“克己复礼”之旨的研究者亦不在少数,如台湾学者沈松侨曾明确提出:“‘内在克制’(innercheck)……就是儒家所谓的‘克己’之道”,白璧德那种“尊崇传统的态度,相当于儒家所谓的‘复礼’”。[2](P128~131)
我们且不论白璧德对孔子之“礼”的定义是否精准(他简单将之目为“内心管束之原理”),以及他本人提出的孔子之“礼”即“高上意志”(即“制止放纵之情欲”的“意志之一端”)的见解是否得当,也不论其他研究者用儒家的“克己复礼”说来沟通白璧德的“内在制约”说是否合理,在此我们仅着重讨论吴宓对白璧德思想的理解问题。此“礼”非彼“理”,可谓昭然若揭,何以以谨严著称的吴宓竟会忽略这一点?或者说,吴宓为何要舍弃更为“相通”的儒学“克己复礼”之旨,独独强调白璧德思想与理学之“以理制欲”说的关系?——仅以“就事论事”的态度来研究眼前的问题,显然收效甚微。或许我们还应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从那个时代的整个氛围和学者的心态入手来找寻吴宓对“高上意志及卑下意志之对峙”作如此解读的原因。
二、“科玄之争”的时代背景
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涌入中国的各种思想观念和理论流派中,我们特别要强调“唯科学主义”(scientism)在当时国内意识形态冲突和价值体系转换中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当时风靡中国的种种口号与运动,无一不是给自己贴上“科学”的标签、乞灵于“科学”战无不胜的神奇力量,由此而获得批判、取代传统价值体系之权力与势能的。五四新文学运动即是以“赛先生”作为内化于自身的灵魂之一(3)(P1~8)对承载着旧价值的旧秩序发起的致命攻击。有论者认为:1900年后的30年隐含了后来中国发展的大量线索:头十年里旧秩序迅速坍塌;在第二个十年里人们就新观念在中国的运用进行了批判性的讨论,在第三个十年里人们已看到了大众对新文化的运用,此时儒学为思想和文化提供参考框架的功能已经衰退,科学精神取代了儒学精神,科学被认为是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哲学,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实体,被引进取代旧的文化价值,并最终在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论争(或科学与玄学之争)中取得了永久性的胜利。[4](P1~8)“科学”作为强劲的时代脉搏,代表了中国当时的核心价值取向,一切旧的价值体系都在那种摧枯拉朽的力量面前一败涂地,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所谓的“玄学”。
关于“玄学”,陈独秀在《科学与人生观》的序言中说:“社会科学中最主要的是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哲学”,并在“哲学”一词后加括弧说明“这里所指是实验主义的及唯物史观的人生哲学,不是指本体论宇宙论的玄学,即所谓形而上的哲学”,并根据孔德(Auguste Comte)对人类社会三个时代的划分,认为大多数中国人还处在“宗教迷信时代”,次多数是“像张君劢这样相信玄学的人”,还有就是“像丁在君这样相信科学的人”,而“由迷信时代进步到科学时代,自然要经过玄学先生的狂吠”,[5](P4)从而“玄学”成了人类进步道路上的一块绊脚石,也是这场论战之斗争矛头直指的对象。
在中国,“玄学”(注:中国唯科学主义的主将丁文江所反对的“玄学”是“中外合璧式的玄学”,即“西洋的玄学鬼”如柏格森等人的主张外加中国的陆象山、王阳明等人的心性说。见丁文江“玄学与科学”一文,载于《科学与人生观》。)就是指宋明理学。如吕思勉在《理学纲要》中论及“晦庵之学”时说:
“人类之思想,可分为神学、玄学、科学三时期。神学时期,恒设想宇宙亦为一人所创造。……玄学时期,则举认识之物分析之,或以为一种原质所成,或以为多种原质所成。……玄学之说明宇宙,至此而止,不能更有所进也。宋学家以气为万物之原质,与古人同。而又名气之所以然者为理。此为当时之时代思想,朱子自亦不能外此。”[6](篇八,P94)
吕思勉在此理所当然地把“宋学家”即“理学家”归入了“玄学”一类,同时,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使用的正是陈独秀在“科玄之争”中使用过的分类话语。尽管吕思勉本人不乏为“理学”辩护之意,(注:如吕思勉曾云:“宋儒所谓理者,……其说自成一系统:其精粹处,确有不可磨灭者,则固不容诬也。”见《理学纲要》,篇十五,第197页。)但从他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上述分类话语的情况看来,我们可以推想“科玄之争”在当时以及后世影响之剧,同时亦可知那些已经深入人心的话语将如何长期陷“理学”于不利的境地。
吴宓在学成归国以前,已强烈地感受到了国内的气氛,自觉未归之时国内时局已无可挽回。[7](P91)由于家庭背景和所受教育的关系,吴宓始终自觉坚持文化守成主义的立场,并主动站到了当时席卷国内的“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早有回国与“势焰熏天”“炙手可热”的“胡适、陈独秀之伦”鏖战一番的想法。[7](P144)同时就吴宓的个人气质而言,他又有着强烈的浪漫主义的、诗人的气质,当他认为自己已经“洞见”到了回国后将面临的种种“苦恼磨折”和黑暗的前途,心中无比的郁激与愤懑,并且在这种长期的心理压力之下多次想到自杀,甚至还有一次自杀未遂。[7](P154~155)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当吴宓突然在1921年5月中旬接到梅光迪的“快函”急召回国“发展理想事业”,吴宓仅“略一沉思”,便即同意到东南大学就聘,并于同年6月中开始办理回国手续,[8](P214~215)真可谓迫不及待、归心似箭。
但吴宓归国后面临的形势,正如他在美国求学期间所预见到的,“新文化运动”已经走向了辉煌胜利的尾声,任何“新文化”的反对者在这时都已无力回天。吴宓回国创办《学衡》(1922年1月~1933年7月)一年之后,中国传统主义者和唯科学主义者之间长期的分歧与论争日趋激化,终于在1923年以“科玄”大论战的形式一举爆发,这也是“科学”最终确立在中国“至高无上之地位”的“决胜之战”。以丁文江为代表的唯科学主义者们坚持科学与人生观不可或分、精神科学与物质科学并无分别;而以张君劢为代表的传统主义者则认为,人生哲学属于内在世界的“我”所要解决的问题,“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5](“人生观”P9)一方坚持科学进步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一方则强调关乎人之内心生活的人生哲学问题非科学所能为力,——这场论战套用白璧德经常使用的术语来说,实质上代表了“物之律”与“人之律”之间的斗争,而前者可以说对后者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学衡派”人士虽然并未加入战团,但《学衡》对此并非完全没有反应,如缪凤林在1924年2月第26期《学衡》的“阐性(从孟荀之唯识)”一文中,以“唯识论”对质“西洋哲学科学所有之因果论”,认为后者“误以增上缘为因缘者。则至是悉破其壁垒。且永不能复行建设”,文末忽然谈到:
“曩有争辨玄学与科学者。主科学之士。咸主因果。谓心理现象之起。必有其因。此诠因果二字。诚属无误。惟其所以说明之者。仍不外一“刺击与反应”S-R之公式。……乃彼犹欣然自得曰。此西洋博士之实验也。差足尽人世问学之能事。”
这自然是对着“科玄之争”而发的感慨。
唯科学主义者们的论争姿态则要激烈得多:当梁启超认为人生大部分问题应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然而有一小部分(或还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超科学的,——甚至这种与其它偏激观点相比不失公允的意见也被陈独秀毫不留情地斥为“骑墙态度”,[5](“陈序”P7~8)我们从中赫然可以见出“科学”或任何一种话语被意识形态化为口号之后所具有的可怕力量。以梁启超在学界分位之尊,影响之大,温和地提出相对执中的意见尚且立刻会遭到批判,其他人之噤若寒蝉也就可想而知。同时,胡适在自己的序言中也大力渲染“科学”具有“无上尊严的地位”,并提出自己所理解的“科学的人生观”就是“自然主义的人生观”,[5](“胡序”P25~29)这样一来,在这场论战中不但“物之律”战胜了“人之律”,并且“自然主义”——白璧德终生的大敌,(注:白璧德终生以批判“自然主义”为职志,他在多部著作中都曾痛陈自然主义之害,如:“人类各种才能之间所形成的人文平衡会受到两种极端趋势相同程度的破坏:一方面是过度的自然主义,另一方面则是过度的超自然主义。”以及“当人被自然主义的气质所左右、而又过分受到权力和成就的吸引,他就会如爱默生所云,遭到“废黜”(unkinged)”等等,见Irving Babbitt,Literature and American College-Essaysin Defense of the Humanities,第28、29页。)也借重了“科学”的辉光在中国“得势”当时。
吴宓对此自然不会全无感触。他在“高上意志及卑下意志之对峙。”一句下面作了“以理治欲”的批注,此时正值“赛先生”在“科玄之争”中大获全胜之后。现在看来,这寥寥数字的批注里蕴含了多少言外之意!要知道,白璧德学说分明与先秦儒学“甚通”,在当时对“玄学鬼”的一片谩骂声中,在上述二者之间相互阐发或许是更为明智的做法,而吴宓却一定要使用理学家的套话来激发人们对“新人文主义”和宋明理学之间的联想,——这在当时的情况下,简直无异于“顶风作案”。在时人眼中,以《学衡》宣扬白璧德学说的宗旨来看,此时将白璧德学说解释为已在国内恶名昭著的“以理制欲”论,可以说是完全缺乏宜传策略的。并且在“科玄之争”胜负已判、尘埃落定之时,再无关痛痒地发出微弱的反抗之声,自然是“慢了半拍”,这不但于事无补,还徒显得是在争戴一顶人人避之惟恐不及的“玄学鬼”的帽子。事实上,吴宓此番苦心为多数同学好友所不解,例如当年意气勃发、宣称“定必与若辈(指胡适与陈独秀)鏖战一番”的张鑫海,回国后转而成了与胡适过从甚密的朋友,认为吴宓办《学衡》是“吃力不讨好,不如不办”,[9](P28)甚至当《学衡》面临停办,吴宓为之奔走至陈寅恪处,陈寅恪也直言不讳地说“《学衡》无影响于社会,理当停办”;面对一生经营之事业终将被毁的厄运,吴宓是夜不能成寐、“怅念身世,感愤百端”。[9](P251)
三、立足于“我”的独特心态
然而,吴宓的行为,绝非“昧于实事”可以解说穷尽。在当时极端不利的处境下,那确乎是“幼稚”,是“不合时宜”,但更是一个勇于担当的知识分子的良心。首先,吴宓可以说很早就对宋明理学深具同情,而他对理学最初的同情与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导师与挚友的影响:首先,白璧德盛赞中国儒家文化,且对朱子有着极高的评价,这必然会对“在哈佛数年仅限于研读白璧德和穆尔的著作”的吴宓产生一定的影响;[10](P82)同时吴宓的好友陈寅恪亦曾多与倾谈对中国儒家哲学、佛学的见解,特别是对融合二者之义理的程朱理学体会极深,吴宓曾在1919年12月14日的日记(见《吴宓日记》Ⅱ)中不惜笔墨全篇详录陈寅恪的谈话云:
“佛教于性理之学Metaphysics,独有深造,……宋儒若程若朱,皆深通佛教者。……采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佛之义理,已浸渍儒染,于儒教之宗传,合而为一。此先儒爱国济世之苦心,至可尊敬而曲谅之者也。……故宋、元之学问、文艺均大盛,而以朱子集其大成。朱子之在中国,犹西洋中世之Thomas Aquinas,其功至不可没。而今人以宋、元为衰世,学术文章,卑劣不足道者,则实大误也。……程、朱者,正即西国历来耶教之正宗,主以理制欲,主克己修省,与人为善。”等等。
虽然吴宓对理学的理解应不仅限于耳学陈氏,但从这些大段的引文可以看出,陈寅恪的见解应该给他带来了不小的触动。(注:吴宓目陈寅恪为人中之“龙”,在日记中曾多次不遗余力地盛赞这位朋友,且经常大段记录陈寅恪的谈话,如1919年3月26日、4月25日以及12月14日诸日记,(均见于《吴宓日记》Ⅱ),可以想见陈寅恪会对吴宓某些思想的形成产生不小的影响。)从这些线索可以知道,吴宓自然会认为当时国内对理学的批评有失公正。他的这种心态在《学衡》中早有显露,如他在1922年4月(即“科玄之争”爆发之前)第四期《学衡》“论新文化运动”一文中就已经在为宋明理学的“以理制欲”说进行辩护了:
“道德之本为忠恕。所以教人以理制欲。正其言。端其行。俾百事各有轨辙。社会得以维持。此亦极美之事也。以上乃宗教道德之根本之内律也。一定而不变。各教各国皆同也。当尊之爱之。而不当攻之非之者也。”
而在1923年4月第16期《学衡》发表的“我之人生观”一文,可以说是吴宓针对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亮出了自己的立场——虽然他采取的是远离论争中心的一种非论辩式的态度:
“主张人性二元者。以为人之心性Soul常分二部。其上者曰理。又曰天理Reason。其下者曰欲。又曰人欲Impulses or Desire。二者常相争持。无时或息。……欲常思行事。而理则制止之。阻抑之。故欲(重点号为笔者所加,“欲”字显系“理”字之误。)又称为Inner Check或Will to Refrain。……理所以制欲者也。……人能以理制欲。即谓之能克己。而有坚强之意志。不能以理制欲。则意志毫无。……人之所以异於禽兽者几希。所谓几希者。即心性中之理也。即以理制欲之「可能性」也。……盖即上节所言以理制欲之工夫也。能以理制欲者。即为能克己。故克己又为实践凡百道德之第一步矣。……能常以理制欲。则能勤於省察而见事明了。”
“以理制欲”在吴宓这篇文章里,简直成了一关键词。甚至就在他刚作了“以理制欲”之夹批的同一段落中,再次不失时机地为“今夫人之放纵意志(即物性意志)与抑制意志(即人性意志)常相争战。”一句加注曰“前者即吾国先儒之所谓理。后者即其所谓欲”,他对“以理制欲”说的强调已经是无以复加,真可谓用心良苦。
吴宓对“以理制欲”概念的反复申辩与陈说,决非单纯学理上的论辩,而实际上是与他的救国热忱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忧国忧民,以天下事为己任,这可以说是五四学人的普遍心态,引入西学,其目的乃是为“我”所用,正如有些研究者认为:“学衡派受新人文主义的影响,其表现与其说是一种内容上的接受,毋宁说是一种思想上的认同。”[10](P73)吴宓等人奉白璧德之“新人文主义”学说为圭臬,无非是要借重来自西方的声音来增援国内日渐失势的旧有传统价值体系。在吴宓等人看来,那些学习工程、实业的留学生不过是学了一些末技,环境稍有改变,便“不复能用”,唯有“天理人事之学”是历久不变的,从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行而上之学)为根基”。[7](P101)因此“科玄之争”中对“玄学”的批判,在吴宓眼中,无异于是在动摇“救国经世”之本!
这样看来,与其说吴宓是在力图宣扬“新人文主义”而不得其法,是以不免“昧于时事”之讥,毋宁说吴宓是在为捍卫国内大受批判的宋明理学而孤军奋战、知其不可而为之。为了支持当时在国内大遭批判的“形而上之学”,吴宓借重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作为一种权威理论资源,转来佐证宋代理学的合理性,指出“以理制欲”通于“高上意志及卑下意志之对峙”这一新人文主核心概念,这可以说正是“六经注我”的典型做法。也就是说,一般看来吴宓是在用“以理制欲”阐释白璧德的“高上之意志与卑下意志之对峙”概念,但实际上却是吴宓发挥白璧德理论的核心概念进一步阐发了“以理制欲”之说!事实上,吴宓从来都是在运用“内在制约”等概念来扩充“以理制欲”说的内涵,而从未确指过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理论的实质就是“以理制欲”。由此可见,即使是一个小小的注解,也须结合注者吴宓所处的时代背景与其特殊的心态来加以理解,否则人们就会看不到其中微妙的差别,也就很容易会造成上文所述的那种误解。
四、当代中国对“新人文主义”的误读
关于当代中国对“新人文主义”的误读,我们不乏相关的例证。如1993年出版的《历史汇流中的抉择——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家与西方文艺理论》一书认为:
“天理人欲论与白璧德的善恶二元论,在程度上或有差别,各自的思想背景也不同,但其理论实质是十分接近的。它们都力图把特定社会的道德要求,行为规范凝聚转化为某种普遍必然的‘理性’或‘天理’,用以扼杀人的感性存在和自然欲求,并通过这种理性对人欲的压抑,来实施和加强社会对个人的控制。”[11](P165~170)
书中还认为,梁实秋与白璧德一样,也强调“以理性节制情欲”,从而“梁实秋文艺思想的真正核心,应该说是理性与理性制裁,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以理制欲的人性论”,书中还提到林语堂“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二者的相似”,并引用林氏的话说“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与通常所谓Humanism,文艺复兴时代的新文化运动不同,他的Humanism是一方与宗教相对,一方与自然主义相对,颇似宋朝的理性哲学”[11](P165~170)(着重号为笔者所加,按林语堂在《新的文评·序言》中原文为“性理哲学”)。[12](P2)
《抉择》一书似乎已认定梁实秋的“以理性克制欲望”的阐释是符合白璧德之原义的,且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之主旨即是“以理制欲”。但首先梁实秋本人的阐释并不符合白璧德的原义。(注:不过,并不能说梁实秋错误理解了白璧德的思想,而毋宁说他是根据时代需要而对“新人文主义”作出了自己的解读,关于此节国内学者多有论述。)虽然白璧德确实强调“理性”之于“冲动”或“欲望”的制约作用,(注:例如他指出,人身上有一能够施加控制的“自我”,还有一需要被控制的“自我”,并引用西塞罗的话说,人类心灵的自然构成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欲望”,希腊人称为“冲动”,另一部分是“理性”,“理性”适合智慧,“欲望”只能服从。见Irving Babbitt,On Being Creative-And Other Essays.London:Constable And Company LTD,1932,"Introduction",第xiv-xv页。)但他还进一步强调,适度的法则乃是人生最高的法则,希腊作为人文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其文明却由于“过度”,即理性怀疑主义的出现而遭受到了巨大的痛苦。[13](P23~25)也就是说,“新人文主义”尽管并不否认“理性”的作用,却认为“理性”如果走向极端、发展成为“理性主义”(rationalism),则根本是无法制约“欲望”的;(注:如1925年2月第38期《学衡》“白璧德论欧亚两洲文化”一文中说:“彼希腊人。甫推翻古来礼教之标准。即不能把持。而下堕於理智主义之渊。无分其为斯多噶派或伊壁鸠鲁派。要之。理智主义决不能管束人心中纵放之情欲也”。按:吴宓在此将“rationalism”(英文原文见Irving Babbitt,Democracy and Leadership,第173-174页)一词译作了“理智主义”,实为“理性主义”。一般而言,“理智主义”的对应英文词应是“intellectualism”。)甚至过分的“理智”(Intellect)也会堕落成一种“欲望”——知识之欲,因此“理智”亦应受到“意志”之制约。(注:“白璧德论欧亚两洲文化”一文中说:“彼东西之大宗教家。力主凡人应当屈服於高上意志者。岂欺我哉。尤要者。则当以理智受高上意志之管束。盖理智之放纵(libido sciendi知识之欲)实为根本上之祸患”。又1931年3月第74期《学衡》“白璧德论班达与法国思想”一文引述“巴斯喀尔”(Pascal)(今译帕斯卡尔)的观点,将人之欲望分为三种:“信仰为更高之意志、所以严制自然人之三欲。何谓三欲。(一)智识欲(二)感情欲(三)权力欲是也。”)所以,“高上意志”对“卑下意志”的“内在控制”并不能完全阐释为“以理性克制欲望”。事实上,西方研究者们甚至普遍认为“新人文主义”最薄弱的部分就是理性概念,例如,在美国学者克莱斯·瑞恩(Claes G.Ryn)看来,白璧德不是在理智、而是在意志中发现了最高的道德权威,且强调实在的“实践标准”的终极性,这显然相对轻视了理性的作用,因为,如果人与实在最重要的关联不是理性、而是无须中介的直接的生活经验,那么“内在制约”实际上就成了一种“强行插入人的意识”的“超验的善”,从而白璧德事实上是将“实在”着落在了非理性的基础上,这在某种意义上便构成了“新人文主义”立论基础本身的内在缺陷。[14](P81~109)
此外,我们知道,信奉“中道”的“新人文主义”不会主张“扼杀人的感性存在和自然欲求”,亦不会主张“理性对人欲的压抑”,同时就其“内在制约”的主旨来看,恐怕还会特别反对“实施和加强社会对个人的控制”,因为,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强调的是“个体的完善”与个人的“内在生活”(innerlife),与社会维度相比,它更着重于个体之维度,(注: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反对“托名之个人主义”(即通常意义上的个人主义),特别是反对那种拒绝一切社会约束与纪律的卢梭式的个人主义,而主张一种“坚守其内心生活之真理”的“真正之个人主义”,或“真正完美之个人主义”,(1923年7月第19期《学衡》“白璧德之人文主义”一文);白璧德还强调“今日世局转移升沈之枢纽。……实视真正之个人主义者与彼托名之个人主义者相争之胜败如何耳。吾以为真正之个人主义者。必能坚守其内心生活之真理。诚如是。则虽尽反前古之成说。亦在所不顾者矣”,见“白璧德论民治与领袖”一文。以往研究者多侧重白璧德对卢梭式个人主义的批判,而往往忽略白璧德对“更彻底之个人主义”的要求,因而会人为地造成一种误解,认为白璧德彻底反对不受任何社会约束之个人主义,因此或会转而强调“实施和加强社会对个人的控制”。)它认为“善与恶之间的斗争,首先不是存在与社会,而是存在与个人”,[15](P251)“在人文主义者的眼中,对于人来说,重要的不是他作用于世界的力量,而是他作用于自己的力量”,[13](P56)“个体的完善”就是要依靠这种“作用于自己的力量”,而非外在的律法与约束,通过个人之“意志”而达于“内在制约”来赢得“洞穴中的内战”(civil war in the cave)的。
无独有偶,1998年出版的《现代文学与现代性》一书在讨论“新人文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得到响应和产生影响”的原因时也说:
“不仅因为中国现代的一场浪漫主义有待清理,而且因为它和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正相契合,特别是宋代新儒家理欲的划分以及对理的强调和新人文主义‘人性二元’的观点与对理性的推崇是相通的。”[16](P237~238)
虽然“相通”的说法比较模糊,并没有坐实“新人文主义”就是等同于“以理制欲”的,但其中仍可窥见因袭前人的痕迹。
这样看来,如果不加分析地接受前人的成说,“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乃是‘以理制欲’的”就会成为一种定论!新时期研究者们往往倾向于忽视对上一代学者之不同心态的研究,这部分由于我们已知的“新人文主义”阐释历史的长期断裂,另外,对于现在阐发西学心态已相对平和的新时期学者来说,可能不能充分理解与同情五四学人在治学研究的背后所蕴含着的那种深切的忧患之思。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应该深入地体悟前辈学者的特殊心态与当时的时代氛围。因为,同样是东西互阐,如果心态不同,立足点不同,结果就会有很大的区别,而这一区别,如没有加以足够的重视,则终不免会导致谬误流传。80年前吴宓的那番苦心,当时固然几乎无人理解,而在80年后的今天,人们却多是吴宓“忠实的叛逆”,他们顺理成章地将“新人文主义”之“内在制约”的核心概念坐实为“以理制欲”,从而彻底误解了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学说的真义、也彻底误解了吴宓在文中批注“以理制欲”的真实用意。不论是《学衡》时代后期“新人文主义”更有力的阐释者梁实秋,还是同时期作为《学衡》反对者之一的林语堂,他们或根据时代需要作出自己的“理性克制欲望”的阐释,或根据个人好恶、“别有用心”地继续发挥吴宓的说法,他们都显示出完全清楚自己是在什么层面上说话的,而新时期研究者们却隔着历史的迷雾、通过与上一代研究者的“共谋”,构成了对“新人文主义”所谓之“误读”的误读,——这一历史的反讽难道还不足以令我们深思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