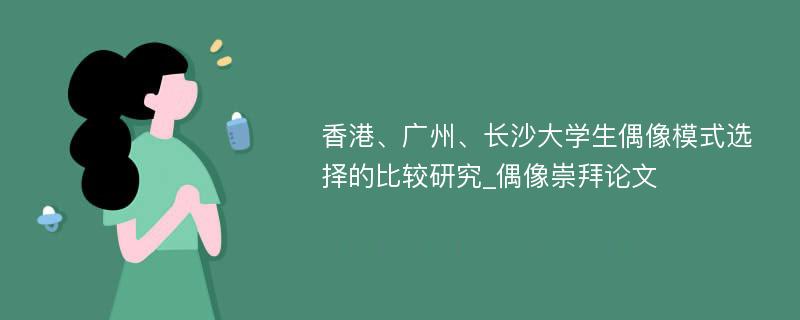
香港、广州、长沙大学生偶像与榜样选择之比较调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沙论文,香港论文,广州论文,榜样论文,偶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青少年偶像与榜样的概念差异
据世界不同地区的调查表明,歌星、影星和体育明星占据了当今年轻人偶像崇拜的主体。许多青少年人把这类人物当作自己的“绝对英雄”,并对他们产生某种浪漫式依恋或认同式依恋。这两种认同一方面可补偿青少年个体化过程中因脱离对父母的依赖而产生的情感真空,另一方面也可促使青少年对其偶像人物想入非非,做出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在这层意义上讲,偶像崇拜可谓个人对其特别钦佩人物的社会认同和情感依恋。弗洛姆(1967)认为偶像崇拜是对幻想中杰出人物的依恋,但这种幻想常被过分的强化或理想化了。艾里克森(1968)也认为偶像崇拜是青少年将对父母的养育式依恋移情到对生命中重要人物的认同和依恋来肯定自我的存在价值(Josselson,1991)。 青少年从自我的迷茫状态中走出来,往往需要通过对一些成年或同龄人中偶像人物的认同来实现其自我确认(Marcia,1980)。
作为偶像的近义词,榜样也可对青少年成长产生深远的影响。榜样可作为一个可靠的基础来推动青少年对自我的探索和认识。社会学习理论强调模仿和榜样学习在帮助人们获得适当社会技巧的重要性。许多研究表明,当儿童认同适合的社会角色时,榜样的积极作用就得到了增强。由此,偶像与榜样,同样可以激励青少年的自我成长,也同样可以填补青少年个体化过程中出现的情感空虚。但在什么条件下,一个令青少年特别钦佩的人物会成为其偶像,而不仅是其榜样?此外,偶像与榜样对青少年的成长各起什么不同的作用?对于这些问题,尚缺乏学者予以深入系统的研究。
为区分青少年偶像崇拜和榜样学习的差别,笔者提出:偶像和榜样之间存在着一种理想化与现实化、浪漫化与理性化、绝对化与相对化的对立关系(Yue & Cheung,1998)。即,偶像一般是个相当理想化、完美化、非凡化和浪漫化的人物形象,而榜样则一般是个相当现实化、世俗化、功利化和平凡化的人物形象。这三组对立概念构成了一个六边形模型,直观地表现了偶像和榜样之间的差异。
为验证这一模式,笔者设计了一项调查问卷以测量青少年选择偶像和榜样的标准(Yue & Cheung,1998)。答卷形式是Likert量表,其中5表示一致性最高,1表示一致性最低。此外,问卷还要求被试分别举出三个最喜欢的偶像的榜样人物。笔者共调查了826 名香港和南京地区的高中生和大学生。结果表明,在青少年之偶像崇拜和榜样学习当中,确实存在着理想化与现实化、浪漫化与理性化、绝对化与相对化之间的对比差异,其中理想化与现实化、浪漫化与理性化之差异更具统计显著性。
结果还显示,在当今社会中,那些令青少年崇拜的偶像多是理想、浪漫、绝对型人物,如著名的歌星、影星和体坛明星等。他们可给青少年带来无穷的浪漫幻想和虚荣满足,甚至令青少年神化其存在价值,沉湎于其追逐当中。相比之下,那些值得青少年敬佩的榜样多是为现实—理性—相对型人物,如著名的科学家、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军事家、企业家等及自己身边的突出人物。他们可促使青少年有选择地认同其存在价值,进而激励自我的成长。此外,香港地区的青少年比南京地区的青少年更崇拜理想—浪漫—绝对型名人。例如,香港中学生中86%的人选及香港大学生中74%的人选,选择的偶像是理想—浪漫—绝对型名人。相比之下,南京中学生中有61%的人选及南京大学生中22%的人选,选择的偶像是理想—浪漫—绝对型名人。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地域性差异可归因于香港地区明星文化的巨大商业包装及内地教育与宣传部门对公众人物的一定的引导作用。
总之,上述之理论构架及研究结果对区分青少年偶像崇拜和榜样学习的差异具有一定指导意义。但它尚不能有效地测量青少年偶像和榜样认同上的差异,也不能完全解答偶像与榜样之间的互动关系。为解答这一问题,笔者设计了本次研究,它有两个目的:(1 )测量青少年对偶像与榜样崇拜程度上的差异,(2 )比较香港与内地青少年对偶像与榜样人物选择上的差异。为有效地鉴别青少年偶像与榜样选择上的差异,本研究提出偶像度和榜样度两个概念,其中前者指青少年对其钦佩人物的偶像崇拜程度,后者指青少年对其钦佩人物的榜样学习程度。
研究方法
1.被试
共有456名大学生参与了本项研究,其中包括138 名香港大学生, 165名广州大学生和153名长沙大学生。在香港大学生中,男性占29.6%,女性占70.4%,平均年龄为20.55岁;在广州大学生中,男性占29.2%,女性占 70.8%,平均年龄为19.61%;在长沙大学生中,男性占31.9%,女性占68.1%,平均年龄为20.40岁。选择这三地的大学生, 是为了有效地体现中国大陆的地域差异,其中香港代表较为西方化和商业化的地区,广州代表沿海开放地区,而长沙则代表较为传统的内陆地区。
2.测量方法
本研究使用的问卷是特别设计的,这首先要求被试填写出三名自己所十分钦佩的人物,并就每个人可成为自己偶像和榜样的程度评分。评分度为1至10,其中1分表示程度最低,10分表示程度最高。此外,为进一步了解被试怎样认同这些人物,问卷还要求被试具体指出其提名钦佩人物的突出方面或特质。
香港、广州、长沙大学生钦佩人物比较
1.三地大学生提名钦佩人物之类型比较
香港大学生所提名的理想—浪漫—绝对型名人之比例(34.3%)明显高过广州大学生(12.2%)和长沙大学生(12.2%)的提名比例。与此相反,广州和长沙大学生所提名的现实—理性—相对型名人之比例(广州:74.4%;长沙:70.4%)明显高过香港大学生的提名比例(33.7%)。这些结果与笔者上次的调查结果相当一致(Yue & Cheung,1998;Chueng & Yue,1999)。
对于名人之偶像度和榜样度之比较,香港和广州大学生对理想—浪漫—绝对型人物的偶像度明显高于榜样度。相反,香港、广州和长沙大学生对现实—理性—相对型人物的榜样度又明显高于偶像度。而对于非名人之偶像度和榜样度比较,三地对所钦佩人物的榜样度均高于偶像度。另外,广州和长沙的大学生分别选取了86.6%及82.6%的社会名人作为其钦佩对象,而香港的大学生只选取了68.0%的社会名人作为其钦佩对象。相比之下,香港大学生选取了近27%非名人作为其钦佩对象,而广州和长沙的大学生只选取了10.9%和14.1%的非名人作为其钦佩对象。这似乎表明,内地的大学生更认同社会名人作为自己成长的偶像或榜样。
2.三地大学生提名钦佩人物之前十名类型比较
香港、广州和长沙三地大学生提名钦佩人物的前10名人选中,三地共同提名的人是:父亲、母亲、邓小平、朱镕基、老师;广州、长沙两地共同提名的人选是:周恩来、毛泽东、比尔·盖茨、吴仪;香港一地提名的人选是:王菲、孙中山、黎明、佐敦、陈方安生。另有广州的大学生还提有居里夫人(2.3%); 长沙的大学生还提有鲁迅(2.3%)。比较其结果,可注意到以下几条有趣的发现。
(1)广州和长沙大学生提名之钦佩人物十分相近, 却与香港大学生之提名人物相差甚远。广州和长沙大学生所提名的钦佩人物几乎雷同,其中九人的提名相互重叠,只有一人提名不相一致。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所有提名人均属现实—理性—相对型名人。相比之下,香港大学生所提名的钦佩人物就有很大差异,其中除了有现实—理性—相对型人物外,也不乏有理想—浪漫—绝对型名人。
(2)广州和长沙大学生提名之钦佩人物以政治名人为首选, 香港大学生提名之钦佩人物以父母师长为首选。具体地说,广州与长沙大学生所提前十名钦佩人物中80%的比例为政治名人所占据,包括周恩来、邓小平、毛泽东、朱镕基等人。其中周恩来的比分最高,超过了所有其他政治名人所占比例的总和。广州大学生首选的四位钦佩人物依次为周恩来(22.0%)、邓小平(7.1%)、比尔·盖茨(6.1%)和朱镕基(5.6%); 长沙大学生所首选的四位钦佩人物依次为周恩来(15.2%)、朱镕基(7.6%)、毛泽东(6.9%)和邓小平(4.2%)。相比之下,香港大学生提名钦佩人物中, 父母亲占据了前两名,其和积占前十名总和的44.6%。香港大学生首选的四位钦佩人物依次为母亲(9.4%)、父亲(8.1%)、王菲(3.2 %)和孙中山( 2.9%)。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广州和长沙大学生的提名中,父母亲也名位列第5、6位,而如果将父母亲的比例加起来,其列位可提到第2位(仅次于周恩来)。
(3)广州和长沙大学生提名之钦佩人物以科学、 文学名人为辅,香港大学生提名之钦佩人以演艺界名人为辅。除政治名人、父母亲和教师外,广州和长沙大学生所首提钦佩人物中还包括了像居里夫人、比尔·盖茨和鲁迅这样的科学家和文学家,共占两地大学生前十名提名比例的8.4%(广州大学生)和8.8%(长沙大学生)。而香港大学生的提名中则包括了像黎明、王菲、乔丹这样的演艺界和体坛名人,共占前十名比例和积的22.6%。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和朱镕基是唯一被三地大学生首选提名的中国名人,比尔·盖茨是唯一被两地大学生(广州和长沙)首选提名的外国名人。
总之,香港青少年对钦佩人物的选择与内地青少年有明显不同,他们更看重理想——浪漫——绝对型名人,而内地青少年则更看重现实——理性——相对型名人。此外,香港的青少年较内地的青少年更看重父母师长对他们的影响。
3.三地大学生提名钦佩人物之前十名偶像度与榜样度比较
调查对三地大学生所提名前十名钦佩人物之偶像度和榜样度进行了比较。其中下列发现值得特别注意。
(1)三地大学生对非名人的榜样度明显高于偶像度。具体地说, 在三地大学生所提前十名钦佩人物中,父母亲和教师皆为非名人。每位提名者的偶像度和榜样度比较显示,偶像度的平均值都低于榜样度,且这些差异大多具有统计显著性。这表明,三地的大学生主要将自己的父母和教师当作榜样来看待,而非将他们当偶像看。
(2)对所提理想—浪漫—绝对型名人的偶像度都高于钦佩度。 具体地说,香港大学生所提的三位理想—浪漫—绝对型名人(黎明、王菲、乔丹)中,其偶像度的平均值均高过榜样度的平均值,且这些差异都具有统计显著性(乔丹除外)。这表明,香港大学生将这些人物视作偶像,而非榜样。
(3 )三地大学生提名之现实—理性—相对型名人的榜样度一般都高于偶像度。对于政治名人的两度比较,除香港和广州的大学生对周恩来、邓小平和孙中山三人的偶像度略高于榜样度外,其他政治人物的比较均显出这一特点。这些结果表明,三地的大学生基本将现实—理性—相对型名人当作榜样来看待。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名人身上,还是在非名人身上,被提钦佩人物之偶像度和榜样度评分上大多不相关联。它表明,偶像和榜样是两个相互独立和分割的概念,它们在被试心目中带有不同的含义。这一结果验证了偶像和榜样之间的差异。
青少年偶像和榜样之选择:两种维度区分的意义与四种偶像和榜样人物的划分
本项研究之意义,除了展示了香港与广州和长沙大学生在偶像和榜样选择上的巨大区域差异外,还可从下面两个方面来加以探讨。
1.区分偶像度和榜样度的意义
本研究表明,在测量青少年之偶像与榜样选择时,划分偶像度和榜样度可有效地鉴别青少年对其崇拜人物的程度差异。数据分析显示,在排除了整体评分倾向之后,偶像度与榜样度之间的相关数只是0.048,这是极低的数值,说明两者各不相关。此外,偶像度及榜样度,在应用于各类人物时,均有显著的分别。
偶像度和榜样度各具有预测效度,其证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在测量对名人的钦佩程度时, 偶像度在测量被试对理想—浪漫—绝对型名人的钦佩程度时较榜样度更适用、更明显,而榜样度则在测量被试对现实—理性—相对型名人的钦佩程度时较偶像度更适用、更明显;(2)在测量对非名人的钦佩程度时,榜样度较偶像度更适用、 更突出。
由此,本研究的数据充分显示了区分偶像度和榜样度的有效性,包括其判别效度和预测效度。其中判别效度指偶像度和榜样度是截然不同的概念,而有其独立的特征。而预测效度指不同类别的钦佩人物均能产生或预测出不同的偶像度和榜样度。所以,偶像度和榜样度皆具判别效度。它们应用于不同人身上有着明显的差异。
2.四种偶像和榜样人物的划分
根据上述之分析,笔者还认为,偶像与榜样人物可依青少年对其崇拜程度的不同而大抵分为四类:纯偶像、榜样型偶像、偶像型榜样和纯榜样。
(1)纯偶像
纯偶像通常包括那些理想—浪漫—绝对型名人,如香港的四大天王、王菲、梅艳芳、梁咏琪之类的歌星,美国的麦克·杰克逊、麦当娜等人物。作为偶像人物,他们可给青少年的精神世界带来极大的向往、幻想和虚荣满足(Cheung & Yue,1998),但也可使某些青少年沉湎于对这些明星的追逐和依恋当中。事实上,纯偶像的出现是与当今明星人物的巨大商业包装和推销密切相关的,其包装形象往往完美于其真实形象。
(2)榜样型偶像
榜样型偶像通常包括那些现实—理性—相对型名人,如像周恩来、毛泽东、邓小平、牛顿、爱因斯坦、达·芬奇、李嘉诚、鲁迅之类的著名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企业家和公众模范人物等。作为偶像人物,他们只是为社会所熟知的成功或杰出人士,通常不会给青少年带来浪漫化或理想化的幻想,而是促进青少年的志向确立和自我奋斗。较之纯偶像,他们多不需要刻意的商业包装和宣传,而是以其特殊的气质和成就来感召他人。
(3)偶像型榜样
偶像型榜样通常包括那些具有一定名人气质和影响力的非名人,如那些深受青少年喜爱和尊重的同窗相好、长辈朋友等。作为榜样人物,他们虽然不具有社会名人的名气和感召力,却胜在贴近青少年,可随时给他们提供帮助和指导,促进其个性成长。而作为非名人,他们最大的特点是就生活在青少年身边,可与之直接交流思想。而在青少年心目当中,他们可能是真正的人生偶像和动力源泉,但其实际价值也可能被夸大、神化甚至浪漫化。
(4)纯榜样
纯榜样通常包括青少年身边的人物,如父母师长、兄弟姐妹、同窗好友、邻居街坊等人物。作为榜样人物,他们可能平凡无比,与青少年相差无多,但他们却能在生活的具体方面实实在在地引导青少年成长,并赢得他们的尊重和信任。事实上,在本研究中,无论是香港的大学生还是内地的大学生,都将父母师长摆在最受钦佩人物之列,这绝非偶然。它说明,纯榜样人物对青少年的成长仍起重大作用。
3.划分四种偶像和榜样人物的意义
划分上述四类偶像和榜样人物,不但可以使我们进一步区分偶像和榜样之间的概念差异,也可使我们更好地了解青少年偶像和榜样选择中的广泛空间,以促使我们更好地帮助他们选择、认同其生活中的关键人物。在这层意义上讲,本划分的意义在于使人们认识到:偶像和榜样不是截然划分的,他们之间存在着一个极为广泛的缓冲区域,若能使青少年看到这一步,则其生活中值得敬佩和认同的人物将会大大增加。事实上,就本研究之统计分析而言,香港和广州的大学生在评价其父母和同学/朋友的偶像度与榜样度时,评分都十分接近,其差异均无统计显著性。这似乎表明,这两地的大学生在提名其父母和同学/朋友为钦佩人物时,似乎把他们既当榜样看,也当偶像看。
事实上,一般成年人的偶像和榜样结构,颇有似于一个底大顶小的金字塔:最底层为生活中形形色色的纯榜样人物,他们大多是平凡之人,却以其某些非凡之处而令人敬佩;上一层是相当数目的偶像型榜样人物,他们也是凡人,却具有某些特殊的气质和精神令人敬佩;再上一层是一定数目的榜样型偶像人物,他们是社会名人,多以其特殊的气质和成就来感召他人;最顶层是少数纯偶像人物,他们具有非凡的气质和魅力,可深深地影响他人的一生。
这个金字塔结构突出表现了人们可以从各种人身中吸取生活的智慧和动力,而非要定位于某几个突出人物身上的特点。此可谓“人人为我师,我为人人师”之理。但在青少年时期,由于他们渴望个性的独立及情感替代人物的出现,他们往往过分关注少数纯偶像人物的言行举止,视他们为自己的“绝对英雄”和精神支柱。这种光环效应的结果,可导致部分青少年无限夸大少数“看得见,摸不着”之明星人物对自己的影响,而大大忽略那些对自我成长起直接指导作用之身边人物的作用。它使偶像人物的影响力大大超过其实际存在,也使榜样人物的实际存在远远不能与其影响相匹配。由此,划分四类偶像和榜样人物,也可使我们更好地认清青少年偶像崇拜中所存在的误区。
结束语
本研究根据以往调查的结果,就如何测量青少年偶像和榜样崇拜的差异提出对比偶像度和榜样度的概念,并假设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互为排斥的反比关系。通过对一批香港、广州和长沙的大学生对其生活中钦佩人物的态度调查,本研究表明,偶像度和榜样度之间的确存在着一种反比的关系,从而进一步验证了笔者早先提出的关于青少年偶像和榜样之间存在的六边型模式关系。此外,本文还提出,依据青少年对其崇拜对象的认知程度不同,可将其崇拜的偶像和榜样分为纯偶像、榜样型偶像、偶像型榜样和纯榜样四种类型。他们可能对青少年的个性成长起着相当不同的影响,但可能因青少年时期的心理变化特点而出现某些畸形发展。
应当指出,本文中提出的概念和结论还都有待于进一步的实证检验。特别是对于比较偶像度和榜样度的作法,还需要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来加以验证其合理性。另外,什么心理或文化因素可导致偶像度和榜样度之间出现相关或不相关的情况,也有待于深入探讨。同时,在选择崇拜对象上,香港的青少年与广州和长沙的青少年表现出极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香港和内地青少年对于偶像人物认识和接受上的差异。这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最后,笔者强调,本研究中所提出的有关偶像和榜样崇拜的概念,都只局限于青少年领域,都是与青少年时期的年龄和心理特点紧密相关的。至于这些概念是否可以适用于成年人的偶像崇拜中,特别是其政治和宗教崇拜中,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调查来验证。由此,在某种意义上讲,本文引发的问题可能比其提出的问题更为重要。因为迄今为止,还很少有学者尝试去测量偶像或榜样崇拜程度上的差异,也还没有人去试图区分青少年偶像崇拜与其他形式的偶像崇拜之间的差异。所以,本文之价值正在于其抛砖引玉,引起人们对这类问题的思考和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