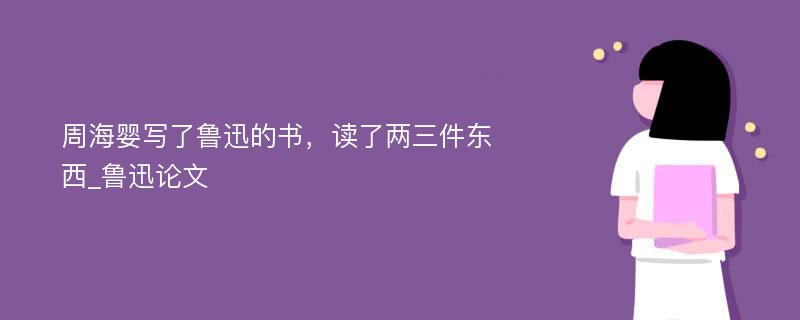
周海婴写鲁迅书读得二三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二三论文,读得论文,周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或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 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沽名获利之具。
——鲁迅《忆韦素园君》
鲁迅是一面镜子,可以从每个人对待鲁迅的态度中,照见其人的人格。
——诗人绿原如此说
鲁迅诞生120周年,周海婴的回忆录《鲁迅与我七十年》问世。儿子写父亲,是家人父 子之间平常生活的亲切纪录,对消除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那阵子将鲁迅给真正的造神运动 陪绑而肆意扭曲鲁迅形象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有益。由于那阵子居心叵测地“神化”鲁迅 ,将鲁迅扭曲为“左”的守护神的恶果,招来了一系列的情绪逆反和思想混乱;又正值 中国社会转轨的动荡时期,这恶果更和文化整合中的各种负势力交叉感染,干扰着人们 的理性选择。因此,如何对待鲁迅,就成了与如何对待文化同义。
问题不在于无知妄人对鲁迅的轻亵,如称鲁迅遗产为“鲁货”,斥鲁迅为“石头”, 以及“鲁迅见鬼去吧”之类的低能儿的叫嚣,这些并不能多大地伤害鲁迅;也不在于起 源于台湾和海外的文痞而为大陆别有用心的附和者恶意传播的造谣污蔑,如瞎说鲁迅如 不早死,抗战时期也会如乃弟周作人似地当汉奸之类的无耻谰言,那种显然敌视鲁迅的 谣言世家的鬼话也没有多少蛊惑人心的力量。将鲁迅给真正的造神运动陪绑却因为历史 的恶作剧而产生了深重的恶果。眼前看得到的最坏的影响有二:其一是,由于曾将鲁迅 钉定在“左”神的牌位上,误导人们将鲁迅视为和荼毒生灵的坏货是同伙,其逆反的结 果,就连带地将鲁迅战斗生涯中一切对人对事的正确判断都否定了,或大打其折扣。比 如,被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一文中评为“拉大旗作虎皮”的后来成 为文学权力中心人物的一伙,鲁迅对他们的评断,参照后来的史实一点也没错,且尚很 留余地;但因为此类人物后来被更“左”的造反好汉所超过,所黜落,人们因憎恶造反 好汉(好汉们确也利用鲁迅的言论打击这些原文学权力中心人物)而迁怒于鲁迅,而不顾 鲁迅原先的评论之无瑕可击。又更如,鲁迅曾无可指摘地批评过梁实秋、林语堂等人, 如果不抽空具体的历史语境,鲁迅是完全正确的;不管这些人以后的表现如何,他们在 被鲁迅批评时都处于负面位置。可是近二十年来,却有人故意吹扬这些人,或明讥鲁迅 为“偏激”或隐喻鲁迅欠高明,进行了一阵“软翻案”鼓噪。甚至连汉奸周作人,也被 捧出来以其“冲淡”来反形鲁迅的“偏执”和“激进”之不可取;更不说以胡适的“公 正和平,允执厥中”,推许为新文化的正宗,人文精神取向的典范,用以反衬鲁迅的“ 过激”为不可师法了。
(这里面也有对“左”的逆反情结。胡适应有胡适的地位,上世纪五十年代对他的“搞 臭”批判是非理性的,不公平的。但胡适的努力并未能溶入中国社会的基层,对动摇中 国社会的旧制度、旧意识、旧风习没有震撼性的力量,他的启蒙,总的说来是“外烁” 性质的。而鲁迅,真所谓是“民族魂”,是生发于民族内部的历史新觉醒的代表,和中 国社会的基层运动血肉相连的。鲁迅与胡适的根本区别在此。)
将鲁迅扭曲为“左”的守护神的恶果之二是,由于反感于“神化”鲁迅,人们努力要 把他拉回人间,这原不错;可是或由于矫枉过正(这样的成分很少),或出于市民的庸俗 趣味和某种阴暗心理,其中也不能排除原因多样的对鲁迅的蓄意抵制,拼命把鲁迅往庸 人堆里拉,使之市俗化即矮化。那办法就是去找一些市井小妇人最热中的东家长西家短 之类的萎琐事由,当作鲁迅“研究”的话题,就像小报的末流访员津津乐道歌星隐私、 影星婚变似地,将伟人扯淡在、淹没在庸俗无聊的口水涎沫之中。前些年台湾曾有谣言 世家编造鲁迅在早年留学日本时期醺酒狎妓等胡说八道,趣味十分低级;近年来国内也 有些人,“探索”肖红与鲁迅交往的“恋父情结”,也有“考证”鲁迅与许广平定情系 在哪年哪月何时何地的文字,据说是用弗罗伊德法或蔼理士法“研究”鲁迅的“新开拓 ”。因投合庸俗趣味,颇有市场。然而这种“开拓”不论花样多么新鲜,“考据”何等 确凿,都不啻“邻猫生子”,能给人带来什么效益?无非是提供点言不及义的无聊谈柄 ,有如鲁迅小说《肥皂》中四铭太太所说的“格支格支,不要脸”而已。通常人们为了 揭露某些头上有神圣光圈的伪君子,才追究其见不得人的隐私,还他们以言清行浊的丑 陋真相,以此来找鲁迅是找错了对象。即使本无恶意,也只如鲁迅在《题未定草·六》 中所说:“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点,画 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性交大师,那当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岂不冤哉 !”
鲁迅逝世以后,关于他的传记、印象记、回忆录,不知凡几。大抵侧重于排比事实, 为人物定位。写得较真恳的如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许广平的《欣慰的纪念》等 ,也只从思想风貌着眼;有的则只是政治宣传,如冯雪峰《党给鲁迅以力量》。总之, 都令人觉得与生活实感疏离。可能因为这些作者都是文学家,有某种“做文章”的框框 存于心中之故。周海婴遵守父亲的遗训,“不做空间文学家”,只从所忆所感,老实写 来,表述的都是事实,正如鲁迅所说:“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 转成新鲜。”(《中国小说史略·清之人情小说》)当然,鲁迅弃世时,周海婴还是一个 孩子,但他的一生都和鲁迅关联而且不得不关联,而鲁迅又和不少人关联着。因此,读 这本《鲁迅与我七十年》时,看得出他下笔时有不少顾虑,某些段落的踌躇畏缩之状也 很显然。这因为,从根本之点说,做鲁迅的儿子就不知有多少难处……
做伟人或大人物的亲属是很难的——我将伟人和大人物分开来,是因为,大人物未必 是而且多数不是伟人,伟人未必是握有权力而且多数不是握有权力的大人物——这在全 世界都一样。在中国这个宗法制度、风习、意识浓厚的环境下,其状尤甚。他们都是十 目所视十手所指的社会瞩目对象,众人指指点点的话柄。在西方民主制国家,子弟只要 不仰仗父兄的权势和名望干非分的事,也就不会遭议论了;西方社会个人主义的人格独 立的牢固观念也能辨别当事人和亲属各自应担承的行为责任,权贵名流子弟所受的社会 压力要轻得多。在顽固的宗法意识和宗法风习影响下的中国,凤子龙孙所享受的荫庇之 优渥,常令平民百姓侧目,舆论监视(注意:只限于监视,谈不上“监督”;“舆论” 也常只限于口议腹诽而难形于文字等正常媒体渠道)自然也(一厢情愿地)较为严厉。这 也能算是社会的一点无形制约力量,当然这点制约也只对要顾点脸自知检束的人才有效 。
鲁迅是一介平民,他的亲属本不该受到权势人物子弟那样的监视;但鲁迅的巨大存在 和无可比拟的望誉却使他的亲属比一般大人物的子弟受到更严格的关注。作为鲁迅的儿 子,周海婴不能说没有得到关爱和照拂,但更多的是限制和约束。且不说他不能如普通 公民那样自由支配鲁迅遗留下来的版税,急需无奈时因遗产权以公民应有的法律权利提 起诉讼,也常成为议论的话柄,而且多半是非议。好像伟人的后代一谈钱就玷污了伟人 的名誉似的。甚至连某些人身自由也受到限制,举小例说,据周海婴自述,因为他是鲁 迅的儿子,在北大肄业时,课余连打桥牌也是不许可的(见《北京青年报》2001年11月1 4日所刊《鲁迅儿孙如是说》)。这当然也许是出于爱护,是怕他荒废学业的好意;但由 此可知即使是善意的窥伺,他也是处于一种何等样的经常性的紧张状态了。
一件发生在别人身上不成问题的事,出在周海婴身上就不得了。儿女婚姻本是有充分 自择权的,周海婴的儿子周令飞在国外留学,和一位台湾省籍女郎相爱结婚,即使算是 “涉外婚姻”,那么耳目所及,中国青年在美国、加拿大等地和外籍、台湾省籍的异性 结婚者也多的是;有的家长还是权力阶层的重量级人物,未见引起过波澜,单单周海婴 的儿子的自由婚姻却不能容忍。有关方面竟向他施加压力,要他公开声明脱离父子关系 ,可谓荒唐之至。诚然,台湾有些传媒恶意散播鲁迅的孙子如何如何的谰言,那是国民 党小报和特务刊物的一贯作风,解放前就造谣惯了的。这也说明鲁迅后人处境之艰难, 常会是谣言世家飞短流长的对象。但谣言比较是谣言,周海婴幸而头脑清楚,顶住了压 力,否则只有更丢格。常人就不会遇到这样的考验。
不仅台湾的谣言世家,大陆也有鲁迅的冤家,幸灾乐祸等着看鲁迅后人的笑话。其中 特别是当年鲁迅的论敌,都七老八十了,仇恨情结之历久不解,也真令人惊愕。碍于毛 泽东曾经对鲁迅作过肯定性评价,不敢公开唱反调,除了叽叽喳喳之外,甚至将一肚子 的怨气向后人发泄。例如,周海婴的书中就记有: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委会扩大会议近代 组的会议上,“前辈李初梨说:‘鲁迅算什么!郭沫若提出革命文学的时候,他还在喊 虚无主义呢!’”并诬蔑许广平“和王关戚关系密切,王关戚一揪出来,就吓死了”云 云(见《鲁迅与我七十年》页294)。周海婴只在书中为母亲辩诬,而对李初梨的训斥只 能忍着听。倘他不是鲁迅的儿子,换了别人,听了这种放肆的“鞭尸”咆哮,就可以反 唇相稽:“先生,您懂得什么叫‘虚无主义’么?您还不如重复当年郭沫若的老调,说 鲁迅是‘封建余孽’更到位呢!”
从上引李初梨的发泄,可见怨毒入人之深,而这类敌意地贬抑鲁迅的言谈终究不敢形 之于文字,也可见毛泽东对鲁迅的肯定,对曾经围攻过鲁迅而又死不服气的这些下属是 有镇慑作用的。
但必须清楚,鲁迅的伟大不是任何人和政党所能捧出来的。并非如美籍华裔夏志清所 妄说:“这种殊荣当然是中共的制造品。在中共争权过程中,鲁迅被认作一个受人爱戴 的爱国的反(蒋)政府发言人,对共产党非常有用。甚至于从未轻易赞扬同辈的毛泽东, 也在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向鲁迅致以最高敬意”,“捏造出如此一个神 话。”(夏志清《现代中国小说史》第二章)这是颠倒因果,毛泽东的赞扬在鲁迅死了多 年以后。最早也是“最高敬意”来自中国人民。鲁迅逝世的噩耗一传出,中国人民如丧 傅保,给伟人以远远高于“国葬”规格的“在中国可说是破天荒”的“民众葬”(章乃 器《我们应该怎样纪念鲁迅先生》)。上海的中外人士未经谁的号召,不顾中外反动派 的禁限,万人吊唁送葬。这种自发的对伟人的崇敬,比任何权威人士的夸赞更过硬,这 不是谁能“制造”得出来的!毛泽东的高明之处正是不违民意,肯定了人民之所肯定。 政治家都必须举民心所向的人物为旗帜,中外古今皆然;直到他自以为强大到不再需要 这旗帜,自己有力量支配一切为止。
在这点上,毛泽东也表现了他的不愧为政治家的魄力和诚实态度,在1957年开展“反 右”运动,他所经营的“舆论一律”的局面已见成效时,在回答罗稷南“要是今天鲁迅 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一问题时,便认真的回答:“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在 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鲁迅与我七十年》页371)这话的意思最明 白不过,鲁迅活到那时如“不识大体”,要“做声”,就只有“在牢里”的命运。从毛 泽东语气的先后看,他“估计”的第一可能是“在牢里”而不是“识大体”。这也正是 毛泽东坦率和睿智之处。因为他认定,鲁迅如在,他要写的必然是和他当时所要求的相 违背,相悖逆,因而他为了政治的需要是必须把鲁迅投放牢里的。毛泽东的这种估计, 和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论断的“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 ”,前后精神完全一致。在钦佩毛泽东的诚实坦率之余,这一意味深长的判断,不是更 能增进人们对鲁迅风骨的理解么?
毛泽东是慎思明辨的,他对鲁迅的判断是有根据的。那根据不仅是看到鲁迅在反对北 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反对蒋介石政府残民媚外的一贯坚定不挠,更在于鲁迅在同情坚决 抗日的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时,仍然坚持自己的独立见解,而不屈服于当时共产党在 上海的代表周扬等人的压力。毛泽东的唯一见不到之处,是鲁迅那时如仍在世,写了拂 逆他的文字,对“舆论一律”意识禁锢等现象进行批判和抗辩,正确的仍是鲁迅一方。 当然,这点后来由历史作出了判断。
由于自己的特殊身份,周海婴在他的回忆录里写别人对鲁迅的议论,他自身所遭受的 种种,都是十分谨慎,不尽欲言的。有些看得出曾使他十分困惑的地方,也大抵采取只 叙事实,存而不论的态度。惟有对鲁迅之死,日本医生须藤是否有谋害嫌疑一事,他的 怀疑是强烈的,这一怀疑也是合理的。
关于这一公案,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周建人曾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提出过,似乎 未曾受到文学界的注意。但我所接触到的医学界人士却曾关注过这个问题。1950—1951 年,我曾在上海医学院(即上海第一医科大学的前身,现在已转属于复旦大学)兼课,一 次在会议间歇,听到朱恒璧院长、沈克非、黄家驷、苏德隆等教授不知由于什么话茬谈 起此事。这几位都是医学界权威,意见值得注意。这几位对解放前在上海行医的日本医 生很有意见(不排除这几位都是所谓“英美派”的医学家,和“德日派”有某种门户之 见),这与本题关系不大。现在我记得他们的意见是:三十年代尚未发明雷米风、链霉 素等治肺结核的特效药,彻底治愈肺结核确很难,但治疗这病也并非没有别的有效手段 (他们举了切割肋骨等一些我所不懂的治疗方法),手术如果准确及时,是能延长患者生 命的。他们断定,这个须藤肯定不是肺科专家,医技平常,耽误了治疗时机。当时根本 不知道须藤有日本军人组织乌龙会的副会长的背景这个可疑身份,所以只判断为庸医误 人,应属于医疗事故。
朱恒璧院长很欢喜读鲁迅的书,和我还谈得来,他说,日本人哪里知道鲁迅先生在中 国的价值(这点他错了,如果真是蓄意谋害,那是正因为高度理解鲁迅对日本侵略者是 最危险的敌人)?如果鲁迅先生当时在中山医院(上海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医治,医生会想 尽各种方法挽救他的生命。言下无限惋惜憾恨,给我的印象极深。
以鲁迅的崇高威望,这不仅是一起医疗事故,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特殊事件。可是要 追查清楚却很烦难,想一想日本的右翼势力连世人皆知的侵略屠杀的罪责尚且要抵赖规 避,就更不说这起历时已久踪迹迷离的悬案了。须藤肯定也早已死去,这事大概将成为 一个历史黑洞。
不过,王元化在周海婴此书的序言中所提到的“鲁迅在有人提醒他之后,为什么坚持 不换医生,这也是一件悬案”的问题,我以为倒是可以解释的。
在鲁迅的心中,有一个十分牢固的“藤野先生情结”。这个情结从年青时代起绾结在 他心头,真叫刻骨铭心。只要读读《藤野先生》这篇一往情深的回忆文字,就能理解鲁 迅是如何感念这位老师和医生的程度了。爱屋及乌,他就认为另一位日本医生也会有同 样的职业品德,不会轻启疑窦。也因为鲁迅在日本学过医,有这个“藤野先生情结”, 所以他介绍亲友医病,也经常光顾日本医院。而且,鲁迅和须藤的关系,已历有年所, 不是亲往就医,就是约他到寓所诊治,从《日记》1933年起的记载中,可知彼此往来的 频繁。海婴生病也由须藤诊治,俨然是鲁迅家的家庭医师。再者,彼此有不少函件往返 ,还多次互赠礼品,互相宴请,已不单单是病员和医生的关系,而且是当作朋友在交往 了。可以想见,这样的关系是不能说断绝就断绝的,人情如此嘛!
还有一层原故使鲁迅碍难谢绝须藤:鲁迅和须藤的往来中还夹杂着不少鲁迅的日本友 人在内。如1933年5月23日的日记,就记有宴日本友人秋田、伊藤等男女二十人,须藤 亦在内。须藤似乎也读点书,日记中鲁迅赠他的书有多起。尤以1935年6月20日,日本 刚寄到《岩波文库》中的日译《鲁迅选集》,只有两册,鲁迅就赠了须藤一册。这就不 是泛泛的交情了。如此真情地对待他,如果须藤真要动鲁迅的坏念头,那真是丧尽良心 ,狗彘不食其肉了。——不过,谁又能保证他不是蛇蝎心肠的呢?如果真是敌寇指派来 暗害伟人的话。
这是中日关系史、世界文学史上一个巨大的谜……
2001年11月 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