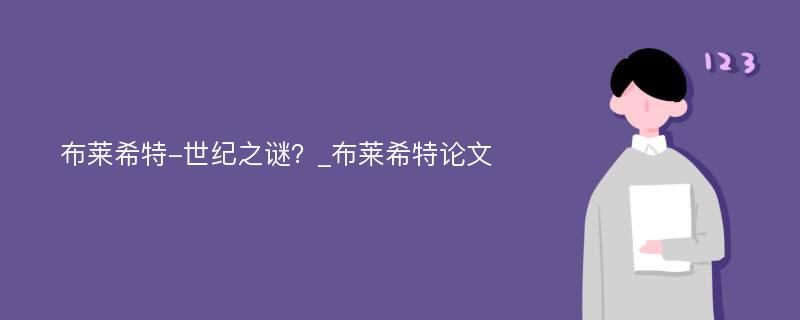
布莱希特——“世纪之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谜论文,布莱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集矛盾于一身的“世纪之谜”?
1978年9月的一天,德国乌尔姆市剧院宽阔的现代化旋转舞台上生发着文化振荡——那天晚上,我正在剧院观看布莱希特的《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台上的情形直令我惊愕摇头:演员表演、戏剧节奏让人感到欠舒张紧凑不引人入胜倒也罢了,这可能是审美文化差异所致,但你能想象和接受居然还有七八个人闲坐在舞台上与台下观众同时观看的吗?坐在台上也就是了,偏偏演员在演出,而这些人却在一旁翘腿偏头抄手抱肚变换姿势,仿佛惟恐别人不知道他们也是观众。更还有人站起身来,大咧咧地招摇过市走到舞台另一角做些小便的动作!这是哪门子戏在演出?!
后来得知,舞台上那排招人眼目喧宾夺主的“观众”是演员扮的,不无做作、夸张,或许更应该说是笨手笨脚的导演之意在强化布莱希特要求的“陌生化效果”;布氏以哲人般理性思辨提出“陌生化”艺术思想,旨在让观众清醒睿智,保持距离,不“移情”,不“共鸣”,得以眼观戏剧,神游八极,深长思考,自省自警,既反思人生也关照社会,最终揭竿而起产生行动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好个激励思维、启迪觉悟的布莱希特!
“我们的剧作是戏剧的坟墓”,布氏当年狂放而豪迈地如是说。他开创“叙事剧”,举重若轻,举世闻名,是对统治欧洲舞台两千多年的亚里斯多德式戏剧结构上千篇一律呆板的反叛和超越,是巨大艺术和思想能量蓄势有年积雄滞发的结果。还在中学生时期,学校木板搭成的简陋舞台便由他自编自导恣意发挥,尽得风流不能自休。念大学学医,仍对戏剧情有独锺,作为戏剧学讲习班旁听生宣读论文,词锋凌厉,针砭激烈,竟无意间“暴露”出剧作家“马脚”,令那位授课的文科教授拍案叫绝,言能写出如此有板有眼的戏剧分析者肯定自己也在搞创作。
布氏最初推出的剧作,尾随一般时尚,表现世道强悍凶险、人类阴冷自私,现代化大城市“丛林化”、生活在都市的人际关系为生物性动物性游戏规则主宰以及市民意识、价值观的庸俗、乖巧、虚假和无聊。20年代德国社会上争取人类进步斗争的浪潮的强劲席卷,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辩证唯物主义著作的深入感读,殷殷体会,使布莱希特洞烛真谛,心雄万夫,世界观达到与历史发展相契合的新境界,创作也点铁变金跃上新台阶。20年代后期剧作,从生活深层发掘题材,展示人被社会几乎还原成兽性的动物,异化为个性丧失的机器(《人就是人》),引导观众伸展思考锋芒、直接认识现实社会制度的罪恶(《三毛钱歌剧》)。30年代初期反映当今社会政治斗争的“叙事剧”(《马哈哥尼城的兴衰》、《屠场的圣约翰娜》)更是横放凌空,挣揣向前,表明思想上艺术上开始走向百炼成钢柔可绕指的成熟。之后发展“教育剧”,又将“叙事剧”推向一个极至。
关注政治的布氏,在柏林并未能活跃长久。他早就感觉到要出现危险,也亲受了这个危险。1933年,希特勒篡权上台,社会环境骤然剧变。发生国会大厦纵火案第二天,布莱希特被迫离开家园踏上流亡他乡路程。对于法西斯主义这个黑色幽灵,布氏运用社会政治经济学观点分析,认为它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产物,因此强调“既反对法西斯主义又想保持资本主义是绝对行不通的”。他呼吁反法西斯知识分子丢掉幻想,要与被剥削阶级即无产阶级携手联合,推翻私有经济制度。他自己当然身体力行,以创作为武器投入斗争实践,确信气焰嚣张的“第三帝国”只不过是极其短暂的一场噩梦。不料,法西斯军队在欧洲处处得手,步步紧逼,布莱希特不得不举家一逃二逃再逃亡。浮家泛宅的流亡生活变得无期无限,翘首向往的“伟大秩序”(社会主义)显得缥缈遥远。最初激情似火的乐观主义情绪逐渐冷清,慢慢沉潜。流亡者需要得到许多方面的保护,别人不能提供便只得自己保护自己。1939年起他停止了对法西斯的直接揭露和鞭笞(1941创作的与卓别林《大独裁者》结构相似的《阿图罗·魏》除外),开始探索对立面事物的(积极)实用价值,评价(人的)面具的防护性功能。凡流亡作家,谁都明白,写小说要比写戏剧较容易获得市场回报。但整个流亡期间布氏仅发表一部《三毛钱小说》,还有1940-1944年间写下的《逃亡者谈话录》。他认为当个“戏剧匠”是他的人生使命,他要忠实自己的使命。后期作品主人公如伽利略(《伽利略传》)、沈黛(《四川好人》)、大胆妈妈(《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马狄(《潘第拉老爷和他的男仆马狄》或者是阿兹达克(《高加索灰阑记》),一个共同特点是缺少英雄主义气概和崇高的人格力量,面临生存矛盾首先想着避害保障自己,虽不愿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但又没有放弃对美好未来的精神追求,这与布氏当时的情形和心境可谓不无几分相似。它们还给人一种对中国老庄敛迹避祸的哲学学以致用的感觉。
有意味的是,布氏前往苏联却不愿在那里扎身驻足。虽说1930年他曾创作《马哈哥尼城的兴衰》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堕落,1941年却要辗转经过莫斯科前往美国寻求庇护。流亡美国,表明布氏对这个国家的态度是既恨又爱,或者,这根本就是一个历史的幽默。青少年时期曾幻想当个行侠仗义的西部牛崽,而今来到这里,如同不少流亡作家一样,也想在好莱坞谋个生活找口饭吃。其时,好莱坞商业文化机器高速运转惟恐不能满足市场消费需求,精当缠绵的招徕技术不停复制着感官刺激精神麻痹就怕君不光顾,而戏剧、文艺的空虚无聊本是布氏高声宣战的目标对头,他鄙薄低级、浮艳、娇饰、柔靡的消遣艺术使哲学丧失智慧,使审美倒了胃口。双方能有机缘么?
布莱希特在好莱坞求而无果,与美国演员劳顿的合作也不尽人意。到美国的最大收获是较系统、完整地写出了“叙事剧”理论《买黄铜》,即1949年修改发表的《戏剧小工具篇》,并且创作完成了后期剧作。与颠沛流亡其他国家相比,在美国期间布莱希特的个人生活状况大有改善,但他心中总有阴影笼罩,挥之不去,摆脱不了被人监视的感觉,直至1947年的一天果然有麦卡锡主义的“非美活动委员会”派人径直上门,昭示传唤。受讯时,布氏申明自己不是共产党员,但同时坦然自若掷地有声地道:“我当然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他的历史观点。我认为今天不去研究马列主义是不可能写出有思想性的剧本来的。”今年,为纪念布莱希特诞辰一百周年,德国威斯特伐仑州剧院特意排演了小歌剧《听证会》,将布氏当年被传讯的情节搬上舞台,而展示的是他作为一个普通人、艺术家和诗人的人生,从2月8日起公演。这或许是另一个历史的幽默。
不过,布莱希特当年可产生不出什么幽默兴致。屈辱的体验使他愤然离开美国返回欧洲寓居瑞士。国土虽小的瑞士友人,其勇气委实令人钦佩,是他们在纳粹德国正肆虐横行欧洲时期就敢吃“螃蟹”,开风气之先,在世界上最先排演了如今在国际上畅演不衰的布氏后期剧作。有人认为,假如没有瑞士的这几场首演,布莱希特作为戏剧家的存在恐怕早就消泯。这绝非故作惊人之语。不过,布氏在瑞士也有不愉快经历,尤其是那股上下翻腾起来反共产主义的非理性情绪使他后来又离开了瑞士。
1948年从瑞士回到苏军占领的那部分德国。东德对布莱希特的热忱十分重视,满足他流亡期间梦寐以求的愿望,让他在当年以《三毛钱歌剧》高放华彩征服世界的地方创建“柏林剧团”,并放手任他按照自己的理论自行实践导演自己的剧作。如鱼得水的布氏果然身手不凡,在他的领导下,“柏林剧团”蜚声海外成就斐然,形成独特风格和演出流派,对战后德国戏剧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1953年布氏当选“德国笔会”主席,1954年又荣获“斯大林和平奖”。布莱希特熠熠生辉,成为东德社会主义文艺的一个当然代表。
然而辉煌的另一面是,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的1949年之秋季,布氏口袋里多了一本崭新的“中立国”奥地利发放的公民护照,他的艺术思想在东德也并非每每都受到褒扬,除“柏林剧团”外并没有其他东德剧院排演他的戏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视布氏艺术为格格不入的“形式主义”),他自己对东德社会和政局也有不满、怀疑或绝望,还在日记中写下称自己是“受勋的人民罪犯”字样而又划掉(根据W·赫希特《布莱希特年鉴》的说法,布氏到东德后一直受到暗中监视,统一社会党政治局是“很勉强地”批准他创建“柏林剧团”的)。他对1953年6月17日在东柏林发生的事件态度含混,模棱两可,面对西方媒体的“根据统一社会党政治局授意而修改戏剧”的无端攻击也不反驳一语,立志作个“戏剧匠”却创作缺产,只写过一个表现劳模的剧本也未搬上舞台。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得热火朝天,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布氏则在研究中国孔子、老庄。顺便提及,今年1月23日,德国柏林有个题为“布莱希特与东亚”的展览会开幕,布氏的“中国情结”显然也是个常说常新的话题。
布氏在他去世前约四个月患病住院时,曾告诉探望者想要改编S·贝克特的荒诞剧《等待戈多》。同事不仅带来了他要的贝克特剧本,还带来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发言。赫鲁晓夫指责的斯大林暴行使他感到极为“震惊愤怒”,于是一反已经表示了的出院后不再导演戏剧的初衷,决定亲自执导《等待戈多》,并计划要在当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岗这两个流浪汉实际上是在绝望地等待救星出现的过程中,在舞台背景上放映世界各地闹革命的千秋风云镜头。难道,他这是要将“孩子连同脏水一同倒掉?”
布莱希特这个人可谓集各种矛盾于一身,变换面具就如同他人更换衬衫那样频繁。难怪有评论引用其早期的幽默话语“我总要忘却我的世界观,却下不了决心将其熟记”,认为人们无论如何穷经皓首,无论因此有何发现,他仍旧是个“世纪之谜”。
不过,曾有一段时期,西方人认定布氏面目可憎。当年他从瑞士返回德国时原想回到西德却遭当局拒绝;被视为“共产主义作家”的作品也在西德书架上销声匿迹,教科书告诫学生关于此人的悲哀是“经常用僵硬的党的思想代替原本的艺术追求”;戏剧被禁止上演,因为若将这些“共产主义的特洛伊木马”放进门来就有被攻城夺池的危险,后来还是上演了却也有当然的道理:是“民主体制之坚强和优越的证明”;更有人在国会、媒体上发出诸如“党徒”、“唆使犯”等不绝于耳的辱骂、攻击声。
星移斗转,世事嬗变。进入60年代,布莱希特却在西方渐渐“热”了起来。剧院上演他的剧作,大学开设研究他的课程;左派团体视他为输出精神能量、善于斗争的榜样,右翼人士说他只不过是个转述刚从书本上阅读来的理论的小角色而已;逝者布氏的确可以被人“盖棺定论”,不可能再有主体性——它早被一些力求发现的学者“解构”得支离破碎。对于普通百姓来说,不论是“叙事剧”、“教育剧”、“陌生化效果”还是“辩证剧”,这些术语都不吸引他们关心在意,但布莱希特仍然深深影响了他们,这就是德国文学批评家M·莱西-拉尼茨基所说的:“不管是自觉还是不知不觉,总之我们几乎是每天都在引用着他(布氏)的话语”。
布莱希特热及颠覆与攻讦
此消彼长,承转变异。随着布莱希特诞辰一百周年的日子到来,已经冷寂了好一段时间的布莱希特“热”又轰地复燃大地。德国在庆祝,美国在庆祝,俄罗斯庆祝,中国也庆祝;你出选集,我出全集,他办展览,大家都在排演戏剧。布氏成为全世界的共有诗人,属理所当然之事,还没有第二个作家能像他那样在全世界范围内深远地影响了戏剧、文学乃至人的政治思维。他的作品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辩证法、法西斯、战争还有科学进步对人类应负的责任等题材,关注了现代艺术形态和审美方式等问题,是我们这个世纪的一面镜子,恰如布氏自己所说:“四十年(后回眸),我的作品演唱了千年历史”。
须知,说此番话时,布莱希特才22岁出头,毛头小子却已有不羁天才的自信:“我发现,我正在成为一个经典性作家”,他在日记中写道。“经典”不假,瑞士当代作家M·弗里施顺着话头而掉转价值评价道,是因为“用力过头”而丧失了作用(“经典”一词又可引申成“过时”之意)。这里,“用力过头”是指布氏关注、思索、改变现实的政治思想太(耳提面命似的)锋芒毕露而又(马克思主义式地)简单划一,因此被人诟病。不言而喻这是一件见仁见智的事情。
譬如,在布氏诞辰一百周年来临前夕,美国戏剧家A·米勒在德国报刊上发表见解认为:“不论怎样,每一位艺术家都至少在一点上应该感激布莱希特,是他将政治生活带进了审美王国,把社会本身变成了艺术材料的必要部分,由此拓宽了我们时代的戏剧艺术天地”;同在同一版报纸上,瑞典哲学家、文学家L·古斯塔夫松却抓住布氏让艺术服务于政治,曾写了认为是支持斯大林犯下的清洗谋杀罪行的《措施》不肯放过:“在所有的本世纪里出现的多得叫人惊讶的令人生厌的文学人物中,最让我厌恶的莫过于布莱希特”。
古斯塔夫或许被偏见蒙翳或许有所不知,布氏后来宣布收回了《措施》这部“无产阶级教育剧”,并规定在他死后也要禁止该剧的演出,只是他那位继承了在美国上演权的儿子却在允许排演。了解情况的研究布莱希特的专家学者们,自然是不会只凭一丝感觉便轻易奉送捧之上天的殊荣或发表按之入地的贬谪。不过,在今年这个“布莱希特年”里他们也有自己的尴尬。必须要写点儿什么可是又还能再写点儿什么呢?用一位举办布莱希特展览的德国人士之话来说,连布氏使用过的“每一张纸条”都早被深挖发掘得世人皆知,耳熟能详。尽管如此,对布莱希特的研究还是呈现出新的动向:他原来并不怎么受人注意的早期诗歌被发现是令人迷途忘返的精彩世界,被视为是活力充沛生气灌注自成高格之作,被提高到了与歌德、盖尔哈特诗歌相提并论的高度。
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动向,布氏正面临着被道德卑鄙化、精神侏儒化、文学地位瘸腿化、生活面目寄生虫化的形象颠覆。攻讦、发难者目前主要来自美国。在布莱希特百年诞辰来到之时,美国学者J·费吉于1994年发表的《布莱希特公司.性、政治以及现代戏剧制作》一书也在德国出版,译本书名《布莱希特公司》,以厚厚重重一千多页篇幅,告诉读者对于布氏作品“必须重新阅读,甚至要以布莱希特式的方式”(即“是谁修建了底比斯城?书上写着国王的名字。然而难道是国王们当年在把那些建筑石料搬运?”这种布氏设问启发民众追问谁是真正历史主人的方式)阅读。J·费吉将他这部花费20年辛苦著成的布氏传记献给E·豪普特曼,认定这位当年女秘书是受布氏巧取豪夺的最大对象羔羊,她本是《三毛钱歌剧》之“百分之八十”作者,荣誉却让布莱希特鹊巢鸠占;指出是当年那些为布氏工作的女性们使“布莱希特成为了布莱希特”,但“龌龊丑陋”(被暗示还有同性恋行为!)的布氏对她们不仅在性生活上利用,而且还经济上剥削,艺术上掠夺,将本属于集体创作的(布莱希特大部分)作品完全窃为己有!
骇人听闻么?有人宁信其有。生活在美国的E·豪普特曼侄女就已经请求享有对豪普特曼知识产权的继承权,还有其他当年布莱希特身边女性的合法继承人也在磨刀霍霍考虑提起诉讼请求权利,而布氏著作的版权商也聘请好律师摆出严阵以待毫不相让的架势。设想,如果一旦请求被法律支持并准予,那么不仅涉及的稿酬补偿高达七八位数,而且对于《布莱希特全集》恐怕也许就真的有人要求其更改为是由“布莱希特公司”所著!
布氏作品中有他人劳作,布氏对待如今非常敏感的知识产权问题的漫不经意,是研究布莱希特的学者专家们达有共识的不争之事。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人反对乃至反驳J·费吉对布氏的概行摈斥作法和其《布莱希特公司》中荒诞驳杂的言谈。在德国其荦荦大者有譬如J·希勒斯海姆和U·沃尔夫主编的《“收获”.奥克斯堡学生报纸及其主要撰稿人》(1997)就以历史文献表明布莱希特有将自己作品让他人署名的举动;再如S·克比尔的《我不过问我那部分·E·豪普特曼与布莱希特一道工作》(1997)也以E·豪普特曼留下的书信、笔记证明J·费吉对她的惜花怜玉打抱不平没有多少道理;还如W·赫希特的《布莱希特年鉴》(1997)更以严肃文字展示布氏在文学创作上锲而不舍顽强向上的坚毅人生,足令你不会产生轻亵之意。
诚然,对布氏其人其生究竟如何看待,每个人都允许拥有自己的评价和立场,而且各自看法中有冰炭之殊也不为奇。有此思想准备,在布氏百年诞辰到来之际,从德国报刊上读到德国东部(前东德)作家K·亨瑟尔表述的“布莱希特令我对他感兴趣的,不是他对社会主义的讴歌,而是他对资本主义的仇视”这段话时,却让我好一阵子琢磨思索。窃以为,这段平实之言淋漓尽致地道出了今天人们对于布莱希特作品的一种新接受。
想一想,约半个世纪以来,(生活在如今是德国东部的)人们一直认为贫困、恐惧、犯罪、老鸨、卖淫、物价飞升、毒品、挑唆战争、新纳粹、一无名小卒被造之为神随即又被暴光“枪毙”等等现象只是在书籍、电影、电视中才有,是另一个世界和社会的专利,是已经被社会主义社会消除了的过去,可是,转眼之间这一切竟又都成为了活生生的生活现实,怎能不叫人不对布氏作品既疏离又情深。
以现实生活为参照面对布莱希特作品产生新感触的还有俄罗斯人。据“德国之声”广播电台报道,为纪念布氏诞辰一百周年,莫斯科排演了其早期戏剧,舞台上的黑手党情景让俄国观众不由得联想到了现实生活中的黑社会猖獗;美国人也排演了《三毛钱的歌剧》,但没激起“布莱希特浪潮”,布氏虽然引不起美国大众兴趣,却有不少导演感觉到了要导演他的戏剧的愿望。仅这两条消息,也足令人不会对布氏产生轻亵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