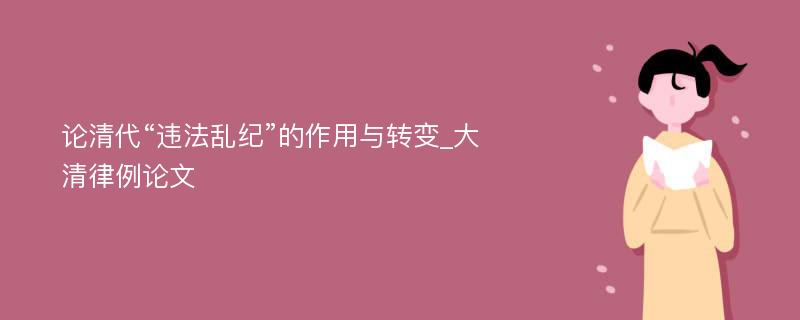
论清代“违制律”的功能及其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代论文,功能论文,违制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076(2016)02-0074-15 问题的提出 “概括性禁律”一词是美国学者布迪、莫里斯在《中华帝国的法律》一书中针对“违制律”、“不应为律”、“光棍例”、“违令律”等具有高度的笼统性、抽象性和涵摄性的法律条款所创设的一个名词。①在清律中,这些法律条款具有了法律规范构成所应具备的逻辑结构要素,属于完整的法律规范。但是,它们逻辑构成中的行为模式却又具有极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②,这就赋予了帝国的统治阶层在适用它们时拥有了较大的裁量空间,因此被称为“概括性禁律”。 “违制律”出现在帝国的正式律典中自《唐律疏议》始,此后历朝的律典均承袭了唐律的规定。③清代的“违制律”是指《大清律例·吏律·公式》中的“制书有违律”,该条规律定: “凡奉制书有所施行,而(故)违(不行)者,杖一百。违皇太子令旨者,同罪。失错旨意者,各减三等。其稽缓制书及皇太子令旨者,一日,笞五十,每一日加一等,罪止杖一百。” 其律前注对“制”做了注解,即:“天子之言曰制,书则载其言者,如诏、赦、谕、敕之类。若奏准施行者,不在此内。”④ 这条律文承自明律,在清初经删定而成。律文中的小注系顺治三年添入,并于雍正三年修定。⑤修订前的原律文中还包括这样几项内容:第一,关于违背、稽缓亲王令旨所应受到的处罚;第二,对“失错旨意”做了夹注解解;第三,小注对“制书”的范围作了进一步的界定;第四,原律文的“律后注”对“故违”、“失错”、“稽缓”三个概念作了辨析和区分。⑥对于此条中的“制书”是否包括太后的令旨,沈之奇认为:“令旨不言后宫者,以母后之旨,不传于外”。⑦实际上,在乾隆五年之前的《大清律例》中,“制书有违”条的律文后面原本是附有两条条例的,乾隆五年修律后或未被登录或被删除。一条为不敢登录之条例,另一条是被删除的为不必登之条例。⑧ 从《大清律例》对“制书有违律”的规定来看,“违制律”本身并不是一款完全的“概括性禁律”,它的行为模式和犯罪构成是具有一定确定性的。它的犯罪行为模式是较为明确的,即违背、稽缓皇帝制书和皇太子令旨的行为。其犯罪事实的构成描述也较为清晰,犯罪行为分为违背和稽缓两种;犯罪主观构成要件分为故违和失错两种;犯罪行为所侵犯的对象不仅包括皇帝的制书,还包括皇太子的令旨。该款还就不同的犯罪情形所应科处的刑责做了具体的区分和界定。总之,单就律典中的“制书有违”条内容来看,是无法看出这款法律具有极为广阔的概括性功能的。 这与同样被称为“概括性禁律”的“不应为律”是不同的。《大清律例》对“不应得为”的规定是这样的:“凡不应得为而为之者,笞四十;事理重者,杖八十。(律无罪名,所犯事有轻重,各量情而坐之。)”⑨可以看出,这条律文对“不应为罪”犯罪事实构成的描述极为模糊,归罪要件极其笼统,缺乏明确的犯罪行为模式,可以说是一种“完全空白罪状”。⑩总之,单从《大清律例》的规定便可看出“不应得为律”是一款具有广阔涵摄性的概括性法律。相对于“不应得为律”,“制书有违律”所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更为具体明确,其归罪要件并不是特别笼统。就其立法形式而言,“违制律”与现行刑事立法中的“不完全空白罪状”相类似。 “违制律”的涵摄性主要表现在后续的律例立法和司法适用中,比如它出现在《大清律例》的很多律条例中,其分布的范围、适用的主体、规制的内容都远超出了“制书有违律”的本意。就《读例存疑》所录的情况来看,涉及到“违制律”的律例共计81条,只有“制书有违”和“失火”、“违令”、“吏典AI写作招草”4条律文对“违制律”有规定,其余77条皆由条例规定。在《大清律例》的七篇中,除工律外,“违制律”在其余六篇中均有规定,共涉职制、公式、户役、田宅、婚姻、仓库、课程、钱债、市廛、祭祀、仪制、宫卫、军政、关津、邮驿、贼盗、斗殴、诉讼、杂犯、捕亡、断狱等21门。由此可知,“违制律”在清代规制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涵摄到国家和社会的方方面面。 总之,从《大清律例》的规定来看,“违制律”本是一款为保障君主的谕令诏旨等御用文书得到遵行而设置的法律,其本意是维护皇权。但在帝国存续的过程中,“违制律”更多地表现为一款具有概括性功能的法律,其规制的范围和适用的主体都远超出了其原有的本意,这使它在帝国的法制体系中呈现出两种法律功能取向。当前,学界尚不存在针对“违制律”的专门研究,已有的少量研究多是从“概括禁律”的角度进行探讨的,并未对“违制律”的本源功能以及它的功能转换予以关注。(11)本文将以清朝为中心,对“违制律”两种功能的具体表现以及其概括性功能的取得方式进行研究。 一、维护皇权:“违制律”的本源功能 福柯在论述西方中世纪以来的法律时曾指出,这一时期的法律“是满足国王要求的法律”,维护王权是这一时期法律的核心任务。不仅法律思想的研究要围绕王权而进行,法律体系的构建也是要围绕君主的利益为中心。法律成为维护王权利益的工具。(12)福柯所论及的这种情况也适用于中国帝制时期的法律。 在中国古代,皇帝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是名义上代表中央的唯一立法者”(13),国家层面的政策法令都是以皇帝的名义颁布的。皇帝的制书、诏书、令旨、谕敕等在很多情况下可以成为国家的法律渊源,即所谓的“口含天宪”。中国古代的律典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涉及到皇权的维护问题。林乾教授在讨论帝制时期的皇权缺乏有效的制约时,曾论及唐律专设“制书有违”罪以维护君命,而限制君权的臣工的“封驳权”却没有法律保障。(14)明季律学大家雷梦麟曾就“违制律”的频繁应用指出:“近则摘引此律者为更多,殊失定律之本意。”(15)总之,在律典中正式设置“违制律”,是君权日益加强在法律中的表现;而在实践中该条款的频繁援用,则反映出“违制律”在维护皇权方面的重要作用。 通过《大清律例》的规定可知,“违制律”的本源功能是维护皇帝的制命能够得到遵守执行,所以“违制律”在清代政治领域的应用首先表现为对皇权的维护。“违制”作为一种带有恐吓性质的词语在清朝皇帝的谕令诏旨中经常出现,犹如握在君主手中的一条鞭子,不断地被用来威胁督促臣工遵从君命。如果根据“制书有违律”的本意来看,这里的“违制”即是指“违制律”。我们不妨通过一些具体的事例来展现“违制律”的这一功能。 顺治元年,皇帝在即位诏书中规定:“向来势家土豪,重利放债,折准房地,以致小民倾家荡产,深可痛恨。今后有司不许听受贿嘱,代为追比,犯者以违制重论。”(16)乾隆皇帝曾多次降旨禁止臣工进贡,并以“违制”相威胁。如乾隆十六年,就地方官员为接待皇帝巡幸而专务戏台彩棚、龙舟灯舫等浮华事项一事,皇帝谕令“嗣后寻常行幸,概不准行。违者以违制论。”(17)乾隆二十二年,皇帝谕令官员:“嗣后各省督抚除食品外,概不得丝毫贡献,违者以违制论。”(18)嘉庆十九年,皇帝谕饬:“上年直隶豫东三省交界奸民滋事……著三省督抚即分饬地方官访明现在巢窟,令其自行毁除。若不毁除,或经官查出,或被人告发,以违制论。”(19)同治元年,皇帝谕令:“嗣后州县解费酬应等项,均著永远裁革。除钦差兵差照例供应外,其余过往差使以及本省上司,一概不准应酬,违者以违制论。”(20)直到清朝即将灭亡的前夕,“违制律”还是皇帝警诫威胁臣民不得违犯君命的法律,所涉领域包括司法改革、铁路收归国有等重大事件。宣统二年正月,法部所奏“酌拟死罪施行详细办法一摺”中有“违者,以违制论”之语。(21)宣统三年四月,在宣布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的谕令中,清廷依然以“违制”作为督促威胁臣民要遵守执行制命的罪名:“……如有不顾大局,故意扰乱路政,煽惑抵抗,即照违制论。”(22) 通过上述几任皇帝的谕令内容可知,他们谕旨中的“以违制论”是针对违犯皇帝的相关制命而言的,所指的便是“违制律”。但是,谕令诏旨中的“以违制论”和“论以违制”起到的只是威胁、警诫的作用,并不意味着最终会真的科以违制之罪。违背皇帝制命的行为,皇帝认为严重时,违犯者可能会有性命之虞;如果皇帝认为不那么严重,或者基于其它方面的考量,则有可能轻罚甚至免于处罚。比如,清朝的皇帝大都曾颁布过诏旨谕令禁臣工进贡,如嘉庆四年正月甲戌,皇帝在谕令中再三申禁臣工呈进贡物,并威胁道:“经朕此次严谕之后,诸臣等有将所禁之物呈进者,即以违制论,决不稍贷。”(23)巧合的是,谕禁当年便发生了福州将军庆霖违例呈进土贡的案件。内阁和兵部的议处意见是将庆霖照违制例革职,但嘉庆却认为:“今庆霖乃循照年例,呈进土贡……即照部议以违制例革职,实为罪所应得。姑念庆霖由侍卫出身……又属初次,著从宽改为革职留任。”嘉庆皇帝担心此次宽宥庆霖会使其他官员心存侥幸,将此前的饬禁视为具文,便在圣谕中一再摆事实讲道理,强调自己宽恕庆霖的原因:“此次朕之所以宽恕庆霖者,实因伊系武职糊涂,所进只系方物,其咎不过冒昧,尚非欲倡为此举”。继而威胁道:“倘臣工等误会朕意,欲藉此营私见好,仍冀得免严议,则是有意效尤,不但照违制例革职,必当重治其罪,决不姑宽。”(24) 另一个案件的当事人只因为悖逆皇帝的意愿(非命令)而被科以“违制”之罪,则显示出“违制律”在一定程度上是掌控在帝王手中的统御工具。嘉庆九年五月丁酉,根据皇帝的谕令,内阁和吏部议请将湖南原任巡抚高杞照违制例革职,这是因为湖南省仓谷亏赔事宜已经总督吴熊光奏定,皇帝已经降旨允准“在各员名下按照时价追补归款”的方案。但是,“高杞辄妄议更张,既以例价追银,复向有粮之家按粮匀买,核计民闲须赔银至二十万两之多。”皇帝认为高杞的这种做法是“袒官病民”,会出现“地方官员等得任意私亏,饱其囊橐,而百姓代官赔补,贻累无穷,岂不大形纷扰?”的结果。所以皇帝认为“高杞妄更成议,实属乖谬。著照部议革职,仍来京候旨。”(25)在这个案件中,高杞的做法是否得当,暂且不论,单就其违反皇帝允准的既定方案,另奏请其他方案的做法是否应该被科以“照违制例革职”的惩罚,则是值得深思的。因为高杞并没有将自己的方案付诸实施,而只是在奏折中提议。作为封疆大吏,难道连在奏折中提出议案的权利都没有吗?或许,皇帝关注的是高杞的提议是对既定方案的否定,这是一种对皇帝意愿的违背,所以要以“违制律”予以惩处。 通过这两个案件可以看出,虽然皇帝诏旨中信誓旦旦地威胁“论以违制”、“以违制论”,但一旦有人真正的违反制命了,是否会真的要根据“违制律”来科责,则是不确定的,这时要考虑到皇帝的性情、他的政治考量以及违犯者的身份地位等综合因素。当然,这种综合考量的权限只有皇帝享有,法司在审断案件时还是会依据律例的规定做出“罚当其罪”的拟判,就如内阁和兵部对庆霖的议处意见是将其照违制例革职。 总之,这些谕令诏旨中的“以违制论”、“论以违制”所起到的只是威胁、警诫的作用,并不意味着最终会真的对这些人科以违制之罪,而且它们所针对的对象是不特定的。如果是真正的要施加违制之罚,则必须是经过一定的程序之后,由相关的机关来做出,其所科责的对象也是特定的。 二、概括性禁律:“违制律”的延展功能 从《大清律例》的规定来看,“制书有违”罪本是对未施行皇帝的制书及太子的令旨,或对施行诏旨等有误的行为进行处罚的罪名,所以它本质上是一款维护皇帝和太子(明朝时还包括亲王)的命令能够得到遵行的法律,所保护的客体是皇权。但是君主的制书和谕令诏旨等有很多,会涉及到当时国家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论以违制”、“以违制论”、“坐以违制”等会频繁出现在这些制命中作为警诫和威胁,这就为“违制律”发展成一款“概括性禁律”提供了基本条件。而各部律典对“违制律”的规定也为其成为“概括性禁律”提供了制度性条件。比如在《大清律例》中,除了“制书有违律”这一条原律文外,还有80条律例规定有“违制律”,涉及的领域和范围十分广泛。更何况,律典中还规定了“断罪无正条”时可以比附援用“违制律”。所以“违制律”是在具备了一定前提条件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一款概括性法律条文的。 在相关的81条律例中,除了“制书有违律”这条原律文外,其余80条律例中的“违制律”均非“制书有违律”的本文,而是作为“概括性禁律”存在于这些律例中,由此也可以看出“违制律”在其他律例中是准用的。这种情况并非是律文制定者的体系性考量,而是基于在“罪刑相应”的立法原则主导下,如何对律无正条、罪该杖责的行为进行规制时的考虑。而“违制律”在律例中的分布和表现形式则进一步证明了它在清代律例体系中的“兜底”性地位,即“违制律”在清朝的律例体系中是准用性的、兜底性的、概括性的。 对于“违制律”在清代法律体系中的兜底性地位,笔者将从对几款涉及“违制律”条例的纂定过程来进行分析,以便使它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更加明晰。比如,《续增刑案汇览》中的记载: “东城御史奏京城粗米贩运出城,如乡民有进城卖细米食用者,一石以内准其出城,一石以上照违制律杖一百。……又,运粮旗丁如因正项亏短,买米回漕,不及六十石者杖一百徒三年,六十石以上者发边充军,数满六百石者拟斩监侯。卖米之人与同罪,至死者减发极边烟瘴充军。各等语。 是商民偷运细米出城及买米回漕俱有治罪专条。至粗米一项例内只言概不准其贩运出城,并无作何治罪明文。……将张三等比依乡民买细米出城一石以上杖一百例,从重枷号一个月,审结在案。 兹据该御史奏称,例载粗米但云概不准贩运出城,并未载运米出城应得何罪,恐乡愚无知,易干例禁,奸猾之徒又明知例无治罪专条,肆行偷贩。且米数多寡不同,定案时无例可援,或不免畸轻畸重之弊,请明定罪名,著为定例。等因。 查断罪无正条,名例原有比附加减之律。故粗米出城例无治罪明文,向来均系核其情节重轻,分别比照定断。然与其随时比附办理恐致参差。诚不如另立专条援引较为划一。该御史奏请明定罪名,系为慎重刑章起见,应如所奏办理。 ……(26) 据上述可知,当时将京城细米私自贩运出城的行为和漕运兵丁买米回漕弥补亏短的行为都已有专条治罪了,只有“粗米一项例内只言概不准其贩运出城,并无作何治罪明文”。在断罪无正条时,本是可以通过比附加减的方式治罪的。但考虑到“与其随时比附办理恐致参差,诚不如另立专条援引较为划一”,这样也可以起到“慎重刑章”的作用。于是便有了《户律·市廛·市司评物价》的一则条例: “京城粗米,概不准贩运出城,如有违例私运出城者,除讯有回漕情事,即照回漕定例办理外,若讯无回漕情事,实系仅图买回食用,或转卖渔利者,一石以内,即照违制律,杖一百。一石以上,杖一百,枷号一个月。……一千石以上,枷号三个月,发极边足四千里充军。至乡民有进城买细米食用者,一石以内准其出城,一石以上即行严禁。如有逾额贩运,照违制律,杖一百。若一年之内,偷运细米出城,至一百石以上者,加枷号两个月。……”(27) 又如,乾隆五十三年,四川省民妇冯龚氏殴伤丈夫冯青致死案件中,冯龚氏殴夫致死,属于“十恶”中的恶逆行为,(28)依律斩决,本无异议。存在争议的是如何处置其子冯克应。四川总督认为冯克应因赴前途点火,并不知道父母争殴情事,所以建议免科其罪。但川督的这一意见被刑部奉谕驳回,理由是冯克应迫于母命,不仅在案发后隐忍不言,即使到案时亦未供出实情。最终,刑部“遵旨酌加薄罚,照不应重律,杖八十等。”(29)只是,刑部在奉旨将此案纂辑为例时建议:“嗣后如有父为母杀,其子到案犹复隐忍不言,较母为父杀子为父隐者不同,应照违制律,杖一百,以示区别。”(30)皇帝估计没有完全认可刑部的这一意见,因为此案最终纂定成的条例时又有所变动:“父为母所杀,其子隐忍于破案后,始行供明者,照不应重律,杖八十。如经官审讯,犹复隐忍不言者,照违制律,杖一百。若母为父所杀,其子仍听依律容隐,免科。”(31) 其实,根据《大清律例·亲属相为容隐》的规定,除了谋反、谋大逆、谋叛三种罪行外,凡同居共财之大功以上亲属皆可相为容隐(32)。本案中,冯龚氏殴夫致死非谋叛以上罪行,其子冯克应为其容隐,本是“亲属相为容隐”律所明确允许的。奈何皇帝特降谕旨,欲加罪冯克应。刑部官员无律可引,只能照不应重律科杖八十,以完成“遵旨酌加薄罚”的要求。 对于这种有律不用、以例破律的情况,固然应了《清史稿·刑法志》所做的批评(33),即便是否有必要针对此种情况专设一例,薛允升就颇有微词:“祖父母为父母所杀及父母为祖父母所杀,并长兄与次兄互相杀伤,如何科断,均无明文。此伦常之变,虽圣贤亦无两全之法,而顾责之区区愚氓耶。此等情罪,律不言者,不忍言也。似可无庸纂为条例。”(34)另外,薛氏还列举了东魏孝静帝天平年间发生的因新颁布的《麟趾新制》规定有“有母杀其父,子不得告,告者死”的内容而在官员间引发争议的例子(35),认为无需制定这样的条例,如遇有此种情况,可以临时议罪。(36) 再如,《户律·户役·赋役不均律》的乾隆五年定例规定,府州县掌印正官如有额外加增征银及滥设差役等扰累民众的行为,督抚应及时纠察,“将有司官依违制律治罪。上司官容情不举,罪同。”(37)此条系前明问刑条例,雍正三年修改,乾隆五年改定。《大清律集解附例》有明确规定。(38)薛允升认为:“此例盖不许额外乱差也。问罪治罪无明文,当依违制科。”(39)薛氏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刑部任职,曾官至刑部尚书,对清朝的法律制度甚为精熟,他对这条按语可谓是代表了时人对“违制律”法律地位的认识和定位,即在律无正条的情况下的兜底地位。 薛允升对另一则条例的评价也可以给我们明确“违制律”和“不应为律”的律例体系地位。《礼律·仪制·丧葬律》的一则条例规定:“旗民丧葬,概不许火化,除远乡贫人不能扶柩归里,不得已携骨归葬者,姑听不禁外,其余有犯,照违制律治罪。族长及佐领等隐匿不报,照不应轻律分别鞭责议处。”此条系雍正十三年上谕钦定的条例,并经乾隆二十一年改定。薛氏在按语中感叹道:“此亦不得已之办法也。”(40)如果对此按语加以解读,“违制律”和“不应为律”是解决这种“不得已”的情况的重要手段。 因为“违制律”在律例体系中的地位是兜底性的,在统治者面临新出现的社会情势时,便会以“违制律”来解决法律缺失等问题。如“违制律”被清朝统治者广泛应用于旗人治理的方面便是很好的体现。“违制律”规制的主体不仅包括一般旗民,还包括各旗王公、八旗官员、旗员子弟、漕船旗丁等不同的群体。“违制律”在被用于旗人子弟的日常管理时,所规制的行为包括了告假归旗、婚丧嫁娶、诉讼、赌博、看戏等情况。清朝以“违制律”对旗人的行为进行规制,实际上是在利用“违制律”的概括性功能。因为清律是承自明律,而明律中又没有关于旗人的规定,因此清朝统治者不得不找出一款合适的罪名来规制不断壮大的旗人群体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具有概括性功能的“违制律”便成为了不错的选择。 “违制律”还被经常用来解决一些疑难案件,如容隐案件。因为容隐案件往往会涉及到国法与情理之间的纠缠与衡量,所以此类案件的案情一旦较为复杂,便会给断案官员造成一定的司法困境。有些容隐案件会使司法官员处于一种无法可依的状态,这种情况下便会将“概括性禁律”派上用场。上引之冯克应案件便是例证。有时候为了实现容隐案件的“情法之平”而对涉案人员适用“违制律”。在道光五年的一宗案件中,案犯宗崇义的弟弟宗四小子与田氏通奸,将田氏的丈夫田泳然欧伤致死。宗崇义获知了案件的情由,“律得容隐”。但是,“宗崇义明知田菁然听从伊弟宗四小子诬告曹继幅等为正凶,向其索借盘费,虑其供出实情,即行借给银两,非寻常容隐可比”,宗崇义最终被照“违制律”杖一百。此案被案例汇编者编辑到“制书有违”门类下。(41) 总之,在清朝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对于这些律无明文规定的存在争议的情况,作为“概括性禁律”的“不应为律”和“违制律”便会被派上用场,这也展示了它们在清代律例体系中的兜底性地位。(42) 三、“违制律”概括性功能的实证分析 前文多次论及,“违制律”在本质上是一款维护皇权的法律条文,设置它的本意是维护皇帝(有时包括太子和亲王)的制命能够得到遵守和执行。对于这一点,帝国的统治阶层也是十分清楚的。比如,在指导“庆历新政”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中,范仲淹曾建议皇帝要重视自己所颁命令的执行情况:“十曰重命令。仍望别降敕命,今后逐处当职官吏亲被制书,及到职后所受条贯,敢故违者,不以海行,并从违制,徒二年。未到职已前所降条贯,失于检用,情非故违者,并从本条失错科断,杖一百。余人犯海行条贯,不指定违制刑名者,并从失坐。”(43)又如,明朝名臣张居正在隆庆元年入阁后给明穆宗上奏了一封“陈六事疏”,其中第三条是建议穆宗“重诏令”: “伏望敕下部院等衙门,凡大小事务既奉明旨,须数日之内即行题复。其有合行议勘问奏者,亦要酌量事情缓急,道里远近,严令限期,责令上紧奏报。该部(院)置立号簿,登记注销。如有违限不行奏报者,从实查参,坐以违制之罪。吏部即以此考其勤惰,以为贤否。”(44) 隆庆二年,张居正又就“重诏令”问题上言: “伏祈皇上握宪贞度,不执乎私情,毋纷于浮议,是谓振纪纲。迩者天子号令,概从怠玩,伏望敕下部院诸臣,奉旨事务,数日之内即行题覆。若其了然易见,不用抚按议处者,便据理剖分。有合行议勘问奏者,酌缓急远近,严与为期注销。稽久以违制论。是为重诏令。”(45) 在列举的上述几条奏议中,范仲淹和张居正都是建议皇帝要重视自己令旨的执行情况,对违背、稽缓皇帝制命的官吏治以违制之罪。可以说,“违制律”在这里应用的是恰如其分。“振纪纲”,使天子号令不被怠玩,正是在帝国的律典中设置这款法律的初始目的。对此,帝国的统治阶层都是十分清楚的。 “违制律”之所以能够演化成为一款“概括性禁律”,最终还是由于它的性质所决定的。“制书有违律”是一款维护皇权的法律,它所要保证的是皇帝的谕令诏旨能够得到官民的遵行。我们常看到皇帝颁布谕令诏旨时,往往会在行文的最后警告:不遵行者,将“论以违制”或者“以违制论”。如果从“违制律”的法定含义来讲,皇帝这样讲是没有任何错误的,因为“违制律”本来是就是保证皇帝及太子的制书、诏书、令旨、敕命等不被违背或稽缓。但问题是,皇帝会针对国家和社会中的诸多事务颁布谕令诏旨,这些御用文书会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社会等各个方面。皇帝为督促这些御用文书被遵行而做出“以违制论”或者“论以违制”的警告,那么“违制律”便相应地适用到这些领域中,这是“违制律”能够演变成为一款具有广泛涵摄功能的法律条款的基础。 下面笔者将以清朝为例,从“谕令诏旨的法制化”和“遵循‘先制’”两个角度来分析“违制律”是如何从一款维护皇权的法律规则演变成一款具有概括性功能的法律规则的。 (一)谕令诏旨的法制化 1.首先看《大清律例》中几款涉有“违制律”的条例的来源。有些条例是奉旨纂定为例的,比如“荒芜田地”律中的规定有“盛京等处庄头,有将额拨官地率请更换,并民人呈请马厂垦种纳租等事者,照违制律治罪”的条例是于嘉庆八年奉旨纂定的。(46)之所以会产生这样一款条例,是因为嘉庆八年六月的晋昌等奏查勘新圈庄头呈请更换马厂地亩情形一摺: “庄头黎永贵等因原领新立屯地生长芦苇荒碱不能开垦,呈请将古同山等处马厂闲荒兑换,本与定例不符。且乾隆三十五年,曾经奉旨庄头等所种地亩,概不准另行拔补,自应永远遵行。今该庄头承种地亩,既查明并非碱片不毛之地,辄欲换马厂边沿,恐启觊觎肥沃之端。除此次违例恳请之庄头黎永贵等不准更换外,嗣后如有将额拨官地率请更换,并民人呈讨马厂垦种纳租等事,即著照违制例治罪。”(47) 在这条圣谕中,需要注意的是“且乾隆三十五年,曾经奉旨庄头等所种地亩,概不准另行拨补,自应永远遵行”一句,这或许是以“违制律”惩治那些请求更换额拨官地及呈讨马厂垦种纳租等行为的主要原因。当将这条圣谕内容纂定为例时,“违制律”也便出现在这款条例中。如此分析,可见“违制律”之所以出现在这款条例中,还是因为与皇帝的制命被违反有关。这款条例是这种情况,那么其它律例呢?当然,此款条例的情况并不能代表其他条例亦是如此。但通过此款条例,我们亦可窥探“违制律”这款本是维护皇权的法律是如何演变成一款具有概况性功能的法律的。当皇帝对某个事项颁布圣谕时,一般会警示臣民违犯圣谕的规定者,将被“论以违制”、“以违制论”。那么,当这条圣谕或者违犯此条圣谕的案件被纂定为例时,“违制律”便会出现在该款律例中。就如前文所言,皇帝的谕令诏旨有很多,涉及到的内容涵盖了当时国家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如此推论下去,“违制律”就具备了成为“概括性禁律”的前提条件。 2.又如“市司评物价”律的一款条例以“违制律”惩处米商囤积居奇的行为,即“各铺户所存米麦杂粮等项,每种不过一百六十石,逾数囤积居奇者,照违制律治罪。”此条系乾隆四十年,步军统领衙门奏准定例,嘉庆六年改定。薛氏按语:“若非图利贩卖,收买何为?既以十石上下分别定罪,已足蔽辜,似毋庸再行计赃科断。此专指平粜时而言(且系官米),若非平粜之时,即不引此例。官米亦然。此专言京城,外省并不在内。”(48) 其实,早在这款条例制定之前的乾隆十二年,“违制律”即在皇帝的谕旨中被用来规制囤积米粮的行为。该条谕令规定,无论城乡典铺,都不准囤积米谷等货。尚未粜卖者,谕令首出,官府照值官为收买,不予惩治。如敢隐匿不报,一经发觉,即照违制律严行治罪。(49)只是这里的“违制律”是针对这条谕旨而言的,是指如违反该谕旨所承载的关于禁止囤积米粮等货的制命,就得被科以“违制律”。这是恰如其分的,因为“违制律”的本源意义便是维护皇帝的制命能够被遵守执行,对违犯者进行惩治。而在乾隆四十年由步军统领衙门奏准的条例中,该处的“违制律”便成为专门惩处囤积米粮行为的法律。当然,因为条例毕竟是法律,其犯罪构成要件、适用的范围、规制的对象等都更为明晰确定。 如此一来,“违制律”也便在帝国的日常运行中成为被频繁用来惩治违法囤积米粮行为的法定法律了。比如,该条例在嘉庆六年修订时,皇帝在十一月壬寅的谕令中讲到:“至京师五城各铺户所存米麦杂粮等项,定例每种不得过八十石。倘逾数囤积居奇,即照违制律治罪。”(50)咸丰十一年十二月癸亥,在处理“良乡县属黄土坡郑吉祥等粮厂囤积居奇一案”的上谕中,皇帝声明:“嗣后各商运卸该处粮厂者,无论数目日期,准其自便。如遇五城平粜之时,仍照旧例办理。倘有逾数囤积,并迟至三月不行粜运者,仍照违制例治罪。所囤之粮,酌量平粜。”(51) 3.再比如在清王朝中后期困扰统治者良久的鸦片问题,“违制律”成为惩治走私、吸食鸦片及栽植罂粟等行为的法律。“匿税”律是咸丰九年督理崇文门商税事务衙门奏准的定例,以“违制律”惩处走私鸦片的行为。根据该条例的规定,商贩置办洋药时如有心偷漏,涉嫌走私,则照违制律杖一百。“巡役及各门书役,通同营私卖放者,与同罪。”(52)实际上,早在嘉庆十八年,清廷就曾颁布过严禁吸食鸦片的法令,名为《吸食鸦片烟治罪条例》,该条例规定: “侍卫官员等买食鸦片烟者即行革职,仍照违制律杖一百,再枷号两个月。军民人等买食者,俱杖一百,枷号一个月。太监违禁故犯者,立行查拿,枷号两个月,发往黑龙江,给该处官员为奴。其兴贩鸦片烟及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仍照旧律治罪。”(53) 《吸食鸦片烟治罪条例》的内容在《大清律例》中也有体现,即为“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律的一款条例。该条例规定:“洋药客商在铺开馆及别铺并住户开设烟馆,照开场聚赌例治罪。在馆吸食之人,照违制律,杖一百。房主知情,将房屋入官;不知者,不坐”。根据薛允升的研究,此款条例与另外两款条例本系一条,雍正七年制定,“原例系兴贩及开馆引诱之罪”。“嘉庆十七年,增人官民太监买食之罪。”原条例在道光十一年修改,道光十九年刑部议覆鸿胪寺卿黄爵滋条奏时改定,分为三条。同治九年复修前两条。”(54) 如此看来,此款条例中的严禁吸食鸦片的内容是在嘉庆十七年加入的,与嘉庆十八年《吸食鸦片烟治罪条例》的立法精神是一致的,两者都是以“违制律”作为惩处违犯者的法律。在司法实践中,不仅在馆吸食鸦片的行为可以被科以“违制律”,栽种罂粟的行为亦可被处以此法律。比如,同治七年说帖规定,严禁内地栽种罂粟花等类,“如违禁私自栽种者,即照在馆吸食鸦片烟,按违制律杖一百”。如栽种过多,情节较重者,还会被酌量加拟枷号。(55) 因为清朝的鸦片走私一般会涉及中外贸易,所以“违制律”在事关鸦片的中外贸易中有所应用。道光十九年五月己亥,宗人府宗令敬敏等建议了查禁鸦片烟章程三十九条,其中最后一条写到:“夷商住澳住行,卖货完竣,即饬遵照定限起程。如逾限久留,照违制律治罪。”(56) 通过上面的律例立法和司法实践可以看出,“违制律”在清朝中后期成为一款惩治鸦片犯罪行为的法定法律。对于这样一个对社会秩序有着极大扰乱作用的相对新生事物,律例中并无治罪明文,那么在这里适用“违制律”便是在发挥这款法律的概括性功能。而将这种适用法制化,则为“违制律”发展成为这一方面的专用法律提供了合法性基础。 4.清律中涉有“违制律”的条例具有不稳定的特征,比如“故禁故勘平人”律的一款条例是以“违制律”科责官员、衙役私设非法刑具行为的:“凡问刑各衙门一切刑具,除例载夹棍、拶指、枷号、竹板,遵照题定尺寸式样……一切任意私设者,均属非刑。仍即严参,照违制律,杖一百……”。根据薛允升先生的考证,此条例原系二条,其中一条系雍正五年的定例,分别于乾隆五年、嘉庆四年、嘉庆十二年、嘉庆十四年修改;另一条系乾隆元年的定例,原载于“决罚不如法”门。嘉庆十五年将两则条例修并成一条。(57)由此可知,此款条例在嘉庆十二年曾被改动过。 而在嘉庆十二年四月的一份谕令中,皇帝“申严地方官擅造非刑并捕役私拷之禁”,谕令各省问刑衙门,将本衙门中存有的此类滥置之非刑速行除毁,违者以违制论。“其捕役违例擅拷,尤当认真访查,有犯必惩,不可稍涉宽纵。倘再任听捕役私设刑具,地方官查禁不严,著该上司据实参处。”(58) 两相比较,我们可以确定两者之间的关系,即嘉庆十二年的这份谕旨内容在该年被立法者规定到“故禁故勘平人”律的上述条例中了,而“违制律”也便成为惩处相关行为的法定法律了。这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了体现。在道光九年发生于陕西的“知州非刑拷讯致犯受伤病毙”案中,阶州直隶州知州马嗣援在审理擅传经咒案件时,因案犯白法显不招供另一案犯白法仲的下落而“令皂役王有元等用木戒尺将其脚踝叠殴”,白法显被饬责五十下之多,伤至骨损,因病身死。法司认为,“木戒尺非例载刑具,脚踝亦非应行受刑之处”,最终刑部将马嗣援照“擅用非刑例”,杖一百,即行革职。皂役王有元等人照“下手之人减一等律,于马嗣援杖一百罪上减一等,杖九十”。(59)道光十九年,蒙古贝子德勒克色楞曾因擅用官刑而获咎。后在得知于得吉得以私造之刑具将绰克丹锁金□靠一事时,该贝子“默无一语,亦不即时送官惩办”,奕纪等将其照违制例议以革职。当然,皇帝姑念其系蒙古外藩,将其“量从轻减”。(60) 5.有时候,一些适用“违制律”的案件也会被纂定为条例。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待这种情况。第一个层面是,将“违制律”应用到这些案件中,说明“违制律”具有概括性功能;第二,将这些适用“违制律”的案件纂定为例,则又在立法层面扩大了“违制律”的适用范围。本部分主要是讨论谕令诏旨的法制化,所以不对案件法制化的情况进行深入探讨,现仅举一例来论证之。在道光十六年之前,《大清律例》并未对旗民结婚作何办理设置专条。根据户部则例的规定:“民人之女准与旗人联姻者,一体给与恩赏银两。旗人之女,不准与民人为妻,亦并无违者作何治罪明文。”在道光十六年发生的镶白旗汉军马甲德恒之母陈陈氏将次女许配与民人高祎保为妻一案中,清朝的司法官员便面临着“无法可依”的局面。对于此案,因双方“业经聘定”,故朝廷开恩“著准其完配”。但是,嗣后如再有此类情况当如何处理,朝廷认为应“明定条例”以为遵行,故“著户部妥议具奏”。户部议定的方案中将“违制律”和“违令律”应用到此类案件的处理中: “请嗣后八旗内务府三旗旗人内,如将未经挑选之女许字民人者,主婚之人照违制律治罪。若将已挑选及例不入选之女许字民人者,主婚之人照违令例治罪。民人聘娶旗人之女者,亦依例科断。至已嫁暨已受聘之女,俱遵此次恩旨,准其配合,仍将旗女开除户册,以示区别。俟命下纂入则例。”(61) 朝廷接受了户部的这一建议,并将之纂定为例,设置在“嫁娶违律主婚媒人罪”律下。薛允升在按语中指出:“此专为旗民结婚而设。《户部则例》尚有民人之女嫁与旗人为妻,及旗人娶长随家奴之女为妻妾,并旗人在外落业,准与该处民人互相嫁娶各层,应参看。”(62) (二)遵循“先制” 在帝制时期,皇帝是国家各项制度的法定源出者,他虽然可以在很多情况下超越帝国的各项法律和制度,但这并不意味着皇权不受一点约束。在皇权运作过程中,官僚体制、成规定例、祖制遗训、礼仪道德等都可以成为制约皇权的重要因素。(63) 在中国古代,祖制和先例是帝国的重要法源。所以,君主就当时国家和社会中的某些事项所颁布的一些谕令,除了会通过法制化这条路径将其固化为定制外,还会以作为“先制”的形式而在帝国的运行过程中得到遵循和援用。如果皇帝就某项事件或某些行为颁发了谕令,那么当该项谕令被违犯时,“违制律”便会理所当然地成为科责违犯行为的法律。如此一来,久而久之,“违制律”便会成为惩治这些事件或行为的法定法律。下面我们将以几项事例来展示这种演变过程。 1.嘉庆二十年发生在江西的邓六等因炒火药被烧身死一案,该案案犯任光世“在街市开设花炮铺”,被刑部照“违制律”拟杖一百。之所以照“违制律”科刑,是因为嘉庆皇帝曾在嘉庆十六年十二月初三日就类似问题颁布过谕令: “据步军统领衙门奏,查明崔大花炮作坊烧毙人口共有十五命之多,甚属可悯。向来制造火药,即官局俱在旷阔地方。此案民人崔大花炮作坊开设闹市,本属非宜,着五城逐一查明,俱饬令迁徙空闲处,所以昭慎重。钦此。在案。”(64) 《大清律例》中并无就此类问题做出过适用“违制律”的规定,所以任光世之所以被科以“违制律”,是因为他在街市开设花炮铺的行为违反了嘉庆十六年十二月初三日的上谕的规定。 2.嘉庆二十二年的预卖时宪书揽刻太阳经等书案: “刘大亨两次翻刻时宪书,并将太阳经等书一并刊刷售卖,因无加重问拟专条,咨请部示等因。此案刘大亨两次翻刻时宪书,于颁朔之前私行刊刷售卖,应钦遵谕旨,照违制律治罪。敬信录玉匣记等类并非禁书,亦无违悖语句,惟不应搀入时宪书内售卖,正与私刻地亩经之例相符,亦应照违制律治罪。”(65) “违制律”在此案中的两次应用并非是无“例”可循。对刘大亨科以前一处“违制律”,是因为嘉庆二十一年十一月,皇帝曾就黄三等人私刻时宪书的行为颁发过如何审拟治罪的谕令: “时宪书颁行天下,以便民用。若不遵钦天监推算,自行私造,干支错误,自应从重治罪。如照依监本翻刻,刑部并无治罪之条。其时宪书册尾所载伪造者依律处斩、如无本监时宪书印信、即同私造等语,实属虚设。即册面钦遵御制数理精蕴印造数语、现在钦天监推步之术,恪遵成法,由来已久,亦无庸特为标著。所有时宪书册面册尾两条,俱可删除。至各省所颁时宪书,向于每年四月初一日由钦天监豫将样本发交各布政司衙门刊刷,至十月初一日颁朔后颁行。近京一带,若由监颁行,势难遍及,或交顺天府募匠刊刷,照各省布政司之例办理。惟总须定于十月初一日颁朔以后,方准出售,若于颁朔之前,私行售卖,即照违制律治罪。”(66) 由上可知,在嘉庆二十二年的刘大亨案中,前一处“违制律”的应用是遵循了嘉庆二十一年十一月的一份相关谕令的规定。而后一处“违制律”的应用,则是援用了乾隆九年在“禁止师巫邪术”律中设定的一款条例的规定:“私刻《地亩经》及占验推测、妄诞不经之书,售卖图利,及将旧有书板藏匿不营销毁者,俱照违制律治罪。”(67) 3.根据规定,八旗官兵置买房地,应在两翼监督衙门投税;民人置产,则应在大宛两县。但是,很多旗人及其家奴在置买房地后,会潜赴大宛纳税,不好稽查。针对这种情况,乾隆皇帝根据刑部尚书德福奏请颁布谕令: “嗣后旗人无论官员及闲散家奴人等置买房地者,概令呈明该管佐领,在两翼监督衙门纳税,并令步军统领会同顺天府尹不时稽察。如有隐匿旗籍,私赴大宛两县纳税者,均以违制论。官员议处,闲散家奴鞭责发落。”(68) 此项谕令在123年后的光绪三十年的依然被法司比附援用: “光绪三十年十一月戊子,谕军机大臣等有人奏,左翼监督私卖禁地,请旨惩办一摺。旗民私卖禁地一案,宜经谕令袁世凯查办。兹据奏称各节,仍著该督彻底根究。镶黄旗满洲俄罗斯佐领荣辉著即解任,由该旗解往归案审办。左翼监督吏部左侍郎溥善未经查明,率准税契,实属冒昧,著交部察院先行议处。原摺著钞给袁世凯阅看。寻都察院议俄主教非旗民,何得在左翼投税?溥善咎无可辞,合比照大兴宛平县私准旗员投税,以违制论例,议以革职。从之。”(69) 4.道光十九年十二月,皇帝就旗人妇女的衣饰问题特降谕旨:“朕因近来旗人妇女,不遵定制,衣袖宽大,竞如汉人装饰。上年曾经特降谕旨,令八旗都统副都统等严饬该管按户晓谕、,随时详查。如有衣袖宽大及如汉人缠足者,将家长指名参奏,照违制例治罪。”(70)此处的“违制”应系指违犯皇帝上年特降谕旨中的制命。 5.嘉庆九年二月,皇帝就镶黄旗汉军秀女内有十九人缠足问题颁发谕令:“……著通谕八旗汉军,各遵定制,勿得任意改装。各该管参佐领等务按户晓谕,各该旗大臣不时留心详查。如有不遵定制者,即行参奏。倘别经参奏,不惟将该秀女父兄照违制例治罪,定将该管都统参佐领等一并治罪……”(71) 至道光年间,皇帝在谕令中再次强调对此类情况要适用“违制律”来治罪: “朕恭阅皇考仁宗睿皇帝实录,嘉庆九年二月内钦奉谕旨,镶黄旗都统查出该旗汉军秀女内有缠足者,并各该秀女衣袖宽大竞如汉人装饰,著各该旗严行晓示禁止等因。钦此。仰见皇考训诫周详,允宜永远遵守。……著八旗满洲蒙古汉军都统副都统等随时详查,如有衣袖任意宽大及如汉人缠足有违定制者,一经查出,即将家长指名参奏,照违制例治罪。(72) 在这两条谕旨中,“违制律”的适用都是为了维护嘉庆皇帝的禁令能够得到遵循执行。但是,道光皇帝在谕旨中的再次强调,则基本上是将“违制律”明确为此类情况的固定法律了。如此一来,“违制律”便演变成为涵摄到这一方面的固定法律了。 6.道光十年的巡役滥拿路过不应纳税车辆案也是此种情况: “崇文门散役杜瑞希图盘获漏税,藉可得赏。于距关二里外将并不进城之家眷车辆妄拿押送,将跟车家人孙兴私行拴锁,事发复敢逃匿。查崇文门税务曾经钦奏谕旨饬禁滥行需索,扰及行旅。该犯胆敢妄拿滋扰,实属违制,应即按律加等问拟。杜瑞应依违制律杖一百,加逃罪二等拟杖七十,徒一年半,在崇文门枷号两个月。徐良、魏三亦系散役,听从杜瑞妄拿滋扰,亦应照违制律杖一百,在崇文门枷号一个月。田瑞、刘贵系监督海巡家人,辄听从散役妄拿家眷车辆,不为阻止,乐二、张二并非在官人役,帮同杜瑞拦阻车辆,均应照不应重律杖八十。”(73) 根据案情表述可知,案中的杜瑞等一干涉案人员之所以被科以“违制律”,是因为皇帝曾就崇文门的税务特降过谕旨,饬禁滥行需索、扰及行旅的行为。而作为崇文门散役,杜瑞、徐良、魏三等人的行为恰恰违犯了皇帝的谕饬禁令,所以他们被责以“违制律”是恰如其分的。 总之,从根本上讲,“违制律”能够衍变为一款概括性禁律,最终的推动者还是皇帝。如果以“制书有违律”的内容为衡量标准,可以发现很多案件的当事人并未违反皇帝所颁布的任何谕令诏旨,但是他们还是被科以了“违制律”。对于这种情况,西方学者给出的解释是:“某人若实施某项行为——虽然皇帝并未颁布诏令禁止该行为,但这只是因为皇帝没有考虑到这种行为;如果皇帝考虑到这种行为,一定会颁发诏旨加以禁止——即构成违制罪”。(74)这种推理是有一定道理的。 根据《春秋左传》的记载,昭公六年(前536年)三月,郑国将刑法铸在鼎上。叔向派人送给子产的信中有这这么一句话:“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结合此信的上下文可以推知,这里“制”不是指“制度”或“法律”,而是指“先王”们的“命令”。信中所提到的“议事以制”是指“临事制刑,不豫设法”,使法律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统治者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进行权宜解释和司法适用,令民众“不测其浅深,常畏威而惧罪”。(75) “违制律”在深层次上体现了“叔向使诒子产书”中的“因事立制”、“临事制刑”、“议事以制”的法律思想。根据既有的研究可知,“制书”在出现之初便是一种承载帝王命令的御用文书。根据清律的注解可知,清朝“制书有违律”中的“制书”是对皇帝和太子的所有御用文书的泛称。所以,“违制律”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惩处侵犯皇权行为的罪名。(76)只是皇帝的制书类型这么多,行为违犯了皇帝的哪一份“制书”,该“制书”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该“制书”是否还具有效力等,则是不得而知的。这种不可预知的法制形态,确实可以令民众“不测其浅深,常畏威而惧罪”。 在帝制时期的中国,谕、令、诏、旨、制、敕等是基本法典之外的重要补充性和辅助性法律形式。由于制定法具有稳定性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整个国家的意志和公信力;而谕、令、制、敕等具有灵活性、适宜性的特征,更多反映的是君主的个人意志和喜好,所以两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的矛盾。(77) 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法律处于一种不可预知的状态,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处于一种人治的状态中,因为人们无法根据法律预知自己的行为是否构成违法,而统治者也可以根据自己统治的需要任意适用。从清朝“违制律”的立法内容和司法实践来看,人们即使没有违反皇帝的谕令诏旨等御用文书也可以受到“违制律”的惩罚,这就使这款法律处于了一种不确定的状态,成为一款统御工具。 概括性罪名泛滥是中国古代每个朝代都有的现象,这说明中国古代的法治特性是一种人治指引下的法治,其本质上是一种人治的社会格局。中国古代政治一直坚持“有治人无治法”(78)的统治思想,清朝的历代皇帝更是坚持这种重人治轻法制的治国理念(79),康熙帝就多次强调“从来有治人,无治法,为政全在得人”(80)。而“违制律”等概括性罪名赋予了皇帝和官员们对一些案件定罪量刑时的随意性和不可预期性,便是这种人治思想最好表现。 “违制律”从一款维护皇权的法律,衍变成一项具有无限涵摄功能的“概况性禁律”,便体现了这种人治思想。因为从法理上讲,“制书有违律”本身并不像“不应为律”那样具有原始性的无限涵摄功能,历代律典对它的适用主体、维护客体、主观要件、客观要件等都做了详细的界定。它的灵活性、涵摄性以及对帝国社会的广泛规制功能,是被统治者通过在谕令诏旨中频繁使用和不断立法的形式赋予的。通过这种方式扩大一款法律的涵括功能,本身便是一种将之视为统治工具的表现。 而且,“违制律”在清朝并没有十分明确的司法适用标准,断案官员可以根据具体情形相对自由灵活地适用“违制律”。在律无治罪明文时,在实现“罚当其罪”的量刑时,在对涉案人员实施象征性的惩罚时,“违制律”都可以被派上用场,这恰是其统御工具特性的体现。 另外,因为“违制”在根本上是一款维护皇帝的御用文书能够得到遵守执行的罪名,所以它还反映了中国古代文牍治国的传统。中国是一个政治早熟的国家,律法规制复杂而完善,然而由于奉行人治之王政,而非法治之宪政,所以国家的运转更多地依赖于长官的意志,其突出的特征就是文件治国。在政治生活中,国家和社会的运转往往不是依靠成文的律法制度,而是靠文件和指示来维系。文牍治国的实质是上峰的意见和指示大于法律。(81) 最后,要对“违制律”的最终命运做一个交代。在清末的司法改革中,虽然有很多罪名被删除,但是“违制律”却出现在制定的一系列新律中,比如在《大清现行刑律》和《大清新刑律》中都有保留。在实践中,直至宣统三年,“违制律”还在被皇帝用来警诫规训臣工。不过,正如前文所多次论及的,“违制”在本源上是一款维护皇权的罪名,所以它的命运是与中国的帝制制度相伴而行的。随着清王朝被推翻,在中国存续了数千年的帝制制度走向了终结,“违制律”也便失去了存续下去的法理依据。这款具有概括性功能的罪名,最终难逃灭亡的命运,恰是因为它是一款与帝制紧密结合的罪名。 注释: ①参见[美]D.布迪、C.莫里斯:《中华帝国的法律》,朱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65、166、181、404-405、420-423页。 ②参见管伟:《中国古代法律解释的学理诠释》,山东大学2008年度博士学位论文,第179-180页。 ③关于古代“违制律”概念的界定、源流的考证、历代立法与实践的梳理,参见杨立民:《制书有违:古代“违制律”的概念辨析与源流考证》,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4年第3期。 ④《大清律例》,田涛、郑秦点校,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58页。官方对“制书有违律”的注释中加入“故”这样一个限定词来限制其适用范围,可见这条律文的适用之广。但是在其他律例及具体的案例中,“故”这个关键词并未起到必要的限定作用。参见[美]D.布迪、C.莫里斯:《中华帝国的法律》,朱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版,第166页。 ⑤参见(清)薛允升著,黄静嘉编校:《〈读例存疑〉重刊本》(二),卷八,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207页。 ⑥(清)沈之奇:《大清律辑注》(上),怀效锋、李俊点校,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62-163页。 ⑦(清)沈之奇:《大清律辑注》(上),怀效锋、李俊点校,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62-163页。对于本条中的“制书”是否包括太后的令旨,《大清律例会通新纂》另有说法:“辑注凡称制者,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子令旨并同”。即该书认为制书包括太皇太后、皇太后与皇太子的令旨。这种说法是有待商榷的,因为该书的解释是以《大清律辑注》为依据的,既然如此,当以《大清律辑注》的解释为准。参见姚雨芗原纂,胡仰山增辑:《大清律例会通新纂》,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二十二辑,文海出版社1987年版,第767页。 ⑧参见(清)吴坛:《大清律例通考》,马建石、杨育裳等校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78-379页。 ⑨《大清律例》,田涛、郑秦点校,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540页。 ⑩关于“空白罪状”的研究,参见孙海龙:《论空白罪状在中国刑法中的命运——从刑法机能二重性看空白罪状和罪刑法定原则的冲突》,载《福建法学》2002年第1期。 (11)“概括性禁律”一词出自美国学者布迪、莫里斯在《中华帝国的法律》一书,参见[美]D.布迪、C.莫里斯:《中华帝国的法律》,朱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版,第420-423页。国内的相关研究参见王志强:《清代刑部的法律推理》,载王志强:《法律多元视角下的清代国家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4-86页;钱锦宇:《论中国古代刑法典中的概括性禁律——以〈大清律例〉为例》,载《求是学刊》2007年第1期;陈煜:《论〈大清律例〉中的“不确定条款”》,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年第11期;管伟:《中国古代法律解释的学理诠释》,山东大学2008年度博士学位论文。 (12)参见[法]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版,第24页。 (13)王志强:《论清代条例中的地区性特别法》,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14)参见林乾:《中国古代权力与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8页。 (15)(明)雷梦麟:《读律琐言》,怀效锋、李俊点校,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96页。 (16)《清世祖实录》,卷九,顺治元年十月甲子条。 (17)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三百八十七,乾隆十六年辛未三月戊子条。 (18)《清高宗实录》,卷五百四十,乾隆二十二年六月壬戌条。 (19)《清仁宗实录》,卷二百八十四,嘉庆十九年二月庚子条。 (20)《清穆宗实录》,卷四十,同治元年闰八月甲午条。 (21)《大清宣统政纪》,卷三十二,宣统二年正月二十四日。 (22)参见《大清宣统政纪》,卷五十二,宣统三年四月己巳朔条;(清)诵清堂主人:《辛亥四川路事纪略》,宣统三年四月十一日上谕、“资政院奏部臣违法侵权激生变乱据实纠参摺”。 (23)《清仁宗实录》,卷三十七,嘉庆四年正月甲戌条。 (24)《清仁宗实录》,卷五十,嘉庆四年八月丙申条。 (25)《清仁宗实录》,卷一百二十九,嘉庆九年五月丁酉条。 (26)(清)祝庆琪等:《刑案汇览全编·续增刑案汇览》(点校本),杨一凡、尤韶华点校,卷四,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02-203页。 (27)(清)薛允升著,黄静嘉编校:《〈读例存疑〉重刊本》(三),卷十七,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408-409页。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读例存疑》中的条例与《续增刑案汇览》的记载有两处明显的不同。第一,涉案犯人的名字问题。薛允升在该条例后面写了一条按语:“此条系嘉庆十九年,刑部具奏王三等贩运米石出城一案,遵旨恭纂为例,道光十四年改定”。但是根据《续增刑案汇览》的记载却是:“据东城御史孥获贩运粗米三石二斗出城之张三等移送到部。”即,涉案犯人的名字《读例存疑》按语中写的是“王三”,《续增刑案汇览》中记载的是“张三”。第二,根据《续增刑案汇览》的记载,条例中涉及粗米的部分方是在道光十四年通过该案纂定为例的,即:“仍先通行在京城各衙门遵照,并于修例时纂入例册。道光十四年奏准贵州司通行。”而薛氏按语的意思则是,这则条例系嘉庆十九年,根据王三等贩运米石出城一案纂辑为例的,只是在道光十四年改定。对于这两个区别,笔者不去过多考证,因为与本文的主体思路关系不大。在此指出,以示标记。 (28)“恶逆”包括殴及谋杀祖父母、父母、夫之祖父母、父母,杀伯叔父母、姑、兄姐、外祖父母及夫等行为。参见《大清律例》,田涛、郑秦点校,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85页。 (29)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三百二十六,乾隆五十四年四月辛卯条。 (30)《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三百二十六,乾隆五十四年四月辛卯条。 (31)(清)薛允升著,黄静嘉编校:《〈读例存疑〉重刊本》(二),卷五,成文出版社1970版,第131-132页。 (32)参见《大清律例》,田涛、郑秦点校,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页。 (33)参见(清)赵尔巽编:《清史稿·刑法志》,卷一百四十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186页。 (34)(清)薛允升著,黄静嘉编校:《〈读例存疑〉重刊本》(二),卷五,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131-132页。 (35)《麟趾新制》的这条规定颁布后,良吏窦瑗对其合理性产生了质疑。在经历与尚书省三公郎封君义的一番激烈辩论之后,此条终被废除。参见(北齐)魏收:《魏书·窦瑗传》,卷八十八,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08-1912页。 (36)参见(清)薛允升著,黄静嘉编校:《〈读例存疑〉重刊本》(二),卷五,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131-132页。 (37)(清)薛允升著,黄静嘉编校:《〈读例存疑〉重刊本》(二),卷九,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252页。 (38)参见《大清律集解附例》,卷四,载《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42页。 (39)(清)薛允升著,黄静嘉编校:《〈读例存疑〉重刊本》(二),卷九,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252页。 (40)(清)薛允升著,黄静嘉编校:《〈读例存疑〉重刊本》(三),卷十九,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445页。 (41)参见(清)许裢、熊莪:《刑部比照加减成案》,何勤华、沈天水等点校,续编卷二,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74页。 (42)对于“违制律”在清代司法实践中的适用特点、适用理念以及其概括性功能的实现方式等方面的研究,参见杨立民:《试论清代“违制律”的司法适用》,载《复旦大学法律评论》(第二辑),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324-359页。 (43)(宋)范仲淹:《范文正奏议卷上·治体·答手诏条陈十事》,钦定四库全书本。 (44)(明)张居正:《张文忠公集·陈六事疏》,《续修四库全书·集部·总集类·皇明经世文编》,卷三百二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页。 (45)(明)何乔远:《名山藏·典谟记二十九·穆宗庄皇帝》,卷二十九,《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杂史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66页。 (46)参见(清)薛允升著,黄静嘉编校:《〈读例存疑〉重刊本》(二),卷十,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285页。 (47)《清仁宗实录》,卷一百十四,嘉庆八年六月壬申条。 (48)(清)薛允升著,黄静嘉编校:《〈读例存疑〉重刊本》(三),卷十七,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408页。 (49)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二百八十六,乾隆十二年丁卯三月甲辰条。 (50)《清仁宗实录》,卷九十一,嘉庆六年十一月壬寅条。 (51)《清文宗实录》,卷十二,咸丰十一年十二月癸亥条。 (52)参见(清)薛允升著,黄静嘉编校:《〈读例存疑〉重刊本》(三),卷十五,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392页。 (53)《清仁宗实录》,卷二百七十一,第674页。转引自曲庆玲:《鸦片战争前清政府颁布的主要禁烟法令评析》,载《黑龙江史志》2010第21期。 (54)参见(清)薛允升著,黄静嘉编校:《〈读例存疑〉重刊本》(三),卷二十二,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521页。 (55)参见(清)祝庆琪等:《刑案汇览全编·刑案汇览续编》,杨一凡、尤韶华点校,卷八,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52-354页。 (56)《清宣宗实录》,卷三百二十二,道光十九年五月己亥条。 (57)参见(清)薛允升著,黄静嘉编校:《〈读例存疑〉重刊本》(五),卷四十八,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1205-1206页。 (58)《清仁宗实录》,卷一百七十八,嘉庆十二年四月己亥条。 (59)参见(清)祝庆琪等:《刑案汇览全编·刑案汇览》,杨一凡、尤韶华点校,卷六十,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121-3122页。 (60)参见《清宣宗实录》,卷三百二十一,道光十九年四月庚辰条。 (61)《清宣宗实录》,卷二百八十,道光十六年正月丙申条。 (62)(清)薛允升著,黄静嘉编校:《〈读例存疑〉重刊本》(二),卷十二,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315页。 (63)参见徐忠明:《皇权与清代司法运作的个案研究——孔飞力〈叫魂〉读后》,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64)(清)祝庆琪等:《刑案汇览全编·刑案汇览》,杨一凡、尤韶华点校,卷五十三,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795页。 (65)(清)祝庆琪等:《刑案汇览全编·刑案汇览》,杨一凡、尤韶华点校,卷五十一,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648-2649页。 (66)《清仁宗实录》,卷三百二十四,嘉庆二十一年十一月庚戌条。 (67)(清)薛允升著,黄静嘉编校:《〈读例存疑〉重刊本》(三),卷十八,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423页。 (68)《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一百三十一,乾隆四十六年五月甲午条。 (69)《清德宗实录》,卷五百三十七,光绪三十年十一月戊子条。 (70)《清宣宗实录》,卷三百二十九,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壬申条。 (71)《清仁宗实录》,卷一百二十六,嘉庆九年二月丁卯条。 (72)《清宣宗实录》,卷三百十六,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丁卯条。 (73)(清)祝庆琪等:《刑案汇览全编·刑案汇览》,杨一凡、尤韶华点校,卷十,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638页。 (74)参见[美]D.布迪、C.莫里斯:《中华帝国的法律》,朱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版,第422页。 (75)参见《春秋左传正义》,(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武英殿十三经注疏本,乾隆四年校刊,同治十年重刊,卷四十三,第18-23页。 (76)参见郑秦:《清代刑法概论》,载郑秦:《清代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7页。 (77)参见林乾:《中国古代权力与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2-108页、130页。 (78)《荀子·君道》。 (79)参见刘凤云:《“有治人无治法”:康雍乾三帝的用人治国理念》,载《求是学刊》2014年第3期。 (80)《清圣祖实录》,卷八十三,康熙十八年八月辛卯条。 (81)参见李俭:《权力的伤口:大清皇位传承内幕》,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1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