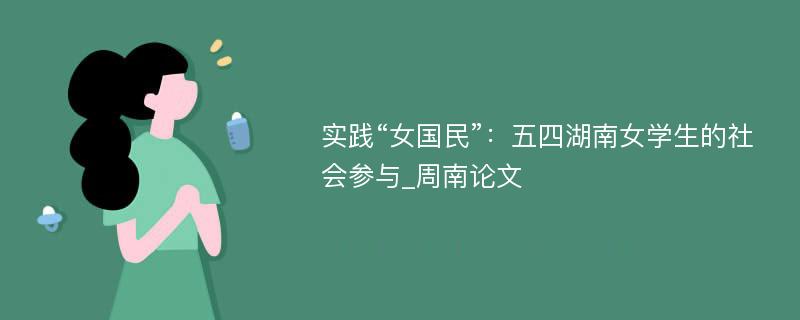
践行“女国民”:五四时期湖南女学生的社会参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湖南论文,女学生论文,国民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44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98(2011)05-0100-05
DOI编码:10.3969/i.issn.1007-3698.2011.05.019
在传统男权制社会,女性作为男性的他者(客体)而存在,几乎没有独立的个体身份(所谓的“在家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自然无法以主体身份与“国家”之间建立联系。近代中国,由于救亡图存和民族国家建构的紧迫需要,知识精英开始强调个体国民身份之重要性,为女性谋求新的身份认同开拓了话语空间和政治空间,为使其成为“女国民”而进行艰苦卓绝的努力,而早期女权主义者也往往通过塑造“女国民”的政治意象,以“同为国民同担责任”来论证男女平等要求的正当性。[1]成立于1903年4月的中国留日女学生共爱会,以“拯救二万万女子,复其固有之特权,使之各具国家之思想,以得自尽女国民天职”为宗旨,首次提及“女国民”一词,甚至将之提升为女子天职。后经晚清、民初知识界的阐发,该称谓广为流传,诚如研究者所言:“女子之先觉者,既为男女平权思想所激荡,对于国家与匹妇有责之义更不轻视,所以有女国民的教育思想。”[2]427-428显然,“女国民”之称谓是对女性身份的重新定位,它突破了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等级序列及单纯生物学的性别内涵,而把女子的性别与国民身份联系在一起,使女性从融于家庭集合体内的身份转化为个体身份,与以往传统的“贤妻良母”划清了界线。
众所周知,近代女权运动经历了戊戌维新揭橥,辛亥革命勃兴,至五四时期进入高潮这一演进历程,饶有兴味的是此中发生了或隐或显的转变,即晚清精英男性主导的“废缠足”、“兴女学”运动,至民国初年被知识女性参与乃至主导的妇女参政权、婚姻自主权、教育平等权等运动形式所取代,不仅实现了运动主体的置换,也使女权运动向纵深发展。在这一转换过程中,作为知识女性中最富朝气、最具群体性特征的女学生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由于以往研究偏重于精英女性,有关女学生群体的研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鉴于此,本文以女学生为表述中心,通过解读湖南女学生(尤其是周南女生)如何凭借五四运动这一契机通过践行“女国民”以完成女性主体身份的建构,进而理解女学生是怎样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冲破性别藩篱、成为独立的政治/社会主体的。
一、改组自治会,加盟新民学会,以谋女子政治参与权
五四前夕,中国的女子教育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教育宗旨仍囿于贤妻良母主义,湖南亦莫能外:“以周南女校、稻田师范两校的规模较大,历史也较久……这些女学校性质虽各不同,但有一点是完全一致的,就是向学生进行贤妻良母的教育。”[3]391值得庆幸的是,1919年秋,朱剑凡在周南大刀阔斧地实施教育改革,为改组原有的极具贤妻良母色彩的学生自治会创造条件。经民主选举,魏璧、周敦祥、劳启荣(时人称“周南三杰”)被推举为学生自治会负责人;自治会分设总务、学术、文艺、体育、风纪、游艺6股;各班设级长,寝室设室长,其他如图书室、校园、食堂,无一不实行自我管理。有了自治会做依托,周南学生开始以“女学生”身份冲破各种性别藩篱,以集体性行动参与社会变革,进而参与政治活动。
1918年4月,以蔡和森、萧子升、毛泽东为核心的进步青年团体新民学会宣告成立,宗旨为“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有会员提议“打破一切界限,无论男、女、老、幼、本省、外省、大学生、小学生,只要他的脑经(筋)受了这汪洋澎湃的新潮洗过,和宗旨相合,都是可以邀为会员的”,此举得到其他会员的赞同[4]106,故这个崭新团体吸引了追求进步的知识女性。翌年10月,向警予、陶毅、李思安、周敦祥、魏璧、劳君展、徐瑛加入学会,成为首批女会员。在当时男女社交尚未公开,风气十分闭塞的氛围下,他们的举动可谓惊世骇俗!为示庆祝,11月16日学会成员汇集周南召开隆重的欢迎大会。会后修改会章,在执行部下设“女子”、“留学”等部,李思安任副执行委员长,陶毅、周敦祥任评议员。1920年又有蔡畅、熊季光、吴家瑛、贺延祜等加盟。据统计,新民学会共有会员74人,其中周南师生20人;女会员19人,其中周南14人。①
五四运动爆发后,以女学生为主体的知识女性在长沙、衡阳、常德等中心城市活跃起来。6月3日,湖南省学联成立,周南、蚕桑派代表参加。“顷闻周南女校及省立第一女校学生以近日省垣各男校学生纷纷罢课,独女校未闻有罢课之举,遂闻开会议决”[5],6月6日,省立一女师、艺芳、周南等10所女校集会,成立长沙女学生联合会,推举唐冰瑜(艺芳)、周敦祥(周南)任正副会长,认为女子游行和讲演暂难办到,决定以联合会名义致函大总统,提出拒绝签字要求。② [6]这是湖南女学生第一次以集体的声音对国事发表观点,标志着女学生作为一个政治主体的出现。
尔后,女学生全力投入“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宣传。省立一女师发布《女学生提倡国会通启》,表示“我女界同人,分属国民之一,国家兴亡,与有责焉,纵不能挥戈杀敌,效力疆场,然抵制外货一端,则人人能尽之责。”[7]各女校相继组织国货贩卖团,走街串户,登台讲演,“各女生仿各男校办法,组织演讲、调查、交际、编辑各部,分股办事,无稍懈怠。惟其讲演方法与男校稍异,每日由演讲部轮流四五人,往各公馆对各太太奶奶小姐将某国如何虐待我国及抵制某货、提倡国货种种情形,仔细讲演,并劝平日所用之装饰品均须改购国货。”[8]6月17日,稻田、艺芳、福湘、益湘、涵德、自治、遵道、衡粹等11所女校组建女学生励进会,以“增进女界的幸福,提倡女子服务社会的能力”为宗旨,发行《白话周刊》,举办平民女子半日学校,致函总商会,要求推行国货,取缔奸商。
为抗议日本制造的“福州惨案”,12月4日,省学联在周南举行各校代表大会,决定实行总罢课。6日,第一师范、商专、修业、楚怡、周南等校率先罢课,接着70余所公私立学校教职员1000余人宣布罢课。12月中下旬,新民学会联合社会各界发起“驱张运动”,一面奔赴衡阳、郴州寻求军事援助,一面分遣代表出省争取舆论支持。据北京《晨报》报道:“昨日旅京湘籍男女学生,因对张敬尧摧残教育一事举行联合会”,商定驱张途径,推举出男代表9人、女代表3人;[9]3天后,“旅京湖南学生已近千人,并于一星期前组织旅京湖南学生联合会,竭力进行‘驱张运动’”,学生一面发电致各机关和团体声罪致讨,一面派代表至总统府、国务院和教育部请求撤张,更有湖南女代表放言“吾等誓必去张”。[10]在此,女学生以政治主体自许,无可辩驳地成为驱张运动中的积极参与者。
二、创办《女界钟》,倡导妇女解放,以争婚姻自主权
1919年10月,周南学生自治会创办校刊《女界钟》,周敦祥任主编,魏璧、劳君展任编辑,教师陶毅、陈启明从旁协助。据周敦祥回忆:“它的创刊是根据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性、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由我和劳君展、魏璧三会友办起来的。它作为《湘江评论》的补充,发出了湖南女界自己争平等、求解放的怒吼。”[11]522《湘江评论》作为省学生联合会会刊,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毛泽东任编辑,发表多篇有关妇女解放的文章,他在创刊号上痛斥男子对女子的压迫:“女子本来是罪人,高髻长裙,是男子加于她们的刑具;还有那脸上的脂粉就是黥文;手上的饰物就是桎梏……”在《民众大联合》中号召妇女团结起来,组建“女子的小联合”,去扫荡那破坏妇女“身体精神的自由的恶魔!”[11]522遗憾的是,《湘江评论》只出4期便被张敬尧封刊。有人提议:“《湘江评论》停刊了,我们不能换个名字出版吗?”不久,周敦祥、劳君展加盟新民学会,大伙儿借此决定创办《女界钟》以延续《湘江评论》之精神品质。可见,自诞生之日起,《女界钟》就肩负着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崇高使命。
事实上,《女界钟》不仅延续了《湘江评论》对妇女解放问题的探讨,且使之发扬光大。《女界钟》稿件大多来自周南师生之手。其中内容极其广泛,既有宣传抵制日货、反对奸商、抨击军阀官僚的,也有主张劳工神圣、实行民主政治的,但用力最多的还是宣传妇女解放、婚姻自主、经济独立等问题。创刊不久,长沙发生“赵五贞自刎事件”,《女界钟》特辟专号,展开婚姻自主权大讨论。师生从实地调查中获悉:赵“颇知书识字,性情温和”,“近四五年来,专在家攻刺绣裁缝,家中大小人等衣服皆此女自裁自缝……”赵父受媒婆怂恿,拟把女儿嫁给叫吴五的老板,赵对婚事“颇露不悦”,曾对嫂子说:“女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做女子真是背时呵!”但其父一意孤行,以致酿成悲剧。[12]可见,赵已认识到女性的屈从地位,但百般无奈下只能以自杀方式表达对包办婚姻的抗议。对此,陶毅痛斥道:“为什么偌大的世界竟容不得一个女子,生生的逼着他去死?……万恶的婚姻制度不知坑死了多少的女青年?”继而发出“自由——牺牲——奋斗”、“我们要自决”的呼声[13],鼓励女子奋力争取婚姻自主权。向警予将赵的个人悲剧视为旧婚姻制度下女性群体的悲剧,号召组建婚姻自决同盟,以团体的方式同包办婚姻抗争。
《女界钟》发行量最高时达5000份,不仅充分地展示了周南女生的主体性,如《新青年》上刊文由衷赞叹:“中国完全由女子倡导‘妇女解放’的杂志,恐怕这‘女界钟’为独一无二的了。”[14]而且推动了湖南乃至全国学生界对封建伦常制度尤其封建婚姻制度的大批判。
三、成立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组建海外大学女子请愿团,以争男女平等教育权
1919年下半年全国兴起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是青年知识分子为追寻国家现代化采取的重要举措之一。这场运动中活跃着女学生的身影,他们来自湖南、四川、广东、直隶、天津等地,其中湖南最多。10月,向警予从溆浦来到长沙,联合蔡畅、陶毅在周南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开设法文班。12月3日,将其扩展为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拟定章程,标举“实行妇女解放,劳工神圣,工读神圣”口号;在“认定体力工作与脑力工作兼营并进”的基础上,规定“会员须随时随地组合二人以上交互工读,每周须互有一次以上之阅读报告,须随时提出关于女子之问题互相研究,以其结论作为本会同人之主张,由本会印刷发行之”,要求会员克服“懒惰之习惯,奢侈之妆饰,邪僻之行为”。[15]12月25日,葛健豪、向警予、蔡畅、熊季光等6人启程赴法。各界人士数十人在上海送行,场面非常热烈,报界称之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史上一件别开生面的佳事”,“女子勤工俭学实为前所未有,亦中国女界之创举”。③
在向、蔡、陶等引领下,长沙掀起女子赴法勤工俭学活动的高潮,女子留法预备团、女学生留法补习班等团体相继成立,它们刊登招考广告(1920年3月1日),对招考目的、名额、方式、时间作出规定,如要求投考者体格强壮,有刺绣或图画之技能,能作浅近文字,能自筹湘沪往返川资等。[16]北京《晨报》称“闻报名的甚为踊跃,这也算是件好现象了。”[17]几天后,结果被公布:“参试者极为踊跃,取录各生,多系周南、稻田、涵德、崇实四校,惟该团经费有限,故于名额不能推广……正取生12名。”[18]3月17日,社会各界召开女子留法欢送会,“闻周南、稻田、涵德、崇实各学校及淑(旭)旦、新民各学会,连日开会欢送,甚为忙录(碌)。”[19]24日,魏璧、劳君展等人也踏上赴法勤工俭学旅途。据统计,从1919年3月至1920年底,全国留法勤工俭学女生20余人,湖南有12人,其中周南有7人。[20]
留法勤工俭学的湘籍女生在如饥似渴的求学之余,将男女平等教育运动由国内延伸到海外。针对海外大学的歧视性规定:“招收名额女生仅占全额十之一,又以考试制度与每年三百余元的学费阻拦女生”,向警予、蔡畅、魏璧为首联络12名女生,于1921年5月30日组成“开放海外大学女子请愿团”,发表《开放海外大学女子请愿团致女界全体书》(下文简称《全体书》)。[21]一面前往教育部、海外大学筹备处请愿,一面将《全体书》寄往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湖南《大公报》《旅欧周刊》等重要报刊媒体,寻求舆论支持。
《全体书》旗帜鲜明地倡导男女教育平等,提出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一是对“贤妻良母”及潜藏背后的社会性别制度发起猛攻。《全体书》指出:“女子秉历史的贤母良妻之沿革,以社会的贤母良妻之地位,受教育的贤母良妻之熏陶,其周围环境,无一非纳女子于贤母良妻之域者,故贤母良妻实为女子惟一归宿地;是以学校有所谓女子学校,教科书亦有所谓女子教科书,自小学以至高等大学,凡冠以女子二字者,无不含有女子之特质,即无不舍(含)有贤母良妻之特质。”其结果是:“女子中学女子师范毕业大多数不能考北大南高……是真社会制度与教育之过,而非女子本身之过也。”他们将“女子实力不足”归于不公平的社会性别制度,是对“男智女愚”成见的断然否定。二是强调请愿团旨在“为女同胞大多数失学者,谋根本解决之方”,提出男女名额平等或不加限制、免除考试、津贴学费三项要求,在逐一陈述理由的基础上,得出“女校未及男校1%,国家补足99%以上‘乃可言平’”的结论。三是指出作为20世纪的海外大学本应“扫除一切贵族式男系式的大学之恶习,而特别建设一种平民式两性式的大学之普遍精神”,它却逆时代潮流而行,是咎由自取。四是将他们的行动赋予社会价值,“夫海外大学解放运动,实为女子教育平等运动之发端,亦极重要之社会运动也。”
四、澄清同仁误解,创办平民女校,以达各界女性携手并进
1920年12月,励进月刊社署名“愚君”的女生针对《周南周刊》上登载的“周南女校想扩展势力,假代用省立女子中学的名义,把小学二年级学生,作为中学班一年级”一事,提出两点质疑:周南扩张势力是否有利于女子教育?湖南今日应不应有女子中学或代用中学?这无异对于“代用中学”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
作为当事人的劳启华等8名女生迅速作出回应,把共同签名的公开信付诸报端。[22]他们首先指出,中学一年级38人中新招者占90%,只有8名相当程度者(指自己)升入,而这些人“上学期已经将小学期限的学完,同人等在这个学期内本来要用中学的教材了”,据此质问:“德国近来所倡的‘能者升进’,我国招学规程也规定该通融办法,难道只准拿来投考他校,在本校就生成不能通用吗?”以国外先例论证此举的合理性。其次,他们指出,近年实施的教育改革取消高小,把小学教育年限由7年减至6年,中学则延长至5年,导致农村女生国民科毕业后无书可读,因受传统性别观念影响,家长绝无可能把“早晚是他人的人”(指女子出嫁)送进城里读书。在此种情形下,周南愿接纳“同人等做中学生”,说明管理者体恤民情,敢于担当。最后,提请励进社同仁分清敌友,携手共进,“吾们的敌人甚多,现社会的法律、风俗、习惯足以障碍吾人的前进者,更是不可胜数”,“我们都是女同胞识字中二千分之一的人,责任何种重大——我们抬头看看,那些熙熙攘攘的,那一个肯加入这第二火线来做我们的后援!我们此时只有互相携手,哪有同类相残之理!”
值得注意的是,此期的女学生开始关注占妇女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劳动妇女的利益,把争取他们加入妇女解放运动阵营视为要务。为此,女学生们走出学校,深入工厂、农村、矿山,创办劳动妇女补习学校、平民女校等。周南自治会、长沙女学生励进会等团体分别举办平民女子半日学校,进行文化补习和生产技能训练,灌输妇女解放思想、启发觉悟,使他们懂得要获取同男子平等地位,必须靠自己去争取的道理。
由是观之,在追求普遍人权的五四时期,女性作为国民应享有的权利与义务的渴望得到了广泛而充分的表达,尤其是女学生将“女国民”思想予以践行,使“女国民”变得有血有肉、具体而且生动起来。湖南《大公报》称“周南学生意志发皇”[23],《新青年》也赞不绝口:“因为这个学校在湖南本是最有精彩的,加以校长朱剑凡极力提倡‘新’的改造,所以一般学生的思想,与一般普通的人,大大不同。”[14]“意志发皇”、“大大不同”只短短八个字,却将周南女学生的精神风貌和主体性生动地勾画出来。周南的女学生如此,湖南乃至全国的女学生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无论他们是以“学生”为身份基础,与男学联合作,相互支持;还是以“女性”为身份基础,团结各界女性,共同行动,都践履着“女国民”这一主体身份,以致汇成声势浩大的“女国民”话语,主宰并影响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整个过程,为“新女性”(主要指职业女性)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集体登场制造了舆论氛围。
收稿日期:2011-08-18
注释:
① 参见韩文斌:《参加新民学会的周南师生》,湖南长沙周南中学校友会编。《春晖芳草(1905—2005)》(内部刊物),2005年。
② “致总统电”全文如下:“大总统钧鉴。鲁事紧急。漆室忧深。旦夕危亡。不忍坐视。涕泣陈词。签恳拒绝。签字力图挽救。长沙女学生全体叩。”
③ 参见《上海申报》,1919年12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