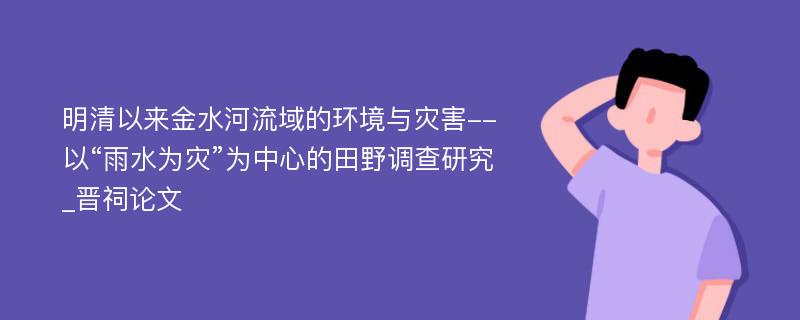
明清以来晋水流域的环境与灾害——以“峪水为灾”为中心的田野考察与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清论文,田野论文,灾害论文,水流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X2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873(2006)02—0010—11
引言:“时过境迁”环境史
全球范围内的环境和生态危机使现代意义上的环境史学科应时而生。
然而,环境史的学术渊源却比环境史要早了许多。伊懋可(Mark Elvin)认为:“作为一个有自我意识的研究领域,它的(笔者按指环境史)学术思想渊源也许可以追溯至十七和十八世纪的西欧,尤其是自然主义者、医官、和行政官员,他们关心全然不熟悉的热带环境,以及西欧人对这些环境之破坏”。① 德国学者约阿西姆、拉德卡则认为:“对历史学家来说,历史和自然的统一依然是一个古老而又十分有趣的梦。早在十九世纪的历史著作中,生物自然主义(Koselleck)就已经蔓延。批判的环境史恐怕开始于历史著作中早已存在的野史中”。② 如此看来,中国环境史的学术渊源更加悠久,即以第一部真正系统的史书《春秋》算起,至今也有两千多年的时间,遑论难以胜计的神话传说和“稗官野史”。如果将环境史的视野放得更加宏阔一点,我们是否可以说,自有文字记载以来,有关环境变迁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已成为史书的内容之一,中国环境史的学术渊源其实比西欧要早得多。“大禹治水”、“精卫填海”这样的传说故事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不也是非常重要的“文本”吗?
学科的产生其实是对现实的回应,亦即时代的产儿。现代学科意义上环境史的出现实在是日益严重的环境和生态危机催生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西方大国经济高速持续的增长,发展和破坏结伴而生:一方面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猛推进,一方面是由此而来的资源和原料的大量消耗。空气污染、水体污染、物种缩减、疾病增多、土地紧张、森林萎缩等等环境和生态问题日益成为社会经济繁荣背后的隐患,一种缺乏安全、甚至是危机四伏的焦灼感笼罩着地球上那块最发达的区域。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现实氛围中,人们开始反思自己赖以生存和习以为常的工业文明,以及这种文明带来的幸福与不幸。由是,席卷西方的“环境主义运动”越卷越大,以环境主义为理论指导研究历史上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的环境史应时而生。就像工业化的浪潮由西而东一样,环境史首先在美国呱呱坠地。包茂宏认为,以人类和环境相互作用为研究对象的环境史最早于1960年代在美国出现,其标志是海斯《保护与效率主义》(1959)和纳什《荒野和美国思想》(1967)两部著作的出版。③ 对中国环境史有组织的合作研究始于1993年年底由台北中研院经济研究所和澳洲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学院联合在香港举办的“中国生态环境历史学术讨论会”,此会的成果便是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的《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近年来,大陆史学界对环境史研究也开始重视起来,管见所及,师兄夏明芳用力甚勤,朱士光、萧正洪、王利华等人也有相关成果问世。2005年似乎是中国史学界的“环境史年”,笔者所知相关学术会议就有四个:“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南开大学);“人类社会经济行为对环境的作用与影响”(陕西师范大学);“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中国人民大学);“明清以来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变迁”(山西大学)。
然而,环境史是什么?环境史研究的范畴又是什么?对于这样一些关涉学科创立的基本问题事实上仍是众说纷纭,难有定论。梅雪芹在新近出版的《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中这样评断:“由于其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不长,因而尚难对环境史做出全面的总结和定论。即使环境史学家对于什么是环境史、如何界定环境史的对象等,也有各自的理解”。④ 1979年即出版《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并获美国历史学最高奖、近年来在国内颇得推崇的美国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曾诙谐地说:“在环境史领域,有多少学者就有多少环境史的定义”。⑤ 这里我们不必过多地去讨论学科意义上环境史的定义和范畴,看看实践层面上布罗代尔那部享有声誉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环境史之“宏阔”也足以让人“头晕目眩”。众所周知,这是一部体现布氏“三时段”历史观的代表作,其中“第一部分环境的作用”,“论述一种几乎静止的历史——人同周围环境的关系史。这是一种缓慢流逝、缓慢演变、经常出现反复和不断重新开始的周期性历史”。⑥ 这里涉及的“环境”包括山脉、山区、高原、山坡地、丘陵、平原、大海、海峡、陆地、岛屿、沙漠、绿洲、大西洋、气候、灾害、季节、流行病、交通、航运、道路等等,甚至还有资源、山民、水利、迁徙、城市、贫困、商队、侨商、经济、人口、粮食等内容。国内的环境史研究也相当宽泛,一篇综述“生态环境变迁史”的文章就涉及到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变迁之关系、古代都城与生态环境之关系、动植物变迁与区域沙漠化、灾害与疾疫问题、气候变迁等5个方面。⑦ 可以说,“很久以来,环境史常常以色彩斑斓的大杂烩的面目展现在世人面前”,⑧ 也可以说,现代意义上的环境史学科尚在成型的过程中。“草鞋无样,边打边像”,环境史只有在研究的实践中才能逐步形成自身的学科理论体系,并且确定其在史学园林中的地位。
环境史首先是一种“时过境迁”的环境史。结合国内环境史研究的现状,笔者以为,在环境史研究的起步阶段,以下几个问题尤其应当引起研究者警觉。第一,环境史应当“走向田野和社会”。“环境史的主要魅力在于,它激励人们不只是在‘历史的遗迹’,而是在更广袤的土地上发现历史”。⑨ 环境史研究需要“流浪者的目光”,需要研究者有敏锐的“问题意识”去发现、去体验环境变迁的历史。如果说,有些学科、包括历史学的一些专门领域可以在书斋和图书馆做出一流学问的话,环境史这样的实证性学科脱离开田野和实践是不太可能的。我们很难想象一个连现实环境状况都没有亲身体验、甚至“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者,怎样悬想和构筑出优秀的环境史著述来。第二,环境史研究要从区域史做起。环境几近无所不包,一个地区与另外一个地区也许有着迥然不同的自然环境条件,何况中国又是一个幅员辽阔、各种自然环境条件错综杂陈的国度。所以,“环境史的真正突破恐怕只有通过对各地区的实地调查研究才能实现”。⑩ 选择一个具体的区域进行田野考察和研究,也许是起步阶段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正途之一。第三,环境史研究要有“长时段”的眼光。环境变迁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缓慢过程,现实环境的恶化是长期积累和演变的结果。环境变迁过程中虽然不排除有地震、火山爆发等突发的灾难,但此类生态灾难往往会带来深远的环境影响。因此,环境史研究应关注自然环境长时期的演变过程,布罗代尔的“长时段”视角在环境史研究中应当是很好的借鉴。
基于以上对环境史的初步认识,本文试图在田野考察和文献解读的基础上,对明清以来晋水流域的环境变迁与水灾、特别是“峪水为灾”现象进行个案研究。不妥之处,尚祈指正。
一 “枕水际山”:晋水流域的环境要素
“环境”几乎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概念,它既属自然,又属人文。气候、土地、山脉、海洋、河流、森林、矿产、生物、作物、灾害等等都与之直接或间接相关。然而,对于一个具体的区域而言,除了气候这样的大环境变迁之外,每一个不同的区域都有其自身的环境特性,亦即决定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环境要素。环境史的研究应避免罗列各种环境因素的弊端,而应抓住区域环境要素,凸现区域特征,真正找出环境与区域社会变迁的脉络。“南涝北旱”本是一般意义上中国南北方的主要差异,但在北方也不排除发生严重水灾的可能。地处北方黄土高原的晋水流域历史时期也曾发生过严重的水灾,其环境要素就是方志中历来引以为豪的“枕水际山”的描述。
晋水流域以晋水得名,晋水即至今仍颇负盛名的晋祠园林中以难老、鱼沼、善利三泉汇合而成的泉水。此区域地处山西省会太原西南部,今属太原市晋源区,包括金胜、晋祠、姚村三镇和晋源、罗城、义井三个街道办事处。鸟瞰太原市区图,汾河自北而南贯穿其中,西南部晋水流域背靠西山,中有晋水四河穿流其间,再东即濒临汾河。“枕水际山”四字确是其地形特征的简要概括,同时也是决定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环境要素。
晋水的开发和利用历史悠久。史载,周贞定王十六年(前453),晋世卿智伯联合韩魏欲取赵氏晋阳城(今古城营村遗址),然晋阳城固若金汤,“三月不拔”,于是开渠决晋水而灌之,城中“悬釜而饮,易子而食”。后赵襄子与韩魏媾和反攻智伯,智伯兵败身亡,晋阳解围,三家分晋,战国纷争的局面由此拉开序幕,“智伯渠”也由此得名。汉代以后,当地民人开始利用“智伯渠”渠道旧迹,灌溉田亩。隋唐时期,晋水进一步得到开发,溉田面积进一步扩大,又两次修建跨越汾河的渡槽工程,将晋水引入对岸的东城。至此,北河、南河、中河、陆堡河四河渠系基本形成。同时,晋阳城经历代增充扩建,至唐代已形成横跨汾河两岸、由都城、东城、中城组合而成规模宏壮的“龙城”。
宋代晋水灌溉系统进一步完善,溉田面积达到鼎盛时期。时,太原尉陈知白鉴于“晋水奔流,溉田无多,诸多田畴,水虽能及,乃民皆惧以水增赋,悉不敢溉之为用,水竟付之东流”的现状,剀切晓谕,浚晋水水源为十分,并划定三七配水比例,使晋水管理有了简而易行的制度。于是,“凡溉田数万亩,民利于是大溥”。(11)
唐宋以后直至元末,太原城郊成为中原统治者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长期争夺交战的重地。923年李存勖建后唐定晋阳为“西京”;936年石敬瑭建后晋在晋阳称帝;947年刘知远建后汉又称帝于晋阳;951年刘崇建北汉也在晋阳。少数民族政权一溜烟的南下称雄,晋阳城郊一系列的建设与毁坏,真应了那“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名句。尤应指出的是,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赵光义第三次征讨北汉,竟放火焚烧经营千年的晋阳古城,次年又复演智伯旧剧,引晋水、汾水狂灌晋阳废墟,晋水又一次扮演了变利为害的角色。连绵不断的战事,使晋水渠系遭到严重破坏,争水冲突日趋激烈,所谓“水利虽云溥博,而水争则极纷纭”。(12)
宋毁古晋阳城后,筑平晋县城于今汾河东岸小店区城西村之东,明洪武初年平晋县城又被洪水所没,复徙县治于汾水以西晋阳古城遗址。洪武八年(1375),太祖朱元璋废平晋县为太原县,清代仍袭之。在晋水利用方面,明清两代用水制度更加严密,尤其是清雍正七年(1729),太原知县龚新特设晋祠总河渠甲一名管理晋水全河事务,同时增定禁饬事宜7款,从各方面限制规范渠甲权力,并通令各河一体执行,至此晋水流域各河渠及村庄普遍丈量田亩、清造《河册》,晋水总河及四河溉田村庄进一步明确:
总河:晋祠、赤桥、纸房。
北河上河:西镇、花塔、硬底、南城角、沟里、壑里、杨家北头、县民、古城营、罗城、金胜、董茹。
北河下河:赤桥、硬底、小站营、五府营、马圈屯。
南河上河:索村、东院、枣园头。
南河下河:王郭、南张。
中河:长巷、西堡、南大寺、三家、东庄、万花堡、东庄营。
陆堡河:纸房、塔院、北大寺、东庄。
以上赤桥村得总河、北河下河之水,硬底村得北河上、下河之水,东庄得中河和陆堡河之水。又,新庄村地处南河末梢,濠荒村、野场村位居四河退水的清水河畔,此三村虽无水例却沾晋水灌溉之利。这样,晋水实际灌田波及到流域共36村。晋水泱泱,惠泽三晋,历来是该地区经济发展民生富足的根本。乾隆年间以力争总河利益而“名扬乡里”的杨廷璇曾作一长联,表达的正是乡民对晋水恩泽的无限情怀:
溉汾西千顷田三分南七分北浩浩同流数十里淆之不浊
出翁山一片石冷于夏温于冬渊渊有本亿万年与世长清
杨氏这里所谓的“冷于夏温于冬”确是晋水的特质。现代科学测量表明,晋水水温常年为17.5摄氏度,并含有丰富的钾、矾等矿物质,加上晋水流域土壤肥沃而略带碱性,是北方地区少有的宜于农耕的“水田沃土”。晋水浇灌了源远流长的三晋文明,同时赐给了晋水流域特有的水利产业。
晋水流域最负盛名的农作物是因晋水浇灌的晋祠大米。晋祠大米在此特定区域水土的滋润下,洁白纤长,“味殊精美”。至今乡民仍称它与天津小站大米一样同为华北地区的米中珍品,甚至一度曾作为“贡品”。按《元和郡县志》“隋开皇六年,引晋水溉稻田,周回四十一里”(13) 的说法,晋祠大米至少也有1400年以上的历史。当地人称稻田为水田,又称稻畦。四周筑埂排列整齐依次灌水的一块块稻畦在晋水流域远看不可望极,刘大鹏说:“晋水所溉稻畦甚多,无虑数千百亩”。(14) 据载,1936年,晋祠大米种植面积共4319亩,平均亩产125公斤,总产量达100万斤以上。(15)
与晋祠大米一样得益于水土而闻名的是大寺莲藕。大寺以北齐创建崇福寺得名,分南大寺、北大寺两个村庄,毗邻晋祠,中河、陆堡河分别灌之。“大寺荷风”为晋祠著名的外八景之一,清代杨二酉“莲村千顷色,真作万荷庄”的诗句,描写的正是大寺莲藕景色。据称,大寺莲藕切开后丝长尺余,可谓“藕断丝连”,制成凉菜可存放七八日而色香味不变。旧时祁县、太谷、平遥一带商家字号逢年过节总要专程前来购买,甚至远销张家口、内蒙、北京、天津等地。(16) 大寺莲藕通常在春季芒种前后埋莲秧于稻田,故而有“水地则种稻与莲”之说。(17)
水磨业是得晋水之利的一大产业。据嘉祐八年《重广水利记》“碾竖之具鳞次而动”推断,晋水流域的水磨业至迟在宋代已经出现。晋水流域地势西高东低,水流湍急,利用水流的重力势能带动石磨加工粮食的水磨业由此形成。刘大鹏《晋祠志》载,晋水流域计有水磨65盘,其中北河13盘,南河10盘,中河28盘,陆堡河15盘。水磨加工粮食需经过水洗、去皮保持纯净,食品品质不易破坏,且有营养高、味道正、口感柔软香醇等特点,加之明清以来晋祠地区商业繁盛,人口集中,水磨业也有很大的市场需求,粮食和米面遂成为晋祠商业交易中的重要部分。“晋水之俗,富者以有水磨为美产,商人以守水磨为良业”,(18) 且“凡磨系面商居之,生意兴隆者,多日日磨面”(19)。若按每盘水磨每天加工2担面,碾3担米,大磨可磨面400~500斤计算,(20) 65盘水磨每年加工面粉至少当在500万斤以上,其数量也不可谓不大。
晋水流域另一个水利产业是传统的造纸业。由于造纸的原料主要是当地的稻秸和麦秸,故又称草纸。这种草纸的制作一般要经过石灰水浸泡原料、蒸草、洗草、粉碎制浆、水洗纸浆、手工捞纸、室外晒纸、整纸成型8道工序。(21) 可以看出,造纸的整个工序需要充足的水量来保证。这样,在晋水流域拥有特殊权利、地处晋水出口的总河流域便在造纸业方面具有了“近水楼台”的便利,其中纸房、赤桥历来造纸业十分发达。世居赤桥的刘大鹏在其《退想斋日记》中多次提到“里人生涯资耕作者十之一,资造草纸者十之九”以及乡民忙碌于造纸的情状:
吾里人民,皆资造纸为生,每岁秋季,家家户户各修晒纸墙,馆之左右,其墙甚多。日来里人鸡鸣而起,即来此间挑水和泥,天晓涂抹,一家抹墙,邻人相助,每日凌晨,馆之左右即人声鼎沸,亦里中幸事也。(22)
民国以后,造纸业虽有衰败之相,但仍为当地农业生产之余的收入之一。1935年的一份社会调查显示:时,纸房村制纸家数21家,占全村家数的47.73%,年收入6720余元;赤桥村78家,占全村家数的61.4%,年收入在2万余元(23)。造纸业虽系“小规模之手工业副业”,但一般家庭也没有足够的固定资本,“各村的资本,多数皆系他人投资,如纸房之资本,半数均系晋祠商人、农人所投”。(24) 赤桥村里没闲人,春夏秋冬生意浓。刮风下雨不能息,男女老幼作纸忙”。这首流行在当地的民谣,既道出了造纸人的辛劳,又蕴涵着温饱生活的惬意。
“枕水际山”的晋水流域,西面背靠的是吕梁山脉的东翼云中山。云中山所属太原地区的大小山脉,自南而北依次有苇谷山、蚕石山、尖山、象山、悬瓮山、天龙山、卧虎山、龙山、太山、婴山、蒙山等,当地人呼为“太原西山”,海拔一般在800~1800米之间,其中婴山石千峰1860米,系西山最高峰。西山诸山脉皆东北西南走向,由此形成大致呈东西走向线性排列的九条山峪,当地人又称“西山九峪”。西山九峪自南而北依次是南峪、黄芦峪、柳子峪、马房峪、明仙峪、风峪、开化峪、冶峪、西峪,其中柳子峪、马房峪、明仙峪、风峪四峪位居晋水流域正西面。步入晋祠,拾级而上,对面群山耸立,一望无际,山与山之间宽度不一的深沟,即民人所称之“峪”。
西山诸峪富有矿藏,尤以煤、矾、铁、硫磺等矿产闻名。道光《太原县志》有卧虎山出“石炭”;尖山“产矾出石炭”;风峪“出石炭石灰”;明仙峪“出石炭”;马房峪“出矾”;柳子峪“出石炭出矾”的记载。(25) 位居晋水流域的西山四峪除马房峪稍短外,其它三峪一般在10公里以上,峪底宽度在40~100米左右,其实也是一种季节性的河流。
枕水际山的特定自然环境,长期以来是晋水流域乃至整个山西境内最美的胜景之一,它带来了美景,也带来了富足,其景其状历来为文人墨客赞叹不已。明代曾官至尚书的太原人王琼有一首《刘大尹邀游晋祠次韵》的诗篇,道出的就是乡人的满足与快乐:
山城西去未十里,风景翛然趁野心,古寺楼台行处近,前村烟树望中深。
闲情似可忘声利,世事何劳问昔今,珍重吾邦贤令尹,四郊春雨布棠荫。(26)
然而,特定的环境既可造福人类,也可以给人类带来灾难,利弊之间其实也只是在特定的时空之间。如果说,宋元以前晋水流域或占地肥水美之位,或得政治中心之利,大体是处于相对繁盛上升时期的话,那么,明清以来“枕水际山”的环境要素就给晋水流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特别是频仍不断的“峪水为灾”日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大患。
二 “峪水为灾”:明清以来的环境恶化与灾害
光绪三十二年(1906),毗邻晋祠的赤桥村士绅刘大鹏在太谷南席村票号商人武佑卿家塾中完成了洋洋上千万言的《晋祠志》,其中第41卷“故事”有一则标题即“峪水为灾”,读之不禁令人悚然:
同治十三年甲戌夏四月二十三夜半,大雨如注,倾盆而至,雷电交加,势若山崩地塌。明仙、马房两峪,水俱暴涨,马房峪更甚。晋祠南门外庐社田园,淹没大半。淹毙男女五、六十口,骡马十余匹,猪羊鸡犬数十头。他乡载煤车夫六、七口,有又许多骡马牛驴。明仙峪淹毙者惟他乡之车夫五口,骡马十数匹而已,佥谓山中起蛟,致有此患。(27)
接着,刘大鹏描述了自己亲眼目睹的灾后惨状:
当是时,余年十八,诘朝偕二三父老抵里南涧河,睹淹毙之车夫,脑浆并裂者二,死尸未损者三,且有死牛死马数头。既而诣晋祠南门外,目击死尸纵横,男女老少不一,其人有母抱幼稚子女同衾而毙者,有父子昆弟同床而殁者,有夫妇姐妹同室而殂者,有覆压于倾屋败垣者,有漂流于稻畦麦陇者。哀哭之声,惨不忍闻。百十人家只有数家被灾而未殒一命,热闹里閈,一夕遂成荒墟,令人为之怅怅。(28)
事实上,“峪水为灾”并非始自同治年间,也不限于明仙峪和马房峪。征诸地方文献,明代以前晋水流域水灾主要是由于汾水暴涨或改道所致,明清以来则是汾水峪水交相为害,尤其是之前不见史载的峪水灾害明显增多,且为害巨大。据方志记载,明洪武、嘉靖年间,清乾隆元年(1736年)、十七年(1752年)、二十二年(1768年)、四十年(1775年)风峪都曾发生过较大水灾,其中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初三日夜,大雨如注,风峪水暴发,浪高数丈,怒吼如雷。西郊尹公祠戏楼逐波倾圮,居民庐舍为之一空,坏西城四十余丈”。(29) 当然,地处黄土高原的晋水流域明清以来也曾发生过不同程度的旱灾,但“峪水为灾”却成为愈演愈烈的灾害主流。如此状况必有其特殊的自然和社会原因。
明清以来晋水流域的“峪水为灾”现象表面上看是由于暴雨形成的自然灾害,但其背后却是明清以来本地人口、资源、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人口增长——资源紧张——无度开发——环境恶化——灾害频发是一个持续连环的过程,我们并不能因为人口、资源、环境三者看似简单的排列组合而去否定其历史存在。笔者4年前曾撰文呼吁从社会史角度研究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史,并从区域史的角度对山西的有关问题作过简单讨论。(30) 其实,晋水流域就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个案。
自明初以来晋水流域就出现了一个人口持续增长的过程,此种人口增长除去当地原有人口的自然增长外,还有一股不小的外来人口迁入浪潮。有关晋水流域36村人口增长的具体数据,文献记载缺失,看看太原县的数据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考。道光六年(1826)《太原县志》载明代洪武年间全县人口53719;永乐年间50228;成化年间51652;嘉靖年间79068;天启年间81200;清代顺治年间27339(丁);康熙年间31735(丁);雍正年间34762(丁)(31);乾隆年间人口213434;嘉庆年间220928;道光初年224253。县志总结说,明代洪武至天启近三百年“所增不过三之一”,清代顺治至道光初年即“视明季几三倍之”。(32) 可以看出,其间虽有明嘉靖年间的小幅波动,但整个趋势是一个不断增长且增幅越来越大的过程。
明清以来晋水流域的人口迁入首先是明洪武年间即已开始的“明初大移民”。明代初年,太原是北方重要的“九边”重镇之一。朱元璋在全国取得政权之后,即封三子为晋王,晋水流域的古晋阳城废墟及其周边地区成为明初军屯的重要场所,流域内的古城营、五府营、小站营、东庄营、马圈屯、河下屯、古寨、西寨、武家寨等村庄名称本身就与明初军屯直接相关,至今本地仍有“九营十八寨”的说法流传。按明代卫军制编制,太原驻屯一卫三千户所,粗略估计屯田数和军户数均在两万以上,占到当时太原县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强。(33) 另外,在明初的移民浪潮中,晋水流域也吸收了不小数量的外来移民,尤其是自本省南部北上的“大槐树移民”。征诸地方文献,结合田野考察所得,我们可以判断晋水流域许多村落和地名的出现都在明清以后,其中明初洪洞“大槐树移民”占有相当数量:
王家庄位于风峪沟内,传说明永乐年间洪洞王姓男子率两个侄子来此定居,村随姓氏,遂名王家庄。
南堰村位居晋水北河下游末端西北处,村中最早的家族崔姓也在明初从河北博陵郡中转洪洞大槐树而来,随后子孙繁衍,就近迁居,又有毗邻的中堰、北堰出现。
南界冶峪沙河的吴家堡村,最早的赵姓相传也是洪洞大槐树移民。
明初白、程、李三家自外地迁至晋水南河下河的大村王郭村偏北处,遂有三家村村落的形成。
三家村附近的东庄,明代曾有高汝行任浙江按察使副使,并在村南建有花园,以此而有万花堡村。
西山九峪之最南峪即名南峪,传说明洪武年间有名阎毡片者由大槐树迁来,故此村又称阎家峪。而位居阎家峪西边的槐树底村即以大槐树移民得名。
槐树底村再往西的圪塔村,相传最初的居民也来自大槐树。此村因附近山丘犹如圪塔,故名。
与南峪诸村隔汾河相望的高家堡、大元、田村相传都是洪洞大槐树的移民等等。
明代初年大量军屯和外来人口的迁入,加重了晋水流域的人口压力。接踵而之的便是流域内不同利益集团对有限资源的激烈争夺,其中对人民赖以生存和生活的晋水资源的争夺达到了有史以来的高峰。系统分析晋水开发和利用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明代以来晋水四河范围内总河与分河、同河村庄与异河村庄、上游村庄与下游村庄为争夺水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各类“水案”明显增多,而且冲突的程度愈发升级。官方和民间在争夺水资源的过程中,不仅诉诸了实际的权力和武力,而且还利用了意识层面上水神的力量。(34) 在严重人口压力下对水资源激烈争夺的同时,地处平原区的部分人口、尤其是不断迁入的外来人口开始向风峪、明仙峪、马房峪、柳子峪等附近山地进入,成为缓释人口压力的另外一条途径。正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如前所述,西山诸山区富有煤、矾、铁、硫磺等矿产资源,不宜耕作却利于开采。大量人口由外地和平原地区的进入,首先开始了对这些矿产资源的土法开采。昔日少有人迹的宁静山区逐渐为“叱牛声、喝车声、刈煤声、运煤车马声”所替代,昔日鸟兽出没一片绿色的情景亦为“灯火荧荧,通宵灿烂”的煤、矾厂矿的火苗所取代。(35) 有关西山诸峪最早矿厂的出现时间也许可能在明清以前,但具体的矿厂见诸文献的是在乾隆年间,刘大鹏在《明仙峪志》中提到一处“水窑”曰:
据山人言:乾隆年间,太谷李某携资来峪,凿山成窑,采取煤炭,矿极精良,获利甚厚,数年于兹,被众羡慕。窑内之水另穿一穴而泄,名曰水道。……水由窑出,因改李家窑之名,竟呼曰水窑。(36)
刘氏《明仙峪志》和《柳子峪志》均成书于1920年,而且亲自在两峪分别经营石门、西坪两煤窑数年,自称“与峪人相周旋,业经数年于兹,颇于峪中情形历览焉而了然于心目。”(37) 所记当为信史。检索此两志,可见煤、矾等厂矿已成星罗棋布漫山遍野之状。以下便是两志所载的大小矿厂:
明仙峪:磺窑口、灰坡、水窑、矾窑崖、老窑沟、老窑、官窑坪、大小官窑、石门窑、石门沟矾厂、黄老岫煤矿、槐条沟“煤窑数座”、前当窑、后当窑、大小长沟“旧窑数穴”、造矾厂、流水泉新旧煤窑数处、前坡窑、梨树沟“煤窑两穴”、坟儿沟窑、烧饼窑、南北大青窑、得坪窑、南窑沟、悬瓮洼窑、白云窑、前后瓦窑。
柳子峪:木鸽湾窑、娃娃窑、道德窑、大龙桥铁厂“三、四处”、红渣窑、杨杞沟窑、威坡矾厂、巍坡窑“煤矿矾矿并出一窑”、桑涧窑、鹿窑、李家窑、大眼窑“煤矾并产”、大瓦沟窑、庄子坡窑、硫磺矿窑、下水窑、窑头村煤窑、矾厂、南窑、窑头、洗脸盆窑、肥美新窑、东窑、西窑、隆庆窑、核桃树沟窑、北岔“设立煤厂数处”、上岔口窑、南坪窑、大窑沟、十字河沟“煤窑颇多”、双庆窑、西坪窑、李家窑、阜财窑、康家窑、天顺窑、新筒窑、黑山窑、肥美窑、南岔沟煤窑及矾厂、义合窑、南边窑、平地窑、宏窑、崖头矾厂、小窑、四亩地矾化博窑、杨树沟窑、上灰沟窑、下灰沟窑、东沟窑、东窨窑、西窨窑、园子窑、小南窑、大观窑、黄楼村五煤窑(隆庆窑、二泰窑、后北窑、枣间窑、南湾窑)、康屹岨窑、庆成要、洪福窑、马家窑、石成窑、永成新窑、老窑湾、继成窑、李家窑、王家窑、水巷窑、川沙河沟共计煤窑九(敦远窑、南坪窑、北大青窑、南大青窑、中屹岨窑、万成窑、南北洞儿窑、圪台窑、合成窑)、柳圈沟煤窑共三(西坪窑、东坪窑、肥美窑)、铲石沟“煤窑数穴”、井筒窑、石盒窑、永成窑、后菜坪窑、中菜坪窑、前菜坪窑、顶天窑、大顺窑。
以上所摘明仙峪、柳子峪各煤矿、矾场早者起自乾隆、嘉庆年间,晚者在刘氏所记的1920年代。在此近200年中,采矿的高潮又集中在乾嘉和清末民初两个时段。乾嘉时代是有清以来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晋水流域明代以来又吸收了数量不少的外来移民,这是人口向山区进发的主要原因。清末民初的开采高潮则与政府鼓励有关。查清末民初各地商人在晋水流域诸峪投资煤矿者渐多,甚至有江浙一带商人“集资万金”前来开矿者,(38) 正所谓“新政既兴,而矿业又盛”也。(39)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大量小煤窑的开采,不仅吸收了相等数量的矿主、矿工、运煤车夫甚至骡马牛驴,加重了山区的给养能力,而且吃水乱挖、烧饭伐薪、道路开凿等等行为又恶化了山区的环境,土法开采、屡开屡废对煤炭资源造成极大浪费,以柳子峪平地窑为例:
咸丰、同治年间出煤正旺,煤质亦佳,所出之炭均系大块,人争购运。至光绪初年,即露衰象。未及窑中不适,非但频遭火患,而且水满其中,遂成废窑,歇业二、三十年。民国成立之初,又有人开采,竟仅在近处采取遗剩之煤,不得入其煤矿实处取之。(40)
造矾与采煤相比较,其对水和木材的消耗更甚,而且制造时间较长。架锅安灶、火烧熬煮、洒硝水洗都对环境带来一定影响。这种情景在刘大鹏的一首诗中有具体描述:
太原九峪产煤优,矾矿多产柳子沟。
釜灶铺陈空谷口,池塘设置半岩中。
煎熬春季生成夏,停止冬时造作秋。
用水煮淘兼用火,加硝才使汁能稠。
柳子峪中出产蕃,厂开涧侧即逢原。
依峰靠嶂安锅灶,甃石和泥作水盆。
日日曾将硝质洒,天天竟把矿苗翻。
几经熬煮几经洗,数月方才造就矾。(41)
大量人口的涌入和煤矿、矾场的开采,使西山地区的森林植被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原来生态条件良好、植被茂密的地区在不断的人为活动中日趋恶化,这样的例子在刘大鹏的著作中可谓俯拾皆是:如槐条沟“以槐树多生于沟故也。深不盈里许,而有煤窑数座”,由此“畴昔沟中尽古槐”变为“于今树木何稀少”。(42) 木林沟“一沟深邃,树木成林,故以为名”,“浓荫宏深,希见曦影。鸟则为巢栖之,兽则窟宅以駓骀。峪人恐有恶虫凶兽,潜伏其身,致遭其害,将木渐次砍伐,俾树凋零,今不成林矣”,所谓“昔日成林今不林”。(43) 不该忘记的是,西山地区自北齐以来就已是著名的风景胜地,此地树高林密,草木繁盛,加之山涧溪水潺潺,经年不断,元以前仍有“路转花溪不踏尘”的景况,明清以后生态环境逐渐演化成为一幅“有草无树,草亦不繁”的童山秃岭画面,思之不禁令人长叹。
西山地区环境变劣的另一个表征就是诸峪水情的恶化。可以想见,大量煤矿、矾场的开采,尤其是井筒式煤窑的开采,必然导致地下水层的破坏。加之山区黄土极易冲刷,植被又遭破坏,一旦暴雨来临,必然形成山洪爆发,沙石俱下的状况。明清以来,为防御“峪水为灾”,各峪口普遍加修石堤,“以束峪水”。柳子峪口“盛夏大雨,山水暴涨”,“口外中为涧河,南北各甃石堤,以束峪水暴涨。石堤延袤七、八里”。(44) 明仙峪也是“峪口之外,左右修筑石堤,以束峪水”。(45) 风峪“遇夏暴雨,每侵城郭,筑堤障之”。(46) 这里的“城郭”即指明清以来的太原县城,亦即故晋阳城遗迹。此县城地势低洼,恰处西山风峪口之下,每逢夏秋汛期,风峪山洪爆发,便有被淹之虞,至今相传农历五月二十七的城隍庙会俗称“漂铁锅会”,意即每遇洪水,锅碗瓢盆到处漂起。县城西门外“乱石滩”,也以风峪山洪冲刷河卵石而名。据县志记载,明成化年间原筑防洪沙堰被毁,正德年间重修;嘉靖七年复坏又修;二十一年又坏又修;乾隆初年堰北截冲毁85丈,十七、十八两年南截冲毁45丈,直至乾隆四十一年又大修,置地扩充,运石添灰,始少纾山洪。(47) 事实上,西山诸峪口都有不同程度的沙石堆积现象,以致晋水灌区各河渠道堵塞,影响灌溉,伤农误时,终无良策。刘大鹏谈及鸳鸯口的情况时感慨良多:
鸳鸯河为中南两河要害之区,而大小神沟所退之山水适当其处,凡遇大雨,山水暴发,二沟沙石随山水而下,遂将鸳鸯口淤塞,水莫能流,两河皆涸,甚至冲坏水平及三角尖。每岁每次挑浚疏通,费工甚巨。往往际农忙之日出此巨工,中南两河人民日趋该河口挑浚,或当需水孔急之时(稻田不可一日无水,至蓝田则时时用水),则挑浚尤不容缓,必也夜以继日。除沙石而疏水通,其害农事良非浅鲜,历年久远,无策可除。(48)
“环境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很简单,即在所有的地区,如果当地居民没有能力控制资源,限制外来人口,环境就会恶化”。(49) 这一结论同样适合于我们所讨论的明清以来的晋水流域。人口增长、资源紧张、环境恶化三者之间有其必然的联系存在,我们并不能以其看似简单的排列而否定其历史和现实的事实。明清以来随着军屯和外来人口的大量增加,晋水流域的自然资源、尤其是民人赖以生活和生存的水资源日趋紧张,西山诸峪进而成为开发的对象。而西山诸峪大量煤、矾矿的土法开采,又带来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的后果,这就是明清以来西山诸峪屡次洪水泛滥成灾的主要原因。
三 “长时段”:并未完结的演变过程
同治十三年(1874年)明仙峪、马房峪洪水大灾才过两年,晋水流域便同样遇到光绪初年波及秦、晋、豫等北方地区的大旱灾。不同的是,虽然此次灾害山西受灾最重,但太原地区、尤其是资晋水灌溉之利的平原区相对受灾较轻,而西山诸峪及山区村庄却受到严重打击。人口亡失严重,煤窑大都荒废成为灾后山区的普遍现象。刘大鹏在《明仙峪志》中专辟户口一则,对灾前灾后户口进行比较,其问亦深切:
明仙峪中村庄凡四:曰明仙村,曰瓦窑村,曰上白云村,曰下白云村。昔年家给人足,生齿甚繁,煤窑、矾厂,各村皆旺。至光绪丁丑(三年)岁大祲,道馑想望,晋人死亡大半,山村更甚,竟至十分之八九,而一峪人民遗留无几,数十年来元气终莫能复。辛亥(宣统三年)变后,政号共和,而峪中户口仍旧寥寥,温饱之家十之一二,穷苦之家十之八九,凋敝情形殊堪恻悯,非但无读书之士,而且无识字之人。……四村之人男多而妇少,而且有一男即为一户者。均藉开采煤矿为生计。峪中煤窑为数无多,亦无畅旺之窑,并无造矾之厂,虽有丁男,均作窑黑子,生计艰难,莫能娶妻生子,则户口何以能多,生齿何望其繁乎?(50)
应该说,山区人口灾后亡失严重且长期难以恢复,与山民只靠挖煤而无耕作直接相关。不仅如此,“峪水为灾”还给晋水流域带来了严重而长期的消极后果,这就是一些村庄的消失和大量农田的毁灭。晋祠镇和长巷村中间的西堡村就是一例。《晋水志》载,西堡村原“有数十家,后渐减少,届同治十三年仅存数家而已,是年四月二十三日夜,雷雨大作,马房峪水暴发,涧河横溢,只留一家,人仅一口。逾三岁至光绪三年大祲,一家亦亡,村随减其河务,归并于长巷村。”(51) 这样一种趋势在光绪初年自然灾害后并没有停止。1921年,晋水《河册》保留了因峪水暴发和汾水泛滥而减少的村庄和田地数字,这里不妨抄录如下:
民国期间,晋水灌溉村庄三十一个,灌溉面积二百六十顷十六亩,民国期间比清代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浇地村庄减少四个,计有西堡村、野场、东庄营、马圈屯。浇地面积减少六顷四十八亩,考察其减少原因,主要有二:其一,西边山各河沟山洪暴发,冲毁水地不能耕种,有八个村共减少水地面积十三顷二十亩,其中:晋祠一顷八十四亩、纸房五十三亩、赤桥一顷五十三亩、金胜一顷四十亩、索村一顷九十九亩、王郭三顷、南张二顷二十三亩、北大寺九十七亩;其二,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汾河大水泛滥,太原城郊土地被淹,十室九空,惨不忍睹。这次汾河泛滥使汾河岸边的土地大为淤高,部分土地不能引晋水灌溉,而退出晋祠水例,计有七个村庄,减少浇地面积四十九顷二十八亩,其中:小站营十顷、小站二顷五十亩、马圈四顷五十亩、五府营三顷六十九亩、万花堡二顷十三亩、东庄十一顷八十六亩、东庄营十四顷六十亩。(52)
新中国建立之后,晋祠水权统归国家所有,1951年传统的“渠长制”为晋源县水利委员会所取代。1951年秋,灌区开展“反水霸、反封建水规、反本位主义”的三反运动,以亩计征,按作物需水轮灌、跟水行浇的灌溉办法彻底取代了旧有的浇水轮程制。同时,灌区进行了一系列渠系改建、渠道防渗、平田整地等工程建设,大大提高了晋水的浇地面积,扩大了晋水的受益村庄。据《晋祠水利志》言,灌溉面积由建国前的1733公顷发展到2800公顷;受益村庄由建国前的31个发展到42个。(53) 然而,1960年代以来,随着工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及流域区内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晋水流域又一次出现了用水紧张的严重矛盾。1960年春,太原氮肥厂开始投产,晋祠泉水第一次大量用于工业生产,当年流域粮食即减产91万斤。1962年,氮肥厂在明仙峪、兰居寺、难老泉三处所凿7眼深井开始抽水,骤使晋水流量大幅下降。1972年,晋祠三泉中的善利、鱼沼二泉干涸。1970年代后期,清徐平泉、梁泉两个自流井及洞儿沟自流井的启用,使晋水流量进一步减少。再过20年,难老泉最终熬到老期,于1993年4月30日彻底断流。(54) 如今,“晋祠大米”不仅种植面积大为减少,而且此大米已非彼大米,资晋水之利而形成的传统水磨业、造纸业也随晋水流量的减少而没落,我们只能在田野工作中寻找到零星的旧水磨和造纸工具。想想两千多年来哺育三晋文明滋养民众生产生活的滔滔晋水竟然无情断流,读读诗圣李白那“晋祠流水如碧玉”,“百尺清潭写翠娥”美妙诗句,再瞠目定睛品味至今难老泉亭明人傅山所题之“难老”匾额,真令人徒生今昔之感!
还有不能不提的是,明清以来形成的西山诸峪植被破坏、树木减少、滥采滥挖、山洪肆虐等现象非但没有停止,且有愈演愈烈之势。1920年代,刘大鹏在《明仙峪志》、《柳子峪志》中描述的许多地方仍泉水流溢、树木苍翠的情景已一去不返,甚至那些本身就富有水草之美的地名,如今乡老人山也难见其迹,或者干脆在记忆中磨灭。我们还是以当时刘大鹏眼里“九峪之最劣者”之明仙峪为例,看看80年前一些地方的生态状况。滴水岩“其水淙淙滴滴,逾崖下泄,响答山谷”;桃沟“其中桃树可数十株”;酸枣沟“沟名酸枣气澄清,荆棘纷披不可行”;姑姑洞坪“旁则老松屹峙,如掌华盖”;明仙村“层峦叠嶂间栋宇相望,桑梓接连”;柏树岩“柏树若霁,俨如翠屏”;条子洼“嘉卉灌丛,蔚若邓林”;流水泉沟“其水清洌,饮之甚甘”;梨树沟“山高沟浅白花迷,其实离离树缀梨”;下白云村“住居枣树林中”;桃园“春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秋则桃之离离,红碧错杂”;蘑菇坪“蘑菇丛生,飑飑纷纷”;香树坪“香树灌林蔚若邓林”等等。(55) 显然,民国时代明仙峪生态环境已大大不如明清之前,但较之再后的岁月仍略胜一筹。民国以来,阎锡山地方政府虽将植树作为“六政三事”来抓,但明仙峪经过明清以来数百年的滥垦滥挖,宜于植树的地方竟然寥寥无几。《明仙峪志》有“树木”一则曰:
民国成立以来,政重森林,年年官令各处栽种树木。吾晋尤重斯政,明仙峪人家稀少,虽奉官令春季栽树,究之所植无多,而宜于植树之处,亦寥寥无几,故植数年见效未多。(56)
建国以后,虽然政府大力推进植树造林,近20年来又有专门的“植树节”,但在西山山区及诸峪效果并不明显。如今除个别如天龙山一些山间可以看到少量松柏树木外,大部分地区已无森林可言,只不过零星灌木、荆棘、杂草而已。
更为严重的是,对西山诸峪煤、矾、石等资源的无度开采,其规模程度都大大超过以往,环境恶化的后果也更加严重。以风峪为例,1958年人民公社时期,风峪八村就普遍以集体所有制形式开办煤窑,采矿的办法仍然沿用传统的“树枝状”。1960年代开始使用机械采煤。1980年代后,西山地区的矿产开发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峰,仅风峪一地政府批准的煤矿就有近20家,私采私挖的小煤窑更是漫山遍野。现晋源区水务局局长在《风峪沙河水利资源》一文中也直言不讳地写道:“流域店头村以上为沙页岩土石山区,一般杂草、灌木植被较好,沟掌有少许森林,地下多煤层,沟底煤窑较多,约60-70座,沟内到处可见矿口、煤堆、矿渣、污水,又黑又脏。店头村以下为质岩土石山区,植被较差,因此石料场较多,可以说到处开山采石,植被破坏严重,石料场约有20余个,石膏窑6-7个,沟内开窑开矿,往来运输,甚是繁荣热闹,嘈杂和尘土飞扬。”(57) 可以想见,一个流域面积只有不足40公里的风峪山区,却有百余座煤窑、石膏窑、石料场分布其间,真到了千疮百孔满目疮痍的地步。还有,1980年代后,太原市最大的煤矿集团西山煤矿集团所属官地矿和白家庄矿均在西山地区开始大型开采,造成严重地表塌陷和地面裂缝的后果。据2000年的一份调查显示,要子庄和周家庄两个行政村塌陷最大长度达500-600米,宽度120米左右,要子庄东南出现严重地面裂缝,在约35米宽度范围内有四条平行排列的地面裂缝,其裂缝宽度在1米左右。(58) 地表塌陷不仅使土壤退化和土地生产力下降,而且使地下水和地表水发生不同程度的泄露,进而影响水循环,导致井泉干涸,水源枯竭,环境恶化,居民生存生活的基本条件受到威胁。1980年代后,赵家山、箱子沟、店头、程家峪、王家庄、田家庄、黄冶村、要子庄、周家庄等所谓“风峪九村”至今已全部迁出山外另建新村。明清时代人口向山区进发定居开采,如今人们迫于环境的压力又不得不迁出山外,一入一出,沧桑百年。笔端至此,能不浩叹!
晋水流域“峪水为灾”的现象建国以后也没有彻底根除。实事求是地说,建国以来,各级政府从兴利除害,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大局出发,对西山诸峪进行过多次大规模的治理,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开挖新河、疏治河道、加固堤防、植树造林、小流域治理等等措施可谓应有尽有,发动组织群众、设法筹措经费、解决木材、钢材、水泥等建筑材料问题等亦可谓不遗余力。但由于山区生态环境日趋恶化,每遇山洪,尤其是特大山洪,仍不免造成严重水灾。现在明仙峪口河床已高出两岸村庄3-5米,柳子峪沙河下游已无固定河道,洪水漫流为三条沙河,水灾的危险仍不能免除。据新修当地方志载:1956年8月暴雨,风峪、柳子峪、开化峪三条沙河13处决口,沿线许多村庄受灾严重;1975年8月底,西山及晋祠一带两日连降暴雨,沙河决口,150余亩土地被冲毁;1981年7月,风峪沟山洪再次暴发,泥石大泄,洪流每秒40立方米。卷走马车2辆,拖拉机3台。(59)
世纪之交,科学发展观已成为举国上下的伟大实践,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开始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重视。时值夏季,在驱车前往晋祠的太汾公路上,远眺西山,布满山野的幼嫩树木已依稀可见,难老泉的泉水据说也已开始复出。只是,人们在欣赏之余仍不免一份忐忑。
生态环境与自然灾害是一对互相作用的孪生兄弟。自然灾害可以造成生态环境短期或长期的危机和恶化,良好的生态环境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防止或减缓灾害的发生和受灾程度。反之,生态环境的恶化可以促使或加剧灾害的发生,灾害的频繁发生又会加剧生态环境的恶化。明清以来晋水流域环境与灾害的演变过程,只是一个较小区域的个案,但它映照的却是一个普遍的历史事实。环境演变虽已“时过境迁”,历史的教训却应警钟长鸣。
注释:
①伊懋可《导论》,载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上),台北中研院经济研究所2001年12月版第1页。
②[德]约阿西姆、拉德卡著,王国豫、付天海译:《自然与权力——世界环境史》,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1页。
③参见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载《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
④梅雪芹:《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⑤参见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载《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
⑥[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唐家龙等译:《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上卷),商务印书馆1998年5月版,第8页。
⑦佳宏伟:《近十年来生态环境变迁史研究综述》,载《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
⑧[德]约阿希姆、拉德卡前揭书,第6页。
⑨⑩[德]约阿希姆、拉德卡前揭书,前言第2页。
(11)刘大鹏著,慕湘、吕文幸点校:《晋祠志》(上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78页。以下仅以《晋祠志》出之。
(12)刘大鹏:《晋水志》卷2,旧制。稿本复印件现存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13)《元和郡县志》晋阳县。
(14)(17)(18)《晋祠志》(上册),第125页,第127页,第138页。
(15)太原市南郊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太原市南郊区志》,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96页。
(16)胡克毅、魏民主编,张德一撰稿:《晋源史话》,北岳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340页。
(19)《晋祠志》(中册),第953页。
(20)按,晋祠地区一担面约有168市斤。参见郝润川:《晋祠水磨》,见杜锦华主编:《晋阳文史资料》第5辑,第246页。
(21)郭华:《赤桥传统造纸》,载王海主编:《古村赤桥》,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3月版,第179-188页。
(22)刘大鹏遗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版,第46-47页。
(23)刘容亭:《兰村、纸房、赤桥三村之草纸调查》,载《新农村》第3、4期合刊。
(24)见刘容亭上揭文。
(25)道光《太原县志》卷2,山川。
(26)引自《晋祠志》(中册),第718页。
(27)(28)《晋祠志》(中册),第1039页,第1040页。
(29)道光《太原县志》卷2,城垣。
(30)行龙:《要重视从社会史角度研究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史》,《光明日报》2001年12月4日。《开展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史研究》,《山西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31)清代人口统计单位前后不一,“丁”仅指16至60岁的“成丁”。一般研究者认为,丁与口的比例约为1∶5。参见行龙:《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1章“人口数量的演变”。
(32)道光《太原县志》卷3,田赋。
(33)袁汉城:《九营十八寨与明军屯考》,载《晋阳文史资料》第6辑。政协太原市晋源区文史资料委员会2002年9月印行。
(34)参见拙文《多村庄祭奠中的国家与社会——晋水流域36村水利祭祀系统个案研究》,载《史林》2005年第4期。
(35)(36)《晋祠志》(中册),第1138页,第1120页。
(37)刘大鹏:《明仙峪记序》,见《晋祠志》(中册),第1102页。
(38)(39)(40)(41)(43)(44)《晋祠志》(下册)第1247页,第1243页,第1403页,第1409页,第1406页,第1214页。
(42)(45)《晋祠志》(中册)第1137页,第1107页。
(46)道光《太原县志》卷2,山川。
(47)道光《太原县志》卷2,水利。
(48)刘大鹏《晋水志》卷2,第10页。
(49)参见[德]约阿希姆、拉德卡前揭书,第3页。
(50)《晋祠志》(中册)第1177页。
(51)《晋水志》卷3,水利,第12页。
(52)(53)转引自《晋祠水利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19页,第3页。
(54)以上均见《晋祠水利志》第6章,晋祠水利大事记。
(55)以上均见《明仙峪志》,载《晋祠志》(中册)。
(56)《晋祠志》(中册),第1182页。
(57)见《晋阳文史资料》第7辑,2003年12月“风峪专辑”。
(58)王献民(晋源区国土资源局局长):《土地复垦项目状况》,见《晋阳文史资料》第7辑,“风峪专辑”。
(59)太原市南郊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太原市南郊区志》,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3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