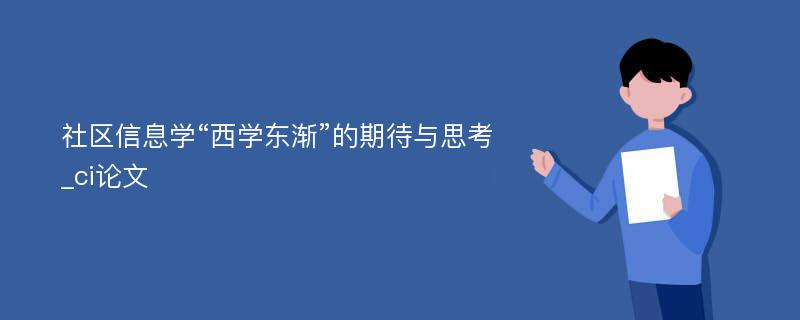
Community Informatics的“西学东渐”——期待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学东渐论文,期待论文,Community论文,Informatics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Community Informatics(CI)在英文文献中的使用始于上世纪末,用于表达当时西方学术界初具规模的一种研究兴趣和应用领域,即将现代信息技术运用于社区发展的研究兴趣和领域。它在汉语文献中首见于2010年[1],是被作为一个新兴学科的名称引介的,存在两种不同翻译:“社群信息学”和“社区信息学”。2010年以后,由于我国学者的介绍[2-7]和西方同仁的推广(特别是两位美国学者Kate Williams和Abdul Alkalimat通过暑期学校、合作研究及学术交流在我国开展的推广工作),这个概念及其表达的学科开始被更多学者所关注。尽管截至目前,有关CI的介绍多于应用,但围绕CI的翻译、介绍、培训及推广工作,已经在我国启动了一段典型的西学东渐过程。
在引进CI之前,我国事实上已经存在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推动社区发展的实践和研究,即已经存在与CI兴趣相同的领域,只是这些实践和研究多以“社区信息化”和“农村信息化”的名义而开展。社区信息化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2006年以后进入较快发展时期;农村信息化起步更早(以金农工程为标志),“十五”开始加速。在这样的背景下引进CI,我们几乎必然遇到的问题是,对我国而言,CI之新究竟新在哪里?我们究竟要引进什么?
如果我们到英语文献中探究上述问题的答案,就会发现,英文文献提供了两种不同的CI定义。第一种比较宽泛地将CI定义为将现代信息技术(ICT)应用于社区发展的研究和实践,即嫁接现代信息技术和社区发展的整个领域(包括ICY接入与培训、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在线医疗卫生服务、信息获取、社区论坛等)。例如,Gurstein将CI定义为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增强社区发展的各种应用[8]11;Williams等将CI的关注焦点确定为社区与数字技术的交互,包括社区如何创造和利用技术影响社会和个人生活[9]9。如此定义的CI至少从表面上看与我国的社区/农村信息化相重叠。第二种定义更加具体地将CI界定为一种由社区(包括基层政府和社区组织)实施的、支持社区发展的活动领域,即“为了社区成于社区”(for communities and by communities)的ICT应用。例如McIver将CI定义为:一个正在形成的跨学科领域,该领域涉及那些致力于解决社区问题、由社区设计或联合设计的信息系统的开发、利用和管理[10]33。如此定义的CI与我国的社区/农村信息化存在很大差异:社区/农村信息化虽然包括部分“为了社区成于社区”的ICT应用,但很多(甚至是更多)属于“成于政府”或“为了政府”(即为了管理)的应用。
回顾CI的历史[9,11]可以发现,“为了社区成于社区”的确是贯穿CI发展历程的基本导向;对此,即使是按第一种方式定义CI的学者也不否认。西方CI的直接源头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90年代的社区ICT应用活动。当时,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已经开始在教育、企业和政府部门得到广泛应用,对于坚信社区繁荣是个人、家庭、社会兴盛的前提的人来说,将现代信息技术运用于社区生活的各个方面,以激发社区(特别是贫困社区)的发展活力,使之成为信息社会发展的强健基础,已经成为顺理成章的期待。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很多社区,都出现了支持社区日常交流、民主参与、信息获取、教育培训、医疗卫生等活动的系统或平台[12-13]。这些早期系统或平台的开发者,大都是社区内部或周边具有社区活动经验的专业人士和社区组织。他们一方面秉承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社区振兴思路,另一方面秉承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中的参与设计思路,特别关注与社区经济、社会、历史、文化、人口相适应的ICT应用,也特别注重社区成员对ICT开发过程的参与。这赋予早期的社区ICT项目显著的“为了社区成于社区”的特色。20世纪90年代后期,虽然很多国家的政府为了消除数字鸿沟,自上而下地启动了一些全国性项目,但在项目落地的社区,社区情境和社区参与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ICT的落地设计、实施和使用。例如美国技术机遇项目(Technology Opportunities Program,TOP)资助的600多个社区ICT应用,就各具特色[14]。20世纪90年代末,当Gurstein等学者开始采用CI概念表达这类ICT应用及相关研究的时候,“为了社区成于社区”已经成为CI不言而喻的特征。因此,即使不将这一特征显性地写进CI定义,它依然被隐含在CI内涵当中。正是这种内涵的CI,构成了2010年以后我国CI学者引介的对象。
如此理解的CI对于社区、ICT以及二者的结合持有特别的见解。有关社群信息学的著述[8,15]对此已有详细阐释,在此仅举数例。首先,CI与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社群主义一样,认为相对于整个社会和家庭及个人,社区具有优先发展和研究的价值,因为强健的社区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家庭及个人福祉的前提。因此,CI关注的焦点是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的社区,这意味着各个可界定的社区整体上构成了CI的分析单元和增强目标。这引导CI更关注那些可以为整个社区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带来活力的ICT应用领域(如促进社区就业的电子商务、促进社区民主的讨论平台等),也更关注整个社区的历史、文化以及资源对ICT利用效果的影响。其次,CI与网络社会理论一样,认为现代信息技术构成了当代社会的重要生产力,网络构成了当代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当代社会因而被称作网络社会)。它同时认为,ICT对于振兴那些被网络社会的流动空间所排斥的社区,具有巨大潜力,是信息时代推动社区发展的重要力量。网络社会的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是当代社会学家、网络社会理论的作者卡斯特的概念[16-17],与场所空间(space of place)概念相对。传统的场所空间是按地理方位及其毗邻性而划定的空间,而流动空间则是由通讯、交通运输、计算机网络等设施安排而构建的空间。一个企业的总部与其所在地的居民和中小企业共处一个场所空间,但同时与它分布在不同地区或国家的生产部门、销售部门、研发部门共处一个流动空间。在卡斯特看来,在信息社会(网络社会)中,流动空间对组织社会生活、划分社会结构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以企业为例,借助于发达的通信、运输、计算机网络,一个企业不再要求它的决策部门、研发部门、生产部门彼此毗邻,而是可以将其决策部门设在世界经济中心,生产部门设在劳动力低廉的国家或地区,销售部门设在市场需求旺盛的地方,研发部门设在创新活动聚集的地方,所有部门可以通过通信与运输网络实现即时交易与沟通。因此,在网络社会中,一个人群、社区、国家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取决于它在流动空间的位置,即取决于它对各类网络功能产生的价值。很多人群(如无技能人群)、社区(如农村社区)、国家(如非洲国家)由于对主流网络了无价值而被流动空间所排斥,沦为信息社会的最底层。CI相信,通过在贫困社区运用ICT技术,可以提高它们对主流网络的价值,将它们重新纳入主流社会的流动空间,实现社区振兴。再次,CI认为,产生于社区成员交往活动的社会资本是社区发展的重要资产。在ICT应用过程中,社区成员及集体的社会资本既是ICT有效利用的条件也是ICT投入的回报。作为条件,社会资本可以促进社区成员的相互学习和技能传授,推动社区成员对ICT的采纳;作为回报,社会资本是ICT投入的收益之一,表现为社区交往的增加、社区参与度的提高、社区互信的增强、社区对外来资本吸引力的增长等。正因为如此,CI注重ICT应用对社会网络的嵌入,即注重联结具有交往关系的成员及其组织,融入各类社会网络的日常交互。第四,基于上述见解,CI强调ICT的普遍应用,因而特别关注社区内部以及社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数字鸿沟,强调公共设施(如图书馆、学校)在弥合数字鸿沟中的作用。
关注我国社区/农村信息化的人不难发现,无论对城市社区还是农村社区,上述见解都蕴含着有益的参考价值。根据相关研究的结果[18-19],目前我国社区/农村信息化中实施的ICT项目普遍存在以下问题:缺乏针对地方情境及需要的功能或内容,缺乏实际应用效果,缺乏公众知晓度,缺乏可持续发展力。正如前面的介绍所显示的,CI恰恰以动员社区参与、植根社区情境、关注社区赋权见长,有望为解决我国社区/农村信息化的上述问题提供重要启迪。
截至目前,CI西学东渐的进程还基本停留在图书馆情报学领域,但鉴于CI的两大支点——社区和ICT——涉及广泛的领域,因此在明确了CI内涵、主要思想及创新之处后,我们将不得不面对与CI采纳相关的更加复杂的问题。首先,由CI提供的新视角、新思路和新方法应该成为谁的视角、思路和方法?是把它作为我国社区/农村信息化的指导思想,用来改造已有的社区/农村信息化思路;还是把它作为图书馆学情报学参与社区/农村信息化的工具,用来补充已有的思路?其次,如何规划CI的发展前景?如何引导相关领域接纳并推动CI发展?在英文文献中,CI被看做是涉及图书馆情报学、计算机科学、社区发展的跨学科领域。如果“接纳”仅限于在我国的相应领域开设一门甚至几门CI课程、获得几项研究资助,或在社区ICT开发中采用CI的指导思想,那么“接纳”或许不会成为问题,但一旦CI以任何方式威胁到已有领域的职业垄断、权威、思维惯性,那么“接纳”就有可能成为问题。对图书馆学情报学而言,虽然它是CI的引介者,但它不太可能企盼CI发展成为与图书馆学情报学竞争生源和就业市场(特别是公共图书馆的ICT岗位)的独立专业(而发展独立的CI专业是西方很多CI倡导者的目标[20])。对政府而言,虽然他们迫切希望解决社区/农村信息化中存在的效益低下等问题,但未必乐意对自上而下地设计信息化方案的思路做出改变。对社区/农村信息化的研究者而言,他们无疑会欢迎扩大其视野的新视角,但未必能在CI理论与中国社区的文化特质(如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差序格局)或制度框架的潜在不谐中找到CI的最佳应用点。当然所有这些问题都建立在假设的前景之上,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与所有西学东渐过程一样,CI不能期待这个过程毫无冲突与磨合,因而不能回避关于CI自身与我国相关学科领域、实践领域、社会文化情境关系的思考。CI如果要在我国发扬光大并对我国的社区发展切实产生影响,就不能不考虑所有可能的前景,合理规划自己的东渐路径和应用领域。
作为一个跨学科领域,CI首先受到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关注和引介并非偶然;它在国外也吸引了很多图书馆学情报学学者的参与。公共图书馆(特别是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图书馆)作为一种社区存在,在向社区提供ICT接入、开展数字技能培训、保障数字化信息获取、支持社区交流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是社区信息化和农村信息化的重要力量;图书馆职业因此对CI的见解与主张具有天然兴趣。有鉴于此,CI西学东渐的合乎逻辑的路径似乎就是:由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率先借鉴CI,在本领域的ICT应用活动(如数字图书馆建设、数字技能培训、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等)中采用CI理论与方法,实现并彰显CI的价值,进而吸引其他学科和实践领域对CI的关注。但这样一来,CI在我国最可预期的前景就是发展为适合不同领域的视角和工具,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和职业。
(收稿日期:2013-03-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