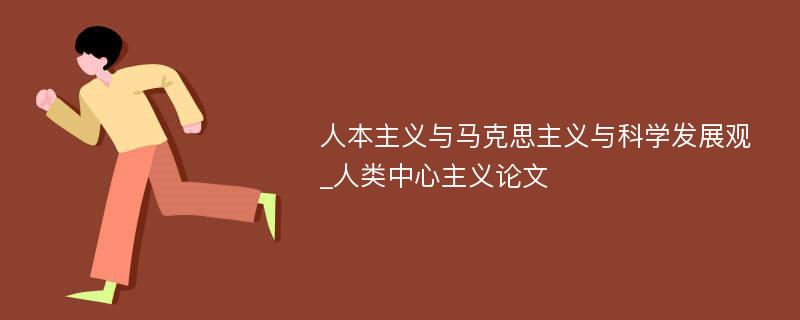
人类中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及科学发展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发展观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人类论文,主义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世纪末,随着全球问题的深入研究,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应运而生。有学者认为,生态哲学作为一种新的哲学范式,是生态学世界观,它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哲学基本观点,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人类目标,因而为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是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哲学基础。
然而,生态哲学并不是一种统一的理论,而只是哲学对人类环境、对生态关注的一种取向。同属于这个范畴的某些理论,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其中,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不同看法,是争论的焦点之一。美国神学家托马斯·贝里指出:“现代社会需要一种宗教和哲学范式的根本转变,即从人类中心主义的实在观和价值观转向生物中心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的实在观和价值观。”[1]在我国,自1994年余谋昌发表《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一文后,引发了不小的争论。时至今日,余波未息。笔者认为,在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中,有一些意见是值得商榷的。澄清这些问题,对我们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并付诸实践,有一定的助益。
一、人类中心主义种种
人类中心主义,或人类中心论,是一种以人为宇宙中心的观点。它的实质是:一切以人为中心,或一切以人为尺度,为人的利益服务,一切从人的利益出发。
人类中心主义并不是一种凝固的、一以贯之的理论体系,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它有不同的表现形态。
在古代,最早的人类中心主义是从价值观和认识论方面得到阐发的。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2]稍后的柏拉图以人的“理念”为出发点,构建了“理念论”的世界观,也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理论体系。
中世纪的欧洲,大行其道的是神学人类中心主义。这种学说的实质是神学目的论。《圣经》说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人是它的最伟大的成就,其他的世间万物创造出来是为了供人类享用的。而上帝对人特别关照,也是有目的的,那就是为了显示它的仁慈和智慧。神学人类中心主义利用托勒密的地心说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既然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栖息于地球之上的人类,也就自然居于宇宙的中心位置。不过这种人类中心主义在哥白尼的日心说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发表后就被彻底否定了。
文艺复兴时代的人类中心主义是对神学的反叛。中世纪的神学人类中心主义表面上高抬人类,但人类不过是上帝的臣仆,一切都得听从神的摆布,是神在主宰人。文艺复兴中诞生的人文主义则反对这样的价值观念。他们的口号是:“我是人,凡人的一切特性,我都具有。”[3]“我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4]。彼特拉克在《秘密》一书中借主人公劳拉对奥古斯丁的回答表明了真正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价值观念。
近代的人类中心主义是随着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而形成的一种观念,其核心思想就是要征服自然,摆脱自然对人的奴役。笛卡儿主张要“借助实践哲学使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和统治者”[5]。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康德则宣称“人是目的”①、“人是自然界的立法者”②。这种人类中心主义因在其后的实践中造成资源紧张和环境恶化的后果,受到了生态学家和环保主义者的非议和诘难。
现代的人类中心主义于是应运而生。它是伴随着生态和环境问题而发展起来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新形态,是对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和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审视。它主张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将人类共同的、长远的和整体的利益置于首要地位,为此,它主张将以人为中心的伦理学向外延伸,不仅按照人的利益平等的原则,将道德关心延伸到子孙后代,而且还依据为了人类利益的原则,将人类道德关心延伸到非人类的动物和所有有感觉的生命,甚至对整个自然界给予道德承认和保护,表示了对非人类道德的肯定。
没有人能否认人类中心主义,特别是近代人类中心主义对人类发展的伟大贡献。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人类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智慧与能力,取得了对自然的一个个胜利,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当然,这个过程同时也造成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反思这种过失,就有了上段所述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这种新的人类中心主义,体现了哲学的批判性和与时俱进的精神,它可以作为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的哲学基础。
二、对生物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的批判
然而,那些激进的环保主义者和生态关注者,对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也不认同。他们认为:“以人类利益或人类整体利益为出发点或最终目的的生态伦理,实际上是把地球或生物圈当作工具或手段的社会伦理。”[6]而生态伦理学除了关心人的福利,还关心地球上各物种和生态系统的福利,它实际上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学。如果人类对自然的行为只能从人类的利益出发,或人类整体的长远利益出发,是很难与人类中心主义划清界线的。一句话,要保护环境和生态,就必须突破传统的观念,走出人类中心主义。
那么究竟从什么出发呢?怎样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呢?生物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生物中心主义是一种认为生命有机体有其自身的“善”,因而主张把道德对象扩展到人以外的生物的环境伦理理论。它的核心观点是认为不同的有机体,虽然有不同自组织方式,但都具有同等的内在价值,因而具有平等的道德权利,应当得到道德承认、关心和保护。
虽然有人认为生物中心主义把爱的原则扩展到生物,主张所有生物都是平等的,达到了新的道德境界。但实际上他们所指的生物主要是动物。尽管施韦兹说过:“只有当一个人把植物和动物的生命看得与他的同胞的生命同样重要的时候,他才是一个真正有道德的人”③,但其后的辛格把道德的底线划在了有感觉能力的存在物那里。他认为石头没有道德利益,因为它不能感受苦乐,而一只老鼠却拥有不受折磨的道德利益,因为遭受折磨它会感到痛苦。
不过,在笔者看来生物中心主义是一种不彻底、不严谨和难以付诸实践的世界观。从逻辑上讲,把敬畏生命作为道德的基本原则,不过是以类推的原理,从人类中心主义延伸出的结论。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7]因为“人有气有生有知且有义”,而得出人类最可贵,是一种把道德看成为人的特性的观点。生物中心主义反对这种观点,他们因生物都“有生”而主张所有的生物都是平等的,其中的部分人更因为动物“有知”而把道德的底线、爱的范围划在动物那里。为什么不因“万物有灵”而泛爱万物,如张载所言“民,吾同胞;物,吾与也”[8]呢?因此,是生物中心主义只不过是扩大了的人类中心主义,从他们的观点可以看出,事物与人相似的特点越多,得到的道德关注就越多。他们对生物物种危机和生存危机的忧虑,恰似“兔死狐悲,物伤其类”。
生物中心主义在实践中也面临许多困境。难以否认的是,人作为食物链的最上端,在自然界是有其特殊性的。抽象地谈众生平等,很有宣传“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味道。对生物来说,生存是最基本的权利,但自然界进化所造就的生物多样性,却又是以生物间的食物链为条件的。当我们保护猛兽猛禽时,对草食动物的生存权利却加大了威胁;当我们保护草食动物时,植物的生存又遭到了侵害。虽然现在不提什么“除四害”了,但对苍蝇蚊子之类,人们还是很难以平等的心态来对待。在对野生动物实施保护措施后,有些物种的繁衍已对部分人的生存造成了威胁。数年前,安徽巢湖的鳄鱼对湖岸农户的侵扰就引发了杀不杀的争议。去年,四川北川县上千野猪进村“抢粮”,迫使小坝乡政府申请限量捕杀野猪,以保护农民的利益。[9]在国外,英国下院2004年9月15日不顾上万人的强烈抗议,通过了猎狐禁令。反对这项禁令的有英国女王,也有普通的猎人和农户。女王反对它是为了维护三百多年的传统,而猎人和农户反对它则是为了利益。可以预见,禁令实施后狐狸的大量增长必将更加激化禁令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的矛盾。[10]
对上述问题,我们站在新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上是比较容易达成共识并加以解决的,为了人类的共同的长远的整体的利益,我们保护野生动物,而当他们的繁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利益时,我们适当捕杀。从新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看来,人类生存的价值大于其他物种生存的价值,而其他物种生存的价值大于人类奢侈享受的价值。我们反对滥捕滥杀,但当非典肆虐时,对可能的SARS病毒载体果子狸则痛下杀手。艾滋病、疯牛病、禽流感发生后,我们不会从生物平等的观念出发,认为这些致病病毒获得了发展的机遇,而人、牛和禽类则遭了天谴;或者认为牛和家禽不应被屠杀掩埋,而应像病人一样得到救治。从同样的观点出发,我们对家养动物的道德关怀限于生存的环境和屠宰的方式,不会因宰杀它们这种杀生而内疚。而生物中心主义对生物平等的宣扬,对敬畏生命的鼓吹,常常造成某些人的思想混乱。尽管在他们的解说中也承认人的权利和动物的权利是有差别的,但从对实践的影响看,一些过激的行为已经发生。芬兰的动物保护组织“动物力量”1999年开始为一些地区提供死人的人皮,用以制造“宠物服装”。“动物力量”的发言人麦佳·克斯克在美国进行的“保护动物巡回演讲”中说:“这是公平的游戏。人类杀死无助的动物,那为什么我们不能用死人皮为宠物做衣服穿呢?人类穿皮革,动物为什么就不能穿人皮呢?”[11]
生态中心主义是另一种反人类中心主义的学说。与生物中心主义不同的是,它认为物种和生态系统比生物个体更为重要,因而提倡整体主义的环境伦理思想。它认为不仅生物,而且非生物的自然存在物,即生物及其环境构成的生态系统和生态过程,都是道德关心的对象。它强调生物物种和生态系统的价值和权利,认为物种和生态系统具有道德优先性。
生态中心主义将伦理学的范围更加扩大了。在他们看来,不仅动物和植物,包括土壤、水域和自然界的其他实体,都有其持续存在的道德权利。在“大地共同体”中,人只是普通的一员。他的角色不应是征服者,而应是好公民。
笔者无意否认维护生态系统的重要性,何况生态中心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被普遍接受的系统论和生态学。但把人类视为生态系统中的普通一员,则大谬不然。一是它与事实不符,人类在其发展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其他任何物种无法相提并论的;二是它不利于强调人类的责任,人类在对环境的保护和修复中的作用也是其他物种无法相比的。
从理论上看,生态中心主义和生物中心主义一样,其缺点都是摆脱不了“生”的缠绕,最终也就无法摆脱人类中心论的缠绕。表面上看,生态中心主义把道德关怀扩展到了空气、水源和土壤等非生物,其实这些非生物存在的意义只在于是生态的一部分,是生命存在的必要条件。撇开与生命的联系,土壤和戈壁、净水和淡水、清气和浊气,都不过是物质的不同存在状态,哪里有好坏利弊之分。我们重视生态环境,是因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依赖着它。在对生态关注迷恋的背后,隐藏着人类的自恋。然而生态中心主义刻意掩饰这种自恋,它抛开人类的生存利益,企图完全从自然界寻找爱护和保护自然的伦理依据,这样它就不得不求助于信仰。
生态中心主义在实践中也经常遭遇困境。人类的生存特别是发展的活动必然影响周围的环境。那些代表着科技进步和文明创造的大型工程更是对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的改变。一些生态中心主义者将生态的破坏归罪于科技和工业的发展,这使得许多受益于科技和工业的人难以接受这种思想。为了宣传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有的人将生态效益货币化,可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些工程影响生态却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如果都将其货币化进行比较,生态中心主义者会感到尴尬。当初关于三峡工程能否上马的辩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实科技确实是柄双刃剑,多的不说,只说避孕药和避孕器具的发明,就让当年马尔萨斯视为千古难题的性欲与生殖的矛盾得到了解决。而人口问题正是当今所有生态问题之源。
三、马克思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
在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中,马克思主义站在哪一边呢?
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哲学来看,它是以实践性为其根本特征的。在被称为新世界观的第一个天才大纲——马克思所著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写道:“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12]上述论断清晰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人类的实践或社会实践中的人类为出发点、立脚点的。
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来看,它的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增值的奥秘,从而说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肩负的历史使命。
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来看,它以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它认为只有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共产党宣言》中写道:“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3]
从上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学说中,我们看到从出发点到最终目标,关注的都是人类。正因如此,在上世纪80年代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质的讨论中,大多数讨论者否认了马克思主义是“人学的空场”,认为马克思主义包含了人道主义,是“革命的人道主义”。如果说人类中心主义实质上是人道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实质上是自然主义的话,马克思主义明显是属于人类中心主义一方的。有些人不同意这种观点,主要是因为马克思早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用过“自然主义”这一术语表达自己当时的思想:“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4]不过这里所用的“自然主义”一词如同“异化”概念一样,被马克思在后来的著作中扬弃。代之而起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对社会发展的论述清晰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属人的性质。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过程。社会发展的动力来自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其中生产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它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和变化。这样,来自亚当·斯密的生产力概念就成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一个概念。我们对它的理解,直到上世纪80年代,还是这样的:“生产力或社会生产力是人们解决社会同自然矛盾的实际能力,是人类征服或改造自然使其适应社会需要的客观物质力量。”[15]后来在环保主义者的批评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对“生产力”的定义纷纷去掉了“征服”二字。但就是这样,改造自然,同自然主义只承认自然界作用于人,否认人对自然界的能动作用的思想也是大相径庭的。
总之,马克思主义在处理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时,基本的立场和态度是属于人类中心主义的。美国哲学家诺顿对现代人类中心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将人类中心主义分为两类:强式和弱式人类中心主义伦理理论。强式人类中心主义以个人感性意愿的满足为价值标准,却不问这些意愿是否合理,它把自然界视为满足人的感性意愿的原料仓库,鼓励了对自然界的掠夺。弱式人类中心主义则把理性意愿的满足作为价值标准,它区分了人的感性意愿和理性意愿,肯定满足人的意愿的合理性,但要求依据合理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对这种意愿的合理性进行评价,从而防止人对自然界的随意破坏。诺顿赞同的是弱式人类中心主义。如果按照诺顿的分类,马克思主义应该是属于弱式人类中心主义的。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以两河流域的变化为例,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16]。这段充满理性的话,不仅可以看作是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先行,更可作为我们现实发展的指导。
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全球问题日益突出的情况下,提出要树立和坚持科学的发展观。所谓科学发展观,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面,就是要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同时,加快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形成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协调,就是要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可持续,就是要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这种发展观显然是以人为中心的,是一种充满现代色彩的人类中心主义。相对它而言,近代人类中心主义显得残酷,非人类中心主义则显得虚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