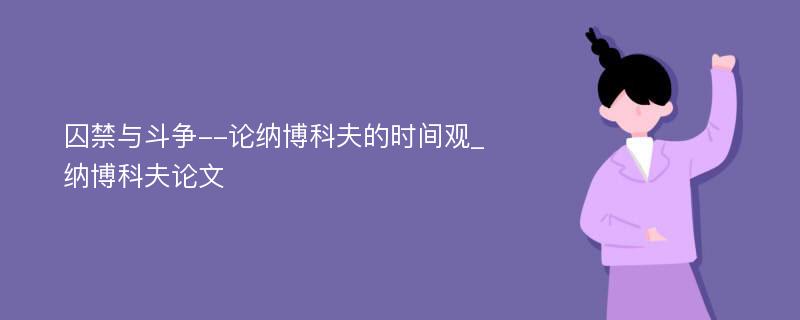
囚禁与抗争——试论纳博科夫的时间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时间论文,博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89X(2003)03-0062-03
美籍俄裔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因其英文小说《洛丽塔》的问世而闻名遐迩。他 独特的文学观点使他在世界文坛上独树一帜,自成一家。纳博科夫的小说往往以凝练华 美的语言、奇谲多变的叙述、扑朔迷离的结构著称,他一直被文坛尊为文体学大师。纳 博科夫曾说:“我既不是说教小说的读者,也不是它的作者……对我来说,一部虚构的 作品的存在仅在于它提供给我的一种我坦白地称之审美狂喜的东西。”[1]然而纳博科 夫并非只是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后现代作家,他的作品也不仅仅是一个五彩缤纷令人眼 花缭乱的“玻璃彩球”,在他的小说中,我们仍可以看到他对人类生存基本状况的审视 ,对人的生命主题的思考。
一
纳博科夫曾在他的访谈录中谈到对时间的看法,他说:“我们可以想象各种时间,比 如‘应用时间’——用于各种事件的时间,这是钟表和日历来计算的。不过,这类时间 不可避免地被我们的空间观念所腐蚀。当我们讲到‘时间通道’时,我们脑海中闪现的 是一条流过大地的抽象的河。应用时间,时间的可测性,对历史学家和物理学家有用。 他们引不起我的兴趣,……”那么什么样的时间能引起纳博科夫的兴趣?“纯粹的时间 ,感知的时间,有形的时间,没有内容和上下联系的时间——这便是我的人物在我的赞 同下描述的时间。”[2]纳博科夫的文学观独特,他的时间观也很独特,而他之所以有 如此个性化的时间观,与他独特的理论思考和人生经历有关。
作为观念性的问题,时间早在纳博科夫意识形成初期就已经引起他的警觉,在他母亲 过生日的一个夏天,他第一次意识到了人与人之间的时间差,这种发现造成了他精神上 强烈的震颤:“我感觉到自己突然陷入了一种光辉而易变的介质,那正是纯粹的时间。 ”[3]在20岁时,他迷上了柏格森的作品。柏格森在其著作中把时间分成两种:一种是 用钟表可以度量的时间,即物质时间;一种是通过直觉体验到的时间即绵延。柏格森认 为物理时间的概念受到空间的腐蚀,它表现出由年、月、日这些标准单位所构成、依次 延伸的一根同质的长键,在这种线形的时间键上,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已被锁定。这种 时间观忽视了瞬间的区别,忽视了时间的流动性;相反,绵延是不同质的,川流不息的 ,也是不可分割的。它的各阶段互相渗透,共同构成一个不断运动变化的过程。柏格森 认为只有绵延才是真正的时间。他认为绵延是纯粹性质的,它不可以物化,因而,只有 自我意识才能把握它,自我意识通过直觉或古代神秘主义论者所谓的“内心默想”来体 会这种互相渗透与纯粹的多样性、这种绵延,从而获得真正的自由。柏格森的时间观深 刻地影响了纳博科夫,使他认识到传统时间观的机械性,在他的眼里,时间不再是彼此 断裂的,而是互相联系的。但时间也不能被简单地想象为“一条流过大地的抽象的河” ,“时间虽然与韵律有缘,但不只是韵律。韵律意味着动作——而时间并不动弹”[2] 。而复杂的人生经历,使纳博科夫对时间的理解渗进了他独特的生命体验。
1899年,纳博科夫出生在一个显赫的俄国贵族家庭,他祖父做过沙皇时代的司法大臣 ,他的父亲是法学家也是政治家,对文学有很深的鉴赏。纳博科夫从小天资聪慧,很小 就掌握了英语、法语和德语。15岁时差不多读遍了俄、英、法19世纪的文学巨著,还出 版了一部诗集,三年后又出版了第二部诗集,被当时舆论称为“神童”,他的亲戚朋友 都对他赞赏有加。可以说纳博科夫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极为幸福的,但好景不长,十月 革命后不久,他家因政治避难流亡到欧洲,那时,纳博科夫20岁,从此,他开始了他一 生永远的流亡生活。
纳博科夫的欧洲流亡生活是异常艰辛的。起初,他靠他母亲变卖首饰进入剑桥大学就 读生物学以及法国、俄国文学。大学毕业后,纳博科夫移居德国。1937年由于他妻子的 犹太血统,纳博科夫一家不得不流亡到巴黎,法国当局对他并不热情,甚至不发给他工 作证,他家的生活陷入困窘。1940年,德国占领法国之前,他带着妻儿又不得不移居美 国,从此,结束了他在欧洲的流亡生活。
漂泊的经历使他对时间有着特殊的敏感和独特的理解。可以说在欧洲流亡的每一天, 纳博科夫都在品尝和咀嚼着生活的苦涩与艰辛。快乐的早年生活与他30多年异常艰难的 流亡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给纳博科夫带来了极深的心灵痛苦。作为一个无根的漂 泊者,在1919年之后的每一天,他都忍受着命运的煎熬,他看不到未来,也回不到幸福 的过去。“我曾在思想中返回……到遥远的地方,在那里摸索某个秘密的出口,但仅仅 发现时间之狱是环形的,而且没有出路。”[3](第3页)如果,时间是绵延的,纳博科夫 也许想通过意识的力量顺着时间之道回到美好的过去,然而纳博科夫很快发现希望落空 了。“最初,我没有觉察到,初看之下如此无边无垠的时间,竟是一个牢狱”[3](第2 页)。纳博科夫通过他的小说中一个人物说:“这种现在性(nowness)是我们知道的惟一 现实,它承继着过去的多彩虚无和引领着未来的绝对虚无。因此,从原本意义上,我们 可以说意识的人类生活常常只延续那么一瞬。”[4]纳博科夫认为过去与现在存在着一 层不可逾越的“时间之墙”,这墙“把我们及我们青肿的双拳与永恒的自由世界隔开” [3](第2页)。时间是静止的,“现在”站在“过去”与“未来”这两个空洞之间,而人 则被囚禁在“现在”中,囚禁人的牢狱便是现在,即当下之狱。
二
在纳博科夫早期的作品中,时间已经作为与生存意义相关联的因素受到重视。著名的 传记作家布·博伊德在《纳博科夫·俄罗斯时期》中曾指出《玛丽》(1926年)的时间主 题,他说:“时间,而不是空间,是纳博科夫的真正主题。……《玛丽》是一部关于时 间的小说:关于过去的真实不虚,尽管我们不能超越当下到达那里;关于我们所期盼的 未来的魅力……关于现在,在这里我们可以自由地行动,但必须对所作的选择负责。” [5]纳博科夫以时间为对象的小说常常通过某种寓言式的构思从概念的高度来表达他独 特的时间感受与全新的时间观念,同时思辨性的观念又以异乎寻常的艺术手段内化到人 物形象的日常生活之中。
纳博科夫作品中的许多人物都有一种身陷困境而寻找窗洞的奇怪感觉。《防御》(1929 年)中的卢辛禁锢在象棋世界难以自拔,最后砸碎窗玻璃从楼上跳了下去;《征兆与象 征》中一个精神错乱者企图在充满敌意的世界里“撒开一个洞好逃出去”;《微暗的火 》中一个黑影紧攥双手,“仿佛抓着看不见的监狱窗栅似的”。在《斩首的邀请》中时 间与囚禁感的关系更为明显。C·辛辛纳提斯莫名其妙地被当局处死刑,一开始,他明 白要死,但始终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时间的主题便浮现出来,从第1章到第19章,他 一直陷入焦虑恐惧之中,而每一章的时间正好是一天,辛辛纳提斯一直在每一天中等待 着死亡,时间的牢狱由此建立起来。小说主要用日历上的时间流逝和钟表上的时针转动 来表现时间,对辛辛纳提斯来说,狱中生活虽然经历了19天,但由于它们总是以“今天 ”的面孔出现,所以体味不到流逝感,他实际被拘禁在“当下之狱”。
《洛丽塔》是纳博科夫最具有影响力的一部作品,讲述了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年男 子追求未成年“性感少女”成癖,并与其十三四岁的继女同居通奸最终为之付出生命代 价的故事。这不仅在当时让人难以接受,即使在现在也会令人瞠目结舌。但是,如果读 者仅从这点来理解小说,显然是一叶障目,未真正读懂它。纳博科夫不只一次谈起有关 这本书最初的创作冲动:“第一次洛丽塔在我的心中悸动是1939年末和1940年初。当时 在巴黎,最初的灵感直接来自一份报纸上所载的故事。讲的是一只类人猿在一位科学家 的数个月的调教下,用木炭笔画出了世界上第一张动物所作的画。画面上所展示的是一 些木栅栏样的东西,犹如这可怜的动物的囚笼。”[6]正是这样一个故事触发了他写作 的灵感。读过《洛丽塔》的读者不难发现小说主人公亨伯特与这只囚禁在囚笼里的类人 猿有着某种相似性,不仅亨伯特最后被囚禁在监狱中的悲剧结局与类人猿有相同的地方 ,而且读者也会察觉到亨伯特似乎时时刻刻都被一种无形的东西囚禁着。那么囚禁亨伯 特的“栅栏”又是什么呢?
显然,在《洛丽塔》中,囚禁亨伯特的那个无形的“栅栏”便是时间。尽管作家在叙 事笔法上极其隐晦,埋设主题的意象呈现为分散的碎片,但时间却像一根若隐若显的红 线贯穿在小说中。如亨伯特把洛丽塔比喻为“时间的虚渺岛屿”,并用时间概念代替空 间概念来界定这座魔岛,“9岁”和“14岁”是其边界。与生活在时间魔岛上的洛丽塔 相比,其他处于相同的年龄阶段但并不属于性感少女的女孩子们“更无比依赖于此时存 在的空间世界”[6](第11页)。作家还为读者制作了“时间谜语”,这便是他惯用的“ 湖”的意象。纳博科夫为他的人物安排了一次湖上野餐,这个湖在亨伯特最初听来是“ 我们的镜湖”(Our Glass Lake)。经过多次延宕后,它才露出真正的面容,原来是沙漏 湖(Hourglass Lake),而沙漏乃是古代的记时器。此外,纳博科夫还常常在别的作品中 为自己的谜语留下注脚。亨伯特在洛丽塔失踪后写过这样几行诗:“多洛雷斯·黑兹, 你藏在哪里?载你的魔毯又是什么品牌?”读完作者的自传《说吧,记忆》中的一段话, 我们很容易明白“魔毯”是什么。他说:“我承认我不相信时间,在使用过我的魔毯后 ,我喜欢把它折叠起来,一个图案置于另一个图案之上。”[3](第128页)经过伪装的时 间线索在此露出了它的真面目。
视时间为生存的牢狱的观念是纳博科夫独特的生存体验的产物。由于他的生活的前后 强烈对比,他对过去比对现在投入了更多的热情,由于流亡者的生活空间的不断转换, 人们普遍信奉的持续的时间在他那里则呈现出某种错乱感,由于“过去”的压迫,对它 的回忆,对回到它的期待,“时间之箭”在纳博科夫的世界里不但失去了方向,而且发 生了形变,实存体会的杂乱感与常识的时间发生了矛盾。而在《洛丽塔》中,亨伯特的 “时间之箭”也发生了变化。
亨伯特出生于法国的一个极富裕的家庭。13岁时与小女孩安那贝尔·蕾发生“恋爱事 件”。起初,他们只是在一起玩耍,但渐渐地“我们疯狂地,笨拙地,毫无羞怯,痛苦 难忍相爱了”。但他们恋爱却“同时还是无望地,我必须补充说;因为相互占有的狂乱 只有靠实际吮吸,融合彼此灵魂和肉体的每分子才能平息下来”。然而,亨伯特始终没 能“占有”他的爱,他和安那贝尔精心策划的一次海滨行动被两个洗澡的人打搅了。几 个月后,安那贝尔死于伤寒。
多年后,亨伯特一直把他与安那贝尔的那段恋情埋在记忆里,他从没走出过这个时间 段,或者说他根本就不想走出这个时间段。他在很多“性感少女”身上寻找着安那贝尔 的影子,最后,他在洛丽塔身上找到了:“同样柔嫩的蜂蜜样的肩膀,同样绸子般温软 的脊背,同样的一头栗色头发。”为了获得洛丽塔,为了逃出时间之狱,为了超越现在 ,回归已经消失的过去,亨伯特进行了一场堂吉诃德式的抗争。
他首先与洛丽塔的母亲夏洛特结婚以便接近洛丽塔,但夏洛特在无形中又阻碍着他接 近洛丽塔。当夏洛特因车祸身亡后,亨伯特终于如愿以偿了。为了最终完全占有洛丽塔 ,他带着她四处流浪,周游美国,他想通过不断改变地方来避人耳目,可不到两年洛丽 塔就被奎尔帝拐走。尽管亨伯特杀了奎尔帝,但洛丽塔仍没回到亨伯特的身边。这似乎 预示着“现在”有某种无所不在的力量,它限制着人们,使之不能穿越时间之狱,回到 过去。
在亨伯特的时间世界里,秩序发生了错位,他总是竭力想把“过去”在“现在”中复 制,想穿过“时间之墙”自由地来回于“过去”与“现在”之间,想将短暂的瞬间变成 永恒,为此他日夜生活在紧张的状态中。当他知道自己永远地爱上洛丽塔时,他也意识 到她不可能永远是洛丽塔。“一月一日,她就要十三岁了,再过差不多两年,她就不再 是小仙女,而会变成一位‘年轻女郎’,然后变成‘女大学生’——那是恐怖中最恐怖 的。”于是他经常给洛丽塔服用安眠药,禁止洛丽塔与其他同龄的男孩子来往,剥夺她 正常发育的社会交际能力和健康的性心理,潜在的意图是不愿看见她长大。但他的一厢 情愿很快就在现实前碰了壁。洛丽塔仍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地长大了,她有了自己的看 法,最后背着他偷偷地与奎尔帝逃走了。洛丽塔这个人物有着深刻的含义。表面上,亨 伯特把她看成安那贝尔的化身;深层上,洛丽塔是一种时间的象征,更确切地说是亨伯 特记忆中少年时代与安那贝尔最激动人心、最令人难忘的过去。亨伯特想永远拥有洛丽 塔,便是想永远拥有过去。其实,换一个角度来看,洛丽塔并非真实的人,而完全只是 亨伯特的意识力量的产物。洛丽塔是他通过意识创造出的生活在“现在”中的“过去” 。亨伯特在占有了洛丽塔之后说到:“我疯狂占有的不是她,而是我自己的创造物,是 一个梦想中的洛丽塔——或许比洛丽塔更真实;重叠又包容了她;在我和她之间浮游, 没有欲望,没有感觉——的确,她自己是没有生命的。”当亨伯特最后一次见到洛丽塔 时,请求洛丽塔跟他走,但洛丽塔坚定地拒绝了。亨伯特想通过复制记忆回到过去的幻 想失败了,洛丽塔就是洛丽塔,不是安那贝尔,也不是“过去”。当下之狱把人的意识 囚禁在“现在”,使人不能立刻进入人们曾生活过的过去,亨伯特想从时间的奴役下解 放出来,回到过去,获得自由的愿望落空了。时间是牢狱,所有的人都是时间的囚徒。 那无形的“栅栏”似乎如影随形,无法摆脱。亨伯特的入狱便是被时间囚禁的生动寓言 。
但亨伯特最终并没向时间妥协,他没有放弃抗争。在小说的结尾处写到:“我现在正 在思考欧洲的野牛和天使,永久颜料的秘密,先知十四行诗,艺术的避难所,而这,是 你和我所分享的惟一不朽,我的洛丽塔。”
失去洛丽塔后,还有什么能让他穿越时间之狱、达到他梦想的自由呢?也许是艺术吧。 囚禁与抗争是亨伯特一生全部的内容。他所面临的困境也是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的,而他 的这种抗争似乎又带有一种堂吉诃德的执着和真诚,让人不能不为他的命运黯然神伤。 时间不仅是亨伯特的情结,也是作家纳博科夫的一个情结,纳博科夫对时间的思考,也 是我们对所面临的生存问题的思考。纳博科夫曾说:“事实上,我相信有一天,有人会 对我的作品重新评估并且宣布——纳博科夫远不是轻浮的北美黄鹂鸟,而是鞭达罪恶与 愚蠢、嘲讽丑陋与残酷——极力主张温柔敦厚的人,他把至高的权力分配给才能与自尊 。”[2]当我们去仔细研读纳博科夫的作品后就会感到,的确是如此。
收稿日期:2003-03-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