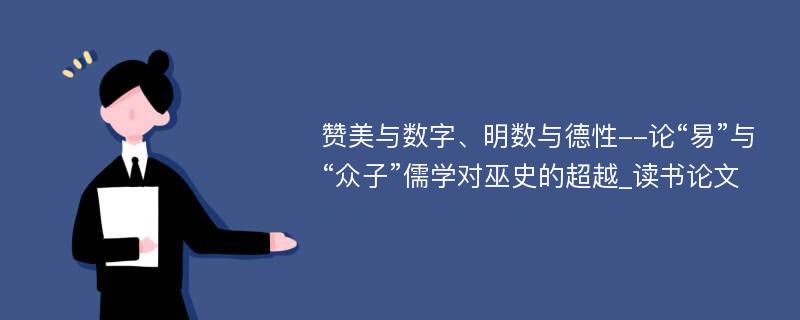
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由《要》与《诸子略》对读论儒之超越巫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诸子论文,达乎数论文,达乎德论文,读论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先秦思想整体性理解最主要的文本是承袭了已佚《别录》、《七略》基本内容的《汉书·艺文志》。《艺文志》中《诸子略》最主要的学说就是“诸子出于王官”。《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各家小序:“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从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又《兵书略》大序:“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数术略》大序:“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方技略》大序:“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此说两千年来被奉为圭臬,如释道安《二教论·归宗显本》:“若派而别之,则应有九教;若总而合之,则同属儒宗。论其官也,各王朝之一职;谈其籍也,并皇家之一书。”①《隋书·经籍志三·子部》即于各家小序逐一引用《汉志》并加阐发。清代民国学者论者尤多。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下》:“诸子百家,不衷大道,其所以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则以本原所出,皆不外于周官之典守。”②针对“诸子出于王官”说,近代学者争论不已。如章太炎引述《汉志》,谓为“此诸子出于王官之证”,并具为申论③。刘师培以之与西方比较:“昔欧西各邦学校操于教会,及十五世纪以降,教会寝衰,学术之权始移于民庶。”④吕思勉强调“抑诸子之学,所以必出于王官者,尚有其一因焉。……平民胼手胝足,以给公上,谋口实之不暇,安有余闲,从事学问?……贵族则四体不勤,行有余力。身居当路,经验饶多。父祖相传,守之以世”⑤。其余如张采田《史微·内篇·百家》:“官各有史以掌其政教,而上辅人主之治,此政学所由合一也。王道既微,官失其守,流而为百家,而后诸子之言始纷然淆乱矣。”⑥刘咸炘《子疏定本·老徒裔》言:“大道散而后有子术,未散而止有官学。”⑦江瑔《读子卮言》谓:“大抵班氏所言,尽本刘氏《七略》。刘氏去古未远,且亲校秘书,其所云云,必有所本。后之学者,亦得藉是而知百家之流别焉。”⑧孙德谦《诸子通考》卷三:“三代以上政教不分,学统于官。故《周官》一书,千古之学案也。志于法家则证之司寇司刑……是可见百家道术其始皆原于周官也。”⑨清末曹耀湘始致不满:“刘歆之叙诸子,必推本于古之官守,则迂疏而鲜通。其曰道家出于史官,不过因老子为柱下史,及太史公自叙之文而傅会为此说耳。若云历记成败兴亡,然后知秉要知本,未免以蠡测海之见。至其谓墨家出于清庙之守,则尤为无稽之臆说,无可采取。”⑩胡适亦痛加驳斥,曰《七略》“所说诸家所自出,皆属汉儒附会揣测之辞,其言全无凭据”,“今试论此说之谬。分四端言之”,“第一,刘歆以前之论周末诸子学派者,皆无此说也”,“第二,九流无出于王官之理也”,“第三,《艺文志》所分九流,乃汉儒陋说,未得诸家派别之实也”,又论“第四,章太炎先生之说,亦不能成立”(11)。
从历史事实的角度来说,“诸子出于王官说”确有疑窦,“判定诸子各家跟古之官守有如此明晰的、一一对应的源流关系,尚缺乏确凿的证据”(12)。章太炎亦谓“固然有些想象”(13)。关于诸子是否出于王官,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14),本文想讨论的是汉人为何提出“诸子出于王官”说。
罗焌尝缕数诸子所由废者,其四为君主专制:“秦始皇时,丞相李斯上言,私学非议造谤,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之。汉武帝时,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张之言,乱国政,请皆罢。秦除百家,专任法律;汉黜百家,推明孔氏。事虽不同,其为逢迎君主以成其专制之私则一也。”(15)其实无论是“焚《诗》《书》”还是禁百家语,其论皆作俑于诸子。原因在于诸子从开始就热衷于治国术,热衷于做帝王师,思以其术干王侯公卿,冀以获用,从而丧失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成为权势阶层的依附者(16)。“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固然出于董仲舒,但这一模式却并非董氏首创。“罢黜百家,独尊某术”的观念早在先秦就已甚嚣尘上,商鞅、韩非、李斯是“罢黜百家,独尊法术”,吕不韦是“罢黜百家,独尊阴阳”(17),司马谈则是“罢黜百家,独尊道德”。吕不韦在理论上未能很好地整合百家语,随着他在政治上失势,“独尊阴阳”之路被打断。法家在秦一统天下后占据主导地位,但以暴力手段消灭异说,致使统治失去弹性,无法灵活处理问题,将暴力进行到底的结果是自身被暴力推翻。汉初惩秦之弊,吕不韦以某一家思想为主体,融汇百家语的路径复受重视。淮南王刘安召集宾客编撰《淮南鸿烈》,即是模仿《吕氏春秋》,而改以道家思想整合百家语,获得成功。但淮南王的诸侯王身份使得《淮南鸿烈》难以成为汉廷施政纲领,随着淮南王集团被武帝铲灭,这一路径也就灰飞烟灭了。
值得重视的,是司马谈整合百家语的方式。《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其《论六家要指》,开篇即言:“《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司马谈所引《易大传》之语,见于今本《易传·系辞上》,不过“一致而百虑”与“同归而殊涂”次序颠倒(18)。其后《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隋书·经籍志三·子部》皆引《易传》此文,可见其影响之大。此语中“一致”、“同归”与“百虑”、“殊涂”,乃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司马谈也正是将六家描述为皆系“务为治者也”,从而在目的上将六家统一,于是其差异便仅仅是具体手段而已——“直所从言之异路”,司马贞《史记索隐》即以“殊涂”释“异路”。质言之,无论是六家还是百家,其目的是一致的,无区分的,也就是混朴的,构成区分的是手段。这非常类似于《易传·系辞上》对于道器的区分:“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系辞上》又曰:“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孙星衍《集解》引荀爽曰:“万物生长,在地成形,可以为器用者也。”(19)更为明确的阐述则见于《老子》(20)。其第三十二章曰:“道常无名,朴。”第二十八章又曰:“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王弼注:“朴,真也。真散则百行出,殊类生,若器也。”(21)《论语·为政》:“子曰:‘君子不器。’”何晏《集解》引包咸曰:“器者各周于用,至于君子,无所不施。”朱熹《集注》:“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22)
《易传·系辞上》又曰:“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这也正可对应于《老子》的“圣人用之,则为官长”。只是老子为史官,其“官长”之语更合于周礼世官制的史实。沈文倬尝道:“西周鼎彝铭文中,授官时常有‘更乃祖(或考)司某事’,更读为赓,训‘续也’。据此而知,宗周存在过世官制度。学者是子或孙,教者是父或祖,这使教、学更为方便……世官制度在西周曾实行过——不仅显要的冢司徒,还有一般属吏的左右走马。而且,某些学术或技能较强的职位,将被某氏所独擅,史某、师某这种世官将非他姓所能问津,世官也有可能成为世学呢!”(23)钱宗范也认为:“贵族世世代代继承上一代的职位,固定做其一种官,也就是说一种官职永远由其一族的族长来承担,这一族的成员也世代从事族长所管理的某一种职业。以谓‘学在王官’‘官有世功,则有官族’,即指此类的世官。”(24)检《左传·哀公三年》:“夏五月辛卯,司铎火。火逾公宫,桓、僖灾。救火者皆曰顾府。南宫敬叔至,命周人出御书,俟于宫。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礼书,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马,巾车脂辖。百官,官备府,库慎守,官人肃给,济濡、帷幕、郁攸从之。蒙葺公屋,自太庙始,外内以悛。助所不给,有不用命,则有常刑,无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驾乘车。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伤人则止,财可为也。’命藏象魏。曰:‘旧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无备而官办者,犹拾瀋也。’于是乎去表之槀,道还公宫。”南宫敬叔为孔子弟子,重视周礼旧籍,故出御书。其余子服景伯出礼书,公父文伯驾乘车,季桓子藏象魏,都是基于他们的职守和学术背景。章学诚尝论《周礼》官掌其学,《校雠通义·原道》:“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易》掌太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领太师,《春秋》存乎国史。”(25)可能也正是由于《老子》的启发,刘向、刘歆父子提出了“诸子出于王官”论。
刘向曾将董仲舒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汉书·董仲舒传赞》引刘向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刘向提出“诸子出于王官”论,就是要继承董仲舒未竟之业,彻底完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谈已将六家之分解释为“异路”,亦即手段的差异,从而使之在目的,亦即“道”的层面归于一统。这一“道器”模式,也正对应于黄老政治哲学中的“君无为而臣有为”的学说。《管子·心术上》:“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心处其道,九窍循理。嗜欲充益,目不见色,耳不闻声。故曰,上离其道,下失其事。毋代马走,使尽其力;毋代鸟飞,使弊其羽翼;毋先物动,以观其则:动则失位,静乃自得。”于是向歆父子改造司马谈之论,以儒家代替道家居于“道-君”之位,而以其余八流九家置于“器-臣”之职,进而将其分别对应于周礼世官体制中的具体官守-官学。因此,所谓“诸子出于王官”所要表达的理念,不是“诸子出于王官”,不是历史上的诸子从周代世官世学中分离出来,而是“诸子入于王官”,亦即汉代现实中的思想自由的诸子应当最新回到复必周礼,重建盛世的汉代大一统的王官之中去。此即《诸子略》序所谓:“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全宋文》卷一七一二李清臣四《史论》下曰:“夫儒者之术,教化仁义而已也。使儒者在人主左右,得以仁义教化为天下之治,则所谓道家者,不过为岩野居士;名法家者,不过为贱有司;阴阳者,食于太史局;而纵横、杂、墨之流,或驰一传,或效一官;农家者流,耕王田,奉国赋,以乐天下之无事:彼得与儒者相抗而为流哉!”(26)颇识向歆之髓。
与此相应,《汉志》论诸子,便是在其出于某一官守的前提下,评议其长短,我们可套用福柯的话称之为“规训”与“惩罚”(27)。其长者往往是合于其所出之官守者,最为典型的是阴阳家:“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对照《尚书·尧典》所言“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汉志》仅仅从训诂角度作了文字调整:阴阳家的长处等同于羲和之职掌。反之,诸家的短处,则是偏离了其所出官守。如其论儒家之辟者:“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辟儒所以别于七十子中“有圣人之一体”者,乃是游夏之徒自知仅得圣人之一体,自知圣人之全体非己所能有,故虽偏而不辟。辟儒则如摸象之盲人,执象之一偏以为全体。儒家之外的诸家,也都是盲人摸象,将其出于某一具体职官之一偏之学,直接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全体之学,又怎能不祸害苍生!其论法家可谓典型:“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周礼体系中的理官,乃是以法辅礼,刑法本身仅为礼制的一部分。但法家不恰当地将出于理官,本为礼制一部分的刑法直接作为治理天下的根本原则,以器为道,废弃本应为天下根本的礼乐仁爱,致使天下大乱,生灵涂炭。又如农家曰:“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农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是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其中“播百谷”一语亦出于《尧典》命弃为稷之辞。则农家所长,亦即农稷之官守。农家之错误就在于,将古农事中的君臣并耕直接作为普遍化的治理天下的原则,使得国无以为国。一言以蔽之,子学中只允许保留相应于其所出王官之学的内容——我们可以称之为“官守之学”,而超出于官守之学,以天下为己任者——我们可以称之为“天下之学”,便必须裁抑。
《诸子略》所载诸子九流十家可以分为三组,前面三家,儒、道、阴阳是一组,法、名、墨是一组,后面的几家,纵横、杂、农、小说是一组。第三组为杂拌。第二组相关于刑名。法与名相需,世所公认,墨亦与法、名关系密切。晋鲁胜注《墨辩》,共六篇,其四篇为上下经及说,“又采诸众杂集为《刑》、《名》二篇”,其叙有云:“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别名显于世。”(28)最主要的是第一组,即前面三家。儒家是“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此当本于《尚书·舜典》舜命契之辞:“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史记·五帝本纪》裴骃《集解》引郑玄曰:“五品,父母兄弟子也。”复引王肃曰:“五品,五常也。”郑、王二家对“五品”解释不同,孔颖达《正义》则弥缝两端:“一家之内,尊卑之差,即父母兄弟子是也。教之义慈友恭孝,此事可常行,乃为五常耳。”金景芳以为:“郑说是,王说非。郑说应据于《左传·文公十八年》‘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29)《诗·大雅·生民》孔颖达《疏》引郑玄《尧典注》云:“举八元使布五教”(30),金说是。《左传》之外,《孟子·滕文公上》亦云:“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31)可证。“明教化”即顺五品,布五教,甚为显明。《尚书》孔安国《传》:“逊,顺也。”(32)是则《诸子略》“顺阴阳”之“顺”即本于《尧典》“五品不逊”之“逊”。由此可见,《诸子略》“顺阴阳”与“明教化”并非并列结构,而应该理解成以“顺阴阳”为手段达到“明教化”的目的(33)。然则其详维何?兹说盖本于董仲舒。《春秋繁露·基义》:“阴者阳之合,夫者妻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阳兼于阴,阴兼于阳;夫兼于妻,妻兼于夫;父兼于子,子兼于父;君兼于臣,臣兼于君。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阴阳二物,终岁各壹出。壹其出,远近同度而不同意。阳之出也。常县于前而任事;阴之出也,常县于后而守空处。而见天之亲阳而疏阴,任德而不任刑也。是故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秋为死而棺之,冬为痛而丧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天出阳为暖以生之,地出阴为清以成之。不暖不生,不清不成。然而计其多少之分,则暖暑居百,而清寒居一。德教其与刑罚,犹此也。故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以此配天。”董生所举之伦虽不同于郑君,然顺阴阳以明伦常之意则颇清晰,故刘氏持以释《书》而论儒。董生造论,固有取于阴阳家(34),且其意盖师诸《易》之《序卦》:“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易传》则为援阴阳以入儒之肇始(35),其以阴阳贯通天人,允为董生之先路(36)。《隋书·经籍志三·子部》儒家类小序乃谓“儒者所以助人君明教化者也”,独删“顺阴阳”三字,亦可略窥时移世变(37)。
道家“盖出于史官”,考史官本出于羲和之官。据《史记·太史公自序》:“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司马贞《索隐》:“案:此天官非《周礼》冢宰天官,乃谓知天文星历之事为天官。且迁实黎之后,而黎氏后亦总称重黎,以重本司天,故太史公代掌天官,盖天官统太史之职。言史是历代之职,恐非实事。然卫宏以为司马氏,周史佚之后,故太史谈云‘予之先人,周之太史’,盖或得其实也。”太史公所言,本于《国语·楚语下》:“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后也,当宣王时,失其官守,而为司马氏。”韦昭注:“尧继高辛氏,平三苗之乱,绍育重黎之后,使复典天地之官,羲氏、和氏是也。”《史记·历书》亦曰:“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其后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废所职,而闰余乖次,孟陬殄灭,摄提无纪,历数失序。尧复遂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时正度,则阴阳调,风雨节,茂气至,民无夭疫。”又《太平御览》卷二三五引应劭《汉官仪》曰:“太史令,秩六百石。望郎三十人,掌故三十人。昔在颛顼,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唐虞之际,分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至于夏后、殷、周,世叙其官,皆精研数术,穷神知化。当春秋时,鲁有梓慎,晋有卜偃,宋有子韦,郑有裨灶,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其言屡中,有备无害。汉兴,甘、石、唐都、司马父子,抑亦次焉。末涂偷进,苟忝兹阶,既暗候望,竞饰邪伪,以凶为吉,莫之惩纠。”(38)
阴阳家“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前已言之,《诸子略》所言阴阳家之长,即是《尧典》所命羲和之语。
是则依《诸子略》所叙,儒、道、阴阳三家溯其源俱出于羲和之职。羲和之职掌如《尧典》、史公、应劭所言,乃是天文星历,数术占筮。故而《汉书·艺文志·数术略》小序曰:“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史官之废久矣,其书既不能具,虽有其书,而无其人。《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春秋时鲁有梓慎,郑有裨灶,晋有卜偃,宋有子韦;六国时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汉有唐都,庶得粗粗。”乃至其所列数术名家,皆不出应劭历举羲和后继之范围。果如是,又怎样区分儒、道、阴阳三家呢?换言之,就是儒、道怎样超越祝卜。
马王堆汉墓帛书《易传》之《要》篇有云:
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39)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40)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41)此节点睛之笔在“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一语。“同涂殊归”与司马谈所引《易传·系辞上》“同归而殊涂”正相反对。此所载孔子乃谓己与巫史同读《周易》(同涂),但所求不同(殊归)。孔子所求者为“德”,那么,巫史异于孔子的所求是什么呢?
众多学者都指出此文可与《周易·说卦传》相参,其文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42)郭沂进而认为:“此将《易》分为五个层面,而其‘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分别相当于《要》篇的‘赞’、‘数’、‘德’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正是《易》的最基本的内容,它们已经涵盖了其他两个层面。”(43)就《要》篇此文而言,池田知久的分析非常到位:“‘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是欲在‘巫-史-君子’这样的人的等级系列中,把‘巫’放在最低的位置。……自不待言,是与‘赞-数-德’这样的德义系列相对应而考虑‘巫-史-君子’这样的等级系列的。”(44)由此,可以发现“《要》篇所包含的不同于《易》的另一个侧面,是分发展阶段构想了三种世界——只进行‘幽赞’的咒术式的宗教世界,依赖于‘明数’的理法的哲学世界,达到‘德义’的伦理的政治世界。而且,最高的‘德义’(君子)阶段,作为作者的理想世界建立在最低的‘幽赞’(巫)阶段以及由之发展而来的‘明数’(史)阶段之上,但那也并不是否定‘幽赞’和‘明数’,而是把后两者作为达到前者的必要阶段而包摄在自己之内”(45)。
众所公认,《要》之“幽赞”,即《说卦》之“幽赞”,同为马王堆帛书的《易之义》中也有与上引《说卦》之文约略相同的文字,首句作“[幽]赞于神明而生占也”(46),“赞”应是与“数”、“德”词性一致的名词。《说卦》释文云:“本或作赞。”汉《孔庙置守庙百石孔和碑》用《说卦》语作“幽赞神明”(47)。看来“赞”之义应从言辞方面考虑。邢文提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解释,他认为,《要》篇文字提示我们,“‘赞’的主语,应为‘巫’无疑。《说文》:‘巫,祝也。’‘祝,祭主赞词者。从示,从儿、口。一曰从兑省。《易》曰:兑为口,为巫。按《说卦》:‘兑为泽,为少女,为巫,为口舌’。很明显,巫主赞词,与‘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相合。赞,告赞。……诸‘赞’,释作‘祝告’,皆较前引各家释说平易通顺”(48)。陈来亦谓:“赞即祝也。”(49)检《说文解字·贝部》:“赞,见也。从贝,从兟。”段玉裁注:“此以迭韵为训。疑当作所以见也。谓彼此相见,必资赞者。《士冠礼》赞冠者,《士昏礼》赞者,注皆曰,赞,佐也。《周礼·太宰》注曰,赞,助也。是则凡行礼必有赞者,非独相见也。”(50)望山1号楚墓卜筮祷词简有云:“爨月丙辰之日,邓逪以小筹为悼固贞:既痤,以闷心,不纳食,尚毋为大蚤(尤)。占之:恒[贞吉]□。”(51)《周礼·春官·占人》:“凡卜筮既事,则系币以比其命;岁终,则计其占之中否。”郑玄注:“既卜筮,史必书其命龟之事及兆于策,系其礼神之币而合藏焉。”考《周礼·春官·大卜》:“大卜掌三兆之法……其经兆之体,皆百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郑玄注:“颂谓繇也。”孙诒让《周礼正义》:“《左》闵二年传云‘成风闻成季之繇’,杜注云:‘繇,卦兆之占辞。’《周易》释文引服虔云:‘繇,抽也,抽出吉凶也。’案:卜繇之文皆为韵语,与诗相类,故亦谓之颂。”(52)扬雄《方言》:“赞,解也。”郭璞注:“赞,讼,所以解释理物也。”“讼”即“颂”古字,“理物”当作“物理”(53)。则占筮之辞亦当可称为“赞”。在《要》篇中,“赞”对应于巫,邢文引《左传·僖公二十一年》“公欲焚巫尪”杜预注“巫尪,女巫也,主祈祷请雨者”,《公羊传·隐公四年》“于钟巫之祭”何休注“巫者,事鬼神,祷解以治病请福者也”,据以谓:“可见先前古巫之职中,包括了祝告祈祷的内容。”(54)邢说甚是。巫之赞辞系针对具体人和事而作,从儒学德义的角度来看,无疑缺乏超越性,这也正合于阴阳家之短——司马谈有谓:“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诸子略》则曰:“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这里只有人对于鬼神的畏惧和顺从,取消了人自身的真实性。因此无论是《要》篇中史、儒之超越于巫,还是《说卦》中圣人作《易》,都必须否定“巫-赞”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某些《易》学旧注在解释“幽赞于神明而生蓍”时过于执著于筮占层面,《说卦》讨论“生蓍”、“生爻”的前提是“作《易》”,而《周易》虽然仍是占筮之书,却与巫祝之占是截然区分的。这一区分就在于“幽赞”。《要》篇中“幽”与“明”相对,且均带宾语,当为动词。《说卦》荀爽曰:“幽,隐也。”此亦据《说文解字》(55)。《易传·系辞下》:“微显阐幽。”惠栋曰:“《仓颉篇》曰,阐,开也。幽,隐也。幽者阐之反,《吕氏春秋》曰隐则胜阐是也。”(56)只有忽略赞辞的具体事件,才能与巫相区分。“幽”即微隐藏匿,“赞”即筮辞(57)。
《要》篇云“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继曰:“赞而不达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乎德,则其为之史。”介于“巫-赞”与“儒-德”之间的,厥为“史-数”。邢文历稽载籍,据《国语·晋语》“筮史占之”,以为“筮官可名作史”。又引《左传·僖公十五年》:“韩简侍曰,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尤其考古发现的数字卦,“可见,筮、数有着古远的传统。”(58)池田知久释“明数”为“通晓《易》所包含的数理系统”(59)。廖名春将此“数”对应于《说卦》“参天两地而倚数”:“演易必须‘倚数’,故云‘达乎数’。”(60)赵建伟曰:“达数,精通《周易》的占法蓍数。”(61)汪显超分析道:“史巫筮占易学在表现形式上是‘数’的演算,演卦就是演数,卦象就是演卦结果的数字记录,解卦就是分析卦象这种特定的数字组合。”(61)陈来则以“数”为“天道变化的数度”、“宇宙变化的数度”(62)。其说过泛。“数”之解当紧扣《周易》卦爻占筮理解,否则即非“同涂”。筮生数,数生卦,卦生象,故《易传·系辞上》曰:“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但无论是八卦、六十四卦,都不足以对应于万物之众。提纲挈领的方法,就是取类。《易传·系辞上》:“其称名也,杂而不越。”韩康伯注:“备物极变,故其名杂也。各得其序,不相逾越,况爻繇之辞也。”又:“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因贰以济民行,以明失得之报。”韩康伯注:“托象以明义,因小以喻大。变化无恒,不可为典要,故其言曲而中也。”于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见矣”。哪怕某则卦爻辞确系出于某一具体事件的占筮,但在《周易》之中已经具备了类的普遍意义。这也正是史所以超越于巫之处。因为史之职掌要求其必须超越个体人的有限生命,在时空交汇中形成国族命运的思考。由是,以《周易》卦爻进行占筮时,占筮者便不再如俗占一般仅仅陷溺于某一具体事件之中,而是将自身的遭遇归之于类,从而可以以故事、先例的方式来处理眼前的难题(64)。《诸子略》曰:“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不但要“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事——此乃《易》、《老》所谓“器”,更要达于“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此“道”即超出于具体事件而知“类”。执类以御万有,“秉要执本”,就成为“君人南面之术”,可以如太史谈所言,“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举例来说,《诸子略》道家类第一种书为《伊尹》,《史记·殷本纪》伊尹“言素王及九主之事”,裴骃《集解》引刘向《别录》具列九种君主,但文有错讹,幸赖马王堆帛书《伊尹·九主》得以校正。其详为:法君、专授之君、劳君、半君、寄主、破邦之主二、灭社之主二(65)。这正是将历史上的君主归纳为九种类型,实际上也就是九种治国方式。最简类型就是《易传》的“阴阳”。这一二分模式也见于《老子》,如“刚柔”、“上下”、“有无”等等,不一而足。其术复为法家吸纳。韩非五蠹、八奸、二柄等,都是非常细密的分类。所以,太史公以老子韩非同传,良有以也。至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吏为师,以更为严苛的分类牢笼天下,甚至于不得兼方(66),故《史记·秦始皇本纪》有占梦博士。
分类的弊病,正在于如果陷入纯技术之中不能自拔,就会有无限分类的倾向,以致走到了自己的反面,成为阴阳家的“泥于小数”。如《周礼·春官·大卜》记龟兆的类型:“其经兆之体皆百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郑玄注:“百二十每体十繇,体有五色,又重之以墨坼也。”区区龟壳上,竟然会出现上千种卜兆类型,这又有何类型可言?必须再次超越“史-数”,上跻“儒-德”。于是儒便得以超越于巫史,亦即超越于占筮传统,吉凶祸福皆依于一己之德行,而非定于外在之鬼神,此即《荀子·大略》所谓:“善为易者不占。”(67)此正《要》篇所载子曰:“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有争议的是此处“德义”的理解。李学勤认为“文中的‘德义’二字,不能作道德、仁义解”。并引《易传·系辞上》“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义易以贡”,论证“孔子所观的‘德义’,当即这里所说的蓍、卦之德,六爻之义,也就是神、智和变易”(68)。陈来则先是提出“其中‘德义’有双重意义”,即一方面如李学勤所说,为蓍卦之德与六爻之义,另一方面指《说卦》的“和顺于道德”、“理于义”,“以发展和完善人的德性人格。如果说《系辞》重在前者,即探讨宇宙大化的变易在理,那么《要》则更强调后者”(69)。此后,陈氏再进一步,明确“《要》篇所说的‘德义’‘德’就是指道德、德性,这从《要》篇本文可以看得很清楚,如孔子说‘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者而义行之耳。’其所说‘观其德义’‘达乎德’就是要落实为仁知而义行之。孔子又说,‘吾求其德而已,君子德行焉求福,仁义焉求吉’,强调儒者以德行求福而很少祭祀,以仁义求吉而很少卜筮,可见这里所说的‘求其德’就是指仁义德行”(70)。至李学勤出版《周易溯源》,重作《帛书〈要〉篇及其学术史意义》,已改援《说卦》释“德义”为“顺于道理而理于义”(71)了。丁四新也引用帛书《二三子》:“《易》曰:‘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孔子曰:‘此言大人之广德而施教于民也。夫文之教,采物毕存者,其唯龙乎?德义广大,法物备具[者],其唯圣人乎?’”论曰:“此德义,大概也是指‘德行’、‘仁义’的意思。”并谓“观其德义”即帛书《衷》篇的“赞以德而占以义”的意思:“占系所谓的推衍之辞,或者说‘占’将卦之‘德’与‘义’连接起来:‘德’是卦义的本体,‘义’从作用的角度对卦义作了更进一步的推衍。既然‘义’是由‘德’生衍出来的,当然前者就可以被概括成后者,所以在帛书《衷》篇中,我们同样看到作者对于‘德’的强调:从‘筮’、‘数’之‘占’到‘德’之‘占’,这是孔门易学的根本精神。”(72)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邢文引《国语·楚语下》:“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纯、二精、三牲、四时、五色、六律、七事、八种、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百姓、千品、万官、亿丑、兆民经人畡数以奉之,明德以昭之,和声以听之,以告遍至,则无不受休。”认为这是以赞、数、德相配的显例,得出先秦古礼中,赞而数,数而德的关联渊源古远(73)。正如邢氏所说,这充其量也是赞、数、德相配,而非如《要》篇所孜孜以求的赞数德相分,邢说未能体现三者的层级区分,未允。
“同涂殊归”的超越之路虽可由个别思想者依循思想之脉络求得,但并不必然意味着这一路径可以在中华文明进程中大放异彩。这一超越之路事实上仅仅昙花一现地闪现在纯思想领域,并未获得进一步发展,尤其未能在政治哲学中得到运用。这是因为现实政治缺乏适宜的土壤。古语所谓“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伪古文《尚书·说命》),美国汉学家倪德卫援引西方伦理学称之为“意志无力”:“孔子和孟子痛切地知道意志无力的可能性,因为在他们的学生和在他们设法鼓动的政治领袖中看见这种无力。倪德卫争辩说,对孔孟来说,最明显的意志无力是漠然,并且这(部分地)反映了早期儒家的社会处境。他们典型地依赖于统治者的赠品或俸禄。但是,接受不足道的统治者的赠品有助于给他们合法的地位。结果,不合适地接受不恰当的赠品是儒者最偏爱的道德无力的范例。当接受赠品时我一开始就处于被动的状态,其他人的行动的目的和要避免的诱惑也处于被动的状态——不能唤起道德耐力去拒绝赠品——这是意志无力第二种类型(漠然)的例子。”(74)随着战国后期集权政体的逐步建立及加强,自由思想的空间越来越小,儒者及其他诸子对集权的抗争也越来越微弱。虽然在秦末起义中孔鲋曾“为陈王涉博士,死于陈下”(《史记·孔子世家》),但在汉代,儒生最终还是和君权达成了合作。于是,《要》篇“同涂殊归”的超越之路虽然传到了汉初,却终归湮灭,在汉代思想涌动的大潮中难觅踪迹。与之相映成趣的。恰恰是汉儒一头扎进阴阳五行灾异谶纬之中。
先秦诸子常思依附于权力,为帝王师,以至于为得君行道,主动扼杀精神之独立、思想之自由,为权力一统思想,多所谋划,最终由董仲舒、司马谈至刘向、刘歆父子告厥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谈“同归而殊涂”,向歆父子“诸子出于王官”,使得诸子被重新纳入一统天下的官学架构之中,归于湮灭。兹以《诸子略》前三家儒、道、阴阳为一组分析。《诸子略》以三家出于司徒、史官、羲和,实则均可溯源于羲和之官,子学中超出相应官守职掌的天下之学遭到贬抑。与“同归殊涂”的沉沦之路相反,马王堆帛书《要》篇清晰地勾勒了另一“同涂殊归”的超越之路。巫、史、儒都以《周易》占筮,然而其方法与追求迥异。不拘执于具体事件而超越于巫,进入《周易》,通过卦爻的类型化理解,驾驭万事万物,是为史官—道家。不陷溺于繁琐的分类,而追求德义,便能超越于史,而成为儒。毋庸置疑,《要》篇虽然长期失传,其思想却死而不亡,从而为今人带来更多思想的启示。
注释:
①释道安:《二教论》,释道宣编:《广弘明集》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9页;参见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原道》,《校雠通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页。
③章太炎:《诸子学略说》,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87-306页。
④刘师培:《周末学术史序·总序》,钱玄同编:《刘申叔遗书》上册,扬州:广陵书社,1997年,第504页。并可参考该书所收《古学出于史官论》、《补古学出于史官论》、《古学出于官守论》诸文。
⑤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第16-17页。
⑥张采田:《史微·内篇》,《民国丛书》第五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第60册,第11-12页。
⑦刘咸炘:《子疏定本》,黄曙辉编校:《刘咸炘学术论集·子学编》上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2页。
⑧江瑔:《读子卮言》,台北:广文书局有限公司,1982年,第27-28页。按:尹桐阳《诸子论略》一书篇目及内容多与江书雷同,此语见第6-7页(台北:广文书局有限公司,1975年)。考江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首刊于1926年,尹书由北京民国大学初印于1927年,或尹袭江书耶?
⑨孙德谦:《诸子通考》,台北:广文书局有限公司,1975年,第242-243页。
⑩曹耀湘:《墨子笺》,北京图书馆编:《墨子大全》第一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第19册,第684页。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以为曹氏“要言不烦,其说是也”(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46页)。
(11)胡适:《胡适文存·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80-186页。
(12)常森:《先秦诸子研究》,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0页。
(13)章太炎:《论诸子的大概》,沈镕纂集:《国语文选》第一集,上海:大东书局,1931年,第24页。
(14)柳诒徵于胡适有系统驳斥,参见柳诒徵:《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柳曾符、柳定生选编:《柳诒徵史学论文续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513-539页。参见李若晖:《诸子出于王官说平议》,《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32-148页。
(15)罗焌:《诸子学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8页。
(16)参见刘中建:《专制王权的依附型合作者》,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3-24、37-42页。刘氏所论主要为儒士,但实际上诸家都是如此,只是对权力的依附程度有深浅而已。最深者为法家,直接参与到现实政治之中。最浅者为道家,但《老子》仍然针对王侯有所建言。关于这个问题,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展开,将另撰文详论。
(17)牟钟鉴先生认为:“阴阳家的思想在《吕氏春秋》中建构了一种形式完备的世界图式,然而未能成为贯穿全书的主线。”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87年,“序”第3页。《吕氏春秋》十二纪全以阴阳家思想撰成,居全书之首,虽未能贯穿全书,是其融合诸家构造完整体系的能力不足所致,不足以否定其以阴阳家思想统一诸家的基本意图。
(18)王蘧常:《诸子学派要诠》,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162页。何泽恒云:“今不知司马氏所见究竟是否与今本《系辞》有异文,若谓基本上是同一本,则为何不称《系辞》,而改称《易大传》?”何泽恒:《孔子与易传相关问题复议》,《先秦儒道旧义新知录》,台北:大安出版社,2004年,第51页。
(19)孙星衍:《周易集解》下册,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88年,第597页。
(20)池田知久据《老子》第五十一章“势成之”马王堆帛书本作“器成之”,认为“《老子》的这一部分中,毫无疑问显然存在着和马王堆帛书《易传·系辞》(包括今本《系辞上传》)相同类型的‘道器论’。”参见[日]池田知久:《道家思想的新研究——以〈庄子〉为中心》,王启发、曹峰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45页;[日]池田知久:《〈老子〉的“道器论”》,《池田知久简帛研究论集》,曹峰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5-29页。
(21)楼宇烈已指出《老子》此处之“器”与《易传·系辞上》的联系。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注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76页。
(2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7页。
(23)沈文倬:《略论宗周王官之学》,《菿暗文存》,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436页。
(24)钱宗范:《西周春秋时代的世禄世官制度及其破坏》,《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
(25)章学诚:《校雠通义》,王重民通解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页。
(26)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78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55页。
(27)[法]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
(28)房玄龄等:《晋书》卷九十四《隐逸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433页。
(29)金景芳:《〈尚书·虞夏书〉新解》,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61页。
(30)参见陈品卿:《尚书郑氏学》,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77年,第176页。
(31)李振兴《王肃之经学》云:“王氏好攻郑氏,其所云‘五品,五常也。’当指《孟子》五伦而言也。”(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80年,第175页)按:五常为仁义礼智信,非五伦,其说非。
(32)参见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四部要籍注疏丛刊·尚书》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813页。
(33)马晓斌《汉书艺文志序译注》标点及翻译皆以“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三者并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7-38页),误。
(34)参见黄朴民:《天人合一——董仲舒与汉代儒学思潮》,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第57-63页。
(35)参见黄克剑:《〈周易〉“经”、“传”与儒、道、阴阳家学缘探要》,《中国文化》1995年第12期。
(36)参见韦政通:《董仲舒》,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第77-78页。
(37)参见李若晖:《顺阴阳,明教化——〈汉志〉儒家小序引用〈尧典〉发微》,《孔子学刊》第三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85-89页。
(38)参见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27-128页。
(39)廖名春于阙文补“守”字,裘锡圭以为“恐不可信”,今仍作阙文。参见裘锡圭:《帛书〈要〉篇释文校记》,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303页。
(40)“好”,裘锡圭指出“从照片看,此字右旁不可能为‘子’字。此字似不能释‘好’”。参见裘锡圭:《帛书〈要〉篇释文校记》,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辑,第303页。
(41)廖名春:《帛书〈要〉释文》,廖名春:《帛书〈周易〉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89页。
(42)参见李学勤:《周易溯源》,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375页。
(43)郭沂;《帛书〈要〉篇考释》,《周易研究》2004年第4期。
(44)[日]池田知久:《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之〈要〉篇释文》(下),牛建科译,《周易研究》1997年第3期。
(45)[日]池田知久:《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要篇〉的成书年代》,陈建初译,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编:《简帛研究译丛》第一辑,长沙:湖南出版社,1996年,第124页。
(46)陈松长、廖名春:《帛书〈二三子问〉、〈易之义〉、〈要〉释文》,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30页。
(47)参见洪适:《隶释》,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8页。
(48)邢文:《论帛书〈要〉篇巫史之辨》,李学勤、谢桂华主编:《简帛研究》第三辑,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19-220页。
(49)陈来:《马王堆帛书〈易传〉与先秦易学的分派》,《竹帛〈五行〉与简帛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240页。
(50)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80页。
(51)参见陈伟等:《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71页。
(52)孙诒让:《周礼正义》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926页。
(53)参见华学诚:《扬雄方言校释汇证》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910页。
(54)邢文:《论帛书〈要〉篇巫史之辨》,李学勤、谢桂华主编:《简帛研究》第三辑,第221页。
(55)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687页。
(56)惠栋:《周易述》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29页。
(57)参见李若晖:《马王堆帛书〈要〉篇“幽赞”解诂》,《简帛语言文字研究》第六辑,成都:巴蜀书社,2012年,第343-350页。
(58)邢文:《论帛书〈要〉篇巫史之辨》,李学勤、谢桂华主编:《简帛研究》第三辑,第221页。
(59)[日]池田知久:《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之〈要〉篇释文》(下),牛建科译,《周易研究》1997年第3期。
(60)廖名春:《帛书〈要〉试释》,《帛书〈周易〉初探》,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第135页。
(61)赵建伟:《出土简帛〈周易〉疏证》,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第271页。
(62)汪显超:《孔子“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含义考释》,张新民主编:《阳明学衡》第二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7页。
(63)陈来:《马王堆帛书〈易传〉与先秦易学的分派》,《竹帛〈五行〉与简帛研究》,第240页。
(64)陶磊曾区分巫易与史易,惜乎未引《要》篇之文:“易在占卜中的运用有两种形式,一种为巫易,其吉凶判断由巫者个人依据具体的处境给出,或者依据其神秘能力作出判断;或者作简单处理,如卜筮祭祷记录所见,一概断为吉。另一种形式是依据像《周易》这样的卜筮书来判断吉凶,如阜阳汉简《周易》所附的卜辞就是为这种形式的易占服务的,笔者称之为史易。”陶磊:《思孟之间儒学与早期易学史新探》,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50页。
(65)参见李学勤:《试论马王堆汉墓帛书〈伊尹·九主〉》,湖南省博物馆编:《马王堆汉墓研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0-118页。
(66)《史记·秦始皇本纪》张守节《正义》:“言秦施法,不得兼方者,令民之有方伎,不得兼两齐。……言法酷。”
(67)邢文举《要》篇“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一语,以之为该篇“巫、史不辨例”,并认为这是“《要》篇中残存的一种古代观念”。参见邢文:《论帛书〈要〉篇巫史之辨》,李学勤、谢桂华主编:《简帛研究》第三辑,第227页。按,此非巫史不辨,而是儒同时超越巫史,作为被超越者而言,此处巫史无别。
(68)李学勤:《孔子与〈易〉》,李缙云编:《李学勤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92页。
(69)陈来:《马王堆帛书〈易传〉与孔门易学》,《竹帛〈五行〉与简帛研究》,第224页。
(70)陈来:《马王堆帛书〈易传〉与先秦易学的分派》,《竹帛〈五行〉与简帛研究》,第241页。
(71)李学勤:《周易溯源》,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375页。
(72)丁四新:《〈易传〉类帛书札记十六则》,《玄圃畜艾》,北京:中华书局,2009页,第222-223页。
(73)邢文:《论帛书〈要〉篇巫史之辨》,李学勤、谢桂华主编:《简帛研究》第三辑,第225页。
(74)[美]万白安:《导言》,[美]倪德卫著,[美]万白安编:《儒家之道:中国哲学之探讨》,周炽成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