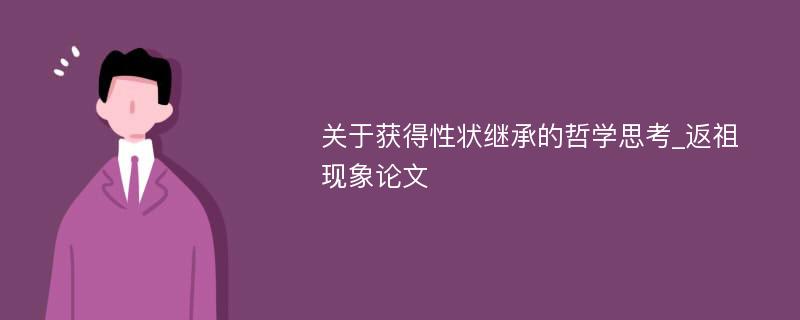
关于获得性状遗传的哲学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性状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九世纪初,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在其不朽著作《动物哲学》中首次系统地阐述了生物进化的思想,抨击了当时泛滥于世的物种不变论,“根据自然哲学,奠定整个生物学的基础”。①但作为拉马克学说两大支柱之一的“获得性状遗传”理论却不断受到各方面的非难,“被贴上‘愚昧无知的、迷信的、声名狼藉’的标签”,②魏斯曼的“种质论”、摩尔根的“基因论”以及被奉为分子生物学圭臬的“中心法则”似乎都是否定它的;还有人宣称,“在分子描述中没有获得性状遗传的位置”。③正如获得性状遗传现象需要时间证明一样,其理论同样要经受时间的考验。一些人坚信,获得性状遗传理论蕴含颠扑不破的真理,必然在科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中显示出来,本文试图从哲学角度阐释获得性状遗传的意义,澄清人们对它的种种误解,进一步论证其合理性。
一、基本概念诠释
1、同化和异化
同化和异化是生命新陈代谢的最基本方式。生物在同外界进行质量、能量交换中,不断将外在物质转化成自身物质,这就是同化,对外在物质而言则是异化;生物还逐渐将自己转化为外在物质,这就是异化,对外在物质而言则是同化。
生物发展中的同化和异化表现为遗传、发育和变异。德国生物学家魏斯曼提出了“种质论”,其要义是:遗传的方式是种质延续,发育的内在原因是种质决定体质。“种质论”把遗传和发育区别开来,对揭示生命运动规律有积极意义。生物要将自身同一性延续到后代,就需要复制与自己相同的新个体。这是前代对后代的同化,也是遗传的基本意义。由于遗传是粒子延续而不是整体延续,因此每一代都有发育过程,这是种质对体质的同化。这两种同化,前者是遗传信息的横向转移,后者是纵向表达。遗传和发育是相辅相成的。没有遗传,发育就没有依据;没有发育,遗传就没有对象。有机体各部相互同化和外界环境对有机体的同化作用,使有机体发生异化,即生物在生命运动的每一瞬间都在否定自身同一性,这就是变异的来源。遗传、发育和变异是生物进化的前提,没有遗传和发育,物种无法存续;没有变异,生物永远只有一种形态,自然谈不上进化了。
然而,魏斯曼将种质的连续不变性和遗传与发育的区别绝对化了,在理论上失之偏颇。首先,遗传中前代对后代的同化必须通过连续物质实现。但种质所连续的只有一半,另一半是复制的。复制在种质与外界环境相互同化过程中进行。当外界环境显示同化作用时,复制就会出现差错,种质就发生变异了。因此种质既是连续的,又是不连续的。这是魏斯曼未认识到的。其次,“种质论”认为种质可以决定体质而体质不能影响种质,遗传可以决定发育而发育不能影响遗传,即种质与体质之间的同化是单向的。实际上,种质与体质是同源的,(70年代有人提出DNA和蛋白质均起源于RNA)随着生物的进化和有机体的分工,遗传信息逐渐趋向某些部分,于是形成了种质。在此过程中种质与体质在层次上出现了分化,并对体质起主导作用,两者的相互同化也逐渐由双向趋于单向,即深层种质可以同化表层体质,而反之则难以实现,没有这种单向同化,就没有遗传的稳定性。然而,尽管种质与体质越来越分化,但两者的同一性永远不会完全消失。无论生物进化到何等高级阶段,种质与体质之间也没有绝对界限,百分之百纯的种质是不存在的。在个体发育中,同一性越来越趋向早期,但绝不会逾越这一阶段。因此,种质与体质之间的单向同化是相对的,是随着它们的分化而逐步加强的,无非是种质一方同化力量较强而已。
生物的获得性状一般认为是发生在体质上的变异,也即发育阶段的变异。对于这种变异,拉马克认为积累起来可以遗传,而魏斯曼则认为是不会遗传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体质上的变异能否影响种质?我们认为,种质完全随着体质而变化是不可能的,否则就没有稳定的物种;然而既然种质与体质之间的单向同化是相对的,种质对体质的变异不会丝毫无动于衷,体质的变异经过许多代积累可以在种质上显示出来。这就是获得性状遗传的理论依据。由于种质与体质是同源分化的,因此低等生物和高等生物发育早期,有机体内同一性程度较高,单向同化尚不明显,发生的变异比较接近于种质,遗传倾向较明显。如果变异发生在种质复制阶段,就是基因突变。而在高等生物发育晚期,有机体内多样化程度较高,种质与体质已明显分化,种质单向同化力量较强,体质对种质的影响力较弱。遗传倾向就不明显。然而,生物为保持自身同一性,对变异有修复功能,于是存在一个变异复原问题。生物在低级阶段或发育早期再生能力较强,变异复制倾向较明显。如蝌蚪断肢能够再生,发育成青蛙则丧失此功能;动物受精卵分裂为二,结果发育成同胞孪而不是两半。生物再生的部分(同胞孪可以理解为一半早期再生)同原来或多或少会有差异,积累起来会影响种质。对种质本身而言,DNA复制中的差错也会在聚合酶的作用下进行校对和纠正,但仍然会有部分差错未能修复而遗传下去。
2、可能性和现实
可能性是物质存在和演变的内在依据;现实是物质的存在形态,是可能性在外界条件作用下的表达。可能性和现实之间有因果关系。可能性对现实起直接的决定作用,而现实则通过外界条件间接地对可能性起影响作用。由于物质是多层次的,层次间又有相对意义。所谓可能性是相对较浅层现实而言的,其自身还有更深层次的内在依据,于是又呈现为一种内在现实,因此物质在不同层次上都有可能性和现实两重性。由于物质深层次同一性程度较高,层次界限和因果关系也趋向不明显,因此越是深层次的可能性越不容易为人们认识。但只要物质没有实现绝对的同一性,其层次界限和因果关系就不会完全消失,不同层次的可能性一定会以各种方式起作用。
在生物遗传和发育中,可能性和现实指基因和表型。生物的基因是遗传信息的载体,一般认为就是DNA片断上的核苷酸顺序,它是通过双螺旋结构的半保留复制实现信息传递的;表型被认为是有机体性状。分子遗传学的“中心法则”(DNA→RNA→蛋白质)表明,只能由核苷酸序列决定氨基酸序列,而不能相反,从而排除了遗传信息从表型到基因的流向。虽然后来发现了RNA→DNA的反向转录,但并没有改变信息从DNA到蛋白质的单向关系。这是因为DNA或RNA复制及DNA与RNA之间的转录是通过A-T(或A-U),G-C的碱基配对实现的,在正常情况下,它们之间的对应是唯一的,信息运行是可逆的,它们也可以互为模板,因此RNA→DNA反向转录是可行的。而RNA→蛋白质的密码翻译是由64种核苷酸经过简并对应着20种氨基酸,是多一对应关系,例如决定亮氨基的密码有6种。信息从核酸流向蛋白质是确定的,而逆行则会迷失方向。因此蛋白质不可能与核酸进行直接对等的信息交流,也不可能以蛋白质为模板合成核酸。有人正以核酸与蛋白质的特殊关系作为获得性状不能遗传的理论依据,认为“从DNA到蛋白质的不可逆的信息传递又进一步说明了环境在遗传信息上不能引起拉马克式的改变(即获得性状遗传)而只能起选择作用。”④
但仔细想来,问题不这么简单。生物的获得性状是从基因到表型的发育过程(也可以说是基因表达过程)中的变异。而“中心法则”反映是大分子之间信息传递,并不涉及分子以上和以下水平,因此无法反映基因与表型、基因与自身内部原因(更深层决定子)两种纵向关系。也就是说:“中心法则”是只讲遗传而不管发育的,它把DNA当成了极终的基因,所以无法解释DNA变异的原因。对于获得性状遗传,必须从分子以上和以下水平,并结合外界条件的作用综合考察。虽然从蛋白质到核酸直接信息流向被否定了,但是外界条件对物质各个层次都会起作用,作用于核酸和蛋白质时产生有机体性状,作用于分子水平以下的原子、电子时决定DNA等遗传基因的分子结构,而这些作用的相关性将使生物的获得性状影响DNA的变异。基因的复制过程中的变异(差错)同表达过程中的变异(适应)是有联系的,但并不意味着两种变异可以以对号入座,而只是表示后者能对前者起一定的导向作用,或者说影响前者发生的几率。如果说基因突变是纯偶然的,那么它发生在任何方向上的机会都应该是均等的,而发育中变异对它的作用正在于打破这种均等。海克尔认为:“个体在生活中所获得的新的特质,可以部分地对卵细胞和精细胞的种质的分子组合起反作用,并在某种条件下,(当然作为潜在的张力)遗传给下一代。”⑤只要我们重视DNA的两重性,这种反作用是可以理解的。此外,蛋白质对核酸的反作用还表现为酶的催化作用。离开了酶,核酸的复制和转录都是不可能的。在这里蛋白酶是作为外界条件发生作用的。
必须指出,DNA对于有机体性状是基因对表型的决定作用;而有机体性状对于DNA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外界条件间接实现的,是缓慢而潜移默化的。由此可见,获得性状遗传也需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
3、积淀和重演
积淀的含义是,现象在本质上的积累,或者说是后成向先成的转化,其原因是物体的相互作用。我们也可以说本质是现象的积淀。但现象并不是直接进入本质,而必须经过浓缩后转化为本质。所谓浓缩就是减少个别和偶然性因素,表现为两方面:一是横向(空间范围)的缩减,即物质种类之间的抽象,是从个别到一般的过程;二是纵向(时间度向)的缩减,即不同时期物质形态的概括,是从偶然性到必然性的过程。积淀是通过物质各层次之间由表及里的同化实现的,因此现象进入本质时的浓缩也是多次连续的。只要有新的成份进来,原来各层次就要连续进行浓缩,并递进至更深层次。于是越深层的积淀物越浓缩,同一性和整体性程度也越高。由于进化过程中不断有新的积淀,所以物质形态日趋复杂,层次愈益丰富。
重演是积淀的反过程,是本质表现为现象,先成转化为后成,将历史积淀的过程由里及表依次再现出来。由于积淀时已经过多次浓缩,重演时也不是原封不动的再现。越早期的因素,重演时越迅速、抽象,所表征的时空范围越大,预成的成分越多;越晚期则越趋现实,后成的成分越多。由于积淀时缩减了偶然性因素,物质形态发生时,以重演中的必然性因素(先成成分)为内在依据,与当前现实的外界条件(后成成分)相结合,产生新的现实形态。
积淀和重演有一个连结点,就是“现在”。积淀是从现在到过去,重演是从过去到现在。“现在”既是积淀的开端,又是重演的终点。由于“现在”是转瞬既逝的,因此在积淀和重演中,开端和终点的延伸也是无止境的。
对生物而言,积淀和重演表现为基因和表型的关系。从表型到基因是积淀过程,从基因到表型是重演过程。DNA作为分子水平上的基因,由个性到共性相关上溯,它积淀了该种系、古生物乃至早期宇宙的发展史,同时自身的核苷酸含量逐渐增加,分子结构日趋复杂;而DNA本身的生成,又要重演从无机物到有机大分子的进化历史,每一条DNA分子链都不能例外。从DNA到有机体性状的产生,重演还要延续到古生物界、该种系乃至其亲代的进化过程。根据“贝尔法则”,所有脊椎动物在分类上亲缘关系越接近,胚胎相似程度就越大,相似期也越长;在发育中,门的特征最先形成,目、科、属、种的特征随后依次出现。这说明脊椎动物胚胎阶段要重演该门类动物进化历程。生物的基因既是历史积淀的结果,又是现实重演的起点,每一代的起点在不断提高。个体发育是先成与后成、历史与现实的统一,是在展现基础上的创造,其内在必然性来自种系进化中的大量偶然性。个体发育中的变异是偶然事件,当它积淀入基因时,就具有了必然性。生物子代接受的是亲代父本和母本两套信息,其每一表型都有两种基因表达的可能,但往往只能取其一。这是因为在等位基因中,有些由于重演机会多,积淀物较充足,在表达上占优势,结果进化成显性基因;反之则成为隐性基因。从积淀和重演的理论出发,我们认识到遗传不仅仅是子代和亲代两代间的关系,而是所有祖先积淀总和的延续,是一种历史整本的同化力量,这也是前述种质同化力量较强的原因。
我们论述了从表型到基因的积淀,实际上也就肯定了获得性状遗传。由于积淀中越深层在时间度向上越浓缩,所以表型向基因积淀时越进入深层所需时间也越多,因而是一个长期过程。我们不能把获得性状遗传庸俗地理解为子代对亲代任何变异的简单继承,但变异经过许多代的积淀进入DNA,就能够遗传。在个体发育的早期,重演的是积淀在深层的内容,因此变异发生得越早对基因的影响越大。所谓基因突变无非是变异发生在重演的早期——DNA复制阶段,这种变异无疑是遗传的。我们终于发现,基因突变与获得性状并没有本质区别,只是在重演过程中前者变异发生较早,后者发生较晚而已。我们也可以广义地把基因突变看成分子水平上的获得性状。
二、遗传现象剖析
1、关于魏斯曼割鼠尾试验
魏斯曼曾作过一项著名试验,将鼠连续22代割去尾巴,而后代仍然长出尾巴。科学界有人断言据此便足于宣判获得性状遗传的死刑。韦斯科夫说:“生物结构的进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是,获得性不能遗传,个体在躯体结构上所遭受的变革永不会遗传给后代”,“躯体结构所遭受的变异对于细胞之中含有新个体蓝图的核酸并无影响。只要蓝图把尾巴设计在内,后代就要长出尾巴来,不管亲体的尾巴发生了什么情况”。⑥
我们认为这项试验是建立在对获得性状遗传曲解的基础上的。有机体性状的生成或消失是基因与外界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诸如尾巴一类活动肢体的消长,可以用拉马克“用进废退”的原理解释。动物之所以生出尾巴,是因生存需要经常使用的缘故,是无数代的表型积淀在基因上的结果。尾巴的消失须通过两个途径;一是渐变的途径。如果置鼠于尾巴无用的环境,鼠尾由于不用而“废退”,经历许多代以后,这一退化过程积淀入基因——在这里我们必须将DNA理解为多层次的。由于后代尾巴的发育要以积淀的层次为序重演前代尾巴的退化史,当尾巴“蓝图”缩入DNA的某一较深层次,而无尾现象的积淀也达到DNA时,尾巴的重演就不会超越胚胎阶段,于是鼠出生时就没有尾巴了。从猿到人过程中,尾巴也是因不用而退化乃至消失的。达尔文说得好,“对于蜣螂前足附节的完全消失以及对于某些其他属性的残迹状态,如果认为不是一种肢体残废的遗传,而是由于长期不使用的结果,也许最为妥当。”⑦二是突变的途径。既然鼠尾是无数代历史积淀的产物,想要将它永远割去,就必须在重演初期动手术,把历代鼠尾性状的积淀物一起割掉。倘若在DNA复制阶段把“蓝图”中的尾巴“割”去,使复制出现差错,从而产生无尾新“蓝图”,后代自然是没有尾巴的。但尽管我们可以改变现实,却无法抹煞历史。即使在“蓝图”中把鼠尾割掉了,但鼠在历史上是有尾巴的,因此在胚胎阶段时尾巴不会完全消失,并且只要在以后的环境中尾巴仍然有用,若干代后它将不可抗拒地再长出来。
然而魏斯曼并没有致力于创造一种环境压力去影响鼠尾发育,使鼠的基因在外界条件作用下产生无尾表型,而是在鼠尾已经长出来后(实际上已完成了尾巴进化的大部分重演)再作机械损伤,企图用几十代的表层手术割去亿万代的深层积淀,以求产生无尾或尾巴显著缩短的后代,实在是徒劳的,正如武谷三男所言,“魏斯曼的批判性的实验从头到尾贯穿着形式的机械论,没能得到任何结果不能不说是当然的。即这样的实验无法否定获得性遗传。”⑧
2、关于本能
美国一本生物学教科书对获得性状遗传理论提出质疑时问道:走绳索的杂技演员的子女一定是出色的走绳索者。这种说法对不对?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牵涉到生物的行为遗传——本能问题。
本能是生物进化过程中形成并通过遗传固定下来,对于个体是有生俱来或在发育中自然形成的行为,用黑格尔的话说“本能是一种以无意识的方式发生作用的目的活动。”本能由进化而成,任何复杂的本能都来自于原始生命最简单的趋利避害行为。这在学术界很少有争议。但对本能进化的方式却存在截然不同的观点,焦点在于习性(经验、习惯等)能否转化为本能。我们认为习性能够转化为本能。任何生物行为都是有机体结构的功能,严格地说生物所遗传的是结构而不是功能。我们把功能分成多级:直接依附于结构的为一级功能,本能随着机体器官等结构发育形成而自然产生,故属一级功能;由一级功能派生的为次级功能,习性是由本能衍生的,属次级功能。在结构与功能关系中,功能不仅取决于结构,也同化结构。这同“用进废退”原理是一致的,同功器官、同源器官的形成也证明了功能对结构的作用。一级功能(本能)的进化是次级功能(习性)同化结构的结果,也即习性积淀入有机体结构产生了新的本能。莫诺认为:“在生命体内的万事万物,包括遗传的天赋在内,不管是蜜蜂的刻板行为还是人类认识的先天框架都是来自经验,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可是万事都来源于经验,这并不等于都来源于每一新世代的每一个体所反复进行的当前的经验,而是来自源于物种在其进化过程中的所有祖先积累起来的经验。”但习性(经验)转化为本能是以获得性状遗传为前提的,即习性不仅要改变有机体结构,而且要改变DNA,新的本能才可能产生。当然这是一个从表型到基因的漫长历史进程。莫诺或许不知道,他的精彩表述有力地支持了获得性状遣传学说。
本能朝特化和泛化两个方向进化。一些生物由于所处环境较稳定而封闭,故习性也较单纯,每次都以大致相同的行为模式注入有机体结构,使结构趋向专化和固结,原来次级功能的任务逐渐由一级功能承担了起来,其结果是一级功能的强化和次级功能的退化。于是本能日趋具体、复杂和精巧,并逐渐取代了习性。它们的行为只能是“展现”而不可能是“创造”。另一些生物所处的环境多变并且是开放的,习性也较多样,经常以不同的行为模式注入有机体结构,结构不可能向某些具体行为方面专化,只能以增强多种适应性实现进化,它们的一级功能可以派生出无数次级功能。对这些生物而言,习性是以“素质”的形态和积淀入本能的,要求本能提高整体能力和可塑性。进化的结果是,这些生物(主要是人类)天生几乎一无所能,但其具备能够学会一切的能力。两种本能孰优孰劣?马克思说:“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头脑中把它建成了。”(12)然而蜜蜂有理由反诘:“可我在出世前就使蜂房在身体内形成了。”究竟谁更高明?我们认为还是建筑师。但高明之处并不在于他能够预先使建筑物在“表象中”或“观念地存在”,(13)而在于他能够不断地改进自己的作品,并创造出其它作品。蜜蜂建巢、蜘蛛织网固然造化精妙,而且是不学自会的,但它们在出世前已注定一辈子只会建蜂巢或织蜘网,而要改进自己的作品或创造另一件作品是无论如何办不到的。
我们再回答那本教科书的质疑,如果把人类的本能等同于蜜蜂的本能。企图以此来否定获得性状遗传,无疑是荒谬的。没有一个赞成获得性状遗传的人会认为“走绳索”一类的技艺会直接遗传给后代。但如果祖祖辈辈都是走绳索者,其后代在灵巧和平衡性等方面会有某些先天的长处,这也是必然的。
3、关于返祖现象
返祖是指子代与亲代不同却与祖先有相似性状的遗传现象,用达尔文的话说就是“消失了几十代、几百代,甚至几千代的性状突然重现”。(14)譬如,有的野马、毛驴、骡子身上呈现祖先才有的黑色条纹,人类也偶尔可见多乳头、有尾巴及浑身长毛等现象。
由于返祖现象是突然出现的,因而在解释上容易被认为是不利于获得性状遗传理论的。但事实正相反,返祖现象恰恰建立在获得性状世世代代遗传的基础上。由于获得性状能够遗传,生物不同层次的基因上积淀了无数代的表型性状。个体发育时的重演是以基因为起点的,但要有合适的外界条件才能实现。于是就产生了一个矛盾:从基因上说重演的是过去,而外界条件却是现在的。如果外界条件不合适,重演就会在某阶段中止;只要个体发育不停顿,表型就会按基因在重演中止时规定的性状呈现出来。重演中止和发育不停顿是返祖现象的两个前提。例如,人的祖先是有尾巴的,在人猿揖别的岁月中尾巴渐退化。因此人胚胎发育中要重演尾巴逐渐消失的历程。人在两个月胚胎期,可以分辨出5个尾椎,以后停止生产转变为骶骨。在此阶段,如果外界条件不合适,尾巴消失的重演过程将中止,而胚胎则继续发育,婴儿出生时就有尾巴了。这就是返祖的机理。既然返祖现象要以有机体发育为前提,重演只能在局部或晚期中止。如果重演在整体上中止,有机体实际上就停止发育,返祖就无从谈起了。如果重演在发育早期中止,肯定有致命的危害,其结果不是受精卵夭折就是胎死腹中,并且由于深层积淀物是高度抽象、概括的、所以即使重演中止而发育得以继续,在表型上也不可能完整地呈现当时的具体形象。由此可见,返祖现象只能发生在有机体局部,并且不可能回溯到过于古老的年代,也不可能充分发育。例如人类返祖现象大致只能以哺乳类动物为限。人类或许会生出尾巴的后代,但决不会生出一个猿猴;人与鱼同祖,人胚胎阶段有鳃裂现象,但绝不可能发育成真正的鱼鳃。
用基因突变的理论难以解释返祖现象。因为突变意味着新的取代旧的,DNA分子链新序列产生的同时,旧序列就不存在了。如果要实现返祖,就必须在很短时间内将过去漫长历史中偶然发生的一连串突变更偶然地反演一遍,而且需要自然选择的密切配合,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而获得性状遗传用的是积淀理论,即新的整合入旧的,旧的基因并未消失,只是经过浓缩而已,返祖就有了依据。
返祖现象会不会遗传?我们的回答是:如果返祖现象回溯的年代非常遥远,重演在DNA阶段中止了,从理论上讲,返祖现象应该是遗传的,但实际会扼杀发育,就不存在遗传问题;如果回溯年代较近,重演中止在较晚期,说明外界条件对深层作用不大,对DNA的影响也较小,所以需要许多代的连续积累才能显示遗传倾向,这同获得性状遗传原理是一致的。
顺便提一下,一部分人具有的某些“特异功能”(如超常的视、听觉等)实际上也是返祖现象,表明人类祖先曾有过这些功能,只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退化了。一些人在胚胎或儿童阶段因故中止了某些方面的重演,于是在感官功能上出现了部分与祖先相似之处,特异功能便产生了。特异功能可以通过诱发而产生,诱发实际上是人为中止重演,在儿童发育早期成功率较高。但必须指出,生物返祖现象的产生是以牺牲一部分进化成果为代价的,过多地诱发特异功能势必损害正常功能,对人的全面发展是不利的。
以上从理论上对获得性状遗传作了探讨和论证。在这里,我们还要对三个问题作补充说明。第一,按拉马克本意,获得性状遗传是建立在“用进废退”基础上的,因而“获得性”等同于“习得性”。而我们把生物在基因表达和适应环境中产生的变异统称为“获得性状”,而不论其是否自觉,所以“获得性”并不局限于“习得性”。在理论上,习得性遗传同基因突变是对立的。习得性遗传可以解释长颈鹿脖子的由来,但在解释其一身斑纹的起源时陷入窘境。如果我们把获得性状遗传推广到分子领域,就同“基因论”统一起来了,也就能圆满地解释生物的习得性及拟色、拟态等方面的遗传和变异。第二,新达尔文主义认为生物的变异同自然选择是不相干的,即变异在前,选择在后。变异本身是没有方向性的。自然选择只是规定方向,“沙里淘金”式地选择有利变异。由于纯随机发生的有利变异是微乎其微的,因此用基因突变理论无法解释生物精密器官或复杂本能的形成。皮亚杰说,如果形成眼睛“所必需的那些突变是同时发生的,那么,它们的概率只有10[42]分之一,换言之,在实际中等于0。反之,如果这是一个连续突变问题,其中,新的突变只是附加在先前的突变中,以致达到积累的效果,那么这种突变就需要许多代,它可以与世界的寿命相同,甚至超过它。”(15)而获得性状遗传理论认为生物的变异同自然选择是有机结合的,外界条件不仅作为选择尺度,而且直接影响变异的发生,即“有利与否”的尺度在变异发生时已经起作用了。因此可供选择的有利变异大为增加,生物进化中的许多疑难问题也迎而解了。第三,为了证明基因变异是纯偶然的、无因果关系的,莫诺等人借助于量子理论,认为“突变就其本身而言,是一种微观事件、量子事件,因而测不准原理对之是适用的。因此,具有这种性质的事件,本质上是不可预测的。”(16)我们认为,“测不准原理”是认识论而非本体论上的。分子水平上DNA序列变化虽然有量子事件基础,但这是发生在自然环境而不是人工舞台上的,不存在主观介入问题,因此操作意义上的“测不准”对之是不适用的。此外,获得性状遗传理论是承认定向变异的。尽管在大量变异中可以使用统计规律,但变异自身仍要服从因果律,浅层的不定变异在深层将被发现是定向变异。当然,我们也不赞成把拉普拉斯的机械“决定论”引入生物学,不定变异永远不可能完全为定向变异所取代,否则获得性状遗传就陷入了“预成论”。由于现代科学对分子水平以下的原子、电子的运动方式尚未充分掌握,对它们同外界条件的联系了解更少。因此要对获得性状影响基因的机制作全面细致的描述,还有待于科学的进步和哲学观念的更新,尤其是人类对微观世界的认识进一步深入。可以相信,在获得性状的奥秘完全揭开之日,就是一门崭新的生物科学诞生之时。
注释:
①海克尔《自然创造史》转引自朱洗《生物进化论》第372页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②莱尔·沃森《超自然现象》第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③M·E·鲁斯《还原论,代替论与分子生物学》载《外国自然科学摘译》1975年第3期第9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④B·D·Davis《生物科学的前沿》载《世界科学》1981年第8期第16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⑤恩斯特·海克尔《宇宙之谜》第13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⑥V·F·韦斯科夫《人类认识的自然界》第187页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⑦达尔文《物种起源》第87页科学出版社1972年版
⑧《武谷三男物理学方法论论文集》第34页
⑨邦尼·B·巴、迈克尔·B·莱顿《生命科学》第195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⑩黑格尔《自然哲学》第541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11)雅克·莫诺《偶然性与必然性》第11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3)达尔文《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第582页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14)皮亚杰《生物学与认识》第266页三联书店1989年版
(15)《偶然性与必然性》第68页
WW郭树森
标签:返祖现象论文; 基因变异论文; 遗传变异论文; 基因合成论文; 获得性遗传论文; 基因结构论文; 同化作用论文; 进化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