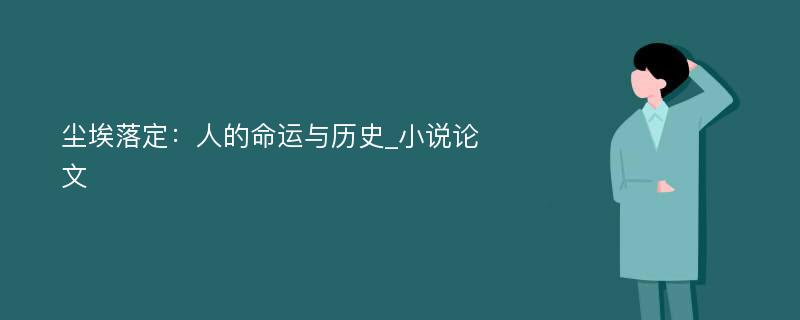
《尘埃落定》:人与历史的命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尘埃落定论文,人与论文,命运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尘埃落定》(人民文学版,1997年)是藏族青年作家阿来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虽不能说臻善臻美,但就其美学创造性来说,却在近年来疯长的长篇小说领域中造就了一道独特风景。
阿来是一位诗人。诗之于小说的滋养,早就是一种不难印证的事实。就我的感受而言,与其说《尘埃落定》是一部小说,还不如把它看作是一首长诗。诗是什么?诗是以意象传达体验的另一种说法,或是一种交融着具象与思情的写意形态——“尘埃落定”便是一句诗。《尘埃落定》所讲述的,虽是麦其土司的统治逐步走向崩溃的故事,而且是一个富有精神原乡意味及人性原色感的故事,但这个故事却以大流动的诗化方式,最终实现了“尘埃落定”的境界。或者说,故事本身就是一种意象的体现。当然,小说的题材是特别的,被描写的人与事是特别的,叙述方式及视角处理是特别的,但“特别”并不是小说的终极彼岸——那我们从小说中感受到了什么呢?是一种与人类进程相通的目光?还是一种解释人的精神家园的描写?或者是一种源自“特别”而又跨越“特别”的形象及意义?因了小说的意象方式:都是但不全是。实际上,我们经由一个精神原乡的“文化亡灵”,或一个历史进程旁观者的记忆,即通过那个“既傻又不傻”的二少爷的极富人性本相的讲述,并从诗意的传达中感受到了一种历史的生动过程,一种社会嬗变的跌宕起伏,一种人的生存景况及命定的循环,一种模糊了智愚界限的人生真实,甚至是一种过去与现在的撞击、最终难分彼此
于是,小说以一种类似寓言的特质刺激了读者的想象力,并难能摆脱“尘埃”这一意象的笼罩。譬如,人是尘埃,人生是尘埃,战争是尘埃,情欲是尘埃,财富是尘埃,而历史进程的某些环节也可能是尘埃,像尘埃那样升腾、飞扬、散落,始于大地而最终归回大地……这便是宇宙的无休无止的歌唱:往复循环,苍凉而又凄楚。对于小说来说,重要的当然是其中的“人的过程”。对于《尘埃落定》来说,更重要的还在于:与“人的过程”相关的各种情节及场面的描写,以及描写任何能实现的意象化程度。不难感觉到,小说中的关于色欲导致杀戮的描写,关于“罂栗花战争”的描写,关于粮食及由此引起的土司间争斗的描写,关于权力、信仰或宗教纠纷的描写,关于土司们的“最后的节日”、特别是其中悠闲、无聊、堕落、阴谋的描写等等,大都在富有象喻色彩或充满张力的过程中获得了思情的凝集与突围。小说具有一种与理念、与“现成思路”、与划地为牢的创作法则相对抗的品质。它不动声色地冷落了设定主题的方式。它不是田园牧歌,也不是英雄驰骋的悲壮史诗。它只是一种寻找,一种置身岁月河流中的感觉与发现,一种以宁静的心态面对人与历史的命定。
我这样说,绝无作品已经完美无缺的意思。或者说,尽管是“佳作”,但仍然留下了一些令人惋惜的粗疏芜杂,以及驾驭长篇构造的某种顾此失彼,甚至是比较明显的“败笔”。如“尘埃”即将“落定”时,作品设计了“白色汉人”、特别是“红色汉人”的直接卷入,便有点儿“画蛇添足”的嫌疑,至少是忘却了原来的含蓄,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初衷及寓意的完成。在我看来,小说描写的只是一个土司统辖的世界,而为了这个世界的写意性,或为了模糊生活的“此时与彼时”,当然,也为了寻找那种“普遍的历史感,普遍的人性指向”,便不能不注意到这个世界的崩溃,即“尘埃落定”超越“特定”的普遍意义。不难想象,因了外部力量的直接介入,也就削弱了“普遍的历史感,普遍的人性指向”,或给人以强调外部力量的印象。实际上,小说的全部描写已经暗示,土司社会的动摇、瓦解或倾覆,只能是一种必然的归宿,而“白色汉人”与“红色汉人”的直接介入,不仅突出了政治色彩或使小说过程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阶段,而且因生存内容的突变而使作品呈显出另一种叙述风格。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可惜的美学损失。
但就总体而言,《尘埃落定》仍然是一部难得的长篇小说。譬如,作品“怀旧”而不“恋旧”,尤其是那种独特自信的文化态度,那种富有现代人激情的对于历史生活及人的命运的感悟,都给作品的思情及表达造就了相当浓厚的新鲜意味。又如,作者虽声称不屑于“畅销书的写法”,也“不期望自己的小说雅俗共赏”,可我们还是读到了一个很动听很迷人的、甚至还带一点儿“魔幻”的故事;与一般故事不同的,只是故事具备了一种诗化的或意象化的物质:是故事而又不仅仅是故事,或不止于特定故事的表层意义。特别值得一说的是,这部独特的小说还刻画了一系列很独特的人物——怎样评价这些人物,这很难,但可以说,这都是一些很有意思的人物,一些值得品味的人物,一些以往中国长篇小说中很少见的或从未有过的人物,如二少爷(“我”)、麦其土司、翁波意西、桑吉卓玛、还有二少爷的两个小厮索朗泽朗与尔依,即便是落墨不多的济嘎活佛与门巴喇嘛,也给人以意味深长的感觉。
在谈论小说创作时,作者对于“人”的刻画所表达的见解,是很值得如今的小说家深思的。作者说:“在我怀念或者根据某种激情臆造的故乡中,人是主体。即或将其当成一种文化符号来看待,也显得相当简洁有力。而在现代社会,人的内心的更多的隐秘与曲折,却避免不了被一些更大的力量超越与充斥的命运。如果考虑到这些技术的、政治的力量是多么强大,那么,人的具体价值被忽略不计,也就不难理解了。其实,许多人性灵上的东西,在此前就已经被自身所遗忘。”(出处同上)显然,这是一种富有历史感的比较或探索,对于作者感受生活、感受人或“人的过程”,也极其有效:不仅是过去的“人”,而且是现在的“人”。重要的是,当作者一旦发现“人”的“被自身所遗忘”的性灵内容,也就意识到了“人”在历史行程中究竟丢弃了一些什么,而留下的又是些什么。在这里,“回忆”显示了巨大的精神收获,也让人感悟到某种“普遍的意义”的真实存在。
从某种角度上说,小说中的一些重要人物,不仅可以视作独特的文化符号(或简洁有力的文化符号),而且能意识到其中的富有意象特质的社会人性标志(或真正作为“人”的艺术形象)。当然,“文化”与“社会人性”是互为印证的一体化的东西,只不过重心的倾斜不同而已。小说中最出色最地道的人物形象,无疑是唱主角的二少爷(即“我”)。他所拥有的那种“既傻又不傻”的品性,以及其中所包容的丰富性或多义性、所透露的历史感与现实意味,决定了这个人物的独特性(至少在中国长篇小说的人物画廊里还没见到过这样的形象)。我觉得,这样的说法并不算过分。这部小说的第一句话是:“那是个下雪的早晨,我躺在床上……”而小说的最后一段描写是:“血滴在地板上,是好大一汪,我在床上变冷时,血也慢慢在地板上变了颜色。”所以我说,这部小说是个“文化亡灵”的“回忆”,而“回忆”的人——既是历史的参与者又是历史的旁观者的二少爷或“我”,也就成为一个拥有多重意义的“叙述者”或艺术形象。正是在这里,二少爷独有的、但又司空见惯的生存状态,以及由此而可能的各种触发读者联想的寓意,也就获得了蓬蓬勃勃的生长。我始终感觉到,他所走过的“既傻又不傻”的生命历程,完全可以成为历史过程中的“人
的状态。二少爷是如此,人类所走的道路或“人的过程”,也只能是这样一种难分智愚、难分天性与理性的混沌风景。
二少爷之所以是“人”或历史的象征,主要在于经由二少爷的人生过程,不仅使人感受到了人在遭受磨难之后“遗忘”自身的情景,同时也发现了人在“既傻又不傻”状态中的天性的真实可爱,以及人回归本相的希望——尽管有点儿游移迷茫,但反过来说,倘若“人”与历史都呈黑白分明的状态,且又清晰可辨可鉴,这个世界也就显得不真实了。
然而,这个世界的混沌或难见本相,并没有导致小说中的人物刻画的无所指向或乱糟糟地如一地鸡毛。在我的印象中,二少爷的“既傻又不傻”,就是一种极富历史感的社会人性指向,而他的生命过程,也散发着相应的文化养成的气息。至于其他人物,亦大抵如此。譬如二少爷的两个“小厮”:小家奴索朗泽朗、小行刑人尔依。他们的“下人”意识决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习得”的,是一种从不自觉到自觉的人性过程,或者说,无论是奴性还是“犬性”,只能认为是逐步养成的,或熏染,或教导,或依仗生存法则的彻悟。索朗泽朗是因他母亲触犯了有关私生子的律条而与母亲一起沦为没有自由的家奴的,而家奴概念的觉醒则是土司太太的皮鞭给他灌输的。在这之前,他之所以毫无顾忌地与二少爷嬉闹,那是因为他幼小的心灵中并无“辖日”(骨头)的意识,或根本不懂得自己的“骨头”在胎中便已是“下贱”的了。从不懂到懂,从不自觉到自觉,直至自觉到可以心甘情愿地为主子(二少爷)的受辱而舍弃自己的一条胳膊……作为生命的过程,也作为社会人性的嬗变及养成,小说的描写很出色地抵达了自己的美学彼岸——不仅仅是所谓的“文化符号”。而行刑人的后代、并注定要成为行刑人的尔依,从起初认为“杀人是很痛苦的”,而且认为
这种相似性对于现代人处境的启示。实际上,读者很容易感受到,索朗泽朗与尔依是两个完全可以区别开来的“小厮”。
小说作者认为:“在一种形态到另一种形态的过渡时期,社会总是显得卑俗;从一种文明过渡到另一种文明,人心萎琐而浑浊。”(出处同上)这见解很精彩,且可以成为我们感受这部小说的启示。的确,这里所说的“卑俗”或“人心萎琐而浑浊”,连门巴喇嘛与济嘎活佛也无法例外。英雄时代过去了,社会开始糜烂腐败;土司们无聊而无所事事,全面的崩溃也就无可阻挡。于是,智慧演变为愚蠢,“傻”与“不傻”的衡量尺度开始被颠覆,人们价值也更加趋于无足轻重。在这样一个愚昧的“尘埃”沸扬飘舞的时代,先是“新教”传播者、后作为书记官的翁波意西,算得上是一位“英雄”或开拓者了。他说,“是那些身披袈裟的人把我们的教法毁坏了”,而且指责了“野蛮土王”及其权势对于“黑头藏民”的统治。于是,“新教”传播者便招来了“割舌”之祸,但也终于悟到了:“为什么宗教没有教会我们爱,而教会了我们恨。”他第二次被“割舌”,是因为他既“聪明”又“愚蠢”地干预了“土司政治”,即对于“逊位”及“继位”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翁波意西的“割舌”之祸,全是因了他们“聪明”及敢言,或在于他不如门巴喇嘛与济嘎活佛那样入世,那样善于应变。于是,在“卑俗”与“人心萎琐而浑浊”的目光中,翁波意西的
《尘埃落定》所实现的诗化的或意象化的叙述方式,尤其是在凸现人的生存状态的特殊性(如土司制度)的同时,艺术地模糊了人或“人的过程”的特殊性与普遍意义的界限,并使寓意超越了描写的具体性(或突破了题材的局限)。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尘埃落定》不仅是一部中国的小说,而且是一部传达了人类或人性存在的小说。
若要细述这部小说的“好处”,那其中的很多情节设置及场面描写,都称得上是“神来之笔”。就狭义的“叙述”而言,那种流畅潮润的表达,那种感觉化的写意方式,那种注重象喻、暗示或“弦外之音”的表现手法,在当下的长篇小说创作中是很少见的。至于长篇小说中一般都会涉足的女性形象,在这部小说中显得逊色一些(或可以认为是一种“特色”)——给人印象较深的女性形象,当推那个当侍女的家奴桑吉卓玛。作为人性过程,桑吉卓玛同样透露出相当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但小说中的其他女性形象,大都停留在“道具”的地位上,或只起到了“穿针引线”的结构作用,而且过于偏重肉体天性的传达——也许,这种传达正是生活真实的艺术反射。但从女性角度审视,不能不显示出一种尴尬,甚至是一种感受的危机。好在小说是一种虚构的“生活游戏”,而其中的探索空间还是极为广阔的。
1998年5月改毕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