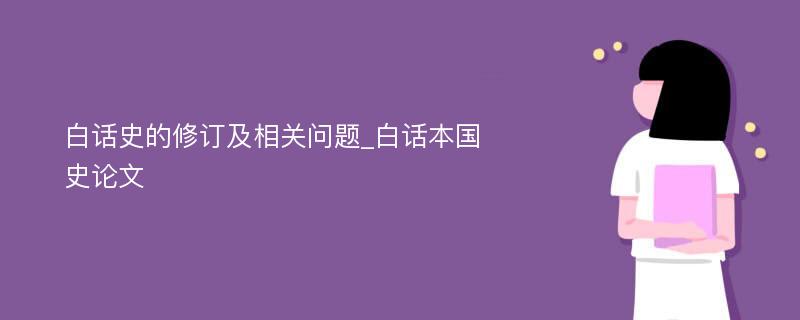
《白话本国史》的修订及相关问题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史论文,白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通常所说的《白话本国史》案,即指1930年代中期因吕思勉先生《白话本国史》中有关“宋金和战”的评述而引出的一段公案,它包含(一)南京政府对《白话本国史》的查禁,和(二)龚德柏先生以《白话本国史》“宋金和议”之评述犯“外患罪”和“出版法”,对出版方商务印书馆及著作人吕思勉、《朝报》经理王公弢、主笔赵超构诸先生的诉讼案。有关查禁及诉讼案的来龙去脉,王萌女士《吕思勉〈白话本国史〉查禁风波探析》①一文(下文简称“王文”)已有详细的评述。然而,与之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如《白话本国史》的修订,吕先生的态度及相关的学术观念,以及因此案牵连到的历史学的求真与致用的矛盾等问题,尚需要有更深入的讨论。本文拟就此三点略作论述,以期能引起学界同人的思考;其所论是否得当,则请学界同人批评教正。 《白话本国史》总共有过二次修订,这里先说说第一次修订。 《白话本国史》刊印后,吕先生曾做过一遍校订,同时作了一些眉批。校订主要是针对刊误的,如“而是间”改为“而其间”,“世仰”改为“世卿”,“《论衡·顺致篇》”改为“《论衡·顺鼓篇》”,“畜五母鸡两亩豕”改为“畜五母鸡两母豕”等等。眉批则记录了作者重读时的一些心得②。有关刊误的订正,吕先生是否做了勘误表转交商务印书馆,现已不得而知。但据笔者的核对,初版的这些刊误,后来重印再版时并未改正;即使“民国二十四年四月订正”版,上述刊误也仍存在。 除了订正刊误,若后来作者的观点、看法有了改变,通常的做法是重印修订本。《白话本国史》是吕先生在中国通史领域最早的一部著作,虽可称为代表作,但书中不少观点看法,后来都有变化。如“汉族的由来”一节所持“汉族西来说”,先生后来就有怀疑,且也不再采用③。“三皇五帝时代社会进化的状况”一节有中国社会进化由“游牧社会”进而“农耕社会”的说法,后来他在《先秦史》中也有改正④。“尧舜的禅让”一节认为“唐虞揖让”实是儒家的学说,非实有其事;先生后来撰《禅让说平议》一文⑤,也对早年的看法有所修正。不过,著作一旦刊印,原先的观点、看法就成为了历史,即使有错,往往再版时也有不作改动的。《白话本国史》虽一再重印,却未有作者的修订本。而修正或改变的观点看法,吕先生只在其他著述中加以说明。有时,史书再版时的修订,并非出于作者自身的原因,而是由于外界形势或社会舆情的迫使。因外界形势或社会舆情的变化,史著重印或再版时需要对书中“不合时宜”的观点、看法,乃至概念、术语进行修改,这也是常见的现象。《白话本国史》的第一次修订,就属于这一种情况。 《白话本国史》初版于1923年(下文简称“初版本”),其近世史(下)第四章第三节“戊戌政变和庚子之乱”内有这样一段叙述: 拳匪怎会得大臣的信任?究竟是堂堂大臣,怎会信任起拳匪来?其中也有个原故。中国自和外国交涉以来,种种的吃亏,自然是不待言而可知的了。有些不忿,想要振作图强,原也是人情。然而图强的方法,却就很难说了。“蹈常袭故”之世,“读书明理”的人,尚且想不出一个适当的法子来,何况处前次未有的变局,再加以揎拳勒臂的,又是一班毫无知识的人?专制之世,人民毫无外交上的常识,是不足怪的。却又有一种误解,很以一哄的“群众运动”为可靠。像煞交涉的吃亏,是官吏甘心卖国,有意退让的。倘使照群众运动的心理,一哄着说:“打打打!”“来来来!”外国人就一定退避三舍的了。这种心理,不但下流社会如此,就号称读书明理的人,也多半如此。——在庚子以前,怕竟是全国大多数的心理。——所以总说官怕外国人,外国人怕百姓。这便是相信拳匪的根源。至于拳匪的本身,则不过是个极无知识的阶级中人,聚集而成。只要看他所打的旗号“扶清灭洋”四个字,是说的什么话。——做盗贼也要有做盗贼的常识,倘使会说兴汉灭满,就够得上做盗贼的常识了。说“扶清灭洋”,就连这个也够不上。⑥ 三年后,即1926年商务重印《白话本国史》第四版(下文简称“第四版”)时,上段文字已被刊落,替换成下面一段叙述: 义和团本是白莲教的支派。元末的韩山童,就是教内一位种族革命家。所以清初时候,明代遗老,也利用他们图谋光复。到嘉庆年间,就有川陕楚白莲教之役、天理教之役。他的历史既长,支派也就很多。乾嘉年间,其中八卦教一派,党徒最众;遍布河北、河南、山东等省。八卦教内最著名的,是震卦、坎卦、离卦三教。离卦教中,又分许多支派:有大乘教(又名好话教)、金丹八卦教、红阳教、白阳教、如意教、佛门教、义和门教等派。义和门教,就是义和团。雍正五年上谕曾说“向来常有演习拳棒之人,自号教师,召诱徒众……甚且以行教为名”等语。可见雍正以前,已有义和团了。嘉庆十三年上谕也说:江苏、安徽、河南、山东一带,有顺刀会、虎尾鞭、义和拳、八卦教名目。后来又常破获传习义和门拳棒案件。这就是庚子年间义和团之源。论起他们的历史,元末韩山童革命,以及清初的排满,清末的排洋,本是传统的民族主义。但是入团的都没有知识,又皆迷信邪术,而在那时候的国人,上自宫廷,下至各级社会,都很相信神怪之谈,以为义和团真有神力,足能驱除外人,就都欢迎他了。(参看劳乃宣《义和拳教门源流考》)⑦ 这是《白话本国史》的第一次修订。比较两段替代文字,其行数正好相同,字数也相差无几(“初版本”10行456字;“第四版”10行463字)。但前者有作者的评论,后者多为史事的叙述。虽注明参看劳氏《义和拳教门源流考》⑧(下文简称《源流考》),实际上只有划线部分的文字相合。此次修订,究竟是吕先生所为,还是商务印书馆编辑代笔?至今找不到可以直接证明的材料。我们依据吕先生稍后撰写的《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下文简称《复兴本国史》)的有关叙述,做点比较、推论。 《复兴本国史》是1934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此时离《白话本国史》的初版已有11年,离“第四版”的修改也有8年。该书第十八章“八国联军和辛丑条约”叙义和团事,其观点、叙事及措辞等,如说“中国从海通以来,所吃外国人的亏,不为不多了,自然,朝野上下,都不免有不忿之心”。说“堂堂大臣,如何也会相信这种愚蠢之说呢?”说“拳匪是起于山东的,本亦无甚大势力。而当时巡抚毓贤,加以奖励,其势遂渐盛”等等,都与《白话本国史》初版本相同。“第四版”新加的有关义和团起源、名目等叙述,此书一无叙述⑨。可以推想:1930年代初,当吕先生撰写《复兴本国史》再次涉及义和团的史事时,想起了数年前有关义和团的修改事,他自行检点,早先“初版本”的有关文字,大致并无不妥,故叙事、措辞等,都延续未变。“第四版”有关义和团起源及门派之名目等,实无详述之必要,故多不采入。唯“初版本”中属于个人的评述(见前文划线部分),则未有录入。核对吕先生后来所撰的另几种中学教科书,情况也是如此(见下文)。由此笔者推断,“第四版”的修订,并非吕先生所为,而是商务印书馆编辑的代笔。 《白话本国史》的第一次修订,改动的只是有关义和团的一段文字,显然,也就是这一段文字,在初版后的二三年里,逐渐显示出与社会舆情、学界思潮的相悖。大约自1920年代起,思想界对义和团的评价发生了转折。其中,1924年是重要节点。此年,孙中山、陈独秀的态度转向最值得注意。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多次有“拳匪之乱”、“野蛮暴乱,为千古所未闻”的说法;写《建国方略》时,提法也未见改变⑩。然而到1924年重新阐述“三民主义”时,观点便发生了大转变(11)。陈独秀在1918年撰写《克林德碑》,说义和团是中国史上“一段可笑可惊可恼可悲的往事”(12)。到了1924年发表《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便全部推翻以前的看法,说义和团“保全了中国民族史上一部分荣誉”!说它“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之悲壮的序幕”(13)。孙中山对三民主义的阐述,意味着国民党意识形态的新整合、新调整;而大革命前的陈独秀,青年毛泽东称他是“思想家的明星”(14),其社会影响可见一斑。舆情的变化,自会对教育界产生影响。1926年召开的第十一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大会,其议决案之第一项便是强调:当下的教育方针,应随时代而转移,应向国民灌输民族主义。“历史教科书,应多采取吾国民族光荣之历史,及说明民族衰弱之原因”(15)。《白话本国史》对义和团一段的修改,自与此时学界思潮、社会舆情之转变有 关。而这一切也自然会影响到出版界,尤其是教科书的出版和修订(16)。 通读吕先生前后的著述,其对义和团的观点看法,甚至是行文中的一些习惯性措辞、叙事的顺序,基本没有变化。最早如1917年出版的《国耻小史》,其叙义和团事,就有“堂堂当国大臣”云云(17),且这种句式、语气在后来撰写的几种教科书中都反复出现(18)。这真所谓“入识最初而终身不可变异者”矣(19)。然而,先生岂不知他的看法与社会舆情、学界思潮之相悖?他既不愿随波逐流、随意改变自己的观点,又不愿不顾外界舆情,故后来所撰的教科书,对此大都是中性的叙事,不作评论,也不掺入个人的意见。然而,意见可以不说,史实不可回避。如义和团的“戕教民、杀教士、焚教堂、拆铁路、毁电线;见洋货则毁,身御洋货的人,目为二毛子,则杀”等(20),在他后来所撰的中学教科书中,都未作回避(21)。当然,外界形势、社会舆情的变化,对吕先生的撰述、尤其是中小学教科书的撰述,还是会有影响。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更新初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也是吕先生所撰。其第二十八章“八国联军之役”云:“当时的拳民,亦有相当的勇气。然既无训练,又专恃血肉之躯,自不足以当大敌。”又引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第五讲》所载西摩的话为注释(22)。这也显示了他顾及社会舆情的一面。总之,坚持自己的观点看法,不刻意回避史实,但也适当顾及社会舆情,这大约是吕先生的基本态度和处置宗旨。而《白话本国史》的第二次修订(即“宋金和战”的修改),其社会背景及吕先生的态度、宗旨,大致与之相同。只是有关“义和团”的评述不太引人注意,未引出查禁、诉讼案罢了。 《白话本国史》的第二次修改,涉及的是“宋金和战”一段(23),其时代背景,王文已有论述,此处不再论及。此次修改,主要删去(一)作者对岳飞、秦桧史事的意见,(二)涉及岳飞的几段史料。与第一次的修改一样,修改替换的篇幅也大致保存一致(“宋金和战”初版共9页半,修订本也9页半)。然而,因涉及的版面较多,且删去的文字多,增补的文字少,故排版上特别将其中3页的叙事改排为罗列式,甚至有五六个字便换行的,以能撑足九页半的篇幅。其结果,便弄得此节与全书的叙事风格、版面样式不甚一致。 有关“宋金和战”的史事,在吕先生早年撰写的《本论·砭宋》和《关岳合传》已有专门的叙及。《本论》共12篇(24),写于1915、1916年间,其中《砭宋》一篇有对“宋金和战”的评述。《本论》当年未曾发表,仅在师友同好间传阅。金松岑先生有“海上七君子诗 武进吕诚之思勉”诗云:“吕子老弥谦,声容和且柔。少壮气遒崒,舌辩不肯休。著为本论篇,符统斯匹俦。体道而用法,谓是赅九流。”(25)可见《本论》的稿子,金先生是阅过的,且为金先生所激赏。比较《本论·砭宋》与《白话本国史》“宋金和战”一节,其叙述之文字、引用之材料、所表达的意见,完全相同。《砭宋》几乎可说是《白话本国史》“宋金和战”一节的初稿底本。 《关岳合传》是吕先生早年所撰的通俗读物,191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的后半部为岳飞传。其第一章论“秦桧”(26),对秦桧的史事多有辨析(27),然书中对岳飞史事的评述,大致按当时社会流行的看法来写。同一段史事,又几乎同时撰写,《砭宋》与《关岳合传》何以截然不同呢?据先生《自述》,1914年的暑假后,他进入中华书局任编辑。他说“予本好弄墨,但在书局,所从事者,均系教科书教授书参考书之类,颇觉乏味。”(28)《关岳合传》是吕先生任职中华书局时所撰,列入中华书局的“学生丛书”,性质与教科书、教授书、参考书相近,大约当时此类书籍,都须按书局的要求撰写,而不能将自己的研究心得融入。所谓“颇觉乏味”,盖也由此?而《关岳合传》仍按流俗的看法撰写,盖也由此。 总之,吕先生有关“宋金和战”的看法,始于1915年的《本论·砭宋》,1923年《白话本国史》沿袭之。自1935年发生《白话本国史》案后,除了出版社约请撰写的教科书,未见有先生专门讨论“宋金和战”问题的文章。但撰写教科书,则不能避开不写,故1936年中学生书局版的《初中标准教本本国史》、1937年商务版《更新初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及1944年开明版的《吕著中国通史》(下)都有专节的叙述。其中,《吕著中国通史》“南宋恢复的无成”一节云: 秦桧的意思,是偏重于对内的。因为当时,宋朝的将帅,颇为骄横。“廪稍惟其所赋,功勋惟其所奏。”“朝廷以转运使主馈饷,随意诛求,无复顾惜。”“使其浸成疽赘,则非特北方未易取,而南方亦未易定。”(叶适《论四大屯兵》语,详见《文献通考·兵考》)所以要对外言和,得一个整理内部的机会。……高宗既无进取的雄才,自然意见与之相合。于是用为宰相。一一三九年,宗弼回上京。挞懒南走。至燕京,为金人所追及,被杀。和议遂废。宗弼再向河南,娄室再向陕西。宋朝此时,兵力已较南渡之初稍强。宗弼前锋至顺昌,(今安徽阜阳县)为刘锜所败。岳飞从湖北进兵,亦有郾城之捷。(今河南偃城县)吴璘亦出兵收复了陕西若干州郡。傥使内部没有矛盾,自可和金兵相持。而高宗、秦桧执意言和,把诸将召还,和金人成立和约。(29) 这一段文字,看似纯为叙事,但引用叶适的话,又注明详见《文献通考》。可见吕先生对“宋金和战”的基本意见没有变。这又是上文所谓“入识最初而终身不可变异”矣(30)。 《白话本国史》案后十年,吕先生撰《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梁任公》长文,其中有一段论梁任公先生云:“他虽与人辩论,绝不肯作人身攻击。人家对他作人身攻击的却不少,他从不肯作一次的报复,只是晓示人家以辩论不当如此而已。……他为拥护真理起见,从不肯作歪曲之论,然又绝无求胜之见,所以到有关大局之处,宁受屈而缄口不言。当他主持《新民丛报》时,和《民报》相辩论。《民报》有一次,把君主立宪不利于满人之处畅发了,他以为这个问题,不可再辩论下去了,若硬说于满人有利,则将流于歪曲,若畅说于满人不利,则将增加君主立宪的阻力,于是缄口不言了。既不肯歪曲真理,又不妨害大局,这真是言论界的模范。”(31)此段虽是评述梁先生,盖也是先生之自况。事隔十年,吕先生第一次含蓄而坚定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不歪曲史事真相,不妨害大局”——这大概是《白话本国史》案发生后,吕先生所抱的态度和宗旨。 《白话本国史》的查禁和诉讼案,引发了当时学界的热议,其中有关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如何塑造民族意识、培养爱国情感问题,值得后人关注。当年熊梦飞先生的批评意见,或可代表历史教学界的一般看法。熊先生认为:历史教学应以“陶铸民族精神,训练公民道德为任务”,而吕先生所编的历史教科书,对民族英雄的事迹“或略而不述,或述而不详,或详而不加宣扬,反加曲解”,不但“于教育政策上所赋予的使命既未能负荷”,于历史学科所具有的本分“也不能做到好处”。他甚至认为,青年判断力缺乏,“读了这种史书,不知不觉会发生媚外心理”(32)。 然而,熊先生所强调的,正是吕先生要努力避免和克服的。1945年出版的《历史研究法》有“旧时历史的弊病何在”一节,吕先生对此有详细的论述。他说: 借历史以激励爱国家、爱民族之心,用之太过亦有弊。不错,爱国家、爱民族,是确有其理的;而借历史以激励爱国家、爱民族之心,亦确是一个很好的办法。然而天下事总有一个适当的限度,超过这限度,就不是真理,而是出于矫揉造作的了,其事就不免有弊。这在欧洲,19世纪后半期各国的历史,都不免有此弊,而德国为尤甚。亚洲新兴的日本,此弊亦颇甚。中国人偏狭之见,较之德、日等国,可谓相差甚远,然亦不能绝无。中国人之有此弊,是起于宋以后的。民族主义,原因受异族的压迫而起,中国自宋以后,受异族的压迫渐次深了,所以民族主义亦渐次勃兴,这固是题中应有之义。然感情与理性,须相辅而行,偏重感情,抹杀理性,就糟了。如中国宋以后盲目的排外之论,是很足以偾事的。近代和西洋人交涉的初期,即颇受其弊。……大抵民族主义误用的弊病有两种:(一)是把本族看得过高,如德、日两国,即犯此弊。(二)则把异族看得太低,如中国人总说蛮夷不知礼仪,甚至比之于犬羊便是。这两者之弊,都由昧于事实的真相而起。昧于真实的真相,惟有求明事实的真相可以救之。所以由矫揉造作的历史所致之弊,惟有用真正的历史,可以做它对症的药。 过分崇拜英雄,则易于发生“利人济物非吾事,自有周公孔圣人”和“啸吟风月天容我,整顿乾坤世有人”的思想。大家觉得只要有一个英雄出来,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而忘却自己应负的责任。其肯负一些责任的,又容易模仿不适宜于时代的人物,甚而至于妄自尊大,陷于夸大狂的样子。(33) 相似的论述,也见之于吕先生抗战前在光华大学任教时的《史学与史籍》讲义。该讲义之“史家宗旨今昔异同”一节,列出借鉴历史容易产生的三个弊端:一是“用以奖励道德”(诸如用以维持社会之正义、资以立身之模范等),二是“用以激励爱国爱种族”,三是“借以传播神教”(34)。其论述也甚详尽,可与上段引文相补充。 无独有偶,远在千里之外的法国学术界,也是在1930年代,曾有过一场类似的学术讨论。当时的法国学术界推崇“进步的哲学”,历史乐观主义、理想主义、实证主义统领天下。教育界弥漫着一种高估历史的道德价值、强调历史教学道德化、教导化的氛围。哲学家、诗人保罗·瓦莱里却保有独特的清醒和警觉,他不惜与学界主流意见相左,告诫法国社会:“这是智力化学生成的最有害的产物。……它引发梦想,令民众迷醉,使他们产生虚假的回忆,夸大他们的反应,继续他们的旧伤,在他们心绪宁静时纠缠不休,诱使他们夸大谵妄,使得各民族痛苦、傲慢、无法忍受和爱慕虚荣。历史完全不做任何教导,因为它囊括并提供了所有例证”(35)。瓦莱里所说“这是智力化学生成的最有害的产物”,指的正是把历史用作宣传品所带来的恶果。就此而言,吕先生与瓦莱里的看法可谓异曲同工。然而直到今日,“借历史以激励爱国家、爱民族之心”的观念,仍为大多数人所赞同;而其可能带来的弊端和危害,却少有关注(36)。 1924年,吕先生所撰的《新学制高中教科书本国史》由商务印书馆初版。三年后,即1927年1月此书重印第四版时(下文简称“《新学制》第四版”),附了一份改正表。表中所列十四条,大都涉及称谓用词,如原写“白莲教匪”的,改为“白莲教党”;原写“川楚教匪”的,改为“川楚教党”;写“白莲教余孽”的,改为“白莲教余党”;原写“洪杨回捻之乱”的,改为“洪杨回捻之变”等等。又有二条涉及概念、术语的,一条初版云“日人遂要求我合办胶济路……迨俄国革命,与德言和。德人在俄势力大张。于是中国有与日本共同防敌之议”。改正表改为“日人遂要求我合办胶济路……迨俄国革命,与德言和。德人在俄势力大张。于是中国一班帝国主义之走狗乃有与日本共同防敌之议。”(37)(另一条见下文)这就是上文提到商务印书馆编辑代笔修改的另一次和另一部著述。 此次修订,笔者之所以也推测是商务印书馆编辑代笔,那是因为核查吕先生在此后所撰的几种中学历史教科书,如《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1934年2月商务初版)、《高中复兴丛书本国史》(1935年5月商务初版)、《初中标准教本本国史》(1936年6月中学生书局初版)和《更新初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1937年7月商务初版)等,“川楚教匪”、“天理教匪”、“捻匪”、“捻寇”、“回乱”、“教匪之乱”、“川楚教匪之乱”、“天理教匪”等术语仍然使用(38);而“一班帝国主义之走狗”一词,从未见之于吕先生的著述。此次修订,虽然大都涉及概念、术语,其缘由则与前两次一样,也是来自外界的影响。这三次商务印书馆对吕著的修改,或许事先告知过吕先生,或也征得吕先生的同意默许。不过,当年也有事属必须,又时间急迫,出版社未事先告知作者,而径直由编辑代笔修改的事。如初版于1934年10月的邓之诚先生《中华二千年史》,其有关南宋韩、刘、张、岳四大将的看法,大致与《白话本国史》同。邓先生认为:岳飞等南宋诸将各自拥兵自重,相互猜忌,不能同舟共济。且军费浩繁,虚糜国帑,对外难建寸功,因而和议不可避免。且书所引证的《文献通考》等史料,也与《白话本国史》同。1935年6月《中华二千年史》再版时,正值《白话本国史》的诉讼案闹得沸沸扬扬,出版社方面唯恐节外生枝、再生麻烦,便在事先未告知邓先生的情况下,由商务印书馆编辑径直代笔修改(39)。 《新学制本国史》自1926年附有《改正表》后,又有多次重印再版,却没有在正文里依《改正表》所列各条一一改正,也未有在书末附上这份《改正表》,这或是编辑发行上的疏漏。尤其是1930年版已改正的刊误,到1933年再版时反而照旧存在,这颇有点不可思议。不过,此类疏漏可能与1932年国难有关。是年,商务印书馆遭日寇焚毁,图书版籍均毁于战火。故国难之后,商务重印再版之书,或“图版装制不能尽如原式”(40),或不能找到修订版而只能按照初版付印。这便造成上述错误,也造成了市面上新旧版本错杂的情况。由此推之,《白话本国史》诉讼案中,龚德柏先生辩解时说当时市面上各种《白话本国史》版本混杂,恐怕也是事实。但是,无论如何辩解,龚氏的错误在于拿1923年出版的书来说1935年的事,这便犯了赵超构先生所说的“张冠李戴”的错误。所以,南京法院最后的判决也说龚氏诉讼的罪名不能成立。然而,这种“张冠李戴”式的错误并非个案。仍是《白话本国史》的这个问题,后来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了不顾时间先后“张冠李戴”的误评(41)。 如上所述,外界形势、社会舆情的变化,对吕先生的中小学教科书的撰述,也会有些影响。《新学制本国史》的《改正表》,有一条(初版)云:“亦有窃取西教之说,以资煽动者。洪秀全,花县人,尝窃取基督教旨,创一教曰‘上帝教’,而名其教会曰‘三点’,广西下流社会信之者颇多。”《改正表》云:“亦有藉西教之说,以资号召者。洪秀全,花县人,尝藉基督教旨,创一教曰‘上帝教’,而名其教会曰‘三点’,广西平民阶级信之者颇多。”查吕先生稍后撰写的各种中学历史教科书,有关太平天国的叙事,不见有“窃取”(大都使用“借用”、“借助”)、“下流社会”(大都使用“下等社会”、“下级社会”)等措辞,而大都采取中性的叙述(42)。但是,在大学用的教材里,如1944年出版的《吕著中国通史》,仍有“下流社会”、“不中不西的上帝教”等说法,以及说其“思想简单、手段灭裂、知识浅陋”等(43)。很显然,大学教材与中小学不同,其叙事论史不必刻意隐晦个人的看法或意见。 其实,这里的问题,主要不是该不该隐晦个人的看法或意见,而是史书的撰写该不该回避或掩盖史实真相。1952年,吕先生任教的华东师范大学开展“三反与思想改造运动”。运动结束时,吕先生写了一份《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下文简称:《总结》)。按规定,《总结》都须检讨自己历年的著述。就吕先生来说,《白话本国史》的这个问题不能回避,也不必回避。他在《总结》中写道:“此书曾为龚德柏君所讼,谓予诋毁岳飞,乃系危害民国,其实书中仅引《文献通考·兵考》耳。……然至今尚有以此事诋予者。其实欲言民族主义,欲言反抗侵略,不当重在崇拜战将,即欲表扬战将,亦当详考史事,求其真相,不当禁遏考证也。”(44)言下之意是:有关“宋金和战”中的看法,我是依据了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叶适的《论四屯驻大兵》等史籍。若要批评我的意见,总须证明上述诸书的记载都是错误。换言之,我们不能为了某种现实的目的或效用,而回避史料,甚至“禁遏考证”(45)。胡适之先生写有《南宋初年的军费》札记一条,云:“宋高宗与秦桧主张合议,确有不得已的苦衷。……秦桧有大功而世人唾骂他至于今日,真是冤枉。”又引《中兴系年录》云:“绍兴十二年右司鲍琚总领鄂州大军钱粮。先是琚奏岳飞军中利源,鄂州并公使、激赏、备边、回易、十四库岁次息钱一百六十五万五千余缗,诏以鄂州七酒库隶田师中为军需,余令总所收。”说“刘军仰给于漕司,岳军取给于酒库。此与今日军人靠盐税、鸦片为饷源者颇相同”(46)。不论适之先生所云“与今日军人靠盐税、鸦片为饷源者颇相同”是否妥当,《中兴系年录》的这段史料,胡先生注明见于王鹏运《花间集跋引》(47),类似的记载,也见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四),却也未见近人所著各种岳飞传记有所提及。 吕先生在《复兴本国史》的例言云:“考据无论如何精确,总只是考据,不能径作为事实,这是原则。……考据问题,一个人的意见,往往前后不同,这是无可如何的事。此书的编纂,距编新学制高中教科书时,将近十年了。鄙人的意见,自亦不能全无改变。如尧,舜,禹的禅让,昔日认为绝无其事,今则对此的意见,较为缓和。此等处,一一都将旧说改正。自信今是而昨非,但亦不知今之果是乎?非乎?惟有仰望大雅弘达的教正而已。”(48)说考据的结论,不能径做事实,且“现身说法”,指出自己的观点也常常是“今是而昨非”。前文所说《白话本国史》中一些观点的改变,也说明这一点。但是,在“宋金和战”的问题上,似乎未见先生有“今是而昨非”。何以如此?笔者认为,这恐怕与吕先生的治史原则有关:(一)考据之结论,虽不等于事实;但要改变原先的结论,须先改变原先的考据。而原先之考据能否改写,在于对马端临《文献通考》、叶适《四屯驻大兵》等前人记载的合理解读。如无法圆满地对反面材料作出解释而回避不用,这不是他的态度。(二)不能因现实的某种目的而掩饰历史真相。1935年3月,吕先生撰写的《中国民族演进史》由上海亚细亚书局出版。他在序言中指出:讲民族历史,“自然当力谋民族团结,但也不能因此而抹杀史实真相。中国现在,就是包含着好几个民族的。诸少数民族,对于主要的汉族,以往的关系是如何?现在的关系是如何?谈民族问题的人,都应该忠实叙述。为要求各民族亲近起见,团结起见,将已往的冲突,和现在未能一致之处,隐讳而不能尽言,未免是无谓的自欺。本书不取这种态度”(49)。此篇序言写于1934年12月20日,而一年前——即1933年12月29日,教育部曾就《编写或审查各项课本如有引起各民族恶感之处,须格外审慎》下达一项法令,强调“本党主张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原无畛域之分,据呈前情合行,令仰该馆,凡编订或审查各项课本时,如有足以引起国内民族间恶感之处,务须格外审慎,以副政府历年融洽各民族感情之至意。”(50)吕先生所说“为要求各民族亲近起见,团结起见,将已往的冲突,和现在未能一致之处,隐讳而不能尽言,”显然是针对这个教育法令而发。几乎是同时(1936年2月3日),陈寅恪先生在讲授“晋南北朝史”时,也谈到中学历史教学涉及民族问题是否当有所回避。他说: 近闻教育部令,中学历史教科书不得有挑拨国内民族感情之处,于民族战争不得言,要证明民族同源。予以为这是不必的。为证明民族同源,必须将上古史向上推,如拓拔魏谓为黄帝之后,欲证明其同源,必须上推至黄帝方可。这就将近年来历史学上之一点进步完全抛弃……然大、中、小学所讲之历史,只能有详略深浅之差,不能有真伪之别。……古代史上之民族战争,无避讳之必要。(51) 陈先生所说的“教育部令”,是否就是1933年12月的教育部法令,抑或如上文所说,只是有关部门非正式的通知之类,现无法查实。但吕、陈的言论都是针对教育部命令而发,都对当年教育部的这种命令不以为然。如将时间再往上推四五年,即1932年,顾颉刚先生为《古史辨》第四册写序言,也说到过这个问题。他说:“我们无论为求真的学术计,或为求生存的民族计,既已发见了这些主题,就当拆去其伪造的体系和装点的形态而回复其多元的真面目,使人晓然于古代真相不过如此,民族的光荣不在过去而在将来。”(52)然而,学界的多数人恐怕未必会像吕、陈、顾先生那样表达自己的真实看法,或未必同意他们的意见。另一位史学大家陈垣先生的意见就截然不同。在1946年12月出版的《通鉴胡注表微》“边事篇十五”中,陈先生说: 史贵求真,然有时不必过真。凡事足以伤民族之感情,失国家之体统者,不载不失为真也。《春秋》之法:为尊者讳,为亲者讳。子为父隐,为尊者讳,父为子隐,为亲者讳也,直在其中矣。六经无真字,直即真字也。(53) 几乎同时,他在给陈乐素先生的信中也说: 据方司铎言,浙大曾有学术论文有伤本地大姓感情之事,足证予近日所主张凡问题足以伤民族之感情者,不研究不以为陋。如氏族之辩、土客之争、汉回问题种种,研究出来,于民族无补而有损者,置之可也。(54) 按陈先生之主张,上起“国家体统”、“民族感情”,下及“本地大姓”,凡因求真而引出“麻烦”的事,都应该避而不谈。换言之,因求真而不获致用,或者反而有害于用,历史学者就不该固执地一味“求真”,此时“不载不失为真也”。 上述引录,并非是让顾、吕及两位陈先生互相驳难辩论。然而将这四位史学名家的看法稍加排列,就显示了问题的奇怪和独特:不能有碍于“用”而“禁遏考证”;学问研究的求真“不必过泥”;学问的求真“无避讳之必要”等等,诸如此类的讨论对于自然科学家而言,简直匪夷所思。但历史学者则是习见已久,恬然不复为怪矣。 就其起源和本质而言,历史学本是一项公益性的事业;出于对整个群体命运的关怀,而不带有任何私人目的和利益取向来从事学术研究,遂成历史学家的使命。故他们有责任,也有权利、有义务把历史真相揭示出来;而社会当有“度量”去听取、参考或接纳历史学家的研究结果。 然而,史实真相的揭示,并非像说说“昨夜邻猫生子”那样简单。在这里,肯定或否定一个史实,揭示或掩盖一个真相,不仅仅是一个是否符合历史实际的问题,还纠缠着各种各样、方方面面的利害关系。 于是,历史学家的求真,有时被斥为不识时务、不合时宜;有时则因言获罪,所谓“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55)以至于有学者惊叹:“历史家的职业几乎同新闻记者一样的危险,因为能够让历史学家勇敢而公正地说出历史真相的条件少而又少,在历史学中,因害怕而未能说出的历史真相,远比已经写出、说出的要多得多。”(56)真所谓“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57),此理之不可解者也! 注释: ①见本期第31-38页。 ②刊误的订正,见于吕思勉自用的《白话本国史》第一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第100、116、124、164页。吕先生的眉批,现已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白话本国史》。 ③参见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下),上海:开明书店,1944年,第350页;亦见吕思勉:《中国通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01页。 ④参见吕思勉:《先秦史》,上海:开明书店,1941年,第59页;亦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56页。 ⑤吕思勉:《禅让说平议》,收入《古史辨》(七下),上海:开明书店,1941年,第267-270页;亦见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8-61页。 ⑥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第4册近世史(下),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第55-56页。下划线为笔者所加,见下文讨论。 ⑦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第1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第62-63页。下划线为笔者所加,见下文讨论。 ⑧劳乃宣:《义和拳教门源流考》,见于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433-439页。 ⑨吕思勉:《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下),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10-112页;亦见吕思勉:《吕著中小学教科书五种》(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647-650页。 ⑩见《与宫崎寅藏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96页)及《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51页)、《论惧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识时务者也》(《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82页)、《建国方略(一)》(《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34页)。 (11)见《“三民主义”之第五讲》(孙中山:《三民主义》,见《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15-316页)及是年11月19日孙氏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的演讲,见(《孙中山全集》第1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40-341页)。 (12)陈独秀:《克林德碑》,原刊《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1月15日出版;亦见陈独秀:《〈独秀文存〉选》,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01页。 (13)陈独秀:《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原刊《向导周报》第81期,第646页,1924年9月3日出版;亦见《陈独秀文选》,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51页。 (14)毛泽东:《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原刊《湘江评论》创刊号,1919年7月14日出版;亦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05页。 (15)《第十一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大会议决案》,刊于邰爽秋等编:《历届教育会议议决案汇编》,南京:教育编译馆,1935年,“教育史料类”第1页。 (16)有关义和团的修改,笔者未能在教学大纲、教育法规、出版法规之类的文件中找到与之直接有关的材料。其实,政府部门对此类问题的指令,惯用的方式是以内部文件或电话通知的方式下达的,而不是正式颁布一个新法规、新文件。如蒋维乔先生1914年3月24日日记云:“教育部有不正式之通知,令各书局将教科书改易,加入颂扬总统语”(张人凤:《〈蒋维乔日记〉中的张元济》,《文汇报》2014年12月12日)。又如邓之诚先生1954年12月14日日记云:“晚,钟翰来,交代阅校样,书中所应避忌者,‘夷、狄、寇、盗’耳,‘夷’不可犯,尤甚于‘寇’。钟翰在民族学院,熟悉此事,故以烦之”(《邓之诚日记》第七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176页)。这显然也是上级部门下达过有关的指令。此外,朱希祖1935年5月24日日记云:“午后二时至中央大学文学院开院务会议,为教育部令开暑期学校中有历史地理组,须史学系教授任课”(朱希祖:《朱希祖日记》中册,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507页)。可见,当年法规之外的各种教育部令甚多。 (17)吕思勉:《国耻小史》(下),上海:中华书局,1917年,第31页;亦见《中国近代史八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69页。 (18)(21)按出版先后,可参见《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第295页(亦见吕思勉:《吕著中小学教科书五种》,第295页);《初中标准教本本国史》第3册,上海:上海中学生书局,1935年,第132页;《初中教本本国史》第3册,上海:上海中学生书局,1937年,第119页(亦见《吕著中小学教科书五种》,第1193页);《更新初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第3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65页。 (19)章学诚撰、吕思勉评:《文史通义·博约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9页。 (20)吕思勉:《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下),第112页;亦见吕思勉:《吕著中小学教科书五种》,第648页。 (22)吕思勉:《更新初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第64、65、68页。 (23)即《白话本国史》近古史(下)第一章“南宋和金朝的和战”第二节“和议的成就”,见1933年10月国难后第2版,第505-515页。 (24)吕思勉:《本论·砭宋》,见吕思勉:《吕思勉诗文丛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82-287页。 (25)金天羽:《天放楼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69页。 (26)吕思勉:《关岳合传》,上海:中华书局,1916年,第41页;亦见吕思勉:《吕著史地通俗读物四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92页。 (27)吕思勉:《关岳合传》,第43页;吕思勉:《吕著史地通俗读物四种》,第93页。 (28)吕思勉:《自述》(即《三反及思想改造总结》,见吕思勉:《吕思勉论学丛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43-744页。 (29)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下),第486页。 (30)另有一例是论汉时匈奴来朝,朝廷有关礼仪位次的争论,吕先生盛赞萧望之(“独以单于非正朔所加,故称敌国,宜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的意见。这最早见于吕先生少年时学写史札的《匈奴朝仪》,后来写读史札记《萧望之对待匈奴之议论》、写《秦汉史》时,仍沿袭此看法,并再三称赞之。参见李永圻、张耕华:《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3页;《吕思勉读史札记》(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673-674页;吕思勉:《秦汉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44页。 (31)吕思勉:《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梁任公》,原刊《月刊》第1卷第3期,1946年1月5日出版;亦见吕思勉:《吕思勉论学丛稿》,第396页。 (32)熊梦飞:《评吕著高中本国史》,原刊《教与学》第1卷第1期,1935年1月出版;熊梦飞:《对于吕思勉著高中本国史的批评》,原刊《文化与教育旬刊》第61期,1935年出版。 (33)吕思勉:《历史研究法》,上海:永祥印书馆,1945年,第35-36页、第34页。亦见吕思勉:《史学与史籍七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1页、第20-21页。 (34)《史学与史籍》,初名《史学研究法》,原为吕先生在光华大学教学用的油印讲义。见吕思勉:《史学与史籍七种》,第62-63页。 (35)Paul Valéry,Regards sur le monde actuel & autres essais,Gallimard,1945,p.43. (36)美国学者詹姆斯·洛温的《老师的谎言——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于1995年初版,中译本由马万利先生译出,于2009年12月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此书所论之根本性疑问,便是本文这里所讨论的问题。译者马万利先生在《译后记》写道:“作者曾经告诉我,他期待看到一本《老师的谎言——中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我期待本书能引起国内史学界及教育界、思想界更进一步的思考。”为了引起讨论,笔者曾撰有《历史书写中的谎言》(《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和《从谎言中读出真相》(《南方周末》2013年11月28日)二文,但时至今日,未见有相关的后续讨论。 (37)吕思勉:《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附《改正表》,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 (38)即《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高中复兴丛书本国史》和《初中标准教本本国史》,俱见吕思勉:《吕著中小学教科书五种》(上、下),第590、591、592、604、893、1146、1147页。吕思勉:《更新初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第三册,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39、40页。 (39)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于1935年6月再版。再版后的《中华二千年史》,对有关岳飞评议的文字悉数删去,而替代以《宋史》、《金史》等叙述战争经过的史料。有关秦桧的评述也做了修改(见《中华二千年史·四卷》,1935年,第301-302页)。据邓之诚先生1935年6月28日记,是日“又致商务书馆责问《二千史》上册再版未通知我之故。”(见《邓之诚日记》第一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249页)著作再版,本是件高兴事,邓先生当致信商务印书馆表示感谢,何以反而去信责问?按笔者推测,此次再版的修改,事先未征求邓先生的同意,或也未来得及告知,故邓先生要去信责问之。 (40)《上海商务印书馆启》,刊于《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6月国难后第13版之版权页。 (41)参见吴玉章:《中国历史教程绪论》“几点说明”,华中新华书店,1949年,第1页;吕翼仁:《关于〈白话本国史〉的两点说明》,刊于《文汇报》1963年11月26日;周劭:《蒋廷黻与吕思勉》,刊于《文汇读书周刊》1997年4月27日。 (42)见吕思勉:《吕著中小学教科书五种》(上、下),第601、1157页;《更新初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第三册,第36页。 (43)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下),1944年,第530-533页。 (44)见吕思勉:《吕思勉论学丛稿》,第756页。 (45)笔者查阅了近七十年来出版的关于岳飞的传记著述,上述史料无一不是略而不谈、刊落不引。按出版时间先后有:彭国栋:《岳飞评传》(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邓广铭:《岳飞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王曾瑜:《岳飞新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刘秀生:《岳飞评传》(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龚延明:《岳飞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等。彭国栋之《岳飞评传》和刘秀生《岳飞评传》,对马端临《文献通考》和叶适《水心别集》之《四屯驻大兵》无一引用。邓广铭《岳飞传》、王曾瑜《岳飞新传》则有选择地引用了《四屯驻大兵》“玩寇养尊”和“任数避事”八个字。至于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张、韩、刘、岳之徒……究其勋庸,亦多是削平内难,抚定东南耳;一遇女真,非败即遁,纵有小胜,不能补过”云云,上述几种岳飞传记都避而未用。 (46)胡适:《南宋初年的军费》,写于1924年10月30日,原刊《现代评论》第1卷第4期,1925年1月3日出版;亦见季羡林编:《胡适全集》第1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2-53页。 (47)王鹏运:《花间集跋》,见《四印斋所刻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2012年,第551页。 (48)吕思勉:《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例言,第3页、第4-5页;亦见吕思勉:《吕著中小学教科书五种》(上),第311页。 (49)吕思勉:《中国民族演进史》序,上海:亚细亚书局,1935年,第2-3页;亦见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两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61-262页。 (50)教育部印行:《教育法令续编(1933,3-1934,6)》,1934年6月出版,第406-407页。 (51)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98-99页。 (52)罗根泽编:《古史辨》第4册,顾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3页。 (53)陈垣:《通鉴胡注表微》(下),《辅仁学志》第十四卷一二合期油印本,1946年,第206页。 (54)“1946年6月23日致陈乐素信”,见陈智超编:《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97页。 (55)刘知幾撰、浦起龙通释、吕思勉评:《史通·曲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44页。 (56)古奇在《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写道:“意大利的王公拒绝穆拉托里查阅他们档案的要求,理由是他可能会找到一些否定他们领土权力的证据。詹姆斯派的卡特因为在附注中提到一个英国人的瘰疠症由于‘僭望王位者’的抚摸而获得痊愈,便被撤销了伦敦市参议会授予的补助金,而他的著作也不让出售。一个老投石党人梅泽雷,由于对路易十四的先人的财政措施作了一些批评,结果被剥夺了养老金。姜诺内为了他的那不勒斯王国史而被流放,后来死于狱中。弗雷雷因为主张法兰克人不属于高卢族,而被投入巴士底狱。”([英]古奇:《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耿谈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90、91页) (57)陈寅恪诗,写于1930年;见《陈寅恪集·诗集·附唐篑诗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