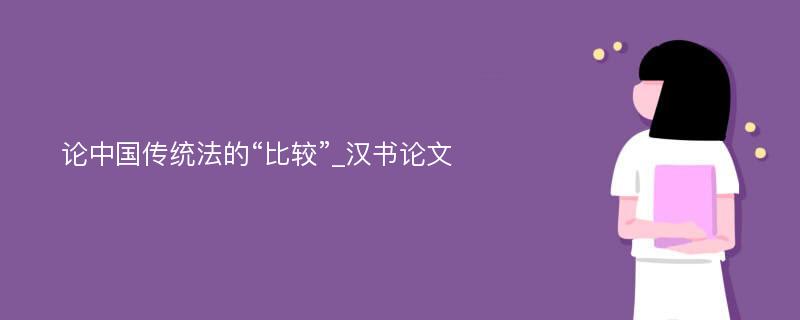
论传统中国法“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法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274(2015)05~039~09 一、“比”字的基本问题 (一)“比”字释义 《说文解字》云:“比,密也。二人为从,反从为比。凡比之属,皆从比。(毗至切。)夶,古文比。”[1]P169“比”是“从”,两个人并行。①甲骨文并不多见“比”字,反而常见“匕”字,故前者应从后者发展而来,犹如“例”字由“列”字演变而生。《说文解字》云:“匕,相与比叙也。从反人。匕亦所以用比取饭,一名柶。凡匕之属,皆从匕。(卑履切。)”[1]P168柶是古代舀取食物的礼器,像勺子,多用角做成。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亦指出,“比当作匕”。②从《说文解字》对于“比”字的释义看,“比”的首要含义应为“密”,而“密”首指空间位置的接近。例如,《左传》“文公十七年”即疏“密迩”为“比近”。汉语常用成语“接踵比肩”“天涯比邻”和“丝纷栉比”,等等,均强调“比”乃相邻的空间位置关系。空间位置的接近,进而引申为心灵距离的亲近。例如,《论语》“为政”即指出“比是亲狎之法”。心灵距离的亲近也就实际上意味着相互关系的认同。例如,《周书》“武顺”即有“比者,比同”的界定。③汉语常用成语“朋比作奸”“朋党比周”“周而不比”,等等,均反映心灵距离的亲近或者相互关系的认同。 《春秋左氏传》“昭公二十八年”云:“择善而从之曰比。”这是将“比”作为一种行事方式。《诗·大雅》“克顺克比”注:“比方损益古今之宜而从之也。”由此可知,“比”是将主观能动性作用于客观事物的一种自觉行为。《礼记》“王制”言“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郑玄注曰:“小大,犹轻重。”“已行故事,曰比。”在郑玄看来,“比”就是“故事”。郑玄还认为:“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即借助典故(故事)含蓄晦涩地表达言者的特定立场。从上述《礼记》的记载来看,“比”已经作为一种名词使用。《汉书》“刑法志”有“奇请他比”,注:“比,以例相比况也。他比,谓引他类以比附之,稍增律条也。”可见,汉代的“比”已是司法实践活动援引他案的一种实际做法。《周礼·秋官·大司寇》云:“凡庶民之狱讼,以邦成弊之。”郑玄注引汉郑司农曰:“邦成谓若今时《决事比》。”唐人贾公彦认为,“邦成”犹如当时“断事”适用法律,“旧事”是其依据,若没有法律规定(“无条”),则“比类”裁判,故又称“决事比”。刘勰《文心雕龙》指出:“故‘比’者,‘附’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附理,故比例以生……”刘勰指出“比”在运用原理、含义等方面的内涵。南宋文人王应麟曾言:“汉之公府则有辞讼比,以类相从;尚书则有决事比,以省请谳之弊。比之为言,尤今之例云尔。(定而不易者谓之法,法不能尽者存乎人。)”[2]P1276总之,“比者,例也”。清人李重华认为“用一故事,俱是比”,[3]即征引典故(故事)表达思想。 (二)睡虎地秦墓竹简“比”字 《尚书·吕刑》即有“上下比罪”一语,表明“比”在西周已经作为一种司法技术而存在。但是,“比”作为一种司法技术大量得以适用,是在秦汉时期。 睡虎地秦墓竹简大量的简文所载“比”字,计十一条简文十四处。④例如,“求盗比此”“比罷癃”“比公士”和“比大父母”是身份之比(前三种是主体身份,第四种是对象身份),“比殴主”是手段之比,“比折肢”和“比疻痏”是后果之比(前者是身体部位,后者是具体伤情),“论比剑”是工具之比,“比群盗”是罪名之比。“行事比焉”是物品之比。 从睡虎地秦墓竹简十一条简文十四处“比”来看,该十四处“比”均作动词使用。当然,从睡虎地秦墓竹简尚未见到作为名词使用的“比”这一事实来看,并不能贸然否认当时存在作为司法活动产物的作为名词的“比”。睡虎地秦墓竹简的“比”字表明,秦代的“比”更多地是一种司法程序或者一种司法技术。“比”字本身并无判例之义,因为这种“比”仅是“一次比”,即仅是一种简单的比照具体实物(法律规定或者具体物品)。但是,秦代是否存在判例,需要继续研究“廷行事”,方能得出一个比较恰当的结论。 二、“比” (一)“决事”“决事比”和“比” “决事”一语,史书记载不绝如缕。例如,《战国策》“楚策一”云:“敝邑秦王使使臣献书大王从车下风,须以决事。”“决事”意为“决断事情”“处理公务”。又如,《汉书》“刑法志”载:“(秦始皇)昼断狱,夜理书,自程决事,日县石之一……”“决事”意为“处理事情”“裁断案件”。再如,《汉书》“朱博传”载,朱博认为出身武人的司法官员不通法律,担心其断狱会出差错,就找人共同编纂“前世决事吏议难知者数十事”,以此断案,“为平处其轻重,十中八九”。另外,《晋书》“刑法志”载:“光武中兴,留心庶狱,常临朝听讼,躬决疑事。”汉光武帝刘秀“躬决疑事”与秦始皇“昼断狱”“自程决事”何其相像!值得一提的是,秦代“事皆决于法”的历史记载也显示“决事”的存在,“事”代表“案件”“事情”,“决”意指“决断”“裁处”。最后,《北史》“刘晖传”载刘晖殴兰陵长公主一案,对此,“灵太后召河清王怿决其事”,即灵太后命令该案由王怿负责审断(“决其事”)。陈顾远先生认为,汉代的决事比后世相继发展为唐格、宋敕、明清例,而决事比本身与汉代的科“疑为一事之两称”。“自清末变法后,成文法规逐渐完备,比附固所严禁,判例亦失权威,汉代决事比之实质亦渐湮没”。[4] 有学者认为,“比”是汉代判例的表现形式,分为“决事比”(判例)与“辞讼比”(案例)两种,“是用来作为比照判案的典型案例”。[5]有学者认为,汉代决事比大体有两种,一种是继承秦代“廷行事”的一般决事比,一种是春秋决事比。[6]另有学者指出,汉魏晋时期的比是对各方面均由普遍约束力的“成例”,其中,某些经过汇编的某些“比”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判例。[7]还有学者认为,秦代“廷行事”在汉代并未消失,因为史籍仍有“行事”之记载,而且汉代还出现“决事比”这种新形式。[8]总的来说,就“决事比”而言,学界所述,大致有三种:决事比(一般决事比,普通决事比);春秋决事比(春秋决狱);奏谳决事比。⑤ “比”在汉代,亦有动词(司法技术活动)之义,最为著名的史料即为《汉书》“刑法志”所载“所欲陷则予死比”。“所欲陷则予死比”意为,奸吏如果想构陷某人,则用死罪条款来“比”。 《后汉书》载光武帝诏书“比青、徐二州以略人法从事”。对于诏书施行之后仍然拘留已被释放免为庶人的奴婢的行为,“比青、徐二州以略人法”追究刑事责任。这是刑事领域的一项“比”的司法活动。 《后汉书》“陈宠传”载:陈宠曾祖父咸性仁恕,常常告诫子孙,依法断罪应当从宽对待,即使有重金利益,也要注意“慎无与人重比”。其意为,须小心谨慎从事,不可运用处罚较重的律令去“比”。 行政、礼制领域亦有“比”之运用。《汉书》“文帝纪”载文帝遗诏“比类从事”。“比类从事”的依据是“此令”,即文帝遗诏。“比类”之“比”乃是比照,动词用法。《史记》“外戚世家”载,窦皇后去世后,薄太后下诏“比灵文园法”,追尊窦皇后的父亲为安成侯,追尊窦皇后的母亲为安成夫人。薄太后令有司处理窦皇后已故父母的待遇,比照“灵文园法”。 汉代之“比”相对于睡虎地秦墓竹简而言,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比”的名词化,即“比”作为一种司法技术运用之后,其产物也称“比”。汉代最为著名的作为名词的“比”是“腹诽之比”和“轻侮法”。 《史记》“平准书”载“腹诽之比”。颜异担任济南亭长,后来升任九卿。武帝以白鹿皮币之事询问颜异,颜异的回答令武帝不悦。张汤本来就与颜异不睦,即以颜异身为朝廷命官,“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判处死刑。 《后汉书》“张敏传”载,建初年间,有人侮辱他人父亲,遭到他人杀死,章帝赦免凶手死刑而减轻处罚。自此以后,该案成为比照处理类似案件的依据。“自后因以为比。”张敏认为“以相杀之路,不可开”为由,反对这种做法。后来,和帝采纳张敏建议,废除子报父仇可免死(“轻侮法”)的做法。 “腹诽之比”与“轻侮法”都是刑事领域的“比”,而且,两案都发挥着判例的作用。这表明,伴随着“比”的名词义项出现,汉代的“比”开始出现判例性质。同时,作为名词化的“比”,行政领域亦有之。例如,《汉书》“陈汤传”载:“后皇太后同母弟苟参为水衡都尉,死,子伋为侍中,参妻欲为伋求封,汤受其金五十斤,许为求比上奏。”“求比上奏”之“比”,当然是此前处理类似问题的先例。 “腹诽之比”和“轻侮法”等上述刑事领域的“比”与行政领域的“比”,尚属孤例的“比”,除此之外,还出现集合形式的“比”,即决事比与辞讼比。《汉书》“刑法志”载:武帝时期,“死罪决事比”竟然达到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后汉书》“陈宠传”载:陈宠“撰《辞讼比》七卷……其后公府奉以为法”。《后汉书》“陈忠传”载:陈忠“奏上二十三条为决事比”,均获施行。《晋书》“刑法志”载:陈忠“奏上二十三条,为决事比”,旨在“省请谳之弊”。以陈忠所上二十三条为例,其所作决事比本属个人行为(具体效力需要考证),但随着“奏上”,即获得皇帝的认可,开始发挥作用,目的在于“省请谳之弊”。⑥ 并非明确存在“比”字才存在判例,某些情况下,根据史料记载,即使没有“比”字,也不妨碍判例的存在。晚近发掘的张家山汉墓竹简《奏谳书》所载“阑送南”一案亦是判例意义的案例。⑦当时处理“阑送南”一案,主审人员援引“人婢清助赵邯郸城”一案作为判案依据。最终,阑被判处“黥为城旦”。 汉代“比”之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发挥如此重要作用,其原因须回溯汉政权的建立及法制基础。刘邦初入咸阳,与兆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其余苛法尽除,吸取秦亡教训,务从“法简刑轻”,“宽省刑罚”,奉行黄老思想,与民休养生息。程树德先生评价:“汉自高祖约法三章,萧何造律,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其时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议论务在宽厚,刑罚太省。”贾谊认为“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后者“法之所用易见”,至于前者“礼之所为难知”,因此,统治者应当一方面要“庆赏以劝善”,一方面要“刑罚以惩恶”(《新书》治安策)。但是,这种无为而治的施政理念应对汉初百废待兴的凋敝社会实情,尚为妥当,但随着社会发展日益复杂,内部矛盾渐次加剧,法律漏洞日渐增多。无论是萧何造律九章,还是日后张汤、赵禹、叔孙通相继努力从而使汉律达到六十篇,都不能从根本上纾缓冰冷、僵硬的法律与复杂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史书记载,武帝时期,“条定法令”以致“禁网积密”(《群书治要》卷四十八),于是,“比”大量出现,以救时需,巩固皇权。“比”的数量不断膨胀,以至于“文书盈于几阁”,而典者“不能遍睹”,进而导致奸吏“因缘为市”,他们“转相比况”,造成恶性循环,“禁网浸密”,使得“死罪决事比”数目达到一万三千余“事”。 鉴于“比”的泛滥造成司法混乱的局面,人们开始尝试规制“比”的创设与适用。例如,陈忠撰“科牒辞讼比例”,归类整理,“使事例相从”,另外“奏上二十三条决事比”,减轻司法工作负担,“以省请谳之敝”。又如,鲍昱为“息人讼”,“齐同法令”,“奏定辞讼比七卷”与“决事都目八卷”。这些都是应对“比”泛滥趋势进行限制的有益尝试。《太平御览》引述《风俗通》所载的《辞讼比》佚文三则。⑧ 司徒鲍昱“决狱”即是“决事”,“决事比”即“辞讼比”。史籍有关《辞讼比》的记载无多,但仍有蛛丝马迹可证其存在。《宋史》“选举四”载:高宗时期,吏部侍郎凌景夏声称自己“尝睹汉之公府有辞讼比,尚书有决事比,比之为言,犹今之例”。凌景夏到底是亲眼目睹过汉代《辞讼比》实物还是见到过有关《辞讼比》的史实记载,由于语言的歧义,后人难以下判,得出准确结论。但是,这至少是证明汉代存在《辞讼比》的一项间接证据。 汉代私家律学授受非常发达,研习包括“比”在内的律学世家层出不穷。例如,颍川郭氏,“数世皆习法律”(《后汉书》“郭躬传”),“凡郭氏为廷尉者七人”。又如,河南吴氏,“三世为廷尉,以法为名家”(《艺文类聚》卷四十九)。再如,沛国陈氏,亦是三代研习律学。家族之内前后相继研习律学,往往较早提高子弟的法律素养。以陈宠陈忠父子为例,陈忠“父宠在廷尉。上除汉法溢于甫刑者,未施行,及宠免,后遂寝。而苛法稍繁,人不堪之。忠略依宠意,奏上二十三条为决事比,以省请谳之敝,事皆施行”。 关于决事比的存在形态,亦有“单比”与“复比”之分。例如,“腹诽之比”与“轻侮法”均为“单比”。“复比”往往体现为“辞讼比”“决事比”等。例如,东汉陈宠所作、鲍昱奏定的《辞讼比》。《后汉书》“陈宠传”载:“转为辞曹,掌天下狱讼……宠为昱撰《辞讼比》七卷,决事科条,皆以事类相从。昱奏上之,其后公府奉以为法。”又如,陈宠之子陈忠所作《决事比》。《晋书》“刑法志”载:“(陈忠)奏上二十三条,为决事比,以省请谳之弊。”再如,应劭所作《决事比例》。《晋书》“刑法志”载:汉献帝建安元年,应劭表奏:“……臣窃不自揆,辄撰具……《决事比例》……”上述《辞讼比》《决事比》和《决事比例》均为“复比”,从产生程序来看,可能起初都是个人作品,奏上经朝廷的认可始获国家法律之效力,而此前可能作为判案的重要参考。 无论“单比”还是“复比”,均须经过皇权的认可。前述《辞讼比》《决事比》和《决事比例》等“复比”显然如此,“腹诽之比”与“轻侮之比”等“单比”的确立亦不能外,即“不入言而腹诽,论死”需要经过皇权的认可,“肃宗贳其死刑而降宥之”更是明确经过章帝的宽赦。汉代“决事比”出现判例的性质。 “决事比”往往指代“复比”形式,而非“单比”形式。原因在于“决事比”是对一系列“比”的概称,而一项“单比”(孤立的案例)只有在其后曾被援引才成为“比”,即只有在其后的案件“决事”的时候才会“比”(比照)。因此,“决事比”是对“单比”与“复比”的统称,具体而言,称“复比”的时候,往往称“决事比”,而称“单比”的时候,往往仅称“比”而非“决事比”,只有不同的案例对比时才会存在“比”,单独的一个案例是不存在“比”的。 (二)“春秋决狱” 《汉书》“董仲舒传”载: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考虑到“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因此“任德而不任刑”。其政法主张得到武帝首肯,体现儒家道德精神的“春秋决狱”正式拉开帷幕。 《后汉书》“应劭传”载:汉代“《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董仲舒退休后,朝廷每遇疑难问题仍多次派遣张汤咨询董仲舒。董仲舒所作《春秋决狱》,内有二百三十二件案例,往往以经义相解。董仲舒认为,《春秋决狱》之文,已经十分丰富,无论是“天下之大”还是“事变之博”,《春秋决狱》“无不有也”(《春秋繁露》,十指)。《春秋决狱》又称春秋决事比,早已亡佚,现存仅有寥寥数事。从现存《春秋决狱》数事观察,今人仍能管窥董仲舒将儒家经义、礼仪道德融入法律实践的努力。⑨ “春秋决狱”溯其源流,秦末汉初即有。例如,《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载:陈胜吴广起义,二世胡亥咨询博士诸生“楚戍卒攻蕲入陈,于公如何”,博士诸生均认为“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博士诸生的回答乃是援引《春秋》“君亲无将,将则诛”的经义。又如,西汉初年,景帝时期,太后打算册立梁王为太子,景帝咨询群臣,群臣认为“汉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当立子”。梁王生恨,令人刺杀袁盎,同时谋反之状显迹,败露案发。对于此案,太后、景帝均深感棘手,最终由明经义的田叔、吕季主主审,两人烧掉证明梁王谋反的罪证,宫廷尴尬得以化解,一场即将上演的干戈得以消弭。 后来,董仲舒的弟子“吕布舒持节使决淮南狱”,其结果“以《春秋》之义正之”,深获好评,以至于“天子皆以为是”(《史记》“儒林列传”)。倪宽、隽不疑等亦“以古法义决疑狱”(《汉书》“倪宽传”)。隽不疑根据《春秋》大义决狱,深获昭帝称赞。昭帝认为,公卿大夫办理案件,“当用经术,明于大谊”(《汉书》“隽不疑传”)。元帝、成帝之后,皇帝诏书与群臣奏议,“莫不援引经义以为依据”,已经离不开经义作为办理案件之依据(《后汉书》“张敏传”)。 《汉书》“终军传”载:武帝时期,博士徐偃矫诏,张汤对其以“矫制大害”判处死刑。徐偃以《春秋》之义反驳,张汤无以对。终军也采《春秋》之义驳徐偃,徐偃伏法。《汉书》“济川王传”载,梁王因为淫乱之事案发,被有关方面指为“禽兽行”并请求处死。谷永认为梁王尚且年少,如果“发闺门之私”,予以治罪,则不符合“《春秋》为亲者讳”的要求。皇帝接受这一观点,“寝而不治”,未加深究。 “春秋决狱”的本质,在于引经代律。《晋书》“刑法志”载,违反“律令节度”可以,但是须合“经义”或者前比、故事。对于“春秋决狱”过分注重当事人动机而超越法律规定的做法,刘师培曾经提出批评:虽然名义上是“引经决狱”,但是实际上仍然是“便于酷吏之舞文”。⑩其实,“春秋决狱”本意是好的,但在司法实践中走样变异,导致“便于酷吏之舞文”。 综上可见,汉代的“比”已经由动词性质大规模逐渐名词化,成为一种判例,一种法律形式(决事比)。也就是说,秦汉时期的“比”含义有二:作为动词的“比”代表一种司法技术或者一种司法活动,作为名词的“比”代表司法技术“比”的产物(法律形式)。这两种含义,后世均予继承。不过,“比”(决事比)在汉代虽然含有判例之义,但并非仅限于司法领域的判例,而且包括行政(政治)领域的惯例。故汉代之“比“(决事比)与所谓判例并非完全同一概念。 蔡万进先生对张家山汉简《奏谳书》进行研究,承认“比”的正式法律地位,认为张家山汉简《奏谳书》可能是一部决事“比”集,“姑且称之为《奏谳决事比》”。[9]P71然而,《奏谳书》所载二十二件案例,只有其中第三件“人婢清助赵邯郸城”一案具有“比”的性质,其余案例仅是单纯记载的案例,甚至有两件属于春秋时期的刑事故事。(11)也就是说,《奏谳书》总体上属案例故事汇编,只不过其间“人婢清助赵邯郸城”这一案例确实明确发挥“比”(判例)的作用。诚如张伯元先生所言:“……作为成案的判例范式应该说还有一个去粗取精,精益求精的过程。……如果这个工作能继续做下去,按判例范式的要求去做些加工润色的话,确实它将是极好的‘廷行事’档案,可惜并没有这么去考虑;或许这件事已经超过了他们考虑的职责范围了。”(12) (三)关于“廷行事” 目前,“廷行事”作为一个专用名词,仅见于睡虎地云梦秦简。“汉代有无‘廷行事’?限于史料,一时也难以下最后的判断。”[10]云梦秦简《法律答问》“廷行事”一语,前后相继出现十二次,分别为第38号、第42号、第56号、第59号、第60号、第66号、第142号、第148号、第149号、第150号、第151号与第152号。另外,第162号简虽未出现“廷行事”一语,但有“行事”字样,两种表述极为接近。第162号简“行事”等字可能是“廷行事”的简称,也有可能“廷行事”是“行事”的一种。(13) 前文所提及十三条有关“廷行事”的简文,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用“廷行事”作具体例证,进一步补充法律规定。例如,第148号简文表明,法律对于行为人强行扣押人质以及被害人自愿置于行为人扣押下的扣押人扣押人质的行为,均处以“赀二甲”的处罚,但未规定作为该行为对向面的被害人一方的行为是否需要接受处罚。廷行事对此进一步补充规定,强行扣押下的被害人,无须承担法律责任,自愿置于对方扣押下的被害人,需要负法律责任。 第二,用“廷行事”对法律进行变通。例如,第38号简文表明,诬告陷害他人盗窃价值一百一十钱的财物而其中只有一百一十钱得实(诬陷部分仅占十文),法律对诬陷的行为人处以“赀一盾”,而廷行事对此变通为“赀二甲”,理由是“告不审”(第42号简文亦是如此)。又如,第66号简文表明,对于罪人格杀“求盗”的行为,法律认定为斗杀,“廷行事”认定为贼杀。贼杀是后世故杀的前身。《左传》“昭公十四年”云:“杀人不忌为贼”。而斗杀,接近当今的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显然,“廷行事”对于罪人格杀“求盗”行为的认定,严于法律。第36号简文、第66号简文对法律进行变通的“廷行事”做法,明显趋于重刑处罚。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奉行法家思想的秦律“轻罪重处”的特点。再如,第142号简文表明,法律(“律所谓者”即意为法律有明确规定)对于“犯令”“废令”有明确界定,即前者指不应为而为,后者指应为而不为,廷行事对于“犯令”“废令”的行为统一作“犯令”处理。另外,第162号简文表明,法律认为鞋上有花纹才算锦履,而用锦做鞋帮不算锦履,但“行事”对于用锦作鞋帮的鞋同样认定为锦履。显然,“行事”的处理重于法律。 第三,直接表明“廷行事”的处理方式。例如,第56号简文表明,“盗封啬夫”的行为,“廷行事”以“伪写印”处理,即“廷行事”对于假冒啬夫封印的行为是按伪造官印论罪。又如,第59号简文与第60号简文表明,官吏弄虚作假罪在罚盾以上,须依判决执行,同时撤职永不叙用;有罪应予流放但尚未执行而亡故或逃跑的,其家属仍须流放。再如,第149条简文与第150条简文对于仓房门闩或者门窗不严密,以至于“容指若抉”或者“禾稼能出”,“廷行事”处以“赀一甲”的刑罚。另外,第151号简文表明,空仓草垫下若有粮食一石以上,“廷行事”对于责任人处以“罚一甲”,同时对于负责监管的令史处以“赀一盾”(第152号简文亦是如此)。这些简文都未表明“律”(法律)的处理态度。因此,上述简文是对律文所未规定的部分,进行补位补漏。 由上可见,《法律答问》所载十三处“廷行事”,其义项不外乎三种:第一,对法律进行细化,第二,对法律进行变通,第三,直接表明廷行事的处理方案(可能对法律进行补漏),均无明显而强烈的判例色彩。值得注意的是,第13号简文未提及“廷行事”,而是提及“行事”,而且是“行事比”,即“行事”与“比”连用。本文认为,从前文分析的结果来看,既不能认为“廷行事”是秦代判例,也不能否认其与判例存在某种程度的交集(即某种特定情形下的廷行事可能是当时的判例)。 从上述列举的十三条有关“廷行事”的简文来看,并没有哪一条是“廷行事”的作出主体针对某一特定案例而创制,都是泛泛而谈某个问题。张铭新先生对此指出:“查阅云梦秦简,凡是讲到‘廷行事’者,没有一处涉及到某一具体的案件事实,而是指对某一类法无明文规定的犯罪在以前的审判中是如何处理的,比如‘斗杀人,廷行事为贼’,‘廷行事,(仓)鼠穴三以上赀一盾’等。所以,说秦的‘廷行事’是‘司法惯例’似乎更为准确。”(14)睡虎地秦墓主人生前乃是地位较低的地方官吏,其所掌有的秦国法律资料虽然并不一定全面,但“没有一处涉及某一具体的案件事实”确实能够质疑“廷行事”的判例性质。 可是,如果说前述十三条有关“廷行事”的简文没有一处针对特定案件事实的话,那么睡虎地秦墓竹简所载“比”字的简文,也没有哪一处是针对特定案件事实。因此,无论是含“廷行事”的简文还是含“比”的简文,都难以证明秦代存在判例。 虽然“廷行事”不必然是判例,但是其与判例可能存在交叉,即“廷行事”含有判例的因素。第162号简文“行事比”即其唯一的适例。(15)此处“行事比”应当包括“廷行事”“比”(“行事”可能是对“廷行事”的简写或者简称)。“行事比”一语表明,官府的惯常做法是将锦缦履比附为锦履的“行事”(包括“廷行事”)也是进行比附的,(16)同时表明,由“比”而形成的“廷行事”仅仅是“廷行事”的一种。这表明,“廷行事”可能含有判例的因素。而这也恰恰说明,“廷行事”与“比”属不同事物。 有学者针对第38号简文,(17)认为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者将“赀一盾应律,虽然,廷行事以不审论,赀二甲”译为“罚一盾符合法律规定,但成例以控告不实论处,罚二甲”反映其两难境地:“试想,如果一个案件按照判例‘应’赀二甲,而按照法律规定‘应’赀一盾,那就只会令人无所适从,不知道究竟‘应’赀几何,徒然增加不必要的纷扰。为了不破坏法律的统一性,在廷行事和法律规定矛盾的场合,整理者不得不背离逻辑的同一性要求,译时极力避免‘应’字的出现。这是整理者把廷行事界定为判例不可避免发生的问题。”[11]P75本文认为,论者的这一认识颇有道理,但未必能完全成立。译者未必在是否两次使用“应”字上存在“两难处境”,即使译者使用两次“应”字,也不形成妨碍,即“罚一盾符合法律规定,但以成例以控告不实论处,应罚二甲”。这样的译法说明,按照秦律规定,应罚一盾,按照廷行事实践,应罚二甲。虽然对于同一行为,秦律与廷行事处断不一,而这恰恰说明了廷行事对于秦律的变通处理。另外,论者主要探讨“行事”和“廷”的含义,未能充分阐释“廷行事”一语作为整体的内涵,而前文所列睡虎地秦墓竹简相关简文显示,“廷行事”频繁出现,先后达十二处之多(不含一处“行事”),这表明,“廷行事”在当时应当已经是一种习惯用语。(18)这同时还表明,“廷行事”作为“行事”的一种,其用语用法呈固定化的趋势。 (四)“廷行事”和“决事比”的关系 “廷行事”可能包含判例因素。“行事”与“决事”可能在某种场合存在同样的义项。从前文所释“行事”与“决事”来看,两者都包括“处理事情”“裁断案件”这样的含义。“行事”与“决事”,均可以“故事”作释。最大的区别在于,“行事”和“决事”往往指称事情当时或者随后不久,“故事”则是往往时间久长之后,后人对先人、前辈所行之事的称谓。归根结底,“行事”“决事”与“故事”,都能指代“做过的事”。但学界论述对二语释义,往往绕过“故事”这一释义。这种迂回做法的原因可能在于“故事”本身就是中国法律史一个重要的概念、术语,相关学者可能担心如果将“行事”“决事”释为“故事”,将徒增廓清不同用语彼此之间界限的麻烦。其实睡虎地秦墓竹简的整理者对“廷行事”作注时,已经声称“汉律常称‘故事’”。这一理解应当能为人所接受。[12]P167 “比”在秦代还仅仅是一种司法技术,尚未形成一种相应的独立的法律形式。而在汉代,“比”的司法技术进一步运用,最终形成“决事比”这一载体。从“廷行事”到“决事比”,两个不同的用语显示古人在司法实践领域用语的“无意识”。“廷行事”之“行事”与“决事比”之“决事”存在交叉乃至高度重合。 不容否认,在“廷行事”是否“决事比”的前身,“决事比”是否“廷行事”的进一步发展的问题上,限于史料,尚难以做出肯定性论断。“决事比”相对于“廷行事”,其用语确实差别较大,按照“汉承秦制”的史实,秦代用语自然应为汉代所继承,例如“爰书”“乞鞫”和“贼杀伤”等制度和术语。但是,确有一些制度或者术语,在秦汉之际有较大变化,例如秦代刑事责任以身高为标准,汉代刑事责任以年龄为标准。杜导正先生《编户齐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一书对此问题有所涉及,秦王政十六年(前231),“初令男子书年”,“至迟秦王政统一中国后,书年制度必普及全国”。[13]因此,从“廷行事”到“决事比”的变化,可能也是这样,有待人们发现其那一缺失的关键环节。顾凌云、金少华两位学者认为“廷行事”是秦代“断案惯例”,其全部功能“应是”为西汉的“令”和“奏谳制度”所“覆盖”(《河北法学》)。显然,论者仍然是在推测,由于文献阙如,并未斩钉截铁做出判断。 我们可以如此推论:秦代“廷行事”开始出现判例的萌芽(类推比附),但是仅限于司法技术“比”,即一种司法程序。(19)而汉代“决事比”在“廷行事”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其称“决事比”而非简简单单称“决事”即表明“比”这种司法技术活动的产物已经开始固定下来,即形成专门的书面文件“决事比”,成为断案依据,先由个人收集,进而编订成册,最终得到朝廷认可,具有法律效力。在未得到认可前,“决事比”应当发挥着重要的参考作用,指导司法实践。 需要指出的是,“比”字存在动词“比”与名词“比”的区分。就“比”内部而言,存在“一次比”与“二次比”的区分。所谓“一次比”,即办案主体比照法律或者其他事物(案例除外)的司法活动(技术)或者因此而形成的“比”(判决),其更多地是一种司法技术活动(不否认其产物也是“一次比”)。所谓“二次比”,即办案主体比照以前相同、相似案例而形成新的案例,其侧重强调案例之义(当然不能否认其适用存在比附)。亦即,“一次比”是指“有类似的情况”可以“推比”,“二次比”是指过去“曾有过此类判例”可以“准照”。(20)例如,秦代“廷行事”将鞋帮带有花纹的鞋子比作“锦履”——“行事比焉”——即为“一次比”,而汉代“腹诽之比”即是“二次比”。作为判例而存在的,实际上是“二次比”。因为,一个案件判决只有在之后的司法实践中获得应用,才能成为判例。 三、从“比”到“例” 汉代出现“决事比”,“比”明确经由作为动词的“比”发展为包括作为名词的“比”。同时,“比”与“例”经常共同出现,甚至“例”单独出现,这往往多见于东汉时期。这表明,“例”开始取代“比”,成为法律领域的常用语,但是并不表明“比”的彻底退出。这是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 《汉书》“薛宣传”载:“宣为相,府辞讼例不满万钱不为移书,后皆遵用薛侯故事。”“辞讼例”即“辞讼比”,性质与“决事比”同。《后汉书》“鲍昱传”引《东观汉记》云:“时司徒辞讼久者至十数年,比例轻重,非其事类,错杂难知。”“比例”即“比”(“辞讼比”或者“决事比”)与“例”的合称。《太平御览》引《后汉书》曰:“(陈宠)又以法令繁冗,吏得生因缘,以至轻重,乃置撰科牒辞讼比例,使事类相从,以塞奸源,其后公府奉以为法。”“辞讼比例”即“辞讼比”。该段文字表明,“辞讼比”开始逐渐改称“辞讼比例”,即“比”开始称为“比例”。《后汉书》“陈宠传”称:陈宠上书:“尚书决事,多违故典,罪法无例,诋欺为先,文惨言丑,有乖章宪。宜责求其意,害而勿听。”“尚书决事”存在“罪法无例”的现象,而用法者往往违法办案。“罪法无例”应当指“罪法”没有相关方面的原则规定,而未称“无比”。“比”为“例”所取代。《晋书》“刑法志”载:建安元年,应劭奏称:“夫国之大事,莫尚载籍也……臣窃不自揆,辄撰具……决事比例……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复重,为之节文……”“决事比例”即“决事比”。《宋史》“选举四”载:高宗时期,吏部侍郎凌景夏声称自己“尝睹汉之公府有辞讼比,尚书有决事比,比之为言,犹今之例”。前文已述,这起码是证明汉代存在《辞讼比》的一项间接证据。 “比”“例”含义起初相近,存在区别。陈顾远先生曾言:“比系以律文之比附为重,例则以已有之成事为主,是其所异。然皆不外据彼事以为此事之标准,得互训之,此或汉重视比而后世重视例,两名不并立故也。”[14]P90后来,“比”和“例”已经可以互相指代。北宋苏辙《栾城集》“论梁惟简除遥郡刺史不当状”云:内臣“梁惟简旬月之间三度超擢,皆以自前法外侥幸特恩为比,仍言他人不得援例”。“特恩为比”本身就是“援例”的行为。南宋著名藏书家晁公武称:“皇朝王安石执政以后,士大夫颇重意律令,此熙、丰、绍圣中法寺决狱比例也。”“比例”合指“决狱”。王应麟云:“汉之公府则有辞讼比,以类相从;尚书则有决事比,以省请谳之弊。比之为言,尤今之例云尔。(定而不易者谓之法,法不能尽者存乎人。)”[2]P1276 就目前所见,“比”在秦代属动词用法,是一种司法技术,而在汉代出现名词用法,即作为一种法律现象或者法律形式。同时,“比”开始与“例”互称。“例”作名词使用,可以作为“比”(名词)的代称。“例”的出现与经学有关,汉代著名的律学家往往本身同时又是经学家,他们将对经学的研究方法应当是很自然地带入对律学的研究,即用“律例”关系比附“经传”关系。 注释: ①关于“比”字的读音,沈家本先生考证:“是比例之比,古读去声,今人则多读上声矣。”参见沈家本:《寄簃文存》,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19页。 ②段玉裁认为:“比当作匕,汉人曰匕黍稷、匕牲体。凡用曰匕也,匕今日之饭匙也。”段玉裁将“匕”认定为器具名称。参见段玉裁撰:《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84页。 ③方汉文先生就“比”字上述三义指出:“从‘比’的第一种意义可以看出,它是从不同事物的空间位置接近发展为一种认同,这种认同是对事物同一性的肯定,承认同一性是比较的基本观念……”参见方汉文:《“比较”方法论释义:从“匕”到“比”》,载《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④第一条:“害盗别徼而盗,驾(加)罪之。”可(何)谓“驾(加)罪”?五人盗,臧(赃)一钱以上,斩左止,有(又)黥以为城旦;不盈五人,盗过六百六十钱,黥劓以为城旦;不盈六百六十到二百廿钱,黥为城旦;不盈二百廿以下到一钱,遷(迁)之。求盗比此。(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150页。)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释义:“‘害盗背着游徼去盗窃,应当加罪。’什么叫‘加罪’?五人共同行盗,赃物在一钱以上,断去左足,并黥为城旦;不满五人,所盗超过六百六十钱,黥劓为城旦;不满六百六十钱而在二百二十钱以上,黥为城旦;不满二百二十钱而在一钱以上,加以流放。求盗与此同样处理。”(同书,第151页。)第二条:臣强与主奸,可(何)论?比殴主。斗折脊项骨,可(何)论?比折支(肢)。(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183页。)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释义:“男奴强奸主人,应如何论处?与殴打主人同样论处。”“斗殴折断了颈脊骨,应如何论处?与折断四肢同样论处。”(同书,第183页。)第三条:“殴大父母,黥为城旦舂。”今殴高大父母,可(何)论?比大父母。(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184页。)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释义:“‘殴打祖父母,应黥为城旦舂。’如殴打曾祖父母,应如何论处?与殴打祖父母同样论处。”(同书,第185页。)第四条:铍、戟、矛有室者,拔以斗,未有伤殹(也),论比剑。(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187页。)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释义:“鈹、戟、矛有鞘的,拔出来相斗,没有伤人,应与拔剑相斗同样论处。”(同书,第188页。)第五条:或与人斗,夬(决)人唇,论可(何)殹(也)?比疻痏。(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188页。)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释义:“有人与他人斗殴,撕破他人嘴唇,应如何论处?与打人造成青肿或伤破同样论处。”(同书,第188~189页。)第六条:或斗,啮人頯若颜,其大方一寸,深半寸,可(何)论?比疻痏。(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189页。)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释义:“有人斗殴,咬伤他人颧部或颜面,伤口的大小是方一寸,深半寸,应如何论处?与打人造成青肿或伤破同样处理。”(同书,第189页。)第七条:可(何)谓“赎鬼薪鋈足?可(何)谓“赎宫”?臣邦真戎君长,爵当上造以上,有罪当赎者,其为群盗,令赎鬼薪鋈足;其有府(腐)罪,[赎]宫。其它罪比群盗者亦如此。(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00页。)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释义:“怎样是‘赎鬼薪鋈足’?怎样是‘赎宫’?臣邦真戎君长,相当于上造以上的爵位,有罪应准赎免,如为群盗,判为赎鬼薪鋈足;如有应处宫刑的罪,判为赎官。其他与群盗同样的罪也照此处理。(同书,第200页。)第八条:“将司人而亡,能自捕及亲所智(知)为捕,除毋(无)罪;已刑者处隐官。”可(何)罪得“处隐官”?群盗赦为庶人,将盗戒(械)囚刑罪以上,亡,以故罪论,斩左止为城旦,后自捕所亡,是谓“处隐官”。它罪比群盗者皆如此。(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05页。)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释义:“‘监领人犯而将人犯失去,能自己捕获以及亲友代为捕获,可以免罪;已受肉刑的处隐官。’什么罪可‘处隐官’?群盗已被赦免为庶人,带领判处肉刑以上罪的戴着刑械的囚徒,将囚徒失去,以过去犯的罪论处,断去左足为城旦,后来自己把失去的囚徒捕获,这样应‘处隐官’。其他与群盗同样的罪照此处理。”(同书,第205~206页。)第九条:罷癃守官府,亡而得,得比公癃不得?得比焉。(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08页。)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释义:“看守官府的废疾者,逃亡而被捕获,可否与因公废疾的人同样处理?可以同样处理。”(同书,第208页。)第十条:“毋敢履锦履。”“履锦履”之状可(何)如?律所谓者,以丝杂织履,履有文,乃为“锦履”,以锦缦履不为,然而行事比焉。(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20页。)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释义:“‘不准穿锦履。’‘穿锦履’的样子是怎样的?律文所说,用不同色彩的丝织鞋,鞋上有花纹,才算锦履,用锦做鞋帮,不算锦履,然而成例同样论处。”(同书,第220页。)第十一条:内公孙毋(无)爵者当赎刑,得比公士赎耐不得?得比焉。(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31页。)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释义:“没有爵位的宗室子孙应判处赎刑的,可否与公士同样减处赎耐?可以同样判处。”(同书,第231页。) ⑤蔡万进《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研究》一书提及“奏谳决事比”,参见蔡万进:《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1页。 ⑥“决事比”又可简称“决比”。《魏书》“刑罚志”载:汉宣帝时期,“于定国为廷尉,集诸法律,凡九百六十卷,大辟四百九十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比,凡三千四百七十二条,诸断罪当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可见,“死罪决比”即为“死罪决事比”之省称。 ⑦“阑送南”一案,参见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93页。 ⑧《风俗通》所载《辞讼比》佚文三则,参见程树德:《九朝律考》,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2~33页。 ⑨程树德言:“考《汉志》有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七录》作《春秋断狱》五卷,《隋志》作《春秋决事》十卷,董仲舒传,《唐志》作《春秋决狱》,《崇文总目》作《春秋决事比》,并十卷。”参见程树德:《九朝律考》,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60页。 ⑩刘师培的观点,具体参见《刘申叔先生遗集》,儒学法学分歧论。 (11)也有学者直接指出,《奏谳书》所载春秋时期案例可以定性为“虚构”的“故事”。参见张忠炜:《读〈奏谳书〉春秋案例三题》,载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编:《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三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2)张伯元:《秦汉律令中的“廷行事”》,载张伯元:《出土法律文献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张伯元先生的立场表明,他否认《奏谳书》具有判例的性质,但是认为“廷行事”具有判例的性质。 (13)第162号简文:“毋敢履锦履。”“履锦履”之状可(何)如?律所谓者,以丝杂织履,履有文,乃为“锦履”,以锦缦履不为,然而行事比焉。(参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20页。)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释义:“‘不准穿锦履。’‘穿锦履’的样子是怎样的?律文所说,用不同色彩的丝织鞋,鞋上有花纹,才算锦履,用锦做鞋帮,不算锦履,然而成例同样论处。”(同书,第220页。) (14)参见明欣(张铭新):《中国古代“法治”形式的演进轨迹及特点》,载高鸿钧主编:《清华法治论衡》(第一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8页,注①。实际上,连劭名先生早就“廷行事”和“决事比”进行比较:“廷行事者,虽律文无所定,然事属多见,已无须引证旧案,法庭处理时自有之定则惯例也。而决事比多奇情怪事,世所罕见,论处时颇感棘手,一经判定,后世可据引比附,更有无旧例可寻,处理时比照他例以取决者,亦可称为决事比。”参见连劭名:《西域木简所见〈汉律〉》,载《文史》(第29辑),中华书局1988年版。 (15)“毋敢履锦履。”“履锦履”之状可(何)如?律所谓者,以丝杂织履,履有文,乃为“锦履”,以锦缦履不为,然而行事比焉。(参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20页。) (16)就字面意思而言,“行事比”其义有二:第一,“行事”(“廷行事”)将具体的某一待判案件中的“锦缦履”比照“锦履”处理;第二,“行事”(“廷行事”)将具体的某一待判案件中的“锦缦履”比照既有“行事”(“廷行事”)的处理方式进行处理。但是,就秦代的“比”的技术及睡虎地秦墓竹简的语言环境来看,第一种含义的可能性最大。也就是说,秦代的“比”就目前所见史料来看,还仅仅是简单的“比照”。 (17)第38号简文:告人盗百一十,问盗百,告者可(何)论?当赀二甲。盗百,即端盗驾(加)十钱,问告者可(何)论?当赀一盾。赀一盾应律,虽然,廷行事以不审论,赀二甲。(参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167页。) (18)其中,第151号简文“廷行事”原本脱漏一“事”字,整理者补之,第162号简文径称“行事”,整理者并未认为此处脱漏一“廷”字,也未认为是笔误,即原本就是“行事”一语。 (19)曹旅宁先生即认为《法律答问》之“比”字,乃是“类推”之义,即“按惯例类推如此处罚”的。参见曹旅宁:《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性质探测》,载《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20)参见陈公柔:《先秦两汉考古学论丛》,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180页。可见,“推比”同于“准照”,皆为比照、比附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