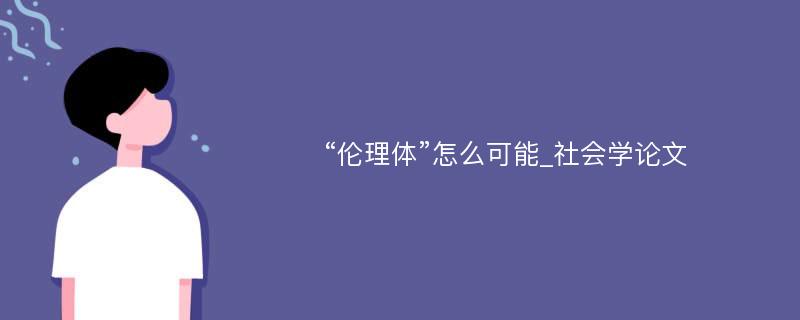
“伦理的身体”何以可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身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3)04-0023-07
20世纪80年代,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技术和知识逐步内化到身体之中,使得身体成为理解科学、技术与社会问题的新视角。身体社会学、身体政治学、身体伦理学等理论的产生,使得身体的自然和文化意义得以凸显。目前,关于“身体伦理”的研究主要有四种路径:其一,社会建构论和后结构主义视域中作为符号、空间和社会场域的身体。这些理论阐明伦理的主体是理性的自我,并认识到身体的多元文化意义,但都倾向于消除或回避身体的肉体性,忽视了身体的特殊体验与文化差异。因此,其伦理原则依然是理性的,难以有效地回应个体化的伦理困境。其二,后现代的“责任伦理学”突出强调伦理身体的情感方面以及伦理学本质上的非理性特征,认为伦理义务不是来源于逻辑和理性,而是道德情境自身的独特性。该观点认为“他者”在逻辑上先于“自我”,强调对他者的道德责任先于理性的计算,因而并未为涉身自我留出空间。其三,现象学和女性主义同时将身体看作伦理行动的客体和主体,把“自我”理解为相互纠缠的身体、心灵和世界,关注身体的特殊体验和文化差异,推行一种反本质主义的策略,较为有效地回应了伦理困境,但伦理行动的现实转化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其四,还有学者认为正是对现代性的不满促成了对身体与伦理关系的讨论,主张以一种后现代的反视觉冲动来回应视觉中心论的现代性的伦理原则,尤为关注伦理学和美学的关系问题。这种观点提出了一种开放、灵活、包容的审美视角,但也面临相对主义的困境。以上四种路径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都不同程度地涉及“伦理”和“身体”的关系,但并未对“伦理的身体”进行集中讨论。它们关于身体的反思更多的是“关于身体,而不是来源于身体”,并倾向于强调“表象的(如社会建构主义)而不是体验的(如存在主义和现象学)问题”①。而本文关于“伦理的身体”的探讨,则主要从来源于身体的角度,从涉身体验出发,对当今时代背景下诸多独特的道德困境进行回应。
一、社会学中的身体转向与“伦理的身体”
(一)社会学中的身体转向
在过去几十年间,身体变成一个时髦的话题。身体曾经只是生物科学领域的话题,而如今所讨论的话题则日趋广泛,从身份认同、社会运动、消费文化、伦理学到社会理论和哲学等。将身体包括在社会考察之中,对社会变化进行批判和反思,使得身体成为当代的某些焦点话题争论的前沿。因此之故,在当代人文社会科学中,除了人们熟知的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外,还有学者提出了“身体转向”,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身体社会”(somatic society)中。正如身体社会学家布莱恩·特纳(Bryan S.Turner)所言:“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我们主要的政治问题和伦理问题都要通过身体这一渠道来表达。”②身体社会学也成了研究“身体转向”的先驱。如今,身体社会学是充满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研究领域,也是理性控制面临争议的研究领域。“在认识论上,对身体的社会考察倾向于实用主义;在方法论上,它包容多元主义;在本体论上,它倾向于逃脱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的陷阱。”③然而,这种新的分支学科的出现,并不只是对理论的多元化和跨学科研究的反映。从现实层面来看,亦有必要对那些引发身体讨论的社会和文化事件进行考察。
社会学家们在强调自然和身体的意义的同时,却很少关注“伦理的身体”。于是,社会学领域有关身体和伦理的研究出现了如此境况:一方面,伦理和身体在社会学中的复兴(尤其是在生命伦理学中)在当今的社会学理论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另一方面,在社会学的身体转向中,伦理的身体却被忽视了。然而,后笛卡儿哲学——尤其是现象学和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社会学家感到有必要审视身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同时,身体自身也经常出现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可以是受尽折磨的妇女、是被终止的胎儿、是战争的受害者、是被移植的器官、是登上月球的人—机混合物、是显微镜下的DNA样本、是作为女人的男人或作为男人的女人、是被手术刀改变的身体、是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露宿街头无家可归的人,等等。所有这些来源于“身体”的问题都需要以伦理和身体的会合为出发点,来分析伦理和身体之间的互动如何反映了当代广泛的文化进步。
通过诸如此类问题的分析,衍生出身体社会学、身体伦理学和身体政治学等学科的研究主题。曾有两位著名的学者对身体类型进行了分析,体现在特纳的著作《身体和社会》和亚瑟·弗兰克(Arthur W.Frank)的文章《身体社会学:一种分析性的评论》中。特纳关注到身体管理的方式是根据社会的组织方式变化的,禁欲主义、父权制和商品化等构成了可能的方式。④弗兰克的“身体类型学”则部分地来源于对特纳的著作的批判性反思。他用“符号互动论”代替了特纳类型学中的功能主义,更加强调积极的身体,而不是受机制和结构束缚的身体。⑤这两种分析方法产生了有理论根基的身体类型。为了研究身体的转向,有学者将身体区分成医学的身体、宗教的身体、运动的身体、性别的身体、残疾的身体、工作的身体、消费的身体、衰老的身体、训练的身体、控制的身体、镜像的身体、交往的身体等等。当然,也有学者提到过“伦理的身体”,只是其重要性并未得到充分肯定和强调。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只是研究身体伦理问题的需要,亦是整个社会学和哲学研究的需要。
(二)何谓“伦理的身体”
身体在社会学中的再现是与理智的衰落相联系的。随着心灵放弃了在身心关系中的主导地位,身体的地位得以高扬。同样,伦理学也从理性中赢得了它的自主性,并且开始作为一个有着独特身份的社会学领域,从与美学的关系中脱离出来。尽管许多社会学者面对身体会有所保留,但他们仍然强烈地发出了道德关切的声音。
“伦理的身体”是在现代性视域中凸显出的一种新的身体类型。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全球化和地方化、后殖民主义和单一民族国家、新民族主义和跨国合作极为扩张的时代。我们生活在一个焦虑的时代,存在论意义上的不安全感是普遍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有趣的时代,过去的一些价值普遍需要重新审视。理性、真理和进步的启蒙价值观受到来自愉悦、欲望、感觉和情感的严重挑战。身体出现在价值的重估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代性和理性权威的消解,以及人们独特的道德困境的增加。
当代生活呈现出这样一种局面,就是依靠“传统”或者“传统的权威”来解决伦理困境再无可能。传统的身体尚未面对困境的增殖,而当代生活是以宗教权威、政治权威和科学权威的确定性的衰落为标志的。曾经,这些权威试图创造并解决20世纪晚期的伦理和道德问题。而今,伦理的增殖和问题化成为时代的特征。戴维·拉斯姆森(David Rasmussen)认为,伦理已经成为一个时代基本的特征,以至于“时代精神具有伦理标志”⑥。这种新的“时代精神”通过谈论道德危机的媒体话语得以加强。人们需要一种秩序感,需要一个与新的伦理困境进行斗争的社会。这种情境激励着具有新的伦理主张的多元声音的出现。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这种道德议程得到了迅速发展,以至于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充满了道德话语的世界中。
正是对现代性的不满激发了关于伦理与身体的争论。为了探索身体“生活的方式”,伦理学将我们带入了哲学或社会学的理论范畴;并且,随着伦理学与以理性为中心的传统之间的斗争不断的推进,作为欲望载体的身体也成为伦理话语重新表述的重要渠道。“伦理既是对内在生命的看护与整饬,也是对外在秩序的诉求和表达,是对生命感觉的梳理和现实生存的规范,而这种梳理和规范又是以身体的在世生存为起点的。”⑦而道德、美学与身体在社会学中的会合,产生了“伦理的身体”的概念。概言之,“伦理的身体”是随着现代性和理性权威的消解,以及主体的道德困境增加而出现的一种新的身体类型。身体出现在价值重估中,身体的感受成为了价值的重要来源。
当代文化中的涉身体验建立在这样一种假定的基础上,即认为身体的外表和内部是易于重构或合并的。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大众文化的兴起,自然和文化之间的界限已经坍塌。身体的可变性、延展性得以充分体现。身体不再被理解为固定不变的本质,身体所经历的变化不再被看作是完全依赖于自然生理进程。身体成为生活方式的附属品,成为可以被雕刻、被形成和被效仿的东西。身体不再承担固有的特定的功能,而是变成不断调整的自我。自然构成的被绝对限制的身体概念逐渐萎缩,身体已经从一个生物学事实变成了一种“工程”和一种“表现”。所有这些,使得身体面临许多新的伦理困境,也使得“伦理的身体”作为一种新的身体类型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二、“伦理的身体”研究的两个重要维度
“伦理的身体”的出现是时代的产物,也是身体与道德、美学在社会学中会合的结果。因此,在“伦理的身体”的研究中,有两个重要维度不容忽视:一是与道德的关系,二是与美学的关系。
(一)“伦理的身体”与道德
在社会学的“身体转向”中,对伦理的身体的忽视是令人惊奇的。尤其是在当今时代,伦理问题更多是在对生物医学技术(如生殖技术和遗传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回应中产生的。特纳用“身体社会”这个术语表达对身体的重视,其意义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就是道德问题要通过身体渠道来表达。从这个视角来看,在当代社会中,由于身体的差异,个人需面对不断增长的复杂的伦理决定。科学、技术和当代媒介为这些决定的判据提供了很多信息,但同时也产生了新的伦理困境。似乎伦理学永远在追赶科学的发展。这种信息超载的局面和伦理问题的增加,使得做伦理的决定更加复杂化,以至于人们认为,道德一直是个人化的、私人化的和成问题的。
现在,我们比先辈们更加清楚这个时代的社会问题和道德问题。我们的先辈们不必担心无性生殖的优劣,也不需要做关于器官移植的决定,更不会考虑克隆人和转基因食品的意义。他们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这些创新背后的技术不存在。在任何时代,技术总是新技术,并且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社会的或者伦理的问题。我们的先辈们之所以不考虑这些问题,是因为有一些更高的权威在告诉他们如何面对。一言以蔽之,“他们只需要了解技术变化带来的解决办法,而不必了解技术变化带来的问题”⑧。我们也经常听到一些诸如虐待儿童、对女性施暴、同性恋恐惧症、种族歧视和环境破坏之类的社会问题。并不是说这些问题过去就不存在,它们过去也存在。但是,在性别不平等或环保意识等领域的广泛的社会和文化变革中,这些问题已经处于当代道德议程的前沿,面临更多的伦理困境,它们在我们传统的文化方案中并没有适当的位置。
如今,围绕一些新社会运动出现的问题和情境,“伦理的身体”作为一种道德考量方式已经无所不在,道德领域也成为一个充满竞争的场域。在道德考量中,身体既被看成是伦理问题的来源,也是身体伦理的场域。代理母亲、胎儿遗传病筛查、流产、安乐死、整容和变性等,它们只是当代生命伦理争论的一部分。然而,这种讨论的焦点与其说是在伦理“问题”上,毋宁说是关于身体在伦理学中“生活”的方式。道德和身体之间特殊的友好关系也因之备受关注。
在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看来,身份认同的建构是积极的、流动的和多元的过程。身体的可变性是与不断变化的文化规则和价值相关联的。这些规则和价值提供了身份认同得以建立的资源和选择,从而将自我的建构与消费商品和生活方式选择的多元性联系起来。换言之,消费文化对身份认同的建构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对吉登斯来说,消费文化并不是伦理学建构或者是体验的场域。他主张,道德已经通过工具理性的控制、体制化和规范化从日常生活体验的世界中隐退。因此,“自我的任何反身性方案都承载着很多自主和幸福的可能性,却不得不在严重缺乏伦理内容的常规语境中被承诺”⑨。
随着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理性至上的批判,以及新的社会运动引发的新的社会知识的生产,使得有伦理色彩的社会学的探寻成为可能,也影响到关于伦理学的社会学的发展。近年来,伦理的争论已经成为社会和文化理论的中心,而伦理学和身体之间的联姻亦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
(二)“伦理的身体”与美学
对伦理的涉身性来说,“伦理的身体”提出了伦理学和美学的关系问题。伦理学和美学的碰撞并不是新鲜事物,美学概念中关于身体的话语产生于18世纪,希腊哲学、笛卡儿哲学以及康德哲学对此都有过追踪。继而,身体伦理在当代消费文化和大众文化中再次活跃,被称为“日常生活的美学化”。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的《美学意识形态》将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联系追溯到当代消费文化。他将日常生活的美学化看做是战后社会的主要特征。在真实的有效性逐渐衰退的过程中,当代社会的审美要素成为了关键的统一力量。他认为,价值已经被审美化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道德被转化成一种风格”⑩。
美学与伦理学之间,美与道德之间的辩证法并非只局限于当代的消费文化。在欧洲文化中,美和道德之间的联系源远流长。伊曼努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将涉身的伦理学概念化为“责任伦理学”(Ethics of Responsibility)。露西·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充分利用列维纳斯的成果,强调伦理的身体的情感的和感性的方面。但是,伊格尔顿认为,这种美学研究的形式并不是伴随启蒙思想开始的,必须追溯到古希腊时代,才能见证美与道德之间最早的相互作用。安东尼·辛诺特(Anthony Synnott)将美的起源追溯到苏格拉底,他在一个形而上的层面,将美等同为善。辛诺特总结道,在当代社会中,美和丑已经不只是象征着“肉体的对立”,还象征着“道德的对立”。(11)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对伦理学和美学之间的后现代联姻进行了深入探讨。福柯的美学伦理学试图探索主体与自我之间的关系,切断了被认为存在于个人伦理和广泛的复杂的道德结构之间的界限。当被问到“哪种伦理学是可能的”时,福柯回答:“在我们的社会中,艺术已经成为某种只与客体有关,而不是与个人或者生活有关的东西。艺术是专业化的,或者是被那些艺术家们完成的东西。但是,为什么每个人的生活不能成为艺术品呢?……从‘自我并非是给定的’这一观念来看,我认为只有一个实践的结果,即我们不得不将我们自己创造为艺术品。”(12)福柯强调,必须将个体自身建构成伦理的主体。也就是说,个人有义务使她/他的生活方式成为美的东西。美德的存在是通过精致的生活实现的。福柯通过美学伦理表达出一种超然的、公正的审美态度。对福柯来说,伦理学作为一种存在的艺术,是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的呈现。它更多的是一个有关于“什么才是对的”问题,而不是“做什么才是对的”。伦理学可以被理解为“存在的艺术”,这意味着伦理的身体可以在日常生活的涉身实践中被认同。
有一种流行的观念是,消费文化是享乐主义的。在消费文化中,自我的感受是与无节制的个人消费观念深刻地联系在一起的,以至于在当代社会中,关于自我身份认同的主流的表述变成了“我消费故我在”。这个世界就像是一个超市,一个有着无限选择却绝少束缚的空间。常规的行动被还原成选择的美学。在这个道德沙漠中,如果有人想达到好的生活目标,那么他最需要的特性就是更好的选择能力。然而,在这种观念中,他们没有充分认识到消费的身体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伦理。同时,也没有看到对于一个有着美学伦理观的消费者来说,消费文化包含着多大的潜力。在审美被商品化的世界中,强加在消费主体身上的束缚是可见的,以至于价值和美丽可以被转换成“那些可以买卖的东西”。辛诺特也主张,在经济学中,所有的买卖都包含着一个审美的维度。吉列恩·本德洛(Gillian Bendelow)和西蒙·威廉姆斯(Simon J.Williams)也曾指出,那些关注外表的消费者可以被理解为,“面对价值和生活方式选择的多元性,尝试成为控制和建构‘正确的身体类型’的那部分人”(13)。这意味着,尽管是在消费文化的道德沙漠中,美学伦理学依然起着调整身体及其外表的作用。
三、“伦理的身体”的主旨——情感的身体
与其他的身体类型相比较,“伦理的身体”旨在强调情感的身体,而不是理性的身体。在关于涉身体验的伦理学中,有两种不同的关注倾向。一种是以福柯为代表,强调“批判的自我反思”在审美生活中的重要性,这就导致了个体对技术和外表的关注。另一种是以米歇尔·马非索里(Michel Maffesoli)为代表,他指出审美伦理是以感受和关系为特征的,是移情而不是理性维系着“情感共同体”的联系。(14)
现代性中的伦理学不仅是在理性主义的框架中建立起来的,而且还建立在“所见即所知”这一假设的基础上。马丁·杰伊(Martin Jay)将其称之为“视觉中心主义”(oculocentrism)。现代性是源于笛卡儿的视觉中心主义的视觉文化,“视觉对身体的塑造是关于身体审美化眼光的改造,也是视觉话语权力的行使”(15)。但是,20世纪的文化批判已经不断演变成对视觉的“断定的”(assertoric)本质进行批判。这不仅巩固了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而且对提升伦理思想和行动的价值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即使后现代转向揭示了一个超视觉的世界和碎片化的图像,在后现代中依然有一种“强有力的反视觉冲动”(16),他们主张一种开放的、关怀的、可变的视觉。视觉是由男权主义主导的,以至于将女性建构为被注视的客体。因此,伦理学应当担负起另一种责任,“它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情感生活和智力发展是最重要的”(17)。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的“责任伦理学”认为,“道德现象本质上是非理性的”(18),因为道德责任(或者是对他者的责任)先于理性的计算。道德语境是有冲突的,而道德自我是不确定的,通过道德行动的变迁来感受道德语境。但是,鲍曼的后现代伦理学并没有给“涉身”留出一个特殊的位置。鲍曼的伦理学主张来源于列维纳斯的反本体论方案。对列维纳斯来说,“伦理义务不是产生于理性的逻辑上的和本体论上的普遍性,而是产生于道德情境自身的独特性”(19)。它要求人们必须放弃哲学上对“存在”的专注,不再以理性或者视觉为中心。我们可以避免复杂的争论,“超出存在”,与他者在一个道德的领域中面对面。无条件的关怀,就是进入道德自我的领域,这是为了他人的自我。爱、触摸、道德、身体和共同体是造就道德公民的主要因素,但它们在现代性中被理性化了。在当代世界,伦理的争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保持开放。
当代的伦理争论是在伦理领域中建构它的话语的,并且处于模棱两可的、感知的领域。如果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必将伴随伦理选择,那么伦理学就无法建立在理性和权威的基础上。伦理的自我很可能生活在亲密的共同体中。它需要开放、宽容,尊重身份认同,保持差异并且超越差异。尽管当代社会语境有模棱两可的本质,但身体依然表现为伦理的身份认同的主要场域。实际上,尽管身体只是在表象的或者符号的层面上被概念化的,伦理学依然是一个有必要关注的领域。
然而,对伦理学及其叙事来说,还有很多比肤浅的对时尚和外表的感受更值得研究的东西。当感受而不是表象成为当代道德行动的争论的主题时,涉身伦理的社会学的潜力就显现出来。正是对情感而不是理性、感受而不是表象的强调,为“伦理的身体”提供了一种更加充分的解释,这才是发展一种更加伦理化的涉身伦理的社会学基础。
四、“伦理的身体”研究的内在逻辑
在社会学领域的身体转向中,学者们虽然意识到了以理性为中心的伦理概念和伦理方法对身体的影响,但尚未形成对涉身伦理的深入思考。这种理论考量和涉身伦理学在后笛卡儿的社会理论中得以统一,但仍然存在一个值得争论的话题:涉身伦理中的身体是否具有肉体性?不管各个流派之间的分歧有多大,有一个事实不能忽视,就是伦理和身体的故事尚未结束。
(一)重新审视伦理与身体
现代性的伦理学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坚持普遍的原则可以并且应该根植于社会生活中。随着后现代性理论对伦理学的不断冲击,有人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义务的社会之中。也有人认为后现代性的评判也是过时的,我们依然不能肯定后现代性可以作为道德的启蒙而被载入史册。
古典社会学认为,身体属于生物学领域,这一主张似乎已经坍塌。随之,身体除了具有生物学意义之外,也变成语言学、文化和社会分析的问题。实际上,身体之所以成为一个吸引人的研究对象,其原因在于,身体的研究方式使得生物学和社会学、自然和文化之间的区分成为问题。在我们理解身体与文化感受性的关系中,存在着这样的历史逻辑,即对身体探讨的兴趣不断增长。随着人们对身体本质的看法的改变,科学和哲学都开始对身体进行重新审视。在很多方面,身体都是作为后现代的指示器而出现的。
在现代性话语中,身体被概念化为社会和文化的范畴,这是有点反直觉的。现在,人们重新认识到身体“肉体性”的意义,并期待从自然身体话语中得到更多。另一方面,人们也认识到,思考和谈论我们自己和他人身体的方式,以及分类、管理和操纵身体的方式,并不只是自然的实践,本质上也是由社会界定的行为。因此,“身体究竟是什么”、“如何看待身体”、“伦理与身体的关系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也将成为科学、哲学以及社会理论研究的重要主题。
(二)不存在“没有身体的思考”
尽管社会学家认为身体是新的文化感受性的指示器,但随着科技力量对身体的大肆入侵(如“阿凡达”、“克隆人”、“机器人”等),身体的日常意义正在不断地下降。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曾经说过,未来人类可能会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如何使没有身体的思考变得可能?”(20)此问题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的基础上,即身体被看做不利的条件,并且可能会被计算机取代。尤其是随着通信和娱乐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赛博空间的不断延伸,人们开始慢慢地怀疑物质的身体对日常生存的必要性。有人可能会说,在赛博空间中可以不受肉体能力的局限。我们的外表、性和肉体的能力都是可以被塑造和重塑的,想象力是唯一的限制。医疗技术的进步使得运用医疗器械可以取代原本必要的身体器官,诸如心脏、肺等。有人甚至认为,赛博格已经成为一种实在。
虽然我们变得越来越依赖技术,但将这些发展与“身体的消解”混为一谈是不对的。技术在什么程度上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形象和意义?身体结束、计算机开始的地方又在哪里?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重新界定我们的身体在赛博空间中的能力,是不能与社会文化的期望分开的。退一步讲,即便是“没有身体的思考是否可能”这样的问题,也是无法逃脱“身体”而存在的。
(三)超越身心二元论
如果我们不够小心,将身体作为解释当代社会生活复杂性的来源,那么心灵作为人的整体维度之一就很容易被忽略。这种错误不仅会证实本体论判断的缺失,还会削弱人文社会科学对作为肉体的—智力的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解释能力。我们也不能把我们的思考终止在身体的肉体界限上。我们的身体本身就是与物质的客体紧密地缠绕在一起的。“通常,只有当身体占据特定的空间和地点,并且通过特定的时间关联运动时,身体对我们自己和他人才是有意义的。”(21)
不管身体社会学、身体伦理学将来向哪个方向发展,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对身体的关注已经进入到社会考察和研究的重要领域,并且不再那么容易被边缘化。有关“身体转向”的一些努力,不过是鼓励大家从“身体”这样一个视角,重新思考社会文化与肉体之间的关系。毕竟,无论是哲学,还是社会学,从其本质上讲,都根植于不断变化和冲突的世界之中。我们与身体的关系,以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也在不断发展和演变。因此,我们相关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都必须跟上这种变化,以应对那些有趣的伦理问题和挑战。
注释:
①S.J.William,and G.A.Bendelow,“Malignant bodies:Children' s beliefs about health,cancer and risk”,in S.Nettleton and J.Watson(eds)The Body in Everyday Life.London:Routledge,1998,p.104.
②B.Turner,The Body and Society:Explorations in Social Theory,2[nd] edn.,London:Sage,1996,p.6.
③P.Hancock,(et).The Body,Culture,and Society:An Introduction.Buckingham:Open University Press,2000.p.2.
④B.Turner,The Body and Society:Explorations in Social Theory,2[nd] edn.,London:Sage,1996.
⑤A.W.Frank,“For a sociology of the body:An analytical review”,in M.Featherstone,M.Hepworth and B.S.Turner(eds)The Body:Social Process and Cultural Theory,London:Sage,1991.
⑥D.Rasmussen,Universalism Vs Communitarianism:Contemporary Debates in Ethics,Cambridge,MA:MIT Press,1990,p.1.
⑦唐健君:《身体作为伦理秩序的始基:以身体立法》,载《学术研究》,2011(10)。
⑧P.Hancock,(et).The Body,Culture,and Society:An Introduction.Buckingham:Open University Press,2000.p.106.
⑨A.Giddens,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Love,Sexuality and Eroticism in Modern Societies.Cambridge:Polity Press,1992,p.176.
⑩T.Eagleton,The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Oxford:Blackwell,1990,p.368.
(11)A.Synnott,The Body Social:Symbolism,Self and Society,London:Routledge,1993,p.95.
(12)M.Foucault,Ethics:Subjectivity and Truth,London:Allen Lane(ed.P.Rabinow,trans.R.Hurley).1997,pp.261—262.
(13)S.J.William,and G.A.Bendelow,The Lived body:Sociological Themes,Embodied Issues,London:Routledge,1998,p.73.
(14)M.Maffesoli,The Time of the Tribes.London:Sage,1996.
(15)黄琴:《身体与身份的视觉伦理关联——视觉的伦理关涉和悖论(续)》,载《道德与文明》,2011(5)。
(16)M.Jay,Downcast Eyes:The Denigration of Vision in Twentieth-Century French Thought.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p.546.
(17)A.Synnott,The Body Social:Symbolism,Self and Society,London:Routledge,1993,pp.156-157.
(18)Z.Bauman,Postmodern Ethics.Oxford:Blackwell,1993,p.11.
(19)F.Ciaramelli,“Levinas's ethical discourse:Between individuation and universality”,in R.Bernasconi and S.Critchley(eds)Re-Reading Levinas.Bloomington,I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1,p.85.
(20)J-F.Lyotard,The Inhuman:Reflections on Time.Oxford:Polity Press,1991,p.13.
(21)P.Hancock,(et).The Body,Culture,and Society:An Introduction.Buckingham:Open University Press,2000,p.121.
标签:社会学论文; 伦理学论文; 消费文化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视觉文化论文; 消费社会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美学论文; 现代性论文; 后现代主义论文; 人文学科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