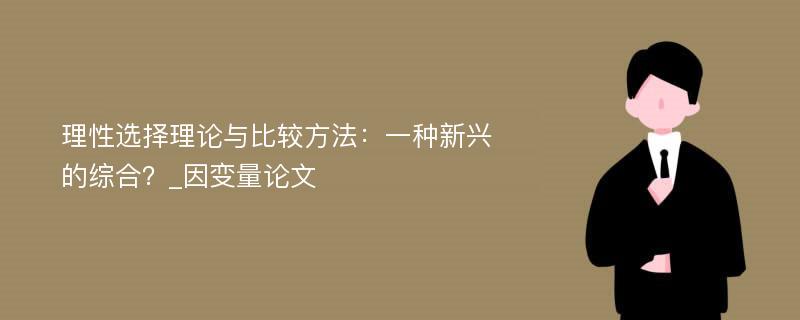
理性选择理论与比较方法:一个正在出现的综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性论文,理论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前沿的理性选择理论家对从特定案例中汲取详细证据这一研究方法越来越有兴趣。在目前已经非常有影响的《分析性叙述》(Analytic Narratives)①一书中,罗伯特·贝茨(Robert Bates)及其合作者明确表示,他们的研究工作“被一种解释特定事件和结果的愿望所推动”。他们把自己的研究努力看成是对“表意传统”(ideographic tradition)的一种贡献,因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对显现在特定时期或背景中的事件的深度调查”。而且,约翰·鲍温(John R.Bowen)和罗杰·彼得森(Roger Peterson)在其主编的《政治与文化中的关键性比较》(Critical comparisons in Politics and Culture)一书中明确表示,他们的研究努力希望发现理性选择理论与人类学二者之间的关联。这本编著的作者们被一种“对描述和解释‘实证丰富性’(empirical richness)的共享的承诺”联系在一起。这本书的核心目标是探索理性选择理论如何可以从人类学中借鉴知识并因而“充分地描述世界,展现其复杂性和变化性”。 通过这种对人类学方法的强调,理性选择理论家将其讨论的重心重新集中到长期以来一直与比较方法——如盖伊·彼得斯(Guy Peters)的《比较政治:理论与方法》中的主题——相联系的学术传统上。例如,这些理论家们重新呼吁一种小样本研究设计(对有限的案例进行系统的研究)。他们指出,小样本案例可以在针对那些经验难点和实质问题的基础上被选择出来,即便这一点意味着某种“因变量驱动”的研究。同时,理性选择理论家强调对高度相似或高度异质案例的深度可控比较,也强调那些将变量联系在一起的过程分析和机制分析的意义。与这些各种各样的关切联系在一起,新的理性选择文献还强调调查者要通过“阅读文件、查找历史档案、访谈和调查二手文献”等方式,将自己浸没在所研究的案例之中。 可能最显著的是,这些文献在系统地弱化演绎研究的重要性,同时又显著地提升了分析性归纳在研究中的作用。贝茨和他的合作者在研究中呼吁,希望在理论与证据之间形成一种互动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分析者可以根据其案例的实际历史状况来重塑其初始理论。通过这种方式,“理论被案例材料所塑造”。同时,在这种研究中,理论普遍性与经验有效性的平衡就显得非常重要,而且对经验事实的正确把握也是这一研究所强调的重点。 理性选择理论在这些新方向上的发展可以被看作是比较方法和小样本分析在比较政治研究领域的胜利。至少我们可以说,理性选择理论家已经在倡导小样本分析者所长期坚持的一些研究倾向:这些长期倾向不仅包括对小样本和解释特定结果的关注,还包括在演绎和归纳研究之间、在理论发展和历史细节之间进行平衡的努力。 然而,如果说新的理性选择研究正在全身心地拥抱比较方法和小样本分析,那可能也是不正确的。更合适的评价是,理性选择理论家仍然习惯用模型和形式推理来解释事件。虽然他们已经放弃了追求普遍性理论的可能不太现实的目标,但是他们的任务仍然是在理性选择理论的假设下证明社会世界是如何被模型化的。这一点将他们与传统的比较方法的倡导者区别开来。传统的比较方法论者不一定会认同理性选择的模型分析。实际上,理性选择分析者把他们的新路径看成是形式理论与比较方法的新综合——一种“两个世界的优势”(best of both worlds)结合在一起的方式。这一方式是对在律则式分析(nomothetic analysis)与表意式分析(ideographic analysis)、演绎推理与归纳推理之间旷日持久的争论的一种尝试性解决方案。 在本文中,我提出了下面的观点:近期理性选择理论与比较分析的接近是比较政治领域中一个有益的发展。理性选择理论的一个广为人知的困难——它的倡导者和批评者都清楚这一点——便是学者们对发展模型关注太多,以至于他们不能告诉我们那些在实际政治过程中真正有用的东西。可以论证的是,美国政治领域便经历了这样的问题:一个相对局限的研究领域被理性选择理论的一些特定标准所推动而向前发展。相比而言,比较政治中的理性选择学者试图通过使用比较方法去抵制这种倾向,并尝试更多地去关注政治本身的实质性内容。 同时,我对将理性选择理论和比较方法这“两个世界的优势”综合在一起的可能性表示一点保留意见。比较政治逻辑和理性选择理论的逻辑之间存在真正的紧张关系,而且这种紧张关系不能被弱化,也不能被忽视。从极端的意义上讲,理性选择理论会通过减弱对严格假设检验的关注或为归纳研究的有效使用设置障碍等方式,对比较方法的一些核心优势产生破坏性的作用。然而,如果理性选择理论家继续把重点放在挖掘比较方法的传统特征并较少考虑一些模型发展的话,那么我会倾向于认为,前述的紧张关系在未来会得到缓解。 在本文中,我会关注近来理性选择研究与比较方法相关的一些议题。我关注的重点不是这些研究所提出的一些具体的实证观点。之所以这样,并不是因为这些实证问题不重要,而是因为本文希望关注在其他地方已经出现的关于理性选择理论的争论。 比较方法 讨论理性选择理论新发展的一个好的起点是对比较方法的一些核心要素进行回顾。当然,比较方法并不是新的;它在政治研究中的应用在30年前就开始被讨论。最初是利普哈特(Arend Liphart)的研究,之后又发生了许多次理论创新。然而,作为其基础,比较方法仍然主要关注那些小样本案例的系统分析,并致力于产生和验证那些以原因分析为内容的理论。虽然这一路径可以与统计方法、实验方法和案例研究方法相比较,但是在实际的研究实践中,它经常与其他方法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在《比较政治:理论与方法》一书中,彼得斯讨论了与比较政治相关的、非常宽泛的一组议题。他的讨论包括不同的比较研究设计、比较研究类型、分析的层次、案例选择、测量、概念的形成和使用、解释的层级、理论的使用、后设分析、事件数据、案例研究设计和统计工具等。虽然彼得斯的研究不可能完全没有纰漏②,但是这本著作集聚了许多从比较政治的实证研究中提取出的有益的洞察和例证。彼得斯对概念的形成和使用——一个在方法论领域被长期忽视的议题——给予了较大篇幅的关注,令人印象深刻。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会关注对理性选择理论与比较方法之间整合最为重要的三个问题:假设检验的方法,在概念的有效性和普遍性之间的潜在平衡,以及使用归纳法来发展新的概念和理论。 首先,比较方法为假设检验提供了一组程序。这些程序不能被认为仅仅是发现理论或假设生成领域中的内容。彼得斯讨论了这些程序中的一部分,包括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求同法和求异法、共变法和布尔代数(Boolean algebra)。另一些重要的方法包括各种各样的“样本内分析”,例如模式配对、过程追踪、事件结构分析和因果叙事等,以及最近关于模糊集合的新发展。鉴于这些研究方法正在界定目前这一领域的基本研究状态,因此所有试图在小样本分析中系统检验其假设的学者都会采用这些方法中的一种或多种。 第二个议题涉及概念有效性(例如我们的概念与我们的观察保持一致的程度)和概念普遍性(例如某些解释可以被应用的案例中)之间的关系。在比较方法传统的范围内工作的分析者在选择其案例时经常面临这样的实证难题:他们的观点可能不能在其他的、数量较多的案例中得到广泛应用。为了满足其概念的有效性,同样也为了避免那些在高度多样性的案例比较中经常存在的原因异质性(causal heterogeneity)问题,这些分析者经常不得不去牺牲普遍性。他们认为,当把某些概念和假设扩展应用在大样本案例上时,概念有效性经常会丢失。因此,在小样本分析中,一方面,对普遍性的限制成为其研究中一个明显的不足;另一方面,从特定案例的深度知识中汲取的实质性概念内涵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平衡普遍性的不足。 最后,比较方法为新概念和新解释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些概念和理论发展部分依赖于学者们的想象,同时也依赖于“让案例材料来证明分析”。这些材料应该是一些没有被某种预设分类或理论倾向的厚眼罩过滤过的材料。许多学者(包括彼得斯)都特别强调了归纳驱动研究(inductively-driven research)在产生新概念、新解释和新的普遍性理论倾向过程中的作用。 接下来的章节将讨论理性选择理论家如何在这三个领域中运用比较方法。 假设检验的方法 理性选择理论本身不青睐任何检验假设的方法。但是,作为一个产生假设的工具,从原则上讲,理性选择理论可以与原因评估(causal assessment)的许多其他不同的方法结合起来使用。然而,鉴于前面讨论的理性选择理论家们都基本上选择小样本展开其调查,所以他们把进行假设检验的几乎所有统计方法都排除在外。这样,当他们检验其假设时,就必须依赖一种或多种前面提及的小样本方法。③ 在我看来,不幸的是,这些新理性选择理论的倡导者们对假设检验的方法讨论得还非常不够。在《分析性叙事》和《政治与文化中的关键性比较》两本编著中的各类理性选择论文中,多数研究者都没有提供关于比较的使用和检验假设方法的讨论。两个不完全的例外是戴维·莱廷(David Laitin)的《种族暴力的比较分析》和盖迪斯的《拉美的文官制度改革》,这两篇论文是这两本编著中最优秀的研究成果。然而,即便是这两位非常有思想的分析者也未能提出一些具体的因果推理策略。从我阅读的情况来看,两位作者着起来都在使用密尔的求同法和求异法。盖迪斯似乎用这些方法来选择基于自变量的案例,而莱廷则用这些方法选择基于因变量的案例。无论如何,假如在这些章节中有一个更为清楚的关于假设检验的讨论的话,那么读者会更容易对提出的假设进行评估。 对假设检验方法的模糊处理会存在一个危险,即分析者可能会简单地对待或忽视替代性的假设。例如,在前面讨论的两本编著的论文中,阿夫纳·格雷夫(Avner Grief)、罗杰·彼得森和罗伯特·贝茨的研究对理性选择传统之外的竞争性假设(rival hypothesis)的关注非常少。对竞争性假设缺乏足够的关注也并不是理性选择理论特有的缺陷,但是理性选择理论的模型分析传统使得这一问题显得更为严重。从这个意义上讲,理性选择理论家们(像所有的理论家一样)可以从比较方法的例行标准中得到一些提醒:假设的价值完全依赖于其与其他竞争性假设相比而言的解释效用。假如其无法得到严格的实证检验,那么从理性选择理论假定推演出的假设的价值就很小,无论其形式模型有多么复杂。 在上述这一问题之外,理性选择研究与因变量分析相接近的方式也是被讨论的内容。其中一个问题涉及因变量的界定,这是所有的小样本分析都强调的一个要求,虽然分析者有时很难做到这一点。在理性选择分析的传统中,因为学者们在考虑某些对具体结果的解释之前花费了大量时间在他们的模型上,所以这一问题显得更为严重。例如,在前述的那两本编著中,一些作者仅仅标明了他们的因变量对于其分析的不同价值,但是却没有说清楚这些具体的比较是解释什么问题的。例如,在格雷夫和莱维(Margaret Levi)的案例中,因变量的具体价值仅仅在其分析的过程中才能显现,这使得对这些案例中观点的评估变得比较困难。 理性选择理论家希望将其注意力仅仅放在一些具体的因变量上,而这种研究往往可以通过形式理论来表达。这一点成为第二种关切的来源。例如,方法驱动(而不是问题驱动)的路径促使米利亚姆·戈登(Miriam Golden)建议,学者应该将其注意力集中在针对小事件(small events)的问题上,因为这些问题比那些产生重要结果的问题可能会得到更充分的回答。然而,从比较方法的视角来看,一个基本的标准是:研究应该首先被重要的实证问题所驱动;对一个大问题的部分回答同样可以是有用的,甚至比一个对相对小的问题的合理回答更加有用。 可能因为大问题更为有意义,所以一些作者一方面将自己置身于一种与某一主要因变量相联系的关系中,另一方面又去解释这一因变量中更容易被理性选择理论接纳的有限内容。例如,让-劳伦·罗森萨尔(Jean-Laurent Rosenthal)先是指出他对法国和英国之间的政治差异非常感兴趣,然后又将他的因变量限定为法国和英国之间的税率差别。这种讨论会让读者对因变量的构成问题产生混淆性的认识。再如,巴里·温加斯特(Barry Weingast)在其讨论中似乎把美国内战或南部脱离联邦作为因变量,但是在笔者看来,其因变量既不是内战,也不是南部分裂出去。从笔者的解读来看,温加斯特讨论的结果似乎是经过几十年的相对和平之后在19世纪50年代发生的地区性政治危机。温加斯特并没有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参议院中平衡统治(《密苏里妥协案》使得蓄奴州和自由州在参议院的席位保持平衡)的打破导致了美国内战或南部脱离联邦。相反,温加斯特只是说,《密苏里妥协案》遭到破坏引发了一场政治危机。从这一意义上讲,在提出一个主要因变量的幻象之后,温加斯特最后得出了一组温和的、相对常规的、关于一个有限因变量的结论。 理性选择理论似乎并没有有效地和明确地使用比较方法的一些精髓,而这一点需要放在特定的情境下去理解。理性选择理论的魅力主要在于其优美的逻辑及其将社会行为模型化的能力。这一领域的声望主要建立在发展精细的模型以及从已有的模型中生成新假设的基础上,其通过检验假设或根据竞争性解释来分析假设的成果非常少。正如玛格丽特·莱维——一位非常活跃的、在方法论上具有自觉意识的理性选择分析者——所指出的:“这一领域对形式理论(formal theory)的发展更为强调,而对如何使用形式理论去解释实际发生的事件或选择却较少关注。” 伴随着理性选择理论家越来越多地接触比较方法。我们可以期待,模型建构的成果会逐渐让位于那些在理论与实践中发生碰撞并从中发展出有效解释的成果。并且,随着理性选择理论家更为青睐比较方法,它们可能会对小事件解释的兴趣越来越小,并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大问题的解释上。在这些关于大问题的分析中,解释性框架(无论是理性选择导向的还是其他导向的)显得尤为重要。虽然有证据表明这些变化正在发生,但是理性选择理论家在多大程度上会实现一种与比较方法的综合,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普遍化、有效性和案例选择 就第二个主题(关于概念有效性和普遍性的关系)而言,近来理性选择理论家并不讳言其在特定案例分析中为得到解释的充分性而牺牲了普遍性。实际上,某些解释所应用的案例范围经常是很少的一些国家(或者有时仅仅是一个国家)。尽管一些学者认为博弈论模型“从理论上清楚地界定了案例的范围(这些范围是某些预测所期望发生的范围)”,但是在新的理性选择文献中,案例的范围非常小,而且经常被时间或空间的边界所限定,而不是被更为抽象的领域条件(scope conditions)所界定。 如前所述,在比较政治方法的传统中,牺牲一些普遍性而实现某种概念的有效性是一种相对常见的做法。然而,传统的理性选择理论家在试图实现这种平衡时往往面临一些困难。为了使用理性选择理论的一些形式工具,学者们必须在某个假定的社会情境中找到相关的行为者和关键决策。这样一个模型化的过程经常会对这些行为者的本质及其可能的决策结果进行一些具体材料的简化。换言之,这种模型化的行为会促使分析者采取分类的方法,而这种分类方法是一种高度普遍化的抽象,其对特定案例的情境化特征缺乏敏感性。对于那些宣称可以生成普遍性假设(在所有的时间和空间中都可以得到应用的假设)的模型构建者而言,这种对高度普遍性分类的方法可能并不构成任何问题,但是在那些新的理性选择文献中,这些模型很明显只是希望产生一些具备有限普遍性的可检验假设。因此,这其中的危险是,新的理性选择文献可能会综合“两个世界中最差的东西”:一方面缺乏解释的普遍性,另一方面又充斥着过度模式化的、非情境化的概念。 上述讨论的情形正在变成一种现实,并已经出现在已有的研究中。在目前的一些成果中,与从历史叙事向模型的转变相伴而生的是概念有效性的巨大流失。例如,虽然格雷夫对中世纪晚期的热那亚有非常细致深入的理解,但是他的模型引导他更多关注两个被假定为持续的战略行动者的家族。罗森萨尔将英国和法国的行动者简约为精英与国王,这也是基于同样的逻辑。在这些研究中,正式的模型似乎将分析者锁定在一个预先设定好的游戏中。在这一游戏中,行为者和决策方案是静止的和非情境化的。虽然分析中的简化对于任何研究都是必要的,但是小样本分析的优势就是,分析者对每个案例都了解得足够多,并期望捕捉发生的政治情境的变动性。在这种变动的情境中,核心的决策者不断发生变化,并且核心的决策也随着情境的演变而发生变化。从理论上讲,理性选择理论可能会对一些细微的差别进行模型化,但是在实践中,学者们很少会牺牲逻辑的简化而去描述细节。 在一些实证的操作中,一些偏好稳定且相对固定的行为体的理性选择假设可能比较适合于小样本分析。在一些游戏规则固定且透明的制度设计中,这一点表现得更加突出。例如,就盖迪斯对拉美文官制度改革的研究而言,因为她的简化假设在民主立法的情境下是合理的(在这一情境中,治理政治行为和政治生存的正式规则依赖于再次赢得选举这一事实),所以她的研究在概念层面非常具有说服力。 然而,比较政治中的一些非常有意义的问题都发生在正式制度之外,发生在一些政治行动很难被模型化的领域中。由于认识到这一点,一些正式模型的分析者可能会倾向于倡导一种由方法驱动的研究。在这种研究中,问题会限定在某些理性选择的简化假设可以持续存在的领域中。相比而言,正式模型的反对者可能会更倾向于认为,在那些少数模式化的领域(那些简化的假设可以运用其中)之外的比较政治研究范围内,理性选择理论应用的空间非常小。然而,在我看来,这些极端的立场都不能为理解理性选择分析的未来演进提供有用的基础。 相对而言,我倾向于认为,目前理性选择的这些新文献暗示了一个看似更加合理的、令人满意的解决途径。也就是说,作者们可以将理性选择的假定作为一种针对比较研究的启发式引导,而不是一个高度形式化的模式建构工具。这样一种解决方式可以让研究者把小样本分析的内在优势充分展现出来,同时也可以避免在牺牲概念有效性和限定研究问题域之间进行困难的抉择。这种解决方式在实践中运用的一个例子是,戴维·莱廷关于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民族运动中暴力模式比较的分析。通过将理性选择的假定作为一种生成假设的启发方式进行运用,莱廷发展了一个很少牺牲概念有效性的微观基础的解释。虽然在他的分析中自变量的多数不是直接来自理性选择理论,但是他的观点中最重要的内容来自形式理论,特别是来自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的“隔离模型”。④然而,在使用这一模型时,莱廷明确地将他对模型的关注从属于解释所要面对的结果这一更为重要的任务。这样,他仅仅在关系上将隔离模型与他的具体问题联系起来,而没有浪费时间和精力去介绍这一模型本身的一些特征。许多研究花费大量的笔墨去抽象地解释那些最终会危害概念有效性的模型。相比而言,莱廷关于隔离模型与种族冲突模式相关性的两页纸的简洁讨论是明显不同的。 新概念和新解释的发展 作为小样本分析的一个分支,新的理性选择文献非常适合为比较政治领域中新概念和新解释的发展贡献力量。在上文提及的一些文献中,一些学者通过发展一些适合解释特定案例的新模型来实现这一目标。例如,盖迪斯(Barbara Geddes)、格雷夫、罗森萨尔、温加斯特等人通过为一些案例(这些案例不同于拉美文官制度改革和美国内战前夕的政治危机等)提供新的形式工具,为理性选择传统作出了有价值的概念和理论贡献。然而,有必要认识到,这些模型仅仅是可以被用来产生可检验命题的工具,它们本身不包含任何具体的命题。在这个意义上,普遍模型生成的最直接贡献是,它可以提供某种被其他学者用来提出新假设的新“元理论”(meta-theories),而不是现实地向其他学者提供那些经验上可以检验的假设。 理性选择学者也明确希望贡献一些概念和命题。这些概念和命题将在提供直接可验证的解释方面为新理论的形成提供一种便利。无论使用新的模型还是旧的模型,他们都认识到分析性归纳对于这一过程的重要性。例如,贝茨这样描述假设生成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在解释和案例材料之间来来回回地行动,鉴于我们不断演进的理解,参照数据修正着我们的解释,而这些解释本身可以在新的路径下得到检视”。在前述的几篇文章中,归纳促成了新的、有意义的概念和假设的产生。例如,通过证据与理论的反复配对,戈登将针对解雇的罢工概念化为一种主要目标,以捍卫工会组织的活动。这种概念化将她引入到一个有趣的假设中:当特定的工会活动家被雇主锁定为解职的目标时,针对劳工减员的罢工多半就会发生。 在新概念和新解释生成的过程中,归纳的有效运用要求学者们对证据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如果学者在观察证据时仍恪守某一具体的解释,那归纳就很难有所帮助。例如,在过去,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者和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家不能有效地使用归纳方法去提出更广泛的新观点,这是因为他们过于恪守理论,以至于遮蔽了他们对数据的解释。由于他们不能认识到那些与理性选择传统不太契合的解释有时会给比较政治中的重要问题提供非常有说服力的答案,所以,在一定程度上,理性选择理论家现在可能会面对一个类似于前述马克思主义者所面对的问题。 理性选择理论家目前可能会被分为两类:一类希望透过厚厚的理性选择理论眼罩来观察具体的历史证据,另一类则保持开放的心态,并在相对中立的理论立场上让证据自己言说。有理由相信,在中长期的时间里,后一类学者更可能在比较政治学领域发挥重要的影响。作出这一判断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学者更容易发明一些对广大的学者受众有吸引力的新概念和新解释。相比而言,那些仅仅在理性选择理论的假设框架内观察证据的分析者,则可能会很难打破狭隘理论的限制。 理性选择理论的新方向代表了比较政治学领域中一种令人欣喜的发展趋势。在过去,理性选择分析者在其关于方法论的讨论中经常强调抽象模型和普遍性理论构建的重要性,以及演绎性研究较之归纳性研究的内在优势。相比而言,许多理性选择分析者则开始强调比较方法的一些传统关切,例如对特定案例进行解释,同时依赖归纳和演绎以及使用详细的案例内信息(within-case information)等。 虽然这一新的文献可以被看作是“两个世界的最佳结合”,即形式理论和比较方法的合成,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我认为这两个传统之间还是存在严重的冲突。实际上,一种最不乐观的图景是,新理性选择文献在未能充分利用比较方法优势的同时也破坏了其独特力量。这样,理性选择理论家就会从其早期关于普遍理论化的可能性以及演绎研究的神圣性的观点上后退。 鉴于理性选择理论与比较方法之间的张力,理论家们可能有非常强烈的动机去做出两者择一的选择:或者放弃与比较方法融合的努力,或者完全转向以比较方法为导向的研究。我认为,后者的情形是未来最有可能的结果。理性选择理论家当初之所以转向比较方法,主要是因为这种转向尝试克服吉拉多·蒙克(Gerardo Munck)所称的“纯粹主义路径”的缺陷(例如,这种路径认为理性选择理论能够提供所有研究领域中所有结果的全部解释)。在转向比较方法并试图解决与这种纯粹主义立场相关联的一些问题时,新问题和新张力也会很正常地出现。但是,如果说分析者要回到纯粹主义路径的假设上去并以此作为对新问题的回应的话,那则是不太可能的。因此,更可能的图景是,分析者会沿着比较方法的路径推进研究。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研究工作将会越来越与那些沿用比较传统的研究难以区分。假如发生这种情况,新一代更为实用的理性选择分析者们将会在为比较政治研究提供最大贡献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最佳位置。 *本文原载《国际发展比较研究》2000年夏季号。 注释: ①这本书已经有中译本。[美]罗伯特·贝斯等:《分析性叙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译者注 ②例如,彼得斯认为,一个最具相似性的系统设计能够比其他原因推理的小样本策略更有效地检验假设,这一点缺乏逻辑基础。再如,彼得斯将“平行展示理论”(parallel demonstration of theory)策略的提出归功于蒂莫西·维克汉姆-克罗利(Timothy Wickham-Crowley),实际上这一策略最早是被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和玛格丽特·索莫斯(Margatet Somers)发展出来的。这种性质的其他错误还可以列举一些。同时,在这本著作中也可以发现无数的拼写和语法错误。然而,最基本的缺陷是,彼得斯过于依赖加里·金(Cary King)等人的编著中提出的分析路径。正如蒙克所指出的,当运用到比较研究中去时,这种路径就展示出一些重要的缺陷。 ③虽然从一定程度上说小样本研究者(理性选择或其他)主要通过样本内分析来进行观察,但也可以说他们已经准备好了使用统计分析方法。 ④原文中使用的英文“tipping model”应翻译为“倾斜模型”。这个模型更常见的译法是谢林隔离模型(Schelling Segregation Model),该模型是一种关于隔离现象的动态模型。参见http://www2.econ.iastate.edu/tesfatsi/demos/schelling/schellhp.htm。——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