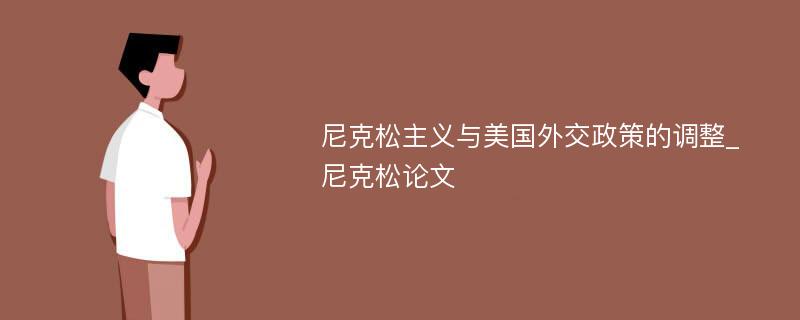
“尼克松主义”及美国对外政策的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尼克松论文,美国论文,主义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9)-04-0046-11
1969年7月23日,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开始了为期13天的环球政治和外交之旅。25日,在关岛(Guam)的军官俱乐部举行了一次非正式记者会,尼克松谈到了美国在“亚太的地位问题”。记者们很快将其谈话内容命名为“尼克松主义”,尼克松看到了这一用语的政治价值,开始公开引用。
过去的研究认为,1969年1月入主白宫的尼克松,有一系列关于外交政策新设想,后来具体化为“尼克松主义”。尼克松主义的主要原则是美国呼吁其盟友运用自身的力量来对抗“共产主义的侵略”,美国将只给他们提供建议、物质及武器援助。大多数学者认为,尼克松主义指导美国在印度支那及其他地区的外交行动,标志着美国对外政策的重大转变,彻底改变前任总统们的干涉主义政策。在印度支那,尼克松通过“越南化”(Vietnamization),试图从印度支那撤军,同时保护南越政府、赢得战争、实现和平、维护美国的“信誉”。①
中国学者有关尼克松主义的研究成果,最主要的是1984年出版的时殷弘的专著。该书引用的英文史料比较丰富,较为全面地论述了尼克松主义的起源、形成、内容、主要政策表现及其历史地位。②该书在中国的美国史研究中,具有一定的开创性。该书出版时,尼克松政府外交档案尚未公开。近年来,中国学者发表的有关尼克松主义的研究论文,在观点和材料方面,并没有多少突破③。
近年来美国学者研究认为,尼克松主义并不构成外交的大战略或一系列指导外交决策的原则和准绳。事实上,在尼克松启用尼克松主义之后,他并没有严格遵照执行,甚至没有打算这样做。所谓尼克松主义也并不标志着美国对外政策的重大转变,前几届政府,也曾应用或试图运用类似尼克松主义的主要原则。在印度支那,“越南化”也不是尼克松政府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尼克松暗中更倾向以武力解决问题。“越南化”并不是尼克松政府的发明,其起源是多方面的——反战运动、国会鸽派、约翰逊(Lyndon Johnson)政府有关官员,以及1968年美国总统竞选时候选人及两党的一个话题。此外,尼克松在上台后很久才实行“越南化”的政策,而且是在总体战略的其他组成部分失灵后,政府相关成员及公众要求他尽快撤军的情况下才开始实施的。④
本文依据尼克松总统档案和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综合考察尼克松主义的历史渊源、形成、演变及实施情况,分析尼克松主义与尼克松政府总体外交的关系。本文的结论是,尼克松主义以及美国对共产党大国苏联和中国关系的缓和,构成尼克松和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外交的两个最主要组成部分。即使在尼克松的言辞和行动相互矛盾的时候,媒体仍将尼克松的新亚洲政策称为尼克松主义。⑤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也是这样做的,这大概是群体思维及语言表达便利所致。尽管尼克松主义并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主义,但所有人都称尼克松的新亚洲政策为尼克松主义。此外,用尼克松主义这一表达方法比试图描绘、解释和总结尼克松在关岛的演说,或描绘和解释其深层含义要容易。与其他所有用总统名字命名的“主义”类似,重复使得抽象的概念获得生命,却与实际情况相悖。⑥
一、美国的外交困境及尼克松政府的政策措施
1969年上台的尼克松政府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结束越南战争。1968年2月南越爱国武装力量发动的春节攻势,表明总统约翰逊有关敌人将很快被打垮、战争即将结束的许诺是不现实的。尽管在越南美军已超过50万人,侵越美军总司令威斯特摩兰(William Westmoreland)要求政府再增派20万美军,这对约翰逊政府来说是无法接受的。3月31日,迫于各方压力,约翰逊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宣布美国部分停止对越南北方的轰炸,并谋求进行和谈,同时声明他本人不再参加1968年的总统大选。越战给1969年初上台的新一届美国政府留下了很多棘手的问题。⑦
除越南问题外,尼克松政府还面临着许多其他挑战与不稳定因素。第一,美国与苏联的关系处于十字路口,尽管在很多方面苏联的力量远不如美国,但苏联在核武器方面已与美国达到基本平衡。从1968年8月苏联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来,克里姆林宫显得信心十足。美国和西欧盟国对华沙条约国军队入侵布拉格的温和反应,表明苏联在中东欧的影响力是稳固的。美国不得不接受苏联及其盟国在东欧使用武力保护社会主义的现实。1967年中东六日战争以后,苏联继续支持一些阿拉伯国家。埃及和叙利亚试图对以色列进行报复性打击。可以说,苏联已经将其势力延伸到中东欧之外。⑧
第二,中国也令美国十分头痛。约翰逊政府非常关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⑨。一方面,美国很担心“十亿手持原子弹的中国人”的威胁;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大大减少了中国直接出兵越南作战的可能性⑩。尽管1969年初的中苏关系十分紧张,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希望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中国支持北越,并谴责美国对南越的援助。
第三,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与欧日盟国的关系也是矛盾重重。欧洲盟国对美国在越南持久的战争很不满意。在尼克松就任总统后的第一次欧洲之行期间,法国总统戴高乐对此有明确表态。1966年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NATO's Integrated Military Structure)(但仍是北约正式会员国)后,法国的影响已大大削弱;联邦德国政府的新东方政策(Ostpolitik)更使美国担忧。1969年9月上台的联邦德国总理布兰特(Willy Brandt)极力谋求与苏联集团改善关系。这使得北约联合一致对苏的政策几乎成为不可能。除了政治问题外,欧洲一体化和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使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国际经济的统治地位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此外,动荡不安的世界局势令美国人担忧。1967年的中东战争之后,阿以矛盾并没有解决。非洲的非殖民化带来的是内战,苏联和中国的影响渗透到非洲。在拉丁美洲,60年代的进步同盟(the Alliance for Progress)并没有为美国培植可靠的盟友,反而使反美思潮上升。在南亚,1965年的印巴战争加剧了印巴之间的历史仇恨和对抗。(11)
尼克松政府面对的是一个极端动荡的世界,尼克松上任伊始,美国外交政策内外交困。尽管面临着重重困难,美国的军事力量仍是世界第一,经济实力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并具有充分的人力优势。美国面临的真正问题是:美国如何解放自己并重建美国作为世界领袖的信誉?尼克松政府如何以国内外敌友都能接受和尊敬的方式达到这一目标呢?这意味着尼克松政府要根据世界局势的变化,寻求一个新的全球力量平衡,而不损害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绝对优势。尼克松政府需要重新确立美国外交的基本原则,使美国从最危险的海外军事冲突中脱身,恢复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当务之急是要从越南撤出,找到与过去的冷战对手——苏联和中国打交道的新办法。
1969年,尼克松已经认识到一个多极世界格局的出现,主要标志是美国接受与苏联的核均势及将欧洲、日本和中国作为有竞争力的力量中心。这是美国自冷战以来力量相对下降的重要表现。尼克松在其就职演说中宣称:“经过一段对抗之后,我们现在进入了谈判时期。”尼克松政府需要重新调整美国的对外政策。尼克松决定放弃过时的两极对抗体系,重建大国间的“均势”,很快提出建立以“美、苏、西欧、日本和中国”为中心的“国际新秩序”。尼克松希望将美国与共产主义世界对抗和战争边缘政策转变为与共产主义世界的和平共处。对苏缓和与打开同中国的关系是这一政策实施的结果。(12)在一定意义上,尼克松主义是“越南化”政策的延伸,与尼克松政府结束越战政策是相互关联的,成为尼克松政府最初两年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1969年夏天,尼克松政府已采取了一系列外交措施:基辛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与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Anatoly Dobrynin)之间的秘密渠道、对柬埔寨轰炸以迫使北越就范以及尼克松主义的出台。
尼克松主义的出台与尼克松政府安全战略思想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执行的是所谓“两个半战争”战略,即美国要在欧洲和亚洲对付苏联和中国两个共产党国家同时发起的大规模进攻,并应付其他地区,如中东出现的紧张局势。其实美国从来也没有这样的力量,来进行“两个半战争”。到了60年代末,随着中苏两国的彻底决裂,中苏两国同时发动进攻的可能性已基本不存在,尼克松在1969年批准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的“一个半战争”战略。“一个半战争”战略的主要出发点是削减兵员和军费,以减轻财政负担,缓和要求更大规模削减军事力量的国内压力。(13)
二、尼克松主义出台的背景
关于尼克松主义的起源,应从越南战争的历史、尼克松对越南战略的演变以及“越南化”的根源追溯。1969年3月13日,也就是在关岛记者会四个月之前,美国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Melvin R.Laird)建议起草一份应急计划,在1969年底之前分阶段从越南撤出约7万美国军事人员,并在之后的日子里撤出更多的人员。尼克松在4月10日才批准这一计划。此时,莱尔德又建议使用“越南化”而不是“非美国化”。因此,“越南化”实际包括两个不同的、然而是相互联系的过程:美国撤军——而为了支持撤军,加速培训、武装和扩展南越军队。6月8日,尼克松在中途岛会晤南越领导人阮文绍,通知他美国将在7月1日至8月31日撤出2.5万人。(14)
当时,尼克松政府内部就撤军的速度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国防部长莱尔德和国务卿罗杰斯(William P.Rogers)希望加快撤军,基辛格不赞成这种观点。尽管基辛格知道“越南化”是他主持制定的白宫战略的基本环节,但他相信,这一战略的其他环节更有可能迫使对方按照尼克松和他本人的条件妥协。(15)
尼克松和基辛格有关越战问题的其他战略包括对苏缓和及三角外交,与越共谈判,扩大地面、空中和反叛乱行动,应用所谓的“疯人理论”,即利用“过度军事力量的威胁”。尼克松和基辛格对越战略任何一部分的重视是不确定的,因为他们要考虑的不仅仅是莱尔德、罗杰斯以及其他政府官员的意见,更要考虑到战争的实际状况、国际关系现状、国内政治和经济因素,包括公众舆论、反战运动、国会及国内预算等问题。(16)
此外,尼克松和基辛格对对越战略的组成部分也各有侧重。尼克松对威胁和武力的重视胜于谈判,基辛格代表尼克松主持谈判,同时也是尼克松重视武力及依赖“疯人理论”威慑的可靠支持者。在河内看来,尼克松和基辛格提供的是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刺激。从积极方面来说,是开始了秘密谈判。从消极方面来看,包括对柬埔寨、老挝及南越轰炸的大规模升级;在整个印度支那扩大军事及反叛乱行动;威胁要摧毁北越,除非北越采纳尼克松政府可以接受的停火协议。对于尼克松、基辛格和他们的幕僚们来说,“越南化”同样也有积极和消极的两方面。这包括要南越相信,“越南化”将强化南越的军队,而南越军队的加强将迫使北越在谈判桌上作出让步。尽管美国政府向莫斯科示好以缓和双边关系,然而尼克松和基辛格同时挥舞军事和外交大棒,他们认为军事威慑将使苏联人担忧。同时,他们将与苏联人签订贸易和军控协定同苏联人在越南问题上是否合作联系起来。1969年底,尼克松和基辛格开始打“中国牌”以压制苏联,希望苏联人在越南停火问题上迫使河内让步。(17)
传统的观点认为,尼克松和基辛格在1969年上台后就制定了从南越“荣誉”撤军的单一计划。而实际上,他们的目的是赢得战争,寻找一个谈判解决问题的办法,以便使阮文绍能继续维持在南越的统治。这就是他们所说的“荣誉”。因此,尼克松政府的越南政策与前任政府没有多大差别:即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及信誉。只是他们自认为具有比前任更好的技巧和策略来实现这一目的。在尼克松任期的第一年,尼克松和基辛格希望他们的战略会迫使对方答应他们的条件。“越南化”——尼克松主义的越南政策,是为了达到在美国国内赢得时间的政治目的,以实现他们战略的其他部分。(18)
在基辛格与莱尔德、罗杰斯就撤军的进度问题发生争论时,尼克松站在基辛格一边。尼克松觉得有必要安抚他的国防部长和国务卿,同时满足国会和公众的愿望,因为在1968年的总统竞选时,他曾经许诺从越南撤出美国军队,结束越战。在1969年7月7日的一次最高决策的讨论会议上,尼克松采取中间路线,表示支持继续撤军,但迟迟不确定撤军的人数(9月,他批准在12月15日前撤出4万人;12月15日,他批准在1970年4月前撤出5万人)。(19)
1969年7月初,尼克松和基辛格感到他们正处于越战战略的十字路口。他们的对越政策未见成效。尽管美国人采取地面攻势、强化轰炸及外交策略,然而北越及苏联人并不合作。在国内,尼克松受到来自国会鸽派、前约翰逊政府官员、反战积极分子甚至主流媒体的攻击,批评他在南越发动的地面攻势、撤军速度太慢、对阮文绍的支持以及明显缺乏领导能力。反对派根据他们了解到的正在越南发生的事情以及尼克松政府言论,得出的结论是尼克松给“南越的敌人施加了最大的军事压力”。(20)此外,右翼鹰派对他不能削减政府开支和所谓的“对北越软弱”(主要指的是“越南化”政策和他同共产党国家谈判的言论)表示不满(21)。
7月,在赴亚洲和罗马尼亚访问之前,尼克松很关注美国在亚洲的盟国和仆从对“越南化”的不安。菲律宾、韩国、台湾及泰国的右派政府及军事独裁者们与美国有安全条约,美国在这些国家和地区驻军。“越南化”意味着美国不仅要从南越脱身,而且也将从亚洲脱身。因此,尼克松此行还要向这些地区重申美国对他们的支持政策。(22)
越南战场上的僵持局面一直困扰着尼克松。在1971年与基辛格的一次谈话中,尼克松回忆他在1969年7月初考虑如何打破僵局,“要么保持现状,要么想办法突破”。这里他指的是“要么军事升级以求得对美国有利的谈判解决;要么军事升级以求得加快撤军并保护美国撤退”。不管做何种选择,“我们都要轰炸这些坏蛋”。(23)尼克松决定将继续撤军与军事升级结合起来。尼克松和顾问们策划在11月1日对北越的河内及海防一带进行为时近6个月的突然大规模轰炸,取名“钓鸭行动”(Duck Hook)。
尼克松由此启动战争升级的第一步:以最后通牒的方式直接向北越施压。尼克松将这一切巧妙地隐藏在美国公众及世界人民的视野之外,通过第三者传话,胁迫河内在“钓鸭行动”之前,采取合作态度。第三者之一是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8月3日,尼克松告诉齐奥塞斯库,他将重新开启对北越的轰炸,除非谈判取得“进展”。尼克松希望齐奥塞斯库将他的话传到莫斯科、北京及河内,同时他援引联动外交策略,告诉齐奥塞斯库:“没有什么比在公正的基础上结束这场战争对我更重要了。我们谈到很多美国与罗马尼亚的贸易关系,战争的结束将有利于美国与中国以及美国与苏联的关系”。(24)
三、“尼克松主义”的形成
1969年7月25日,在关岛的军官俱乐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尼克松谈到了美国在“亚太的地位问题”。他感到需要赢得一些时间使他的战略得以实施。他认为,可以通过战争升级达到迫使对方让步的目的,从而将“约翰逊的战争”转变为“尼克松的战争”,并检试国内对他的政策支持的底线。(25)尼克松知道,这是在走政治钢丝,他必须向盟国和仆从包括阮文绍表示美国政府的承诺,同时又要作出撤军的姿态。此外,他要向大多数美国人以及美国的盟国,特别是日本和欧洲表明,美军不仅要撤出越南,而且要以此为鉴,避免大规模陷入亚洲泥沼,特别是对美国利益并不十分重要的地区。
记者会一开始,尼克松说:在回答记者们的提问之前,先谈一谈美国在“亚洲和太平洋”的地位问题,因为亚洲国家的领导人急切希望知道“因越南战争的挫折,”是否会导致美国“从太平洋撤退并在将来发挥很小的作用”。尼克松说:“因为战争将要结束,这是个需要作的决定。”但是,不管如何,本届政府需要“长远观念”,提前制订计划。尼克松反对英国、法国以及荷兰从太平洋撤退的做法,认为“避免再次卷入亚洲战争的最好办法是美国在亚洲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尼克松强调:“看看今日的亚洲,世界和平”正受到来自中国、北韩和北越的威胁。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今后的4年至20年内,“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在太平洋地区”。尼克松同时指出:“我们不要忽视,这里同时存在着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日本、台湾、韩国、泰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已经取得经济成就。“我们需要制定政策,以表明我们发挥了作用,而且是符合情况、得体的作用。”这包括“民族荣誉”及“地区信誉。”亚洲人“不需要外人摆布”。尼克松最后总结美国在亚洲的地位时说:“太平洋地区的非共产党国家正在实施的政治经济方略是非常有希望的。我们将帮助他们实施。我们将信守条约的承诺。就我们在亚洲的地位而言,我们要极力避免亚洲国家过分依赖我们,将我们拖入像越战这样的冲突。当然这样做起来并不容易,但我相信,只要适当规划,我们是能做到的。”(26)
接着便是记者提问。第一个问题是:总统将如何对一个与美国有密切军事关系的亚洲国家领导人保证,美国将在“与亚洲安全的安排方面,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尼克松回答说:大多数安全条约及相关安排主要是为了保证菲律宾、韩国、印度尼西亚及泰国等的“内部安全,”主要是为了对付来自这些国家的反对派及叛乱者的“内部威胁”。尼克松指出:“当我们谈论亚洲共同安全时,我们关心的是对任何一个亚洲国家的内部威胁,这里指的不是来自一个核国家的威胁。我认为这是自由和独立的亚洲所追求的目标,美国应给予支持。”当有记者问到如何避免另一次越南战争时,尼克松回答说:美国“将避免悄悄卷入,因为这将把自己淹没。我并不是批评我们是如何卷入越战的,但我知道我们可以从过去的经验中学习到有益的东西。我们一定要避免今后进一步卷入这样的战争”。(27)
如果尼克松就此结束记者会,记者和学者们也许不会认为尼克松所说的避免军队大规模卷入未来重大危机是一次重大外交变革。但尼克松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我回想起1964年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Ayub Khan)的建议。他说:‘在那些有内乱的国家,美国的作用是帮助这些国家赢得战争,而不是代替他们打赢这场战争。’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政策。我们希望这将成为我们在处理世界事务中的普遍性政策。”(28)
尽管尼克松关岛谈话当时未全文发表,但第二天的《纽约时报》报道了谈话概要,引起国内外广泛重视。媒体很快将尼克松关岛谈话称为“关岛主义”(Guam Doctrine),这一词至少用到1970年9月。以后,媒体评论员和记者们称之为“尼克松主义”。(29)
结束亚洲和罗马尼亚之行回到华盛顿之后,1969年8月4日,尼克松在与国会领袖谈话时,阐述了他的亚洲新政策。尼克松强调:“美国的政策正处在过渡时期,我们应当认识到,对亚洲不同国家,应当采取不同政策;美国应当从过去的单一化政策改变为不同国家不同政策。”尼克松最后指出:“所谓新方法,就是从物质上,而不是人力上给他们以帮助。”(30)
1969年8月29日,基辛格在给尼克松的一份报告中,对尼克松主义作了如下表述:美国将继续承诺保护相关国家对抗外来军事大国的侵略,但不会派军队去为这些国家对付内部颠覆而战。美国将主要以提供适当的军事和经济支持,以帮助这些受到威胁的国家自救。(31)
在一定意义上,基辛格的表达比尼克松的更清楚,但与美国长期以来奉行的政策并没有多大差异。尽管在尼克松主义指导下,美国在支持相关国家对付内部颠覆时将发挥有限的作用。然而,如果一场对付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战争对美国的全球利益至关重要,或政策制定者们将内部威胁与外部大国的阴谋联系在一起,那么大规模陆、海、空军队的卷入还是可能的。同时还需要个案分析,很难有统一的对策——也就是说,越战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即使不是完全一样的情形和方式。(32)
1969年9月,尼克松更加重视尼克松主义的公关价值,他要求基辛格帮他设定一些“外交政策目标——特别是除越南问题之外可能取得进展的方面”。尼克松提到拉美、尼日利亚,外援以及“尼克松的亚洲政策的实施”方面。尼克松建议基辛格,“你不如教你手下一个精明能干的人考虑考虑,搞出几条我们可以实现的目标计划”。(33)尼克松在这里使用的是“尼克松亚洲主义”,在关岛讲话时及以后的一些其他场合,尼克松和他的助手们却会说“尼克松主义”适用于全世界。
基辛格将此任务交给了温斯顿·洛德(Winston Lord)。洛德于1970年1月23日提交了一份报告。在这份报告中,洛德指出,尼克松主义既不是亚洲政策的“大战略”,也不是“总计划”。尼克松主义的政策“与过去政策的表述没有很大差别”,然而,它确实有“操作层面的价值”,因为它为已经实施的但还没有总结为持续模式的行动增添了“血肉”。洛德认为,尼克松主义在以下方面已经开始实施:越南(越南化)以及希望美国在越战之后多承担防务的盟国、对日政策(亚洲地区盟国多作贡献)、泰国和菲律宾(美国撤军或强化美军基地,但弱化美国影响)、中国(放松对华贸易及旅行的限制、重新启动华沙大使级会谈以及在中苏冲突中保持中立)。他同时指出,如果尼克松主义要成为指导原则,对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需要个案处理,并根据不同国家区别对待。(34)
在洛德提供研究报告之前,尼克松就在公开声明中使用尼克松主义。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在1969年11月3日对全国的电视讲话中,他将尼克松主义概括为“美国外交的新方向”,将“越南化”说成是尼克松主义的越南版本(35)。这次讲话标志着越战进程的转折。当时,尼克松已决定放弃“钓鸭行动”,(36)他批评反战人士,呼吁“沉默的大多数”支持政府的越战政策。尼克松知道,在美国公众的心目中,越战将成为尼克松的战争。在继续从越南撤军的同时,他准备了新的计划,以便对敌人施压。“越南化”被赋予了新的意义。私下里,尼克松更看重军事行动,这可以从他1970年4月27日与基辛格的一次谈话得到印证,这次谈话正好是在入侵柬埔寨之前。尼克松说:“过去一年,我们受到赞扬的大多是我们不太想做的事:将冲绳(Okinawa)归还日本、限制战略武器谈判(SALT)、化学武器谈判以及尼克松主义。”现在我们终于能做我们想做的事情了。(37)在缓慢撤军的同时,尼克松一而再、再而三地采取军事行动:1970年入侵柬埔寨、1971年入侵老挝以及1972年两次大规模轰炸北越。
在担任总统的前四年,尼克松每年向国会提交一份题为《1970年代美国外交》的报告,全面阐述已经取得的成就和未来目标。 “和平”是这些报告的主题。尽管这些报告充满舆论宣传功效,但也包含对新政策的阐述和对即将出台政策的暗示。(38)例如,《1970年对外政策报告》讨论了尼克松主义,提出了以“伙伴关系、实力和谈判”为三大支柱的“新和平战略”。报告宣称,“伙伴关系”即是尼克松主义,“实力”和“谈判”是美国对付“共产党对手”的政策中不可分割的两方面。他在1971年对外政策报告中进一步阐明:“伙伴关系”是美国新的对外政策的核心,而“实力”和“谈判”是其“必要的附属物”。(39)他说:尼克松主义的“中心论点是美国将参与盟友的防务和发展,但它不能也不会制定全部方案,拟定全部计划,执行全部决定,承担世界自由国家的全部防务”。在以后的一些政策声明中,尼克松交替使用“新战略”和尼克松主义,把它们都当做整个对外政策的指导原则之一,或者把贯彻“实力”和“谈判”原则的一些具体措施也当做尼克松主义的表现。尼克松主义已成为尼克松政府时期最初两年美国对外政策的代名词。可以认为,尼克松主义狭义地说是关岛主义及其延伸,广义地说是“伙伴关系、实力和谈判”。(40)狭义的尼克松主义旨在调整美国的海外义务,它主要涉及美国力量的收缩。(41)广义的尼克松主义可指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总体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美国依赖并支持地区性反苏反共强国充当美国的代理人,以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最典型的例证是美国扶持伊朗国王巴列维充当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的代理人。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广义的尼克松主义,多由后人总结和发挥逐渐形成。
四、尼克松主义的实施情况
尼克松政府在地区安全政策方面(特别是尼克松主义和有关地区自给自足的言论)被广泛认为是美国真正接受新生的多极,也就是所谓的“新多边主义”的观点。尼克松政府希望,美国的收缩和撤退不会使共产党大国得手。尼克松政府通过联结机制贯彻同大国缓和与尼克松主义的政策被认为是解决撤军和保持承诺之间矛盾的方法。地区性努力也表明,尼克松主义不只是作为与大国妥协的附属物而设计的,它也是作为地区性安全网,在出现地区性危机时,保护美国利益。(42)
尼克松和基辛格把缓和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看成是他们在亚洲实行的政治军事收缩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缓和政策与尼克松主义双重政策以实现美苏之间在全球范围的妥协,这也是美国希望缓和与中国的关系所要达到的目的。(43)同中国改善关系,被认为是有利于维护稳定的地区环境,以便于美国稳步地从亚洲撤出军队。在东亚,根据尼克松主义,美国撤出后担当重任的理应是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很快崛起成为经济大国,然而,基于可能出现的国内和地区性敌意反应,日本避免在亚洲地区发挥重要作用。1969年美国将冲绳归还日本,显示日本将有可能在亚洲地区发挥重要作用。但是,这一希望因美国对日本政治和经济的多次冲击而破灭。第一次,美国在没有事先与日本打招呼的情况下,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并宣布尼克松即将访华;在经济政策方面,尼克松于同年8月宣布对从日本进口的商品增加10%的附加税;10月宣布美日纺织品问题以有利于美国的条件解决;12月,美国强迫日元升值,使日本对美国作为可以依赖的盟友的信心大打折扣。同时,1973年至1974年的能源危机,更显示日本经济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脆弱性。这几件事,有力地阻止了日本采取更为积极的外交政策。(44)
尽管尼克松主义强调发展地区性的中等大国,但尼克松政府很不情愿将区域性安全责任转让给盟友中两个最有力量、最有可能承担这种责任的中心:日本和欧洲。对欧洲问题,在华盛顿看来,尼克松主义所指的“责任分担”等同于在大西洋联盟国家之间的经济负担的均分政策(economic "burden-sharing"),例如要求支付美国在联邦德国驻军的费用等。尼克松政府试图将安全和经济利益挂钩,却反对欧洲国家独立的外交主动性(如联邦德国的新东方政策),同时也抵制国内要求削减驻欧洲美军的呼声(体现在曼斯菲尔德修正案中[the Mansfield amendment])。一般认为,所谓美国转让防务责任给欧洲,实际是给联邦德国。在缺乏欧洲共同防务努力的情况下,欧洲大陆有可能会处于苏联军事强势的控制之下。美国不少分析家警告,西欧可能出现的芬兰化(Finlandization)的趋势。(45)
美国从印度支那撤军的政策,使东北亚国家对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地位和利益问题产生不安。韩国成为美国对亚洲大陆遏制政策的最后一个堡垒。自朝鲜战争以来,美国在韩国驻军成为美国对韩国防务承诺的象征。在很大程度上,其象征性意义比实际驻军更为重要,因为这是美国维护朝鲜半岛现状的最有效的例证。美国在韩国驻军对维护东北亚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尽管美国在韩国的驻军规模很小(根据1970年统计为67,000人),美国的军事承诺对韩国和日本十分重要。由于韩美防务条约并没有规定美国在南韩驻军的时间,韩国政府担心美国对亚洲地面战事的厌倦和失望会成为美国继续在韩国驻军的心理障碍。(46)
尼克松政府于1970年3月20日发布国家安全决策备忘录(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Memorandum),预计将于1971年中旬,撤出驻扎在韩国的两个美国步兵师中的一个师。3月底,韩国人被告知,撤军对实施尼克松主义十分必要,是贯彻“一个半战争”战略的美国新遏制政策的不可缺少的部分。为了保证从越南撤军不显得太引人注意,美国要向所有盟国推行尼克松主义。因此,削减2万驻韩国美军的时间定在1971年中旬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强化尼克松主义的信誉,因为韩国是越南之外实施尼克松主义最合适的地方。(47)尽管韩国政府极力反对,但无济于事。(48)
尼克松主义最初是尼克松政府为解决越战问题和减少美国对亚洲盟国所承担的义务而提出的,其应用也推广至中东及拉美地区。尼克松政府认为,美国与相关地区强国的长期利益一致性将维持美国与这些国家的长期盟友关系。这种认识,却没有很好区分某地区之内和地区之间对安全的概念是不同的。这在分析层面上出了问题:首先,在某地区内,往往对威胁并没有统一的认识和概念;其次,所谓安全,地区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差异。(49)
在处理与巴西的关系方面,出现了拉美地区内相互冲突的安全利益。华盛顿认为巴西是美国处理拉美地区安全的关键,这一点在1971年12月巴西独裁者麦德奇(E.C.Medici)总统访问华盛顿时有充分体现。在白宫举行的宴会上,尼克松称赞巴西奇迹和麦德奇的贡献,尼克松声称,华盛顿将根据巴西来调整对拉美的政策。(50)尽管巴西是一个地区性具有绝对强势的国家,并对美国投资者采取优惠的政策,看上去很能满足尼克松主义的条件,但尼克松主义以地缘政治的词汇概括安全问题,错误估计了美国对麦德奇政权的政策倾斜对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影响。在美收缩政策外衣下的干涉主义行为,尽管有“责任分担”的借口,却被该地区很多国家看做是巴西希望以牺牲邻国利益为代价而进行的扩张。一直致力于联合本地区讲西班牙语小国对抗美国和巴西霸权的阿根廷,对尼克松政府对巴西的优惠政策,十分不满。尼克松主义是建立在假设地区利益具有共同性的基础上,足以将本地区不同国家与美国利益联系在一起,并将它们相互联系在一起。尼克松主义在拉美应用的案例中,尼克松政府错误地估计了美国与巴西利益的一致性(例如尼克松政府对巴西单方面宣布200海里海洋权极为不满,公开争论),同时巴西的邻国对美国与巴西的特殊关系也表示强烈不满。(51)
从很多方面来看,1969年以后美国与伊朗的关系被尼克松政府看做是实行尼克松主义的范例。从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就开始参与对伊朗的各种军事发展项目。然而,伊朗国王巴列维对伊朗安全需求的认识与美国的存在很大差异。1953年美国帮助伊朗国王恢复王位之后,伊朗领导人对美国的心理依赖明显增强。同时,伊朗对美国在物质和财务上也有依赖,这一状况持续到1967年。在尼克松主义出台前的两周,基辛格令国家安全委员会相关人员研究波斯湾地区的情况,并形成了国家安全研究66号备忘录(National Security Study Memorandum66)。该报告提出,由美国经济和军事支持的伊朗可以填补英国人留下的空缺。从尼克松主义的角度考虑,至少从表面看来,伊朗是一个理想的、其领导人在心理上有准备、在物质上有能力担当起在本地区安全体系中绝对优势地位的国家。(52)
尽管伊朗强调与西方利益的一致性,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伊朗巨额的石油收入,使其从依赖美国援助到可以用信誉支付,在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中,有了更多可以周旋的余地。随着尼克松主义的出台,美国对伊朗的军售不再实施控制。在1972年5月30日至31日举行的伊朗国王和尼克松会谈中,尼克松和基辛格接受了对伊朗军售不受任何限制的概念。尼克松政府以尼克松主义及其所倡导的军事援助哲学为依据,不顾五角大楼的反对,坚持对伊朗出售F-14和F-15轻型战斗机。(53)不到一年,伊朗国王在接受采访时证实,“我们得到一切美国拥有的非原子武器”(54)。从尼克松主义的角度来看,与伊朗发展特别军售关系是与逐渐形成的对波斯湾地区“双支柱”策略(55)一致的政治信号。
在评估1969年至1976年的美伊安全关系时,记录是明确的。在遏制伊拉克、与沙特阿拉伯建立工作关系以及镇压南也门支持的在阿曼境内的佐法尔叛乱(Dhofar rebellion)等三方面,伊朗国王在波斯湾地区确实起到了提升地区安全的作用。从1968年1月英国宣布撤退起,美伊安全利益开始融合。然而,美伊在油价问题上的利益是相互冲突的。1972年5月的对伊朗无限制军售政策并没有开创美伊相互依赖关系,而是美伊相互依赖关系的结果。(从伊朗国内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一美伊安全利益融合的观点完善了始于1953年的美伊合作进程。)由此,美国在伊朗的利益与伊朗国王的命运紧紧相连。(56)作为这一微妙的过程,尼克松主义与美国其他冷战政策一样,孕育了这样一种美国外交决策的环境,即一个“国家”的安全(这里指的是伊朗)与这个国家的某一个政府(指伊朗巴列维政权)的命运紧密相关联。因此,1979年,伊朗巴列维政权垮台成了自1975年南越政府垮台以来美国遭遇的最大的外交挫折。不少论者指出,1979年的伊朗革命标志着以强调依赖具有绝对优势的地区性大国作用的尼克松主义的结束。
五、结语
1969年到1974年,在尼克松担任美国总统期间,有一系列关于改变美国外交政策的思想和措施,最主要是减少美国在亚洲承担的义务。然而,尼克松主义并非形成于1969年7月的关岛记者会上,当时尼克松并没有提出美国外交战略调整的策略。所谓尼克松主义是在尼克松第一任期内逐渐形成的,并由相关官员、记者和学者们总结深化而成的。其实,尼克松在1969年关岛记者会后,也并没有严格执行所谓的尼克松主义。在尼克松主义的实施问题上,也必须区别对待,如从1969年到1971年,美国确实减少了在越南、泰国、菲律宾、日本、韩国的驻军,但尼克松政府在印度支那多次使用军事升级的手段,支持老挝及柬埔寨政权。(57)
在尼克松任内,尼克松主义是一把政治双刃剑。从肯定方面来看,媒体和公众认为美国在海外的军事行为已经逐步收缩,许多人轻信尼克松的花言巧语,认为他不会再使美国卷入类似越南战争的冲突中。尼克松主义与“越南化”、三角外交、打开与中国的关系及和平的结构等时髦的词语相联系,不仅使尼克松在任内,而且在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后,依然提升了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外交地位。
从消极方面来看,批评者利用尼克松主义反对尼克松,特别是当他对柬埔寨轰炸升级,对老挝轰炸,在1971年的印巴战争期间派巡洋舰到印度洋。在中东地区,尼克松确实遵循尼克松主义,美国加强对伊朗国王巴列维的支持以对付内外威胁。然而,美国这一外交政策到卡特政府时期最终以灾难性结局收场。在拉美,尼克松政府对巴西的政策倾斜,引起阿根廷等国对巴西的强烈不满,形成对美国的抗衡。在智利,美国也试图实施尼克松主义,但尼克松政府却积极支持右翼分子及军人密谋反对阿连德政府(Salvador Allende)、从事绑架、暗杀、军事政变和侵犯人权等非法勾当。(58)尼克松和基辛格通过切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智利的援助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策划,支持1973年9月政变,推翻合法的阿连德政府,随后上台的是专制独裁实施暴政的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政权。
注释:
①早期研究尼克松主义的论著有:Melvin Laird,et al.,The Nixon Doctrine (Washington D.C.: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1972); Virginia Brodine and Mark Selden,eds.,Open Secret:The Kissinger-Nixon Doctrine in Asia (New York,Harper & Row,1972); Katsumi Kobayashi,The Nixon Doctrine and US-Japanese Security Relations (California Seminar on Arms Control and Foreign Policy,Discussion Paper,No.65,October 1975); Robert S.Litwak,Détente and the Nixon Doctrine: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ursuit of Stability,1969-1976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 Joo-Hong Nam,America's Commitment to South Korea:the First Decade of the Nixon Doctrine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Earl C.Ravenal,Large-Scale Foreign Policy Change:The Nixon Doctrine as History and Portent ( Policy Paper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no.35.Berkeley: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89); Robert Osgood,"Introduction:The Nixon Doctrine and Strategy," in Osgood,et al,Retreat from Empire? The First Nixon Doctrine(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 ,pp.1~27; Earl C.Ravenal,"The Nixon Doctrine and Our Asian Commitments," Foreign Affairs,January 1971,pp.201~217; Richard Butwell,"The Nixon Doctrine in Southeast Asia," Current History,December 1971,pp.321~326.美国近年来出版的有关尼克松时期美国外交研究的专著,对尼克松主义也有讨论,参见William Bundy,A Tangled Web:The Making of Foreign Policy in the Nixon Presidency (New York:Hill and Wang,1998),pp.67~68; Robert Dallek,Nixon and Kissinger:Partners in Power (Harper Collins,2007 ),pp.143~144.
②时殷弘:《尼克松主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4年。
③主要中文论文有刘清:《浅析尼克松主义出台之因素》,《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5期;刘琳:《尼克松主义——美国对外政策的分水岭》,《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吕桂霞:《论尼克松主义与越南战争的终结》,《学海》,2005年第5期;孙俊华:《尼克松主义对日韩安全合作关系的影响》,《日本学论坛》2006年第4期。另参见何慧《尼克松与中国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3~114页。
④Jeffrey Kimball,"The Nixon Doctrine:A Saga of Misunderstanding," 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36, no.1(March 2006 ),pp.59~74.
⑤See,e.g.,Henry Kissinger,White House Years (Boston:Little,Brown,1979),p.224; New York Times,26,31 July and 3 August 1969,29 June and 2 July 1970; Chicago Sun-Time,17 September 1970.
⑥Kimball,"The Nixon Doctrine," p.64.
⑦Jussi M.Hanhimaki,The Flawed Architect:Henry Kissinger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28.
⑧Jussi M.Hanhimaki,The Flawed Architect:Henry Kissinger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pp.28~29.
⑨关于约翰逊政府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反应,参见Michael Lumbers,"Staying out of this Chinese Muddle":The Johnson Administration' s Response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Diplomatic History,Vol.31,No.2,April 2007,pp.259~294.
⑩Yafeng Xia,Negotiating with the Enemy:U.S.-China Talks during the Cold War,1949-1972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6),p.121.
(11)Hanhimaki,The Flawed Architect,p.29.
(12)Melvin Small,The Presidency of Richard Nixon (Lawrence,Kansas: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9),pp.61,97;张曙光:《美国对华战略考虑与决策,1949-1972》,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26~330页。
(13)Nam,America' s Commitment to South Korea,pp.74~75;时殷弘:《尼克松主义》,第43~43页。
(14)Kimball,"The Nixon Doctrine," p.65.
(15)Jeffrey Kimball,Nixon's Vietnam War (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8) ,pp.137~139; Jeffrey Kimball,The Vietnam War Files:Uncovering the Secret History of Nixon-Era Strategy (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2004),pp.87~89; Thomas C.Thayer,War without Fronts: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Vietnam(Boulder,CO:Westview Press,1985),Table 4.6.
(16)Kimball,"The Nixon Doctrine",p.66.
(17)有关美国的越南政策以及巴黎谈判,参见Kimball,Nixon' s Vietnam War; The Vietnam War Files;关于越南化问题,参见Vietnam Policy Alternatives,July 1969,in Memrondum,Halperin and Lord to Kissinger,5 August 1969,folder: Misc.Materials--Selected Lord Memos,Director's Files (Winston Lord),1969-1977,Policy Planning Council (S/PC),Policy Planning Staff (S/P),GRDOS,RG59,National Archives,US (之后引为NA).关于中国牌,参见Bundy,A Tangled Web,p.104.
(18)Kimball,"The Nixon Doctrine",p.67.
(19)参见Memorandum,Kissinger to Nixon,7 July 1969,subject:Sequoia NSC Meeting on Vietnam,folder:Vietnam Papers,box 338,Director's Files (Winston Lord) ,1969-1977,S/PC,S/P,GRDOS,RG 59,NA.
(20)关于最大军事压力的印象,参见记者提问,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Richard Nixon :Richard M.Nixon,1969 (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1 ),p.556; Tom Wicker,"Mr.Nixon Looks at Asia," New York Times,6 July 1969.
(21)Entry for 7 July 1969,Journals and Diaries of Harry Robbins Haldeman (JDHRH),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s Project (NPMP),NA.
(22)Kimball,"The Nixon Doctrine," p.68.
(23)Oval Office Conversation no.527,Nixon, Haldeman,Kissinger,and Ehrlichman,9:14 a.m.-10:12 a.m.,23 June 1971,White House Tapes,NPMP,cited in Kimball,"The Nixon Doctrine," p.68,note 18.
(24)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Nixon and Ceausescu,3 August 1969,folder:MemCons--The President and President Ceausescu,2 August 1969,box 1023,President/ HAK MemCons,NSCF,NPMP.
(25)Kimball,"The Nixon Doctrine," p.68.
(26)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the United States,1969,pp.544~548.
(27)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the United States:1969,pp.548~552.
(28)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the United States,1969,pp.553~554.
(29)全文可见1971年出版的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the United States:Richard M.Nixon,1969,pp.544~556.
(30)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69-1976 vol.1 Foundations of 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 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03),Doc.34.
(31)Memorandum,Kissinger to Nixon,29 August 1969,subject:Press Reaction to "Nixon Doctrine",folder:Haldeman File 1969 San Clemente [Part I],box 52,White House Special Files/Staff Member and Office Files(WHSF/SMOF):Haldeman,NPMP.
(32)Kimball,"The Nixon Doctrine",p.70.
(33)Memorandum,Nixon to Kissinger,22 September 1969,box 228,Presidential Memos,WHSF/SMOF:Haldeman,NPMP.
(34)Memorandum,Lord to Kissinger,23 January 1970,subject:Issues Raised by the Nixon Doctrine for Asia,folder 2:Misc.Materials-Selected Lord Memos,box 335,Subject-Numeric Files,1970-1973,Department of State Central Files,GRDOS,RG 59,NA.Lord' s covering memorandum suggests that it was drafted by Lord or by Lindsey Grant,another Asian specialist on the NSC Staff.
(35)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1969,pp.901~909.
(36)关于尼克松为什么取消“钓鸭行动”并代之以核警报,参见William Burr and Jeffrey Kimball,"Nixon' s Secret Nuclear Alert:Vietnam War Diplomacy and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Readiness Test,October 1969",Cold War History 3 (January 2003); pp.113~56; Kimball,Vietnam War Files,pp.21~24;110~20.
(37)Entries for 8 and 11 October 1969 and 27 April 1970,JDHRH,NPMP.
(38)Small,The Presidency of Richard Nixon,p.62.
(39)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the United States:Richard M.Nixon,1970,pp.116~190;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the United States:Richard M.Nixon,1971,p.221.
(40)Laird,The Nixon Doctrine,pp.3~4,6,19.
(41)时殷弘:《尼克松主义》,第35页。
(42)Litwak,Détente and the Nixon Doctrine,p.136.
(43)Library of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1971 Chronology of Events (Washington D.C.:GPO,1972),19 July 1971.
(44)Litwak,Détente and the Nixon Doctrine,pp.133~34.
(45)Litwak,Détente and the Nixon Doctrine,pp.136~37.
(46)Nam,America' s Commitment to South Korea, pp.76,78.
(47)Investigation of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report of the House Sub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95[th] Congress,2[nd] session (GPO,1978),p.60.
(48)Investigation of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p.67.
(49)Litwak,Détente and the Nixon Doctrine,pp.137~38.
(50)Library of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1971 Chronology of Events (Washington,DC:GPO,1972),7 December 1971.
(51)Litwak,Détente and the Nixon Doctrine,p.139.
(52)Litwak,Détente and the Nixon Doctrine,p.140.
(53)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Gruman Sale of F-14s to Iran,Part 17,pp.173ff; US Congress,House,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New Perspectives on the Persian Gulf (93[rd] Cong.,l[st] session,1973),pp.5~6.
(54)"Interview with Arnaud de Borchgrave,International Heraid Tribune,14 April 1973," cited in Litwak,Détente and the Nixon Doctrine,p.141.
(55)美国确认沙特阿拉伯作为维持波斯湾地区稳定的第二支柱的做法,一方面反映了美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的增强;另一方面也是美国试图平息那些对伊朗企图表示担心的阿拉伯国家的做法。尽管沙特阿拉伯与伊朗有同等的地位,尼克松政府并不希望沙特阿拉伯在维护地区安全方面起多大作用。在美国人眼里,伊朗是这个“单一支柱体系”的中心。参见Litwak,Détente and the Nixon Doctrine,p.210,note 47.
(56)1979年之前的美伊关系,参见Shahram Chubin,Security in the Persian Gulf IV:The Role of Outside Powers(Gower for IISS,1982).
(57)Butwell,"The Nixon Doctrine in Southeast Asia," pp.323~325.
(58)Kimball,"The Nixon Doctrine",p.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