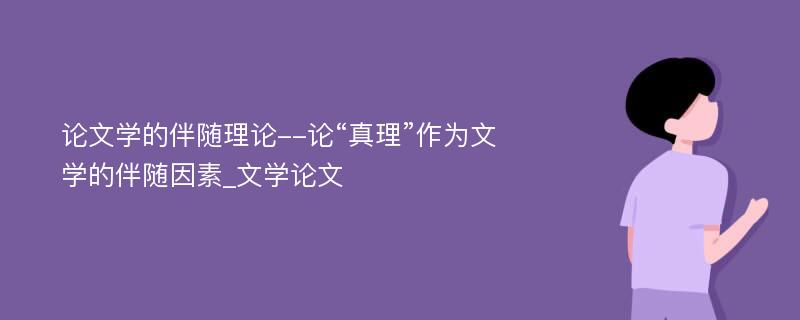
文学伴随论——论“真实”作为文学的伴随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论文,因素论文,真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类型与情节的合理性:一个例子 《神雕侠侣》中有一个情节,在绝情谷里,杨过和小龙女中了剧毒,小龙女已经无药可医,而杨过还有救,小龙女为了让杨过吃下解药,就跳下悬崖,写了几行字,说十六年后在此相聚。这里对这段情节复述得很简单,只是整体情节的概述。既然是概述,就省略了很多东西:曲折。曲折的产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外来因素的干扰,一种是掩饰。在这里曲折的产生出自掩饰。掩饰是一种有意为之。谁为之?小龙女。她明明跳崖了,但却留下几行字:“十六年后,在此相会。夫妻情深,勿失信约。”她知道自己必死,却给杨过传递必活的信息:十六年后再相遇。这话说得模棱两可,就像赫尔墨斯所传递的神谕一样令人难以琢磨。首先因为十六年后再相遇不太可能:她中了毒,危在旦夕,从实际情况看可说必死,但她留的话里的意思却说还可能活十六年,这不能不让入迷惑。此话充满矛盾,一般无解,小龙女写下这行字的时候,难道认为杨过会相信吗?我们不知道。不知道不是因为小龙女的心思难猜,而是因为我们问了一个不该问的问题。这里根本没有相信或不相信的心理变化,只有一个:情节设计的合理性。而情节设计的合理性与其后的解释和发展直接相关。还有一个隐性的相关,这个不在情节中直接出现,而是作为类型在起作用的,即武侠小说的特质。 情节上的发展需要此处有一个对这“神谕”的解释者,这个解人就是黄蓉。从小说中所塑造的人物来说,黄蓉是有此才能的,她天资聪颖,擅长揣测别人心理。黄蓉说“十六年后,在此相会”是大喜。这话就很不同凡响。其实如果小说情节线索不发生大的转变,一个悲剧的模样已经出来了。如果照直写,就只有杨过跳崖自杀这一种可能。要想不把它写成悲剧,在这儿必须转一下。怎么转呢?怎么转到最后的大团圆结局上?黄蓉这个解人的话就要把这种悲剧的气氛转过来。她说,有一个南海神尼,十六年一现江湖(对应小龙女的十六年之约),而且性情古怪(可以解释小龙女的不告而别,因为南海神尼不让说),说不定小龙女遇上了南海神尼也未可知,如果是这样,当然是大喜。为了增强现实性,黄蓉拉上了在场的一灯大师,问一灯是否听过南海神尼这个人。一灯从来不说谎,就含糊其辞:“老衲无缘,未曾得见。”这话没断定什么,但听起来是真的,因为否定的是没见到,而不是这个人物不存在。但对于一个心存希望的人来说,反而坐实了这个人的存在。黄蓉又说她的父亲黄药师还蒙南海神尼开恩,传授了一套掌法(说明南海神尼武功之高,也很真实),这就更增强了可信性。然而这些可信性都是黄蓉说的,没有任何别的证据。 我们来看这里的情节元素:两个十六年,两个不合情理。这两种元素对应上,就产生了一种微茫的可能:小龙女被南海神尼所救。未了,黄蓉加上了“也未可知”。这个限定反而更加增强了可能性。因为对于一件不那么笃定的事情,用揣测的方式说出来反而更加增强了事件的可信度,让杨过在等与不等之间选择等待。小龙女的留言,黄蓉杜撰的南海神尼,两种行为合在一块儿似乎比较合拍,那么一个解释就成了。 情节巧合的运用是武侠小说的一大特征,这实际是对生活中的不可能性的反对,是对奇迹生活的追寻,表征了人的内心欲望。小龙女被南海神尼所救,是一件概率极低的事情,但在武侠世界中却可以发生。杨过这一人物处于这样的类型设计产生出的武侠世界中,他选择相信这一偶然性,倒是在现实情理上有根据。当然在阅读的时候,读者是闭上眼睛,并不会跑到小说外面,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出现之类的话来要求小说,而只关心情节的发展。情节的其后发展从现实角度看更离奇:小龙女跳下悬崖竟然没死,并且遇到奇遇,在碧水深潭里治好了奇毒,等待了杨过十六年,杨过竟然真的跳下来,而且跳下来还没摔死,竟然又发现了这个深潭,同时也发现了小龙女。除了奇迹还是奇迹,所有的奇迹,构成了小说最后的大团圆结局。如果有人把这个故事当作真实事件向我们讲述,我们绝不会相信;我们同时也决不会说,武侠小说是假的,不合情理。阅读至此,我们只会感到一阵阵的阅读快感,有一种畅快淋漓的感觉。但我们设想一下,把这样的情节安在《山乡巨变》这样的小说里,我们除了感到不可思议以外,没有别的。所以奇迹也不是随意的——写到这儿,让我想起了“恶搞”文学和电影,似乎这些作品是随意的,其实根本不是。我们既然叫它“恶搞”了,就说明这是一种类型,否则我们根本没办法称呼它。 对于一部小说而言,情节的合理性最终需要由它所属的小说类型来保证,而不是由它所描绘的真实与否来保证。比如这里的武侠小说,顾名思义,是关于武术与侠客的。在这类小说中,武术是至高无上的,比如金庸的武侠小说《侠客行》中,在侠客岛上,岛主说他招的那些徒弟本来都是读书人,一生愿望都是功名利禄,结果被侠客岛主掳到岛上,去解那旷世武学难题,却从此浸淫其中,以为习武比功名好。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类型设计。只有在武侠当中,我们才会认为武比功名高;在现实生活中实际情况完全相反。这个武侠类型设计是金庸的创造,并贯穿金庸所有的武侠小说,梁羽生也没有打破这一现实性。在这儿要附加一句,类型是不断改变的,没有一种先验的类型,更没有一种关于类型的先验推理,我们只能根据某一类型的实际变化来谈论这一类型。 类型最终保证叙事的合理性,情节的合理性显出作品水平的高低。当然顶级的类型作家,如金庸,运用情节设计以及场景等各种类型契约创造了新的类型,情节设计与类型之间达成一种共振,这是我们称他为大作家的原因。或者说,情节是类型的脸,而类型是情节的外形。——用这两个词是想说,这都是摆在表面的东西,没有深藏之物。两者结合在一起。 二、“真实”在文学中的地位 这个例子中有“真实”的位置吗? 传统的讨论方式是:文学中一定有真实,我们可以从文学作品中发现真实的存在。比如武侠小说是社会现实的曲折反映,一定有真实在里面。这是比较传统的观念。传统的激进观念认为小说里什么真实都没有,有的只有虚构,唯有虚构才有小说。 激进观念中的虚构其实是真实的反面,其基础还是真实。虚构一定与真实相对,否则它什么也不是。那么,剩下的问题是,这个真实是什么样的真实。如果我们不去追踪真实(reality)复杂的概念史(这是一个如此艰巨的任务),只将真实做粗线条的区分,即理念的真实、生活真实和情感真实,那么这里的任务就简化多了。从后面的理论陈述中,我们将会看到,那些真实概念史的追踪根本就不在应该行进的道路上,根本解决不了文学真实概念所面对的困境。 虚构的作品模仿生活吗?是的,模仿。从生活出现在作品前面这一点来说,是这样。后面的东西如果与前面的东西有相似之处我们会认为后面的模仿前面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说不模仿,因为虚构明显与生活中的事情不一样。的确如此,假如作品与生活中的一样,我们为什么要看作品呢,生活本身就足够了。还有一个可能的角度,即认为作品就是生活,由于我们在生活中实际上看不到完整的事件(故事),所以我们就求助于作品,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完整的事件(故事)样貌,或者在诗中我们窥破生活的真相。但这样一说,我们就发现,实际上生活与作品不可能一样,我们只是预设了作品完整地把握了生活,实际如何,我们根本不知道,只有相信。 如果我们再进行一下概念的内涵划分,我们就发现,虚构与模仿也可以说并不矛盾。我们可以把模仿视为一种艺术手法,它遵循的是现实性的原则,比如《西游记》,人物的性格写得活灵活现,事情的发生符合生活逻辑,虽然它在给我们讲故事,但是又让我们觉得事情这样子是可能的,是合情合理的。这个现实性原则指的是现实可能性,就是说这样的个性或事件是可能在生活中发生的,但这个人不一定在生活中出现。比如猪八戒这个人在生活中是没有的,但猪八戒的某些个性或处理事情的方式在生活中却比比皆是。模仿在这儿是部分模仿,而这个部分模仿可能被视为更深刻的模仿。再说虚构。人们常说“艺术源于现实而高于现实”,“高于”这两个字里面就是虚构的意思。为什么要“高于”?就是某个部分不是模仿,而是模仿之外的东西。这个东西可以称之为虚构。当大家说《西游记》或者《荷马史诗》不真实的时候,是因为它们是神话传说,现实生活里面没有神仙,可是当《西游记》把孙悟空等人的出身交代得清清楚楚以后,我们就相信了取经过程中发生的一切故事都是有可能的。这一可能性,或我们经常说的文学真实性是类型赋予的。作品是虚构的,但它是真实的,并不虚假;当大家嘲笑一部艺术作品虚假可笑的时候,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我们在看某部电视剧的时候经常会说,这个电视剧太“假”了。它里面并没有神仙妖怪,全都是活生生的演员,也表演的活生生的生活,为什么还要说它“假”?这是因为它与类型中的细节要求相左。类型有其强大的力量,它会筑成一些更细致的规则要求,这些要求由卓越的文本来建立,其后作品一般要遵从。所以,在作品中,虚假和类型规则相对,不是与现实生活相对。在生活中,虚假与真实相对。大部分的文学作品都可以说是虚构的(当然报告文学除外),但是有的作品却是虚假的,这指的是低劣的作品。 纳博科夫说:“一本书中,或人或物或环境的真实完全取决于该书自成一体的那个天地。一个善于创新的作者总是创造一个充满新意的天地。如果某个人物或某个事件与那个新天地的格局相吻合,我们就会惊喜地体验到艺术真实的快感,不管这个人物或事件一旦被搬到书评作者、劣等文人笔下的‘真实生活’中会显得多么不真实。对于一个天才的作家来说,所谓的真实横祸是不存在的:他必须创造一个真实以及它的必然后果。”①这说的主要是情节方面的合理性,其中隐含着小说类型的力量,即“自成一体的那个天地”。 在《为人生而阅读》一文中,吉布森指出文学可以是一种档案的作用,它记录人类的各种处境和情感,就像巴黎的标准米一样,它既是一米,又不是一米,因为它跟一米这个标准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文学既是生活,也不是生活,它是保存下来的生活,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倘若没有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创造,没有我们的更一般的文学遗产,我们真的不能够恰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看待这个世界,因为,正是文学作品给我们提供一个共享的编制物,在它上面我们能够编制我们世界的如此错综复杂的图画。”② 这里认为文学就是关于我们整个世界,它既不反映世界什么,也不表现世界什么,而是世界的一部分。文学就是生活,而不是反过来,生活是文学。文学只是对于有此需要的人的生活,无论这个人是多么偶然或多么经常地生活在文学中。我们直接在现实生活中发现意义,文学不是发现生活意义的必要方式,但文学作为一种生活形式让我们看到生活的某种独特意义,正如法律、政治、经济都是一种生活形式一样。而作为一种生活形式,文学有其自身的特点和游戏方式。 虽然文学是文字的,它看起来就跟我们日常生活不一样,但我们不能把生活跟文学分开。文学与生活编织在一起,很难把两者完全剥离,所以那种认为文学与生活相对的文学观念是十分可疑的。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文学语言与日常生活语言③又不一样。日常的生活语言有其自身的实践性,它是严肃的实践着的语言形式,但细节上容易消逝;文学语言作为一种模仿性话语实践却起到情感和细节的保存作用,它是从日常的生活语言中的剥离,也是从其他的书面语言记录的剥离。如果没有剥离,也根本不会产生“编织”这样的理论观念。 三、“真实”之为文本解释的功能 对于“真实”,我们可以说得很多,这时最好的办法就是考察一下在文学这个情境中,“真实”这个词一般是怎样使用的。无疑,在一个具体的文本中不会对这个文本真实与否进行提问(我们也可以设想存在一种极其特别的写作方式,在文中就对此文的真实性进行质疑,但那样的写法只是一种技巧,并不能瓦解上述判断)。在文本内部,会出现“真实”这个词,但这个词往往内蕴在文本所描绘的事件中,并不对文本本身进行判断。提出文本与真实这个问题就意味着,我们进行的是另一种不同于具体文本的游戏,这个游戏与文本内部游戏不同、又极其密切。这个游戏就是对文学的整体反思。只有在这个游戏中,“真实”才成为不断被提及的,起到支撑作用的概念。 对于这种极其复杂的概念使用,维特根斯坦建议我们回到概念的原初语境中去考察,才能发现这个概念的真正内涵④,但概念的原初语境的意义不是时间上的,即不是回到文学最初草创的时代,研究那个时代文学是怎样使用的,这种历史主义人类学思路不是维特根斯坦的方法。在文学中提及真实,其原初语境就在文学中,不在文学之外,这一真实与文学是不可须臾离之的。原初语境指是概念的使用方式。“文学真实”的概念使用里面有一些历史因素,但并不是决定性的。那么什么是决定性的?什么是原初的?就是我们现在怎样在文学中使用“真实”这个词的。——更进一步说,连“文学”这个词也是与“真实”结合在一块儿的,不可能分开谈论。 “真实”在文学中怎样使用?它执行什么功能?我们再回到头来看南海神尼的例子。在文本中,南海神尼这个人物的功能是什么?解释一些事情,解释一些关联,这些关联存在一些麻烦,所以要解释。而这个解释是对准一个人的,就是杨过,当然也连带其他不知情者。解释有利于疏通某些关联,它不是作为一个实际的事情处于事情的关联当中,而是作为一个网的结处于网的某个位置上。文本当中的事件或人物可以从解释功能的角度来理解,那么从文学整体的反思上来看,是否也可以这样来理解呢?同样可以。文本内部构成一系列解释的网格,对整个文学做出的解释也构成解释的网格。 我们往往把某个特殊的情节发展视为一种解释,但并不把全部情节都视为解释,因为更多时候,我们不解释,而只是跟随情节;从作家的角度来说,他也并不总是在解释情节,而是在设计情节,我们在判断一个作品成功与否,往往就是从情节设计的角度来判断。所谓情节合情合理,这一判断中包含两个标准:合情、合理,达到这两个标准我们就认为作品成功了。这其中有解释的成分,但如果解释成分过多,一定会形成败笔。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如果我们把每一个情节的推进都视为对其前或其后的情节的解释,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情节就是解释。只是这样一来,我们就在改变“解释”的一般含义。而我们应该努力在平常意义上来思考。 文学的整体解释与具体文本内部的解释不同。文学的整体解释往往在文学批评或主要在文学理论这一层面上做出的。一般来说,只有在这一层面上,我们才真正谈到真实的问题,比如“文学反映了生活的真实”,“文学包含着本质性的真实”,“真实是文学的基础”,“内在真实是文学之为文学的保证”,“文学真实来源于生活与心灵”等等观念。这些只是一长串文学与真实观念的简单罗列而已,如果要更细致的区分可以写一个长长的书系。但我们看到,这里的“真实”往往被预设为三种:生活的真实、理念性的真实和心灵的真实。这些“真实”都提醒我们某种“存在”,文学必须与这种“存在”相联才能得到真正的解释。然而,无论哪种“存在”都不过是一种解释框架中的概念而已,所以我们不如先把这种“存在”的实在性放在一边,先看看在理论解释框架里面,这种“存在”是怎样用的,它在整个理论解释框架里面执行什么样的解释功能,这样可以从过于复杂的语境中摆脱出来,回复到一个相对简单的语境中进行分析。这一语境就是原初语境,它是对概念的用法进行澄清和分析的语境。在这一语境中,“真实”不再是一种实际的存在,而是一个有待解释的概念,我们的工作将由勘定真实的疆域和地图变为厘清“真实”这一标尺的标准和使用方法。 四、一个独特的例子:诗如何成就生活事实 诗是从生活中剥离得最彻底的语言形式,相对诗而言,小说和散文剥离得没有这么彻底。正由于它剥离得彻底,所以我们一般只在诗中寻找纯心灵的东西,它保存着最心灵化的记录。但是诗也可以是生活,从诗里我们能够找到生活的踪迹。然而,从诗中可以考证出实际生活来吗?往往不能。但一个极端的相反例子是陈寅恪创立起来的。——在这儿,我们只能说创立,因为只有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才存在着这么极端的以诗证史,而不是以史证诗。以史证诗易,而以诗证史极难。今人屡屡出现承接以诗证史手法者,与陈寅恪的手法高下不可相提并论。 以《柳如是别传》第二章“河东君最初姓氏名字之推测及其附带问题”为例。陈寅恪首先指出“明末人作诗词,往往喜用本人或对方,或有关之他人姓氏,明著或暗藏于字句之中。斯殆当时之风气如此,后来不甚多见者也。今姑不多征引,即就钱柳本人及同时有关诸人诗中,择取数例,亦足以证明。……”⑤这一条理据极为重要。此为诗史互证的重要部分:诗与人的经历有关。这在唐诗中是不可想象的。李白:“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赠汪伦》)仅见汪伦人名而已。而明末人的游戏习气却可以提供某些史料,这必定是诗发展到一定阶段才有的事情。诗不仅吟情,而且记事(清人喜排律,但并不一定可以做史料用)。这是其一。其二是游戏习气。这两条,可以提供某种佐证,但对于判断者来说要求却很高,一是对当时其他史料的熟悉度要高,二是诗词修养要高。判断者既要是史家,也是诗家。这一点陈寅恪正好具备。当然,仅有上面两条准则尚不足以从诗词中推出哪首与柳如是有关,哪首不是,还必须涉及相关人物复杂的生活经历,而如何选择哪条生活经历又是一个巨大的难题。——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惊叹陈寅恪的诗才和史才。这种以诗证史方法以实证为基础,但不完全是实证,在实际证据缺乏之处,我们是允许做可能性的推测的,陈寅恪在做这样的推测时往往多重材料参证,在似无可证之处依然提出让人信服的证据来,在《柳如是别传》中呈现的是如此精致的考证让人极为惊叹。 比如,有关河东君(柳如是)少年时的事迹的资料比较少,有些材料还是以诋毁为主,陈寅恪如何处理这些材料的呢?以王沄为例。 乾隆修娄县志二五王沄传略云:“王沄字胜时。幼为陈子龙弟子。处师生患难时,卓然有东汉节义风。以诸生贡入成均,不得志。著有辋川稿。” 李叔虎桓耆献类征初编四四四顾汝则传,下附王沄事迹,引章有谟笔记略云:“陈黄门子龙殉难后,夫人张氏与其子妇丁氏居于乡,两世守节,贫不能给。王胜时明经沄常周恤之。”⑥ 记载者的个人事迹以及他与此事之关系,决定他如何记载这件事。事实往往掩盖在陈述的后面。但如果由此判断事实根本无法寻出,那不过是未深入材料的缘故。 上述两条可见王沄与张氏关系。王沄孙女嫁给陈子龙曾孙,这种姻亲关系更加让王沄憎恶河东君。不过王沄憎恶河东君并不是结为姻亲之后,而是一开始就对河东君不喜欢。想来也是自然。河东君是擅长诗词的名妓,以情与色迷惑子龙,自然让家庭不满。子龙夫人张氏是精明强干之人,为子龙选妾也只中意良家女子,必不喜河东君。河东君入子龙家也不会如意,而河东君禀性刚烈,也无法受气,所以很快就离开了陈子龙,另投他处。王沄与子龙家庭接近,故憎恶河东君可想而知。他出于尊师与尊亲(张氏),不能提及此事,所以只是以诗词贬刺河东君。陈寅恪出一片爱护之意,说:“明季士人门户之见最深,不独国政为然,即朋友往来,家庭琐屑亦莫不划一鸿沟,互相排挤,若水火之不相容。故今日吾人读其著述,尤应博考而慎取者也。”⑦其爱护柳如是之情溢于言表。王沄直接言及河东君的材料有一则: 辋川诗钞四“虞山柳枝词”第一首云:“章台十五唤卿卿。素影争怜飞絮轻。(“影”及“怜”二字可注意)白舫青莲随意住,淡云微月最含情。”(“云”字可注意)自注云:“姬少为吴中大家婢,流落北里。杨氏,小字影怜,后自更姓柳,名是。一时有盛名,从吴越间诸名士游。”⑧ 去其讥讽,则可作为一则史料。 在这里,文学中的“真实”变成一个个的事件,我们不能说这是错的,因为我们同样没有根据这样来判断,但文学中的“真实”是如何成为生活中的事件的,却是一个独特的话题。从上面已经展开的理论阐述中,这个例子似乎是个反例。在这里,文学中的描述的确变成真实的事件。陈寅恪的分析让人叹为观止。这是一个最高级、最有难度的学术分析,兼通文史,而且不是一般的通,要兼有诗人才情、史家眼光、杂家广博以及超前意识(预流),其中自然有从实证的角度来说过不去的地方,但作者可以用其他方面来补,审情度势极富创见,而又合情合理,只有大师才能做到。这就是卓越的学术范例。 然而,前面不是说,“真实”是文本解释的功能吗?这个例子中的“真实”最后就是变成了生活中的真实,这不是矛盾了吗?并非如此。“真实”既非是文学中的一场横祸,也非真实的事件,这里举的例子正好表明:文本中的一些描述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解释为生活中的事件。请注意这里做的工作是由文本通过解释转变为生活,不能得出这样的逆向推论:生活是文本的基石。我们变换一个角度会将问题揭示得更清楚:为什么其他的描述不能解释为生活中的事件,而这些可以?其中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只能说,陈寅恪提供了解释的周边情况(我们必须把明末之季的诗人游戏情绪视为这样一种周边情况,而不限于一些事件,比如子龙弟子王沄与子龙家的密切关联),我们依据这些周边情况,可以对一些诗句描述做合理推测。——这里存在的完完全全是解释,而没有别的。即使关于柳如是的生活情况也是解释中得出来的。 “真实”,在文本解释的层面完全是伴随进去的。“真实”这一成分在文本解释中会随着文本类型的变化发生变动。我们对诗进行史的研究,其中一个隐含的维度就是对作者写作进行推测,而作者的写作对于文学解释工作而言永远处于另一端,它既是敞开的,又是隐匿的,我们不可能通过猜测作家心中之意来进行解释,而只能通过掌握的周边情况进行文本解释,并且,不同的周边情况构成不同的解释。比如,1949年后的三十多年时间里,文学理论观念是现实论,那么现实论就是一种最强的周边情况;80年代后,表现主义倾向抬头,主张内在心灵的优先性,那么表现主义成为周边情况的一个构成部分,虽然它不如以前的现实主义那样强大;新世纪以来,文类创新性写作开始占上风,那么文本的类型试验成为最强大的周边情况。在不同的文本类型中,“真实”的成分在其中是变化的。这一点从20世纪以来各种真实观的论争及其调和就可以看出。 五、文本内的“真实” 文学的意义需要真实来保证吗?它必须通过复杂的方式指向文本外部世界以保证语词构成的文本具有深刻意义吗?对这样问题的回答,构成了传统或现代现实主义观念的各种变型。然而,从语言学出发的文学理论已经越来越远离这样的现实主义倾向,因为只要问一下,到底我们怎样知道的文本反映的一定是那个现实,文本与现实之间不可跨越的鸿沟就如实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无论是哪一种回答,无论在文本与现实间设立什么样的曲折关系,都难以填平这一鸿沟,除非彻底转向,将切断文本与现实关联的先验做法⑨抛弃掉,重新建立文本“真实”观,才有可能寻着正确的路径。 文本是第一要义,没有文本,就没有呈现出来的世界,我们不要从现实生活出发,把文本设计成现实生活的反映,而要从文本出发,把现实生活(或真实)设计为文本中的要素,只有这样,才可以找到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既是现象学的,又是语言学的,或者说是语言现象学的。走在这条道路上的,基本来自现象学(比如英伽登、伽达默尔、日内瓦学派等等)领域和语言学领域(主要是日常语言学派或结构主义)。对语言现象学的描述当然不是从语言出发的意识流描述,而是对文本现象的语言分析。从语言游戏的角度,我们可以把意识的本质直观转换为语言的本质直观,因为我们之所以看到一种游戏,完全是语言让我们如此看到,这也是语言的功能,“本质在语法中道出自身”⑩。 文学作为人的一种生活形式(或作为本质直观的形式现象),同时也是一种语言游戏,它有自身的规则和范围,它既可以看作脱离生活,也可以看作内在于生活。但对于文本本身而言,它的意义并不来自外部的世界,而源于内部描绘以及它所属的体裁,更进一步说,外部世界的现实生活已经凝结在文本的语词当中,根本不可能分出单纯的现实或单纯的文本,然后再将现实赋义给文本。这种康德式的先验思路是导致错误的根源。所以,文学的意义是在体裁中,或者根本性地说,是在描绘中展现出来的。继续以《神雕侠侣》为例。武侠小说是一种体裁,它本身就预设了一些东西,比如现代武侠小说中预设了一个独立的江湖,武功至上,侠义精神等等。但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们还得看小说里是怎么写的,我们往往是一边看小说,一边调整自己的预设(这就是文学的教化),我们判断小说的好坏是依照小说本身的预设来进行的,而不是根据它是否符合现实来判断它。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口味,如果小说的某些预设与我们的口味不符合,我们就不喜欢。但一个成熟的读者,或者说一个批评家,就应该尽量地放弃自己的口味,尽量地从作者在作品中的预设进入,进行同情的理解。此所谓理想的读者。我们也可以想想魔幻、各种变形小说,从现实论的角度我们该怎样说它们:曲折地反映了现实。到底有多曲折?——曲折只是一个形容词,它让我们知道某种程度,但不能形成某个图画,如果有某幅图画的话,那不过是一条弯曲的路。 那么,“真实”在文学中是什么地位呢(11)? “真实”在文学中的地位可高可低。在某些文学类型中,比如纪传体文学,“真实”几乎就是生活中的那个样子,或者我们预设是这个样子。在这样的文学类型当中,也并不表明文本中的情节一定就与生活中的真实事件一样,因为把一些事件摆入文学中就意味着选择,不同事件的排序,建立前后因果关联就意味着从一个人的纷繁复杂的生活经历中选择出来明确因果内涵的脉络进行描绘,而这样一来,就意味着或潜或显地改变生活的样态。在1949年后的三十多年里,大陆文学一直主张现实主义,“真实”生活是文学的绝对意义来源。但从实际上看,这种“真实”完全是一种假想,是虚伪的“真实”。从这段极端的文学观念史来看,“真实”也绝不是像一般想象的那样处于意义的中心。从其他类型上看,文学也不提供所谓“真实的内核”。从写实性文本到幻想性文本,以及其间各种过渡形态,“真实”在其中的位置都是变动的,在不同的文学类型当中,它执行的功能也不一样。比如在抒情诗中,所谓的生活真实在此是隐退的,剩下的是所谓情感的真实,但我们决不去考量诗人在抒情的时候是否真的激情澎湃、泪流满面。一般来说,激情必须受到控制,语言才能自如地吐露;而且我们之所以能够判断“情感的真实”,完全是从文本中得出的结论,而不是从创作者的神态。 就像南海神尼是一个杜撰一样,小说也是杜撰,但它像那么回事儿,在这一类型当中,像是真的事情,这就够了。假如你照文学来索隐实事,那就让人不知说什么好了。当然古人有借传奇讥讽他人的实例,比如据说《江左白猿传》就是讥讽欧阳询的,这是一时习气,并不是主流。而且我们也可以说,那是古代的传奇,与现代的小说还不一样,还不是成熟的文学。对于这样的讥讽文学或更严重的恶意文学,我们也不会去拿情节中的事件取代真实的生活事件,除非存在这样糊涂的读者。所以,“真实”只是保障文学描绘进展下去的手段,文学描绘是否成立,不取决于它的内容的真实,而取决于它描绘的整体是否有理有据。这一整体包含类型、情节以及与上述两个因素通过语言结合在一起的生活事件。生活事件为文学的解释提供周边情况,而不是解释的基础。 六、“真实”作为文学的伴随要素 在本质论看来,真实是一个实际存在的对象,这种事实研究曾经带给我们无数的启示,但它的诸种路线延伸也慢慢让我们警觉其无法跨越的障碍,“真实”在文学中慢慢变成了一场“横祸”——我们在文学中看到的事件在生活中往往并不真实。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转换本质论之处就在于消解了“真实”的横祸,这一“横祸”本来就不存在。“真实”从实存变为概念考察,这就消解了模仿论的诸多困境。当然,它还要处理文学如何与现实相关这一传统话题。新批评曾经以为文学只是文本,文学研究应该只关注文本,而不应该关注文本之外的东西。但这样一来,文学文本就成了一种与现实生活的完全隔离(literary isolationism)(12)。这一思路已经渐渐被研究者怀疑:如果文学只是它本身,它与生活有什么关系呢?人们为什么需要它呢? 文学与人的生活相关,这基本是一个自明的观念,重要的是怎样相关。模仿论是文学与现实关系中最强的本质论表述,而形式主义的隔离论是站在模仿论反面的本质论表述,在此中间存在着各种理论表述,都力图解决文学与人的生活相关性问题。这些理论都属于强理论形态。强理论一般是建构型的,本质论是最强力的理论;而弱理论则是防御型的,是为解决某些强理论无法解决的难题的情况下提出来的。这里的伴随论就是一种弱理论,不提供建构和体系,也不提供预测,只提供解释。 吉布森提出为人生而阅读,这是力图从文本向生活回溯,但这一回溯的问题也是存在的:我们无法判断这一回溯的合理性,主要是标准缺失。吉布森的观点从后期维特根斯坦出发,但还是偏离了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观念,没有把语言游戏和遵从规则贯彻到底,在游戏中,只关注了规则,而忽视了规则的样本,即生活中的事件。因此,他微妙地在文学文本和生活中插入了一个空间,小心翼翼地将两者分开,然后再力图填补这一空间。错误发生在第一步,而不是其后的步骤。更恰当的理论设计应该是,阅读即人生,文学本来就是生活,它是人的不可或缺的一种生活形式。当然,文学不是生活的全部,生活形式多种多样,与之对应的语言游戏也多种多样,我们不能为整个文学与现实设置一个普泛的关联模式,我们只能为它设计一个能够随着生活形式变化的关联模式。 文学伴随论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伴随”指“真实”这一概念在文学文本中的伴随,它是相对于文学本质论说提出的一个解决方案。伴随第一层面的内涵指文学的意指功能是弱化的,它的所谓真实性并不是基础性的,它可以被抽掉,只是作为一个建议性的因素保留在文学论述当中。第二层面是文学形式并不因此替换真实性成为基础性要素。它与真实性因素一样,是一种建议性的伴随因素。第三层面的内涵,文学并不因此成为空心的,无所指的对象。从对象与意指方面来思考文学问题本来就是一条错误道路。它本来并不是一个对象,而是一种充满了各种相近或相似游戏形式的游戏类型,不同文学形式具有不同的要素组合方式,而且各要素间在某一特殊组合中重要性各不相同,变换一种组合也会改变各自的重要性。 从上面的陈述可以看出,文学伴随论是一种弱理论,一种防御性理论,是对本质论基调的否定。伴随只是表示出一种关系的变化,在不同的文学类型游戏中,“真实”作为一个构成性概念其位置也是变化的。“真实”所指涉的现实是与文本相伴随的。我们不再主张反映现实论了,但并不代表现实不重要,现实非常重要,只是在伴随论这一理论框架里,现实生活不再是文本的支架或基础;而是,文本表述与现实共同构成文本的支架,规则在文本表述与现实的交错中,形成一个文本整体。在本质模仿论指导我们去寻找现实生活的地方,应该仔细思考一下我们是如何使用这些语词的,在文本表述中执行什么样的功能,那么对于文学与真实的关系会有不一样的理解。同时,也应该看到,文学描述与语言分析不一样,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不过是文学呈现与现实呈现的关系,它不同于词对物的描述关系,而是两种呈现方式的不同,是不同的语言游戏。 ①纳博科夫:《文学讲稿》,申慧辉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7页。 ②(12)约翰·吉布森:《为人生而阅读》,约翰·吉布森、沃尔夫冈·休默编《文人维特根斯坦》,袁继红等译,吉林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167页,第148页。 ③塞尔《虚构话语的逻辑地位》一文为文学语言和日常语言的区分做了极其重要的工作,深深地影响了英美文论界对此问题的看法(John R Searle,"The Logical Status of Fictional Discourse",New Literary History,Vol.6,No.2(1975):319-332)。本文采取了与塞尔相近的立场。同时参见我对塞尔此文的批判性论文《为了文学的虚构》,载《学术论坛》2014年第1期。 ④⑩参见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第178页。 ⑤⑥⑦⑧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6页,第43页,第44页,第46—47页。 ⑨各种关于真实与文学的实在性关系的讨论都预设了文学文本与某种真实的一致性,但正是这种一致性预设,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先验观念的可疑,因为这种一致性还需要其他的标准来保证,并在具体的论证中被无限期拖延以致放弃实现的可能。 (11)在文学中,“真实”一词应该指“相信为真实”(the truthful),而不是“真”(truth),所以它与“现实”(reality)有关联,但不等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