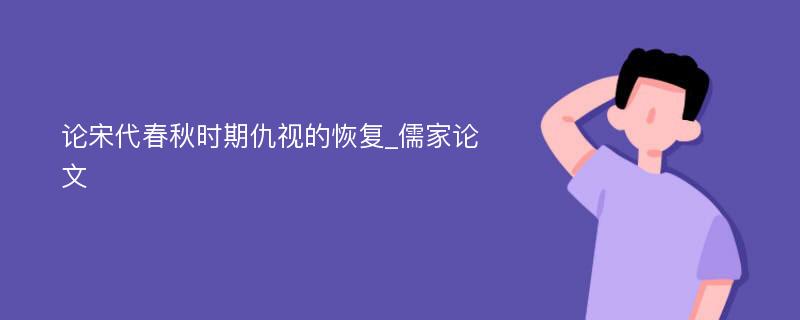
宋代春秋學復仇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代论文,春秋论文,學復仇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公羊家歷來有“《春秋》大復仇”之說,即認爲孔子作《春秋》,經中凡事涉復仇,必會予以特殊的記載,以張大復仇之義。所謂“大復仇”,就是以復仇爲大,即推崇復仇,這裏的“大”與“大一統”的“大”同義。漢武帝“獨尊儒術”以後,《公羊傳》在漢代地位崇隆,復仇論影響很大,各種復仇故事不斷涌現,而官府對于復仇者通常都會免予治罪,甚或予以褒獎,連漢武帝發動對匈奴戰争也要打著《春秋》大復仇的旗號。 漢後公羊學衰落,但“大復仇”作爲《春秋》大義,影響依然深遠。後世學者研究《春秋》,論說《春秋》史事,都無法回避復仇之義,歷代評判、處理現實中的復仇案例,也經常要稱引《春秋》復仇之義作爲依據。歷代統治者都陷入一種兩難選擇,也就是韓愈所說的“蓋以爲不許復仇,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仇,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舊唐書·刑法志》)。而學者們也常常陷入如何理解及如何落實《春秋》復仇之義的争論之中,唐代陳子昂和柳宗元曾在七十年之間,先後寫下《復仇議》和《駁〈復仇議〉》。 有宋一代,春秋學實爲顯學。《四庫全書總目》稱,宋明時期“解五經者,惟《易》與《春秋》二家著録獨多”(《春秋後傳》條)。兩宋研究《春秋》的著作,影響力較大的主要有孫復(992-1057)《春秋尊王發微》、劉敞(1019-1068)《春秋權衡》和《劉氏春秋傳》、孫覺(1028-1090)《春秋經解》、蘇轍(1039-1112)《春秋集解》、胡安國(1074-1138)《春秋胡氏傳》、葉夢得(1077-1148)《葉氏春秋傳》和《春秋三傳讞》、高閌《春秋集注》、張洽(1160-1237)《春秋集注》等。其中又以劉敞、胡安國影響最著。① 宋承五代之後,宋代學者對五代時期政治混亂、戰亂頻仍、綱紀廢弛尤爲痛心,因此宋代對《春秋》的研究和闡發比較側重于社會名教綱常之序。而復仇之義與儒家倫理密切相關,是儒家倫理內在的價值要求,是孝悌觀念的必然延伸,《禮記》中即明確規定出了依親等需承擔不同的復仇義務。②《公羊傳》所說的“大復仇”其目的也是要從根本上維護儒家倫理和社會秩序。因此,宋代復仇之論必然相當繁盛。尤其是宋室南渡之後,雪靖康之耻、復二帝之仇的觀念深烙士人心頭,復仇之論自是更熾于前。 從宋代春秋學的學風來看,宋代春秋學承襲唐代啖助、趙匡所倡導的捨傳求經之風,大都不信傳注,捨傳求經或援經駁傳,欲直探孔子原意,清人納蘭成德指出:“自啖助、趙匡稍有去取折衷,至宋諸儒各自爲傳,或不取傳注,專以經解經;或以傳爲案,以經爲斷;或以傳有乖謬,則弃而信經。往往用意太過,不能得是非之公。”(《春秋經筌》序)因此宋代學者立論更爲大膽,敢于打破三傳窠臼,對三傳之說展開了更多的批評,闡發出許多新義,但由此又不免導致空言說經或隨事發義、憑私臆决。正如《四庫全書總目》所指出的:“生臆斷之弊,其過不可掩;破附會之失,其功亦不可没也。”(卷二十六)基于這樣的學術背景,宋代春秋學的復仇論注定大有可觀,對其進行考察就尤爲顯得重要。 《春秋》三傳,皆有復仇之說,而又以《公羊傳》爲最。考諸《春秋》所載史事,涉及復仇的大概集中在以下幾事:一、隱公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二、桓公十八年“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三、莊公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四、莊公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郜”;五、莊公九年“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六、定公四年“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莒,楚師敗績”。下面我們主要圍繞上述六事,考察宋代學者對這些史事的評論,嘗試梳理宋代春秋學的復仇論。 一、隱公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公羊傳》: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弑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討賊,非臣也。不復讎,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不繫乎臣子也。 隱公十一年,隱公薨。《公羊傳》以爲《春秋》只記載了魯隱公的薨而没有記載葬,是因爲隱公是被弑身亡的,魯國臣子卻没有追討弑君之賊的罪行,没有爲君父報仇,而臣子不爲君父復仇就失去了作爲臣子的資格,而禮葬君父是臣子之事,魯國已經没有臣子,葬事無所依托,所以只能隱而不書。《公羊傳》由此揭示出來了一條“臣不討賊非臣,子不復仇非子”的《春秋》大義,也就是强調君父之仇必報,以復君父之仇爲臣子不可推卸的責任和義務。 “臣不討賊非臣,子不復仇非子”,作爲《春秋》大義,屢屢被後世稱引。宋代學者更爲强調君臣父子之倫,對《公羊傳》此義多無异議,如張洽《春秋集注》以爲:“不書葬者,君弑臣子當戮力討賊以復君父之仇,故賊未討則不敢葬。其不知討賊而遂葬者,《春秋》絀其葬以見其臣子之不忠孝,而忘君父之讎也。”而劉敞《劉氏春秋傳》則有更大的發揮,其稱: 何以不地?弑也。弑則何以不言弑?不忍言也。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以爲人道所未有也。人道所未有,是以不忍言也。何以不書葬?賊未討也。賊未討則何以不書葬?君弑臣討賊,猶親弑子復讎也。讎不復則不葬,不葬則服不除,寢苫枕戈,所以明爲臣子也。葬者,臣子之終事也,其義未終,故不敢以急葬也。 “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語出《禮記·檀弓下》,即弒君之臣,凡官吏都可以殺之,不能寬赦;弒父之子,凡當時在場的人都殺之,不能寬赦。劉敞認爲臣弑君、子弑父是“人道所未有”的罪行,絶對不可以寬赦,人人皆有責討罪。臣爲君討賊猶如子爲親復仇,是臣子之爲臣子必須履行的義務。這裏,劉敞明確把爲君討賊和爲親復仇同質化,討賊就是復仇,把二者等同起來。他在《春秋意林》中更說:“不發君仇,不復其罪,與親弑者無以异,是乃《春秋》所當絶也。”(卷下)不爲君復仇,其罪就等于親弑,可謂非常嚴厲。劉敞還進一步聯繫《禮記·檀弓上》孔子對“居父母之仇”的要求——“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認爲臣子對待君仇也應該如此。 胡安國對劉敞的說法有所繼承,他說: 隱公見弑,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者,仲尼親筆也。古者史官以直爲職,而不諱國惡。仲尼筆削舊史,斷自聖心,于魯君見弑,削而不書者,蓋國史一官之守,《春秋》萬世之法,其用固不同矣。不書弑,示臣子于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不書地,示臣子于君父有不没其實之忠。不書葬,示臣子于君父有討賊復讎之義。非聖人莫能修,謂此類也。夫賊不討、讎不復,而不書葬,則服不除,寢苫枕戈,無時而終事也。以此法討罪,至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春秋胡氏傳》) 胡安國接受了劉敞聯繫《禮記》“寢苫枕干”的說法,而且直接將“臣不討賊非臣,子不復仇非子”歸結合併爲“臣子于君父有討賊復仇之義”。胡安國更是認爲《春秋》書“公薨”而見“臣子于君父有討賊復仇之義”,絶非史官可得作,只能出自孔子筆削,由此也可以看出孔子作《春秋》爲萬世立法、令亂臣賊子懼的意義。 《春秋胡氏傳》裏復仇之說的分量非常重。胡安國在宋室南渡之後,著成《春秋傳》,其激于時勢,往往藉《春秋》以寓意,引申議論時政,以實現其振起朝綱、攘夷復仇等政治主張,因此對“《春秋》復仇之義”再三致意,屢言“《春秋》以復仇爲重”,即使三傳未說以復仇的史事也常常作復仇解。自其之後,《春秋》幾成復仇之書。③因此,胡安國强調復仇之義必出自孔子,是其表彰《春秋》是復仇之書的必有之義。 我們看到,對于《公羊傳》所說的“《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和“君弑臣不討賊,非臣也;不復讎,非子也”,宋儒有相當的認同。即使如葉夢得專作《春秋三傳讞》以駁難三傳,對此義也没有絲毫反駁,而只是針對《左傳》說的“不書葬,不成喪也”反駁說:“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此《春秋》責臣子之義,不爲其不成喪也。”(《春秋三傳讞·左傳讞》)葉夢得在其《葉氏春秋傳》中還宣稱“《春秋》之法,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責臣子也,以爲所以事君親者,人得以任其責”,也是站在了《公羊傳》的立場之上。 總體看來,宋儒所發的議論,雖然從立場上看要或許比《公羊傳》更爲嚴厲,但究其實際並無多少新意,只是在爲《公羊》舊說尋找更多的支持而已。 二、桓公十八年: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外也。讎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 《穀梁傳》: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不責逾國而討于是也。 魯桓公在齊國被齊襄公殺害,依據“臣不討賊非臣,子不復仇非子”之義,只有在魯國臣子報仇了的情况下纔可以書葬,但桓公之仇未報卻書葬,《公羊傳》以爲這是因爲仇人在國外,不能苛責魯國的臣子。《穀梁傳》與《公羊傳》所持觀點基本一致。何休說:“時齊强魯弱,不可立得報,故君子量力,且假使書葬。于可復讎而不復,乃責之。”能報仇而不報仇是必須予以譴責的,而在力所不能及的情况下君子也會予以諒解。《公羊傳》雖因“讎在外”給予紓緩,但絶不是因“讎在外”就主張臣子可以不復仇,否則也不會在莊公四年譏斥莊公不思爲桓公復仇而與仇狩了(下詳)。《公羊傳》所要表達的應當是:葬事不可無限推延,在形勢不允許立即報仇的情况下,君子推想魯國臣子當有復仇之心,先書桓公之葬,以示恕道。這無疑是在堅持君父之仇必報的大義下,又提供了一定的靈活性。 但《公羊傳》說辭過于簡略,而在何休“齊强魯弱”、“君子量力”的解釋下,這種說法似乎就很難自洽。“君弑臣不討賊非臣,子不復仇非子”,難道因爲仇敵强大就可以不報仇了嗎?這未免也太可耻了吧?劉敞《春秋權衡》就此批評說: 《公羊》曰:“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外也。讎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非也。君弑臣不討賊非臣,子不復讎非子,復讎者以死敗爲榮,故曰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齊襄公復九世之讎,《公羊》賢之,奈何爲讎在外,則勿復乎?必曰量力而動,不責逾國而討者,又何以稱復讎者以死敗爲榮乎?伍子胥藉吳之力以復楚,《公羊》是之,即以量力不責者如子胥乃可耳焉。有據千乘之勢而知讎不報乎?(卷十) 《穀梁》曰:“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不責逾國而討于是也。”非也。父之讎不與共戴天,豈限國哉?若以齊强魯弱,量力不討,故君子不責,是復讎者常行于柔弱而困于强禦也,不亦妄乎?(卷十四) 劉敞對《公羊傳》“讎在外”和《穀梁傳》“不責逾國而討”之說極爲不滿,尤其對“量力”之說痛加駁斥,以爲若此說成立,復仇者豈不都成了欺軟怕硬之徒了。他質問,難道還有力量足够强大而故意不報仇的人嗎?他舉“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之義,否定“讎在外”之說;舉“君弑臣不討賊非臣,子不復讎非子”、“復讎者以死敗爲榮”之義和齊襄公復九世之仇、伍子胥藉吳之力以復楚之仇,否定“量力”之說。“君弑臣不討賊非臣,子不復仇非子”是《公羊》之義,“復讎者以死敗爲榮”是何休解《公羊》之說,齊襄公復九世之仇和伍子胥藉吳之力以復楚仇都是《公羊傳》所贊許的復仇之事,劉敞可謂用《公羊》駁《公羊》。 葉夢得在《春秋三傳讞》裏與劉敞的看法幾乎完全一致。他說: 君子辭者,謂桓見弑于齊,讎在外,《春秋》不責魯,以力所不能及,故書葬。若然,則前所謂君父弑而臣子不復讎爲非,臣子者止施之內而已,豈所謂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者乎?傳言齊襄公以九世之讎而復紀,伍子胥藉吳之力以復楚,又何以皆賢而與之?《春秋》者,因事以立法,不爲一人設也,此但論讎復不復爾,若以齊强魯弱,因以恕之,遂廢天下之復外讎者,亦何足以爲法?(《公羊讞》) 而在《葉氏春秋傳》裏,葉夢得又另外闡述了一套討賊、復仇兩分的理論: 葉子曰:桓公之葬不葬,在法之爲弑不弑,學者皆臆以桓爲弑,吾不知其罪在齊侯歟?夫人歟?……二氏(公羊、穀梁)皆以爲讎在外,不責逾國而討,則以齊侯言之也。夫齊侯安得爲弑哉?當討不討,義也;能討不討,力也。使齊侯不爲弑,則《春秋》雖欲責之討固不可。若誠爲弑,莊公雖不能討,桓公固不害不葬以正其義,乃以逾國不盡其責而爲之辭,則何以爲《春秋》?《春秋》有復讎、有討弑,言讎則不爲弑,言弑則不爲讎,二名不可以相亂。弑則凡國之在官者皆得以殺之,而君父之讎不共戴天,有遠之以使避,無責之以必討,曰殺之者無罪云爾……爲莊公與魯之臣子者,則如之何?正齊侯之罪而告于王,曰:請以諸侯之師討焉,暴內陵外則壇之,先王之刑也。 劉敞强調爲君討賊猶如爲親復仇,二者是一回事,胡安國、張洽都因之爲說,葉夢得卻將復仇與討賊明確區分開來,以爲二者不可以相混淆。葉夢得認爲,君薨書不書葬,不在復仇不復仇,而在君是否被弑,弑君賊是否得討。而弑君只能是臣子弑君,桓公被齊襄公所害,顯然不能稱之爲弑,所以也就不存在討弑君之賊的問題,只能是復仇的問題。葉夢得試圖通過區分討賊和復仇,從而在維護“君弑臣不討賊非臣,子不復仇非子”的大義下爲桓公書葬做出合理解釋。但他的這種解釋顯然缺乏强大的解釋力。葉夢得還非常書生氣地提出,魯國君臣當時正確的做法應當是上告周王,對齊襄公施以九伐之法。試想如果當時周王尚有權威的話,春秋何以成亂世,孔子又何必作《春秋》呢? “讎在外”說在宋代也不乏支持者,胡安國就基本持一種維護的態度,他說: 《公羊》曰:“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外也。”穀梁子曰:“讎在外者,不責逾國而討于是也。”夫桓公之讎在齊,則外也;隱公之讎在魯,則內也。在外者不責其逾國,固有任之者矣;在內者討于是,此《春秋》之法也。故十八年書王,而桓公書葬,惟可與權者,其知之矣。(《春秋胡氏傳》) 胡安國認爲,在內必討、在外不責逾國,這是《春秋》之法,“惟可與權者”纔能做出這樣的掌控。這裏的“惟可與權者”,顯然是指孔子,與其之前强調復仇之義必出自孔子是一致的,同時這也暗示《公羊》此說正暗合經權之道,乃是權宜之變。不過,胡安國完全没有提及强弱、量力的問題,顯然他雖然同意“讎在外”的說法,但並不能接受量力復仇的說法,可是又似乎找不到周延的解釋,只好含混地表示“在外者不責其逾國,固有任之者矣”,說一定會有人承擔起責任的。 與胡安國有所保留不同,張洽則對“讎在外”說完全没有异議。張洽說: 《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外也。讎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詞也。”蓋國有强弱,勢有順逆,今齊强于魯,而天下既不舉九伐之法,諸侯亦未有以方伯之事自任者,故君子量力且假使書葬,于可復讎而不復,然後深責之也。(《春秋集注》) 張洽同意《公羊傳》“讎在外”而可紓緩臣子之責的說法,更對葉夢得舉九伐之法而正之的說法作出了糾正,明確支持何休的“君子量力”之說。張洽所處的時代已值南宋中後期,君臣上下已經認清復外仇無望的現實,對于“讎在外”而力所不能及自然多了一份同情的理解,因此他與之前的宋儒態度明顯不同也就可以理解了。 若說宋儒之中,對葬桓公之事持論最中正者當推高閌。高閌在所著《春秋集注》中說: 夫《春秋》之法,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爲人臣子而不能衛其君父,乃至見弑于人,又縱賊不討,忍耻以葬之,則雖葬猶不葬也。故必待賊既伏誅,然後書葬,所以少寬臣子之責,而示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也。今桓公見弑于齊,《春秋》不著討賊之文,而遽書其葬者,此《春秋》之變例,聖人之微旨也。蓋《春秋》責臣子以討賊者,以爲可討而不討也;至其所不能必討者,聖人亦無責焉,忠恕之道也。夫以魯視齊,齊爲强又非魯之臣,如欲討賊,則必至于侵伐以傷其人民,争奪以亡其社稷,君父之讎未必能復而先君之土地先已危亡,無辜之人民先已殘賊,則其爲害于我又有甚于不討賊之耻也,况擅動干戈以伐人之國,王法所不容乎。故魯之臣子,聖人非不責之,但責以其君見殺于他邦,不責其必討强齊,此《春秋》所以曲盡人情之難,而深慮危亡之必至也。 高閌以葬桓公爲《春秋》之變例,體現聖人的忠恕之道,可謂深得《公羊傳》之旨。他深刻揭示了魯國復仇强齊所面臨的困境和强行復仇于國于民的巨大危害,既維護了君父之仇未報的《春秋》大義,又反對了那種無視後果、甚至招致更大混亂和禍害的復仇舉動,避免了何休之說給人的那種欺軟怕硬的感覺,進而又將不討外仇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聯繫在一起,論說得頗爲周全。 三、莊公四年:紀侯大去其國。 《公羊傳》: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何讎爾?遠祖也。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以襄公之爲于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先君之耻猶今君之耻也,今君之耻猶先君之耻也。國君何以爲一體?國君以國爲體,諸侯世,故國君爲一體也……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爲若行乎?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爲爲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緣恩疾者可也……此復讎也,曷爲葬之?滅其可滅,葬其可葬。此其爲可葬奈何?復讎者非將殺之,逐之也。以爲雖遇紀侯之殯,亦將葬之也。 齊襄公滅紀,《春秋》記成了“紀侯大去其國”,《公羊傳》認爲這是《春秋》以齊襄公爲賢而褒揚他,因爲周夷王時紀侯進讒言而導致齊哀公受烹殺,齊襄公滅紀是爲已隔九世的遠祖齊哀公復仇。《公羊傳》這裏不僅認爲齊襄公復九世之仇是正當的,而且還提出即使是復百世之仇都是可以的。但復九世之仇是有限制條件的,首先《公羊傳》把復九世之仇明確限制于國仇。與私仇不能“怒其先祖,遷之于子孫”(何休《公羊解詁》莊公四年)不同,國仇具有特殊性,因爲國君一體,世代相傳,後君是先君的繼體者,先君之仇等同後君之仇,先君之罪也等同後君之罪,因此國仇可以綿延百世。其次,《公羊傳》强調,復九世之仇必須是在“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的狀態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社會秩序混亂,正義不能伸張,纔可以用極端的手段去討回有序狀態下應有的公道,給予有罪行的人以應有的懲罰。而如果“有明天子”在,社會正常秩序有保障,則應當首先遵循正當正常的途徑去伸張正義,不得實施這種復仇的行爲。 復九世之仇或復百世之仇的說法,是“大復仇”論的核心,但因其立論過于驚駭,在後世非議巨大。如許慎《五經异義》說:“《公羊》說復百世之讎,《古周禮》說復讎之義不過五世。許慎謹案:魯桓公爲齊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齊桓公會,《春秋》不譏;又定公是魯桓公九世孫,孔子相定公,與齊會于夾穀:是不復百世之讎也。”許慎此說又被孔穎達收入《禮記正義》,流傳甚廣。 宋代學者對九世復仇說也多是明確表示質疑和反對。如孫覺《春秋經解》說: 《公羊》之說最爲誕妄,齊襄復九世之讎,而紀侯當絶滅,是《春秋》滅人之國猶爲賢也。此不近人情矣。 蘇轍《春秋集解》: 《公羊》曰:何以不言滅?爲齊襄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齊哀公烹于周,紀侯譛之,于是九世矣。世蓋有復九世之讎者乎?且襄公非志于復讎者也,雖或以是爲名,《春秋》從而信之,可乎? 高閌《春秋集注》: 先儒以齊襄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此尤害教之甚矣!復讎乃亂世之事,况以九世乎?漢武帝因此而雪平城之耻,興大兵伐匈奴,連歲不已,天下彫弊,戶口減半。嗚呼!不達《春秋》之旨,而貽萬世之禍者,其此言也夫! 高閌對九世復仇說的批評堪稱激烈,以爲對儒家倫理的破壞非常嚴重,甚至將漢武帝興兵伐匈奴而帶來的負面影響也都歸咎于此義。 另如孫復《春秋尊王發微》、劉敞《劉氏春秋傳》和《春秋權衡》、胡安國《春秋胡氏傳》、葉夢得《葉氏春秋傳》對“紀侯大去其國”則根本未作與復仇相關的評論。而胡安國本是宣揚《春秋》復仇論最積極的人,很多三傳未作復仇解的史事他也都以復仇來進行論說,但對九世復仇卻采取完全回避的態度。實可見九世復仇說在宋代支持者的缺乏。 不過劉敞還是在《春秋權衡》卷八藉公羊學“三世說”展開了對九世復仇的批駁,以爲《公羊》此說自我矛盾: 《公羊》以謂國君以國爲體,故先君之耻猶今君之耻,雖百世猶可復讎,而言《春秋》之義遠則不諱,豈不橫出三世,反戾其言乎? 上述儒者或審之以周制,或查之以史事,或責之以情理,但卻不知《公羊傳》“藉事明義”之法。清儒皮錫瑞辯之甚明:“止是藉當時之事做一樣子,其事之合與不合,備與不備,本所不計……齊襄非真能復讎也,而《春秋》藉齊襄之事,以明復讎之義。”(《經學通論·春秋》)《公羊傳》就是要通過齊襄公滅紀之事,來張大《春秋》復仇之旨,而齊襄公是否真的是爲了復仇,周制實際如何規定,是否合乎情理等等,則皆不在考慮之中。這也正是《公羊傳》“大復仇”等義成爲“非常异義可怪之論”的原因。 要說宋代儒者中,九世復仇說持比較正面看法的則是朱熹。朱熹雖然也對“《春秋》許九世復仇”之說多有微詞,如在《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三,朱熹說:“謂復百世之讎者是亂說。許五世復讎者,謂親親之恩欲至五世而斬也……《春秋》許九世復讎,與《春秋》不譏、《春秋》美之之事,皆是解《春秋》者亂說。”又說:“復讎,須復得親殺吾父祖之讎方好。若復其子孫,有甚意思?漢武帝引《春秋》‘九世復讎’之說,遂征胡狄,欲爲高祖報讎,《春秋》何處如此說?”不過朱熹又稱:“事也多樣,國君復讎之事又不同。”但究竟如何不同卻又未明說。聯繫其在《戊午讜議序》中所說的“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讎”來看,朱熹在國君復仇問題上是同意九世復仇的,他甚至還超越九世或百世,提出“萬世必報之讎”的說法。《戊午讜議》一書是朝臣關于和議的奏議稿合集,朱熹爲之作序,他對南宋君臣在三、四十年之間就已經“國家忘讎敵之虜,而懷宴安之樂”的現象非常痛心,因此高舉九世復仇甚至萬世復仇來對現實進行强烈的抨擊,企圖發揮一種震懾的作用。 當然,不排除一種情况,就是宋儒很可能在理論上不能接受九世復仇或百世復仇,但在情感上卻又傾向之。如劉敞作有《題幽州圖》一詩,抒發自己在看到契丹占領下的幽州之圖時的感慨,其中就有一句“復讎宜百世,刷耻望諸卿”(《公是集》卷二十六),能說他完全反對九世復仇嗎? 四、莊公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郜。④ 《公羊傳》:公曷爲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狩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爲獨于此焉?譏于讎者將壹譏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其與讎狩也。于讎者則曷爲將壹譏而已?讎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爲大譏,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同。 《穀梁傳》:冬,公及齊人狩于郜。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爲卑公也?不復讎而怨不釋,刺釋怨也。 莊公四年,魯莊公跑到齊國的郜地與齊襄公一起狩獵,而在《春秋》中齊襄公被記成了齊人,好像就是一個地位低微的人一樣。《公羊傳》認爲這是避諱魯莊公與仇人一起狩獵。魯莊公的父親魯桓公是被齊襄公殺害的,齊襄公就是魯莊公的殺父仇人,莊公不僅不報殺父之仇,居然還與仇人狩獵,顯然非常惡劣。《公羊傳》又提出了“讎者無時焉可與通”的原則,强調任何時候都不能與仇人交往。《穀梁傳》也以不復仇不能消解怨恨,對莊公進行了譏刺。 宋代學者對莊公及齊人狩之事的評論,意見出奇地一致,除了劉敞說這是譏刺“公之去南面而下與微者狩也”(《劉氏春秋傳》)之外,基本上對《公羊》、《穀梁》二傳没有太多的非議,都認爲這是在譏刺莊公與仇人狩獵。如孫復《春秋尊王發微》說:“父之讎不共戴天,莊公父親爲齊殺,而遠與齊人狩。”蘇轍《春秋集解》說:“公忘齊之讎而越境以與其人狩,非禮甚矣。或曰齊人,齊侯也。不言齊侯,爲公諱也。”葉夢得《葉氏春秋傳》說:“齊人者何?齊侯也。齊侯殺人之父,而通其子;莊公忘父之怨,而與其讎人。齊侯所以人,公也主王姬,天子命之可也;會于禚、享于祝丘,夫人爲之可也;狩于是,則公無辭矣。”胡安國則兼綜《公羊》、《穀梁》之說,又突出了《公羊》“讎者無時焉可與通”的原則: 穀梁子曰:“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爲卑公?不復讎而怨不釋,刺釋怨也。”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與同國,九族之讎不同鄉党,朋友之讎不同市朝。今莊公與齊侯不與共戴天,則無時焉可通也。而與之狩,是忘親釋怨,非人子矣。(《春秋胡氏傳》) 張洽則乾脆將《公羊傳》之論用自己的語言復述了一遍: 《公羊傳》:公不當與微者狩,蓋齊侯也。齊侯而稱人,諱與讎狩也。公前此後此皆有事于齊,而獨于此譏者,譏其一以例其餘,蓋通讎之罪俱重不可勝譏,而尤莫重乎與讎狩,故于此一譏,而其餘從同同也。(《春秋集注》) 而孫覺則重在揭示復仇背後孝的涵義,批評莊公不孝之甚,並對《公羊傳》所說的“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爲獨于此焉?譏于讎者將壹譏而已”作了展開,細數了莊公與仇通之事,從中得見與仇狩爲何最爲嚴重。孫覺與衆不同的是,他不認爲《春秋》所書“齊人”是指齊侯。他說: 公之父見殺于齊,公之于齊有不同天之讎也。然而莊公忘其父之讎而貪齊之利,畏齊之强,元年主其婚,三年臣會其伐,《春秋》一書之以見其罪。然元年之婚見命于天王,雖有交仇讎之罪,其責差輕也。三年臣會其伐,罪已重矣,然公猶未親也。于是又親與其臣狩于其地,蓋公之不孝而釋讎也,于此爲甚。聖人深疾之,書曰“公及齊人狩于禚”,莊公釋仇讎之罪惟是爲重也。不曰齊某而曰人焉,又所以重之也。其父見殺于其國,而爲子者乃與其臣狩于其地,不同天之恨則俄頃忘之,游畋之樂則晏然爲之,雖甚不孝、甚不肖者有所不爲,而莊公安爲之……按不書齊侯實非齊侯也,不書其名嫌以臣而敵我也。(《春秋經解》) 高閌認爲魯莊公與齊襄公之仇,不止在齊襄公殺其父,還在齊襄公通其母。在這樣的深仇大恨下,魯莊公居然還遠越境遠出與齊襄公狩獵,况且國君冬狩與祭宗廟息息相關,如此莊重的事,居然與仇人一起進行,足可見魯莊公罪惡之深重。他說: 父母之讎不共戴天,此言公及齊人者,即齊侯也。貶而人之,惡其賊吾君之父,通吾君之母也。夫齊侯自元年以來見于經者數矣,何獨于此焉貶?曰前此欲著文姜、襄公宣淫,而無忌憚文,勢不可云齊人,今因與公狩始得一貶也。莊公父爲齊侯所殺,母爲齊侯所通,而乃越境遠出而就之狩,且狩以奉宗廟者也,與人共之猶且不可,况其親之讎乎?爲人子而忍情如此,故不没公而書及,所以深罪之。(《春秋集注》) 由上可見,宋儒對《公羊》、《穀梁》二傳所論的公及齊人狩之事多無意見,頂多是對齊人是否是齊侯而有所争論。宋儒對《公羊傳》所說的“讎者無時焉可與通”也頗爲認同,這與當時士人多反對與金和議的立場有關。紹興四年(1134),胡安國之子胡寅上疏宋高宗,即引此義宣揚復仇、反對和議,其稱: 女真驚動陵寢,殘毁宗廟,劫質二聖,乃吾國之大讎也。頃者,誤國之臣遣使求和,以苟歲月,九年于茲,其效如何?幸陛下灼見邪言,漸圖恢復,忠臣義士聞風興起,各思自效。今無故蹈庸臣之轍,忘復讎之義,陳自辱之辭,臣切爲陛下不取也……當今之事,莫大于金人之怨。欲報此怨,必殄此讎。用復讎之議,而不用講和之政,使天下皆知女真爲不共戴天之讎,人人有致死之心,然後二聖之怨可平,陛下人子之職舉矣。苟爲不然,彼或願與陛下歃盟泗水之上,不知何以待之?望聖意直以世讎無可通之義,寢罷使命。(《宋史·儒林傳》) 胡寅張《春秋》復仇之義,義正詞嚴,宋高宗雖一心苟安,無心復仇,卻也不得不表示“嘉納”,裝模作樣地說:“胡寅論使事,詞旨剴切,深得獻納論思之體。”這也可從側面反映出當時宋儒藉《春秋》闡發復仇論的現實意義和作用。 五、莊公九年: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公羊傳》: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伐敗也。曷爲伐敗?復讎也。此復讎乎大國,曷爲使微者?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不與公復讎也。曷爲不與公復讎?復讎者在下也。 《春秋》對于魯國軍隊的戰敗一般是避諱不書的,而莊公九年的“我師敗績”是《春秋》中唯一的例外。《公羊傳》認爲這是因爲乾時之戰是復仇伐齊,“復讎以死敗爲榮”(何休《公羊解詁》莊公九年),所以被記録下來。但《公羊傳》卻没有給予莊公此次復仇絲毫的贊許,反而表明了“不與公復讎”的態度。乾時之戰實際上是莊公親率大軍,《春秋》卻故意不提莊公,好像只是一個地位卑微的人領軍一樣,《公羊傳》認爲這是不承認莊公的復仇。所謂“復讎者在下也”,何休解釋說:“時實爲不能納子糾伐齊,諸大夫以爲不如以復讎伐之,于是以復仇伐之,非誠心至意,故不與也。”也就是說,乾時之戰明明是爲了幫助公子糾争位,復仇只是一個藉口,而且這個藉口還是出自諸大夫之意,並非莊公心存復仇之念,因此對莊公繼續予以貶斥。《公羊傳》這裏强調的是復仇的“誠心至意”,主張臣子爲君父復仇必須是內心油然而生的一種使命感。 宋代學者對于乾時之戰的評論可謂分歧很大。一種意見是不以乾時之戰爲復仇之戰,以孫復、孫覺、劉敞和葉夢得爲代表。孫復《春秋尊王發微》說: 此公及齊師戰于乾時也。不言公者,公伐齊納讎人之子,喪師于此,此惡之大者,諱之也。內不言敗,此言我師敗績者,羨文,蓋後人傳授妄有所增爾。(卷三) 孫復以爲乾時之戰就是莊公伐齊納糾之戰,《春秋》不記莊公,是因爲公子糾是齊襄公之子,是仇人的兒子,莊公居然爲了仇人之子而兵敗,非常可耻。但這樣一來,《春秋》獨于乾時之戰記録魯敗就没法解釋了,于是孫復就將之歸爲“羨文”,以爲是後人竄入。這也暴露了孫復隨己意改經的學風。 孫覺也同樣不以乾時之戰爲復仇之戰: 及齊師戰者,公及之爾。不曰公,承上文“公伐齊”也。先言伐而後戰,則戰者公也。《春秋》省文,故不曰公及齊師也。《春秋》之義,內不言戰,言戰則敗。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未有內言敗績者,乾時之戰書戰、書敗,此《春秋》之變例,而聖人之新意也。莊公父見弑于齊,齊爲仇讎,仇讎之國無時而通。莊公受公子糾之來奔,志欲納之,已盟其大夫,伐齊而納糾矣,而公子小白先之。既忘其讎也又不量其力,而與齊戰焉,戰不勝而至于敗師,徒崩喪而子糾不免于死,爲莊公者其罪如何也?莊公有諸侯之位、國君之尊,民人之所瞻望,一國之所矜式也。父之仇讎則忽而忘之,仇讎之子則决而納之,既不果納又戰而敗其師焉,不同天之讎已不報,而與之交矣,無辜之民又驅之戰而至于敗焉。十二公之間二百四十二年之久,興師之惡未有甚于莊公者也……《公羊》曰:“曷爲伐敗?復讎也。莊公實納讎子而敗,故書,以罪之。”無復讎之意,何得推言復讎乎?(《春秋經解》) 孫覺也認爲乾時之戰是在譏刺莊公納仇子,但他主張乾時之戰不記公,並無深意,只是承接上文的“公伐齊”作了省略而已。而書敗,纔是體現聖人譴責莊公忘父仇、納仇子而敗其師,不報仇反與仇通,于其中寓有新意的地方。孫覺還反駁《公羊傳》說,既然莊公没有復仇之意,那怎麽又可以說乾時之戰是復仇之戰呢?孫覺與孫復的立論方式雖然不同,但究其觀點實質,其實都是以乾時之戰爲譏刺莊公通仇、納仇,只是孫覺較孫復說得顯然更爲圓融。 劉敞與葉夢得則在不以乾時之戰爲復仇的同時,把評論的重心放到了《公羊傳》所說的“復讎者在下”上。如劉敞說: 《公羊》曰:“內不言敗,此言敗者,伐敗也。”非也。若魯實以復讎而戰者,《春秋》不宜不言公。若以復讎者在下,故不言公,《春秋》豈奪人臣子意哉?臣有善言,君行之則君善也,故《書》曰“股肱良哉”,言一體也,奈何以復讎者在下則不以其美歸公哉?且謀之者臣也,行之者君也,臣謀而君不行貶君可也,臣謀而君行又欲何嫌?(《春秋權衡》卷十) 葉夢得說: 內辭皆諱敗,唯乾時之戰不諱與外同辭書敗績者,不正其忘仇讎而納子糾,故雖敗不以爲耻也,何復讎之謂哉?范寧謂“讎者無時而可通”,其言是矣。且是時小白雖已入齊,而子糾猶在魯,不以是爲納子糾,而强以“復讎在下”言之,孰有知其然者?其曰“不與,復讎在下,而不言公”者,尤非。復讎審出于誠耶,則臣子言之,公行之可以無貶矣;如不出于誠,而姑以爲言則臣子亦僞而已,何獨責于公哉?(《公羊讞》) 劉敞和葉夢得都認爲,臣爲君謀,臣子本來就是給君主出主意的,只要臣子提出建議,君主采納了,那就成了君主自己的主意,怎麽可以因臣下出的主意就否定君主復仇的誠意呢? 另一種意見則認爲乾時之戰是復仇之戰,以高閌和張洽爲代表。高閌《春秋集注》說: 糾之不立,蓋由公不即遣而要盟也。今公雖伐齊,而更欲納之。然齊已有君矣,公班師可也,奈何必欲取勝而遂戰乎?曰此不書公,蓋國人以辭直自欲戰,而公弗能禁也。辭直者糾當立也,自欲戰者蓋自我桓公遇弑之後,仇讎之人復與吾君之母宣淫于通道大都,魯人羞之甚矣,曾未嘗一與齊交鋒,以少雪我國之耻也。令公興師伐齊,故魯人樂致其死以紓稽年憤懣之氣,初不繫于納糾也,故納糾雖不克,而衆怒不能自已,于是戰于乾時而敗焉。內敗不書,獨此書我師敗績者,魯人咸自誇其能伐讎,樂于死戰,而不以爲辱也。先儒謂復讎者以死敗爲榮,此言是矣。于是可見魯國之人不忘君父之讎,而莊公特以納糾興師,初無力戰刷耻之意,遂致軍氣不振,績用弗成也。 高閌明確肯定乾時之戰是復仇之戰,但卻是魯國之人的復仇之戰,而非莊公的復仇之戰。莊公伐齊自是爲了納公子糾,本無復仇之心,但魯國人雪耻之心高漲,甘于死戰以復仇洩憤,雖敗猶以復仇爲榮。高閌這一番評論,說的雖是春秋時的魯國,但卻分明讓人看到了當時的南宋,高宗無心復仇,而臣民卻對靖康之耻痛心疾首,群情激昂。 我們再來看張洽,張洽《春秋集注》說: 《春秋》書及而没公,又不諱內敗,蓋復讎而敗,雖敗亦榮,故不爲內諱。獨莊公非有復讎之心,而納不正以取敗,故諱公以貶之也。 張洽言簡而意賅,一以乾時之戰爲復仇,二以雖敗亦榮故書敗,三以無心復仇貶莊公。短短一段話,《公羊傳》的意思大體都在,又雜糅進來一點自己的意思,即以公子糾爲不正。但復仇之戰和莊公無心復仇之間的邏輯落差卻没有作任何交代。 還有一種意見很特殊,是把乾時之戰定位爲“與仇戰”,以胡安國爲代表。胡安國《春秋胡氏傳》說: 內不言敗,此其言敗者,爲與讎戰,雖敗亦榮也。按《左氏》“戰于乾時,公喪戎路,傳乘而歸”,則敗績者,公也。能與讎戰,雖敗亦榮,何以不言公?貶之也。公本忘親釋怨,欲納讎人之子,謀定其國家,不爲復讎與之戰也,是故没公以見貶。若以復讎舉事,則此戰爲義戰,當書“公”冠于敗績之上,與沙隨之不得見,平丘之不與盟爲比,以示榮矣。惟不以復讎戰也,是故諱公以重貶其忘親釋怨之罪,其義深切著明矣。 胡安國認爲,乾時之戰是跟仇敵之間的戰争,只要跟仇敵開戰就應該贊許,雖敗猶榮。但乾時之戰卻不是復仇之戰,因爲莊公開戰的目的不是復仇,所以《春秋》就不記公來貶斥他没有復仇之念。胡安國這種說法很新穎,其實只是將《公羊傳》之說做了一個小的改動,但原來的曲折和違礙感頓時全消,而推崇復仇之義卻又絲毫無損。 以上三種意見雖然各有不同,但他們都以爲乾時之戰是在譏刺莊公無復仇之心,在一點上他們是一致的。 六、定公四年: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莒⑤,楚師敗績。 《公羊傳》: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憂中國奈何?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以干闔廬。闔廬曰:“士之甚,勇之甚,將爲之興師而復讎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爲也。”于是止。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于南郢數年,然後歸之。于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爲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爲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爲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于是興師而救蔡。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爲可以復讎奈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復讎不除害,朋友相衛而不相迿,古之道也。” 《穀梁傳》的叙述與《公羊傳》大體一致,只是没有最後那段評論性的問答。 伍子胥父被楚平王誅殺,伍子胥投奔吳國,吳王闔廬要興兵爲伍子胥復仇,伍子胥卻說,不能爲復父仇而虧君之義。復仇不虧君義,將家事與國事截然分開,即類似《左傳》所說的“私仇不及公”(《哀公五年》)。《公羊傳》特別强調復仇的正義性,提出“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如果父親本身有罪,那兒子就不能爲父親復仇,否則兒子復仇没有正義性,那麽仇人之子還可以就這種復仇繼續復仇,一來一去就會陷入循环報仇。《公羊傳》還提出了“復讎不除害”和“朋友相衛而不相迿”等準則,即復仇的對象只能限于仇人本身,而且復仇的主體也只能是被害者的兒子,對復仇擴大和過度作了防範。 最爲重要的是,《公羊傳》這裏提出了一個非常特异的主張,那就是臣可以向君復仇,其旗幟鮮明地提出“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如果父親無罪受誅殺,其子作爲臣子是可以向君主復仇的,並以此來支援伍子胥向楚王報殺父之仇。 同爲傳解《春秋》的著作,《左傳》在臣可向君復仇的問題上與《公羊傳》的立場存在相當大的差异。《左傳》定公四年:“鄖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用一個同樣與楚平王有殺父之仇的事例完全否定了臣子可以向君復仇。 《公羊傳》的“臣可向君復仇”是最具有先秦儒家思想特色的主張之一。而後世,隨著君主專制的逐漸强化,即如漢代公羊家何休,也已經不能完全秉持《公羊傳》的這種君臣觀念,轉而强調“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公羊解詁》宣公六年)了。但爲了彌縫與傳文之間的裂隙,何休又不得不解釋說:“諸侯之君與王者异,于義得去,君臣已絶,故可也。”(《公羊解詁》定公四年)把臣可對君復仇限定爲諸侯君臣間的特例,以避免對君主專制制度産生衝擊。到了宋代,綱常羅網日密,有弟子問朱熹“君以無辜殺其父,其子當報父之讎,如此則是報君”,朱熹則直斥“豈有此理”(《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三),“謂之亂臣賊子,亦未可”(《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四)。《公羊傳》的這種思想已經完全没有生存空間了。但朱熹也認爲“古人自有這般事,如不爲舊君服之義可見。後世天下一家,事體又別”(《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四),可以說朱熹也基本認可了何休的解釋。 《公羊傳》藉伯莒之戰闡述了諸多的復仇大義,但宋代學者對伯莒之戰的復仇內容卻普遍予以冷處理,或作夷夏之辯,或作義利之辨。究其原因,大概就是因爲伯莒之戰若談到復仇問題,就是伍子胥爲父報仇,而伍子胥報仇的對象是楚王,那麽就必然涉及到臣可報君的問題。宋儒的態度多似朱熹般以爲“豈有此理”,自然不願去談這個問題。像孫復《春秋尊王發微》、孫覺《春秋經解》、蘇轍《春秋集解》、胡安國《春秋胡氏傳》,不僅不談伯莒之戰的復仇,甚至全書中一次伍子胥都不提。 而宋儒中即使是談到伯莒之戰的復仇問題或伍子胥的復仇問題,大多也都想盡辦法回避臣復君仇的問題。如葉夢得說: 蔡以楚圍請救于吳,吳子爲之興師,故以蔡侯、吳子及楚人言。蔡之主戰也,吳何以稱子?進之也。召陵之會、皋鼬之盟,諸侯既無能爲,吳子能爲之出師一戰而復楚讎,則中國之不若也。(《葉氏春秋傳》) 葉夢得雖然只說了寥寥幾句,但我們也能很清楚地看到,在他的筆下,吳國伐楚是爲蔡國復仇,根本與伍子胥没關係,那當然也就没有什麽報復國君的問題了。 高閌《春秋集注》對伯莒之戰的評論也是未涉及復仇,但卻在評論下條“庚辰,吳入郢”時發表了相關的看法: 夫吳子救蔡伐楚,斯可善矣,然而至于入郢,則吳之志乃不爲蔡也,伍子胥復讎之故也。舉吳國而爲匹夫復讎,故乘囊瓦之敗長驅入郢,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聖人又惡其乘人之敗而深爲利,故反其狄道而稱吳。又謹而日之,疾其已甚也。 高閌認爲伯莒之戰是吳救蔡,而吳入郢纔是爲伍子胥復仇。伯莒之戰是善的,吳入郢卻是惡的,吳國做出了很多的惡行,其中就包括動機的不正確——“舉吳國而爲匹夫復讎”。高閌明顯表示出對此的反對,甚至是厭惡。 而蘇轍更是明確表示了反對“臣得仇君”。他的《春秋集解》在評論“癸巳,陳夏徴舒弑其君平國”之事時說: 徴舒,陳大夫夏姬之子也。靈公之惡,甚矣,其稱臣以弑,何也?罪不及民也。君以無道加其臣子,臣子以弑報之而得不名,是臣得讎君,而子得讎父也。 蘇轍說得很直白,陳靈公固然無道之甚,因此被弑,但《春秋》還堅持要把弑君的夏徴舒的名字記下來,就是要表明君雖無道,臣卻不得仇君。 宋儒中,比較大方地談伍子胥復仇的非劉敞莫屬,他在《劉氏春秋傳》裏說: 吳何以稱子?進也。曷爲進之?吳强國也,自卑以聽蔡侯之義,達天子之命,成伯討焉。其成伯討奈何?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以干闔閭。闔閭曰:“士之甚,勇之甚,將爲之興師復讎于楚。”子胥復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爲也。”于是止。及蔡侯不得志于皋鼬,楚復伐蔡,圍之,蔡請師于吳,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爲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爲可矣。”于是興師而救蔡。 其實劉敞這段評論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東西,就是《公羊傳》或《穀梁傳》說的一個複製版,當然更像《穀梁傳》的複製版,因爲他也完全回避了最後一段涉及臣可向君復仇的對話。不過,劉敞倒是專門作有一篇《復讎議》,主動去談這個問題: 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乎?曰:可。君臣義也,父子性也。曰:不以親親害尊尊乎?曰:親親內也,尊尊外也。親親本也,尊尊末也。重內而輕外,先本而後末者,道有在焉。若是,則可以報君,手之亦可乎?曰:否,非此之謂也。君之于臣也,固有誅道,若何其可手哉?然則奈何而復之?曰:以告于方伯……告于方伯而不從,則告于天子……告于天子而復不從,則是上無天子,下無方伯。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則緣恩而疾之可也。請問其人?曰:伍子胥是矣。曰:伍子胥亦嘗告諸方伯天子而不從乎?曰:否,子胥未嘗告也。未嘗告何以得專復讎?曰:子胥知雖告焉猶無益也。當是之時,周爲天子而楚以王自居,晋王諸侯而楚與之狎主盟。周晋之下不能行于楚也久矣,惡能誅之?此《春秋》所以緣恩而疾之者也,君子以謂猶告。(《公是集》卷四十一) 劉敞首先旗幟鮮明地確認,父親無罪受誅,子可以向君復仇,並以“親親本也,尊尊末也”爲論據。那麽,這是否意味可以親自動手來報復君主呢?劉敞說,不是這個意思,你看君主本來有誅殺臣子的權力,那君主也没有自己動手殺人的道理啊。所以正確的報仇方式應該是遵循正當的途徑,上告方伯、上告天子,讓方伯和天子來處理。只有在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的混亂時期,纔能像伍子胥那樣不告而自行復仇。通過劉敞的論述,我們看到,實際上劉敞把臣爲君復仇的君限定爲了諸侯,跟何休、朱熹一樣采取了與當時的君主專制制度相切割的辦法。尤其是他提到,應通過層層上告的“法律途徑”來實現復仇,其實是把臣可向君復仇的問題給瓦解掉了。 據此,綜合來看,宋儒對待臣可向君報仇的問題,基本上都是持否定態度的。 除了以上我們考察的六事之外,宋儒還于莊公元年“秋,築王姬之館于外”、莊公元年“冬,王姬歸于齊”、莊公二年“秋七月,齊王姬卒”、莊公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蔇”、莊公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等事多有復仇之論,只是囿于篇幅,本文不及討論。 宋代儒者之中,對《公羊傳》的“大復仇”說背後的意義揭櫫得最爲透徹的當推王應麟。王應麟在《困學紀聞》中在評論朱熹《戊午讜議序》“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讎”之語時指出:“吁!何止百世哉!‘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讎者無時焉可與通’,此三言者,君臣、父子、天典、民彝繫焉。公羊子大有功于聖經。”(《困學紀聞》卷七)一個“大復仇”,君臣、父子、天典、民彝都含攝其中,王應麟極其深刻地看到了以《公羊傳》爲主的《春秋》復仇論的最終標的,即儒家倫理和社會秩序。 宋代學者對《春秋》的研究和對《春秋》史事的評論極具現實感,尤其是復仇之論更是如此。宋鼎宗說:“《春秋》大復仇之說……宋儒則一言之不足,至于再;再言之不足,至于三者。北宋盛時,猶屢敗于契丹,及女真入京,欽徽遂爲之北擄,康王倉皇南渡,既心存偏安,又誤信寵佞,一無匡復之志,再乏雪耻之計,雖能苟延殘喘于一時,終不免爲蒙古所吞噬。故儒者之釋《春秋》,屢以復仇爲大義,要皆在彼而不在此也。”⑥ 稽考《宋史》之中,臣子上疏或對策之中,尤其是南渡之後,以復仇之義說時事者比比皆是。如: 紹興九年(1139),兵部侍郎張燾北上朝陵,返回時奏稱“金人之禍,上及山陵,雖殄滅之,未足以雪此耻、復此讎也”,並在高宗問及陵寢時憤然回答:“萬世不可忘此賊。”(《張燾傳》) 隆興元年(1163),朱熹入對,稱:“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朱熹傳》) 隆興五年(1167),陳亮上書:“昔春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爲三綱既絶,則人道遂爲禽獸,皇皇奔走,義不能以一朝安。然卒于無所遇,而發其志于《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今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讎,此豈人道所可安乎?”(《儒林傳》) 《宋史·刑法志》稱“復讎,後世無法”,而《舊唐書·刑法志》中也引韓愈之言說復仇“律無其條”,韓愈還明確說“非闕文也”,可見唐律、宋律對復仇都采取了一種模糊的處理,究其原因也就是本文之前所提到的歷代統治者的二難選擇。而稽考《宋史·刑法志》,復仇條下列有復仇案例三宗,兩宗被免死罪,其一爲仁宗時,單州民劉玉父爲王德毆死,王德被赦免後,劉玉私殺王德以復父仇。“帝義之,决杖、編管”。其二是神宗元豐元年(1078),青州民王贇幼時父爲人毆死,及其成人復仇,以仇人肢體祭父,並自首。官府原定當斬,神宗“以殺讎祭父,又自歸罪,其情可矜,詔貸死,刺配鄰州”。第三宗是宣州民葉元以其兄淫亂其妻爲由,殺兄及兄子,又强迫其父與嫂不告官。事發後地方政府爲其求情,皇帝“以妻子之愛,既罔其父,又殺其兄,戕其侄,逆理敗倫,宜以毆兄至死律論”。 可見在宋代,復仇之類的案件,在實際操作中很多時候最後都要由皇帝親自來裁决,而其中爲父復仇大體上都是會被寬宥免死的。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即使是在現實復仇案件的判决中,《春秋》復仇大義也是發揮了指導作用的。 ①皮錫瑞《經學通論·通論》云:“宋儒治《春秋》者……以劉敞爲最優,胡安國爲最顯。“ ②《禮記·檀弓上》云:“子夏問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鬥。’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鬥。’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曲禮上》云:“父之仇,弗與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國。” ③戴表元《剡源文集·春秋法度編序》云:“咸淳中,余備員太學博士弟子,見學官月講必以《春秋》,竊怪而問諸人,曰:是自渡江來,以爲復讎之書,不敢廢也。夫復讎之說,初非《春秋》本旨,中興初,胡康侯諸公痛數千年聖經遭王臨川禁錮,乘其新敗,洗雪而彰明之,使爲亂臣賊子者增懼,使用夏變夷者加勸。” ④“郜”,《左傳》作“禚”。 ⑤《左傳》作“柏舉”,《穀梁傳》作“伯舉”。 ⑥宋鼎宗:《春秋宋學發微》,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第19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