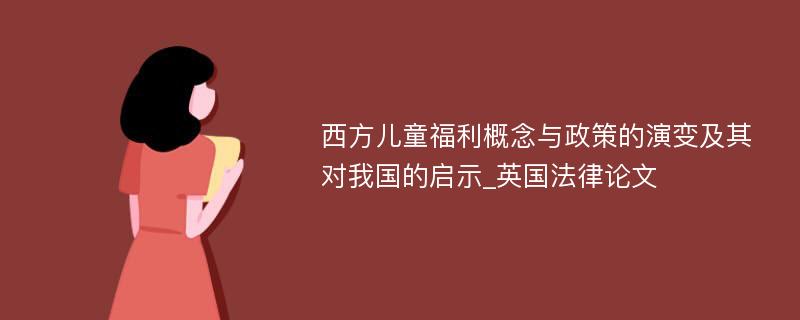
西方儿童福利理念和政策演变及对中国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启示论文,福利论文,理念论文,儿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4)11-0116-07 理念是基于对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指导性思想和价值观念,它是经过实践检验而不断完善的。历史上,西方国家儿童福利的理念曾随着时代和实际情况的变迁经历巨大变化,并对政策的制定和完善产生直接影响。本文根据国家在儿童福利中的作用,把1601年英国《伊利莎白济贫法》(以下简称《济贫法》)之后西方儿童福利理念和政策的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17世纪初至19世纪中叶的“失依儿童救济时期”;19世纪下半叶现代儿童福利兴起至20世纪80年代的“儿童福利与儿童保护时期”;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生效以来的“儿童保护与家庭支持融合时期”,即儿童和家庭福利时期。儿童福利是指满足全体儿童及家庭的普遍需要所提供的各种制度、措施和服务;儿童保护是指国家依法救助保护受到或可能受到虐待、忽视等伤害的儿童的各种制度、措施和服务,以保障儿童安全。这种狭义的儿童保护包括在西方当代儿童和家庭福利体系中。从西方主流的儿童福利理念演变及其对政策的影响角度入手,研究儿童福利的发展经验,对中国明确理念、促进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的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一、失依儿童救济时期的理念和政策 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人性堕落的观念使得儿童被认为带有与生俱来的“原罪”,常常被描述为“邪恶”和“破坏”的形象,此外,由于婴幼儿的存活率极低,父母在儿童的存活得到保障(大约7岁)之前一般不投入很多感情①,因此溺杀或遗弃儿童,特别是残疾多病的儿童,在当时的社会是常有的事情。16世纪在欧洲盛行的文艺复兴运动冲击了神学的禁锢,重新审视了“人”的价值,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儿童的态度。从1601年英国《济贫法》开始,西方政府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开始承担救济贫民的责任,并建立初步的救济工作方法及行政制度,这对其他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开启了政府依法救济儿童的时代。17世纪初至19世纪中叶,西方国家奉行不干预家庭的“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faire)②的政策取向,只有当儿童失去家庭或家庭无能为力时才提供有限的救济,属于儿童福利的残补模式。这一时期主要的理念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儿童天生无辜“值得救济” 17世纪,人们逐渐认识到儿童是“值得救济”的弱势群体。《济贫法》将孤儿、弃儿和部分贫困儿童包括在“值得帮助”的穷人中,与“不值得帮助”的穷人区分开来。18世纪,伴随着对人权和人的主体性认知的加深,儿童在启蒙运动的思潮中被“发现”。法国哲学家卢梭不仅认为儿童是“天生无辜”的,而且认为应该“把儿童看作儿童”。儿童“原罪”观念被摒弃,其生性善良的观念被人们认同③。这一时期,很多西方国家社会福利或社会保障的政策法律中都有对孤儿和贫困儿童进行救济和技能培训的内容。 (二)救济“失依儿童”是政府的责任,其他儿童是家庭的责任 这一时期,儿童被认为是父母的私有财产,照顾和养育儿童完全是父母的责任和家庭的私事。家庭是提供儿童福利的主体,而国家只扮演家庭的“补充者”角色。国家救济儿童的范围仅限于“失依儿童”,即没有父母的孤儿和弃儿以及父母无法依靠的贫困儿童,救济的深度仅是满足儿童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儿童生活的济贫院条件很差。18世纪早期,英国济贫院中婴儿死亡率极高,出于减少儿童死亡率以增加国家人口的目的,1767年英国议会通过《汉韦法令》促使教区加强和完善对弃婴的照顾④。当时,政府及慈善界的态度受到重商主义的影响,认为增加人口是增进国家财富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因此救济儿童、减少婴儿死亡率不仅是出于人道主义,也有保护国家利益的功利性目的。虽然这一时期国家救济儿童的范围和深度有限,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国家对儿童的生存状况持比过去更加负责任的态度。特别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欧洲出现儿童与国家关系的新理念,即国家救济儿童不仅是因为儿童是脆弱的,而且因为儿童是国家未来的公民⑤。这一理念对此后各国儿童福利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儿童是“小型的成人” 虽然启蒙思想家们已经开始认识到儿童的特殊性,但儿童仍然被普遍认为是“小型的成人”,因此这一时期救济儿童的政策法律并没有将儿童和成人进行区分,儿童与成人混住在济贫院中。直到19世纪初,一些西方国家才逐渐将对儿童的救济与成人分开,成立专门为孤儿、聋哑儿、盲童和流浪儿童等提供照护的孤儿院,但最初的发展缓慢。 但由于当时生产力发展的需求,儿童还必须像成人一样去工作,为家庭生计和经济发展做贡献,贫困儿童经常会被父母送去当学徒(学徒制)。政府对儿童的救济也往往伴随着对儿童工作和实现经济价值的要求,根据《济贫法》的规定,大龄的孤儿或弃儿会被送去做学徒,济贫院中年幼的儿童要进行职业技能训练,并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至13岁再去做学徒。这一时期,童工普遍存在,工业革命进一步加剧了童工问题,儿童的工作环境恶劣,工作时间超长,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报酬却远远低于成人。在人道主义者的长期呼吁下,英国1802年颁布《学徒健康与道德法案》,开拓了欧洲立法保护童工的先河。此后又陆续颁布一系列《工厂法》,其中对儿童工作的年龄、时间、劳动强度和种类、劳动条件和生活环境做出越来越严格的限制。这些法案体现了对儿童的人道主义关注,改善了童工的生存状况,但尚未意识到儿童的权利,因而都没有真正解决童工问题。1834年英国颁布的《新济贫法》对接受救济的贫困者提出了更严苛的工作要求,对儿童的救济也抱有更大的工作期望。这说明,虽然人们开始意识到儿童与成人有些区别,但是还没有现代的“童年”和“儿童权利”观念。 二、儿童福利与儿童保护时期的理念和政策 西方现代儿童福利兴起于19世纪下半叶⑥,学校教育和儿童保护立法开始出现,专门的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机构大规模建立。在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80年代,积极主动干预家庭的“国家家长主义”⑦的政策取向盛行,西方儿童福利出现由残补型走向普惠型、由关注“失依儿童”扩展到全体儿童的趋势,儿童福利行政体制和服务体系形成。在人权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下,20世纪初期,人们认识到儿童不仅是需要保护的脆弱个体,还与成人一样拥有权利,随后,整个国际社会在儿童权利保护的立法上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这一时期主要的理念可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童年”期是重要的、独立的人生阶段 19世纪西方近代自然科学获得巨大发展,其中物种进化理论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儿童”研究的兴趣,并在19世纪90年代汇聚成了“儿童研究运动”。“童年”这一概念得到前所未有的研究和关注了,学者们不仅认为童年是根本区别于成年的人生阶段,而且认为童年是由不同的阶段组成,儿童在每一阶段都有其特点与需求⑧。在被称为“儿童的世纪”的20世纪里,西方社会尊重儿童的呼声日益高涨,使得人们更进一步认识到儿童的主体性和童年的重要性。 儿童不再被认为是“小型的成人”,而是需要特别照顾和教育的独立个体。首先,现代儿童福利服务大量出现,儿童逐渐从济贫院转移到孤儿院,孤儿院作为专门安置儿童的重要选择得到了显著发展。20世纪初,随着“将儿童带离贫困家庭”理念的流行,美国由1851年的77家孤儿院发展到1900年的400家孤儿院⑨。其次,儿童被认为不应该像成人那样工作,而应该受到专门的教育和照护,儿童教育得到显著发展。1840年,德国教育家福禄倍尔正式建立了“全德意志幼儿园”。1870年英国《初等教育法》颁布实施,强制5到12岁儿童在公立学校接受教育。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义务教育法案是1852年麻萨诸塞州《义务教育法》,解决了8岁到14岁儿童的教育问题,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所有的州都通过《义务教育法》,大部分州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年龄增加到了16岁。儿童应该受照顾和教育的观念在这一时期成为西方国家的共识。 (二)儿童是权利的主体 20世纪是国际社会保护儿童权利的立法取得巨大成就的世纪。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国家开始认为儿童拥有一些法律权利,并立法保护儿童,西方国家的童工问题逐渐得到解决,很多危害儿童权利的问题得到关注。国际联盟1924年通过了《日内瓦儿童权利宣言》,首次在国际上提出了“儿童权利”概念,但更多涉及的是成人有义务满足儿童最基本的物质及精神需求,儿童仅是权利的客体。“二战”后,人权意识在世界范围内普遍高涨。1949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提出保障全世界儿童的生存权、保健权和受教育权,决定每年的6月1日为国际儿童节。195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儿童权利宣言》,明确了儿童应当享有的各项基本权利,提出了“儿童的最大利益”原则,儿童成为权利主体,为现代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但是,这些宣言并没有法律约束力,直到1989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才使这些理念得到国际法的认可,以法定的形式使“最大利益”成为保护儿童权利的一项基本原则。公约认为,儿童与成人同样是完整的人,儿童作为权利主体拥有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和参与权,特别是参与权的提出更明确了儿童的主体地位。 (三)家庭是比机构更适合儿童成长的环境 家庭寄养作为一种新的替代性儿童福利服务发端于英美两国,并逐渐被西方社会广泛接受。基于家庭寄养比机构养护好的理念,19世纪50年代前后,西方国家掀起了将不幸儿童从贫困的父母和拥挤的城市中解救出来的运动,其中以美国的“免费家庭寄养运动”最为著名。1853年,美国学者查尔斯·布瑞斯成立“纽约儿童援助会”,并实施将城市中的“失依儿童”转移到美国中部农村的“孤儿列车”计划,开启了现代意义的家庭寄养。1909年,美国白宫儿童会议明确提出家庭是最适合儿童成长的环境,这一理念对西方儿童福利的政策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促使西方儿童福利中的替代性服务由机构照顾向家庭寄养转变。这一时期所重视的是给儿童一种“家庭环境”,而不一定是真正的“家”。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寄养家庭中的儿童数量超过了机构养护中儿童的数量,“去机构化运动”进一步推动了这种趋势,使机构安置逐渐减少,至20世纪末期,大型的机构照护服务如孤儿院在西方发达国家消亡,代之以基于社区的小型的短期儿童养护机构。直到现在,对困境儿童的保护措施中,家庭寄养成为各国普遍使用的照护模式⑩。 (四)国家有权干预家庭,保护儿童免受虐待 西方社会关注儿童保护的转折点是1874年美国首个因虐待儿童而被刑事检控的“玛丽·艾伦案”。由于当时保护动物的法律比保护儿童的法律更加有力,玛丽是作为动物王国的一员被解救的,唤起了人们对儿童虐待的公共意识(11)。在此案件的推动下,“纽约防止虐待儿童会”同年成立,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专职儿童保护的民间机构。1889年英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个专门针对儿童权益保护的法案《预防虐待儿童和保护儿童法案》(简称《儿童法》)“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法律上粉碎了孩子是父母私有财产的神话,为国家干预儿童抚育事务提供了充分的法律基础,成为现代儿童保护与儿童福利制度的重要基础”(12),也开启了西方各国为儿童保护立法的时代。加拿大和欧洲很多国家都颁布了类似的儿童保护法案,保护儿童免受父母残忍对待。荷兰授权政府机构调查儿童成长环境及儿童虐待问题,并且提出救助儿童比惩罚罪犯更加的明智和经济的理念。 儿童保护进一步突破性发展得益于临床医学的研究发现。20世纪40年代以后,美国放射医生借助X光发现了许多儿童受伤案例。1962年儿科医生Henry Kempe及其同事的论文“被殴儿童症候群”(13)首次界定了“儿童虐待”,这不仅激起了很多专业人士及社会大众对儿童保护的兴趣,还促使儿童保护进入了国家议程,美国人权协会和儿童福利联盟等社会组织开始说服联邦政府更多地参与到儿童保护的工作中(14)。20世纪60到70年代,儿童虐待被建构为社会问题,对儿童虐待和儿童保护的关注逐渐成为西方国家儿童福利的重点(15)(16)。1974年,美国第一个针对儿童保护的重要联邦立法《儿童虐待防治与处理法》通过,规定了对虐待儿童的强制报告制度,并有专门的政府部门负责处理。其他欧洲国家也立法明确了政府责任部门调查儿童虐待案件的权力以及儿童虐待报告制度。这一时期,西方发达国家均建立了以预防和干预儿童虐待为中心的儿童保护制度,日益通过公共权力干预家庭中的儿童养育。 (五)国家应承担儿童福利的主要责任 西方各国在这一时期相继建立儿童福利行政体制和儿童福利体系,国家开始由不干预家庭生活变为“居主导地位”,扮演家庭的“监督者”角色。美国召开“白宫儿童会议”并于1912年成立儿童局,标志着美国联邦政府第一次认识到为儿童提供服务的责任(17)。但在此后的20年里,美国儿童福利仍然主要由非政府组织和各州政府而非联邦政府主导。直到1935年,联邦政府才开始与州政府分担照顾儿童的责任,将“抚养未成年子女援助计划”包含在《社会保障法》中。20世纪中叶是西方福利国家高速发展的时期,国家的权利和角色得到很大的扩张,社会各界广泛认同国家的社会福利角色,国家开始积极地承担照护儿童的主要责任,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制定政策分担家庭照护儿童的责任,如家庭儿童福利津贴或现金救助制度、税收减免或优惠制度等;二是提供专业的服务满足儿童及其家庭需要;三是当家庭缺失或父母缺位时,国家为儿童提供替代性照顾。儿童福利的范围空前扩大,各类困境儿童处于政策议程的优先领域。很多欧洲国家开始推行更慷慨的儿童福利政策,包括实施普惠的儿童和家庭津贴制度、亲职假制度等,为儿童和家庭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儿童福利无论是在内容和形式上,还是在范围和程度上都有了根本的扩展和深入(18)。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更是明确把保护儿童权利的责任强加于各国政府,并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国家承担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的主要责任的理念成为国际共识。 三、儿童保护与家庭支持融合时期的理念和政策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儿童权利公约》1990年9月2日正式生效,它以法律的形式厘清了国家和家庭对儿童的责任,西方国家由强调“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变为强调“儿童和家庭福利”,尊重家庭及父母权利成为主导的政策取向,国家扮演“支持者”角色,提供家庭所需的服务以支持和提升家庭功能。西方儿童福利领域长期争论国家干预家庭的界限在哪里,应该帮助父母还是惩罚父母,关注儿童权利还是父母权利等问题。一些国家的儿童福利是“儿童保护导向”,例如美国、英国、加拿大等,个人的权利和家庭的隐私是其中心价值,只有当家长侵犯了照顾儿童的最低标准时,保护儿童的权力机构才会介入该家庭,主要依赖法律的权威和司法途径来实施对家庭的干预,一般通过将受虐儿童带离家庭的形式来实施儿童保护,即惩罚不合格的父母。另一些国家的儿童福利是“家庭服务导向”,如法国、瑞典、荷兰等,首要关注点是提供对父母与儿童之间关系的支持,更多强调与父母达成协议,儿童受伤害不是接受家庭服务的前提,儿童和家庭福利服务与提供给大众的服务并不明显区分开来(19)。这两种导向逐渐取长补短,呈现出儿童保护与家庭支持融合并重的趋势。围绕国家和家庭对儿童的责任问题,这一时期出现以下三方面的新理念: (一)在保障儿童安全的前提下,尽量保留原生家庭和支持家庭 儿童保护导向的儿童福利体系过去忽视原生家庭及父母权利,家庭得不到足够的支持与帮助,大量被认定为受虐待或忽视的儿童进入家庭寄养系统,造成儿童福利机构不堪重负。合理缩减儿童保护体系的范围是美国目前儿童福利改革的重要方向(20)。在保护儿童的种种尝试中,人们逐渐意识到原生家庭对儿童和父母的重要性,父母与子女有血缘上的生物性连接和心理性、情感性的连接。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儿童福利理念发生变化并推动了儿童福利制度改革。学术界和政府的关注点从给儿童一个“家庭环境”到尽量让儿童生活在自己的家中,儿童保护尽量保留原生家庭,支持和帮助家庭。美国1993年专门通过《家庭保留和支持法案》,明确并加大了家庭保留的力度。此外,20世纪后期以家庭为基础的服务普遍开展。家庭服务的理念是,家人是重要的并且应该生活在一起,家庭是儿童首要的照护场所,社会服务项目应该不遗余力地提高父母的能力,强化家庭功能(21)。 然而,由于有些家庭的问题难以解决,美国1997年的《收养和安全家庭法案》又强调“儿童的安全至高无上”,规定继续在资金上支持增强家庭功能的预防性服务,支持在保障儿童“安全、幸福和永久”前提下的家庭保留,如果在原生家庭中出现危及儿童安全的行为,需要终止家长的监护权。2001年英国《评估儿童需求及其家庭的框架》反映了英国政府观念上的转变:从关心是否在儿童保护上失职改变为关心是否在为困境家庭提供帮助与支持上失职(22)。对于经过合理努力依然无法返回原生家庭的受虐儿童,亲属照护和收养是首要选择,目的是帮助儿童加入另一个能使他们获得永久关爱和支持的家庭。以支持家庭、服务家庭的方式来保护儿童也逐渐被儿童保护导向的国家认可。 (二)儿童优先,对儿童的投资是效益最好的社会投资 20世纪90年代中期,西方福利国家的改革开始实施发展型的福利政策,变“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型国家”,把国家对儿童福利的投入看作一种投资。社会投资理念将社会政策与人的不同生命阶段相结合。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儿童处于生命周期的“上游”,童年孕育着未来无限的发展潜能,这个阶段的任何不利因素,都会影响他们的一生。因此西方国家更加重视“上游干预”,投资儿童,帮助家庭满足儿童的需要,包括营养、照顾、教育、医疗等需要,消除人生早期阶段的儿童贫困,避免贫困的“代际传递”,变事后补偿为事前预防,消极福利为积极福利。在制定法律法规、政策规划和使用公共资源等方面西方国家一般优先考虑儿童的利益和需求,从1980年到2001年,虽然很多发达国家的儿童数量减少,但是在儿童及其家庭方面的公共投资都增加了,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不论是对儿童及其家庭的公共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还是花费在每名儿童身上的平均支出都增加了(23)。投资儿童、上游干预、预防为主成为发展型儿童福利政策的核心理念。 (三)家庭、国家和社会应合作承担儿童福利和保护的责任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西方福利改革实质上是对国家与家庭责任界限的再次界定,改变国家干预过多、负担过重的情况,从战略角度给予家庭积极的支持,强化家庭功能和责任。此外,公众对儿童保护机构强制干预家庭的做法提出了严厉批判。20世纪末期,美国公众和学术界对儿童保护服务改革的呼声不断,呼吁政府通过最有效率的方式干预家庭,强调支持家庭及儿童虐待的预防服务(24)。根据《儿童权利公约》第18条的规定,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对儿童成长负有首要责任,国家应向他们履行抚养儿童责任提供适当协助。于是,西方儿童福利政策和实践表现出支持儿童和家庭、寻求与家庭及社区合作的倾向。一些国家努力为父母与社工在儿童保护上的冲突提供协商的条件和机会,在司法权力正式介入之前,努力达到服务机构、儿童、父母三方的一致认同。21世纪初,美国在保护儿童免受虐待和忽视的服务中,表现出建立社区中的合作、提高对受困家庭的支持的积极发展方向(25)。在2000年至2002年之间,法国一些重要的官方文件表明进一步改善儿童福利服务者与家庭之间的关系,更加明确地向着与父母合作的新方向发展(26)。这一时期,西方国家、社会和家庭逐渐形成养育和教育儿童的联盟。 四、对中国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的启示 中国正处于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制度建设的关键时期,理念对于相关政策设计和制度建设起着主导作用,而我国在这方面的理念善不明确。西方儿童福利经历了从“儿童救济”到“儿童保护”,再到“儿童与家庭福利”三个阶段,国家在儿童福利中的角色也由对家庭最小干预的“补充者”到全面干预的“监督者”,改变为现在的有限干预的“支持者”,支持家庭、投资儿童、重视预防的发展型儿童福利政策理念成为主导。西方儿童福利理念和政策的变迁对我国儿童福利的完善有以下启示。 第一,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的发展要有清楚的理念做指导,有助于国家同一时期儿童政策的一致性。我国提出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实际上是从关注孤残儿童扩展到其他困境儿童,仅是对象的简单扩大,且没有包括所有困境儿童,这种制度安排具有明显的工具性,应基于儿童权利和需要而非政府需要,作出制度安排,即使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也应该优先投资儿童。我国目前面临很多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方面的问题,急需明确理念和发展方向,基于发展型儿童福利政策理念,构建中国的儿童福利和保护体系。 第二,“为儿童立法”,制定儿童福利法是发展儿童福利的法律保障。西方国家重视法律先行,而且都制定了儿童福利法和防止虐待儿童法,成为保障儿童福利和权利的重要手段和推动力。我国目前缺乏这样的法律,现有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不仅在儿童保护上原则性规定多,缺乏操作性,而且其内容无法代替儿童福利法。在法制社会里,“为儿童立法”可以提高全社会对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的重视程度,可以更好地保障工作的落实和可持续性。在“儿童优先”原则下,中国儿童福利法的制定应提上议程,改变我国儿童福利长期以来依靠大量政策文件开展工作的状况和“零散补救”的状态。 第三,加强研究和宣传倡导,提升全社会对儿童需要和儿童权利的重视程度,这是发展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的社会基础。国家和公众对儿童、童年、儿童需要及儿童权利认识的进步推动了西方儿童福利理念和政策的演变,在这个过程中,学者和媒体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27)。我国对儿童和童年的研究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儿童权利公约》确立的新儿童观未得到广泛传播,童年期仍被视为只是通往成年的一个阶段,对儿童的关注往往是对其“未来”成才而非“现在”幸福的关注。在此观念影响下,儿童学业负担过重、挨打受骂的现象十分常见,公众的儿童保护意识相对薄弱。因此,我国学术界应该加强对儿童及童年的本土研究、宣传教育和政策倡导。 第四,正确认识儿童、家庭、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明确国家责任,从战略高度重视支持家庭,是建立现代儿童福利制度的理论基础。在我国,“养育儿童是家庭的责任”的观念根深蒂固,国家对家庭的支持力度一直很小,导致家庭养育儿童的负担较重;国家也很少干预家庭,儿童权益未得到全面保护。我国应吸取西方的经验和教训,一方面积极支持家庭,提供现金福利、工作福利和家庭服务,提升家庭功能,使儿童拥有良好的家庭生活环境;另一方面当父母侵犯儿童权益时,国家有权干预家庭,对严重虐待儿童或拒绝履行监护职责的父母依法剥夺其监护权,以收养、寄养或机构养育的方式转移监护权,强调国家、家庭和社会对儿童都负有责任。 第五,把“儿童虐待”作为社会问题来处理,将儿童安全放在首位,是完善儿童保护制度的重要前提。虐待儿童的丑闻只能引起社会对儿童保护的短暂关注,西方国家把儿童虐待建构为“社会问题”以后,才真正推动了在儿童保护方面的立法和干预。由于文化、社会的发展水平及文明程度的差异,西方国家对儿童虐待的认知可能不容易被我国大多数居民接受和认可(28)。我国应该把儿童虐待作为社会问题来预防和干预,而不是仅当儿童重伤或死亡时才作为刑事案件处理,应当明确政府主管部门和工作程序,完善儿童保护体系,避免儿童受到伤害时求助无门或无效。 ①Woodhead,M.& Montgomery,H.,Understanding Childhood: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UK:John Wiley & Sons,2003,pp.55-67. ②⑦Fox Harding,L.,Perspectives in Child Care Policy.Harlow:Longman,1997. ③Archard,D.,Children:Rights and Childhood(2nd Ed.).London:Routledge,2004,p.45. ④吕晓燕:《从汉韦法令看近代英国的儿童福利立法》,《学习与实践》,2011年第10期。 ⑤(26)Grevot,A.,"The Plight of Paternalism in French Child Welfare and Protective Policies and Pratice".In N.Freymond and G.Cameron(Ed.),Towards Positive Systems of Child and Family Welfare: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Child Protection,Family Service,and Community Caring Sstems.CA: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6,pp.151-170. ⑥Lindsey,D.,The Welfare of Children(second edi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⑧Hendrick,H.,Child Welfare:England 1872-1989.London:Routledge,2005,p.29. ⑨(17)Crosson-Tower,C.,Exploring Child Welfare:A Practice Perspective.Boston:Pearson Education,Inc.2004,pp.5-7. ⑩乔东平、谢倩雯:《中美家庭寄养的比较及启示》,《中国青年研究》,2013年第10期。 (11)DiNitto,D.M.,Social Welfare: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6th Ed.).Boston:Pearson Education,Inc.,2007,p.411. (12)程福财:《家庭、国家与儿童福利供给》,《青年研究》,2012年第1期。 (13)Kempe,C.H.,Silverman,F.N.,Steele,B.F.,Droegemuller,W.& Silver,H.K.,The battered-child syndrome.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1962,181,pp.17-24. (14)(20)(24)Waldfogel,J.,The Future of Child Protection:How to Break the Cycle of Abuse and Neglect.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71-109. (15)Spector,M.& Kitsuse,J.I.,Constructing Social Problems.Menlo Park,CA:Benjamin Cummings,1977. (16)D'Cruz,H.,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Child Maltreatment.Journal of Social Work,2004,4(1),pp.99-123. (18)陆士桢:《简论中国儿童福利》,《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6期。 (19)Cameron,G.& Freymond,N.,"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of Child Protection,Family Service,and Community Caring Systems of Child and Family Welfare".In N.Freymond and G.Cameron(Ed.),Towards Positive Systems of Child and Family Welfare: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Child Protection,Family Service,and Community Caring Systems,CA: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6,pp.3-26. (21)Downs,S.W.,Moore,E.& McFadden,E.J.,Child Welfare and Family Services:Policies and Practice.Pearson Education Press,2008,p.243. (22)Hetherington,R.& Nurse,T.,"Promoting Change from ‘Child Protection' to ‘Child and Family Welfare':The Problem of the English System".In N.Freymond and G.Cameron(Ed.),Towards Positive Systems of Child and Family Welfare: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Child Protection,Family Service,and Community Caring Sstems,CA: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6,pp.53-83. (23)Gabel,S.G.& Kamerman,S.B.,Investing in Children:Public Commitment in Twenty-one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Social Service Review,2006,6:pp.239-263. (25)Schene,P.,"Forming and Sustaining Partnerships in Child and Family Welfare:The American Experience".In N.Freymond and G.Cameron(Ed.),Towards Positive Systems of Child and Family Welfare: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Child Protection,Family Service,and Community Caring Systems,CA: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6,pp.84-117. (27)Miller-Perrin,C.L.& Perrin,R.D.,Child Maltreatment:An Introduction(2nd Ed.).CA:Sage Publications,Inc.,2006,pp.12-17. (28)乔东平:《虐待儿童:全球性问题的中国式诠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