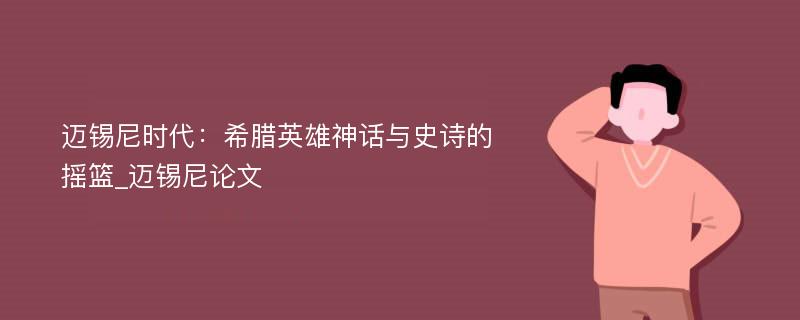
迈锡尼时代——希腊英雄神话和史诗的摇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希腊论文,史诗论文,摇篮论文,神话论文,英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迈锡尼时代(约公元前1600—前1100年)是古希腊史前文化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而特殊的阶段,属于希腊本土青铜文化(希腊底文化)晚期,也是其鼎盛期,其文化持续发展达500年之久。 迈锡尼时代已属文明时代,有自己的文字体系——线形文字B,现已证明是希腊语, 表明迈锡尼文明已属希腊文明的一部分,一个早期发展阶段。由于迈锡尼时代残存的线文B泥版文书绝无该时代政治历史方面的记述,因而, 迈锡尼时代仍属考古上的史前时期。然而,考古展示的迈锡尼世界却是个物质文化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有雄伟的城堡、豪华壮观的宫殿、圆顶墓、精美的壁画、陶器和金属工艺品。王室档案库泥版文书所揭示的希腊本土迈锡尼诸王国的行政和经济管理制度也是相当发达的。这一切表明,迈锡尼社会的文明程度已达到相当的水平。那么,迈锡尼社会的精神生活又如何呢?是否存在一个适合于神话和英雄史诗生存发展的社会环境呢?古希腊英雄神话和史诗最初是在哪个时期形成的?是迈锡尼时代还是稍晚的黑暗时代(约公元前1100—前800年)? 其具体的发展脉络如何?这些都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一、造就英雄的时代
透过华美的物质表象,我们看到迈锡尼社会古朴豪放的另一面。考古实物、造型艺术(壁画、印章、陶器图案等)以及历史时期流传的英雄传说给我们勾勒出一个尚武的贵族武士社会。“独眼巨人”建造的巍峨坚固的城堡、镶金镀银的青铜刀剑、与人同高的8 字形盾牌和矩形盾以及野猪牙头盔、青铜甲胄、战车战马等,处处流露出贵族武士的好战气质。战争狩猎是造型艺术最热中的表现题材:攻城、肉搏、围猎、人兽搏斗的场面屡见不鲜。给人的印象是:迈锡尼社会的上层是一群尚武少文的职业武士,他们是统治者,是战士,以攻城略地、追逐野兽为生活方式,以获取战利品和猎物为生活目的,以炫耀财富、门第和勇武为荣。他们的文化素养、旨趣不一定很高;侍奉他们的是一批有造诣的工匠、画师、识文断字的书记、职业化的宫廷乐手、歌手、通晓仪式的祭司、先知等,他们才是迈锡尼文明的真正缔造者。
迈锡尼时代是个列国纷争的时代,希腊神话讲述的诸王国间的战争或许有某些真实的历史影子。“七雄攻忒拜”的故事反映了迈锡尼时代南北两大强国——迈锡尼和忒拜——争霸的史实。神话还讲述了派罗斯与伊利斯的战争、赫拉克勒斯对派罗斯和伊利斯的征讨、忒拜与俄耳科墨诺斯为争夺彼奥提亚霸权而进行的旷日持久的战争、克里特国王米诺斯对雅典和麦加拉的战争,等等。迈锡尼时代也是海外扩张的时代:阿耳戈英雄夺取金羊毛的历险可能暗示了伊奥尔库斯邦的美尼亚人对黑海的一次商业远征;柏勒洛丰的历险故事表明迈锡尼希腊人开始充当海外雇佣兵;赫拉克勒斯的海外冒险表明迈锡尼王国的扩张足迹已延伸到色雷斯、小亚、北非甚至地中海西部地区;特洛伊战争则是希腊人记忆中迈锡尼人最大的海外军事冒险。考古证实:迈锡尼人确属开放的海上民族,他们的商业和殖民活动遍及地中海东岸地区;西向的商业开发也有迹可寻。狩猎活动也是迈锡尼人热中的生活方式:神话中伟大的英雄也是出色的猎手,如赫拉克勒斯、墨勒阿革洛斯等,甚至还出现了著名的女猎手阿塔兰塔。卡吕冬狩猎野猪的神话汇集了全希腊最伟大的英雄。劫夺偷盗畜群马匹是一种光荣的冒险:赫拉克勒斯劫走色雷斯王的宝马、巨人革律翁的牛群,被认为是建立了盖世的伟业;派罗斯王涅斯托尔少年时偷袭伊利斯,获牛50头,战马150匹,遂扬名世间。 阿伽门农在奥里斯港口集军待发之际,仍忘不了围猎消遣,射杀了阿耳忒弥斯女神的赤牝鹿,结果触怒神明,惹出诸多事端,等等。神话大量充斥的狩猎内容同迈锡尼壁画、印章上所反映的丰富的猎兽场景十分吻合。
这样一个战争频仍、生活方式粗朴豪放、颇具冒险传奇色彩的社会环境,无疑是滋生繁衍英雄传奇故事的深厚土壤。迈锡尼时代是充满冒险和进取精神的时代,迈锡尼人是尚武好战的民族,迈锡尼贵族是自命不凡,以神裔自居,以门第为荣,以战争、狩猎为乐,渴望建功立业、扬名后世的人。有了这样的社会环境,这样的社会成员,这样非凡的生活经验,英雄传奇故事应运而生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二、迈锡尼时代的神话及其证据
迈锡尼时代是造就英雄的时代,有英雄故事滋生的土壤。“迈锡尼时期的主要功绩,在于英雄时代以及种种丰功伟绩的构想之形成。”(注:塞·诺·克雷墨主编:《世界古代神话》,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10页。)迈锡尼贵族们喜欢听歌颂其先王先祖业绩的传奇故事, 也希望自己的业绩流传后世,因而,迈锡尼时代的英雄冒险故事当为数不少,但未必象后世渲染的那样神乎其神。英雄故事多以当代的人物和事件为蓝本进行加工创造,因而尚去事实不远。比如忒拜战争和特洛伊战争,均发生于迈锡尼文明寂亡前一二百年间,尚不可能被加工得十分离奇。只有那些发轫于迈锡尼时代早期或传承更古远的英雄传奇,神幻色彩才更深厚些。迈锡尼时代的英雄故事必有其当代社会的现实基础,但流传到历史时期时已变成离奇荒诞的神话了,其虚构的成分远远超过了写实的成分。即使如此,我们仍能从历史时期的神话中一窥迈锡尼人热中的英雄故事主题:如部落、王朝之间的战争;列国间政治上的纵横捭阖,外交、联姻、结盟以及向敌国避难者提供政治庇护等。对海外的劫掠冒险、海盗式的商业远航、移民迁徙活动、建城故事、狩猎活动、王室内部的倾轧和诸王族的谱系等也是英雄神话热中的主题。从线文B 泥版看,迈锡尼神祗的数量已颇可观,其中1/2为后世神话所熟知,如宙斯、 赫拉、 波赛冬等(注:华尔特·伯克特:《希腊宗教》(WalterBurkert,Greek Religion),哈佛1985年版,第48页。)。 可以想象迈锡尼时代有关神祗的神话也颇可观,可能涉及男神女神的“圣婚”、神秘祭礼的阐释、诸神的谱系和创世神话等。迈锡尼时代是开放的时代,迈锡尼人是开放的民族,印欧的、东方的、前希腊土著的种种神话成分都在这个时代熔炉中相聚合。迈锡尼时代的前两百年是所谓“米诺化”的时代,克里特的神祗、祭礼和神话涌入本土;后三百年是史前希腊本土海外交往的极盛期,是东方神话流入本土的一个重要历史契机。有些社会条件和历史机遇,迈锡尼时代神话的繁荣是完全可能的。然而,如果我们试图寻找该时代直接的神话证据,必定大失所望,所获甚微,这是应作出解释的事实。迈锡尼时代直接神话证据的匮乏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没有同时代的书面神话文献传世。迈锡尼时代虽有文字(线文B),但只用于宫廷账目登记用,绝无政治历史的记录, 更无神话和任何形式的书面文学作品。与同代东方古国相比,迈锡尼社会的统治者们尚武而少文,可能根本就不谙文字,缺乏东方君主的那种文学雅好。迈锡尼世界迄今未发现那种东方式的图书馆。迈锡尼时代的文学可能仅仅停留在口传阶段,神话是以口传方式在宫廷和民间流传的,不著文字。
第二,神话主题的艺术造型有如凤毛麟角,且难以辨别确认。克里特迈锡尼时代的艺术造型,如壁画、印章、雕刻、陶画等,有装饰风格的图案;有自然写实的图案;其中不乏祭礼、战争、狩猎的场景和神灵精怪的形象。一些后世神话熟悉的形象也时有所见,如人身狮首的斯芬克斯、鹰首狮身的格里芬等。然而,反映神话故事情节片段的图景却极鲜见,即使有也意义模糊,难以确认。现知所谓反映神话内容的造型如下:其一,某陶器图案:一男子手执天平状物立于驾御战车的武士前,被解释为荷马史诗《伊利亚得》中的一个场景:宙斯执天平决定特洛伊战争交战双方的命运;其二,登德拉蓝玻璃饰板图案:上刻一妇女骑在公牛背上,被推测是表现宙斯化作白牛诱劫腓尼基公主欧罗芭的场景;其三,登德拉另一饰板,其图案是:一男子面对一头站立的狮子,狮背上似乎长出一颗人头,狮尾很长,马丁·尼尔森(M.Nilsson )相信这是表现英雄柏勒洛丰与女妖喀麦拉搏斗的故事;其四,宝石雕刻图案:两个肯陶洛斯(神话中的马人)各手执一把匕首;其五,克里特印章图案:一男人立船上,似乎正同一跃出海面的海妖搏斗,此妖被当作史诗《奥德赛》中的海妖斯库拉,但神话中描述的斯库拉形象却是长着6 个狗头的怪物;其六,克里特印章:上刻婴儿吮吸山羊奶的图案,似为婴孩儿宙斯在克里特狄克忒山喝山羊奶长大的神话……。马丁·尼尔森曾奠定希腊神话起源于迈锡尼时代的理论,但也承认迈锡尼时代神话艺术造型之匮乏。他指出:“米诺艺术所表现的内容是文化而非神话,迈锡尼艺术则完全照搬前者。”他进而指出:“迈锡尼人有丰富的神话却未付诸于形象,尽管他们的艺术水平很高。这似乎有些令人惊异,但这又非不可想象的事实。同样的情况亦见于几何陶艺术中,后者喜欢描述男人、女人、马匹和船,但并不表现神话场景,尽管晚期有一二例外。几何陶时期亦属荷马时代,神话本来是很丰富的。”(注:马丁·尼尔森:《希腊神话的迈锡尼源泉》(Martin P.Nilsson, The MycenaeanOrigin of Greek Mythology),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32年版, 第32—33页。)
迈锡尼神话证据的匮乏不能证明迈锡尼时代神话本身的匮乏,只能说明迈锡尼时代的神话是口传的,且不习惯于用艺术表现出来。那么,迈锡尼时代神话的口传方式和载体又是什么呢?这是笔者下文探讨的问题。
三、英雄史诗的产生年代
如果迈锡尼社会仍属传统的口传社会,那么,神话的口传文学载体是什么呢?在黑暗时代和古风时代前期,英雄神话的口传载体是史诗(叙事诗)。史诗属口头文学,在民间口头流传,其传承者是职业化的诗人歌手。30年代美国学者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曾对南斯拉夫乡村口传史诗进行考察,并将考察结果推广到荷马史诗的研究,结论是:古希腊史诗的语言单元不是单个的词,而是合乎韵律的现成的格式化套语。这些现成的套语构成一个语库,供职业歌手们在表演吟唱时随机取用,即兴创作,灵活快捷,又便于长期记忆。古希腊的英雄史诗主要以迈锡尼时代的历史事件——忒拜战争和特洛伊战争为素材,形成所谓诗组(cycle epics)。古风前期,经荷马等大诗人的加工整理, 英雄史诗趋于定型,此前曾经历了漫长的流传加工过程,年代颇久远,至少可以追溯到黑暗时代。是否能把史诗的源头追溯得更古远呢?这就引起了学术界的争议。米尔曼·帕里的研究表明:史诗的格式化套语相当古老,必经历了漫长的积累过程。然而,帕里只关心史诗的形成方式,并不关心史诗起源的断代问题。在荷马史诗中,迈锡尼时代的历史、语言、文化遗迹时有所见,如反映迈锡尼时代政治地理格局的“荷马船表”、埃阿斯使用的“大如城楼的盾牌”、野猪牙头盔、“涅斯托尔的金杯”、“饰银钉的宝剑”等,均得到考古的证实。因而,早在本世纪30年代初,尼尔森就曾独立地断言:“史诗经历了相当长的发展时间,可回溯到迈锡尼时代的早期,史诗中夹杂的迈锡尼成分已证明了这个事实。”(注:马丁·尼尔森:《希腊神话的迈锡尼源泉》,第24页。)此后,他又借助帕里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其新著《荷马与迈锡尼》(1933)中进一步论证荷马语言的古老,史诗包含着迈锡尼时代真正的历史文化信息(注:约阿基姆·拉塔兹主编:《荷马》(Herausgegeben von Joachim,Homer Latacz,Tradition und Neuerung), 达尔姆斯塔德特1979年版,第502页。),可以说,将史诗的产生溯源于迈锡尼时代,其奠基者是尼尔森。
英国古典学者丹尼斯·帕格(Denys Page)支持这种看法,认为荷马史诗经数百年流传,诗句中仍保存着迈锡尼早期(约公元前16世纪)的遗迹,唯一可能的解释是:史诗仍沿用着古老的格式化套语,“它证实了史诗的古远性,同时确保了来自遥远往昔的事实和幻想得以世代延存。”他举出的有趣例证是史诗《伊利亚得》中的希腊英雄埃阿斯使用的盾牌。史诗共有170处描述盾牌,涉及100多位有名姓的阿卡亚武士,但没有一位使用埃阿斯那样的“大如城楼的”“裹着七层生牛皮的”几乎遮住全身的大盾。而考古证实:只有迈锡尼时代早期(约前16世纪)才流行使用这种大盾,特洛伊战争时期(约前13世纪)早已不再流行。“这种记忆历经黑暗世代仍保留于我们的《伊利亚得》中,只能靠口头创作连续传诵的希腊史诗为媒介”,“希腊史诗因而在迈锡尼时代就已被创作着。”由于大盾牌只同埃阿斯一人的名字相关联,因而“传说不仅保留了迈锡尼式的盾牌,还记住了它的使用者,一对分不开的搭档。”帕格进而推断:“如果埃阿斯和他的盾牌是分不开的,那么,埃阿斯这个人应在这种大盾流行时期就被诗歌吟颂,远在特洛伊战争之前;而特洛伊战争这块磁石将这位更古老的冒险英雄也吸收进来。”帕格进而证明:在“荷马船表”中埃阿斯是唯一没列出领地的诸侯,这并非偶然。帕格通过这个例子证明史诗的古老,史诗的格式化套语是远古历史文化信息的语言化石(注:丹尼斯·帕格:《历史和荷马的伊利亚得》(Denys L.Page,History and the Honeric Iliad),加利福尼亚出版社1959年版,第222、233—238页。)。尼尔森、 帕格的观点在目前不乏支持者。威斯特(M.L.West)在其《希腊史诗的产生》一文中即指出:“希腊的史诗传统至少回溯到迈锡尼时代晚期几乎是人人接受的观点。事实上,有理由认为,史诗早在(公元前)15世纪即已存在,而且在此之前,尚有一个古老的诗歌传统,在某种意义上是属于英雄性质的,可追溯于一个印欧根基。那么,在某种意义上,希腊史诗的兴起不得不追溯到不晚于两千纪中期。”(注:威斯特:《希腊史诗的兴起》(M.L.West,The Rise of the Greek Epic ), 《希腊研究杂志》(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第108期(1988),第151页。)
然而,史诗的迈锡尼起源论并非“几乎是人人接受的观点”。著名学者杰弗里·柯克(Geoffrey S.Kirk )即主张史诗形成于“黑暗时代”。他认为史诗起源于迈锡尼时代的证据不足,荷马史诗中可确证的迈锡尼语言文化遗存十分有限,无法证明史诗直接传承于迈锡尼时代。他指出:如果荷马史诗形成于青铜时代,就不可能对当时的战争状态和宫廷生活有严重失实的描述。例如,荷马不懂战车的实战作用,只将之描述为将领们的代步乘具;对宫殿的国家经济管理职能也茫然不知。柯克因而认为:迈锡尼时代不大可能有史诗流传,传世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迈锡尼时代的英雄传奇故事,如忒拜、特洛伊战争的故事,可能以非诗歌的讲故事的方式(散文方式)通过青铜末纪劫后余生的迈锡尼遗民一代代延存下来。这种散文式的故事也能将某些古老的词汇、套语、地名等保留于记忆中,但难以持久,一般传承两三代就模糊变形了。因而,迈锡尼时代的英雄故事经两三代非诗歌的散文式流传,在黑暗时代之初只剩下故事的梗概、框架。于是,黑暗时代的口传诗人发明了便于记忆的六步韵史诗诗体,将那些濒于遗忘的传统情节抢救记录下来,进行艺术上的再创作,赋予大量想象创新的成分,融入了黑暗时代社会本身的内容,经过几百年的口头加工,最终发展成我们所知的荷马史诗模样。总而言之,荷马史诗是黑暗时代的产物,并非直接传承于迈锡尼时代(注:详见杰弗里·柯克:《荷马与史诗——〈荷马之歌〉缩写本》(Geoffrey S.Kirk,Homer and the Epic,a Shortened Version of 'The Songs of Homer'),剑桥1965年版,第63—82页。)
笔者认为:迈锡尼时代存在口传英雄叙事诗的可能性是有的。比较语言学力图证明:印欧语族有古老的诗歌传统。古印度吠陀史诗和希腊的荷马史诗均有“不可磨灭的荣耀”、“男人的荣耀”、“赐福祉者”等格式化套语,表明古印欧社会可能存在“英雄诗”和“颂神诗”(注:简·布里摩尔主编:《希腊神话解析》(Jan Bremmer,Interpretations of Greek Mythology),伦敦和悉尼1987年版,第2页;华尔特·伯克特:《希腊宗教》,第17页。)。如果比较语言学的结论可靠,那么,作为印欧人一支的迈锡尼希腊人,茫然不知诗为何物,总有些讲不通。格式化的口传叙事诗(史诗)是文盲社会传播神话的有效载体,迈锡尼社会已属文明时代,但尚未发现文字记录的诗歌存在,说明迈锡尼社会亦属口传社会,其口传诗歌尚未书面化,但并不等于没有诗歌。“青铜时代无须把诗诉诸文字;山上的缪斯是足以捍卫事实和真理的,记忆则是诗人最大的天赋。”(注:埃米莉·沃尔缪勒:《青铜时代的希腊》(Emily Vermeule,Greece in the Bronze Age),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308页。 )考古证明:古爱琴世界有着悠久的诗歌音乐传统,基克拉迪文化的大理石竖琴手、长笛手;克里特石棺壁画上的七弦琴手、双管笛手;派罗斯宫殿中的“俄耳甫斯壁画”均能说明之。其中“俄耳甫斯壁画”的造型是:一位祭司装束的乐师坐在岩石上抚琴而歌,一只飞鸟似被动人的音乐所吸引,徘徊不去。此外,还有一些青铜、象牙的乐器模型出土。音乐的存在表明诗歌的存在,后者吟唱时是需要音乐伴奏的。埃米莉·沃尔缪勒(Emily Vermeule)称:迈锡尼社会的歌手们有业余专业之分。派罗斯壁画上的歌手从打扮装束看是位职业歌手(注:埃米莉·沃尔缪勒:《青铜时代的希腊》,第308页。)。他们服务于国王、贵族和大众,在宫廷、市场或节日祭典等场合表演;服务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婚、丧、嫁、娶、祭礼、丰收等;演唱的内容很广泛,可能包括颂神诗和英雄传说,后者最受宫廷和贵族的欣赏。权贵们对讲述其家族先祖功业、荣耀、谱系、蒙神恩眷顾的内容情有独钟。迈锡尼的宫廷、贵族可能有自己的御用歌手,专门从事英雄故事的创作和表演。权贵们虽然尚武轻文,但对欣赏英雄史诗这种古朴的娱乐方式还是乐此不疲的。再加上迈锡尼社会大量现实的英雄素材需要表现,古老的英雄素材需要传承,一种便于记忆的格式化的叙事诗体,其存在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迈锡尼时代的英雄史诗即使存在,传至黑暗时代时也早已面目全非了。口传的内容是恒常变化的,极不稳定的,每次表演都有所改动、创新。尽管史诗的格式化套语沿袭古远,但随着社会的变迁,旧的格式化套语不时兴了,自然也会被淘汰,因而,纯属迈锡尼时代的格式化套语必定所遗甚少;而且,更多的套语是一般性的,并不局限于某个特定时代;迈锡尼方言(阿卡亚——塞浦路斯方言)风格的史诗语言也逐渐转变成伊奥利亚或爱奥尼亚方言风格的史诗语言。传说的大量情节被删改、被淡忘;新的内容不断加入;原有的故事结构也不断被调整,被重新组合。于是,当我们看到荷马的史诗版本时,史诗内容已同迈锡尼时代英雄故事的原貌相去甚远了。迈锡尼社会留给我们的英雄故事只是一个框架,一个梗概,一个传统素材,更多的则是新增益的内容。诚如埃米莉·沃尔缪勒所言:“荷马所重述的很多神话的本源是迈锡尼的,因为它们讲的是青铜时代的人民和城镇。然而,我们可以确信:这些神话的荷马版本并不是迈锡尼人所知的版本,因为神话每次讲述时都有所改动,而且不断地被改进,使之更‘现代化’和更‘富有意义’”。(注:埃米莉·沃尔缪勒:《青铜时代的希腊》,第311页。)
英雄史诗是发源于迈锡尼时代还是发源于黑暗时代,学术界仍有争议。柯克的看法自有其道理。只要没有史诗存在于迈锡尼时代的直接证据,争论将持续下去。柯克本人也没有完全排除迈锡尼时代存在史诗的可能性,但他强调:即使迈锡尼时代有史诗,也没有以任何书面的或细节的形式大量保留到黑暗时代(注:柯克:《荷马的诗歌》(Geoffrey S.Kirk,The Songs of Homer),剑桥1977年重印, 第125页。),荷马史诗是黑暗时代的发明,迈锡尼史诗与历史时期的荷马史诗不存在任何连续性。若真如此,讨论迈锡尼史诗的意义也就不大了。
四、黑暗时代英雄神话和史诗的发展
为了说明迈锡尼时代到黑暗时代这个希腊社会历史转型时期神话和史诗发展的连续性,笔者将在本文的末尾对黑暗时代的神话和史诗发展作简要分析如下:
“黑暗时代”(约公元前1100—前800 年)是古希腊文化发展相对停滞的时期。迈锡尼文明的毁灭,多利亚人的入侵,使希腊社会陷入动荡不宁的状态,引发了一批批海外移民浪潮。伴随着移民潮,迈锡尼时代的神话与英雄传奇也随之飘洋过海,在小亚西海岸的伊奥利亚和爱奥尼亚地区以及爱琴诸岛上扎下了根,经一些职业化歌手的世代加工传唱,以英雄史诗的面目流传于民间。英雄史诗主要以迈锡尼时代的忒拜、特洛伊战争为主线展开情节,吸收了民间流传的大量英雄传奇和神祗故事,终于荟萃成蔚为大观的史诗诗组,荷马的《伊利亚得》和《奥德赛》则是其中的杰作。据传这两部史诗出自开俄斯岛盲诗人荷马之妙手加工,在公元前8世纪中晚期基本定型。其余史诗则是在公元前7——前6 世纪被口传诗人们加工整理成型,陆续形成文字。史诗是否起源于迈锡尼时代目前尚无定论,笔者倾向于肯定迈锡尼史诗的存在,但迈锡尼史诗和荷马史诗的联系只是神话主题和素材上的联系,而不是诗文上的联系;或者说,它们是同一主题和素材的不同版本。荷马史诗所保留的典型迈锡尼词汇毕竟十分有限。迈锡尼史诗能完整保留到黑暗时代的段落必定微乎其微,哪怕是极小的一部分。荷马史诗只是继承了迈锡尼史诗的主题和素材;在具体内容上,荷马史诗的创新成分远远超过了从迈锡尼史诗直接继承的成分,更多的内容是黑暗时代口传诗人们根据他们自己对青铜时代的理解、想象而新增益的。黑暗时代的希腊人从青铜末纪的社会动荡中劫后余生,经历了奔波迁徙之苦,在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生存下来,生活艰难困苦。他们对生活感到绝望,对自己生存的时代兴趣索然。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他们去记忆和歌颂,甚至到了古风时代,大诗人赫西俄德仍为自己不幸降生于黑铁时代而悲哀(注: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6页。)。然而, 尽管黑暗时代希腊人过着贫乏的物质文化生活,目不识丁,但精神世界并非一片空白。他们仍沉湎于对青铜时代先祖丰功伟绩的追忆和幻想中;怀念阿伽门农王统治下的国力强大、物质繁华的迈锡尼帝国。他们是厚古薄今的一代,以传诵先辈英雄的伟业为精神寄托。由于事过境迁,记忆朦胧,对迈锡尼时代的神秘感和崇敬感与日俱增,在黑暗时代希腊人的心目中,迈锡尼时代犹如一个神话时代,迈锡尼时代的贵族武士们则是“神一般的比较高贵公正的英雄种族”,是建立了不朽功业的一个种族;而黑暗时代希腊人自己则是被神遗弃的“黑铁种族”(注: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第6页。)。于是,一个充满奇幻色彩的、理想化、半历史、 半神话、半现实的英雄世界在黑暗时代文盲诗人富有想象力的头脑中被创造出来。迈锡尼时代提供了英雄传奇的蓝本和素材,这些素材在黑暗时代被加工成神话。然而,尽管黑暗时代的希腊人鄙视他们生存的时代,但他们还是不自觉地以自己时代的社会现实和生活经验去构思青铜时代先辈的世界。在荷马史诗中,迈锡尼的圆顶墓不见了,精美的壁画消失了,却出现了青铜时代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如铁器、火葬等。迈锡尼英雄们则通通变成了文盲。“阿喀琉斯的盾牌”所体现的精湛的金属镶嵌工艺是迈锡尼时代早期的技术水平,而盾牌图案所描绘的却是黑暗时代的现实生活。黑暗时代的军事民主制被移植到远征特洛伊的阿卡亚人远征军中。
英雄史诗是在小亚沿岸的移民地区发展起来的。移民中有爱奥尼亚人、伊奥利亚人,他们从希腊本土带来了各自部落的英雄传奇和神祗故事。这些故事大都会聚在特洛伊战争这一共同的神话主题下。荷马史诗的语言以爱奥尼亚方言为主,兼有少量伊奥利亚和阿卡狄亚的方言成分,后两种方言在迈锡尼时代分别是希腊北部和南部的方言。一些学者推断:史诗在希腊本土先经历了一个伊奥利亚方言和阿卡狄亚方言的加工发展阶段。随着多利亚人的南侵,讲伊奥利亚和阿卡狄亚方言的人携带着他们的英雄史诗迁移到小亚地区,与讲爱奥尼亚方言的人相比邻。爱奥尼亚的职业歌手们将伊奥利亚—阿卡狄亚方言的史诗继承下来,进一步充实发展,形成爱奥尼亚方言的史诗,后者至公元前8 世纪臻于成熟。史诗中残存的伊奥利亚、阿卡狄亚方言成分以及伊奥利亚英雄在史诗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如色萨利英雄阿喀琉斯),均支持这种假说。另有学者认为:爱奥尼亚方言与阿卡狄亚方言极接近,在迈锡尼时代,两者同属一种方言,在希腊南部的伯罗奔尼撒半岛流行。多利亚人侵入半岛后,部分迈锡尼土著留在阿卡狄亚山区,依旧讲自己的方言,被称作“阿卡狄亚人”;另一些人向外地移民,其中包括派罗斯亡国后逃难的王族成员。他们经雅典向小亚的爱奥尼亚地区殖民,是为“爱奥尼亚人”,他们的方言也逐渐偏离了阿卡狄亚方言。爱奥尼亚人的史诗是他们从家乡(伯罗奔尼撒半岛)带来的,而不是从伊奥利亚人那里移植来的。当然,爱奥尼亚人吸收了伊奥利亚史诗的某些词汇、人物和情节。伊奥利亚、爱奥尼亚两地的史诗并无继承关系,而是平行发展,交互影响的。荷马史诗是在吸收北部伊奥利亚史诗成分的基础上,在爱奥尼亚地区独立发展起来的。(注:参见柯克:《荷马与史诗——〈荷马之歌〉缩写本》,第82—90页;威斯特:《希腊史诗的兴起》,《希腊研究杂志》第108期(1988),第162—165页; 简·罗里摩尔:《荷马与遗迹》(H.L.Lorimer,Homer and the Monuments),伦敦1950年版,第459—461页;帕格:《历史和荷马的伊利亚得》,第219—221页。)
悠悠300年的黑暗时代,一个无文字的文盲社会, 一个传统的口传社会,却奠定了后世神话的基础。它上承迈锡尼青铜时代的原始神话素材,下启历史时期希腊神话的繁荣,史诗则充当了重要的神话口传载体。我们可以说,迈锡尼时代是英雄神话和史诗的摇篮;黑暗时代则是英雄神话和史诗的主要形成时期。黑暗时代的神话和史诗,其内容是不稳定的,恒常变动的,这是口传社会的特征。进入文明时代后,史诗、神话的内容逐渐固定下来,陆续形成文字,转化为书面文学形式,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希腊神话和荷马史诗。
标签:迈锡尼论文; 神话论文; 史诗论文; 希腊历史论文; 荷马史诗论文; 希腊移民论文; 特洛伊论文; 青铜时代论文; 黑暗时代论文; 诗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