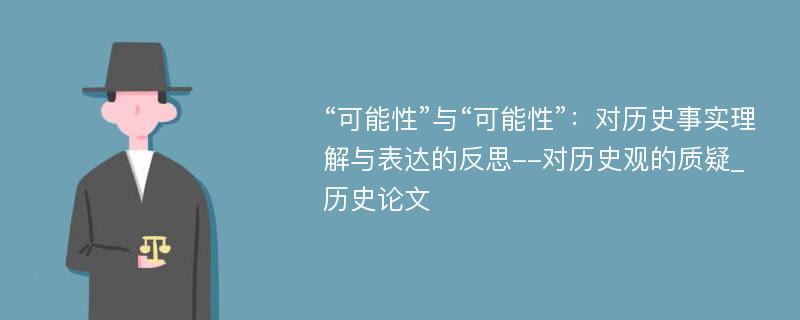
“可能”与“可能性”:关于历史事实认识与表述的思考——对一种史学观的质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可能性论文,事实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曾业英先生在“评‘192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以下简称“曾文”)中坦率谈了对一些论文的意见,并以较多笔墨表达了自己的史观。他写道:“‘还原’、‘再现’历史真实,是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的共同追求”。就某篇用了较多“可能”的论文,他评论道:“学术论文是科学,不是文学创作,是不能虚构和想像的,也不是简单的推理所能奏效的,必须经过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严谨、周密的论证,才立得起、站得住,……模棱两可的推测,未能给人留下一种‘事实俱在,不由你不信’的踏实感觉。……‘大胆假设’,尚需‘小心求证’,科学结论必须建立在充分的有事实根据的论证基础之上。遗憾的是通观全文,不但缺少这样的论证,且作者自己也似底气不足,不敢断然肯定这些认识是否真实可靠”。据他看,另一篇论文,只顾追求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创新,但“作者的取向和解读,与历史真实,差距甚远。”接下来,曾文指出:“不管你采用什么新方法,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寻求、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并不是为了标新立异,改变历史的本来面目,而历史的本来面目也只有一个,而且是永恒不变的。”①
读后,我们感到曾文提出了十分重要的史学观问题,具体而言,即史学能否“还原”、“再现”和“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除了所谓“实证研究”,可否及如何运用想像和推测;史学论著应否使用带有“可能”的叙述以及提出某种情况的“可能性”等问题。这些恰恰也是近年来令我们感到困惑并深入思考和探讨的问题。本来我们探索这类史学理论问题只是想求得自己心里明白,但近来发现在国内史学界,这些问题已经到了无法回避、亟应弄清的地步了。有曾先生对学术批评和争论的大力倡导和示范,我们不揣冒昧在此就上述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② 并顺便将近来学习有关理论的若干心得结合研究实践的体会与大家交流,祈望指正。为缩小范围,本文以可能判断与表述为主线展开讨论。但深入追究下去,便要探讨如何理解、认识历史真实等问题;上升至哲学高度,就涉及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对惯于在地上爬(指从事史学研究)的我们,一下子到天上去飞(指探讨理论问题)显然困难重重。这里要申明,本文所摘引的一些论述都是东一点西一点择取的,没有系统,甚至出自被视为对立体系的理论家。但不管这些理论家之间的分歧和其自身在理论上可能具有的矛盾,只要我们觉得某人的某些话有道理,有助于阐明自己的论点,便拿来为我所用,就算是“喜鹊方法”(magpie approach)③ 吧。
二、“可能”、“可能性”与“必然”、“不可能”之对比
“可能”与“可能性”可以在逻辑学、法理学、认识论等多种学科上来理解和研究,这里我们决无全面探讨的企图,只想在与历史研究有关的范围内来讨论。可能性涉及有可能的事、可能的状态、潜在的选择、关于可能的观念等。任何客观事物的发展往往包含各种可能性。黑格尔认为,“实在的可能性是实际存在的各种与其有关条件的总和,就其是实在的而言,可以说它本身就是现实。”“可能”带有能成为事实的属性,含有“并非不可能”的意思。某种可能性具备了一定条件可以转化为现实性,因而可能性是潜在的、尚未展开的现实性。④ 人们的思维及其表达反映了客观事物发展有多种可能性、及事物可能具有多种属性的情况。
“暂时的可能”常应用于关于过去真实的问题。波普尔认为,“在人类事物上,任何情况是都是可能的。”⑤ 历史的进程中有着很多不确定因素,充满了各种偶然、随机、独特的事件;历史人物的背景、心理、动机及其所处的环境、条件等提供了行动的诸多可能性;历史并不沿着一个设定的模式发展,也不是直线平面地演变;历史运动是多面向、多线条、多层次的。正如吴志翔用文学语言描述的那样,“历史之流绝非清澈而是始终有些浑浊的,历史之树绝非如修剪过后那般整齐而是枝枝桠桠的,历史之路绝非曾经以为的那样‘非如此不可’而是充满了种种别的可能性的。”⑥ 何兆武甚至指出,历史研究“不能局限于只研究已经在现实世界中出现了的现实”,而应当“把眼界扩大到既成事实之外的一切可能性”,并形成包括“可能世界”在内的历史构图。⑦ 本文主旨不在讨论何文已经阐述得十分透彻的关于反史实的可能性,而着力于那些一般人们认为已经发生过的历史事实认识与表述的探讨。
为了对过去发生过的事有所认识,史学研究时时涉及对各种各样的判断。有的学者认为历史事实本身也是“以判断的形式呈现的”。⑧ 韦伯指出,“可能会发生”涉及历史事实重建的关键因素,“在史书的每一行之中,尤其每一档案或资料之选择刊行,都会,或者更确切地说,必定会发现‘可能状况的判断’”。⑨
判断是以命题这种语言形式表达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就命题写了如下的话:用以表达思想的命题是对可能事态进行描述的实在的图像;命题包括被投影者的可能性,而不是被投影者本身;命题具有本质特征和偶然特征,其真是可能的。在人们关于一个事实的知识不完全但却又知道一些东西的这种缺少确定性的情况下需要使用概率命题,对特定事件的发生给予某一概率度。⑩
按照笔者对此的理解并应用于史学上就是,在资料比较充足、情况基本弄清楚的情况下,史家所作的对实在事态的判断及其表达—命题的真尽管无法保证,而仅仅是可能的,也不必随处使用概率;但在资料不足以确知某历史活动和事件及其发生的原因、或在资料分歧且无法判断哪些资料准确等情况下,就需要依据已有的知识和已知的线索、根据一定规则作出推测。这时,在文字表达上就不免使用“可能”、“大概”、“也许”、“或者”、“似乎”等表示一定概率度的语词。为使读者了解在何者境况下(这里排除被视为史学的一项功能的预测未来的情形)史学研究者会用到这类语词,兹举若干史学著述中偶然读到的语句为例:
陈子展写道:“《天问》所问,其中许多可能根据了古本《山海经》或《山海经》同类的文献”。(11) 钟敬文认为楚诗人屈原之能写出《天问》,大概是因他熟悉南方采用问答体歌词的民俗。(12)《奥德赛》中译本前言申明,荷马史诗中的有些地名“可能是历史上曾经有过、以后随着所指地点的消失而逐渐消亡的地理名称。”(13) 拉迪里的《历史学家的思想和方法》(14) 第60页有两个“可能”,再往前翻两页,又找到三个“可能”。他用以表达法国南部于1347—1348年爆发流行性肺炎和淋巴鼠疫的“可能原因”和“不确定因素”。(15) 马克思论及欧洲封建制下农奴逃亡的情况时写道,由于农奴对封建主的赋役降低到中等水平的代役租和徭役地租,“就使农奴有可能积累一些动产,便于从他的领主那里逃跑出来,并使他有可能去当市民”,还推断“掌握了某种手艺的农奴获得动产的可能性最大。”(16) 柏林在“休谟和德国反理性主义的起源”中推测哈曼“很可能是在早年逗留伦敦期间”读过休谟的《人性论》;并说哈曼很可能是本着某种精神而着手翻译休谟著《自然宗教对话录》的。(17) 伯纳尔认为康有为《大同书》中的一些想法可能于1891年后形成,并且可能受到了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的刊物中所介绍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18) 肖超然认为印有北大“亢慕义斋”的八本德文书“极有可能是威氏和随后来华的其他共产国际代表秘密送给李大钊同志和马克斯学说研究会的。也有可能是马克斯学说研究会通过其他途径向共产国际出版机构秘密订购的。”(19)
在中外历史著述中,这类例子俯拾皆是,不胜枚举。
我们检视自己的论文,发现也用了不少“可能”、“大概”,兹举其要:在“苏俄在华发表的第一个文件”里推测符拉迪沃斯托克苏维埃对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1918年的二月指示“作了若干更动的可能性较大。”(20)“《上海俄文生活报》与布尔什维克早期在华活动”一文列举几种关于《上海俄文生活报》报社地址的不同记载后,用了“可能”、“大概”来讨论各种可能的情形。(21) 在“霍多洛夫与苏俄在华最早设立的通讯社”里根据霍多洛夫曾于1920年春从天津去过上海等记载,提出“李立三所说的那个曾与陈独秀一同到上海讨论组党的共产国际在天津的通讯社人员非常可能是霍多洛夫。”(22)
经仔细考量,上举数例中的“可能”、“大概”等词汇均不能去掉。因为史学家必须遵循的一条基本道德规则就是其声言发现的东西不要超越证据所能证明的。(23) 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如果对历史上的不确定情况或因素作肯定判断和陈述,便会流于武断。体味上述数例,除上举报社地址之例是在资料较多且存在歧义的情况下作出的选言判断,其余均是在资料不足的情况下,在探讨过去的事实和原因及追溯思想渊源时作出的或然判断。
断定事物可能性的或然判断又称可能判断,它属于一种模态判断,与其相应的是实然判断和必然判断,它们分别反映了客观事物之间以及事物与其属性之间联系的程度。休谟曾指出,或然判断可以用来表示确定性的种种不同程度,其判断的或然程度愈大,则它的确定程度愈增,愈少则它的确定性愈减;具有或多或少的或然性的判断无论在科学中或在实际生活中经常可以见到的。(24) 必然判断反映的是关于自然和社会的规律性的认识,对于以过去发生的独特、偶然的事件为研究对象的史学来说,实然与或然判断更为建构关于过去的实在图像所需。
历史陈述是目前无法直接观察的事实陈述。然而,某些历史著作中常见“必然”、“一定”、“肯定”、“确实”、“不可避免”等语词构成的必然陈述,或在没有事实根据的情况下用实然陈述。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里充斥着如下语句:“基洛夫同志被刺事件,就是由这一联合的托洛茨基、布哈林匪帮干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滚进反苏维埃泥潭的事实已是不容置疑的了。……他们既已抱定破坏布尔什维克党的目的,也就必然要滚到破坏苏维埃国家的道路”。(25) 现在人们已经知道,这些都是斯大林对其政治对手的诬陷和栽赃,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毫无任何真实性可言。遗憾的是,多年来国内有些学者对这类武断言说和充满必然判断的宏大叙事似乎习以为常,并在写作中对于没有充分根据的事也用必然或实然判断的表述,譬如写“从夏禹到夏启,劳动者的劳动所得个人消费后肯定有积余。”(26) 社会主义研究社的性质“自然不是党的组织”,并且该社“自然设在陈独秀寓所内。”(27)“王明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成员和共产国际派回的代表,毛泽东理应是非常重视的;……自然希望搞好关系,与其同心同德,协力工作。”(28)
上述文字实际上均表达了作者的推断,虽然其中有些可能是符合客观情况的真的判断,但作出这种判断的理由却不充分,使用的判断形式也不恰当。这是因为,我们不能够说过去的事只能这样、不能那样存在或发展,从而完全排除其他可能的情况;再者,历史上没有由于另外某个事件的发生,一个事件就必定会发生的强制性,并且这种因果关系的推论也无法被证明为正确;其次,如果资料缺乏时,不应当用必然判断,而资料很充分时则没有必要用任何模态词来推断。况且,每个命题(即表达判断的语言形式,如“孙中山是同盟会领袖”)已经具有一个意义,“肯定并不能给命题以意义”,再用“显然”、“一定”、“自然”等词就显得多余。(29) 克里普克指出,人们对于必然事实不能提出充要条件;“必然的”问题实为单纯形而上学问题;而不依靠经验资料而得到的所谓先天的知识,根本不需要“必然”等模态词。(30) 那种以决然语气描述历史上不很确定的情况的语句,除了显示述者的自信和武断,没有给所述增添任何可靠性,并让读者产生踏实感觉。至少我们遇到这类词语时总感到有些可疑。
史学家卡尔曾搜寻自己早年著作中令人不适的刺眼词汇,并举例检讨说,如果把“1917年革命后,布尔什维克与东正教教会的冲突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中的" inevitable" 改为" extremely probable" (极有可能)则更为明智。他认为,史学家应当讨论各种可能的选择,避免使用“不可避免的”(inevitable,unavoidable)、“无可逃避的”(inescapable)甚至“难免的”(ineluctable)这类词汇。(31)
“可能”的反义词是“不可能”,它也是一种必然判断的用语,常用于无论事实的真或假它都为假的矛盾式命题。我们不妨举一个含有这种用语的例子:
向青曾写道:“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中俄交通便陷于完全断绝,两国关系断绝了,两国之间的革命,更不可能有任何联系。”当其他学者根据一些史料对其“维经斯基使华是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建立联系的起点”的论点表示质疑时,向青逐一否定了这些资料的可靠性。比如对王若飞报告中所谈“1919年共产国际就派人到中国来了,起初是苏联华俄通讯社社长,以后有巴克京春到中国来组党”,他认为王若飞根本不会知道这些事,并断言1919年华俄通讯社社长“不可能在中国出现”。(32)
这些用决然语气写成的话,其真实性又如何呢?我们因认为王若飞说的事可能是有的,便以此为线索,努力寻找各种资料,终于弄清“巴克京春”就是曾任韩人社会党总书记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的朝鲜人朴镇淳。1919、1920年他确曾两度来华试图用共产国际经费在中国建立共产党并指导远东共产主义运动;(33) 并证实1919年来华的俄华通讯社社长是罗斯塔社首任驻华分社经理霍多洛夫。(34) 后来公布的苏俄档案证实了我们所写的符合历史实际,而向青用必然陈述作出的结论却是不对的。
从以上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抱持可能性的心态进行研究,便不会轻易否定一些看似不可信的史料,而会视其可能蕴含一定程度的真实性,这样就有可能探寻到被遮掩的前人留下的若有若无的脚印。一般说来,要能“发前人未发之覆”,不仅需要以更大努力来挖掘稀少资料,有时还需要在忠实于基本史料的基础上对不明情况进行推论。这样作出的描述和结论或许会让某些人读起来感觉不那么踏实,但对缺乏证据的事作必然陈述,尽管底气十足,却往往距离历史真实更远。断言历史上某事不可能发生的人,多囿于先入为主之见,常常只承认或乐于沿用前人著作中引用过的那么几则史料,并因袭权威的、流行的说法和观点,因而面对呈现出“分叉的历史”的史料和据此提出的观点往往采取排斥态度。比如向青就称自己的观点是“老一辈革命家和中外历史学家所公认的。这不是我们想要突破就能突破的。”然从他驳斥王若飞和其他历史学者的说法便可知道,其观点并非为老一辈革命家和中外历史学家所公认,只不过是想借此说明历史真相已被自己掌握。持有这种心态的史学家不乏其人。最近有位党史学家就断然否定叶剑英就西安事变某些情况口述回忆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可信性,表示“听之则可,信则未必”。因为他认为“真相并非如此”,并且坚称:“真理只有一个”。(35) 这里,我们遇到了什么是历史真相以及真理的问题。
三、历史事实与真理
把事实、真相认作真理并不妥,因为事实与真理在中文里意思差异很大。据《现代汉语词典》,事实与真相均为“事情的真实情况”;真理则指“真实的道理,即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人的意识中的正确反映。”不过,这几个词都涉及“事实”,因而彼此密切相关。历史似乎与真理特别有缘,希腊文的“历史”(historia)初义为“真理的寻求”;(36) 西塞罗曾把历史表述为“真理的光芒”;(37) 史学家艾尔顿认为“历史研究近于追寻真理。”(38) 的确,弄清过去的真相以及探求历史揭示的“真理”是历史学的重要任务。
然而,自古以来对真理问题就争论不休,相应地,历史学家们对历史真确性也持有不同信仰。到了现代,早先那种认为知识具有确定性和科学能提供绝对真理的观念,已经被知识和真理的暂定性、相对性所取代。随着观念的变化,甚至“事实”、“实在”也不再像过去那样不容置疑了。牛津词典将事实的定义从“一个经验的资料”发展成也是“推论的证据”的双重含义。(39) 早有学者指出,历史的真确性仅是“为人类所确信的事情”,因此,“历史研究不是位于纯粹理性的王国,而是位于人类意志、观点和可能性的王国。”(40) 历史事实成为史家据以构成不同历史图像的数据、线索。
曾文认为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历史的本来面目”,并以一座3000米高的山作比喻,说这座山尽管从不同角度观察“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但它仍是一座3000米的高山。我们就借这个比喻(41) 入手来展开讨论。
说一座山3000米高,只是描述了这座山所具有的一个短暂的表象——高度。由于地壳的水平运动和升降运动、外营力和内营力的相互作用、以及风雨对顶部岩石的侵蚀以及冰雪的积聚和消融,山的高度在不断变化。比如珠穆朗玛峰在1852年测得高度为8,882米,1975年为8,848米,下一次测量结果大概又会不同。若从更长远的过去看,喜马拉雅山所在之处曾是一片海洋,3000万年前才开始从海底升起。所以只能说某座山在被测量时曾经是3000米,或说它在一段时间内大约是3000米,而不能把3000米认作山永恒不变的本来面目。况且,山的高度并没有涉及山的其他表现形态和它的内部结构等。地质、矿物、地理、地貌、生物、考古等专家会对一座山进行各种项目的考察、研究,对他们来说,该山的面目并不相同。一个外行人观察山,也会看到山峰有时呈现出洁白色,有时则为粉红色等。哪种颜色的描述是正确的呢?鉴于物体的颜色不过是该物体的表面物质在吸收了一定波长的光线后所反射出来的光,所以物体颜色随着周围环境(比如大气浓度、光源)的变化而变化,不是非红即白的。故人们所观察到的多是相对的、表面的现象。如果一座山3000米已经成了人们获得的对该山的唯一认识,再去研究它便毫无意义;若说3000米高的山就是3000米高的山,便是同语反复,人们不能从中得到任何新的知识。
须知,许多现象同事物的本质不相一致,并非真相,如庄子所说“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是指事物的内在联系,只有靠思维才能把握。任何一个客观对象都是许多本质规定的统一体,其内部有复杂的结构层次,以及事物整体与其外部环境、条件之间的联系;且事物本质有许多层次,只有比较深刻的本质才能说明事物的本来面目。(42) 应当承认,人们难以一下子把握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过程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对其认识总有未被穷尽的更深的层次。多学科、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的综合研究的成果也无法获致唯一的“本来面目”。
此外,宇宙中没有任何事物是绝对静止、永恒不变的。一切事物都处于不断发生、发展并消亡的无休止的运动和变化中。大至天体小至微粒子莫不如此。每个生物体的细胞和组织都在不断死亡和更新。正像恩格斯所说:“每个有机体永远是它本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存在在每一瞬间,即和自己同一而又和自己相区别”,没有什么是非此即彼的。“甚至在无机自然界中,同一性本身在现实中也是不存在的。”(43) 这就是说,不仅事物没有单一面相,且其本质都会随着时间和条件的改变而发生变化。譬如,正是决定生物特性的基因不时发生变异,才会产生物种的多样性;甚至构成不同性质物质的元素也会在一定条件下发生改变,譬如钍受中子轰击可变为铀—233。
史学研究的对象不是孤立、静态的事件,而是历时性的“历程”。李大钊曾说,历史是“人类生活的变迁”、“传演”,“是社会的变动”、“变革”,是“周流变动的东西”,因而历史事实本身“永远生动无已。”(44) 史学不是研究在过去某一时刻表现出来的某个固定不易的现象,或过程中的一个点。即使以事件史为中心的“瞬间历史学”也要研究过去某事件在一定时段内发生、发展、终结的全部或片断的历程。经验还告诉我们,甚至同一个人的思想、行为也会有变化。
从上段所引李大钊的话可以看出,他有时似乎把过去发生的事与关于过去的知识等同起来。的确,历史事实既属于于本体论范畴也属于认识论范畴,过去的事实不独立于认知者之外,因为要寻求存在物及其本性就必须通过考察如何获得前者的方式。考察历史本体必须先通过历史认识,所以二者在根本上是一致的。(45) 尽管过去发生过的事是已经凝固的客观存在,是永远不会再改变了(我们愿意相信曾文可能是就这个意义上写“永恒不变”的),但它们却不是自明的或者可以自行解说的。由于史学家无法直接观察到历史实在,更无法保证其能了解全部史事及其深层的东西,所以不能说只有一个历史的本来面目,并且对其认识是唯一正确、不可更易的。
反映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和条件下才适用。恩格斯在举波义耳定律在某种情况下失效,只是近似正确为例后写道,“物理学上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就是这样的。”他进一步指出,在历史科学中,“永恒真理的情况还更糟。……在这里认识在本质上是相对的,……而且按其本性来说都是暂时的。因此,谁要是在这里猎取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猎取真正的、根本不变的真理,那么他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46) 史学研究的对象是过去发生的一些具体的、个别的、特殊的事物,对这样的事例进行归纳不能保证其结论的真实性,也难以获得可靠的、必然性的规律,即所谓“真理”。
固然,某些常识性的知识,如人有一个头两条腿,和拿破仑死于1821年5月5日等比科学认识有着更大的确定性;而且像某时间发生了什么、著名人物的生卒年月等这类历史常识在编撰年表、大事记时是用得着的。但在这方面,也常会碰到不那么确定的情况。简单的历史记述有时也不容易,比如老子和孔子到底谁先出生至今仍争论不休,纵使发现二人的遗体,能用碳14方法测定出谁先入葬,也难以确定二人出生孰先孰后。有时对简单史事的确定都需要作烦难的考证。比如为了说明拿破仑死因,就有史学家、医学家等运用各种手段来探查,作出抑郁而死、病死、被毒死等不同推测。可见,并不复杂的史实也不会轻易地呈现在史家面前。况且,历史不是过去事实的简单堆积,对这类史实即使描述正确也算不得什么科学上的真理。在马克思看来,常识“仅抓住了事物的表面现象”,“如果事物表面现象的形式和本质都完全同一,那所有科学就将多余了。”(47)
历史运动是复杂、多样、变动不居的,并总有什么被遮蔽住而使人们不能一下子完全知道和了解。而科学正是要探索未知的东西。如果史学还有科学性可言的话,就在于它除了要弄清发生过什么,还需要探求为什么、怎么样等隐藏在表层历史现象后面的事件的起因、事物的内在联系、与他事物的关联,以及对后来的影响等;此外还特别需要揭示关键人物的思想、动机,并考察当时社会的经济、文化、政治、心理等各种因素。各史学家对这些并非显而易见的诸多因素和关系进行探究往往不能达至一致的结论。
海登·怀特认为历史不仅是关于过去的事件,而且历史叙述还提出了事件之间可能的关系;这些关系并非过去给出的,而是存在于反映了过去的历史学家的心中。(48) 况且,随着时代变迁,史家的观念会发生变化,对同样历史事实反映的历史人物与事件的认识也会不同。李大钊对此有所认识,曾说:“历史的真实,亦只是暂时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对同一历史事实,今昔解释不同,故要对历史不断地改作。(49) 思想史更是如此。熊铁基等在撰写《中国庄学史》时便申明:“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庄子’,每一个注解者有每一个注解者所理解的‘庄子’。”一个学者若深信自己之所知、所解、所评就是真理,乃是错误的意见。(50) 总之,与自然事实那种意义上的客观性不同,人们所认识的历史真相没有那么确定可靠;历史研究只能不断地逼近历史真相,从历史中寻求到的真理也仅是历史运动呈现的某种大致规律的近似正确的反映。
四、准确认识与表述历史事实如何可能
对于“历史的本来面目只有一个”,还应当追问:人们何以能够知道历史的本来面目只是这样而非那样的呢?过去发生的事的客观存在不可否认,但问题在于:史学家能否准确无误地认识并表述历史真实?这就需要探究历史认识问题。
上百年前,不少史学家以为人有无限的认识能力,可以用科学方法确立史实。兰克的话很有代表性:“对可靠资料的批评考证,不偏不倚的理解,客观的叙述,所有这些结合起来,就可以再现全部历史真相”,并能做到“如实直书”。(51) 一些史学家相信历史学像自然科学一样是一门可以获致精确、可靠结果的实证科学。到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使很多人不再过分相信人的理性;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为代表的现代物理学和科学哲学打破了传统的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科学家们发现,微粒子的运动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随机性;在对之进行测量时,由于有主体实验手段的介入,其运动不是绝对客观的。自然科学的一些研究结果也仅能得出带有概率性的规律。爱因斯坦认为,科学家对物质结构的认识实为一种形象化的比喻和一幅简化的图像;企图以精密性和逻辑完备性来重现比较复杂的事件,非人类智力所能及。(52) 这样一来,被传统史学当作使历史学达到“实证的”、“精确的”知识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石动摇了。此外,心理学和语言分析等学科的研究成果也揭示出史学难以绝对客观地认识历史真相。
所谓“实证”,原义是指可以通过实验来检验、证实在感觉经验中观察到的无可置疑的事实。(53) 而史学研究的对象不可再现、不能重复,故今人无法直接感知、经验与观察,且关于过去的知识又无法验证,因此史学难以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实证科学。所谓“实证史学”将历史事实视为彼此隔离、并独立于认知者的孤立事件;主张历史由大量无可反驳的、客观的事实编撰而成,史家不可加自己的判断。这种把过去的事实当作原子式的、一串可实证的孤立事件所组成的“念珠”或“序列”的史观早已遭到一些历史哲学家和史学家的批评。柯林武德认为,历史事实与在科学里事实是可在它们发生时被知觉到的经验事实不同,不是实证主义知识论所认为的那样被直接给定的,“而是按照一种复杂的准则和假设的体系来解释资料的过程中而推论出来的。”(54) 沃尔什也指出:“过去的事实是不能再接受检验的”,通常用以检验的历史证据也不必然带有可靠性,史家应以批判性的态度去对待它,并须决定是否要承认和相信它,或相信多少。历史事实是以判断的形式呈现的,是被人建立的。(55) 因此,布洛克曾说:“历史的事实,乃是心理学上的事实”。(56)
史学家们在追寻历史真相的同时,也越来越多地思考这样的问题:如何并且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够知道现在已超出回忆或复述之外,故已不能成其为知觉对象的那些事实呢?
往事已逝,历史知识的来源并非过去实际存在的事实,而是现在遗存的证据所显示的事实。如埃尔顿所说,历史事实就是发生在过去,并在一些文献上留下线索,足可让现今史学家加以重建的事实。(57) 史学家仅能利用人类过去活动的痕迹—残存的实物和传下来的文献、口碑等来进行研究,故历史认识是通过史料为中介体的间接认识。但问题是,通常被史家视为重要证据的文字记录和口述回忆是否都记载和保存了完整、真实的过去呢?古代伟大的史学家修昔底德曾感叹“不同的目击者因有缺陷的记忆和出于偏向对于相同的事件给出了不同的叙述”,这使他难以发现真相。(58) 的确,过去的事在最初被记下来时由于记录者的疏忽及其观察范围局限、角度不同等,都会导致记录的错误、疏漏和片面,甚至所谓“实录”也不能幸免。怀特便质疑“精确地记载”这个概念。(59) 即使正确的文字记载所传递的历史信息也只占实际发生过的事情的很小部分,因此只保存了部分史实,不可能与真实的过去确切对应。须知,关于过去的记录绝不等于过去,纵使史料真实也不等于历史真实。
况且有些记载一开始便经过记录者有意的筛选、歪曲甚至虚构,随后这样形成的历史文献又经过整理者、研究者不断的剪裁取舍,甚至篡改等加工处理。因此,有些社会记忆被废弃或歪曲,有些则刻意保存、推广。是以,留传下来的史料多打上了制造主体的主观烙印,不能简单地被视为“客观史实”的载体。(60) 譬如,有些“亲历记”的作者会因其所持立场对一件事作出歪曲的描述。因此,当事者就同一件事情作出多样而不同记述的情况屡见不鲜。就连被视为“史家的绝好材料”(61) 的报刊记载,也并非完全可靠。如大跃进期间报纸上亩产数万斤的报道,其虚妄现已人人皆知了。可见,所谓原始资料也有可能不符合史实。史学家吕思勉便认识到“世无纯客观之记载”。(62)
再者,过去遗留下来的历史记录多残缺不全、零星片断,纵使“上穷碧落下黄泉”地努力搜寻,仍难以收集齐全。因此任何史学家“无论喜欢与否,只能将就使用现存的资料”,并都“可能因为资料的残缺,而无法获得有力的结论。”(63) 连博学多闻的史学大家也仅能依据残余段片,来窥测某事的结构。
近现代史的资料尽管保存得较多,而且还有一些当事人可作为活的史料来源,但在搜集过程中仍然会遇到种种困难。面对浩如烟海的中外档案、报刊等各种资料,史家总要带着一定问题或兴奋点把搜寻目标限定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和某些人物和事件的范围内,不可能漫无边际地去翻阅。超出一定搜寻范围的资料、在注意点之外的内容便易被忽略。还有时一些档案、报刊明明藏在某档案馆、图书馆,却由于资料本身的破碎、霉烂或馆方的规定而不允调阅;或者史学家因语言、财力、身体等限制而无法查阅或收集。口述回忆也会由于当事人的记忆不清、有意矫饰,或访问者提问范围过窄等原因,造成种种缺陷。
资料的收集没有止境,否则便不会有所谓“新资料”的不断面世。而且每个历史研究者的生命有涯,穷毕生之力都不能保证把哪怕一个课题的相关资料收集齐全。因此,史料不完备是“永远的难题”,并且历史学的知识通常被视为“不完全的知识”。对于人的知识的局限性,许多古代先贤早有明见,如庄子便云:“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史料之成其为史料,离不开史学家的识别、筛选、抉择。以不同眼光、不同方法处理同样资料,导致的结果亦不同。陈寅恪甚至利用诗歌作为文字史料去证史,而有的学者却对可视为第一手资料的某些回忆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有人珍视看似荒诞不经的古代书籍、民间传说,有的则对那些可能蕴含着珍贵历史记忆的东西轻率否定、遗弃。卡尔指出,一件过去发生的事,要被史学家视为一个历史事实而加以接受之后,才能成为一件历史事实,而能成为证据的才叫史料。“事实唯有当史学家要它们说话时才说话。”(64) 由此可知,史料的鉴别、史实的建立与历史认识主体有关。
有时学者们面对同样的资料、语句甚至单词常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解读。韦伯说,“即使是简单的叙述性历史,也是用当时惯用的方法来表达概念的。……要经常提到所有确切概念的非事实性。”(65) 不少情况下,在一种语境下所说、所写的话,很难为没有身历其境者所完全了解。譬如现在的年轻人就很难理解文革语言,更不要说今人理解古代语言了。同一个古代典籍常有不同的标点、注疏。譬如《道德经》首篇第四句就有“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和“故常无,欲以观其妙。”的不同断句、标点,反映了对同样文字的不同理解和解读。古汉语今译如此,中外文互译亦有此问题,如中国文化上的“气”,外文根本找不到对应的词。哲学上有所谓“译不准原理”,即一种语言表达的意义,不可能在它原来使用的意义下,无歧义地翻译为另一种语言,两种语言的对应关系无法被证实,因而解释不具唯一性。不同的解释具有等价性,所以追问何者真正描述了世界的本来面目是无意义的。(66)
历史著作不仅是研究的成果,有时也成为一种历史认识的来源(特别在原始资料亡佚的情况下)。而史学家因成长背景、心理倾向、立场、观点的不同会对同样的事会做出不同的叙述、分析、解释。孔子尽管说自己“述而不作”,但其所编《春秋》的倾向性是明显的。史家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对史家的思想和史著的写作有很大影响,甚至有的史家会在外界压力下作违心之言。随着社会思潮的变迁、史学方法和视界的改变等,史家的认识会发生变化,从而对同一个研究对象的描述和评价不一样(“文革”前、中、后对太平天国和戊戌变法的研究便是显例)。故史学虽提倡“价值中立”的客观研究,但史家受到自身生活经验的限制,却难以做到;史著的撰写也就不免掺杂史家主观的因素。
此外,史著中错误的表述也会造成以讹传讹。写作涉及语言的应用,而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其能指与所指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关系,同一个话语可以表示很多意思并有不同解释;并且语言使用者常用转喻等手法,所以语言有一定的模糊性。使用文字这种并非十分精确的表达工具来撰述,常无法准确无误地传达思想和被理解。此外,写作过程难免有笔误或疏漏,不要说一般人,就连马克思这样严谨的人也不能幸免。他在表达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时写到:“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而在后来出版的、马克思亲自校订过的法文版中这里是“成正比”。(67) 还有时,一些史著原作的文字在编辑和出版过程中被修改得失去原貌。我们有的文章在发表时就遇到关键史料被删除、重要历史日期被修改和主要人物姓名被错写等情况。
如此看来,由于资料的缺乏、真伪难辨、收集困难,以及史料筛选、识别误差等因素,史学很难达到对历史真实全面、客观的认知;另外写作环境、文字表达、发表出版的误差又妨碍史学著作准确无误地反映史家的认识。总之,在各种条件的限定制约之下,绝对正确的的历史理解和历史构图难以形成。甚至被普遍接受的所谓历史事实也可能并不正确。克里普克曾举“莎士比亚是剧作家”为例,说句中的摹状词(相当于谓语)并不具有必然性,只表达对象的偶然属性,因为有可能是不符合实际的(不少史学家认为,以往归于莎士比亚名下的那些剧作可能出自培根的手笔)。(68)
关于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与表述的局限性,恩格斯说,“认识就其本性而言,……由于历史材料不足,甚至永远是有缺陷的、不完善的”,人的认识能力,“在客观上被历史状况所限制,在主观上被得出该思想映像的人的肉体状况和精神状况所限制”,谁要自认为“无所不知”,能解决科学的最终的任务,便“封闭了一切科学走向未来的道路。”人对整个外部世界的有系统认识是由一个挨一个、一个跟一个的“无限多的人脑”来从事的,因而是“相对的而且必然是逐步趋于完善的”。(69) 他在致康·施密特的信中谈到,“一个事物的概念和它的现实,就像两条渐近线一样,一齐向前延伸,彼此不断接近,但永远不会相交。……现实同一切思维成果的符合仅仅是非常间接的,而且也只是渐近线似的接近”。(70) 他还指出,那种试图对客观世界部分与整体的系统联系“作恰如原状的、毫无遗漏的、科学的陈述”,“对所有时代来说都是不可能的。”(71) 同理,由于过去发生的事不能直接观察,关于过去的记载又有疏漏和错误,再加上历史认识主体的种种局限,史家只能做到其历史认识与历史实际近似,史著也仅能勾画出罗素所称的“模糊轮廓”(72),而不是“对过去所发生的一切事的描述性再现”(73)。
五、若干史学方法及开放的史观
本文开头引述了曾文表达的对想像、推理、推测的若干看法,似乎认为它们并不科学,并且提到了假设。对于这类思维和论证方法在史学中的运用有些史学家持有比较否定的态度。(74) 其实,推测、推理、假设、想像均为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方法。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就高度赞扬进行推测的想像力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并说科学原理是由具有虚构特征的假设组成的。(75) 社会学家韦伯亦认为,任何对客观事实的描述没有推测和假定是不可能的。(76) 那么,史学呢?
福尔布鲁克在《史学理论》中反复强调,史学是一门“需要想像力”的学科,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是以“推论的形式”呈现的。(77) 史学研究常在掌握一定材料后,根据已有知识,经过推理提出一些初步的、具有不同程度可靠性的看法和解释—即假设。假设包含推测,那么它就包含想像因素。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论述道,在史学中,思想的正常过程是推理的,要根据事实进行推论得出结论的一部分。若要赋予历史的叙述或描述以连续性,史学家必须运用想像,去构造一幅关于过去事物状态的、在权威陈述所提供的点之间展开的网。(78) 如此看来,史学家要把过去的事写得比较完整也会用到想像和推理,不管自己意识到与否。不少史学家可能会有这样的体验:自己所研究的对象在自己脑子里活了。这就是想像的作用。有的学者甚至说,“好的历史学家和差的历史学家,其中差别之一,就是有没有想像力。”(79) 史学大家陈寅恪曾直接以《李唐氏族之推测》、《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为题发表论文,等于公然宣称自己的研究成果是一种假设。
假设的形成需要推理。史学研究中由于资料的缺乏多采用不完全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由于这类推理的根据不充分,只能提供或然性的结论,不能提供必然性的结论。德雷认为史学家需要解释的是那些在某种情况下似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因而历史解释应当用“如何—可能”(how-possibly,即它可能如此)的模型来代替“何以—必然”(why-necessarily,即它必然如此)的模型。(80) 据纳吉尔总结,史学推论常以下述形式表达:“B的发生,可能是由于A的发生”;或“若A发生,那么B可能也会发生”。(81) 历史推论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逻辑推理,因为历史并不像有人常挂在嘴边的那样“合乎逻辑地发展”,逻辑具有的必然性无法处理超乎意料的偶然性的东西。如沃尔什指出,没有任何事实性的陈述(包括历史学中的)可以被抬高到逻辑上的必然真理的地步。(82)
此外,史学作为一门人文(精神)科学,特别要了解的是关于人的思想、感情、动机、意图等,这些多超出史实之外的知识更不具有自然科学的客观和真确性,完全无法用抽象、普遍的认识形式来把握。18—19世纪的一些哲学家兼史学家如维柯、赫尔德、狄尔泰等便认识到,史学家应当运用静观沉思的体验、直觉的洞察、移情作用、同情的理解等艺术去解释人的心灵和行为,并充分发挥合理的想像力去推测“想必会呈现的状态”。(83) 20世纪以来,对历史的理解和解释成为史学发展的一个方向,史学甚至被视为一种“理解的社会学”。后现代史学家詹金斯说,写史所根据的证据是那么微薄,所有这类的知识都像是假设性的,因而,历史无可避免是解释性的。由于过去和历史的缀连程度没有大到只有一种对过去的解释是绝对必然的,不可能产生独一无二的解释。在这种对过去的解释中,“诠释性、推测性的字眼,其塑造力是没有什么限制的”。(84) 尽管后现代史学理论过分的怀疑主义对史学根基造成冲击和伤害,但其对史学特殊性的理解以及方法上所强调的解释、诠释、推测、假设,实际上已被许多史学家接受并采用了。
史学无定法,无论是直觉洞见,还是运用各种推理方法、比较方法、计量方法、心理方法、人类学方法、逆推方法、跨学科方法、系统方法等,史学家都很难“断然肯定”自己对过去的认识是否“真实可靠”。况且历史解释向来便不能从“适切的”、“合理的”越到“正确”的阶段。(85) 甚至主张历史事件应以科学规律加以解说的亨培尔也承认盖然性的解释总是不完善的。(86)
历史学家总是在确定与可得的证据相符的不同程度的可能性。(87) 剑桥大学历史教授伊万斯写道:“大致而言,史学家并不会以自视他们所说的每一件事都是绝对真理的这样的态度去写作。相反的,历史学家向来所使用的语言,对于他们所说的事实的不同程度之确定性或可能性总是特别地考究。不只是‘可能’、或许这类词汇经常出现在历史著作中;态度审慎的历史学家会构思各式各样不同的文体,去显示他所提出的论据之强弱,以显示他所获致的结果确定与否。”(88) 韦伯谈到,如果史学想要超越大事记、大人物年表的水平,并且不企图“毫无遗漏地‘复制’整个事件”,就要“从无限的决定因素作可能的选择”,这是史学研究的趣味所在,唯有如此,才可能对知识的增进产生贡献。(89)
一般而言,使用“可能”等语汇的学者,多是在依据第一手资料作研究时,对未知情况、原因等作出推测,其研究成果往往更富于创见和意义。而那些惯于抄袭他人著作的叙述和结论,并善于像文学写作那样编造情节的“史家”倒是绝少用“可能”。同时,写“可能”者多持有较为谨慎、严肃、谦虚的态度,因为这样做就等于不认为自己所写绝对正确,并且在用“可能”的地方暗示出哪一步推论可能会出错。这即是承认自己研究成果的可错性。科学知识和理论就是通过试错法,通过猜测与反驳、证实和证伪、修改与补充而前进的。(90) 爱因斯坦说过,说明感觉经验的理论是假设性的,“永远不会是完全最后定论的,始终要遭到质问和怀疑。”(91)
历史意识随科学观和方法论的进展早有深刻变化。1907起出版的《剑桥近代史》的总主编阿克顿曾深信有终极的或完善的史学和所谓“国际研究的最成熟的结论”;但1957年起出版的《新编剑桥近代史》总主编克拉克便认为历史的探究永无止境,后世史学家“期望自己的工作将会一再被超越。”(92) 新的史学观具有开放性,历史的假设也是“暂定的和可改正的”。(93) 如陈寅恪就在作出若干推测后写道,他准备“有误必改,无证不从,庶几因此得以渐进事理之真相。”坦承自己研究成果的不完善性和可误性便为同辈或后辈学者对同一问题的继续探讨和对自己结论的反驳或补充预留了空间。终极史学的观念已被许多史学家所抛弃,几位现代美国女史学家曾说:“由于没人能确信自己的解释绝对正确,人人都要听听别人怎么讲。所有的历史都是暂定的,谁也不能自认为是定论。”(94) 史学家持可错性、开放性的态度带来的是历史表述、解释及史学方法的多元化。
有越来越多的史学家认识到,历史研究不再像以前那样追求唯一真实的支配叙事,而认可对一件史事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描述和解释,尽管各自都不免有缺点且不全面,却至少可以对形成比较全面的了解和建构较为真确的历史构图作出贡献。(95) 反对把历史研究的结论看成一套真理的罗素就主张,对重要的历史事实“有必要提出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假说来”,(96) 甚至认为应当容许有偏见的著作出版。除了内容之外,一些学者认为学术论著在选用什么样的语言构架上也应当有充分自由,即在允许语言形式方面采取宽容态度。对同一段历史有更多可供选择的历史著作出版,实际上是“朝客观性迈进了、而非远离了一步。”(97)
学术的宽容和学术成果发表的宽松环境有利于史家间的相互交流、商榷、批评、辩驳、以及史料的互补,也为读者提供了选择、比较的机会。如此,史学研究才能深入进行。若历史被定于一尊,表述形式也强求一律,研究者不得不遵从某些权威著作,并引用、照抄那上面似乎不容置疑的叙述、结论、乃至用词,稍有偏离和不一致就被要求更正、消声,史学研究便不会有百家争鸣的局面,就只能成为摘录和拼凑各种权威记载和著述而成的“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学”(98),造成如曾先生告诉笔者的那种“低水平重复”的状况。
史学家在了解到史学的局限性、可误性,以及方法的多样性以后,绝不意味着可以走到另一个极端—即认为过去的事实和虚拟之间没有任何区分,历史不过是“主观的再现”;第一手资料由于已被加工整理过,故和第二手资料没有分别;因史学需要想像样、建构,所以与文学创作并无二致,类似一种“诗性的”工作。(99) 我们十分赞同范文澜先生提倡的天圆地方、甘坐冷板凳的精神,主张从事史学研究除了要视野开阔,了解历史哲学、史学理论的要点和最新发展而外,仍然要沉下心来,努力搜寻原始资料,并可借鉴和运用实证史学方法去考订史料;下笔写史仍应谨慎遵循各种学术规范,杜绝胡编乱造。可话还要说回来,无论是考实性判断还是推测性解释,历史著述中仍不免要用到“可能”、“可能性”。
注释:
①《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6期。
②我们对曾文就某些论文发表的批评不予置评,故拙文不是其批评的评论,仅试图讨论曾文表露的史观问题。历史地看,相对于在“文革”中登峰造极的歪曲历史事实的“影射史学”,和长期以来的“党派史学”,曾文所表达的史观有积极作用;其强调的根据证据来写史也是我们所赞同的。
③Cf.S.Sim & B.V.Loon:Introducing Critical Theory( Incon Books UK,2004) ,pp.6—7; M.Fulbrook,Historical Theory( 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2) p.47.
④参《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哲学卷、T.Honderich(ed.),The Oxford Companion to Philosoph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现代汉语词典》等有关词条。
⑤K.R.Popper,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y,( 1952) ,Vol 2,p.197.
⑥吴志翔“被历史忽略的历史——读余世存的《非常道》”,http://www.yuedu.org/books/book—20051117203218HG.htm。
⑦《历史研究中的可能与现实》,《史学理论》1988年第1期。
⑧沃尔什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哲学——导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⑨韦伯著,黄振东、张与健译:《社会科学方法论》,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242、230,223、228页。
⑩参维特根斯坦著、贺绍甲译《逻辑哲学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7、31—33,40—47,78—79,60,66—67页。
(11)萧兵:《楚辞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版,第454页。
(12)《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08页。
(13)荷马:《奥德赛》,陈中梅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14)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杨豫等译中译本。
(15)这位法国年鉴派第三代大师在这里还用到了类比推理。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卷第85页。
(17)柏林著,冯克利译:《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204、213页。
(18)M.Bernal,Chinese Socialism to 1907( Ithaca &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6) ,p.22,pp.31—32.
(19)《北京大学与“五四”前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
(20)《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
(21)《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
(22)《民国档案》2001年第3期。
(23)F.E.Beringer,Historical Analysis,Contemporary Approaches to Clio' Craft(New York,John Wiley & Sons,1978) ,p.3.
(24)参休谟:《人类理解研究》,转述自洪谦:《论逻辑经验主义》,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82页。
(25)《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49年版,第400、351页。
(26)《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
(27)《党史研究资料》1993年第4期。
(28)《百年潮》2001年第11期。
(29)此段有的部分参考了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第65、85—86、101、47页上的论述。
(30)刘放桐等编著:《现代西方哲学》(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上册第447页。
(31)E.H.Carr,What Is History? ( Palgrave Publishers,2001) ,p.90.
(32)向青:《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6期;《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建立联系的起点》,《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3期。后来收入向青《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中的有关文章,那种决然的用词就少了一些。
(33)李丹阳:《朝鲜人“巴克京春”来华组党述论》,《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
(34)我们曾在“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联系的起点——兼与向青先生商榷”中写到霍多洛夫。但该稿于1991年寄到某编辑部后,审稿人在上面写了许多“不可信”、“不可能”的批语,被退回。十年之后,我们才在《民国档案》发表了改写的关于霍多洛夫的论文。
(35)《百年潮》2002年第8期、2003年第6期。我们不排除一些亲历者对往事及其发生时间的回忆有误的情况,及当事者有歪曲事实的可能性。
(36)李宗侗:《中国史学史》,台北:中国文化学院1979年版,第1页。
(37)凯利(Donald R.Kelley)著,陈恒、宋立宏译:《多面的历史》,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66页。
(38)引自詹金斯著、贾士衡译:《历史的再思考》,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年版,第69页。
(39)参方志强:《“历史事实”——“事实”与“解释”的互动》,《新史学》(台)2002年9月。
(40)凯利著,陈恒、宋立宏译:《多面的历史》,第390,386页。
(41)卡尔在What Is History? 中也曾以山举例来表示不赞同历史研究中的极端相对主义态度。
(42)参考《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上册第330—337页。我们在写此段时感到有些困惑。因为如果读者追问什么是山或一段历史的本来面目(即深刻本质),我们也无法回答。按照“反本质主义”理论,没有一种特性可被称为本质,因此追问本质是什么一类问题是根本不可能回答的。这似乎可为我们解除困惑和困境。
(43)恩格斯:《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
(44)李守常:《史学要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
(45)参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史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二章。
(4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1页,第128—239页。
(47)Thomas Sowell,Marxism-Philosophy and Economic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1985) ,p.8.
(48)Hayden White,' The Historical Text as Literary Artifact' ,in Tropics of Discourse,Baltimore,MD,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5,p.94.
(49)《史学要论》,第5—9页。
(50)见罗素:《真理的定义》,李良忠主编:《在剑桥听讲座》,中国民航出版社2002年版,第84页。
(51)徐浩、侯建新:《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页。
(52)爱因斯坦:“自述”、“探索的动机”,《走近爱因斯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44页。
(53)在自然科学上,对于某种可以被称之为“确证”的东西也受到质疑。如洪谦认为,无论是“原始记录语句”,还是“观察陈述”,都不具有任何绝对确定性,因为“陈述的真理性或确定性不能由瞬间经验来保证,确凿无疑的经验和不证自明的感知显然都是十分主观的、心理上的。”洪谦:《论逻辑经验主义》,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30页。
(54)柯林武德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的观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97页。
(55)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第11、82页;译序二,第15页。
(56)引自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9页。
(57)转引自理查·伊万斯著,潘振泰译:《为史学辩护》,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2年版,第66页。
(58)Harriet Swain( ed.) ,Big Questions in History( London:Jonathan Cape,2005) ,p.3.
(59)怀特海:《思维方式》,第17页。
(60)参王明珂,“历史文献的社会记忆残余本质与异例研究——考古学的隐喻”,《民国以来的史料与史学》,(台)国史馆,1998年。
(61)李守常:《史学要论》,第44页。
(62)吕思勉:《吕著史学与史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5页。
(63)黄进兴:《历史主义与历史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2页。
(64)Carr,What Is History,p.5.
(65)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第118—119页。
(66)刘放桐等:《现代西方哲学》,上册第444页。
(67)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卷第707页。
(68)刘放桐等:《现代西方哲学》,上册第445—447页。
(6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0、125、76、421—422、554—555页。
(7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5页。这里用“两条贴近的平行线”较好。因为若非平行线,两条相互内向的线距离再远,也总会相交;若彼此外向的两条线则会渐行渐远,永远也不会彼此接近。但“平行线永不相交”的几何定理也有问题。因为在实际中并不存在这种想像出来的平行线;地球上的测地线在南北极还是要相交的。这里,是要举例说明,谁都有表述不准确的时候,但某些有毛病的语句也并不妨碍人们了解其意思,所以不必过于追究语言的准确性。波普尔就认为语词上完全的精确性是不可得的,如果纠缠在语词上,“为了言语的问题放弃真正的问题,这必然导致理智的毁灭。”
(7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6页。
(72)罗素著,何兆武等译:《论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73)魏洪峰:《真正的历史》,《读书》1997年第8期。
(74)如翦伯赞曾主张写史时不要推论。见其《历史哲学教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61页。现在也有史学家认为假设仅是数学方法。
(75)爱因斯坦:“论科学”、“论理论物理学的方法”,《走近爱因斯坦》,第149、157—8页。
(76)Mary Fulbrook,Historical Theory,London & New York 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2,p.89.
(77)Fulbrook,Historical Theory,p.25,p.21.
(78)《历史的观念》,第324—337页。
(79)“葛兆光教授答问”,www.chinesenews.net,2006/4/7.
(80)参见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第265页。
(81)参Ernest Nagel,The Structure of Science(New York,1961),p.559,引自黄进兴:《历史主义与历史理论》,第103页。
(82)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第88页。
(83)参威廉.狄尔泰著,艾彦、逸飞译:《历史中的意义》,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版,第18、140页;《译者前言》第21页。柏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第139—143页;H.A.Hodges,Wilhelm Dilthey:An Introduction,pp.72—83;黄进兴:《历史主义与历史理论》,第95页。
(84)参见詹金斯:《历史的再思考》,第55—59、61—66页。
(85)黄进兴:上引书,第105页。
(86)Carl G.Hempel,' Reasons and Covering Laws in History' ,Patrick Gardiner( ed.)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4) ,p.97.
(87)Beverley Southgate,History:What & Why? Ancient,Modern,and Postmodern Perspectives( 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96) ,p 84。
(88)伊万斯:《为史学辩护》,第125—6页。值得一提的是,此书是为反击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冲击而作的。
(89)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第242、230,223、228页。
(90)参Honderich( ed.)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Philosophy,pp.266—269; K.Popper,Historicism and Its Poverty,pp.5—6,p.13.
(91)《走近爱因斯坦》,第161页。
(92)What is History? pp.1—2.
(93)Pieter Geyl,Use and Abuse of Histor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5,p.70.
(94)J.Appleby,L.Hunt & M.Jacob:《历史的真相》(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薛绚译,台北:正中书局2000年版,第12页。
(95)参Fulbrook,Historical Theory,pp.28—29.
(96)《论历史》第3页。
(97)J.Passmore,The Objectivity of History,in P.Gardiner( ed.)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p.153.
(98)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358页。
(99)参王佳晴、古伟瀛著:《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