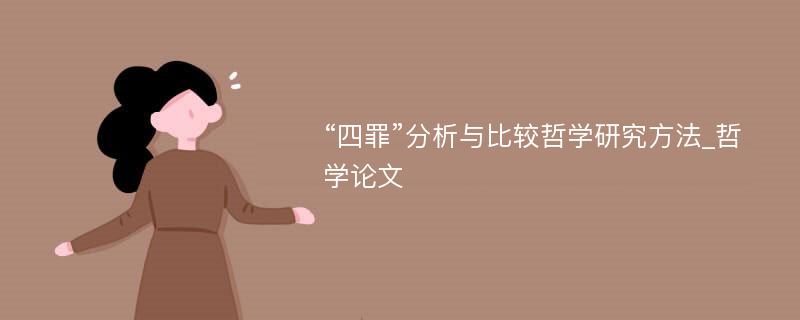
关于“四宗罪”的评析与比较哲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哲学论文,四宗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02 文献标识码:C
探索中国哲学①与西方分析哲学②之间的建设性互动③如何可能的问题,既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一方面,中国哲学与西方传统的分析哲学,作为两种主要的哲学传统,都曾各领风骚,取得了诸多灿烂辉煌的成就;然而,另一方面,在很多人心目中,这两种哲学传统却不仅互不相干、难以相容,甚至彼此对立;双方中的一些人往往认为对方的另一种哲学研究传统充其量只具有一种边缘性的价值,或干脆将二者视为本质上是完全不相容的。事实上,一些误解或至少是严重的误导是源于一方对另一方哲学的无知或缺乏深入的认识,而另一些则是由于某些理论本身的混淆,甚至对其自身传统的真正本质也未有准确的把握。今天,两大传统中越来越多的哲学家们已充分认识到,中国哲学(或曰中国思想的哲学维度)与西方哲学(包括其分析哲学的传统)本质上并非是彼此不相容的:在一系列基本问题上,它们有着共同的关切,而探究问题的方法则各具特色,因此,它们能够彼此相互借鉴,通过建设性的对话和互动而携手共同促进整个哲学事业的发展。
要深入理解在西方传统的分析哲学与中国哲学之间所展开的建设性互动这一事业的本质与意义,读者必须首先对比较研究中具有不同的方法论路径的几种主要的基本取向以及它们之间的应有关系问题有所认识。④
我无意于详尽无遗地讨论所有工作取向,在这里,我将试图着重探讨比较研究中所存在的三种最主要的取向及其不同的方法论路径问题,在我看来,对它们展开应有的考察,将最有助于比较哲学研究的健全发展。⑤我将通过对比较哲学研究活动中常常或明或暗地遭到指责的“四宗罪”的恰当性问题的评析来阐明这一点。我采取这一战略的理由在于:“四宗罪”的恰当性或合法性取决于一项比较研究活动的本质、目的和取向——它们将决定性地确定应该采取何种方法论路径以及何种期望为宜。要识别那些不同取向与方法论路径的各个方面和目的之间如何不同,由此在对待自己的比较研究活动或评判别人的比较研究时,更好地洞察出其目的和取向如何不同,并因此确认什么才是它最适于期待的,这一战略无疑是一个有效的方法。
当人们对比较研究项目展开评判时,似乎总会有四种抱怨或责难。这些被归咎的“罪过”是: (1)过分简单化;(2)过度利用外在资源;(3)夸大差异;以及(4)模糊差异的同化。所有这些,或其中的一些,有时候以两种方式被人们想当然地认定。其一,人们认为,任何将研究对象简单化或运用外在资源来描述其特征,都注定是过分的,因此难免遭遇否定性的所谓“过分”夸大其特征的责难;其二,人们还以为,在评价任何比较研究项目时,可以无视该研究的取向和方法论战略,而不分青红皂白地扣上这四顶帽子。对这四宗“罪过”的元哲学考察无疑将有助于我们更有效地识别各种取向及其方法论路径的彼此不同的特征和目的。
首先要考察的一种基本取向,是旨在给出一种关于历史事实的描述性的说明,即是说,这种类型比较研究的基本关注点和目的在于准确地描述相关的历史事实,探求比较过程中思想家们实际所思所想,他们实际上采用了何种资源,在哪些方面似乎相同,又在哪些方面相互差异。这种类型的比较研究的取向因而可以被称为“历史的取向”,其方法论路径是指向对历史事实的准确描述。这种历史的取向要求其实践者必须占有充分的历史资料,如此才能给出这样的“事实描述”研究。这种取向及其方法论路径在传统的中国学术研究或汉学研究中堪称典型,似乎被视为中国哲学和比较哲学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
毫无疑问,按照人们的设想,那些致力于历史取向的比较研究活动注定与上述的经常被指斥的“罪过”难脱干系。第一,要准确描述某件事物,理所当然地意味着他不应该将实际上复杂的事物简单化;换言之,简单化本身就总是意味着过分简单化:任何简单化的做法必然被斥之为贬义的言过其实,因此简单化也就等同于虚假化;第二,接下来是过分运用外在资源的问题,即任何用作解释一位思想家的待考察的观念而不是实际上被思想家本人所采用的概念或解释性资源被视为不恰当或过分地采用:外在资源的运用也总意味着外在资源的滥用;⑥第三,在这种方法中,由于忽略一种传统或解释性说明与另一种传统或解释性说明之间所具有的某些共同的因素,而将处于比较考察中的一方或双方过分简单化,便常常形成夸大差异的现象;这样一来,只要过分简单化的缺陷存在,所谓夸大二者之间应有差异 (如果有的话)的指责也同样相应地能够成立;第四,在这种方法中,模糊差异的同化常常源自滥用外在资源去解释处于比较考察之中的一方或双方,当用来描述一方特征的外在资源来自另一方时尤为如此;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只要滥用外在资源的“罪过”存在,则模糊二者之间差异的等同化的弊端也必然随之出现。
如果历史性取向/路径被恰当地视为若干可供选择的取向/路径之一,而不是排他性的“天下第一路”,且在比较研究中当其用于其他不同的目的时,人们能够认识到它的界限,则这种取向及其方法论路径本身就并无什么错误或不恰当之处。如此一来,有一个问题便会油然而生:除了历史性取向以外,是否意味着有任何其他的取向和路径更为恰当,而且,更重要的是,对于比较研究中某种特定的目的而言更具有必要性?对于这一疑问的正面的回答实际上在前文的讨论中就已预先设定了,这一疑问可以以另一种方式来表达:另外的合法的取向和方法论路径如何可能并具有必要性?在下文中,我将集中阐述另外两种取向及其相应的方法论路径。
比较研究中的第二种基本取向则是试图通过深入阐发有待考察的思想家的观念而对文本展开进一步的解释⑦。这种取向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某些有效的概念和解释性资源来增进我们对一个思想家的观念的理解把握,不管这些资源实际上是否为该思想家本人所运用。很显然,纯粹历史性的路径在这里并不适合:详细阐述和解析一个思想家并不等于精确地描述该思想家实际上如何所思所想;况且,这样一种解释和解析本身也许就包含了解释者对该思想家观点中所蕴含的含义的深入发掘,而这一切也许并未被思想家本人所意识到;也许解释者对思想家观点的阐述更为清晰、逻辑上更为连贯一致,或以思想家本人并未采用的某种更具有哲学色彩的方式来进行的。⑧在这两种情况下,倘若要解释的是某种传统或解释性说明中一个思想家的观念,在另一种传统或解释性说明中得到很好发展的一些有效的概念和解释性资源被有意识地用来增进对该思想家观念的理解,并对之展开详尽阐述;就这样一种关于两种不同种类的资源的比较不是明确而直接地进行而言,这些如此被使用的资源因此是按一种潜在的和隐含的但又具有建设性的方式而与该洞见或视域以某种方式借以形成的那些原初的资源加以比较对照。所谓“建设性地”一词,这里指的是这样一种潜在的比较路径,它内在地涉及到解释者能够借鉴另一种传统或解释性说明的相关资源以增进其对于所研究的思想家观念的理解,因此,这种基本取向及其相应的方法论路径潜在地涉及到在不同传统的彼此差异的资源之间的某种建设性的哲学互动。
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所谓过分运用外在资源的方法论并不必然是一种“罪过”,恰恰相反,它可以真正增进我们对于某个思想家的特定观念的理解,或澄清关于其观念的某些模糊和含混的表达。既然在这种取向中所出现的运用外在资源的努力本来就没有什么不恰当之处,因此并不像在历史性取向那里一样,注定是一种“罪过”。值得注意的是,当这些解释性的资源和概念资源被运用时,并不意味着古代思想家已具有同样的明确体现出来的思想系统性,或同样已掌握某些概念性和解释性资源,而是为了增进我们对文本所传达的其观念的理解。对于这种解释的目的来说,下述做法不仅具有合法性,而且有益于运用更明确或更清晰的概念资源来详尽阐明某些否则只是在思想家的观念中所隐含和潜藏着的思想 (即内在的脉络和联系),而后者由于古代思想家们缺乏我们今天所能有效运用的那些有利解释的概念资源而有时候并未明晰地表现出来,甚至造成扭曲的表达。⑨还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说一个思想家的思想脉络和其观念在它们的语言表达中缺乏明确体现出来的系统性时,并不足以认为该思想家的思想脉络和一系列观念本来就没有在其深处(潜在隐含地)具有一致性和内在联系。随之而来的是,我们不能仅仅只是根据语言表达中缺乏这种明确体现出来的系统性,就去断定该思想家的文本本身就不具有哲学意义,而事实上该文本也许也试图传递思想家的反思性观念。在这一点上,基于前述的和当前的方法论考虑,为了促进我们对该思想家的观念、包括其内在应有含义的理解把握,通过运用被我们所掌握的恰当的概念和有利于解释的资源对该思想家的思想线索和由此构成的反思性观念展开更深入的阐发解读无疑是非常必要的,而不仅仅只是一种主观偏好问题。
如同在讨论历史性取向时所指出的那样,模糊的等同可能源自在解释处于比较考察中的一方或双方时过分采用外在资源,特别是当被用来刻画一方特征的外在资源实际上来自另一方时尤其如此。然而,为了达到解释的目的,由此导致的这种等同化并不必然是一种“罪过”,而是可能说明被等同的观念之间的本质联系和在根本层面上的共同之点,由此加深我们对这些观念的理解。
很显然,一种旨在解释取向而不是单纯历史描述取向的比较研究活动,可以是自由开放的,或者的确倾向于基于该研究项目的目的、投身该活动的研究者的理论兴趣等等,而专注于某个思想家观念的特定方面、层次或维度。毋庸讳言,不是全面地涵盖研究对象的所有方面和维度,而是聚焦于其中某一个方面或某一个维度,的确是一种简单化。现在的问题是:是否任何简单化本身都注定应不加区别地被斥之为过分简单化的“罪过”?需要澄清的是,如果一项比较研究的目的是专注于解释或阐明一个方面或维度,而不是假装要给出全面的历史的描述,那么,指责致力于这种研究的探索者过分简单化或过分简单地专注于问题的一个方面或维度,则将既有失公平,也偏离了问题的实质。
我们不妨同意,比较研究应该为某种全面性的理解所引导。但是运用某种特定的角度取向性方法、通过专注于研究对象的一个方面而进行的比较研究活动与一种全面性的理解并非不一致。在这一问题上,需要认识到的是,作为当前正在运用的角度取向性方法与方法论指导原则之间的重要区别,后者乃是当事人在运用这种角度取向性方法时先行设定的、且将被当事人用以指导或规范应如何在考虑某些另外相关的角度取向的情况下来进行和评价当前的角度取向活动。一个人采用某种特定的角度取向性方法的反思性实践本身既不意味着反思性地否弃某些另外相关的角度取向性方法,也不意味着预设一种将其他的角度取向性方法(如果确实存在的话)视为不相关的方法论指导原则。⑩
我们已经讨论了可能被指责为危害所谓解释性取向的比较研究活动的三宗“罪过”(即“过分简单化”、“外在资源的过分运用”和“模糊的等同”),又将如何认识剩下的另外一宗即“夸大差异”的“罪过”?这一问题比其所显现的复杂得多。正如前文所讨论的那样,当该比较研究活动采取历史取向时,这一“罪过”乃是与过分简单化的“罪过”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当一个比较研究活动采取解释取向、且通过专注于研究对象的一个方面而将研究对象简单化时,它也会自动地犯下“夸大差异”的“罪过”吗?前述的关于具体的角度取向性方法与方法论指导原则之间的差异问题的讨论在这里再一次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一问题。存在争论的问题是,解释者是否业已设想一种恰当的方法论指导原则,以指导和规范如何看待被用作为正在运用的角度取向性方法,与将指向研究对象的其它方面的其它相关的角度取向性方法,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与之相应的是,当人们评价一种比较研究活动时,对他来说,真正重要的是,看一看在正在运用的角度取向性方法背后,先行设定了何种方法论指导原则;只有考察了这一问题之后,关于“夸大差异”的指责才能获得恰当的评判。
现在让我们转而考察第三种基本取向,即旨在协同促进共同的哲学问题的解决而关注于建设性互动这一基本取向。比较研究中这种基本取向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反思性批判和自我批判,寻求处于比较考察之中的双方如何能够协同、建设性地贡献于某些共同关注的哲学问题,(11)而不只是满足于提供对于每一方的历史性或描述性的说明,或只是单纯解释在某个传统或解释性说明中所历史地形成的某些观念而已。从典型性上说,在通过比较来阐明某个共同关注的哲学问题过程中,在不同的哲学传统或解释性说明中历史地形成的某些实质性的观念将会明确而直接地有助于揭示它们何以能够协同而互补地以某种哲学上有益的方式促进对共同关切的问题的认识。在处理各种共同的关切和哲学问题时建设性的互动是最有益于哲学发展的就此而言,这种比较研究的取向和其方法论战略就将直接、明确而建设性地导致哲学上的互动,并因此被视为最有益于哲学的发展。在充分注意到一种以此作为其根本取向的比较研究活动的本质特征的情况下,让我们考察一下在前已述及的、有时候甚至常常用来批评这种取向的比较研究的四宗“罪过”之其中三宗的恰当性问题,这三宗即是所谓过分简单化的“罪过”、过分利用外在资源的“罪过”以及模糊等同的“罪过”。
在这样的比较研究活动中形成一种哲学上建设性互动的典型程序无论在概念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可以分成三个阶段:(1)前互动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将不同传统或解释性说明中与有待考察且与共同关切的问题相关的、因此与该研究项目的目标相关的某些特定的观念识别和突出出来;(2)互动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这些观念根据共同关切的问题和所服务的目的彼此相互促动;(3)后互动阶段——至此,那些来自不同资源、相互差异的观念现在被吸收或同化成一个以供解决处于考察中的共同关切问题的新方法或路径。前文所述的三宗“罪过”可以被看作有代表性地分别与上述不同的阶段相联系。针对从某个传统中被选择出来的某个观念所指斥的过分简单化的“罪过”典型地与前互动阶段的反思性努力相联系;针对详尽阐述从特定传统而来的某个特定观念时过分利用外在资源的“罪过”与互动阶段中的反思性努力有着典型的联系;而模糊等同的“罪过”则与后互动阶段的反思性努力有着典型的联系。现在,让我们简要地评判一下与这三个阶段分别对应的三宗“罪过”的恰当性问题;以这种方式看待这些“罪过”将有助于从根本上凸现以建设性互动为导向的比较研究活动的特征。
(1)在前互动阶段,将一个传统或解释性说明中的某些观念简化和抽象为下述这样一种角度取向性的观点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恰当的乃至必要的:这种角度取向性的观点是完全按照与建设性互动式的比较研究活动所面对的共同关切问题与所服务的目的最为相关的方式而提出来的,而无涉于角度取向性观点所由以形成的传统或解释性说明中的无关的因素,尽管那种传统中的那些无关因素也许对于领会那些观念的含义不无益处。其理由在于:第一,这种研究活动的根本意图不是在于揭示这样一个观念如何与所在的传统或解释性说明中的其它因素相联系,而是在于它如何有助于解决当下所考察的共同关切的哲学问题;第二,人们需要在其由以提出的本文中理解一个观念的含义,而一旦他理解了这一含义(或者通过利用基于前两种取向的比较研究活动所提供的资料,或者通过基于前两种取向之一的人们固有的关于背景的比较研究活动),单纯的对背景的讨论便变得无的放矢;第三,很显然,这样一种方法本身并不蕴含地否定特定传统中特定观念的社会和历史的完整性。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样的完整性的存在并不能自动地保证一种不加区别的优先性,甚至不能保证在不考虑比较研究项目的基本取向和目的情况下,明确地阐述它究竟相关性何在。
(2)在互动阶段,从不同传统而来的那些相关的具有角度取向性的观点将建设性地彼此相互交融。从每一方的观点来看,另一方乃是某种外在的东西;但从更广阔的哲学视野和共同关切的问题角度来看,不同的观点则是内在互补的。在这种语境下,“外在”这一术语在这里对于这一目的来说,将误解问题的实质:所围绕的关键之点不在于这种或那种不同的具有角度取向性的观点,而在于那些问题本身——那些具有角度取向性的观点所指向的正是其各个方面。就所关注的问题而言,所有这些具有角度取向性的观点从它们是互补的和对于全面理解所不可或缺的意义上说都是内在的。
(3)在后互动阶段,某些同化典型地源自前述的建设性互动;即是说,这样一种等同将校准、淡化并吸收不同的具有角度取向性的观点,形成作为一个整体的新的理路;这正是比较研究中这种建设性互动真正所期望的,而决不是什么“罪过”。
应该注意的是,如果说一项明确地具有上述基本取向之一的比较研究活动被视为比较研究中的单一型研究活动的话,则哲学实践中的比较研究项目,也许是将两个或更多取向相综合为复合型。例如,一个关于历史人物的比较研究活动便包含着这样一种综合性。对上述三种不同的比较取向之特征及其分别相应的方法论路径的认识,将有助于我们有区别地对待复合型比较研究项目中的不同阶段或不同构成部分。
在我看来,基于对传统因素影响的考虑,当前应该特别强调上述第三种和第二种取向的比较研究项目(特别是当诉诸于当代哲学发展和资源时尤其如此)的重要性。其理由是:第一,就关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项目而言,它有时候趋向于被视为只是关于中国古典哲学研究的副产品或外在延伸,而后者本身有时候也在很大程度上,趋向于被视为只是关于中国(古典)哲学发展史的历史性研究;第二,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方法论路径的研究进路还没有从根本上被视为一种有效的探究哲学本身的进路;第三,前文所述的四宗“罪过”(特别是“过分简单化”、“过分利用外在资源”和“模糊的等同”的“罪过”)或多或少已经被视为某些“当然的”“罪过”,因此阻碍了朝着第三种取向方向(或甚至第二种取向的方向)而做的反思性努力,而正是后者在很多情况下常常不可避免而又恰当地“犯下”了这些“罪过”;第四,最重要的是,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特别是它的主流传统(12)),有时候被看作是本质上互不相容的;在我看来,对于立足于第三种取向的比较研究项目来说,这种态度将暗中损害或预先堵死任何严肃认真的反思性努力,易于负面地使西方哲学家和一些从事中国哲学和比较哲学研究的学者形成一种偏见,认为中国哲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像西方哲学(特别是其主流传统)那样的本质上专注于一系列根本主题、具有特定内涵的哲学。
今天,由于中国哲学和比较哲学研究领域中越来越多的哲学家已对西方哲学形成全面的认识 (既懂得其历史也了解其当代发展状况,既熟悉其各种表现形态,也洞察其深层关切,既理解其不同的当下实际运用的角度取向性方法也透彻地领悟其深层方法论指导原则),且在一系列根本的共同关切的问题上逐渐与西方哲学展开建设性的互动,对于那些既熟悉中国哲学也熟悉西方哲学的哲学家们来说,正如本文第一部分业已指出的那样,已形成越来越广泛的共识: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本质上不是互不相容的,而是在一系列根本的哲学问题上有着共同的关切,而它们在解决问题的方法、进路上又各具特色。因此,它们完全能够相互借鉴,通过建设性的对话和互动而协同地促进共同的哲学事业的发展。因此,迫切需要强调指出第三种和第二种取向的比较研究活动的意义,尽管这种强调绝对不否认第一种取向作为一种有效的路径所具有的合法性与应有的价值,而是侧重提示其与另外两种取向之间所具有的富有建设性的相容性。
而我们正在展开的“戴维森哲学与中国哲学:建设性互动”这一研究项目,正如其标题所突出显示的那样,就其主要方面而言,正是属于前文所述的第三种基本取向的比较研究项目。
(Bo Mou“On The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Comparative Philosophy Studies in View of Comment on The Four 'Sins'”原载Davidson's Philosophy and Chinese Philosophy:Constructive Engagement,Edited by Bo Mou,Koninklijke Brill NV,Boston,2006.)
注释:
①这里所说的“中国哲学”,我主要指的是从周 (约公元前11世纪至256年)到晚清(1644-19世纪中叶)的中国古代各种哲学思潮及其当代研究与发展形态。
②所谓“西方分析哲学”或“西方传统的分析哲学”,我指的是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经笛卡儿、英国经验论和康德,到当代分析哲学思潮的西方主流哲学。
③所谓“建设性互动”,我指的是通过反思性批判和自我批判,从哲学上探求来自各种不同的哲学传统、或来自同一传统自身之内不同趋向的各具特色的思想模式、思维方法或实质性观点,如何能够相互借鉴、协同一致地促进整个哲学事业的发展。
④本节的主要内容源自我对本人的另一篇论文《论比较研究中的三种基本取向与“四种罪过”》的进一步修订,载《美国哲学协会会讯》,2002年秋季号, V01.02,No.1,第42-45页;亦参见拙文《关于孔子“道德金律”理论之结构与内容的再考察》的第一部分关于相关方法论的论述,详见《东西方哲学》杂志第 54卷,第2号,2004年4月,第218-248页。
⑤所谓“比较哲学”,我不仅是指不同哲学传统之间的比较研究,而且还指任何来自不同传统以及来自相同传统内部不同趋向的不同思想模式、方法论途径(包括角度取向性方法、指南性方法或工具性方法)或实质性观念之间关系的比较考察,尽管就本论文集而言,只是通过戴维森哲学的案例,集中地致力于中国哲学与西方分析哲学传统之间的比较性互动。
⑥所谓“外在资源”,我指的是那些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或在历史性的取向下来确认资源身份时,并非为待讨论的古代思想家所实际采用的资源。不过,正如我稍后将要解释的,在某些语境下,就将要讨论的第三种取向的目的而言,使用“外在”这一术语可能会偏离问题的实质。
⑦在这里,我是在狭义或直接意义上使用“解释”这一术语,具有特定的涵义(指的是详细阐述和理解),而不是指的广义或内含的意义,在后一种意义上,这里所讨论的所有三种取向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被视为“特定的解释”。
⑧如此说来,便能认为这些含义为该思想家的文本中的观念所具有(因此属于该思想家真正所意味/反对或该思想家的观念真的所具有的)?从重要的意义上说,答案将是肯定的:因为这些含义真地为该思想家所提出的观念所蕴涵,虽然人们可以确定地说,这些含义实际上并未被该思想家所表达,因此人们也许可以说,它们并不是该思想家实际上(或真正地)所意指/曾意指的。(在这一点上,人们不难看到,诸如“某位思想家真正所意指/曾意指的”或“其所真正具有的”之类的表达法不免模棱两可和含混,因此值得澄清,尤其是当人们就一位思想家真正所意指/曾意指的或其观念真正所具有/曾有的这一问题做出断定时更是如此。)
⑨如果一位思想家有意识地使用某些似乎似非而是的语言来表达某些特定含义,则是另外一回事。不过,这样一些情况既不意味着,由这些语言所表达的观念本身实际上并非连贯一致,也不意味着问题中的观点不能以一种更明晰的术语而不再是自相矛盾的形态、从而更有效地表达出来。
⑩关于角度取向性方法与方法论指导原则及其含义之间的区别问题的系统而详细的讨论,参见拙文:《从比较哲学的角度关于哲学方法论结构的分析》,载牟博编:《两条智慧之路——中国哲学传统与分析哲学传统》,芝加哥:Open Court,2001年,第337-364页。
(11)可以有根据地认为,很多传统上被界定为不同传统中的一些“独特”的问题业已转化为本质上是关于某些共同关切的、更具有普遍性的哲学问题的不同方面、层次或维度的问题,尤其是从一种更广阔的哲学视野来看更能认识到这一点。这也正是我在前已提及的若干论著中一直所尽力倡导和阐明的。
(12)我之所以使用“主流传统”这一术语的复数形式,是为了指明一种主流传统的认定不是排他性的,而是在整个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随时间和空间而不断变化的。在20世纪,分析哲学传统在英语国家中堪称主流,而在欧洲大陆,作为其主流的则是大陆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