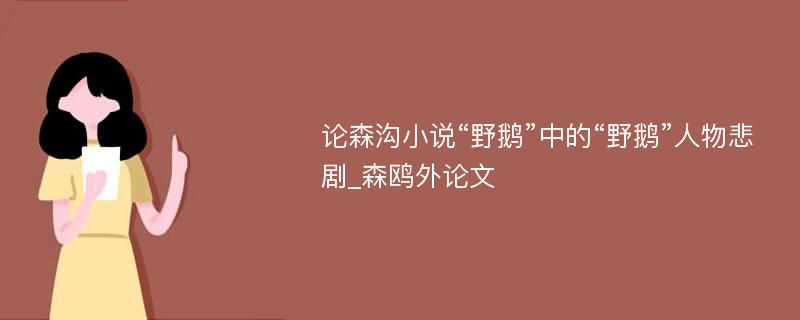
论森鸥外小说《雁》的人物悲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悲剧论文,人物论文,小说论文,论森鸥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称雄日本文坛的森鸥外,身为近代文学的启蒙者,是与夏目漱石难分轩轾的文豪。他为日本文学做出的诸多杰出贡献,已深得世人肯定。鸥外留学德国归来,以优美的汉文笔调创作的“留学三部曲”——《舞姬》、《泡沫记》、《信使》,公认是新艺术打破旧视野的浪漫主义文学先驱之作。鸥外的作品,其可贵之处表现在对伦理道德的严肃思考,对最“个人化”的情爱结构的深掘。其文学生涯后期代表作长篇小说《雁》(注:基于《雁》高度的文学价值,1953年由“大映”将其搬上了银幕。),就是他理智的双眼对爱的凝视,感伤的意马向青春旅路的回驰。
《雁》1911年9月开始发表,1915年5月籾山书店刊行了单行本。鸥外在这部以情爱为内容的作品中,尽情渲染了主人公的恶运,揭示了情感解放与社会现实之间的激烈冲突,显示了鸥外在文坛上力反自然主义、高扬浪漫主义的艺术精神。
文学艺术借助作者的审美意识与想象力,调遣语言来表现人的内部和外部世界,其中心作用旨在创造性地描写人的各种感情。感情之源虽出自多方面,但不容否认,情爱是一大主源。明治维新后,日本究竟如何对待“爱”这一大主题?深加探究就会发现,尽管当时的日本西化日甚,但纯属独立的个人同个人之间的感情——情爱,却依然残酷地为传统的旧道德和爱的某些要因所束缚。追求自由和传统道德束缚,二者殊死格斗,形形色色的情爱悲剧由此而生,从而构成日本近代文学中鲜明的一大主题。
处于上述时代文化背景下,鸥外围绕人的醒觉与爱的萌生、发展乃至悲剧命运的结局,在日本文学史上留下了《雁》这部历久弥新的艺术精品。
一、阿玉的自我牺牲与觉醒
《雁》的时代背景设在明治13年(1880年),时当日本文明开化初期。贫民的独女阿玉,是一个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女性。其母早亡,她和靠做糖泥人糊口的老父相依为命。阿玉自幼立誓:将来若能时来运转,定让父亲晚境幸福!为尽孝,鲜活水灵、天然美貌“胜于出水芙蓉”的阿玉,继被无赖警察欺骗之后,又违心地做了所谓“出色实业家”末造的小妾。阿玉走极端,只抱定一个主意:“为了救父亲于贫苦的深渊而出卖自己,所以买方是什么人,都无关紧要”(第7章)。她关心父亲比关心自己为重的心理,在第16章里,有明显描述:
阿玉除了要让父亲幸福这一目的,再没有其他任何目的了。因此,她硬是说服了固执的父亲,自己做了他人的小妾。阿玉感到自己已堕落到不能再堕落的地步了。她只有从自己的这种旨在利他的行为中,寻求一种自我安慰。
出于如此意义的自我牺牲伦理意识,阿玉住进了“无缘坂”的妾宅,由此而让父亲享上了清福。然而,阿玉却痛感“自己的这种喜悦中,混进了一滴苦汁”。阿玉出卖了不该当商品出卖的自己,这“一滴苦汁”,正是出卖肉体的痛苦。阿玉苦涩地抹消了人生欲求和人的权利,将自己下而降至与金钱等价交换的“物”。
鸥外塑造的阿玉的为亲子爱而牺牲自我的这一伦理现象,在近代日本文坛上无独有偶。明治36年(1903年)5月,新声社出版了永井荷风的小说《梦之女》。其内容梗概是,没落士族的女儿阿浪为了父母和小妹的幸福,16岁便到名古屋一家陶器制造商家当女仆。旋遭老板奸污怀孕。阿浪痛不欲生,但念及一家的生存,她含垢忍辱,做了老板的小妾。不久,老板暴亡,阿浪被逐回家。迫于穷困,阿浪又以500元身价沦为娼妇。其后从良,又成一富翁小妾。汲取已往教训,阿浪力求经济独立,在富翁支持下当上了茶馆老板娘,把双亲和妹妹接来,以共享富裕生活。岂料仅一年之间,妹妹阿绢堕落,和顾客私奔,父亲不适应新环境,且思念阿绢,精神恍惚,被邮递马车撞死。阿浪苦苦做出的诸般自我牺牲,到头来非但未能救助一家,倒是引出相反结局。阿浪陷进无边的烦恼与虚无感之中。
我认为,荷风的这部小说旨在证明:正像贫困是一种灾难一样,对于缺乏充分文化心理准备的人来说,暴富也是一种灾难。所以,爱(奉献)的付出,应据对方的素养情趣程度差异而把握好限度,并非只要牺牲自我,凡是“无私奉献”,均能救助他人。双方的生活审美意识某种程度的趋同,乃必要前提。能否适应社会环境,这是颇为重要的个人文化心理。社会环境尚处混沌状态,如果人对社会环境的美恶辨别能力又甚低,这时,如果一味顺随自己的素朴的善意,无限度地自我牺牲,结果往往会适得其反。《梦之女》的结局,便是一个极有说服力的佐证。
与《梦之女》相异,《雁》里的阿玉牺牲自我,救助的仅限于只渴望安定生活的老父一人,其有碍于自我牺牲的正常发展的不安定要素,远比《梦之女》少,使得阿玉的自我牺牲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初衷。
阿玉完全为父亲而活着。她搬至“无缘坂”第三日,鱼店老板骂道:“我的鱼不卖给放高利贷者的小老婆!”阿玉此时才察觉:自己竟是被人嫌恶的放高利贷之人的小妾!精神遂受刺激,开始怨恨自己的命运。此后,平素“含羞脸红、谨慎而面带微笑地给末造斟酒”的阿玉,对末造的印象渐趋复杂。她曾认为:“末造是可以依赖的人,他机灵,温厚”,未料到他竟从事“令人嫌恶的行当”。阿玉百般忧恼,怀疑狡诈的末造之人格。她向父亲告白:
我是很坦直的。可是,最近我常仔细思索,再也不愿上当受骗了。我不撒谎骗人,但也不愿被人骗……娶我为妾的事,他瞒着他老婆,他能这样撒谎,谁敢保证他对我说的全是真话。我也得提防受他欺骗。(第11章)
阿玉的苦乐全依赖他人。她要向父亲诉苦,哀叹命运的不幸。但是,孝女想及父亲好容易过上了无忧的生活,不忍心向父亲“手举的杯子里滴进一滴毒汁”(第16章)。阿玉的觉醒,发生在察觉末造乃寄生式金融业者之后,她满腹苦水无处吐,极端苦恼的结果,“奇妙地精神振作起来”,觉醒之青芽悄然萌生,“她饱受世间压迫,走投无路。走投无路促使她逐步觉醒”(注:〔日〕岸田美子:《〈雁〉的遇感》,载《解释与鉴赏》1946年6月号。)。这是“有压迫就有反抗”这一理论的实践。阿玉觉悟到:能救助自己的惟有自己:
须强化自己,让别人看到健全的自己……阿玉觉得迄今沉睡自己胸中的某种东西觉醒了,自己迄今全依赖他人,如今意外地好像独立起来了。阿玉快意地走在不忍池(注:位于东京上野公园西南部的水塘。自1625年初建立之时起,池畔祭祀主管吉祥的女神“辨财天”,故有名。池中莲花名传远近。)畔。(第11章)
阿玉发现了“自我”这块焕然一新的精神生活领域,女性被抹杀的意志解冻苏醒了。她发现自己跃动的“真心”在嘲笑低俗的末造和成为末造的玩物、麻木的自己。阿玉“胸中的某种东西”和“真心”,不外是渴望解放自我、掌握自己命运的那样一种力争自由的独立自强精神。她认为,为追求应有的幸福而生活,乃人生最大目的;人的生活是流荡不息的希望的继续,这是做人的权利。阿玉开始逐渐疏远“除了金钱之外什么也不想”的守财奴、独见肉不见灵的末造,意欲逃出肉欲火炕,憧憬有精神交流的灵的生活。阿玉把这种希望寄托在经常从门前通过的大学生身上。阿玉恣放想像,严密思索,周密筹划,以期实现改变自己命运的愿望。
二、爱的偶然发生与发展
秋季到来,阿玉敏感的双目捕到了一个理想目标——风度翩翩、充满自信又具文学气质的医学部大学生冈田。阿玉和窗外的冈田偶然目光相撞,遂送去嫣然一笑。其后,冈田一经过无缘坂,都本能地想起阿玉,朝窗口“投上几缕注意的目光”。他散步至此,几乎准能见到阿玉。日久,冈田突然脱帽向阿玉敬一礼。顿时,阿玉白晰面颜染上一片红云,
寂寞的笑颜,变得像绽开的新花一样美丽。“
从心理机制看,爱的成立以互不厌嫌为必要前提。阿玉为获得爱而费尽苦心,其努力初见成效。阿玉心有灵犀,悟到了冈田和自己的心理感受已初步相通。“感觉是幸福的最大窗口,这方窗口是新鲜生活流动的通道。”(注:〔日〕石丸梧平:《艺术与生活创造》,小西书店1923年5月版,第8页。)。如此的心理跃动乃至来自敏锐的女性直感激动,推动阿玉靠近了幸福的路口。同时,阿玉由沦为末造掌中玩物这一苦境,朝理想的爱这一光明目标迈出了一大步,她将冈田的形象镂上了自己的心版。
论述《雁》的情节发展,对于事理上不一定发生而发生的、超出一般规律的情况——“偶然”,不可避而不谈。这里,让我们解析一番此作中“偶然”的实质。第一个“偶然”——初遇,在冈田,纯属预想之外的“偶然”;但在阿玉,其中则“必然”要素甚浓。觉醒了的阿玉,每日绞尽脑汁,像猎人虎视眈眈搜寻猎物一样,将爱的目标选择范围严格限定于“门前通过的大学生们”,阿玉时刻准备着。
不过,这种情况下,按逻辑学原理,阿玉单方面努力只能构成事物成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求成功,对方共鸣不可缺。第一次“偶然”,幸运的是冈田发出了初步的共鸣,通过“灵魂的窗口”,二人心田里冒出了朦胧爱的嫩芽。
接着,末造买来红雀,为阿玉和冈田的感情升华客观造成了第二次“偶然”。在末造眼中,阿玉的价值与红雀无异。鸥外在第17章写道:“笼中鸟大概是害怕笼子摇晃,双爪死死抓住木条,紧收双翼,一动不动。……末造眼观可爱的小鸟,心里想着可爱的阿玉,坐在餐馆里,把并不怎么好吃的茶泡饭吃得喷喷香。”
针对两只红雀在作品中的重要作用,森安绿先生指出:
二只红雀象征着阿玉心灵(精神)和肉体(现实的境遇)。……被蛇咬住惊恐欲死的红雀的形象,可谓阿玉孤弱的形象,她对被末造紧抱的自己的境遇表示绝望。同时,为逃出蛇的恐怖而扑腾不止的另一只鸟的形象,令人感到是象征着一个女人为摸索命运的新境涯、为追求自立而挣扎不止。(注:〔日〕《〈雁〉论考》,《就实语文》1986年11月号。)
笔者认为,这一观点言之成理。可以说,在鸟、笼、蛇的艺术设定上,鸥外注入了新颖的艺术匠心。笼和蛇皆旨在暗示末造对阿玉的束缚与蹂躏。自古以来,按艺术审美意识,飞在文艺世界里的鸟,一直是自由的象征。欧阳修的《画眉鸟》中“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实例。
蛇咬鸟,冈田斩蛇救鸟。鸥外的如此艺术用意,在于让冈田救阿玉逃离人生泥沼。在这一事件发生现场,二人打开了亲切对话的闸门。阿玉从冈田身上感到了无限魅力、忧郁心空突然变得晴朗,她觉得冈田向自己送来了精神上的光明。
斩蛇救鸟事件的意外发生,促使二人在情爱台阶上高登到至关重要的一级。偏于理智的冈田,其感情世界隐而不彰,因此,鸥外把浓墨涂在阿玉一方。此后,阿玉的恋情发生了“惊人程度的急剧变化”,求爱的心理活动直线升级。
围绕女性面对爱产生的微妙心理变化,鸥外在第20章里做了简洁明了分析。即:第一,女人购物时有这样的心理,尽管喜欢那物,但并不想买,于是,“喜欢”和“不买”两种心状混溶一体,生发一种带有微细的甘美哀伤情绪,女人以品味如此情绪为一种审美快感;第二,女人想买的东西强烈地吸引着她,促使她不立刻如愿便苦痛难熬,纵然明知稍待几日便极易到手,她还是焦燥得度日如年。
思索起来,阿玉的爱,完全是自发而强烈的感情,其心状相当于上述两种情形中的后者。阿玉觉得,冈田“如今突然变成自己‘想买’的‘东西’了”(第20章)。阿玉极欲接近他,思量着送给他藤村牌“乡村馒头”等礼品,企冀通过物质奉献,达到精神夺取。阿玉心室里只收纳冈田一人:
末造来了,二人隔火盆聊天,阿玉觉得对面坐的是冈田。起初,阿玉责怪自己这样的心理太放恣,渐渐觉得思念冈田,这种心理其实很正常。她常常心不在焉地迎合末造的话尾,末造不采,阿玉得自由,便闭目想冈田,经常梦中和他在一起,秩序和发展过程简化了,没有烦琐。阿玉正觉得“啊,太畅美啦!”惊喜中睁眼一看,对象不是冈田却是末造!于是,阿玉的神经兴奋得难以入眠,有时甚至焦虑得哭泣起来。(第20章)
爱是一种根源的热情与强烈的愿望,其神髓表现在双方高度的融合与统一。对于爱的本质,有岛曾下过这样定义:“爱是掠夺性的激越之力”(注:参见〔日〕有岛武郎:《爱是恣意夺取》第17章。),“个性为了自身的成长和自由,以爱为手段,意欲从外界夺取一切可夺取的东西。……个性越是活跃,爱的活动越是触目惊心”(注:参见〔日〕有岛武郎:《爱是恣意夺取》第18章。)。体现在阿玉身上也确是这样。她极欲占有(夺取)冈田,哪怕只是两三天没相见,胸口便堵得透不过气来。究其因,这正是一个觉醒了的女性做了自己感情的主人之后,能动的感情强烈律动的结果,是贯通于“爱”这一复杂事象构造底奥的铁则——“夺取”原理发挥作用后产生的正常现象。这条铁则不问古今中外,永恒控制着每一个有真爱的人之心理活动机制。《诗经·关睢》中“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以及白乐天的千古绝唱《长恨歌》中表现的爱的底流,都不难看到爱的“夺取”法则的显著功能。阿玉的心理,当然也无法违背爱的本质规律。
究明爱的神髓,是《雁》的一大主题。爱在日本近代文学中,是一块衡量自我觉醒和个性自由的试金石。举凡二叶亭四迷的《浮云》、《面影》,漱石的《虞美人草》、《其后》、《门》、《心》,武者小路的《友情》,有岛的《一个女人》、《宣言》等等,无不通过解剖恋爱内质来揭示近代人的自由和解放,进而证明一个命题:人一旦享受到来自主体的爱,其精神生活必定为之一新。阿玉正是这样,因有了主体的爱,她风采卓然,神情鲜活,富于女性魅力。这变化的奥妙,连老谋深算的末造竟然也无法看透,他居然得意洋洋地误认为:“阿玉终于懂情了,这是我培养出来的。”
阿玉的爱蓬勃增长之际,第三次“偶然”发生了:末造到千叶出差。阿玉喜不自禁,痛畅接近冈田的良机终于来临。她把女仆阿梅打发回家,无人掣肘。面对爱,阿玉抱紧如下主张:
女人无论做什么事,在做决断之前往往苦痛地踌躇。可是一旦下定决心,她不像男人那样左顾右盼,而像戴着“蒙眼”的马一般,径直朝前方猛然狂奔。即便深思熟虑的男人心怀疑惧的那种障碍物横阻前进的途中,女人也满不在乎。总之,女人敢为男人不敢为之事,并且会意外地获得成功。(第21章)
这很合乎女性心理发展轨迹。针对爱,女性属精神专注型,她甚至可能调动自己所有的注意力投注于爱。为了爱,阿玉像《舞姬》中的艾丽丝一样,全身心倾注于冈田。她感到时机成熟,万事俱备,相信自己筹划的周密性,对实现目的充满自信:“事情的发展这样顺畅,纯是终极目的很容易实现的前兆。”阿玉心中生出空前的勇气:“今天无论付出多大牺牲,我也要向他畅诉我的衷肠。”
然而,阿玉万没想到,由于最后一次“偶然”和自己的命运,她的理想彻底破灭了。鸥外的历史小说《最后一句》和《山椒大夫》中,“偶然”与努力,二者有机融合,理想终获成功。《雁》的前半部分,阿玉的积极努力与一连串“偶然”也达到了巧妙暗合。由“偶然”和人智相结合产生的动力,驱动阿玉渐入爱之顶峰。遗憾的是,在命运之力重创下,阿玉的爱,如鸥外《泡沫记》中的巨势和玛丽的悲剧,先甜后苦,化作泡沫,消失在恶运中。
三、命运引发了爱的凋落
按日本学术界流行的观点,阿玉的悲剧因于第四次“偶然”,即“酱煮秋刀鱼”。之后,各种不祥的“偶然”纷至。冈田的友人“我”,将这次“偶然”喻作西方文学中《一根铁钉》的故事:“那故事的内容是,车轮掉了一根铁钉,紧接着坐在车上的农民的儿子迭遇难关。……酱煮秋刀鱼起的效果,与那根铁钉相同。”
“我”吃晚饭时,桌上出现一盘自己最讨厌的“酱煮秋刀鱼”,遂“罢饭”,约冈田外出散步,“我”成了阿玉、冈田相会的障碍者。阿玉大惊,失去了二人的世界,绝好的密会被惨烈破坏。她失神地望着冈田背影,陷入无限的哀伤。
面对阿玉的举动与神情,冈田沉默不语,悄然走过。同行的“我”认为冈田极不自然,冷静得近似冷酷。“我”在心中这样地批判冈田:
像冈田那样被美女追慕着,是多么愉快的事。……我要是冈田,决不能逃走。我上前和她搭话。……我要像爱妹妹一样爱她,助她一臂之力。救她逃出泥沼。(第22章)
纵观鸥外个人性格特色及其文学表现特征,我们有理由认为,如果把俯首疾步走过无缘坂的冈田看作是理智的、现实的冈田,那么,“我”的以上独白,则可认为是情热的、浪漫的冈田内部世界状貌。被创作主体严格操纵着的、作为鸥外分身的冈田,他胸中“理智”与“情热”两种心态一直处于纠结搏斗状态。
最后的结局,作者这样设定:冈田站在池边,为赶走池心岛上雁群抛去一石,不料竟打死一雁。雁的死,象征着阿玉爱情的破灭。
“偶然”似波澜,不断冲击二人的感情世界,这确是事实。不过,洞察其本质,关于二人的永远别离,“酱煮秋刀鱼”和“雁之死”等“偶然”,至多只起到象征性艺术作用,而最实质性原因,其一是冈田突然应邀出洋留学。不难想象,当年的留学,对功名欲强烈的冈田会有多么大的魅力。面临学业(功名)和爱二者择一之际,总是取前者,这是不能彻底献身于爱的、理性的鸥外性格使然。鸥外把如此意识移入作品,令冈田代己展现出来。冈田(鸥外)偏重理性,他和“青春小说”《舞姬》中的丰太郎(欧外)属同一类型人。冈田懂得爱,也需要爱。他既憧憬爱,一旦爱来到眼前,他又踌躇不定,最后割舍了来自阿玉的纯情。丰太郎走进爱河,酿出了悲剧;与之相比,冈田却徘徊河畔,进与不进之间,心绪千万难,最终还是在保持距离的情况下分手了。文艺美学家冈崎义惠先生这样评断鸥外的情爱观:“他是以自己的悟性掩盖心底的情热。是一个看似情热很枯淡的人。”(注:参见〔日〕《鸥外与漱石》,要书房1955年1月版,第12页。) 鸥外恰恰将自己的这种基于理性的“悟性”活用在冈田身上,令他以“悟性”来支配爱。归根结蒂,《雁》在爱的美学观上与《舞姬》其揆同一,是《舞姬》这株艺术之树的主干上长出的新枝。
《雁》的命运性爱情悲剧的致命的本质原因,在于二人个人文化背景和社会地位的悬殊差别。二人分别属于两个世界,分别被赋予了不同命运。冈田是医科大学的高材生,他立于明治文明开化的潮头,肩负日本社会发展的未来。这样的冈田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庶民阿玉,无论在个人文化背景上还是社会地位方面,都横亘着一条宽阔的断层。其实,阿玉已痛感自己文化教养低浅,“连一封令自己满意的信都写不出来”,与冈田不般配。两者之间的这种障碍,与《信使》中目不识丁的纯情牧羊少年挚爱富有同情心的贵族小姐伊伊达的情况相似,其悲剧结局亦无大异。
正直纯情的阿玉确实觉醒了。她无限欢喜地追求着真正的爱。然而,她得到的却是不可名状的苦涩。阿玉没有坚实的社会地位和属于自我的独立经济基础,所以,无论她如何渴望真正的爱,希望逃出深渊,过人的生活,但残酷的现实不容许阿玉得到这些,这美好、正当的理想,对阿玉而言,只是一簇绽开在峭崖上的鲜花,可望不可及。这才是阿玉的命运悲剧。
按作品中情节看,降临在阿玉身上“偶然”的恶运,是“酱煮秋刀鱼”和“雁之死”,乃至冈田出洋。其中除了“出洋”(鸥外的德国留学),余皆作者根据自己的意志做出的虚构。作者通过如此设定,企图将爱的悲剧归于不可知的宿命论。实则不然。不难看出,最现实的恶运,是阿玉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及立于其上优越的社会地位。这正如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论断:“钱,——高雅地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关于经济与女性的独立和爱的深层关系,终生关心女性命运的有岛,亦明示出以下见解:
现代女性可谓都是卖笑妇。她们寻求的结婚对象,或者是有地位的男子,或者是有财产的男子。
为什么说与有地位和有财产的男子结婚是卖笑行为?因为在现代组织中,女子不具有经济独立性、不依赖有地位有财产的男子,便无法生存。
缺少经济独立性的女性,依赖男子的怀抱而生存下去,通过与男子同衾以获得生活之资,她们除了选择卖笑妇手段外,还能选择什么呢?
……只要不根本改造现在的经济组织,不消灭财产私有制度,女子就永远不能由当卖笑妇这种失常的命运中逃脱出来。(注:〔日〕《爱的纯真与女性独立》,载《新女性》1923年2月号。)
有岛的尖锐观点,乃针对日本大正时代挣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女性命运而言,同时,本质上也准确掘出了特定社会关系和历史环境中阿玉命运之源。病根已经找到,但是,经济组织的改造是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弱女子阿玉对此是无能为力的。这是缠在阿玉身上的恶运,人的生涯一旦为如此命运所支配,悲剧很难避免。
贫困往往使人卑怯和不自由,人的价值也常常受金钱制约。阿玉做末造之妾,为的是摆脱贫困,她明确意识到自己品尝的是“苦汁”和“毒汁”。尽管如此,一旦在经济上中止了对末造的依赖,阿玉和父亲又势必立即陷入寸步难移的窘境。可见,建筑在经济基础之上的高贵的社会地位,与阿玉风马牛不相及。
爱,是一种能动的内部生命活动,是个性自由的高度实践能力,它具有“自我存在和自我完成的绝对性”。(注:希梅尔(Georo Simmel):《爱的断想》(日文版),岩波书店1980年版,第20页。)但是,这种意义的爱,其前提是:人必须是一个能独立起来的人。尽管阿玉觉醒了,觉察到“自我就是目的”,并向命运挑战,但她欠缺的关键一点,正是与个性自由血肉相关的个人独立。被这种恶运的“必然”死死束缚着的“明治新女性”阿玉,其境遇已经超出了她个人的悲剧范围,广泛代表了明治时代大多数社会下层女性欲爱不能的社会性悲剧。
作品是以作者所体验的感情感染人为其一大特征的。阿玉原型是鸥外自传小说《性欲》中初恋时难忘的“秋贞姑娘”。理智支配下的鸥外创作《雁》,在主观意图上,亦含有是对青春时代失去的爱做出的回想和鉴赏之成分,流露的是哀伤和感叹。作为自己恋爱史的彻底清算,《雁》的诞生,是鸥外自己胸中潜藏的爱最后一次总括性艺术升华。对此,冈崎义惠先生做了令人信服的评论:
《雁》的问世,证明鸥外对恋爱持有的热情已倾诉净尽。与此同时,他的创作力开始低沉衰微,创作素材转向追随历史事实,文艺中“美”渐次让位于“真”。其发展的终极点,是晚年的历史考证作品。(注:参见〔日〕《鸥外与漱石》,要书房1955年1月版,第5页。)
应当承认,此论可谓的评。从鸥外的文学生涯看鸥外文学的发展变化轨迹,《雁》确是决定鸥外文艺美学意识分界线的一部十分重要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