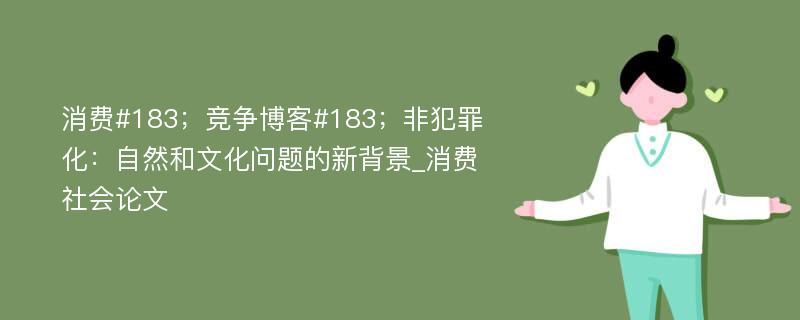
消费#183;赛博客#183;解域化——自然与文化问题的新语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赛博论文,自然论文,文化论文,解域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献编号〕1000-2952(2007)05-0095-08
关于“自然”,威廉斯这位现代术语溯源大师说,它“可能是语言中最复杂的词语”。①这个“语言”在威廉斯当然是指英语,但是“自然”一词的复杂性并不只是限于英语,也不只是限于现代的或古代的西方语文,即使在汉语言里,同样包括古代的和现代的,情况亦复如是。这是因为,自从有了人类的文化思考,“自然”就无时不是我们之所是、所欲是,或者我们与之相交往的对象;它无论是什么,但都不在我们之外。那“自然”就从来是我们的“自然”。
而说到“文化”,其复杂程度也许较“自然”有过之而无不及。威廉斯曾经抱怨:“我不知道有多少次我希望我压根儿就未听说过这个该死的词语。”②不过就他本人说,作为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先驱,他不仅未能澄清反倒是加剧了“文化”一词的语义混乱,因为由他启动的“文化研究”总是致力于将那些通常不属于“文化”甚或与之相对立的东西如“反文化”也容纳进“文化”的范畴。“文化”被扩大了,它无边无际,似乎涵盖了一切的人类活动,成了与纯粹“自然”相对的“人文”或“人文科学”的又一称谓。
面对如此语义超载的“自然”和“文化”,任何的研究尝试都可能冒着无功而返或徒添乱象的风险。笔者所以仍然选择这一研究乃是首先基于一个原则性的认识:捍卫一个词语的边界并无多大的意义,对于我们重要的是人们何以要变更它的边界,而不是另立新词。这里从形式上看是有符号的惰性的原因,文字一经创制便不轻易改变,活跃的是对它的使用,在不断的使用中不变的字词被赋予新的意义。而往深处究问,此中则更可发现文化运行的一个内在规律:文化史就是对传统的尊重和超越。因而研究不变的“自然”和“文化”如何被不断的修改其语义界线,也就是对人类文化史、思想史轨迹的呈显,以及对其未来走势的窥测,或者说是意味着达到一种文化的自觉、省思和选择。
老话题是可以常说常新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其自身的普遍性和永恒性,而另一方面当是有来自于日日更新的现实以及我们相应的新感受、新理论的刺激。重提“自然”和“文化”这种古老的话题,因而一方面就是由于它们来自于传统,来自在于我们永恒的存在难题,我们总是徘徊在“自然”和“文化”的话语之间,而一方面或许更具决定性意义的是由于一个当代新语境的出现,是它赋予我们之谈论“自然”和“文化”以新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 生产的终结与消费的兴起
如果说在古代名利缰索对人性的捆绑让我们的先人时时怀有回归自然的冲动,如老庄哲学之尚“自然”与“无为”,“无为”即从否定方面而言的“自然”——“希言自然”者是也,再如陶诗之所叹,“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如果说工业革命孕育了文艺上的自然主义倾向,例如在华滋华斯、劳伦斯和卢梭那儿;那么,以符号增值、“物符”以至“拟像”为标志的消费社会则再一次地提出了何谓“我”之“自然”的问题。
根据波德里亚的观察,真实的消费欲望已经随着生产的终结而终结了;进入消费社会,一切物品都变成了符号,都归属于一个符号系统,一个所谓的“物体系”,由此一切表面看来纯为个人性的消费都不再是个人之自然需求的满足,而是对商品作为抽象符号之价值的认同和追逐。我们日日所见的广告拟像,例如,不是将消费者引向具体之物,它不在乎物之具体性,即一件商品的使用价值,它关注的是,如何将消费者带向超越具体之物的但仍由它们所表征的符号天国。消费社会是自然的丧失,是个人性的磨灭。但是,波德里亚辩白:
这并非要说不存在需要,或者自然用途,等等。而是说要认识到,消费作为当代社会所特有的一个概念,不是按照这些线索来组织的。因为,这些在所有的社会都存在。在社会学上对我们重要的以及给我们时代打下消费符号之印记的,确切地说,是将此一初始层次(即需要或自然用途的层次——引注)普遍化地重组进一个符号系统之中。这看起来就是一种从自然向文化的特殊的转变方式,或许,这也是我们时代那特有的方式。③
这样的分辩,与其说是准备承认真实需要或“自然”在消费社会在“文化”中的留存,毋宁说是更加坚持了它如何消失在一个被符号化的过程之中。在符号所标记的消费社会,我们仍然是通过消费活动来满足我们的实际需要,不过这种需要一旦被整合进一个远远超越它之上的符号系统,便不再能够继续维持其本然的存在。它被纳入一个系统,一个结构,而成为其中的一个元素。借用索绪尔关于“语言”和“言语”的区分,波德里亚指出:“这就是当今的交流结构:一种语言(langue),而与之相对,个人需要和享受不过是言语(parole)的效果罢了。”④我们仍然在“言语”,但我们所“言语”的不是我们个人的愿望,而是“语言”的定或强加。我们为“语言”所控制,我们为“符号系统”所控制。
人是“符号的动物”,如卡西尔所言。自人类结绳以记事以来,符号从来就是用以把握现实、交流信息的工具。但是,在波德里亚标志着消费社会之特质的“符号”,有必要辨别,并非卡西尔意义上的素朴的符号,亦非索绪尔那个虽不直接指称现实却通过指称“概念”而间接地意谓了现实的符号。对于索绪尔来说,既然“符号”包括了“概念”和“音响形象”或“所指”和“能指”,那么也就用不着奇怪他有时是将“符号”作为“能指”而有时又是作为“所指”。⑤任何符号诚然对于具体之事物都是一种抽象,但抽象并不等于抽象了事物,相反恰恰是由于其作为抽象而浓缩了尽可能多的事物真实,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概念” (begriff)之丰富性、之能够作为“一切生命的原则”。⑥而发生于消费社会的符号制造术执行的是一套与此完全不同的抽象化指令,波德里亚指出:
今日抽象已不再是地图、替身、镜子或概念的那种抽象。模拟不再是对一个疆域、一个指涉物或一个实体的模拟。它是依据一个实在物的模型的生产过程,这个实在物没有来源或现实性:一个超现实疆域不再先于地图,也不再比它更长久。从此而后,是地图告于疆域——拟像先行——是地图造成疆域。⑦
“模拟”是对一个模型的模拟,作为其产品的“拟像”也就不再有所指涉,不再作为某物的“表征”,它是“无物之词”。通过“模拟”和“拟像”,波德里亚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真实缺失的世界图景:迪斯尼乐园、水门事件、海湾战争、印度Tasaday原始部落、Lescaux岩洞、足球赛事、民意测验,等等,这一切一旦被“模拟”而成“拟像”,便不再是其原本的存在了。“模拟”扼杀了“真实”并以“拟像”冒名顶替,我们知道,“拟像”从来就自诩为比原本更原本、比真实更真实,由此“拟像”就成了如今没有现实性的基本现实。陶醉于这种对“模拟”和“拟像”“文化”现象的漫画化批判,后期的波德里亚似乎丢弃了前期的“消费社会”理论,但是只要我们愿意刨根问底儿,是谁创造了“模型”,然后又是谁在“模拟”,以及究竟谁更需要“拟像”,“消费”这一前期的视角就仍然是这一切仿佛是无根的后现代文化现象的最终解释,即一个现代性的解释,消费社会仍然是为资本主义所规定的消费社会。就此而论,波德里亚有绝对的理由拒绝一个“后现代主义”桂冠的赠予。消费社会在他是一个符号的社会,这是其前期的观点,但更切本质地说,是一个符号控制的社会,结合后期的观点,是一个为“模拟”和“拟像”所突显、所剧烈化的符号控制的社会。
在关于“消费社会”、“模拟”和“拟像”的论述中,波德里亚注意到新技术在其形成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例如电子技术,原则上它能够无限地复制图像;再如克隆技术,更是将“复制”观念推向一直是上帝的权力范围,人的独特性、不可重复性在源头上就被剥夺了。技术在波德里亚这里,如同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尽管程度不同,实际上就是意识形态,即在虚假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它使人不再能够真实自然地“言说”,而是纷纷认同于一种被抽象出来的“语言”系统,它如果不是虚假的,那至少也是远离于真实的言说和自然的欲望的。
马尔库塞深感绝望,在一个发达的工业社会里,也就是一个以技术为其本质的社会里,人们几乎不可复得地失掉了辨别其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即被强加给个人的需要的基本能力,一味地“按照广告的宣传去休息、娱乐、处世和消费,爱他人所爱,嫌他人所嫌”,⑧而且“只要他们继续是不自主的,只要他们是受说教和被操纵的(甚至渗透到他们的各种本能),他们对这个问题(即什么是真实的需要和虚假的需要的问题——引注)的回答,就不可能当作他们自己的。”⑨技术不是中立的因而也不是无辜的;技术所崇尚的是最大化效用,而最大化效用的实现标志就是能够被用于复制,被用于批量化生产,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再那么简单地说是技术推动了一个工业社会或消费社会的形成,事实上它本身就是消费社会。技术的目的是满足大众需要,它决不在乎什么私人性的需要。中国广告目前流行的所有人性化的技术或设计,指的不是对单个人的体贴入微,而是着眼于许许多多的单个人的。技术通达于生产,通达于消费,它本质上归属于一个大众化的意识形态。马尔库塞同意阿多诺的一个观点:“在一定意义上说,发达的工业文化比它的前身是更加意识形态化的,因为今天的意识形态处在生产自身的过程之中。”⑩是生产、技术和商品制造了一个符码的系统,用所谓的“社会需要”置换了个人需要。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体系中,波德里亚所控诉的广告拟像,它谋杀了真实的指涉,并试图取而代之,由此看来,不过是生产、技术和商品这些真正凶手的替罪羊。马尔库塞对技术所发起的意识形态批判或可能较波德里亚发展自索绪尔的符号论批判更近于资本主义反人性、反自然的本质。顺带指出,由于波德里亚对“生产”的终结,那么尽管他也注意到技术的意识形态性,但不可能像马尔库塞那样深刻地理解到技术的“生产”性,进而“生产”的意识形态性。
二 越界的赛博客
以上是就技术之“用”而言的,我们再就技术之“体”来看,如果可以认为科学是对自然的理论化,那么技术就是对自然的实际行动或手术。在技术的作用下,自然无论将是什么,但都不可能是曾经的原初的自然了。即使不从意识形态批判的角度看,如今高科技对自然的改造也已经是触目惊心的了。这里不是指为科学和技术所支撑的工业化对自然的掠夺、榨取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环境灾难,当然也不是说高科技战争夷自然为废墟的能量及其演示,我们倒确也不必完全排除这些,因为在一定的强度上它们同样唤醒了人类对自然的意识,现在我们拟强调的是,技术对自然的介入、渗透和重构已经达到了技术与自然难解难分、浑然一体的境地,似乎自然成为人的世界,反过来,人成为自然的世界,例如仿生技术和基因工程等所谋求的那样。
根据唐娜·哈拉维(Donna J.Haraway)的描述,如果不是夸张的话,发展到20世纪末的美国科技已经使三个关键的界线不复存在,一是人类与动物的,二是动物—人类即有机体与机器的,三是物理的与非物理的,其结果就是她所谓的“赛博客”(cyborg)的出现,一个并非由她发明但被她实质性地扩展从而取得了广泛知名度的术语。我们已经步入了一个“赛博客”时代,一个“人机合体”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就是原本恒定的一切界线被逾越,一切似乎颠扑不破的分类原则被打破,哈拉维宣称,“我的赛特客神话关乎被侵越了的边界,关乎有威能的融合,以及种种危险的可能性”。(11)进而言之,“赛博客”意味着自然与文化之间传统上分明的界线正在变得暧昧起来:面对“基因改良食品”(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诸如带有鱼类基因的番茄或致癌鼠等,我们无法说清它究竟是“自然的”还是“文化的”。有学者在阐述哈拉维的这一思想时指出:“当一篇文章宣布一种改良蔬菜将‘天然地’ (naturally)抵抗疾病之时,这正是‘自然’范畴不再存在的一个小小的征兆。它已经被一个至今还没有新名字的混血儿取代。”(12)这个新范畴当然就是“赛博客”,如果我们不需要为每一位“赛博客”分别命名的话。在“赛博客”之中,“自然”被“文化”化而不再存在,“文化”被“自然”化即被赋予物质现实的形式也不再存在,准确地说,不再以先前的方式或者不再独立地存在,但混合地存在于“赛博客”之中。“赛博客”是一种新的主体或身份,一种新的社会现实。哈拉维宣布:“到20世纪末,即我们的时代,一个神话的时代,我们统统都是喀迈拉(chimeras,希腊神话中的吐火女怪,狮头、羊身、蛇尾,这里被引申为一种怪异的组合物。——引注),都是被理论化的和生造出来的机器与有机体的杂交品;一句话,我们都是赛博客。赛博客是我们的本体论;我们由它那儿得到我们的政治学。”(13)这里所谓的“本体论” (ontology)就是那个挑明了“本体”为何物的另一汉译“存在论”(或“存有论”)。将“赛博客”作为我们的“本体论”,哈拉维至少有两重指谓:其一,“赛博客”是我们当前最本己的存在,既是我们存在的实际样态,又是我们存在的构成方式或本质;其二,我们这样作为“赛博客”的存在将重构我们关于这一世界的精神图景,因而“赛博客”就是世界观、神话和意识形态,就是她所称之为的“我们的政治学”。当然对她作为一个女性思想家来说,这一“政治学”首先就是“赛博客女性主义”政治学,其中“性别、种族和阶级不能为那种对‘本质性’统一的信仰提供基础”,(14)所有的“身份看来都是矛盾的、片面的和策略性的”,(15)正如被拼凑起来的“赛博客”一样。这于是也就超越了早先那种将女性作为男性之对立范畴的二元论的和普遍主义的女性主义。包括“女性”在内的任何身份都是碎裂的、复合的、混杂的和马赛克的,或者就是那个“喀迈拉”。没有纯粹的男人,也没有纯粹的女人,或许只有她所提示的“女性男人”(female man)。哈拉维的宣言是:“我宁愿做赛博客,而不做女神。”(16)这些决非号召放弃作为女人,确切地说,是放弃隐藏于“作为女人”背后的单一身份;“女神”虽好,但她是被男性所建构的普遍主义的单一身份。
因此这“赛博客宣言”的最终意味又是超越于女性主义及其政治学的,它是“本体论”,是“哲学”,(17)它控诉的是“普遍而整体化的理论的生产”,(18)因为这种生产“可能总是但现在则肯定是错失了大部分的现实”。(19)由此而言,赛博客这一新现实的出现,无待于哈拉维代其宣言,其本身就是颠覆普遍主义乌托邦的革命性力量和声音。“成为——就是成为自主,成为权势,成为上帝;但成为——也是成为一种幻觉,即陷入与他者的启示辩证法。然而成为他者就是成为多元,边界不清,残破不全,无形无体。”(20)
赛博客现实瓦解了一切形式的二元对立,哈拉维举出的例子有“自我/他者,意识/身体,文化/自然,男性/女性,文明/原始,实在/表象,全体/部分,代理/本源/(agent/resource),制造者/被制造,积极/消极,正确/错误,真理/幻觉,完整/片面,上帝/人”等等,(21)因而也就是瓦解了任何绝对化的实体,因为它们之一直作为绝对实体而存在完全是依靠了我们的二元对立概念,它们以尖锐对立的方式相互区别、标异、宣示独特性,因而取得其似乎是各有独立不倚的存在,但其存在究竟是相互性的、辩证法的。赛博客现实解除了“二”,即二元论,于是也取消了“一”,即普遍主义的“一元论”。(22)历史地说,一元论从来就假定和包含了二元论;或可换言之,二元论不过是一元论的两次述说,这在一切形式的形而上学那里都无例外。
在以上哈拉维所列举的诸多二元对立概念中,我们所最关注的是“自然/文化”界线在赛博客中的内爆,这一方面是由于赛博客对它挑战的直接性,而且更由于“自然”一语从来所体现的本质主义而普遍主义的观念,即是说,因其本质就必然地普遍。无论从技术上还是从哲学上,赛博客对于传统的“自然与文化”的二元对立及其中对它们各有纯净身份的设定都是一场足以使其灭顶的灾难。在赛博客面前,追询“自然”将是迂腐的,哈拉维通过其“赛博客”取缔了“什么是自然”的问题。但是当哈拉维仍然试图“重建日常生活的界线,在与他者的局部性连结中,在与我们所有的构件中”,(23)当他指出赛博客形象“同时意味着建设和毁灭机器、身份、范畴、关系和空间故事”,(24)在这些拆毁和重建中,她将依据什么来进行赛博客实践?她反对批评者视她为相对主义者,但即使相对主义,也有言说的绝对性,言说那不可言说者,只要我们有意图去把握一个对象。只要有“重建”,甚或只要有“拆毁”;只要有“联结”即使是局部的,只要有“沟通”即使单个性地,它们都是意图行为,都是对对象的一种把握,那么这就必然要求一个原则,即使是临时的。简言之,只要哈拉维不是相对主义地或者即使是相对主义地对待“自然与文化”,那么“何谓自然”的问题仍将一再绽现。
按照我们的理解,赛博客决非取消了“自然与文化”的问题,倒是以它对自然与文化之界线的凌越而突显了二者在当代技术社会的问题性以及作为一个问题的严重性。“自然”即“本质”,“本质”即“理性”,除非我们不再运用理性,不再作为理性的动物,否则我们就将一再地探问“自然”,尽管我们永远无法得到一个标准而普适的答案。
三 作为解域化的全球化
使“自然”与“文化”及其关系突显为一个当代论题的另一语境是如今我们正在经历着的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的文化性首先来自于经济实践本身所赋有的文化内蕴。约翰·汤姆林森写过一部关于全球化与文化关系的专著,虽于此基本上未曾触及,但其于“文化”和“全球化”的界定并在此界定中对二者关系的阐发则在另一条路线上揭开了全球化之内在的文化性或深刻的文化后果。这些定义,单独来看,其实都不怎么新鲜,甚至或有可能使人产生一种熟腻的疲惫:所谓“全球化”就是“解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就是“复杂联结”(complex connectivity);而“文化”则是那总与一定的地域性相关联的日常生活实践。然而就是这些皮相的老生常谈却在一个理论之相勾连中将他带入了隐藏于全球化深处的文化奥秘:他发现,全球化,“其文化影响的关键点在于地方性本身的转型”,(25)“解域化是……全球联结的主要的文化影响”。(26)他的意思是,全球化以其解域化而必然地重塑了文化体验所依赖的地方性,于是全球化就一定与文化相关,可以进一步说,全球化本身即是文化性的。
但是接此我们必须强调汤姆林森这里不太在意或者说在其《文化帝国主义》一书为他所反对的一个论点:全球化既然作为一种“解域化”,究是具有“解域化”的行为主体,如果不单纯是那个“文化帝国主义”,应该也包括反抗“文化帝国主义”的被殖民者的反作用力量。因此,全球化就可以被更准确地描述为一个文化竞争的过程。哪里有“解域化”,哪里就有“再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而无论“解域化”或者“再域化”,其中都必定充满着各种力量的矛盾、斗争和相互施加影响的努力。全球化之作为文化性的实质恰在于不同文化之间所发生的这种种的关系,对抗性的或协商性的;更明白地说,全球化的文化性恰在于它的“文化间性”,在于汤姆林森所谓的“文化影响”(cultural impact),即在于它的影响性,其越界影响和相互影响;虽然对汤姆林森或许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但他似乎仍是不够重视或者不能重视,因为他曾经根本上是批判于此的,这样我们就仍需强化和伸张全球化的主体性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即使说不是全部,越界的经济就是越界的文化,经济的主体也是文化的主体。
“文化间性”,“主体间性”,我们不怀疑,这些概念的提出是为了在不同的文化之间、主体之间建立对话性和交往性的关系,但这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凡对话或交往之进行,必涉及两个前提性假定:第一是对自我身份及其特殊性的确认,第二则是对自我之局限的意识从而对他者的开放。当前解域化所引发的剧烈的文化冲突当来自于前者,即来自于自信、自我确证和自我中心的文化主体意识,而绝非是对他者的理解、对其异质性的德里达意义的“宽恕”,包含了“先行给予”的宽恕。
全球化或者说就是解域化引发了文化间的冲突,如果说作为解域化的全球化内在地就是文化性的,那么我们也可以略嫌极端但仍是合理地说,全球化本身即意味着文化冲突。汤姆林森之文化地界说全球化在继续地启发我们由他出发、由他前行:文化冲突既是全球化的显在形式,更是它自身的内在构成或本质存在。进而文化冲突也必然涉及文化的自我辩护,即前述全球化的第一种假定。自我的确立依赖于对超于自我的一个普遍合理性的诉求。找不到一个合理性的支撑,自我的建构将是脆弱不堪的。这外于自我的合理性不可能出自于“文化”,因为“文化”显系人为,是二级的和派生的。
前现代神化“自然”,现代性似乎祛魅“自然”,其实那是现象的“自然”,在作为规律性、普遍性的意义上, “自然”仍是其最终的依据。以当代世界一个最基本的价值“自由”来说吧,其论证在启蒙哲学家例如卢梭那里就是以“自然”为不可继续解释的即绝对的本体论的。请看他的名言:“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27)人的“自由”也包括“平等”(28)是与生俱来的,是生命存在的本然状态,是所谓“天赋人权”。生命具有无上的权威,我们可以由它来解释一切,而它自身却是无需解释的,它是自明的,如斯宾诺莎所说的“自然”,是以其自身为原因的。这是卢梭格言所表达的基本意思,而联系于其法语原文的分析将向我们揭开卢梭所言的“生”与“自然”的同义,与生俱来的权利就是从无需证明的“自然”那里得到承诺的权利,“自然”的无可问辩的权威保证了从它那儿所得到的权利的无可置疑:
L'homme est né libre,et
par-tout il est dans les fers.(29)
其中“né”是汉语所不习惯的一个思维“被生”,即生命是被给予的,但这个被动式中实质上又不存在施功者,生命是生命的自我呈现,因为这个“生”就是“自然”,是自行作为的。在法语中,“生”的原形为“naitre”,“自然”是“nature”,二者共有一个拉丁词根“na”。而在拉丁文中,“生”是“natus”,“自然”是“natura”,相似性则看起来更多一些。这种“生命”与“自然”的同源性暗示了它们在原初上的同一,它们根本上就是同一个东西。其他如“纯真”(naif)、“民族”(nation)都与“生命”或“自然”具有微妙而可见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全球化作为现代性通常即采取卢梭这样的合法性论述。一切原本属于西方文化传统和理想的东西,都被说成是本之于自然的,具有普遍的有效性。例如说,资本主义是“历史的终结”,因为它反映了“自然”本身或人性“自然”的要求。“文化”尽管由“自然”而来,如李凯尔特的定义所指示,但它毕竟经过了人的“耕作”,因而便不再等同于“自然”。文化间的相异性由此而生。全球化使相异的文化相遇、相冲突,而与文化冲突必然地相伴生的则是援之于“自然”的自我申辩。如果说全球化本身即意味着文化冲突,那么它同时也是意味着对“自然”的不同阐释间的竞争和斗争。全球化使古老的哲学问题“自然”和“文化”及其关系呈现出新的迫切性,当然还有新的复杂性和新的魅力。
以上我们只是从当代语境中挑选出三个突出的方面,消费、赛博客、作为解域化的全球化,以证实“自然”与“文化”作为一个问题的永恒的当代性。岂止是这些,在女权主义对男性话语的颠覆中,在对当前所发生的各种伦理道德问题如克隆人、堕胎和反堕胎、死刑之存废、乞讨的权利等等,在对环境问题的讨论中,在动物保护者组织那儿,其实在人的一切文化行为方面,也就是说,凡有文化问题的地方,都有“自然”问题之存在,因为我们总是生活在文化的自然中或自然的文化中。没有无关乎自然的文化,也没有无关乎文化的自然,永远地“剪不断,理还乱”。(30)大概永远地去剪理“文化”与“自然”的问题将是人类难以逃脱的宿命。不过既然如此,我们倒不如当它为一项事业好了。
注释:
①Raymond Williams,Problems in Materialism and Culture:Selected Essays,London:Verso,1980,p.219.
②Raymond Williams,Politics and Letters:Interviews with New Left Review,London:New Left Books,1979,p.154.
③④Jean Baudrillard,Selected Writings,ed.& introduced by Mark Poste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p.47~48.
⑤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00页以后。
⑥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27页。
⑦Jean Baudrillard,Simulations,trans.Paul Foss,Paul Patton and Philip Beitchman,New York:Semiotext(e),1983,p.2.
⑧马尔库塞:《单面人》,《法兰克福学派论著选辑》(上卷),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外国哲学研究室编,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494页。
⑨⑩马尔库塞:《单面人》,《法兰克福学派论著选辑》(上卷),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外国哲学研究室编,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495、499页。
(11)Donna J.Haraway,Simians,Cyborgs,and Women: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New York:Routledge,1991,p.154.
(12)乔治·迈尔逊:《哈拉维与基因改良食品》,李建会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5~106页。
(13)(14)(15)(16)(18)(19)(20)(21)(22)Donna J.Haraway,Simians,Cyborgs,and Women: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p.150、155、177、181.
(17)出于对西方认识论的反感,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和德里达都将“哲学”作为“本体论”。这是对“哲学”概念的狭义用法。
(23)(24)Donna J.Haraway,Simians,Cyborgs,and Women: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p.181.
(25)(26)John Tomlinson,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Cambridge:Polity,1999,p.29~30.
(27)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6页。
(28)卢梭又言:“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同上,第7页)。
(29)J.-J.Rousseau,Oeuvres Complètes,Ⅲ,Paris:Gallimard,1964,p.351.
(30)因此,威廉斯才说:“虽然常被忽视,自然的观念却是包含了极其丰富的人类历史的。”(Raymond Williams,Problems in Materialism and Culture:Selected Essays,London:Verso,1982,p.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