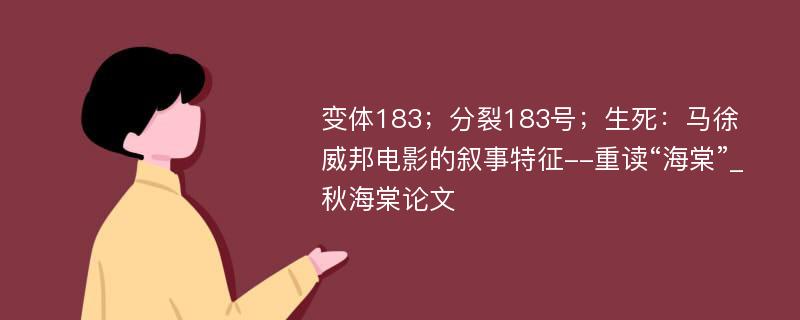
变容#183;分裂#183;生死:马徐维邦影片的叙事特色——重读《秋海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秋海棠论文,生死论文,影片论文,特色论文,徐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电影史的长河中,马徐维邦及其电影一直都是一个独特的案例。《夜半歌声》是他最为知名的一部影片,其主要原因不仅仅在于它是一部经典的恐怖片,而且也是一部“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横行霸道,描写了宋丹萍的反封建斗争”的影片。(注: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年2月版。)其实,马徐维邦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恐怖片是1926年为朗华影片公司自编、自导、自演的首部影片《情场怪人》,这部影片也被公认为中国第一部恐怖片。(注:有关中国第一部恐怖片的说法,有人认为是《情场怪人》,也就是马徐维邦的导演处女作。在这部影片中已经显露出他奇特而诡异的导演风格。也有人认为第一部恐怖片是他的第二部影片《混世魔王》,请参考张伟《纸上观影录》,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49页。)此后,他为天一影片公司拍摄的《混世魔王》(1929),把他娴熟的化妆技巧融入进导演的叙事之中,开启了恐怖片的另一个空间。1934年,马徐维邦为“联华”拍摄的《暴雨梨花》和《寒江落雁》开始更多地融进伤感的情调,引起了当时人们的争议。“记得在联华曾经有两部戏,差不多得过各方面的好评,一部是《暴雨梨花》,一部是《寒江落雁》,前者是曾经引起过好多文化人的大笔伐,后者曾经博得过许多太太小姐们数不清的泪珠。尤其是《寒江落雁》,当时的风靡情况,不下于今日的《秋海棠》。”(注:陈维《千千万万观众所热烈崇拜的——马徐维邦先生》,载《新影坛》,1945年1月,第3卷第5期,中华电影公司。)然而,这一切却并未获得当时左翼影评人的好评。“我想起了剧作者在过去曾昭示我们的两部力作《暴雨梨花》和《寒江落雁》,曾泛起不少惋惜之感。”(注:陈播主编《三十年代中国电影评论文选》,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年12月版,472页。)直到《夜半歌声》,这部影片几经田汉的修改,给了音乐以较大的篇幅,马徐维邦主动将田汉和冼星海为这部影片写作的主题歌《夜半歌声》和插曲《黄河之恋》、《热血》用来结构影片,最终使得该部作品成为了一部时代之作。此后,他为“天一”、“联华”、“艺华”等十余家电影公司编导了《古屋行尸记》、《冷月诗魂》、《麻风女》、《夜半歌声续集》等恐怖片,马徐维邦便以擅长拍摄恐怖片蜚声影坛。这一时期的马徐维邦影片是最为纯粹、最为本色的。上海沦陷后,马徐维邦曾经一度为“华影”拍摄影片,参与合作导演《万世流芳》,这是他创作生涯中最为复杂的一笔。但是1943年,马徐维邦单独执导的《秋海棠》(上、下集)和《火中莲》,由于其基本创作倾向是积极健康的,在当时获得了轰动和批评界的肯定。1947年马徐维邦到香港,先后在“长城”、“新华”等影片公司执导了《琼楼恨》、《碧血黄花》等影片。他一生共导演32部影片,1961年不幸因车祸丧生。
回顾马徐维邦的影片,我们发现,在他丰富的恐怖片影像语言中,他所昭示出来的世态炎凉、变形的人物、压抑的情感、独特的人物命运,以及复杂的故事,都呈现给观众一个个独特的文本,由此,也更凸现了被誉为中国的“希区柯克”的他异于中国其他早期电影导演的特质。1943年马徐维邦改编自小说家秦瘦鸥的代表作《秋海棠》,“耗一年的光阴”把它拍成上、下集的影片。他曾经说,这是他“生平心血的纪念”。事实上,积累了十多年的拍片经验,马徐维邦的《秋海棠》也确实是他的集大成之作,也最能突显出他的整体创作风格:一个建立在经典商业的叙事文本上,并融入了他个体生命经验,将“生死变容”作为他最大的叙事沟壑。
叙事:分裂的文本
《秋海棠》的故事缘起于一个艺人所遭遇的命运。从剧本上来看,这不过是一出“戏子私通姨太太”的故事,“但是在我导演的时候,我就曾经下过这么一个决心,就是我所要介绍给观众的,并不是戏子私通姨太太的单纯的故事,而是要描写出‘秋海棠’的人物和中国青年人在恋爱问题上的命运,所以我觉得这部戏在我以往的全部作品中间,是比较满意的”。(注:陈维《千千万万观众所热烈崇拜的——马徐维邦先生》,载《新影坛》,1945年1月,第3卷第5期,中华电影公司。)可见,这部影片之所以能够受到当时评论界和观众的肯定,主要在于整部影片一直着意表现以秋海棠和罗湘绮所代表的受欺压的社会男女对当时以袁大帅和季副官所代表的社会邪恶势力的反抗。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影片后半部分的叙事沟壑反复纠结在秋海棠对自己脸上的刀疤造成的心理障碍,并将这一“障碍”放大,使其成为最终导致男主角悲剧命运的根源。
在马徐维邦的系列作品中,“自恋的伤痕”和“残酷的命运观”一直是理解他作品的两把钥匙。纵观马徐维邦多数的恐怖片,其中的主要人物,如《古屋行尸记》中的蒙面人,《麻风女》中的“麻风女”,《夜半歌声》及其续集的宋丹萍,甚至包括《秋海棠》中的“秋海棠”,他们的命运都涉及到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变容”,并由此引发出关于性压抑和死亡的复合母题。镜像等衍射物在影片中的出现,突出地表现出这些物象带给人物内心的压迫和挣扎,表达了男女主人公自我的缺失。
毕业于上海美专的马徐维邦,一直迷恋各种艺术化妆,并且毛遂自荐到明星公司,既担任美术、布景、化妆,又客串演员。从对镜给自己勾脸、化妆到为别人化妆,马徐维邦似乎经历了从自恋到对客体转化的过程。精神分析学中关于“认同”和“自恋”的理论认为,儿童通过镜像来认同自己。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从字面上理解镜子,“拉康把他的发现放在与他人(如在转换[transitivesm])现象中,儿童把自己的行为推诿给另一个儿童,甚至是布娃娃”。(注:李恒基、杨远缨主编《外国电影理论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467页。)由此可见,自恋的客体选择是基于客体对于主体的相似性,而马徐维邦将电影这一本身具有镜像特质的媒体作为一种推诿物,融入了他对生活、生命的独特理解。特别是在《秋海棠》下集的叙事过程中多次出现的秋海棠与女儿梅宝之间的矛盾都和镜子和唱戏有关。“镜子之争”是马徐维邦精心设计的一场重头戏。心事重重的秋海棠坐在前景,后景中的梅宝在做着什么。一个反打镜头解决了观众的疑问,梅宝正对着镜子打扮自己,秋海棠进入镜头,看见镜子大怒,与梅宝发生了争执,他一再强调,“家中是不许有镜子的”。尽管梅宝悔悟到自己的疏忽对父亲造成的伤害,但是,镜头却突出表现秋海棠一看再看自己出现在镜子中的夸张的丑脸。这样的画面处理一方面似乎推动了剧情,奠定了秋海棠不见罗湘绮的心理基础,另一方面,在视觉造型上带给观众的心理冲击是巨大的,在视觉奇观的冲击下,观众认同了秋海棠病态心理存在的合理性。在精神分析学中,“自恋的伤痕”是一种自尊受到伤害的外化。影片中的秋海棠多次面对镜子痛苦呻吟,他也正是透过镜子来重新进行自我的认定,戏剧性叙事逻辑得以进一步推进,巨大的叙事鸿沟建立起来。后面类似的一场戏中,梅宝颇具天赋的京剧表演和唱腔,也可以认为是秋海棠精神生命的一种衍生和映射,而当这种映射被秋海棠发现的时候,招来的却是秋海棠更大的精神痛苦。影片有一组镜头是在这场争执之后,用一组空镜头的叠映及室内的秋海棠捂着头痛苦呻吟的表情,再一次渲染了这种“伤痕”所造成的自我缺失后的痛苦情状。在影片故事的后半部分,秋海棠瞒着梅宝在舞台上演过场的武生,掩饰在小丑脸谱下的秋海棠孱弱的形体表现,将主人公的命运进一步推向了绝境。
马徐维邦这种“自恋的伤痕”的母题不仅在《秋海棠》中极尽渲染,还反复出现在他以往一系列具有恐怖色彩的代表作品中,例如,《夜半歌声》中毁容后的宋丹萍,恋人近在咫尺,却不能相认,失去所爱之人,也暗示一种自我的缺失,只留下“自恋的伤痕”。而《麻风女》中的麻风女也历经磨难,一直不敢与书生婚配,直到自己病愈。
与此相呼应的是马徐维邦影片的人物设置又更加有别于其他同时期的中国影片中的人物。马徐维邦影片的叙事逻辑主要是受了中国传奇故事的影响,非常注重故事的完整性、戏剧性的巧合,并将这种巧合赋予了一种符号的意义,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学当中的意向美。“传统电影是作为历史故事,而不是话语来呈现的。传统电影的秘密在于,它抹消了话语陈述的一切标记,并伪装成一种故事的形式。”(注:王志敏《电影美学分析原理》,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年版,第169页。)无可否认,传统电影努力地把叙事者本身隐藏起来。遵循这一传统叙事模式,马徐维邦的影片所运用的传统叙事逻辑和伦理理念,让“观众不再与其他任何东西认同,而只是与看的行为本身认同”。(注:王志敏《电影美学分析原理》,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年版,第169页。)因此,在马徐维邦的电影里面,明显借鉴中国民间文学中人物的安排和故事悬念设置的叙事逻辑,“巧合”的一再出现,毫不妨碍观众自觉自愿地被卷入“故事”中。例如,人物的心性发展与这些巧合的出现有着明显的关系。在他的影像图谱中,总会出现两个有着对应的人物,后一个人物总是前一个人物命运的再版,当然影片中真正的悲剧人物是前者。例如,宋丹萍与孙小鸥之间,宋教孙唱歌,宋丹萍要求孙小鸥假装自己去安慰晓霞,以及后来孙小鸥的恋人再一次遭遇到同一个“敌人”的侮辱,旧故事重演,戏剧的高潮也由此到来。而《秋海棠》中的梅宝更是身兼着父亲和母亲命运的延伸,梅宝可以唱得像秋海棠,做艺人也会遭受同样被羞辱的命运;梅宝再长得像罗湘绮,在片中干脆由李丽华一个人饰演。
此外,除了上述的两部影片,还有《古屋行尸记》、《冷月诗魂》、《夜半歌声续集》、《寒山夜雨》等影片中的主人公都是非正常人的形象,不是鬼怪,就是被毁容、变形者,而他们的命运大都被扭曲,十分悲惨。马徐维邦的这种非常规的叙事视角,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病态,让观众在经历了恐怖的快感之后,依然易于感受回味现实的人生。马徐维邦有一段著名的“谈鬼”论:“《寒山夜雨》中有鬼,但这鬼倒有着天良,他们并不倚着‘鬼’势杀人,他们是钦服孝义的人,同时也痛恨无法无天,蛮横非凡的‘活鬼’。这就是一个人不如鬼的例证。”(注:《寒山夜雨》说明书。)此外,他在《冷月诗魂》的本事中,也开宗明义:“这里是一个离奇怪异的故事,虽则荒诞不经,而寓意却有奖善惩恶,有裨于世道人心的,我们决不是提倡迷信神权,正像志异说怪一类,寓意深奥而富诗意的文章一般。”可见,马徐维邦对社会是批判的,对社会种种不公现象的曲折反映,也加深了恐怖片的社会内涵。
电影的魅力是能够让观众看到一个好的故事。这个“好”不仅包括了伦理、道德等精神层面的创作主题或内涵;而且还暗指电影技术层面的叙事的建立。在建立叙事结构的过程中,如何建立叙事的“鸿沟”成为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从任一或所有冲突层面却产生出一个在他意料之外的反应。其效果是,在期望和结果之间裂开一道鸿沟,把他的外在时运、内心生活或二者同时从正面转向负面或从负面转向正面,其衡量标准是观众所知道的押上台面的风险价值。”(注:[美]罗伯特·麦基《故事》,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第272页。)马徐维邦的叙事有别于中国三四十年代其他成就斐然的电影导演就在于他甘于在恐怖片类型中,暗含一个个体自我迷失的文本。个体(秋海棠之类)“自恋的伤痕”成为最终构建叙事的最大“鸿沟”。在《秋海棠》的叙事表层,他的命运似乎来自社会的因素,如以袁大帅、季副官为代表的社会恶势力的压迫,而真正导向秋海棠死亡的是他的心理动因,脸上的“十字”和病残的身体让他无法面对罗湘绮的到来,生活于是不再继续。
影像:类型的建立
马徐维邦是一位类型片导演,也是一位作者导演,就像希区柯克一样。希区柯克在类型片上的专注,被以特吕弗等理论家为代表的后辈们尊为电影作者的先驱。马徐维邦是中国早期电影中少数热衷于类型电影的代表人物,尤其他在中国恐怖片类型上的开创意义是无法抹杀的。
讨论马徐维邦的影片,无法回避他的影像风格对影片叙事的影响。马徐维邦已经到了“形式就是内容”的地步,他对场面调度的掌握并不逊于同时期的导演,如费穆、吴永刚和孙瑜。马徐维邦更是借场面调度、蒙太奇、镜头的运动等手法来强调人物内心的真实,以达到叙事流畅的目的。在《秋海棠》中,马徐维邦对摄影机的把握相当成熟。我们可以明显发现,他在每个段落的镜头处理上都匠心独运。例如,针对每一个人物的出场,人物的外在形象和内在个性都在每一个镜头的处理中体现出来。当秋海棠出场时,是一系列流畅的摇镜头,从戏班子学徒的生活图景,摇到主人公的面部,顺着主人公远眺的眼神,摇到一个楼角的远景。通过他与师兄的对话,我们了解到他正在忍受着思母的煎熬。而非常有趣的是,影片在罗湘绮出场的段落中,有一个从袁大帅视角来看她的摇镜头,而这个镜头是从她的脚部开始往上摇,到腿部、臀部、上身,一直到罗湘绮正在演讲的激愤而漂亮的脸。这种纯粹男性视角对女主人公的窥视,在当时可以说是非常大胆的。同样,在袁大帅到戏班侮辱秋海棠的一场戏中,摄影机从袁呈“人”字形的穿军靴的腿间拍摄到秋一张躲避的脸。这个镜头虽然与吴永刚在《神女》中著名的镜头相类似,但是《神女》中表现的是阮玲玉,这一真正的女性所受到的欺辱。而同样的展现手法被运用到秋海棠的身上,则更加显示出马徐维邦对秋海棠这个人物所赋予的暧昧性,也是非常符合男权社会观影的性心理。
在《秋海棠》影像修辞中,马徐维邦开始更多地考虑到中国观众的观影趣味,因而一改以往过分夸张的视觉造型,将中国文学中的比喻等语言学表现手法运用到故事的修辞中去。例如,在罗湘绮和秋海棠第一次约会的一场戏中,梅花叠映的特写,拉出罗湘绮复杂的表情,这场戏是在中式的房间里,梅花多次出现,甚至最为精彩的是在梅花掩映下的罗湘绮看秋海棠的镜头,视觉造型非常丰富,在人物关系推进的同时带给观众一种美好的感受。在这里,被比者(罗湘绮)、比者(梅花)、比关系(“好比”之类的词)、可比者(建立比关系的依据,即“美好之处”)都非常完备,而摄像机的推拉摇移则将这四者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并流畅地表达出来了。这场戏对中国电影修辞格的成熟体现并不亚于费穆在《小城之春》中的贡献。
虽然马徐维邦的作品叙事法则深受中国民间故事的影响,但是,他依然能够从传统的叙事法中脱胎出来,更是源于他对电影符号有着天然的直觉和探索精神。“因为我自己知道,我的导演手法颇受了德国片和前苏联片的影响,以致颇多和他们出品所相同的作风。……同时,因为我本来就是研究绘画的,现在一旦从事起电影来,自然也有将研究绘画时的某种风格运用到电影上来的地方。”(注:陈维《千千万万观众所热烈崇拜的——马徐维邦先生》,载《新影坛》,1945年1月,第3卷第5期,中华电影公司。)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表现主义是一个把文学、戏剧、绘画上的表现主义风格运用于电影创作的电影流派。它的创作倾向主要是探索各种手法,运用夸张、变形、失真等形象,以及奇异、怪诞的造型,来强化和突出表现人物的主观世界和内心活动,如恐惧、焦虑、爱慕、憎恨等情绪。它们都迷恋于表现光影、线条、节奏等。德国表现主义电影的视觉风格就是:奇特的布景造型、特别角度的摄影、棱角分明的画面构图、阴沉朦胧的照明,这些反映人物恐惧心理、渲染紧张气氛的手法和技巧,在马徐维邦的电影中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挥。在《夜半歌声》中,影像的造型、光影的运用、布景的陈设、摄影的倾斜和夸张角度,无不透露出他对德国表现主义视觉造型的借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冷月诗魂》中幽怪的团团雾气;《夜半歌声》夜雾清冷中身着白纱的晓霞;甚至不安的老鼠和蛇在不同影片中的使用,这些都充满了意象和符号特征。蛇在《夜半歌声》中的出现,只起到恐怖的作用,而在《麻风女》中,丽玉饮下蛇酒,病情不治而愈,则充满了意蕴和象征。在拉康的精神分析学中,镜子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意象和象征符号,镜子的同类物,诸如水(江、河、酒)和月亮等都有“反映自我”的镜子功能。而宋丹萍投“江”自尽;丽玉饮下蛇“酒”;月夜下,丹萍以歌声抚慰晓霞;湘绮伏“血”殉情等等,无不是蕴含着“性与死亡”母题。正如前文所述,《秋海棠》中对镜子的直接运用,正是典型的“反常自恋”(Ironic Narcissism)的影像表现。
结语
欧洲中世纪的学者们为了探讨心理学,设计出一个有趣的名词:“心灵虫”。他们假设这种“虫”能够潜入大脑,从而完全了解一个个体的梦、恐惧、优点和缺点;并假设这个生物还有能力导致世间事件的发生。其实,细想起来,生物界、心理学方向的理想,却在电影上做到了。电影创作者其实就是一个心灵虫,他潜入他所创作的每一个人物的心灵,发现他的各个方面,探索人性的内在特质,用富于想象力的密码来表现一个一贯的主题——人及其“人性”。因此,对人物的创作是建立梦的开始。其实,马徐维邦的头脑里,也一直有一个心灵虫,这个心灵虫所建立的电影世界完成了他对自己所洞悉世情的表述,也完成了对自身生命印记的曲折反映。
其实,文章写到这,似乎人们一直有一个疑惑,为什么他的电影特别,而他的名字更特别?由于马徐维邦个人的资料非常少,我们对他的成长过程不得而知,只知道“原姓徐,因入赘马家,遂改姓马徐,浙江杭州人,中国电影导演”。(注:《中国电影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10月版,第649页。)“马徐”两个字就像烙在脸上的“十字”一样,是生活的印记,犹如“自恋的伤痕”。就像雷诺阿所认为的,一个电影家一生只拍摄一部影片,其他影片仅仅是第一部影片的再创造。如果这种推论是正确的话,马徐维邦的第一部影片是什么?会不会是他自己的故事?
标签:秋海棠论文; 电影论文; 叙事手法论文; 夜半歌声论文; 麻风女论文; 暴雨梨花论文; 影视论文; 中国电视剧论文; 剧情电视剧论文; 爱情电视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