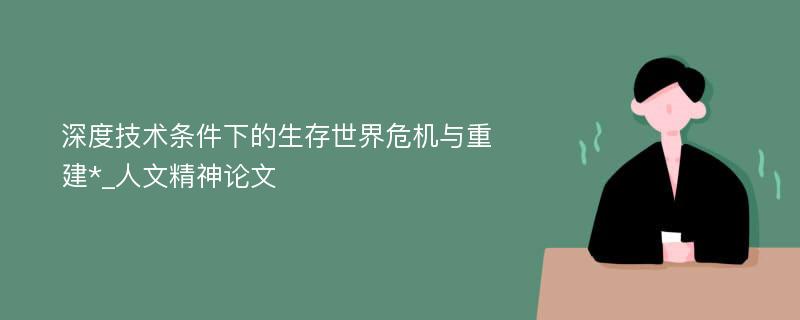
深度技术化条件下生活世界的危机与重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条件下论文,深度论文,危机论文,世界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人类生活世界的深度技术化,人类文明史正展现为人—技术关系互动极化的过程。一方面是人的技术化:生活实践被技术工具化,交流理解被技术媒体化,人体与技术的结合产生了“西柏格难题”;另一方面是技术的人化:技术日益智能化、自组织化,产生了许多值得深思的人—技新问题。此外,当人类生活世界在技术一体化过程中日益趋同、整合之际,人类个体作为生活主体及精神承载者却在技术单面化制度下日渐萎缩。人—技关系问题及其“二律背反”现象,是我们思考生活世界危机及其解救之道的前提。
一
生活世界是人类生活形式的历史展开图景。而生活形式作为人们日常活动的一般形式,是人类心性活动过程与物性活动过程的叠合展现程式;前者是一种精神的过程[1],后者虽然也折射出某种精神性的东西,但它越来越展示为一种技术化的过程。正是因为生活形式的日益技术化,甚至有人把技术看作是生活形式的根本方式,是一切人的存在都可以在其中展现的具体形态的框架[2]。
现时代生活世界愈演愈烈的一种趋势是全球化(据汤因比,全球化的本义即是“全球在技术上的一体化”[3])的趋势——以信息化为特征的全球化,正在使人类稳步迈进真正的信息时代(Cyber Times)。在这个崭新的时代里,人类生活世界的状况产生了深刻的质变——人和技术结成了更为亲密的共同体,生活世界从形式到内涵越来越被本质地技术化:“人—技术关系反映着人类实践或行为”[4]。
但是信息时代并非是一个能令人高枕无忧的时代,因为它不仅带来了新的危机,也使生活世界中原有的危机——种种“全球化问题”(生态危机、环境污染、人口膨胀、能源紧张、贫富分化、政治腐败……)愈加清晰地突现出来了。
在全球化起步的60年代,马尔库塞就细致地研究了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情形并精辟地指出,在深度技术化的时代,由于技术合理化及其配套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是其主体)的迫压,人们日益丧失了批判性的思维勇气,丧失了创造性的原动力和超越性的理想追求,成为思想僵化、目光短浅、麻木不仁的“单面人”(One dimensional man)。
深度技术化时代“单面化”制度的形成,一方面与技术本身所固有的“精神无涉性”有关。因为技术作为一种物性活动的过程,它最终只是在物的层面丰富了人类的生活,它所折射出来的精神——“科学精神”,也主要是在物性的层面提升了人性。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作为互补的人类精神模式,它们同以“人之为人”的东西即人性的提升为深层次追求目标。科学精神作为一种“外向性”的精神模式,它追求理想态人性的外在的、物性面的实现方式;人文精神作为一种“内向性”的精神模式,它强调通过内在的心性提升去实现理想态的人性。因此,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尽管在通达目标上是一致的,但在通达方式上是相互“颉颃”的。是以,技术的进步并不必然伴随着人文精神的提升,相反,从历史的后果来看,人文精神曾经充当科学技术进步的中介,尔后却沦为技术“螺壳”里的一只“寄居蟹”。当人类不注意人文精神的护养时,以建立社会秩序和引导社会为目的的人类道德能力和知识的发展,将远远落后于人类在技术上掌握自然的能力的发展[5],从而因心、物两面差距的扩大而产生危机。
另一方面,仅仅关注经济效益、漠视人的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既是单面化制度形成的主因又是其核心内容。正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以增强人们交流深度和广度为特征的信息时代反而使人们的交往形式发生了深刻的危机。马克思曾经指出:“个人之间进行交往的条件是与他们的个性相适应的条件”,并且这一条件是由个人“自主活动创造出来的”[6]。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个人因“更加受到物的力量的统治”而丧失了活动自主性[7],进而丧失了有效交往的前提。正因为如此,进入信息社会后的资本主义世界,反而因信息化程度的增加而使个人面对“以技术为媒介的生活方式”日益感到依赖性和孤独无助,无力形成共同体认同感[8]。同时,信息化传媒带来的“单向度的无回应的”话语方式,使人们倍感到“自己与他人、自己与世界之间的铭心刻骨的疏离”[9]。
交往危机迫使人们向内在的精神家园退却。然而,技术膨胀发展中精神的被冷落和“零增长”,已使得人类的“心性情怀”在信息围城的惶恐与困惑中荒芜、萎缩。结果是,无路可退的人类不得不返回到感官的物欲享受中去,沉溺于玩消费的“文化”。生活形式因而日趋浅薄化、平面化,在一些时髦的年轻人眼里,这一词已变得同“时装”毫无二致[10]。至此,人类失落的不仅仅是人文精神,在某种意义上还涵括了科学精神。
然而,“人是精神,人之为人所处的境况就是精神的境况”[11]。人类精神的全球性的全方位迷失的境况,正是现时代生活世界最为深刻的危机。为了更好地阐清生活世界危机的这一实质并探寻解救之道,我们借助于Popper的“三个世界”模型来进行分析。在这里,生活世界可以静态地划分为三个亚世界:世界1是被深度技术化了的实践世界(即“客观物质世界”);世界2是被消解了批判性内涵的精神世界(即“主观精神世界”);世界3是被科学理性化了的文化世界(即所谓“客观知识世界”)。于是,生活世界的危机就是世界1、3的膨胀式增长与世界2的“零增长”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导致的“全球化问题”与人的精神全面迷失的危机。
二
人类的精神境况一直备受思想家们的关注。早在工业革命之初,法国思想家卢梭就指出:“随着科学与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天边上升起,德行也就消失了。”[12]尼采认识到“苏格拉底式”的理性(即工具理性)是“一种破坏生命的危险力量”,而“科学追求的非精神化影响”,必将导致人性的奴化与沦亡[13]。胡塞尔也注意到,“只见事实的科学造就了只见事实的人”[14],陷于物役的人将无暇顾及人生的意义从而导致精神的危机。他们预见到了世界3中理性的(极端)工具化以及知识的过度科学化将会引起生活世界内在构架失衡的事实。
传统地看,世界1的深度技术化与世界2的科学单面化同样不可避免地导致人性的堕落。马克思曾经指出:“……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15]斯宾格勒也把所谓“浮士德型”的技术看作是禁锢人性的“魔鬼”。雅斯贝尔斯形象地阐明了技术对人性的毁灭式“还原”——“本质的人性还原为普遍的人性,还原到作为动物性肉体存在的生命力,还原到琐碎的恣情享乐”[16]。而技术对人性的“还原力”就在于它本质上是一种物性化的生活方式。这里,雅氏所谓“本质的人性”就是心性面与物性面相和谐的人性,而“普遍的人性”是指物性面的人性。人性“还原”的现象表明,如果人类过于关注物性化的生活形式,那么,生活世界必然向着不断地消解精神内涵的平面化生活形式转换。
那么,如何挽救人类生活世界之大厦于将倾呢?思想家们提出了不同的重建方案。
承继卢梭浪漫主义传统的法兰克福学派,提出要全盘抛弃技术;企图通过对技术的所谓“辩证的否定”去解救被畸化、异化、单面化的人性。但是人们已经认识到技术之路无论多么黑暗都是一条“既不能停止,也不能倒退”的历史之路[17],“我们必须用以反对技术恶果的唯一武器,还是技术本身,没有别的武器”[18]。于是“技术替代论”产生了,如芒福德的“生命技术”、舒马赫的“小型化技术”以及里夫金等人的“低熵技术”等等。“技术替代论”的实质是在“世界1”中对技术进行生态化,用低能耗低物耗的安全洁净技术去取代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的技术,最后达到技术利用的理想境地——“太阳能时代”。
尼采等人注意到技术的片面化发展带来“世界2”精神失衡的事实。他提出用非理性的权力意志去弥补技术理性的缺陷,用“酒神精神”去拯救技术对生命本能的压抑。海德格尔要求人们重返大地,通过艺术地维护大地,用“诗”与“思”去缓解技术“框架”(gestell)对人性的禁锢,实现人类在大地上“诗意般地栖居”。
斯诺的“两种文化观”是对“世界3”文化(知识)失衡的深刻探讨,他分析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隔陔状况,但并没有能够指出两种文化的隔陔本质上在于它们是人类在不同生活层面上探寻生命真谛的根本方式。正由于这种本质的不同,所以萨顿的“新人文主义”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因为他的“新人文主义”,“是围绕科学而建立……在科学——在人性化的科学——之上的文化”[19]。
思想家们对生活世界危机的探讨与重建都是不自觉地针对某一亚层世界而不是针对生活世界的整体展开的,这是他们共同的局限性。但是他们还是给了我们许多宝贵的启示,他们都认识到生活世界危机根源于某一亚层世界的维度失衡,并认为要摆脱生活世界的危机就必须实现各亚层世界的“非单面化”。如对于世界1,要实现技术的“生态化”;对于世界2,要实现精神的协调平衡;对于世界3,要实现两种文化(知识)的和谐共进。
从整体来看,生活世界的危机根源于技术(及工具理性)在亚层世界中的单面化发展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人类生活形式在物性面与心性面上的离异;这一现实又表现为生活世界在文化上(两种文化)的隔陔以及精神上(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龃龉。人类实践的、精神的、文化的生活世界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相互关联的辩证关系,并且这种关系是建立在生活形式(实践)的心性面与物性面的谐和基础上的。这就是我们重建生活世界的前提。
三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对生活世界的重建应该是基于“本质的人性”的实践的、文化的、精神的“辩证的”的方法论重建。
首先,从实践方面,即对于世界1,历史(“技术替代论”与海德格尔)给予我们的遗产是对技术进行非单面化的“生态化”重建。对技术进行“非单面化”重建并不是简单地去实现技术的多样化,而是要把生活世界中的技术化生活形式“非中心化”或“背景化”,大力张扬心性化的即人文化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通过生活形式的多维度化,最终使技术成为生活背景的一部分,使它成为与作为生活背景(也是生活内容)的制度的、宗教的、文化的、习俗的因素具有同等意义和功能的东西。这样,技术对人类的危害或增益将不再主要地基于它所固有的“威慑”与“行善”的本性,而是基于作为生活主体的人与作为生活环境的技术之间的选择关系和调适关系。技术的非中心化不仅意味着技术作为生活形式不再具有根本性,也意味着,它霸道地侵凌一切人文领域的现状必须改观。也就是说,要实现人类实践世界的多样态的生态化,就必须彻底地反对技术的中心化和一元化。通过技术的“非中心化”,人—技术关系的互动极化关系将由于丰富的人文实践方式而得到缓和。而人们的“单面病”也将由于多维化的生活实践方式而得到缓解。
此外,技术“非单面化”的生态学原则还要求实现技术本身的“生态化系统”,即把技术体系建造成有机的、良性的自洽体系;它具有对本身负效应的自转化、自消化、自净化能力,而只对外界输出正效应。
显然,技术的生态化是以生态伦理、人文关怀、科学预见力以及技术本身的生态化进步为基础的。因此,对世界1的重建必须与精神的文化的措施配套进行。在对世界1的非单面化的生态学重建中,科学化与人文化正是其内在要求。
其次,从文化的方面,对世界3的重建遵循文化生态学原则,即文化适应的“多样性”原则和文化发展的“多线路”进化模式。任何一种单维化的独断文化形态,都将由于缺乏多样性的谐调互补机制而逐渐走向僵化、封闭、停滞,最后由于“熵增”而衰亡。因此,必须打破工具理性和科学思想的独尊,实现理性与非理性的互补、人文知识与科学知识的互补。而两种文化(知识)的谐和互补是以两者之间的彼此宽容为前提的。
从精神方面,即对于世界2,我们从萨顿那里继承到的只是一个对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结合方式的设想。显然萨顿并没有认识到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作为目的性精神模式的统一性以及作为过程性精神模式(即操作意义上)的非相干性。认识到这一点,就会自觉地放弃那种想在科学的核心上建立“新人文主义”的企图;就会进一步认识到,人文精神作为人性的(心性面的)内在完善性意向和作为人性的(物性面的)外在完善性意向的科学精神之间的完美结合与进化,不是彼此敌视也不是相互“化”掉对方,而是要保持彼此间的宽容和相互间的恰当张力。只有确立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之间具有张力的协同关系,人类才有资格继续充作“存在的看护者”。这不仅是解决世界2的失衡问题,也是实现生活世界非单面化的必要前提。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之间的“既紧张又协同”的张力关系表明,它们作为建构精神世界的方法论原则是密不可分的。这就是人文化(人文精神化)—科学化(科学精神化)的原则。
至此,我们从历史的逻辑的分析中得出了重建生活世界的基本方法论原则:生态化的原则和人文化—科学化的原则。其中人文化—科学化是生态化原则的内在要求,而人文化—科学化原则内在地包含了生态学思想并必然导向生态化的进化路径。这就是重建生活世界的“人文化—科学化的生态学原则”——一个源于历史认识和时代特征并要求诉诸实践的方法论原则。同时我们还认识到,世界1作为实践的世界,它是世界2和世界3的客观基础,因此运用人文化—科学化的生态学原则着重于世界1的非单面化重建是我们取得成功的前提。
注释:
[1] 【美】L.A.怀特著,沈原等译:《文化的科学——人类与文明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0页。
[2] 【德】F·拉普著,刘武等译:《技术哲学导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5页。
[3] 【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著,荀春生等译:《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51页。
[4] Don Ihde,Technology and Life-world,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0,P.20.
[5] 曼海姆曾指出,“人类在技术上掌握自然的能力发展要远快于以建立社会秩序和引导社会为目的的人类道德能力和知识的发展”。见【德】卡尔·曼海姆著,刘凝译:《变革时代的人与社会》,台湾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25页。
[6][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84页。
[8] 【德】伽达默尔著,薛华等译:《科学时代的理性》,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74页。
[9] 王岳川:《无回应的传媒与心性交流的中断——后现代文化语境中对话单维化透视》,《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5年春季卷。
[10] 【日】扇谷正造等著,何培忠编译:《怪异的一代——新人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2页。
[11][16] 【德】雅斯贝尔斯著,周晓亮等译:《现时代的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1页。
[12] 【法】卢梭著,何兆武译:《论科学和艺术》,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6页。
[13] 【德】尼采著,周国平译:《偶像的黄昏》第3节“德国人所缺如者”,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4] Edmund Hussel,The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70,P.163.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8~79页。
[17] 【德】斯宾格勒著,齐世荣等译:《西方的没落》,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771页。
[18] 【英】C·P·斯诺著,纪树立译:《两种文化》,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4页。
[19] 【美】乔治·萨顿著,陈恒六等译:《科学史与新人文主义》,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2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