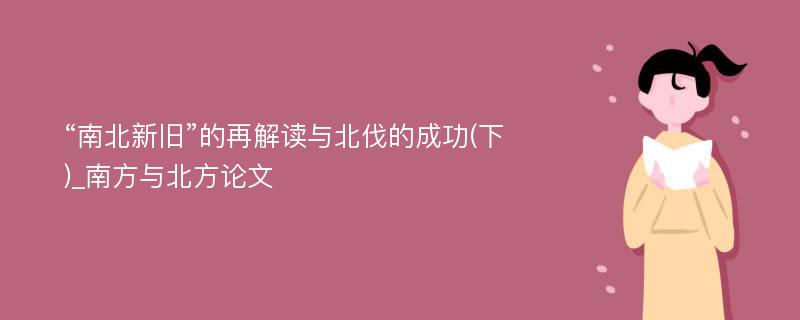
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二论文,新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不过,关于宣传作用的迷思也就起源于北伐的当时。胡宗铎在占领长沙之后的庆功会上曾说:此次占领长沙,与其说是“军事战胜,不如直截了当改云是民众胜利。因叶[开鑫]部之跑,不是打跑的,是民众在其后防故意恐吓赶走的”。(注:《民国日报》(广州),1926年 7月30日,转引自顾群、龙秋初《北伐战争在湖南》,第65页。)湖南民众的支持固然显著,但若能将叶部恐吓赶走,唐生智何须投国民党,桂军亦不必进长沙了。胡氏为桂军将领,对湘人说话不免客气些。但此话既出自军人,又经国民党报纸转载,影响遂广。而民众之所以能在后方起而恐吓敌军,自然是敌后宣传之功,宣传功用的迷思遂广为人接受了。
美国学者朱丹(Donald A.Jordan )早已辨明在作战之前派大量宣传人员到敌占区去发动群众的说法是迷思。 (注: Jordan,
The Northern Expedition,pp.241~246。)实际上,宣传队只是尾随军队进发,甚少有先入敌后者。北伐时主管宣传的郭沫若曾回忆。由于北伐军事进展速度超过预料,他所率领的宣传队要跟上作战部队的前进已十分困难,遑论到军队之前去搞什么宣传了。(注:郭沫若:《革命春秋》,上海海燕书店1947年版,287~331页。)即使确有一些数量不多的宣传人员深入敌后,但一涉具体,他们所能为者,如《国军政工史稿》所言,即“敌后宣传,仅凭宣传人员一张嘴巴一支粉笔,到处演讲,到处书写而已。至多有时散发一些传单,张贴一些标语”。(注:《国军政工史稿》,上册,第288页。)这在城市,因白话文的推广, 或确能使边缘知识分子兴奋一阵;若在农村,则扰乱一下敌方的军队或有可能,要发动民众支援北伐军作战,可能性实在太小。
实际上,即使在北伐军已占领的区域,宣传的功效也比一般人所想像的要差许多。北伐军进入河南后,各部队政治部的报告均强调宣传的重重困难。这些政治部的报告说:河南社会以小农经济为主,“人民识字的程度非常低下,不及十分之一二。标语宣言,失其效力”。这是第一重障碍,而文字宣传的能力已减去十分之八九。其次则是“言语不通,莫论广东福建的语言,即是湖北话也不能通用”。更有甚者,“即直隶山东人说话,也不通行。非本地人不易收效”。这是第二重障碍,口头宣传的能力亦已基本减去。即使克服上述两重障碍,仍有困难,因“我们在武昌时所用的成语,如军阀、贪官、打倒等,亦须反复解释”。(注:《第十一军政治部报告》,1927年6月, 《第十一军十一师政治部报告》,1927年4~5月,《总指挥部政治部(唐生智部)报告》,1927年5月,均收在曾广兴、 王全营编:《北伐战争在河南》(以下径引书名),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2、358~359、327页。)这是更要紧的第三层障碍,这才是关键。盖双方的心态和思想言说根本不在一个时段之中,没有共同语言。
若说“打倒”一词尚属新异,“贪官”则是通俗戏文中久用的字眼,何须反复解释?这里分明透露出河南民众自觉或不自觉地抵制北伐军宣传的消息。所以在这些北伐军政治工作人员看来,河南整个是“民智闭塞”。更因为“久受军阀压迫,反动宣传,久已注入他们的简单的脑筋中”,所以“大都封建思想蒂固根深”。(注:《总指挥部政治部报告》,1927年5月,《北伐战争在河南》,第319页。)问题在于,何以久受军阀压迫的河南人民要抵制北伐军的宣传,却反愿接受所谓“反动宣传”呢?这里的一个关键因素,即河南属北方,南人到此,地缘文化的优势一下变为劣势,与在南方的情形适成对照。可以想见,在已占领的区域里宣传尚如此困难重重,若要到敌后去发动群众,实不啻痴人说梦。
事实上,就在北伐军占领河南之后,也曾发生红枪会与北伐军大规模冲突的所谓柳林、信阳事件。据北伐军政治人员的调查,红枪会“分子复杂,乡土观念甚深……专以排外以及取得敌人之枪械为情”。这样,河南红枪会固然曾攻击外来的奉军和国民军,同样也攻击北伐军。不仅武装攻击,同时还“掘断铁路”阻止北伐军前进。更“反对农协,破坏党部”。(注:《总指挥部政治部报告》,1927年5月, 《北伐战争在河南》,第315~316页。)这些积极反抗大约还是少数,更多的是消极的抵制。故北伐军总结其在河南的经历是“只见民众对于革命军之口头应酬,未见到行动上的援助,更谈不到物质上的救济了”。(注:《第十一军政治部在豫工作之报告》,1927年6~7月,《北伐战争在河南》,351~352页。)
正如黄郛当时所认识的,长江流域及近海一带人民的乡土观念及“厌恶北军之心理,有助于国民革命军甚大”。一旦北伐军“出长江后,北上至黄河流域,这些有利条件逐渐冲淡,反之加强了北军的乡土观念,故用兵亦渐困难”。(注:沈亦云:《亦云回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8年版,第254页。)黄氏的认知大体是正确的。的确, 北伐军在河南作战之烈,为北伐以来所最甚。担任主要作战的第四军(此时包括从该军分出的第十一军)虽最后获战役之胜利,但死伤的惨重乃使这一支北伐前期功勋卓著的“铁军”元气大伤,在以后的作战中负多胜少,在中国军事史上再也未起到什么决定性的作用,竟渐退至二流地位了。(注:参见《第四军纪实》。第四军的衰落,当然也有别的原因。如中共南昌广州两次起义,实际上针对和破坏的均是一向维护中共的张发奎部的第四军主力。)
另一方面,国民党的宣传虽然对其作战的帮助不大,对于造成全国性的舆论却作用甚大。而其之所以能造成全国舆论,又甚得力于北伐军的军事胜利。正像有人所说的,与拿破仑的军队将自由、平等、博爱推向全欧洲一样,北伐时期主要不是宣传帮助了枪,而是枪促进了宣传。胡适当时也十分注重国民党的宣传机构,他向美国人描述说,北伐军军行所至,宣传人员就通过张贴标语和散发传单小册子,到处宣传国民党的党义和党纲。这些传单小册子更成千上万地散布到全国。故胡适的结论是:北伐时期国民党这些宣传手段在造成舆论方面的作用已超过一般的报纸杂志。(注:Forward or Backward in China?pp.41~42。)
胡适所说的“全国”,自然只能是城镇,因农村识字率的低下使任何宣传品的功效甚微。但彼时一般所谓舆论,基本是指识字者言。故胡适所见,恰道出国民党宣传功效实际所到之处。同样,美国军事情报人员在1926年底也注意到国民党宣传在北方的成功,特别是其军事胜利对宣传效用的促进。(注:USMI,vol.25,p.11411;Jordan也观察到是北伐军的声誉促进了其宣传在北方的作用,
参见其
TheNorthern Expedition,p.246,但他也未注意区分城乡。 )美国军事情报人员的资讯很可能是来自说英语的中国人,这些人同样也是外国报纸在华记者的主要资讯来源。当外国通讯报道再译成中文而刊布在中国报纸杂志上时,说英语(或其他外语)的城市中国精英观点就转了一个圆圈而回到本土。在尊西崇新的趋向下,由外国人口中说出的这些中国人的认知又更具影响力了。
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一个半真实半迷思的党军“新”形象在北洋统治的城市地区形成。故宣传虽甚少在战区促进作战,却在非作战区帮助造成了党军的新形象。这中间虽然迷思成分颇重,却为国民党在全国的胜利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国民党的形象既然一“新”,北方有“新思想”的人自然或主动或被动地倾向于认同南方。据时人的观察,“此次大战,国内许多思想较新的人”之所以“集中于党军旗帜之下”,实亦因其“在北方确有点不能相容”。北洋政府随意捕杀文人的作法已迫使不少上层知识分子南行。北伐之前陈独秀的被捕即引起第一批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南投。北伐期间李大钊等人的被捕杀更促成北大教授29人南下。实际上,即使不遭捕杀。这些人亦“因思想较新不见容于旧社会而生活受窘”。故即使为生活计,他们也不得不南投。(注:百忧:《以科学眼光解剖时局》,《晨报副刊》,1926年10月5日。)
但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已树立上层地位的所谓“英美派”知识精英的主动南下。蔡元培早就认识到留学生替北洋政府“帮忙”的重要性,故主张若北洋政府不采纳其意见时,大家即应相率辞职,使政府“当不起”。这个意见在北伐前似很少为人所接受,此时则情形一变。1927年3月即有周鲠生、王世杰等一批留学英美的北大教授南投武汉。同年7月,报载《现代评论》派陈源等亦全数投入国民党合作。孙传芳当时曾言,许多人为国人所弃,却为党军所收。殊不知这一主动或被动的趋新知识分子南向流动正是北方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注:蔡元培:《辞职宣言》,《东方杂志》,20卷1号(1923年10月1日),45~47页。知识分子南投的报导见《晨报》,1927年3月9日3版,1927年7月7日2版。孙传芳语转引自百忧《以科学眼光解剖时局》。)
知识精英数量毕竟有限。更重要的乃是大量边缘知识分子的南投。自黄埔开办,全国各地的边缘知识青年往广州投军者已络绎不绝。北伐军兴以后,这一南投趋势有增无减。据时人在1926年10月的观察:“近一两月来各地知识阶级(包括学生言)往广东投效的踵接肩摩。……据报载,自北伐军占阳夏,由沪往粤投效者三日内达三百人,由京往粤投效者六百人,类皆大学生。”一个月后,吴鼎昌注意到南北学生投效革命军的势头不仅未减,而且“为数日多”。(注:百忧:《以科学眼光解剖时局》;前溪(吴鼎昌):《智识阶级与革命》,《国闻周报》,1926年11月14日。)美国驻华军事情报人员也观察到同样的现象并立即写入其日常报告中。(注:USMI,vol.25.p.11394。)
孙传芳曾攻击国民党“利用青年,为其替死。旬月以来,迭据各方泣诉,年轻学子冒锋镝而死者,无虑万千”。孙本人的军队就报告说在数小时内毙敌人“幼年学生军二百余人”。这恰表明边缘知识青年南投的趋势。后来鲁迅到广州,也注意到原来在前线拼命的党军竟是学生。(注:孙传芳:《通电》,1926年9月7日,《国闻周报》,1926年9 月12日; 鲁迅:《沪宁克服的那一边》, 原载《国民新闻》(广州),1927年5月5日,重印在《中山大学学报》,1975年3期,第26页。 )据当时对黄埔入伍生职业的统计,以中学生为主的学生约占总数的60%;以小学教员为主的教员约占总数的19%。这些人基本为边缘知识分子,合占总数的78%。(注:伍生:《五四以后青年运动的倾向》,《入伍生周刊》,第2期(1927年5月),转引自张培新《北伐时期群众战之研究》,第171页。)黄埔的正式学生要经过文化考试, 其边缘知识分子的比例应更高。
士人和边缘知识青年的南投,不仅大大增强了国民党的力量,而且体现了国民革命运动的全国性,是北伐“有道伐无道”性质的鲜明表征。此时的国民革命,以其“新”而得全国响应。故北伐之所向披靡,如胡政之所言,“实由人心厌旧,怨毒已深,对于新兴势力,怀抱一种不可明言之企望”。(注:(胡)政之:《主义与饭碗》,《国闻周报》,1926年10月10日。)
南新北旧的具体检讨
既然南方的取胜主要不是靠兵员和装备的优势,则其致胜之道,除了地缘文化因素外,似可从南北体制的不同来探讨。这在北伐的当时,已是相当流行的思路。一般而言,南北体制的不同之处,也就是南方之“新”的具体表征。当时人注意较多的,除了前述的宣传外,主要有党的存在、“主义”的有无、政治工作和苏俄的援助等。这些因素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贡献于北伐的胜利,便是下文要检讨分析的。
北伐军与北洋军最明显的一个区别就是前者有党的存在。虽然国民党军队从1925年6月起已改称国民革命军, 但到北伐时不论南方北方,仍多以党军称之。(注:据《国军政工史稿》,军政训政时期都是党军,要到宪政时期才成为国军(第35页)。则此时仍为党军无疑。)党的存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南方的政治更加复杂化,但同时对北伐的成功也起了很大作用。北伐军虽实际上得益于南方地缘文化因素甚多,但当时统一安定是全国人心所向,若过分强调地方观念,必减少国民革命的吸引力。故蒋介石对孙传芳所谓“强分南北”的指责,立即驳回,并特别以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的象征来强调其全国性。(注:蒋介石:《致孙传芳》1926年9月13日, 收在《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770页。)实际上,如前所述, 国民党高出北洋之处即在于其尚存统一全国的愿望。
国民党党组织的存在,也有消解地方观念负作用的功能。国民党本系全国政党,虽在1921年放弃护法口号而开府广州,已渐有南方的地方色彩,但在北方治下的主要城市,也都设有党部。故国民党的成员虽以南人为主, 至少象征性地有全国性质。 (注:参见 Jordan, The Northern Expedition,p.289。)相比之下,吴佩孚虽有统一全国之念,张作霖虽开府北京,却都不能摆脱其在世人观念中“直系”和“奉系”的认知。故“党”的存在,多少使国民革命和北伐在占尽南方地利的同时,兼具全国性政治运动的标帜。在民族意识上涨的20年代,特别是各界因内乱而不能苟安于本行而产生全国意识、对中国问题寻求一个全国性解决的情形下,国民党的全国性对北伐的成功是颇为有利的。
党的存在,同时也有助于消弭文武之间的紧张和疏离。北洋时期,文武之间的紧张是一全国性的问题。(注:参见罗志田《五代式的民国:一个忧国知识分子对北伐前数年政治格局的即时观察》,《近代史研究》1999年4期。)南人之反北洋驻防悻 多少因有文人肤对武人腕治的意味。虽然南北双方都有相当数量的“尚武文人”支持军人的统治,但许多“尚武文人”派系色彩过于浓厚,渐失文人的独立身份。当军人主政者本身更迭频繁时,便需要一些相对独菱于各派系的文人操持具体政务。如北方之顾维钧、罗文干等便是这样的人。但这样发展的结果,乃是北方之武人不仅临驾于文人之上,同时也疏离于文人。文武之间既紧张又疏离是北洋统治失去正当性的重要因素。在南方,文武之间也有不同程度的紧张和疏离,但党的存在却能起到消弥紧张和整合双方的功用。(注:参见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卷,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97页。)
理论上,党是属于文人一方的。宋子文曾明确表述:“国民革命的主旨是以党治军,就是以文人制裁武人。”(注:参见胡适《追念吴稚晖先生》,《自由中国》(台北》,10卷1号(1954年1月1日), 5~6页。)通常“维护党权”即是强调文人制裁武人的意思。但是党也并非完全认同于文人。汪精卫在黄埔军校开学时即指出:过去国民党的失败,在“党自党、兵自兵”。今创办黄埔,“实欲合理与力为一致。办党者为理,办兵者为力。力以抵抗罪恶,镇压反革命,补理之所不及。故党与兵实相依为命。兵出于党,无党即无兵;党赖于兵,无兵即无党。”当时任职于粤军的叶剑英曾简言之为:“军以党化,党以军成。”(注:汪的讲话原载于《民国日报》(广州),1924年6月22日, 收入广东革命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以下径引书名),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3页;叶剑英的话引在潘乔石《革命洪流中的叶剑英》,《星火燎原》(双月刊,北京),1983年特刊,第8页。)
仿苏俄政委制的党代表制正是为发挥党的特殊作用而设置的,其目地为“贯输国民革命之精神,提高战斗力,巩固纪律,发展三民主义之教育”。(注:《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收在《黄埔军校史料》,第139页。)这一制度是否真起到这样的作用,颇难估计。 盖军事指挥人员与党代表间一直存在不同程度的紧张,后来许多军人支持清党,多少有反党代表的意思。但党代表制在一定程度上确起到整合文武关系的作用,这正是北洋体系十分需要而又未能产生的。
引人注意的是自由主义者胡适曾大力赞扬这种军党合一的制度。胡适以为,各级部队设党代表和“全党也多少在军事纪律约束之下”使国民党的党和军队“实际上已成为一体,至少也是联锁式地结合起来了”。他认为这是“极为卓著而且重要的”。其结果,“这样组织起来的军队当然要打败没有组织的旧军队”。(注:Hu,"Address at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pp.278~279。)胡适的看法有相当的代表性,蒋介石就注意到:“现在帝国主义也看见了我们党的势力——它对于我们军事尚不重视——只想法子来破坏我们的党。”(注:蒋介石:《在湖南省党部欢宴大会讲演》,收在文砥编《蒋介石的革命工作》,上海太平洋书店1928年版,下册,第299页。)
正是有了“党”,国民革命军乃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支军事政治并行的军队。《国闻周报》的时评说:“党军长处,在能以军事政治并行。故师行所至,事半功倍。质言之,一举一动,皆有政治的意味。”这是军政疏离的北方所不能比的。《现代评论》的一篇文章说:北方不能用文人,“只剩下一个赤裸裸的武力”,而南方则“枪与笔联合起来,所以到处如入无人之境”。(注:《斗力与斗智》,《国闻周报》,1926年12月15日;无名:《从南北到东西》,《现代评论》,1927年6月 11日,第5页。 )服务于北方但又力图保持独立的顾维钧也有类似的见解。他后来回忆,国民党以政治组织支持军事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因素”,极大地决定了北伐的胜利。(注:《顾维钧回忆录》,第303页。)
国民党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即是“运用主义”。蒋介石曾指出:“为什么要有党?……党是有主义的,运用主义的。没有主义,固然没有党;没有党,也不能运用主义,就是不能革命。”(注:蒋介石:《在湖南省党部欢宴大会讲演》。)“主义”的有无,是南北军队的又一大不同。
民初的中国社会,因政治制度的转换和传统的崩坏,不再存在一统的意识形态,结果是各种“主义”的兴起。人人都在“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注:胡适:《问题与主义》,《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版,卷二,第151页。 )谈的人一多,“主义”就渐脱离其具体的思想观念,而兼具进一步的功能。平民教育派的周德之曾说:那些开口闭口言“主义”的人十分之九并非真诚,而是“有的为权,有的为利,有的为名,有的为吃饭穿衣”。(注:周德之:《为迷信“主义”者进一言》,《晨报副刊》,1926年11月4日。)既然衣食名利权势皆可自“主义”中得之,人们又进而不再高谈这种那种既存“主义”的新奇奥妙,而是如马君武所观察的,“无论何种主张,均安上‘主义’二字”。(注:马君武:《读书与救国》,《晨报副刊》,1926年11月20日。)上引这些人对“主义”的泛滥均持反对态度,但一种东西能在社会上不胫而走,必有适合的环境。“主义”在20年代的中国,确有其特别的社会和政治功能。(注:参见田柚:《主义在民初中国》,《中时晚报·时代副刊》,1993年5月14日。)
实际上,比较成功的军阀,也多少有些“主义”,用以整合其部队。吴佩孚是以关羽岳飞精神号召全军;冯玉祥有基督教统一部属;唐生智则有“佛化”的军队,后来投入国民党仍主张“佛化革命”。(注:参见Chi,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pp.54~56,95~100,115; 唐生智事尚未见专门研究,可参见《李品仙回忆录》,59~62页;《晨报》,1927年7月15日3版,10月18日6版,12月20日6版,1928年2月24日6版。)但是这些军阀的运用“主义”,又远不及国民党的成功;而北伐时作为北洋主体的奉鲁军阀,更连上述的“主义”都不曾有。故一般的看法,北伐军才是有“主义”的,北洋军则是无“主义”的。蒋介石即称:“我们是有主义的军队……北方军阀……是没有主义的。”(注:蒋介石:《对国民革命军宣传员训练班讲演》,《蒋介石的革命工作》,下册,278~279页。)胡政之虽然对南方的“主义”本身颇有保留,但也指出:“主义之优劣是一事,主义之有无又是一事”。胡氏以为,北伐时的南北相争,正是“无主义者与有主义者抗”。(注:(胡)政之:《主义与饭碗》。)
南方运用“主义”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党的存在和政治工作。所以总政治部的郭沫若发现,所有来归附的军队,最先请求的便是派遣政治工作员。“他们并不知道政治工作的真意,但很知道南军和北军在组织上的重要的不同处便是在这种工作的有无。有了这种组织的南军打了胜仗,就觉得这种东西是使军队强盛的良法,因而政治工作便成了一个时代的宠儿。”(注:郭沫若:《革命春秋》,第393页。)
揆诸其他各方的看法,郭氏的观察大体是不差的。但其中已有迷思的成分。盖派遣政治工作人员乃是谈判“归附”时国民党一方的要求,当时凡是投诚的军队,其前提便是承认三民主义及同意在其辖区设党部等。这些军人无论是否真以为政治工作能使军队强盛,都不得不要求派遣政治工作人员。故政治工作之所以成为“时代的宠儿”,多少也有强制的因素在起作用。
实际上,南方的军政结合,较北方固然远胜之,但事实上的成绩,恐怕要打不少折扣。蒋介石在北伐结束后曾说:“关于政治,则向者以急于铲除军阀之故,凡百精力,皆萃集于军事之故,而未能切实进行。或粗具规模,或徒有名目。”(注:蒋介石:《今日党员与政府军队及社会之组织惟一要素》,1928年8月7日,载《盛京时报》,1928年8 月18日1版。)北伐时期,实际是军事压倒政治,应是不争的事实。 故关于党军政治成功的迷思,实已起于当时。
南北之间的另一大差异,便是南方有苏俄的直接援助,北伐军上述的诸多新因素,大半与俄援有关。如前所述,胡适是将俄援本身视为南方的“新”而加以鼓吹支持的。苏俄的军火援助和军事参谋人员所起的作用,各方评价不一。在广东的东征时,苏俄的物质和战术援助,应有决定性的作用。北伐后战区较广,苏俄的物质援助所起的作用也渐小。
在一定的意义上,俄援的重要恐怕是心理的多于实际的。自尊西崇新风气大兴以来,中国人自信心下降,各政治势力如无外援便少安全感。顾维钧曾指出:“在中国,特别是在民国初年,不同的军事和政治派系有依附某一个外国势力……来巩固支持其政治前程的普遍趋向。”(注:《顾维钧回忆录》,第397页。)国民党亦不例外,孙中山在1922 年尝谓:“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运用外交政策的是否有当,实有密切的关系。……在列国之中,有两个国家,尤其和我们休戚有关。这就是我们的近邻日本和苏联。假如这两个国家都成为我们的盟友,当然最好,如果不能,至少也要获得其一,我们的革命工作才能顺利进行。”(注:“孙中山1922年在广州对国民党同志训话”,转引自孙科《中苏关系》,中华书局1949年版,第26页。)
而且,帝国主义支持军阀是当时许多人的共识。如日本支持皖系和奉系,尚有迹可寻。但英美支持吴佩孚,本无根之谈,却也是南北许多士人共同的认知。(注:国民党固一向攻击吴是英美的走狗,就是北方一些人亦有相近看法,参见隐之:《反对各国预闻内战》,《国闻周报》,1926年9月12日;前溪:《注意国内与国际之变化》, 《大公报》(天津),1926年9月5日。)国民党人一般认为北伐到最后关头,帝国主义必出而支持军阀。故蒋介石的对策,即是联俄以防列强支持军阀。蒋特别强调,并非军阀才联合外国人,革命军人也要联合外国人,只是联合的对象不同而已。(注:《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636 ~637页;蒋介石:《革命军人与军阀》,《蒋介石的革命工作》,上册,第163页。)
后来反共的王柏龄回忆第一次俄援到黄埔时,“全校自长官以至于学生,无不兴高采烈。尤以一般要革命的学生,喜得无地自容,拍手打掌……个个笑脸不收……无不欢天喜地。”王氏短短一段记述,反复出现这些兴奋的描述,很能体现一种心理上突获安全感的瞬间喜悦。王氏并云:“这一次踊跃情形,决非第二次第三次所能及的”。(注:王柏龄:《黄埔创始之回忆》,节选在《黄埔军校史料》,71~73页。)何以如此?即因第一次更具象征意义也。故俄援的重要,固然在物质及组织方法等方面,但那种有一邻近强国为后盾的心理支持,尤不可小视。国民党后来的绝俄,在其已获大利初具信心,特别是在列强明显改变其态度,转向亲南而弃北之后,亦良有以也。(注:关于列强态度的转变与国民党绝俄的关系,拟另文检讨之。)
胡适尝认为,俄援最重要的是其组织方法。今日的美国学者,多同意这一看法。(注:《胡适日记》,1926年10月 8 日; Forward
or Backward in China?pp.43~44;C.Martin Wilber and Julie
Lien-ying How,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 :Soviet Advisers
and Nationalist China,1920 — 1927,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pp.416 ~ 417; Jordan,The
Northern Expedition,pp.15,302(note 6)。 )胡政之在北伐当时也十分强调俄式组织方式对国民党的重要性,他认为南方“自采用俄国式组织之后,全部民党,恍若节制之师。政治上之主张俨成宗教上之信仰,此为国民党胜人之处”。(注:(胡)政之:《主义与饭碗》。)可见这一点大约是中外许多人的共识。
但即使对这一点,亦须再加以必要的界定。北伐时作战较多的第四、七两军,所受俄援明显比黄埔军要少。尤其是李宗仁的第七军,加入国民党一方的时间不长,对俄式组织方式亦无热情。该军的党代表政治部等人员设施,倘非其旧人,即形同虚设。可是四、七军在战场上的表现却远胜过黄埔军。这说明即使是争议最少的俄式组织方式的作用,也有迷思的成分。
同样,最能代表南方各种新因素的黄埔军在北伐中表现却最差,最能反映关于北伐的种种认知与实际的差距。有学者以为:“黄埔生的素质从一开始就很高……黄埔军校的申请者比国内所有其他军校的申请者质量高, 有时甚至比其他军校的毕业生质量还要高。 ”(注: Chi,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p.112。)黄埔开办时,恰值北洋的保定军校停办。若仅以学校论,则两者不同时。而不计保定军校,以黄埔与北南军人自办之讲武堂训练班一类比,其素质更高大致是成立的。但若讲到作战,则保定毕业生正任职于全国,保定二期的何遂在1926年春的通电中说:“国内袍泽,半属同年学友。”(注:《晨报》, 1926年3月26日2版)北伐时正是保定毕业生鼎盛之时。 虽然“素质”可有许多不同的界定,但若以军事素质而论,则黄埔生是绝对不能与保定生相比的。
保定生入学前要求9年的陆军小学和陆军中学教育,入校后要学习2年整。(注:参见河北省和保定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合编:《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事实上,黄埔军校的许多教官即是保定毕业生。而黄埔生并不要求入校前的军事教育,入校后也只半年就毕业。黄埔生在校的半年期间,学习也不是十分正规的。孙中山在黄埔的《开学训词》中明确提出:“革命是非常的事业,非常的事业不可以常理论。……现在求学的时代,能够学多少,便是多少。只要另外加以革命精神,便可以利用。”(注:转引自《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第8页。)这正是黄埔教育精神的鲜明写照。 关于黄埔生素质高的认知有可能是受了既存文献的误导。若从文献看,对黄埔生入学考试的要求的确很高。可是据后来许多黄埔生的回忆,实际的入学考试远不如文献所记载的那样严格。(注:参见徐向前、宋希濂、覃异之、王大文、宋瑞柯、文强的回忆,收在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以下径引书名),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214~222、237~260、271~282、283~291、303~ 318 、319~345页。)以当时属革命非常时期及南方对军事人材的急需,这些回忆大致是可信的。
从另一方面看,黄埔生的“素质”正体现在其“革命精神”。民初社会变动甚剧,当兵“吃粮”已是一条生活的重要出路。但当兵既为“吃粮”,则作战时必以自保为目的。冯玉祥的队伍在北方号称能战,一个主要原因即是其不征召所谓“兵油子”,而仅收年轻人。(注:参见USMI,vol.26 所载美国军事情报人员以《中国军队》为题的长篇报告,收在1927年1月22日至2月4日的双周报告中,页码单列。 )黄埔生则不仅皆是年轻人,且多系各地主动投军的热血青年,故黄埔军与其他军队的一大差别即是不怕死。以北伐时期的军事装备和技术而论,不怕死常是决定胜负的第一要素。黄埔生不怕死的名声在广东的东征时既已树立。东征一役,黄埔生(一至三期)2327人中战死者即达217人,约近1/10。但自1926年春的中山舰事件后,许多共产党员被清除出军,实际是失去相当数量不怕死的青年,同时又使另外许多不明国共之争真义的战士思想混乱。结果是黄埔军的战斗力锐减, 不怕死的精神亦不如以前。 到1927年4月止,黄埔生一至四期近5000人在北伐中战死者为101人,约为2%。(注:这些数字均引自《黄埔军校史料》,第496~499、 502 ~503、93、451页。)
北伐的规模比东征大得多,敌手也更强大,战死者反比东征少得多。是不是黄埔军的战斗技术大大提高了呢?不是的。蒋介石在1926年10月末说:黄埔军(何应钦率领的东征军除外)自北伐以来,“没有打过一次胜仗”。实际上,黄埔军在此后数月间的表现亦甚不如意。(注:《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55页。该书716~895 页的大段篇幅中, 常有蒋介石因黄埔军作战不力受人耻笑的痛心语。 参见
Chi,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pp.200~201。)
不过,黄埔军的表现不佳只是在南方内部为人所知较详。在外界和北方看来,四、七各军的胜利也都是在总司令蒋介石指挥下所得。故一般是将北伐军以整体视之。蒋介石在北伐军内部或遭到粤、桂、湘军将领不同程度的轻视,在外面却正因北伐的节节战胜而声誉日隆。
北方既视南方为一整体,而且颇以为南军的取胜是靠了主义、党和宣传等新事物所致,北方自己也很快就学起南方来了。与南军接触最多的孙传芳学得最快,孙不久即标榜“三爱主义”以对抗南方的三民主义。到1927年夏,张作霖一方也先后提出“爱国党主义”和“四民主义”,即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上又加一个“民德主义”,既对南方有所包容,又有自己的发展。同时,像张宗昌这样素以不通文墨著称的人也发表演讲,大力提倡国家主义以对抗南方的“世界大同主义”。不久,北方更成立了以潘复为中心的“新国家党”。(注: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三联书店1983年重印三卷本,卷三,第1589页;《晨报》,1927年5月6日,6月15日,均2版,7月18日7版,8月7日3版,12月 2日3版,1928年1月1日2版,1927年6月16日3版。)
同样,北方也学南方设立宣传机构。孙传芳的南京总部“特设宣传机关,日以印刷文件,传播各省”;(注:《东南时局感言》,《国闻周报》,1926年11月14日。)在其辖区各县均设有讨赤宣传委员,专司宣传之责。奉军也设有宣传部,人员达数百人。奉军和直鲁军也都向前线派遣宣传队。但总的说来,北方在宣传等各方面均远不如南方成功。就孙传芳而言,其地处南方,地缘文化的不利使其宣传很少能生效。另外,北方的“主义”和“党”都名实不符,基本是仅具招牌。北方的一些宣传机构形同虚设,宣传的开展本身亦用力不足。再加上北方捕杀文人记者,失去了知识分子和边缘知识青年的支持,宣传人员的来源本身就成问题。故《国闻周报》说北方虽知专恃武力不足济事,但“舍武力,讲宣传,东施效颦,正所以暴露弱点”。故北方学南方是学亦难,不学亦难,学又学不会。但无论如何,其试图学南方的趋势是明显的。(注:《斗智与斗力》,《国闻周报》,1926年12月15日;亦参见《晨报》,1926年10月15日5版,1927年2月1日2版,3月29日3版,1928处1月16日3版,3月13日7版,4月11日6版,5月28日3版。)
最后,北方也认识到其“旧军阀帽子不脱必倒”。除孙传芳坚持中国的青年已大半误入歧途,挽回浩劫之责“全在四十岁以上之智识界稳健人物”外,其余军阀,特别是奉系总思给人以“新”的形象。杨宇霆对北京学界力辩过去“外间不察,多底东北方面思想陈旧,军队暴烈。其实东北对于政治学术,纯抱革新愿望”。张作霖任职大元帅时,也宣言要改革政治,“务使百物一新”。(注:《晨报》,1928年1月 7日2版,1927年7月15日2版,12月19日7版; 张作霖的《宣言》收在前引《北洋军阀》,第5卷,383~384页。)
很明显,北方在强调绝无新旧之分的同时,也渐认识到中国社会的趋新倾向和“旧”形象对自己的不利。惟北方之求新,亦与其在主义、党、和宣传等方面的作为一样,仍是一种学而不会的格局。但是,学得好不好是一回事,学不学是另一回事。北方之学习南方而求“新”的种种努力恰证明了新旧之分在北伐时期的重要作用和影响。
略具讽刺意味的是,北方之学南方多是在宁汉分立特别是清党之后,亦即在南方自身已部分放弃其“新”因素之后。清党期间的“白色恐怖”(注:George E.Sokolsky,Tinder Box of Asia,Garden City,N.Y.:Doubleday,1932,p.341.白色恐怖一词由反共的索克思口中说出,特别发人深省。)以及宁汉之间的武力斗争,颇令时人感觉南方也类似北方而对南方失望。蒋介石辞职又复出后,由于国民党左派已基本不复存在,右派(包括西山会议派和胡汉民派)也再次失势,南京新政府乃不得不大量援用政学系一类所谓“北方国民党”。结果是国民党进一步淡化其南方地缘文化色彩,同时显得更加具有全国性;但也进一步给人以南北相类似的印象。简言之,国民党所代表的“新”(包括事实上的新和人们期望中的“新”)也已大大地淡化了。(注:这里所指“北方国民党”,也包括黄郛。黄虽不是正式的国民党员,但一般人均认其为国民党人。参见《亦云回忆》,291~293页。黄氏的私敌郭泰祺就曾公开发表声明,警告北方旧官僚在国民党内影响日大的危险性。关于南北已类似的认知,参见《晨报》,1927年11月6日6版,12月15日2版,12月31日3版,1928年3月17日3版。)
后期的北伐即是在这样一种南北新旧之分已淡化的局势下进行的。宁汉分开初期,双方尚能各自继续北伐。武汉一方在河南以血战击退奉军,南京一方也曾挺进到徐州。此时若宁汉未分裂,即可利用当时中国惟一一条东西走向的陇海铁路,集中兵力于任何一侧,本可轻易完成北伐。当时奉张已在做出关准备,但宁汉的内斗延阻了北伐的胜利。孙传芳乃乘间倾全力反攻南京。南京附近的龙潭之役是北伐在河南之外的又一大血战,此役黄埔军与桂军配合较洽,表现甚佳,终于彻底击溃孙传芳的队伍。(注:关于龙潭之战,参见《东路军》,第99—118页;《李宗仁回忆录》,上册501~517页;Jordan,The Northern Expedition,pp.137~141。)
从此北方乃完全失去向南方进攻的士气,此后除奉晋间北人与北人之战外,南北方之间没有什么大的战斗。最后一段的北伐,因日本出兵山东并造成济南事件,奉军在民族矛盾面前不能再与南军打内战,主动撤退出关。(注:奉军因国难而主动撤退可参见张学良、杨宇霆和常荫槐在1928年5月5日至7日的往返秘电, 原件藏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张静江文件中,档案号3004/189。 并参见罗志田《济南事件与中美关系的转折》,《历史研究》1996年2期。 )故南方虽已失去南北新旧之分的许多有利因素,却又因中外民族矛盾的尖锐化而得以基本不战而胜。日本人策划暗杀张作霖,进一步促进了东北的易帜归附。北伐终以全国统一在国民政府之下而结束。
结论与反思
美国学者朱丹以为,北伐军到底是“赢在战场上”。(注:Jordan,The Northern Expedition,p.287。)这话基本是不错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北伐战争与旧时的“逐鹿中原”亦相类似,无非是争夺全国的政权。杜牧曾说:灭秦者,秦也;非六国也(《阿房宫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北伐。换言之,北洋体系在北伐之前已分崩离析。北伐军既因利乘便,其取胜亦渊源有自。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若从有形战力看,北方无论如何是强过南方许多的。故北伐军之所以能“赢在战场上”,恰恰是靠了无形战力的巨大作用。
在运动比赛中,常有一种“观众效应”,即一个弱队有时能在观众(通常是家乡观众)的鼓噪声中打败实力更强的对手。可以说,北伐的胜利即是在这样一种场外的鼓噪声中得来。南北的地缘文化意识、新旧的区分。特别是党、主义、宣传等新事物合在一起,给北伐军在战场之外造成一片支持的鼓噪之声。大概言之,是地缘文化因素推动了军事的进展,军事的成功又促进了宣传的功效,宣传的功效有助于造成战场之外的舆论,而舆论影响人心(这只是大概而言,具体的一时一事并不一定依此秩序,且各项之间每有互动的作用)。国民党正是在这样一种有道伐无道的声势下,才能势如破竹,一举打垮实力更强的北洋军阀。
但凡事有一利便有一弊。南北新旧之分,从根本上说是带有分裂性的因素。国民党在形式上统一中国之后,这些过去致胜的因素即因其分裂性而影响国民党对全国的统治,造成一种形式统一而人心不统一的局面。梁园东曾说:“由南方和由北方统一的思想”是不应有的,“根本是南北的畛域观念即不应有”。(注:梁园东:《现代中国北方与南方》,《新生命》,3卷12期,转引自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第127页。)
国民党在统一后定都南京,将故都北京更名北平,本有其特定的考虑。可是在北方人看来,这就有某种“征服”的意味。故“北人皆不以为然”。青年党的李璜在北伐后到北方,就发现国家虽然统一,但“在精神方面,北人对于南人,在此次国民革命之后,怀着一种嫉视的心理。革命而既以主义号召,而要称作‘北伐’,这足使北人感到南宋之对金人,把北人当作异族看待。何况更将北京要改成‘北平’呢?”李氏初以为这只是失意军人政客之见。及一调查,“乃知此一误解与怨言相当的普遍于北方社会”。(注:李璜:《学钝室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165~166页。)南北之间的地缘文化差异,更因有意无意的人为因素而扩大了。
南北猜忌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1930年的蒋冯阎中原大战,其战斗的规模远超过北伐之役。蒋介石在无法以己力战胜冯阎情形下,不得不以1500万元巨款买东北军入关“武装调停”。东北军与冯阎,同属北方,故能不战移防。冯阎对中央的威胁虽消除,蒋却不得不将北方政务托张学良“全权办理”,南京对北方实际上已不能控制。九一八后,张学良在1933年被迫辞职,南京略能插手北方事务,但直到抗战爆发,北方的实权仍掌握在半独立的北方军人手中。(注:关于蒋买张学良入关事,参见刘心皇辑注的《张学良进关秘录》中南京与其派东北代表的来往秘电,特别是第107、121、126~127、138、141、148、150、199页; 引文在第168页。关于南京不能控制北方,参见Hsisheng Chi(齐锡生),Nationalist China at War: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1937~1945,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2,chapter I。)
另外,北伐结合后,蒋介石也不再讳言新旧之分,反而明确宣布:“吾党革命之真意,在除旧布新。……旧不能除,则新不易布。”在南新北旧的大格局下,这样的话北人听起来是不会很顺耳的。实际上,南方新贵对北方旧人也甚感难于处理。蒋介石说:“今之行政机关所最难者,不用一旧有人员,则手续多有不便。用一旧有人员,则旧有之积习,照随之而入。”新旧之分,显然已成为掌权之后的国民党的一个遗留问题。(注:本段与下段,参见蒋介石《今日党员与政府军队及社会之组织惟一要素》。)
蒋介石主张的解决办法,是“行政机关军队化”,故即使用旧有人员,“亦不至有输入旧习之患矣”。而且,蒋以为对中国问题的总的解决方法即是军队要党化,而党、行政、社会以至全国都要军队化。这样的方法是否能解决问题是一回事,但对许多国民党文人来说,国民革命本来是针对北洋军阀的军人统治,同时在国民革命运动内部也要以文人制裁武人。宁汉分立之时,宋子文已认为既然文人制裁武人的局面被推翻,革命已失去意义。今则一切都要军队化,是国民党已走上其革命对象的老路,且有过之。故唐悦良在1929年指出,许多人都认为“国民革命已经失败了”。 (注:唐悦良文刊在英文的《密勒氏评论报》 (China Weekly Review),1929年6月15日。国民革命是否“失败”,是需要专文讨论的,但当时许多人都有和唐氏类似的认知,也是事实。)北伐的胜利却与国民革命的“失败”几乎同时,这样一种诡论性的结局大约是出乎时人所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