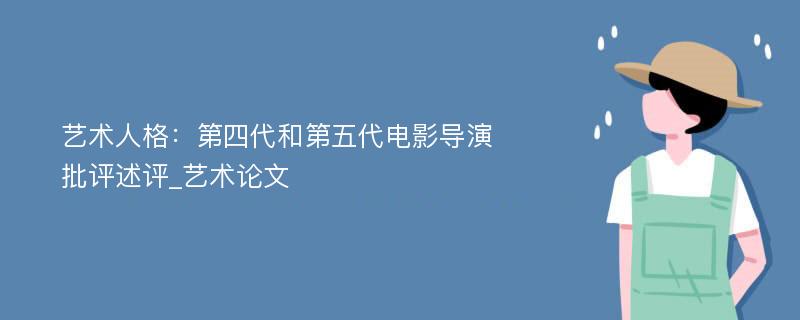
艺术人格:第四、五代电影导演的批评札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札记论文,电影导演论文,人格论文,批评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第四、五代电影导演是新时期电影导演中最为重要的两个群落。本文从艺术人格的角度,阐释了他们在历史态度、文化取向、价值判断、群落集约等方面的意识形态状况,显示了各自不同的人文背景与艺术精神。
Summary
The fourth and fifth generations of filmdirectors aretwo important groups in China. The essay discusses theirattitude,their cultural angling,their stance in value andtheir locale,revealing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artisticspirit of each.
序
作为一种特定时期社会文化语境下的艺术生长,每一位电影导演都会不可避免地泄露其为年龄工期所制约的独特的心理编码,体现出相应的人文内涵以及艺术精神,其所经历的文化培养、人格塑造,以及政治侵染、时代风范都将表现出某种群落意识的共性倾向。即使是在几个年龄工期阶段的电影导演同时创造艺术,共处于一个时间维度,也会表现出各自的不同成长所带来的相异的艺术构思与表达。本文将以此作为学术立论的概念基础。
当“第四代”电影导演以其艺术体现的传统倾向与现代特性之间最高弹性的精神衔接,展开独特的叙事形事和人性抒发时,作为文化新生质的“第五代”电影导演则带着灼热和阴冷的啸呼,送来了《一个和八个》等的艺术幽灵,“第四代”电影导演确实愣住了,加上后来理论导向上的偏颇,在艺术的本性上找不到感觉了,束缚了手脚,弱化了进取意向,但更多的“第五代”电影导演仍然苦苦地追求,不时调整着艺术的体现策略。因此,实际上许多“第四代”电影导演的后期电影创作是和“第五代”电影导演同步进行的,自然要受到“第五代”电影导演的先锋和前卫艺术的侵蚀和渗透,以至向“第五代”电影导演趋齐的倾向,虽然“第四代”电影导演多数曾是“第五代”电影导演的师长,曾经手把手地扶持他们开始艺术创作,并以自己的理论作风培养了“第五代”电影导演的学术意识。但是,历史对小心谨慎的“第四代”电影导演给予过分的嘲弄,“第五代”电影导演毕竟冲上了时代艺术的制高点,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文化新岛群落。当然,“第四代”电影导演后来无论怎样受“第五代”电影导演的影响,都有自己独特的情感传达和艺术运行机制,具有无可替代的自我特质。这也是需要说明的。
一
“第四代”电影导演的艺术理论与实践,一定程度上具有回归传统的意义;“第五代”电影导演则以电影本位的再发现及其在新的审美意义上的重构为突出标识。
“第四代”电影导演受命于中国电影的危难之际。从文革的文化废墟中走出,“第四代”电影导演面对个人和民族的巨大灾难,于意识形态领域拨乱反正的同时,必然对刚刚过去的历史劫难进行深思与反省,从而获得独立思考的人格素质。他们由于文革后所经历的两个否定,灵与肉经受了难以忍受的惶惑以及自省。正因如此,“第四代”电影导演与“第三代”电影导演不同,他或她们开始艺术起步,就不再盲从于主流性的意识形态,体现了某种程度的精神独立,努力将自己的真诚思考体现于银幕上。“第四代”电影导演一方面籍之于理论思辩的学术力量,开始了思想大解放式的理论自觉。主要进行了三次:关于电影创新与民族性、电影新观念、电影特性与艺术本位,虽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但却大大开阔了“第四代”电影导演的理论视野,为从事艺术实践提供电影命题上的原则支持,而且也培养了“第四代”电影导演的学术作风,对“第五代”电影导演向“文化电影”靠拢也起到了推进作用;另一方面,随着开放性的文化态势,“第四代”电影导演开始将艺术的眼光转移到了世界领域,企图以此来更新中国电影的语言结构,确立一种更为深刻且更具个性风格的电影形态,主要进行了两个阶段:一是技巧美学层面上的,大量吸收法国“新浪潮”、“先锋派”以及德国“新电影”所惯用的某些艺术语汇,诸如时空交错、闪回跳接、声画分裂与对位、变速摄影、彩色黑白片的混用,以及多层次、多视角的叙述体例,以至于景物、光影以及梦境与幻想的运用。杨延晋导演的《苦恼人的笑》可以说是这一阶段的集大成者,不仅采用前卫性的修辞手段,而且运用较为成熟,以写实、怪诞和浪漫手法分别对应处理现实、梦幻和回忆等三者不同的时空,在风格样式上,兼有正剧、悲剧、悲喜剧、怪诞剧、闹剧、杂文剧之特点,但文本总体又相当和谐;第二个阶段是纪实美学,由于技巧美学的普泛化,出现了玩弄技巧的浮华习气,而且多数艺术处理尚嫌生硬,加上当时政治、哲学、文化意识渴望真实,于是,法国巴赞的“影像本位论”和德国克拉考尔的“物质现实复原论”成为“第四代”电影导演的艺术时尚,强调主题的多义性、多层松散结构以及板块效应,采用长镜头与运动镜头,追求自然光效、音响、崇尚使用非职业演员并鼓励即兴表演。《沙鸥》、《他在特区》、《见习律师》、《邻居》即是这一阶段的典范作品。纪实美学虽然在实施过程中发生颠覆:传统现实主义的渗透与修正;中国古典美学的写意性原则,诱导其向“诗化”转变,因而不是那么地道,但纪实美学与前面的技巧美学,毕竟使中国电影克服了假、粗、俗的恶劣现象,并且开始走向世界。
由于“第四代”电影导演处于意识形态正本清源时期,从某种意义上他或她们的任务在于矫枉过正,澄清被“四人帮”所搞乱的电影命题,例如“三突出”与“主题先行论”的伪现实主义,因此,“第四代”电影导演的艺术理论与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回归传统的意义,或者说是属于补课性质,再加上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第四代”电影导演取得独立电影导演权,已是人到中年,经历了超长的专业准备时期,而且饱受了坎坷和苦难,心态已和青年时截然不同,艺术的棱角磨钝,失却了许多激烈的艺术冲动,加上长期作艺术导演的助手,到了该成熟期仍然处于被支配的位置,在人格意义上容易缺乏自信,因此,到了后来自己独立制作艺术,也习惯性地缺了些历史性的判断与人性体认的气势以及力度。
第二,“第四代”电影导演受教育于五、六十年代,而这时期正是新中国最美好和浪漫的年代,金星火炬,队鼓咚咚,诚挚、纯情、认真、严谨,时代给予了“第四代”电影导演一种浓郁的“恋母情绪”,或者曰“共和国情愫”,加上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文以载道”的精神,都长时期地作用于他或她们的情感世界,即使遭受文革灭顶之灾,也坚信民族会重构真、善、美。这一切,成了“第四代”电影导演无法改良的心理编码。
第三,新时期的几代电影导演同时并存,尤其是“第三代”电影导演的二度崛起,其以现实主义为基本审美特征以及银幕修辞的规范性,也对“第四代”电影导演产生一定的影响。
因此,“第四代”电影导演从某种意义而论,继承多于反叛,总是小心地摸索着,旗帜不怎么鲜明,目标也似乎不太明确,甚至有不顾左右而言他,因而不可能与“第三代”电影导演构成大幅度的反差,在社会叙事与人情抒写上,对传统有下意识的保留和眷恋,于艺术上不可能过于超前而体现出一定的历史回归倾向,从回归电影本性作为艺术建构的开端,逐渐拓张与发现电影反映现实的艺术可能性与潜力。“第四代”电影导演的艺术总体色调比较温和,而且比较正气。
而“第五代”电影导演则不同了。如果说“第四代”电影导演正在成长中遭受创痛,“第五代”电影导演则是在创痛之后成长。随着大文化战略的重新调整,人本主义的价值观成为社会共识,以标举自我与张扬个性为标志的文化新生代正在崛起,加上“第四代”电影导演的艺术成功,“第五代”电影导演产生了严重的紧迫感,因此,在文化认同和艺术选择上,作出大胆的判断,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文化意识与审美期望,形成整体性的扬弃,对历史的严肃选择与现实的彻底改变获得新的生命意识,少有体现某种历史的承续性,以电影本位的再发现及其在新的审美意义上的重构为突出标识,于叙事形态、时空构筑、镜象语言上实现大幅度的美学超越。
这首先表现在张军钊导演的《一个和八个》中的一枪:突围之后,女卫生员杨芹儿与土匪瘦烟鬼、“逃兵”小狗子,再一次遭遇日本鬼子。小狗子被日军用刺刀扎死,而杨芹儿则被围住,眼看要遭到污辱,刚从河边汲水回来的瘦烟鬼,藏在一个土丘后面,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终于……
——[中景]他颤抖地举起了枪(画外是鬼子下流的狂笑声)枪膛里压进了最后一发子弹。
——[特写]画面上突然一切声音都没有了,只有一只手哆哆嗦嗦地寻找着板机。终于摸到了,手指的压力使板机慢慢地向后移动着。突然,整个枪一震,出画。
——[特写]杨芹儿无声地趴在地上,后背一个圆圆的枪眼,但没流一滴血。她死得那么洁净。
鬼子们被这突如其来的一枪打懵了,紧接着,是一个全景的长镜头:只见:
瘦烟鬼平静地走出土丘,泥塑般站在那里,他既是对鬼子、也是对自己一字一句地:“老子——中国人!”说完扔掉大枪(枪膛弹尽),将大褂脱掉扔向空中,背转身去,沉着地向远处走去(背影,走向画面纵深)。走着走着,他佝偻起身子,慢慢咳嗽起来。突然,响起一声干涩的枪声,咳嗽中断,他倒了下去,他的躯干和两条大腿冷静地组合成了一个光彩夺目的“人”字。
当时,看完试映以后,人们骤然发现:原来罪恶同善良同在!这可不是普通的一枪啊,是土匪为了捍卫民族的圣洁,而向曾经是他的征服者的八路军女卫生员发出的一枪,而且拍得那么神圣。“第四代”电影导演开始了人性抒情的独特结构:人的分裂与复杂性,不再局限于“第四代”电影导演的人情意义,而表达人的深度体验,乃至于形而上的天人合一的自然人性或者性本善的意识层面,并努力体现作为历史沉淀物的民族意志与精神氛围。
“第五代”电影导演不仅于社会话语与人情刻画上产生质的突破,而且在艺术修辞方面,大力强化画面造型自身的表现力量,凸现它的内外张射度,例如对单色调象征性内涵,冷色、重色静态画面之凝重沉雄,大块面浓色调视角冲击,贯穿整个影片的基本色大写意的把握与建构,使“第五代”电影导演的语言体现,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象外之象”的提升,使前几代电影导演主要依赖艺术情节叙事的张力来结构的电影发生根本性的颠覆。“第五代”电影导演于情节叙事观念的绝对崇拜与影像本体功能的绝对崇拜,在田壮壮导演的《猎场扎撒》和《盗马贼》可谓达到了极至。剧中的情节作用降低到了极限,主要凭依画面视象的冲击力量,而直接进入到人与自然、人与宗教的思考境界,也使电影上升到了文化的学术地步,甚至达到了“历史判断”的境地。
二
“第四代”电影导演的文化切入点,常以横向评判作为惯用的艺术处理手段;“第五代”电影导演则从历史的反思中,探究民族发展的内部规律,采取纵向进取的文化策略。
艺术的最高要义在于表现文化,而每一个电影导演群落都会有各异的文化切入视角与兴奋焦点。“第四代”电影导演对文化的体认和重构,往往从社会或历史的横向面入手表现出两种价值形态:第一从人学意识而论,将人置于政治社会关系与现实处境的诸种矛盾中,由此传达出人的现实生存形态及其价值;第二从社会历史关切的层面,从社会历史的深切关怀开始但又止于深切关怀,表现出某种同情或怜悯的情愫。“第五代”电影导演多从纵向入手,以当代意识去重新体察民族历史的内在运行规律,正如陈凯歌所说的:“在经济振兴的时代背景下,找出一个民族观念形态上的历史继承。我们想追溯历史,表现对养育我们的人民、土地的感情”〔1〕。因此,俯视人生,反思历史, 具有了理性电影的反思色彩。陈凯歌导演的《黄土地》,将翠巧一家两代人的生活命运同古老的黄河、以及那块带着千百年封建历史积淀的黄土地联系起来,把艺术的审视目光更多地投入历史深层,努力表现民族的惯性与惰力带来的正负面,触及了民族性格中的“源”,以及封建制度与小农经济下农民的贫困、落后和愚昧,从而折射出深蕴于我们民族内部渴求变革的历史情绪与潜在力量,从理性与非理性的层次上同时走向深化,而且在采集和陈述历史时,没有丝毫的猎奇与贵族姿态,只有一个对于自己民族过去的郑重的回顾。剧中有一个抒情主人公,即作者本人,他将人与黄河、土地、历史同化为一体,表达着各种理性和非理性的历史情思,例如翠巧在黄河边上挑水,长焦距将静默的黄河水的景深缩小,充溢着画面,翠巧的形象便与浩淼的黄河溶合一体,也寓意着她最后的命运;大远景的高天厚土与塬上耕作的渺如蝼蚁的人,这种极强的大反差处理,展示了人对黄土地的依赖又始终无法摆脱黄土地的束博所因袭而来的精神重负与惰性,具有历史的沉重与苍凉的穿透力量;滚滚黄尘中惊天动地的腰鼓方阵、高高天宇下虔诚迷信的祈雨人流,都寄托着艺术家对历史的热烈情思。剧中的父亲形象,更是表达了作者的历史追根情怀,某种程度上可以寓意为中华民族的整体象征。陈凯歌导演的另一部电影《孩子王》,表现了两个范畴的事物:第一有生命的,第二是文化的构成,艺术家将其处理成了对立的层面关系。凡是有生命的,例如山上的野火、流动的云彩、放牛的孩子以及走动的牛群,都是沉默的无声的;而文化的世界:写字声,读书声,唱歌声,却是生机勃勃的有声,这里组合成了一个颇耐玩味的寓意:作为文化的文字符号本来是人制造的,为人所服务的,但是而今学了这样一部文字,却限制了人的活力,这里艺术家超越了社会意义的层面,而走向传统文化历史反思的深刻境地:文化是人的生命的创造,但文化又制约了人的生存。田壮壮的《猎场扎撒》、《盗马贼》更是深入“异域”的民族历史,借助少数民族的“理想国”以及“理想国”的破灭,来反射自己民族历史的文化背景。黄建新导演的《黑炮事件》,也以纵向把握故事文本的手法,揭示了长期的封建意识所造成的某种惯性给予知识分子的二元分裂性格(两个自我)。一个自我具有民族尊严感以及时代庄严感,例如与汉斯的激烈争论,事业上有所成就,体现出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正面价值;另一自我则是遇事唯唯诺诺,凡事都检讨着自己,承袭着民族传统心理自轻自贱的缺陷,表现出负面的价值。当“黑炮事件”水落石出以后,“左书记”还将WD工程的事故推到他的头上,他仍然唯唯诺诺地听着,还躬身自审地说了句:“我以后再也不下棋了”,触目惊心地刻画了传统历史文化心态对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严重腐蚀。
“第四代”电影导演由于特定的人格向度,在文化的切入点上,常以横向评判作为惯用的艺术处理手段,提取一个发人深省的社会故事,发现一些哲理性的乃至某种程度上的人性的命题。但是,文化层面上的横向把握,缺乏历史纵深度的支撑,极易产生失准乃至错位的现象,表现出于传统的事物有所保留和眷恋,从而失却某种深刻度。吴天明导演的《人生》,对剧中女主人公巧珍偏爱有加,对她的不幸寄予了无限的同情,而且还暗示了这一迹象:仿佛,巧珍的一切不幸都是高加林的“负心”造成的,将巧珍作为中华民族美的象征来加以歌颂。如果是横向的文化叙事方法,这个价值体系是可以自圆自足的,但是一旦脱离这一文化视角,作纵向观,把巧珍的遭遇置于民族文化历史加以重新批评,可以发现巧珍的美具有极大的缺陷,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传统文化的牺牲品,正是由于巧珍的缺乏独立性,把对男子的依附作为自己的唯一幸福,才是造成她悲剧的历史根源。导演的横向评判,还体现在对高加林的态度上,对这一位在人生的道路上奋力拼博的青年,置于人生怪圈式的历史循环:即从零状态又回到零状态,离开土地开始,经历若干的体验和事件,又重新回到了土地,好象他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因为他背叛了导演心目中的美的象征——巧珍,最后当高加林回到村前的山岙时,还用一首“信天游”作了总结:“哥哥你不成材,卖了良心才回来。”滕文骥导演的《海滩》,也产生某种错位:将代表现代文明的工业与象征传统观念的渔村置于横向透视的两极,将之对立起来。剧中凡是一切陈旧的东西都加以装饰,用极美的画面篇幅去表达,老鳗的渔歌,对大海的传统方式的朝拜升腾为一种理想的化身,隐约地传达了潜意识中艺术家对渔村古朴文化与文明的深深眷恋,也压倒了大工业林立的烟囱所传递的人类未来生存状况的信息,表现出某种“文化回视”的意识格局。张暖忻导演的《青春祭》本来是对文革时期一段生活经历的沉重反思,但导演却将艺术的笔触,去描写南国少数民族美丽的民俗生活,以及生发着的温馨的人际关系。剧中的女主人公对那个美丽的地方的一切是那么地留恋,客观上削弱了作为青春之祭的艺术主题,具有了人返自然的倾向。黄建中导演的《良家妇女》体现出某种文化纵向批判的势头,但导演一方面大力歌颂了女主人公为追求自由婚姻所作出的反抗,另一方面又浓彩重墨地刻画了“小丈夫”对“大媳妇”的所谓感情,以及婆婆对媳妇的同情、理解,尤其是林中告别一场戏,处理得过于缠绵与揪心,一定程度上与创作者的原意产生疏离。
文化判断的横向与纵向的区别,其实是由“第四代”电影导演与“第五代”电影导演不同的深层文化心态或者说是内心情绪使然的,有其特定的内在制约因素。“第四代”电影导演除了传统文化的惯力沿袭之外,也跟其独特的人生经历有关,总把温柔的依恋,对社会的崇敬,以及对美好人性的信念体现在自己的艺术中;坚信民族总有力量使荒芜的原野上再生茵茵绿草,殷殷红花,因此,不可能也不习惯从纵向上去剖析文化;而“第五代”电影导演则于民族的巨大灾难中,痛感某些传统恶习对民族前行的阻碍乃至破坏,加上对现代化的渴望,便竭力从历史的反思中,努力探究民族发展的内部规律,肯定作为原动力的积极因素,抛弃和拒绝落后以及腐朽的消极事物,从而采取了纵向进取的文化策略。
三
对传统文化的审视,“第四代”电影导演在感情上较难摆脱对传统文化的依赖和眷恋;“第五代”电影导演更多地倾向于揭示传统文化的负面意义。
当电影进入文化审视范畴,就会表现出价值取向的相异特征,或从正面或从负向对传统文化进行体认和重构。“第四代”电影导演虽然是文革以后最早使电影具有文化和艺术品格的,从学术的思辩中开始电影思维与艺术修辞的更新,并为“第五代”电影导演的艺术成长培养了良好的人文环境,但是,“第四代”电影导演毕竟有其特定的生长文化语境,五、六十年代的学历教育留给他们太深的情感记忆,传统文化的沉淀很厚实,乃至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在时代的意识形态大调整中,他们也渴望建立一种新的文化秩序,从理性上追求电影艺术的重构,但是,他们不可能对曾哺育过自己和自己以为神圣的传统文化加以全盘否定,在感情上摆脱不了对传统文化的依赖和眷恋,体现了“第四代”电影导演温馨善良的情愫。吴贻弓导演的《城南旧事》,将善良的人本关怀,贯穿于全剧的主要人物,成为表达人性意识的永恒创作母题。黄蜀芹导演的《人、鬼、情》中,秋芸跟着省里来的戏校老师走了,她的父亲望着他们的背影,在丝丝的怅然中,给身旁的小狗喂油条,终于无可奈何地走了,小狗颠颠地跟上去……短短的几个镜头,却余音袅袅,传达了难以言说的情感内涵。谢飞导演的《本命年》,几次将艺术的镜头对准主人公李汇泉挂在墙上的母亲的遗像,表现了对逝去的母亲的无限思念与眷恋,即使在他最终离开这个世界,他的潜意识里也尽是女性的声音和形象,甚至连逃犯方叉子最后的心愿也被凸现为“去看看我娘”。
“第五代”电影导演的反思精神,体现在文化的价值判断上,更多地倾向于揭示传统文化的负面意义,乃至通过否定式的寻根,挚爱与叹息交加,以及理解与批判掺杂,正如黄建新所说的:“只有对祖国充满着挚爱的艺术家才有权在作品中指责自己祖国的缺点。”〔2〕他们的艺术往往在消极的层面上衬托正面形象,于冷峻的外表中深藏着一颗赤子之心。因此,“第五代”电影导演的作品解读,需要耐心,且有相当的智力,因为它们的表征总是那么“调子有些低”或“有些灰”。陈凯歌导演的《黄土地》,剧中有二场婚礼,开头是那位不知名的女子,后来当翠巧出嫁的时候,又将前面这一段落中的镜头同机位、同景别、同焦距的重复了一遍,惊心触目地说明了翠巧的婚礼只是无数次互相重复的迎亲仪式中的一次,象征着中国的女子千年不变的命运,尤其是前面的一场婚礼,当十四岁的新娘坐在床上,画面外伸进来一只黑乎乎的显然已是中年男人的手,画面构成的震憾力是强烈的。同是表现婚礼,吴天明导演的《人生》里巧珍的婚礼,则温馨多了。陈凯歌导演的另一部电影《孩子王》,剧中的主人公老杆终于因为不按规定教材教学而被辞退了,临别之时,他用粉笔在树墩上写着:“王福,今后什么都不要抄,字典也不要抄。”艺术家一下子将艺术题旨上升到人与文化的关系,从老杆的失落中,重新审视传统的文化精神与教化方式,以较为彻底的否定批判精神,体现了某种独立的人格价值。田壮壮导演的《猎场扎撒》,剧中描写的“理想国”,当两村重新实现和睦,两村的四名骑手一同跪在马桩前忏悔,四个人的剪影一再被叠化,便将这种忏悔的情绪推向了高潮,再切入古猎场与“扎撒”巨石傲岸指向苍穹的最后一个镜头,巨石上的蒙文字迹上面叠映出汉文:“苍天在上,大漠为证,愿吾臣民,持仁爱之心,奉公守诚……成吉思汗”,此时此刻,田壮壮的主体已渗透于对蒙族文化精神的确认之中,从而构成一种反差。到了《盗马贼》,田壮壮则通过人与宗教的互制关系,人为了追求情感的寄寓而制造了宗教,而宗教却深深地限制了人性的生存与发展,这种自虐性的人类文化运作模式,田壮壮彻底绝望了,陷入了对自我和历史的双重否定,特别是“雷击神箭台”一场,罗尔布历经磨难、频临绝境的时刻,望着以前心目中神圣的神箭台被巨雷击中、燃烧、倒塌,他对神的怀疑与绝望,骤然地涌上他的心头,显示着一种信仰的彻底崩溃,而后他再次盗马并终遭杀害,奔向天葬台而死,皑皑雪原上留下他的腰刀和血迹。田壮壮说:“我拍《盗马贼》时完全是一种绝望心理……不仅人对于社会是软弱无力的,因而我绝望;人对自然也是软弱无力的,所以更绝望”〔3〕。 而这种“绝望”渗透于罗尔布悲剧命运与藏族宗教仪式的描绘中,又历史性地与田壮壮自己在文革中经历和体验的“绝望”重合在一起,所以田壮壮说:“《盗马贼》是我的自传”〔4〕。但是, “第四代”电影导演于民族文化的负面揭露,透示着一颗赤诚的心,是冷中见热的艺术结构方法。《孩子王》中,当老杆离开学校时的主观幻听幻视:在“烧坝”那一场大火中,在熊熊的火烟升腾中,画外传来了学生的玩闹声、欢呼声、钟声、开山的炮声、砍伐声、大树倒裂声、牛铃声、口哨声以及知青齐念“从前有座山”的循环故事愈来愈强烈且压倒一切的声音,这分明是陈凯歌心目之中理想的文化与人的境界。黄建新导演的《黑炮事件》,对知识分子性格组合中的负面因素进行了剖析,而且全剧贯穿了冷峭而苦涩的幽默,但这与西方国家的“黑色幽默”与“荒诞派”不同,而是于冷峭与苦涩中透示着热忱与希望,表达了“第五代”电影导演的独特人文话语。
四
作为一个导演群落,“第四代”电影导演于五、六十年代接受较为稳定正规的教育,其文化底蕴,艺术气质,思维特征,乃至于情操与修养,都有相当的普遍性,互相落差不是很大,加上文革以后,在理论层次的学术争论中,都经历了形式美学和纪实美学阶段,有共同的艺术复合部位,于艺术体现上存在趋同结构,选择合理中庸的策略性叙述,表现出善良怜悯的内心情结,而“第五代”电影导演作为文化新岛群落之一,遇上了八十年代难得可期的历史契机:整个世界正面临着新的文化转型或文化组合。于东西方文化互相撞击与渗透中,“第五代”电影导演得以重构自己的文化传统与电影诗学同世界发生对话,在新的现代意义上重建着中国的人文理想与艺术精神,确立自我的文化与艺术位置,因此,“第五代”电影导演传达自我,张扬个性便成为其艺术的标识。与“新浪潮”电影一样,注重渗透于题材中的自述性,即无论历史题材或现实题材,无不凸现着艺术个性与主体的折射,烙刻着艺术家灵魂的印记。“第五代”电影导演纷纷占领艺术的制高点,进行独特的文本叙述。陈凯歌往往于强化了的政治文化背景中,揭示民族历史与个性生命的复杂与分裂,因为这种背景最容易表现民族的受伤之处和个体在此制约下的扭曲与异化。陈凯歌在“中原寻根”,总把自然人格化了,把环境因素作为艺术叙述的主角,其实《黄土地》、《孩子王》的主人公是黄河和黄土地、红土壤,在这些所有的形象之中,更有一个隐含的主人公,即作者本人,虽然始终没有出场,但却无处不在。剧中的情绪与思想,甚至于情绪特征与思维线路,都属于这一个抒情主人公的。因此,陈凯歌的艺术是“相当个人化的作品”,某种程度上达到了“作者电影”的境地,具有了文化哲学的意味。与陈凯歌艰深费解的思辩风格不同,张艺谋选择了另一种艺术战术:于故事的叙述层面与造型的意象层面同时强调很强的观赏价值与情绪感染意义,采用传奇性的神话原型,将客观形象重新进行解构与重组。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五代”电影导演到了张艺谋这一阶段,发生了分裂和新的突进,开始疏离了陈凯歌等的艺术中由历史与文化的重重积淀给人的精神负累,强调对叙事表意系统的张力作用,采用超现实的与浪漫的表现手法,体现了于传统电影与现代电影的双重反思,而且,张艺谋的电影在人性抒情上,极力淡化它的政治文化背景,将人置于相对真空的精神环境中,揭示人的自然人性与性本善的层面,从社会历史的意义收缩到天人合一的范畴。田壮壮与陈凯歌不同,不是“中原寻根”,而是借助那些尚未进入现代文明的人类文化的“荒原”与“异域”,去寻找与重建某种相对肯定的文化价值,可以说是“异域寻梦”。尤其重要的是,田壮壮所采取的情节策略,从淡泊、朴素中表达现代感受,超越社会意识层次,直接进入人与自然、人与宗教的思考境界,将情节的叙述因果降低到极点,几乎主要依靠画面造型的张力度,把“符号美学”推向了极至的境地,以展示它的终极魅力。因此,田壮壮大量的艺术超前,与电影的现成规范以及观众的承受能力发生了距离,在艺术的经济意义上处境尴尬。吴子牛则选择了战争题材,于生与死的临界点揭示人的性灵,爱与恨都得到了最原始、最淋漓尽致的大力渲泄。在他的电影修辞语法中,摒弃了温柔如水的一面,而充斥着朝圣者痴迷热诚般的低回、高亢、苍凉或者悲壮,于情节的传奇性表达中,体现了人的最终形式——死亡的诸种意义。黄建新的《黑炮事件》、《错位》,侧重刻画知识分子双重的人格和心态,而且以“现代寓言”的方式加以结构。胡玫注重对女兵的心理描写,她的《女儿楼》、《远离战争的年代》,都体现了她的敏捷与机智,镜头运用的峭奇性,时空处理的快速交插,充满诗意的画面造型,以及对人物内心的层层表现,象征与写实的巧妙融合,平稳与强烈的鲜明对比,体现了作为一位女性导演的精神特质。而张泽鸣的《绝响》与《太阳雨》则以表现城市题材见长,表达了来自现代文明本身所造成的内心分裂,描写了一个城市成长的情绪,那种渴望、力度以及脆弱,而且与北京胡同和上海弄堂不同,南国都会广州的商业气息十分浓郁,具有很丰富的现代人间气息,在艺术风格的设计上又表现出对温柔敦厚的古典式阴柔的过多偏爱,传达了特定地域的城市感觉。
注释:
〔1〕陈凯歌:《追求与苦恼》,载《文艺情况》1984年第10期。
〔2〕转引自张成珊:《第四代和第五代文化分野》《艺术世界》1990年第二期;
〔3〕〔4〕田壮壮:《与壮壮谈壮壮》,载《当代电影》1989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