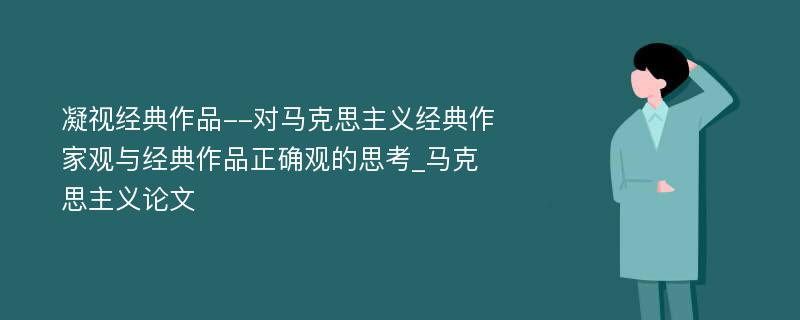
凝视经典——关于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经典著作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典论文,经典著作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正确论文,作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虽然在表面上是一个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合法性问题,但在实际上,却是一个如何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经典作家、防止真理的个人独断或以权威言论为标准的认识问题。真理的标准之所以常常偏离实践检验的轨道,造成理论的停滞和实践的心理障碍,往往是由于社会传统中长期积淀的非科学、非理性的权威崇拜的心理惯性造成的。因此,端正对经典著作和经典作家的科学态度,虽然不是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全部问题,却是必须首先解决的关键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不仅在七十年代末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即使在改革开放承上启下,新老交替的今天,同样有着解放思想的现实意义。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经典著作和经典作家呢?
一、看待经典,需要科学的态度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最丰富,最宝贵的思想遗产,它们已经并将继续对中国的发展产生长远而深刻的影响。但是,历史已反复证明,经典的实践意义,往往并不单纯取决于经典理论本身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实践者对经典理论所采取的态度。当我们能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看待经典时,经典就会成为我们手中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工具,从而使理论经典的指导作用和内在价值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把社会推向新的进步。相反,如果我们不能实事求是的看待它,对它进行教条式的理解时,它就可能成为束缚我们思想的桎梏,社会实践就会遭受挫折,就会产生马克思曾嘲笑教条主义者的“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得却是跳蚤”、事与愿违的尴尬结果。错误的不是经典,而是人们对经典的错误的运用。
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门科学,因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经典著作,就要求人们必须把它们当做科学来对待。用科学的理性眼光去研究它、认识它、学习它,而不是迷信它、重复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是教义,而是行动的指南。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却从未根除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教条化、神圣化的思想倾向。每一次新的理论突破和新的思想解放之后,随之而来的往往是新经典的教条化和神圣化,用新的教条代替旧的教条,新的迷信取代旧的迷信,思想解放者往往又不同程度的演化成新的思想禁锢者。于是就产生了“经典教条化(思想僵化)→思想解放→新经典教条化(新的思想僵化)”,这样周期性的怪圈循环。尽管这种周期循环具有螺旋式上升的特征。但它的僵化时期毕竟造成了思想匮乏,社会停滞的后果,并有积累矛盾激化矛盾导致政治动荡的可能。僵化的思想常常是以牺牲社会的精神创造力为代价的,它也常常潜伏着巨大的思想危机和心理逆反。
值得指出的是,政治意识形态这种周期性循环,并不同于科学哲学家库恩所说的新旧科学范式的升级方式。因为,如果说在科学界,对一种科学范式的接受,是出于自愿或学术规范性强制,那么,对于一种理论经典的接受则是出于自愿或“权力话语”的超学术强制。前者是一种学术或科学行为,后者则是一种政治行为。后者的优点在于当经典的理论基本正确时,它便于直接的社会动员,高度的统一社会思想意志,推动社会前进。但它的缺点是,当经典的论断发生僵化或失误时,它就可能压抑社会思想的进步,并且由于它缺少外部批评校正机制,它的校正往往只能通过自我反思来实现,所以它的校正过程常常是缓慢和不确定的,甚至会出现正反馈,使错误扩大化,使局部性错误演化为全局性错误。因此,从长远看,经典理论的形成和更新越是从政治运作转变为一种科学运作,它就越具有可靠性和稳定性,越易于得到社会普遍检验和认同。二十年前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就是这一运作方式的可贵尝试。
从某种意义上说,培养一个民族成熟健康的理论态度,比简单地宣传某种正确理论更重要,更具有基础性的意义。社会的总体理论态度是一个“思想场”,有什么样的理论态度,就会有什么样的理论。因为,如果只有正确的理论而缺少社会正确理论态度的配合时,正确的理论就会被不正确的理论态度所异化,而变得面目全非,正确的理论文本往往会被自觉不自觉的误读、误解、误用,而不能得到正确的发挥。甚至会在实践中,产生极其荒谬的结果。而当一个社会具有成熟的理论态度,它就不会为任何表面的光环所诱惑,任何错误的理论观点,都会在理性的审视中失去市场。即使暂时没有一个现成的正确理论,他们也会在实践中,在讨论中,在探索中把它创造出来。对于当代中国来说,缺少的不是科学的理论,而是科学的理论态度。所以,在我们对伟大的经典作家们保持深深敬意的同时,也要对经典著作保持科学的理智。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和经典作家。
二、要理解经典,不要迷信经典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经典学说,无疑是它们所处时代的思想精华和智慧结晶,它们以其真理的深刻性和实践的有效性,而赢得社会的普遍认同和信服。经典不是自封的。它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具有权威性的理论经典,是因为它们代表着自己时代的最高理论成就,代表着真理和正确。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种真理不是绝对的和永恒的。绝对化的真理,往往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理论错觉。因为,现实是异常复杂的、不断变化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把握它,认知它,任何经典著作都不可能完全摆脱时代和个人的局限。它们虽然包含着许多真理,但却不可能囊括所有的真理。
概括地说,经典著作一般包含两个层面的理论:一个是基础理论,即立场、方法、世界观、价值观等,这是经典中最具历史生命力的灵魂和核心部分,也是最具恒久性、普适性和使用价值的部分。另一个是具体理论或应用理论,是关于当时具体问题的具体结论和见解,具有针对性和特殊性,因而也具有极大的真理相对性,其现实时效性将随时代的变迁而递减。正是由于经典著作这种不同的理论构成,特别是那些具体的“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范围内才是正确的。”(恩格斯语)相对真理的大量存在,就使我们不可能完全照搬经典的个别结论来解决现时代的问题,而必须在新的具体背景下重新思考,进行新的“思想实验”,在实践中寻找新的恰当的结论。经典著作真理相对性的客观存在,是我们反对一切教条迷信的内在依据。学习经典不等于简单地重复他们的结论,而是要重新或继续他们的思考,只有通过思考,才能深入经典的灵魂,才能使经典理论获得生命力,变成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活生生的思想。学习经典是一个真理的再发现、再确认、再选择的过程。经典著作应该是我们思考的起点而不是终点,它启迪人们思考而不是代替人们的思考。经典的意义在于解放人们的思想,而不是束缚人们的思想。我们不应该是经典被动的受话者,我们不应该丧失作为经典阅读者的能动主体性。阅读经典是与大思想家们的精神对话,经典的读者应该是思想着的人。自我独立思考的缺席,只能造就精神侏儒和思想傀儡。我思故我在,我行故我在。教条主义只会阉割马克思主义自我发展的创造力。每一代人都面临着新的事物、新的变化、新的知识、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因此,他们必须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科学方法基础上,重新思考一切。也许我们应该向经典作家们学习的最重要的一点,恰恰就是他们学习经典,却从不迷信经典的品质。马克思、列宁是如此,毛泽东、邓小平也是如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兴盛和发展,只能建立在迷信和盲从的基础上。所谓解放思想,就是要从对理论经典的崇拜中解放出来,从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束缚中解放出来,不唯书,只唯实,在实践中实事求是。
三、学习经典,需要民主精神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典不是教义,而是科学。而科学是需要民主精神滋养的,就如树木需要阳光、土壤和空气一样。因此,在我们阅读经典著作时,必须倡导一种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民主精神,激发人民群众的思想活力,而不是把学习经典变成一种精神崇拜,把理论探讨变成少数人的特权和专利。一个国家只允许一两个大脑思维的状况是不正常的。思想发展和理论创新是人民群众共同的事业。没有民主的参予,缺少民主氛围,就必然缺少独立思考和创造。
任何理论都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正确,正确的东西里也可以包含一些错误的东西。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社会心理的权威意识的积淀和民主精神的缺失,常常使我们无法正视经典著作中的某些弱点和片面,这也成为教条迷信长期流行的精神病源。倡导民主精神,就是要求我们不要象“文革”时期那样,将经典著作人为的神圣化,使之成为凌驾于科学和民主之上的“超级语言霸权”,造成对社会思想活力的压抑。对经典著作和经典作家过度的尊崇,就会使合理变成荒谬。那种以压抑社会集体思想活动为代价而突出个人理论权威的做法,往往得不偿失。过度的个人尊崇和权威膨胀以及强迫式的求同思维,势必造成社会的集体不思考、全民性智力退化和创造力萎缩。一个只有经典的时代,必然是一个理论贫乏、思想单调的时代,越是简单的思想系统越容易失衡和崩溃。不同观点的相互制约、补充,才能相反相成。经典理论只有在民主精神的滋养下才能发展壮大。如果,经典著作被拔高到一个吓人的高度,失去了社会民主环境中的平等交流,拒绝任何善意的和正确的批评与修正,那它就会象拔离地面的参天大树一样,因失去土壤和水份而枯竭。经典理论是民主精神的果实,我们应该恢复和保留经典著作的民主气质。担心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同其它理论的交流中被淹没是多余的,马克思主义远远没有那么脆弱,它只会在碰撞、交流中更加强大,而不是衰落。我们应该有这种理论的自信。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无限的包容性和消化吸收能力。相反,如果让经典孤立存在,结果却可能会走向反面。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其它理论或思想流派之间,存在着一种类似于“生物链”或称之为“思想链”的共生互补关系。“测不准原理”表明,任何一个理论都不可避免的存在着自己的盲点和误差,而一种理论在封闭的自我循环论证中,往往不能及时发现和修正自身的缺点。所以只读经典,就不可能客观全面的理解经典。只有当我们使经典理论与非经典理论,主流话语与非主流话语,主导思想与非主导思想,在民主的氛围里进行沟通、对话、论证、反驳、竞争时,才能形成健康的理论生态,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社会思想中真正起到整合和统摄的作用。才能激发经典学说的活力和魅力,使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之树常青。马克思主义是大海,而不是小溪。我们应该保持它容纳百川的气度和博大胸怀。
诚然,经典的指导作用是重要的,它是我们不可缺少的思想源泉。但是,对于跨世纪的中国来说,仅仅依靠几部经典著作显然是不够的。中国的发展理论应该建立在全社会思想创造力和倾听群众呼声以及人类创造的全部科学文化成果这个更广阔的民主基础上。人民才是我们智慧和力量的最终源泉,人民才是我们的上帝。而这一点也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全部经典的精髓所在。
四、尊重经典、但更要重视实践
理论和实践是相互推动,互为因果的矛盾运动过程。理论经典产生于实践,也将归之于实践,实践才是最终的目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实践中不仅要自觉以科学的理论经典为指导,同时还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检验和校正理论经典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个开放性系统,理论经典对实践不是单向的输出,同时,也需要实践反馈信息的输入,在实践中发展。真理的发展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不断反复的过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原则和常识。但是,这个原则在巨大的权威的声誉面前,常常变成无足轻重。特别是在以住的实践中曾取得过巨大的成功的理论,当它的某些理论观点,在新的实践中被证明是不适宜或不完备时,人们总是因它昔日的光荣而不能正视它今日的缺陷,不能予以实事求是的纠正。但是,这种对经典表面光荣的维护正如马克思所说: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页。)常常是以牺牲社会实践为代价的。
从根本上说,包括经典著作在内的一切理论,都是以社会实践为目的的。理论既是实践的产物,又是实践的工具,它们只有在服务实践中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社会实践是理论研究的终极目的,而不是个相反。因此,主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决不等于主张检验真理是实践的唯一标准,决不等于主张检验真理是实践的主要或唯一目的。社会实践本身有着自己的目的,那就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人民群众耗费巨大人力、物力、财力的社会实践目的,绝对不是去为了证明某个理论观点的正确与否。社会实践的核心问题是满足广大人民的利益,而不是是否合乎某个经典理论的观点。但在实际中,却常常被人们本末倒置。把实践当成某个理论观点的附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典之所以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恰恰在于它契合了人民的利益并有助于人民实现自己的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社会政治领域,人民是真理的最终评判者,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在相当程度上就是真理的人民利益标准。一个主张或观点的正确与否,最终要看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因此,最终决定一个党、一个国家命运的,并不在于打着谁的旗号,而在于它真正为广大人民谋取了多少真正的利益。所以,我们只有坚持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方法认识和分析问题,有效地回应现实的各种挑战,切实解决好实践中的每一个矛盾,我们的事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的确,学习经典是重要的。经典的重要在于它们凝聚着前人的实践经验、方法和智慧。虽然,经典是昨天实践的总结,但它们却有着超时空的理论先导性、预见性和预警性。学习它们能使我们少走弯路、少受挫折、减少失误。但是,如果我们仅仅阅读经典,而缺少实践的参照,我们就将永远无法真正理解经典。只有在实践和理论的彼此观照中,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经典的意义和价值。另外,我们也应该清醒的知道,相对广阔无边、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而言,经典毕竟是有限的,而实践则是无穷的,我们不可能在经典中找到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许多东西要靠我们去发现和创造出来。所以,我们还必须去阅读另一部活的“经典”——实践,在实践中我们能学到许多新的、在经典中学不到的东西。实践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必修课。没有哪一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是靠从前人的经典中寻章摘句得来的,它们都是从社会实践的开拓探索中总结出来的。实践是经典的经典。总之,我们要尊重理论经典,但更要尊重实践,蔑视实践的人是不能不受惩罚的。而尊重实践,就是尊重人民,尊重人民利益,尊重客观发展规律。真理是很朴素的东西,经典只是为实践服务的工具,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偶像。
五、超越经典,面向未来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发展的理论,它必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经典学说,象思想的阶梯,构成一个不断攀升的过程。这种发展,过去不曾停滞,今后也不会停滞。科学没有终点,科学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发现的开放体系。每一部经典著作都是一个里程碑,都是一个时代的理论杰作,但每一部理论经典都不会是终极真理,而是真理发展进程中承前启后的中间环节。它超越前人的经典,也将被后人所超越,这就是认识发展的辩证法则。经典的主要意义在于指导自己时代的社会实践,创造历史,在历史实践中实现了自己的理论价值。对未来时代的指导只是经典的第二价值,越是伟大的经典对未来的影响力就越长久。但是,经典对未来的指导性必然是间接性的,它必需是以后继者的主体性为中介的。理论经典可以成为后继者极具指导价值的未来启示录,却不可能成为解决未来事务的答案大全。我们不能过分苛求前人的经典,也不能过份期望前人的经典。没有一劳永逸的科学。正如斯大林所说:如果幻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以后可能发生的一切理论问题给我们作出现成答案,使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后代可以安然地躺在暖炕上来咀嚼这些现成的答案,那就太可笑了。”(注:《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68页。)形势在变化, 时代在发展,即使理论经典中,那些曾在过去的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的、成功的主张,搬到新时代的今天,也未必就能包治百病,再创辉煌。实践的检验也是相对的,昨天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在今天的实践中并不必然正确。“一个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所以,以守株待兔、刻舟求剑式的态度学习经典著作,只能是做茧自缚,难有作为。没有理论上的突破和超越,就不会有实践上的飞跃和发展。学习经典就是为了超越经典。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使命。我们不能在前人的经典面前,高山仰止,固步自封,而应该站在巨人们的肩膀上,“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老托尔斯泰说得好:“正确的道路是这样,吸取你前辈所做的一切,然后再往前走。”
超越不是否定,而是扬弃。是继承中的发展,发展中的继承。没有继承就没有发展,而没有发展也就没有真正的继承。超越不是追求浅薄的轰动效应而哗众取宠,超越也不是标榜自己的政治炫耀,而是一种现实的需要。任何脱离实际的、主观的去炮制新理论、新思维,制造各种时髦理论泡沫的虚张声势的“超越”,往往是头重脚轻、昙花一现,欲速不达。真正有效的超越,往往是植根于现实的需要,在日积月累、一点一滴的创新中逐步形成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经典著作中正确的理论,完善它所不完善的主张,创造它所缺少的思想。我们既要善于吸收经典著作中正确的、科学的、有现实价值的部分;又要善于及时发现和校正经典理论与客观实际相矛盾、相脱节和不相适应的部分。对经典著作既不能盲目迷信,一味照搬,更不能盲目怀疑,一概否定。两种极端的做法都是错误的。轻视继承是幼稚的,而轻视超越则是另一种幼稚。因为,历史既是连续的,也是发展的。当然,无论是对经典的继承,还是对经典的超越,都不是主观任意的,它取决于现实的需要和实践的可能。对一种经典理论的继承程度取决于它满足现实实践需要的程度,而对经典理论的超越程度则不仅取决于实践发展的需要程度,同时也取决于我们是否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的勇气。继承是必需的,但我们不要为继承而继承。超越也是必需的,但我们不要为超越而超越。我们只有根据现实,在继承和创新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才能使社会获得迅速而稳定的发展。现实的发展,既是我们继承的逻辑起点,也是我们超越的起点。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但黑格尔说过:人类社会一个最深刻的历史教训,就是人们常常不接受历史教训,总是不断地重复过去曾犯过的错误。在我们经历了几十年的经验教训之后,在看待经典著作和经典作家的问题上我们是否已经变得足够聪明,足够理智了呢?但愿在未来的实践中,我们将得到圆满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