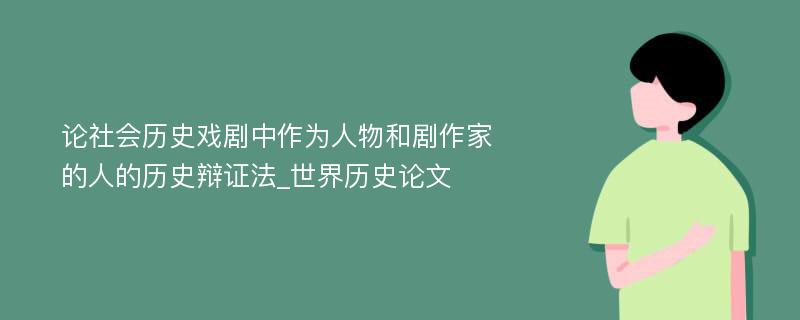
论作为社会历史剧中人物和剧作者的人的历史辩证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的人论文,剧作者论文,历史论文,辩证法论文,剧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提出后,社会发展中人的作用问题又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深入挖掘马克思关于人是社会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的历史辩证法思想,对于准确把握当代社会人的作用问题以及人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都是有所裨益的。
一
1847年,为反对蒲鲁东宣扬的“不是原理属于世纪,而是世纪属于原理,换句话说,不是历史创造原理,而是原理创造历史”的唯心主义历史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明确提出了人是社会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的历史辩证法思想。他指出,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但是要弄清为什么某一原理出现在某个世纪而不出现在其他世纪的问题,我们就必然要仔细研究那个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在每个世纪中,人们的需求、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也就是要“研究每个世纪中人们的现实的、世俗的历史,……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1] (PP.148—149)。
在1850年的《1848—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1852年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1871年的《法兰西内战》等著作中,马克思一再把社会历史比喻为历史剧,运用人是社会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的历史辩证法思想分析重大社会历史事件、发现重大的历史运动规律和阐发历史唯物主义,从而使他常常“在伟大历史事变还在我们眼前展开或者刚刚终结时,就能准确地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后果。”[2] (P1)
第一,在《1848—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把法国1848—1850年间发生的政治事变比喻为一幕有其“官方的舞台——布景、服装、台词、演员、配角、哑角、提词员、各种角色的位置、戏剧题材、冲突内容和整个格局”[3] (P415)的“大型政治历史剧”[3] (P403)、“没趣的谬误喜剧”[3] (P475),并以辛辣的笔调评论道:“建立中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是在1848年6月通过对无产阶级的空前搏斗载入历史出生登记簿的;而已建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则是在1849年6月通过它与小资产阶级演出的难以名状的滑稽剧载入这个出生登记簿的。1849年6月是对1848年6月实行报复的涅墨西斯。1849年6月,并不是工人被打败,而是站在工人与革命之间的小资产阶级遭到了失败。1849年6月,并不是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一出流血悲剧,而是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的一出包藏牢狱之灾的可悲的戏剧。”[3] (P433)
第二,对于1848—1852年间法国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变,与同时代的维克多·雨果“只是对政变的负责发动人作了一些尖刻的和机智的痛骂”和蒲鲁东虽然“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在他那里关于政变的历史构想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人公所作的历史的辩护”不同,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把社会历史比作历史剧,以证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3] (P580),并第一次完整地阐明了作为社会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的人的历史辩证法思想的含义。他指出:“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3] (P584)而在马克思看来,“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们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他们效劳,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3] (P585)
第三,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把资产阶级对巴黎公社的镇压喻为一出“滑稽剧”[2] (P71)、“历史的恶作剧”[2] (P112),并预言“不管路易·波拿巴同普鲁士的战争进程如何,第二帝国的丧钟已经在巴黎敲响了。它以一场模仿丑剧开始,仍将以一场模仿丑剧告终。但是不应该忘记,正是欧洲各国政府和统治阶级使路易·波拿巴能够把复辟帝国的笑剧表演了18年之久。”[2] (P17)
二
诚然,相对于宗教神学的神创历史论和哲学唯心主义的绝对精神或自我意识创造历史论来说,马克思坚持人创历史论。但是,马克思的人创历史论并非如前者那样从某种预定的前提或目的论出发来勾画历史,而是把历史看作是人通过人的劳动实践而生成的过程和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究其实质,马克思在历史观上实现的根本变革并不在于简单地把上帝创世论和绝对精神或自我意识创世论中的神、绝对精神或自我意识置换为人,而在于彻底消解了传统历史观根深蒂固的“创造论”意识,坚持“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4] (PP.118—119),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5] (P131),从而把社会理解为“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6] (P532)。这种在实践基础上的历史生成论,构成马克思关于人是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的历史辩证法思想的理论基础。
由于科学和实践的发展,创世论受到了自然发生说的致命打击和强有力的驳斥,这就使“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说来作为人的存在,已经变成实践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所以,关于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即包含着对自然界的和人的非实在性的承认的问题,在实践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5] (P131)也就是说,社会历史是由集剧中人物和剧作者于一身的人自己在社会历史舞台上出演的具有多重主题又充满波澜曲折的情节和节奏的历史活剧,它本身就生成了支配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决定性力量,根本不需要用超自然的神或某种精神力量来说明人类的历史:“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5] (P128),“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5] (P131)。在马克思看来,只要把社会历史看作是人通过人的劳动实践而历史地生成的过程,看作是作为剧中人物和剧作者的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那么,思想史上长期困扰人们的“历史之谜”,即“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等等的对立,就可以得到科学的说明:“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决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生活的任务”[5] (P127)。正由于破除了那个长期纠缠着人们的“创造论”意识,马克思就能够从现实的个人以及“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3] (P67)出发阐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他把生产力看作全部历史的基础,坚持“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的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6] (P532),认为“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3] (PP.67—68),进一步说,“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3] (P71)既然历史不过是各个世代的依此交替,那么,“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作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越益发展而越益成为人类的历史。”[6] (P532)
在笔者看来,马克思所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肯定了人对历史的创造作用,更在于强调历史的属人性以及人创造历史的条件性和过程性,其真实意义在于说明:第一,人类史与自然史的区别。自然史是无意识的、盲目的力量起作用的结果,是不能被人创造出来的,而人类史则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人的活动的结果,是由人创造出来的。人对自然的关系的问题,曾经“是一个产生了关于‘实体’和‘自我意识’的一切‘高深莫测的创造物’的问题。”[3] (P76)但是,在马克思看来,“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的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3] (P56),既然“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在每一个时代都随工业或快或慢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就像人与自然的‘斗争’促进其生产力在相应基础上的发展一样,那么,上述问题也就自行消失了。”[3] (PP.76—77)一方面,自然界是人们创造历史活动的前提:“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5] (P92)因此,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外部自然界,始终保持着对人的优先地位,是不能被人创造出来的;另一方面,“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3] (P66),人们“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3] (P76)正是“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构成了“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3] (P77),才形成了所谓“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3] (P76),即人类的自然史和自然的人类史。第二,人类史与动物史的区别。马克思指出:“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3] (P81)动物也有一部“历史”,但是动物仅仅利用自然界,通过改变自身的状态来适应自然界,因而动物只有适应史而没有创造史:“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5] (P96)相反,人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5] (P96)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不是由自然界现成地提供的,而是靠自己的创造性的劳动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信息、能量的交换而得到的,“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3] (P67)第三,人类史与神学史和精神史的区别,人类史是人类自己创造的,而不是由神或绝对观念、自我意识创造的。基督教神学历史观把人类历史所趋向的目标看作是神意早已安排好的,认为人类所致力的并不是自身独立的历史发展过程,而是按照神意的安排来行动,这种历史与其说是人的历史,倒不如说是神的意志的工具;哲学唯心主义或者如黑格尔那样把人类历史看作是绝对观念在自身演化过程中产生出来并借以实现自身的工具,或者如青年黑格尔派那样把人类历史理解为某种实体或自我意识,认为人们之间的关系、他们的举止行为、他们受到的束缚和限制,都是他们意识的产物,所谓人的解放问题就是把人从束缚他们的观念中解放出来。相反,马克思“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3] (P92),即在历史自身中寻找支配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决定性力量,从而宣告了那种用超人类力量来解释历史的神创史观和绝对观念或自我意识创造史观的终结。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3] (PP.74—75);历史没有自己特殊的目的,所谓“前期历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观念’等词表示的东西,终究不过是从后期历史中得出的抽象,不过是从前期历史对后期历史发生的积极影响中得出的抽象”[3] (P88);历史并没有离开人的活动而单独存在的权利,“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4] (PP.118—119)
三
正是坚持历史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生成的过程这一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立场,马克思把人看作是他们自己的社会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并在关于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中给予准确把握。
人类历史是世世代代的人们在连续不断的实践活动过程中创造的,人作为社会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的双重身分,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实现的。
第一,人是社会历史的剧中人物。历史是人们自己创造的,但是,历史决不是人的自由创造物,任何一个时代的人们都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处于历史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受到前人创造的既定历史条件的制约,从而规定着他们的生产方式和活动方式。如果说人作为社会历史的剧作者体现了人的活动的能动性的话,那么,人作为社会历史的剧中人物,则体现出人的活动要受到自己所设计的“舞台”和“剧本”的制约,体现出人的活动的受动性或受制约性,反映着“环境创造人”即客体的非对象化方面——以环境客体的客观性、对象性、社会历史性的存在限制人的活动范围和活动方式,并以环境客体的本质和各种形式的规定性以及本质之间的联系即客观规律性,制约着现实的人的活动的性质和人的本质力量的形成。
社会历史作为一代又一代人连续不断上演的没有终点的“系列剧”,既然就可能性来说,“我们还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2] (P426),那么,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就必然要受到已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在历史上积淀而成的精神成果等等因素的制约,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人的存在是有机生命所经历的前一个过程的结果。只是在这个过程的一定阶段上,人才成为人。但是一旦人已经存在,人,作为人类历史的经常前提,也是人类历史的经常的产物和结果,而人只有作为自己本身的产物和结果才成为前提。”[7] (PP.545—546)
不仅如此,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还受到自己创造的社会历史规律的制约。社会历史虽然是由人创造的,然而它一旦形成,就成为一种有其运动的客观规律的物质力量,规范着人们活动的性质、广度和深度。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规律构成人们实践活动的内在逻辑,人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必须遵循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也只有与社会规律发展方向一致的人的活动,才能成为创造历史的力量。马克思指出,正像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产力一样,人们也不能自由地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因为“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而“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6] (P532)
第二,人是社会历史的剧作者。人作为社会历史的剧作者,表现出人创造历史的主体能动性和自觉性,是对“人创造环境”即主体对象化的形象表达。人对环境的认识和改造即作为主体的人的本质力量在环境中的对象化,就是将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自然力和社会力、创造性和能动性赋予作为历史客体的环境,使环境具有人的意义,成为人的环境,这是一个充满了主动性、创造性的能动性过程,充分展示了人的生命活动的特点,它超越了一切动物的活动方式,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对环境的强大的物质塑造力和精神塑造力的生动体现。马克思指出:“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3] (P88)
人之所以要作为创造社会历史的剧作者,就在于人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物,既是受动的又是能动的。一般说来,“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5] (P167);但是,从根本上说来,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更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5] (P167),正“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5] (P169)因此,与其他自然存在物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人以自己的本质力量即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与自然界进行物质的、能量的和信息的交换,创造自己的人的生活,从而创造历史。
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作为创造社会历史的剧作者,就在于人的独特的类本质——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人作为一种自然存在物,固然是受动的,然而人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物,又是一种超越性的、理想性的、能动的类存在物。马克思指出:“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也就是说,是为自身而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他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5] (P169);又说:“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5] (P96)自然界在其自在的形式上,“都不是直接地同人的存在相适应的”[5] (P169),这就决定了人必须在实践活动中把自然变成人的自然,成为自己实践的对象,而人的类本质力量的发挥即实践的展开过程,也就是社会历史的形成过程。正是这种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即实践活动,为人的存在和人创造社会历史奠定了现实的基础,社会历史就诞生和存在于人的实践活动中;也正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人根据自己的情感、智慧、需要、愿望和理想创造着社会和历史,同时将自己的情感、智慧、才能、想象力和创造力熔铸于其中,才使社会历史成为一部既有深厚凝重的宏大主题又充满了激情和活力等情节的历史正剧。
从共时态上说,实践创造着社会生活。马克思指出:“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3] (P80)人在实践活动中把自在自然转化为人化自然的同时,也改造着人自身及其社会关系,从而创造着人的社会生活本身:“正象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5] (P121)这是因为,人们在实践过程中,不仅要发生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而且要发生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前提条件:“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相互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3] (P344)从历时态上说,实践创造着历史。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全部历史的基础,社会历史是生产实践活动在时间中的延续和展开。因而,“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5] (P132)。
第三,人是社会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的统一。社会历史既是人的活动的结果,又是人的活动的客观前提条件,这就决定了人扮演着作为社会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的双重角色。人是社会历史的剧中人物,体现了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受动性;人是社会历史的剧作者,体现了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受动性是能动性的前提和客观根据,受动性的状况决定着能动性可能发挥的程度;能动性的发挥又会改变受动性的状况,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辩证统一。正因为在社会历史舞台上扮演着剧中人物和剧作者的双重角色,人才能尽情地展示自己创造社会历史的物质本质力量和精神本质力量,发挥能动性,克服受动性,推动社会历史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并实现其自身的自由全面发展。
第四,实践和交往是作为社会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的人的活动的舞台或环境。实践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对象性关系,交往是人与人之间的主体间性关系,实践和交往构成人们活动于其中的舞台或环境。在这个舞台或环境中,实践形式、交往形式与人的活动交融互动共同发展。马克思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3] (P55)。
人们基于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而形成一定的生产力,由此形成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各个人之间的交往形式;这些各个人相互交往的形式,并不是什么外在于他们的条件,而是与他们的自主活动相适应的条件,或者说这些条件就是由他们的自主活动产生出来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些起初是各个人自主活动的条件就成为不断发展着的个人的旧的桎梏,这样,“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从而“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一个有联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3] (P124),即人类历史。因此,全部人类历史,既是各种交往形式相继交替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由每一个新的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3] (P124)
总之,基于对实践和交往基础上的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生成人类历史的基本立场,马克思把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归结为人的实践和交往活动本身的发展过程。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3] (P74)只是由于现代生产力日益迅速的发展,才使“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3] (P276),而“各个互相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3] (P88)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相适应,个人的活动也由过去那种依附于狭隘的地域性共同体的活动而日益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使得个人的存在成为与世界历史相一致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正如个人的解放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是可能的一样,作为“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3] (P86)共产主义,也“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3] (P87)。这样,人的解放和共产主义就不再是一种道义主义的价值追求,“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3] (P87)也正是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个人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成为社会的新基础。”[3] (P91)
我们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尽管社会主义为作为社会历史剧中人物和剧作者的人创造自己的历史提供了以往所没有达到的主客观条件,然而,鉴于过去因片面强调人的活动的能动性忽视受动性而遭受挫折的教训,因此,在倡导“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今天,准确把握马克思关于人作为社会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的历史辩证法思想,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标签:世界历史论文; 黑格尔辩证法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生命本质论文; 唯物辩证法论文; 能动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