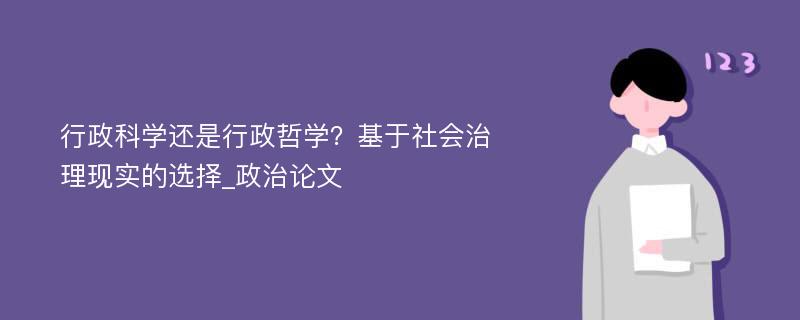
行政科学还是行政哲学?——基于社会治理现实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行政论文,哲学论文,现实论文,科学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 【文件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26[2013]06-0100-06
在行政学的发展史上,行政科学与行政哲学的争论不绝于耳,两种研究取向的支持者都试图证明其方法在研究行政现象上的优越性,进而获得主导行政学发展方向的话语权。但其实,行政科学与行政哲学的存在理由并不是由两种研究取向本身的优劣所决定,而是由社会治理的实际需求所决定的。行政科学与行政哲学所代表的是社会治理中不同层面的问题,因而,二者在行政学中的地位也会随着社会治理状况的变化而改变。具体来说,行政科学有助于常态社会治理问题的解决,因而,在常态社会的治理过程中,它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行政哲学则有助于关于社会治理变革的思考,因而,在变革社会中,或是在我们希望进行社会治理变革时,行政哲学能够贡献更为积极的力量。当前,人类进入了一个变革社会,这种变革社会的出现为行政哲学的繁荣创造了契机。
一、常态社会中的治理科学
现代政治学是以一种革命理论的面目登堂入室的,也正是因其革命性的内容,才使它被冠以了区别于“传统”政治学的“现代”一词。从“传统”到“现代”,这本身就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的理论成果之一就是,造就了以社会契约论为代表的革命性的现代政治理论。其实,不只是现代,在人类历史上,每当政治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革时,都会孕育出一种伟大的政治理论,反过来看,每当一种伟大的政治理论得以诞生,也就意味着人类的政治社会发生了或即将发生重大的变革。对于具有尚古幽情的人们来说,变革往往意味着“伊甸园”的失落,因而,新的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呱呱坠地也就被听成了“黄金时代”的丧钟。“在这一点上,政治哲学的历史是不能令人宽慰的。作为希腊政治制度的杰作,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写于这一制度寿终正寝之时;波利比阿赞美罗马共和国的政治体制体现了终极的与永恒的政治科学的所有要素,但在他写作他的代表作时,距离恺撒的诞生已不到半个世纪……”①有鉴于此,莱斯利·斯蒂芬(Leslie Stephen)得出结论:“幸福的民族是没有政治哲学的,因为这样一种哲学通常不是一场新近发生的革命的结果,便是一场即将发生的革命的征兆。在相对平静的18世纪,英国人与其说是在严肃地讨论政治理论,不如说是把政治理论当作一种消遣。对政治学的兴趣主要是个人性的。对一般原则的讨论采用了华丽的辞藻,却并没有构成严肃讨论的基础。在大多数填满我们图书馆的小册子与演说词中,连政治哲学的影子也很难见着。”②
当然,就英国来说,18世纪之后仍然出现过伟大的政治哲学家,比如密尔。但就密尔的代表作而言,尽管《论自由》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仍然可以被归入政治哲学的范畴,他的另一部代表作《代议制政府》则无论如何都不能被视为哲学著作了,相反,它应当被我们看成现代政治科学的奠基性作品,它第一次对现代国家是(is)如何运行的而不是应当(should)如何运行的问题作出了系统的回答。也就是说,在密尔这里,政治哲学(political philosophy)与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开始发生了分化,尽管现代社会治理仍有许多哲学上的问题需要理清,但对治理制度与治理行为的科学安排则成了学者们更加紧迫的一项使命。
对治理制度与治理行为的科学安排不仅是政治科学,也是法学的研究对象。事实上,历数18世纪以来对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建构作出了重要贡献的英国学者,从边沁到布莱克斯通,从白芝浩到戴雪,法哲学家或宪法学家占据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相较之下,政治哲学家们的贡献则黯然失色。这种情况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因为,政治哲学是一种关于应当(should)与为什么(why)的追问,而在这两种追问之下,任何既有的治理安排都是不足的,所以,政治哲学的思考必然要求变革,要求颠覆既有的秩序而重建一种更好的秩序。事实上,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什么是最好的政治秩序。③从这一问题出发,显然,所有现存的政治秩序都不是最好的,都需要进行变革,所以,政治哲学内在地是一种革命性的理论,当政治社会重建完毕,进入常态的治理过程之后,它是不会有什么市场的。在常态社会中,政治哲学的衰落不可避免。
那么,常态社会需要什么?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常态社会最需要的是秩序,常态社会之于变革社会的最大区别也就在于它拥有一种相对确定的秩序。在某种意义上,常态社会的治理过程就是一个维护与更新秩序的过程,因此,好的治理安排应当既能包容常态社会自身的波动,又不使这种波动给社会造成大的混乱,易言之,好的治理安排与治理行为应当保证社会处于一种有序的状态之中。这是常态社会的基本治理需求,而符合这种治理需求的治理科学也应当能够对常态社会秩序的维护与更新作出贡献。政治科学与法学就是这样的治理科学。当然,政治科学与法学并不是唯一符合常态社会治理要求的治理科学,事实上,在20世纪,行政学在常态社会的治理过程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前文中,我们将密尔的《代议制政府》视为现代政治科学的奠基性作品,有了这样一部著作,人类可以骄傲地宣称,我们已经获得了关于现代社会治理的一种相对科学的认识。但在19世纪的英国,却并不存在一种独立的政治科学研究,事实上,密尔本人就既是一位哲学家和政治学家,同时也是一位经济学家,在他的身上充分体现了当时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以及政治学与经济学之间难以分割的关系。英国学者尽管在政治科学研究上走在了前列,但由于缺乏充分的学科分化,他们却不能主张对现代政治科学的发明权,今天,现代政治科学的诞生通常是以1903年美国政治科学协会(APSA)的成立为标志的。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美国在许多方面都落后于英国甚至是欧洲大陆,但在现代城市与现代企业的发展上,当时的美国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因而,美国社会的专业分工得到了非常充分的发展,这种分工反馈到学术研究中,就会促进学科意识的生成,推动不同学科的分化。美国的各主要学科协会都是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的:1865年,美国社会科学协会(ASSA)成立;1884年,美国历史学协会(AHA)成立;1885年,美国经济学协会(AEA)成立;1892年与1900年,美国心理学协会与美国哲学协会(英文简称均为APA)分别成立;1903年,美国政治科学协会成立,等等。从这些专业协会的发展来看,19世纪后期,美国社会科学的学科分化过程非常清晰,区别于传统政治哲学的政治科学及行政学就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
不过,政治科学的独立并不是直接以政治哲学为参照对象的,相反,在学科分化的背景下,政治科学的独立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是以整个社会科学,在较为狭隘的意义上则是以历史学以及政治经济学为参照对象的,具体来说,美国政治科学协会是从美国历史学协会和美国经济学协会中分化出来的。在美国政治科学协会成立之初,这三个协会的年会都是联合召开的。④此外,政治科学显然与法学也有着紧密的联系,但美国的法学专业协会是由律师组成的——美国律师协会(ABA)成立于1878年,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特征,与这些科学团体之间反而表现出了较弱的学源联系。所以,在美国政治科学协会建立的时候,它的建立者们力图排斥的是美国历史学协会与美国经济学协会这两个科学团体以及它们的研究对象历史学和(政治)经济学,却并不排斥法学研究,相反,他们是把关于公法的研究纳入到了政治科学的学科版图之内的。
在作为美国政治科学协会首任主席的就职演说中,古德诺(Frank J.Goodnow)对政治科学下了这样的定义:“政治科学是关于国家组织的科学。”⑤在他看来,国家的活动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国家意志的表达,国家意志的内容,以及国家意志的执行。其中,作为国家意志之表达的立法是政治理论与宪法学的传统研究范围,所以,政治科学应当包含政治理论与宪法学研究。同时,由于政党的出现,除了立法之外,政党对于选举过程的参与和控制也成了表达国家意志的基本活动,因而,政党政治与选举问题也属于政治科学的研究范围。第二,国家意志的内容通常就是法律,就政治科学而言,它所研究的对象则是公法。第三,国家意志的执行就是与“政治”相对的“行政”,在当时,这主要包括行政法与各级政府的行政方法等问题,因而,政治科学也应当包括对行政法以及政府机构、地方政府、市政行政等问题的研究,这部分内容实际上就是后来的行政学的内容。三者之中,古德诺尤其强调公法研究的重要性,他认为,“也许存在一个政治哲学家的群体,他们满足于在思辨的苍穹中翱翔,但是,对于一名研究过往或当前政府制度的政治科学家来说,他必须了解支配着这一制度的法律。如果这没有冒犯某些醉心于关于政治事务的哲学思辨的人的危险的话,我将倾向于认为,一个人对公法的了解越深,他距离政治科学家的位置也就越近,他从纯粹政治哲学家的立场上回退得也就越远。”⑥也就是说,政治科学家之所以可以被称为科学家,是因为他对于公法的运行机制与实施细节有着精细的了解,进而,才可能对以这种法律为依据和工具的现代政府及其运行有着科学的认识。
古德诺的这篇演说可以被视为现代政治科学与传统政治哲学决裂的宣言,尽管作为学科名称,政治科学仍然将政治哲学纳入了自己的名下,但在研究取向上,以想象和思辨为主要内容的哲学方法已经受到了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对科学与“价值中立”的事实的崇拜。正是出于对科学与事实的崇拜,古德诺才会要求把对公法与行政体制的细枝末节的研究作为政治科学的核心内容。也正是出于对科学与事实的崇拜,行政学才得以在连政治科学的独立地位都没有得到普遍承认的条件下脱颖而出,在20世纪初期美国的“进步主义运动”中成为了所有治理科学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支。
今天看来,无论法学院在整个20世纪的强势,还是行政学在提高现代政府治理水平上的成功,都证明了古德诺对政治科学要素的界定中所蕴含的远见,只有对公法与行政过程都有着细致的了解,政治科学才能成为一门有用的治理科学。然而,另一方面,无论是对于公法的认识还是对于行政过程的探索,政治科学都远远比不上法学以及后来逐渐从政治科学中独立了出来的行政学,究其原因,在于法律和行政都是非常专门的活动领域,都有一个极其复杂的规则体系,因而,需要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了解和掌握,政治科学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所做出的研究则是很难切合这两个领域的实际需要的。所以,尽管政治科学宣称要把法学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但在整个20世纪,法学都远比政治科学繁荣;尽管直到今天行政学仍然被许多人视为政治科学的一个分支,但在20世纪,行政学的发展则远比它的母学科迅速而充满了活力。
如前所述,常态社会最需要的因素是秩序,而秩序又是由规则所构成的,因此,常态社会需要能够对其秩序的维护与更新提供支持的治理科学,也就是需要能够对构成了其秩序的基本规则的维护与更新提供支持的治理科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法学与行政学成了20世纪最重要的两门治理科学,它们分别承担着为现代社会治理中的宏观法律规则与微观组织规则提供支持的任务。当然,政治体制与政治过程也是由规则体系构成的,但这里的许多规则都是由法律所规定的,在这些法律规则的问题上,政治科学并没有太多发言权。另一方面,在政党政治与选举过程中又存在许多法学和行政学都无法解释的“游戏规则”,这就成了政治科学的保留地,在这个问题上,政治科学也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使现代政治中最重要的选举活动获得了数量化的特征。但在现代社会,纯粹政治活动的领域受到了法律规则的严格限制,并且具有周期性的特征,因而,它在常态社会治理中的实际影响是相对较小的,以政治活动为对象的政治科学的研究范围远远比不上以政府活动为对象的行政学。不过,随着公共政策日益成为一项重要的政府工具,政治科学也开始凭借政策研究而逐渐渗入了宏观的规则体系之中,并与法学和行政学都产生了新的交集。
总之,政治哲学是一种关于“什么是最好的政治秩序”的追问,这种追问总是会逻辑性地导向变革既有政治秩序的结论,所以,政治哲学内在地是一种革命理论,不能满足常态社会的治理需求。常态社会的治理活动是一种维护与更新既有秩序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一种维护与更新既有法律规则与组织规则的活动,因此,它需要能够为其法律规则与组织规则的维护与更新提供支持的治理科学,法学与行政学就是这样的治理科学,它们成为了在20世纪的常态社会治理中发挥了最大作用的治理科学。同时,政治活动也是一个规则的领域,政治科学则在这一规则领域中扮演起了重要的角色,因而,法学、行政学与政治科学就成了常态社会治理中最重要的治理科学。
二、常态社会中的行政科学与行政哲学
政治哲学不能满足常态社会的治理需求,那么,常态社会是否就完全不需要政治哲学了?显然,从政治哲学在20世纪虽然出现了衰落却并未消亡的情况来看,不是的,常态社会也需要政治哲学。这意味着,政治哲学并不仅仅是一种关于“什么是最好的政治秩序”的追问,因而,在一个政治社会无需对其秩序进行变革的情况下,政治哲学也能有它的用武之地。作为美国政治科学协会的创立者之一,威洛比(Westel Woodbury Willoughby)清楚地认识到了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在常态社会治理中的分工关系,他认为,“至少在今天,首要的目标是对我们政治生活中的事实与势力的科学分析。同时,对乌托邦的建构也并不必然是一项没有价值的或者危险的工作。至少在理想的与具有现实可能性的事物没被混淆的情况下,如果构建得当,这样一种政治范型将提供一个激励人们奋斗的理想,或这样一个标准,通过它,可以衡量当前事态的成功与否及其道德品质。”⑦也就是说,在宽泛的意义上,政治哲学实际上体现了人们对于更好的政治生活的一种追求,在常态社会治理中,这种追求虽然不能解决具体的问题,却可以为人类的政治实践提供一种前进的方向和激励。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哲学代表了人们对于政治的一种理想观念,这种观念在历史上与现实中都经常被它的反对者斥为乌托邦,但实际上,它与乌托邦是有着显著区别的。“理想政治包括形成一种真正的国家观念,思考它的完善(当然,在人的思想允许的限度内),并最终向社会提供一种模型,正如道德向个体提供模范一样。没有任何国家能够达到那种完善,达到比任何英雄或圣徒曾经达到或可能达到的道德完善更加完美的境界。但如果我们没有禁止道德向人类提供理想,我们又怎能禁止政治向人民和政府提供理想呢?”⑧所以,即使是在科学的时代,政治哲学也有着充足的存在理由。
的确如此。尽管如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所说,“今天,如果它还没有完全消失的话,政治哲学也处于一种衰退或也许是败落的状态之中。”⑨但纵观整个20世纪,政治哲学从来没有淡出过学者们的视野,即使是在实证主义甚嚣尘上的50年代,也有斯特劳斯这样的斗士站出来为它摇旗呐喊,甚至所谓的“斯特劳斯派”还一度占据了美国政界的主流舞台。这些充分印证了政治哲学存在的合理性,当然,无论是在实际治理问题的解决,还是在现代政治知识的创造上,政治哲学所作出的贡献都已无法与政治科学相比了。政治学的发展走过了一道从政治哲学到政治科学的演进轨迹。行政学的发展则截然相反。如前所述,行政学是作为政治科学的一部分而产生的,因而,它从发生上就属于一种科学,而不是哲学。事实上,在“行政之研究”一文中,威尔逊(Woodrow Wilson)所提出的是建立一门行政科学(science of administration),⑩而不是行政哲学的目标;在进步主义运动中,市政研究者们也是根据科学的精神而对公共行政这门学科加以建构的;当作为科学管理运动与市政研究运动理论结晶的《行政科学论文集》(Papers on the Science of Administration)于1937年出版时,行政科学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了。
当然,如果说早期行政学研究中完全没有哲学思考,也是不符合实际的,事实上,只要学者们对公共行政“应当”怎么做和“为什么”应当这样做的问题做出了思考,就探讨了行政哲学的问题。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样的哲学思考并没有得到学者们的自觉运用,甚至,由于科学话语的强势,哲学思考不仅会被认为是无用的,而且可能被认为是危险的。这是因为,行政科学的目标在于不断提高行政效率,在这一目标下,行政科学的任务就是不断创新可以助益于行政效率提高的方法和工具,行政科学家的任务则是埋头做事,而不要把精力浪费在关于“为什么要这么做”的毫无效率的思考上。相反,行政哲学思考则必然会提出为什么要这么做的问题,必然会追问公共行政以效率为目标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而这样的追问显然不仅是没有效率的,而且对于行政科学来说也是危险的,所以,在那个以“科学管理”为名的时代,行政哲学研究必然不受欢迎。公共行政学的早期历史是由行政科学一力书写的。
行政哲学的觉醒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其标志是沃尔多(Dwight Waldo)《行政国家》一书的出版。《行政国家》的副标题是“对美国公共行政学政治理论的研究”,清楚地表明了它与主流行政科学的区别。不过,作为一部文献研究,《行政国家》虽然阐明了美国的公共行政学也有着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上的渊源的观点,也对以效率为核心的行政科学“正统学说”做出了批判,却并未对行政哲学本身提出什么独到的见解,没有告诉读者行政学本身需要思考什么样的哲学问题。但也许正是通过对主流行政科学的政治哲学检视,使沃尔多意识到了行政哲学研究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从而为他与西蒙(Herbert A.Simon)之间那场影响深远的争论埋下了伏笔,为行政哲学与行政科学的分化创造了前提。
1952年,在刊载于《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的“民主行政理论的发展”一文中,沃尔多对西蒙做出了一种基于“误引”但却影响深远的批评,认为西蒙在《行政行为》一书中对决策行为作出了一种错误的二分,即将行政决策区分为了事实决策与价值决策,而实际上,西蒙只是在决策过程中区分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从这样一种基于误引的误解出发,沃尔多对西蒙及他所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发起了攻击,进而对行政科学的研究传统提出了挑战,认为行政学研究在科学化的道路上走得太远,甚至陷入了歧途,因此,未来的公共行政研究应该更多地接受来自政治理论的指导。对于这一直接针对自己的无中生有的指控,西蒙作出了强力的还击,并将战火烧向了沃尔多所提倡的政治理论,批评所谓政治理论家或政治哲学家连基本的逻辑课程都没能通过,因而根本就没有资格谈论行政科学(11)。由此,行政科学与政治理论的矛盾被放到了台面上,随着更多学者加入到这场争论之中,公共行政研究也逐渐走向了分化。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场争论中,由于实际上缺乏一种独立的行政哲学研究,政治哲学被沃尔多与西蒙拿来当成了行政科学的对立物。在当时美国公共行政学会(ASPA)已经从美国政治科学协会中独立了出来因而行政学也可以被视为一个独立学科的情况下,仍然把政治哲学用作反击行政科学的武器显然是不合适的,对于行政学者来说,甚至是令人难堪的,它反映了公共行政研究中哲学思考的极度贫乏。而既然行政哲学研究如此贫乏,它又如何能够阻止行政学继续沿着行政科学的道路而大步前进呢?所以,尽管在50年代的争论中西蒙受到了多位学者的攻击,行政科学的主流地位却并未受到动摇,相反,由于实证主义方法的引入,公共行政研究在科学化的道路上反而走得比以往更加理直气壮。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在这场争论中暴露出了行政哲学研究的不足,使一些学者意识到了加强行政哲学研究的必要性。但在缺乏足够学术积累的情况下,当时的学者还是只能通过对政治哲学甚至哲学的借鉴与模仿来探索如何对行政现象作出哲学思考。这样的探索到了60年代后期逐渐结出了果实。
与18世纪那个革命年代相比,尽管西方社会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许多革命性的躁动,却没有发生可以称之为革命的事件,但就20世纪而言,60年代则的确称得上一个革命的年代。革命是哲学的天堂,所以,正是在60年代,政治哲学经过长期的低迷而走向了复兴,行政哲学也终于在行政科学的压制下发出了自己的呼喊。当美国的行政哲学研究者由于缺乏学术积累而不知从何入手的时候,1966年,一位精通现象学的巴西学者拉莫斯(Alberto Guerreiro Ramos)作为难民逃入美国,并在南加州大学公共行政学院获得了任教的机会,讲授现象学课程。按照当时也在南加州任教的哈蒙(Michael Harmon)的说法,拉莫斯很快成为了当时就读于南加州大学的包括全钟燮(Jong S.Jun)、柯克哈特(Larry Kirkhart)、维尔米尔(Richard VrMeer)、比勒(Robert Biller)等对20世纪后期美国公共行政学有着深远影响的学者在内的公共行政学博士生和包括哈蒙在内的年轻教员们的精神教父(intellectual godfather)。(12)1968年,在拉莫斯到来之前已经在南加州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进入锡拉丘兹大学任教的弗雷德里克森(H.George Frederickson)向柯克哈特、哈蒙和比勒发出了邀请,从而将南加州的现象学运动带到了明诺布鲁克会议,进而扩散到了整个公共行政学界。在通过“新公共行政运动”而宣告了行政哲学研究的正式出场的同时,也给初生的行政哲学研究烙上了现象学的深刻印记。
行政哲学研究的获取承认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1969年-1970年间,明诺布鲁克会议文集中半数左右的学者开始参加美国公共行政学会的会议,但他们的“理论”取向一直不受重视,学会拒绝给理论探讨增设专门的会场。这种状况持续了将近10年。在1978的凤凰城年会后,理论研究者们终于对美国公共行政学会失去了耐心,在亚当斯(Guy Adams)的召集和组织下,公共行政理论网络(PAT-Net)成立,并开始出版会员刊物《对话》(Dialogue)。1992年,《对话》改版为公开发行的《行政理论与实践》(Administrative Theory & Praxis)杂志,成为行政哲学研究者发表意见与开展交流的主要阵地。(13)至此,在有了独立的学术团体和学术刊物之后,行政哲学已经可以被视为美国公共行政学中的一个独立的分支领域了。除此之外,行政哲学研究在内容上也取得了许多成果。1984年,由弗吉利亚理工大学的几位学者共同执笔的“黑堡宣言”(Blacksburg Manifesto)在《对话》上发表,掀起了自“新公共行政运动”以来最激烈的理论研究热潮,由“黑堡宣言”所激发的关于公共行政合法性问题的讨论更是延续到了21世纪,成为行政哲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理论主题。90年代中期,《公共行政的语言》、《后现代公共行政》与《公共行政的合法性》相继出版,在行政学界掀起了一场引人注目的“话语运动”(Discourse Movement),用后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对行政哲学研究进行了更新换代,大大拓展了行政哲学研究的视野。然而,尽管取得了这些成就,行政哲学在美国以及整个世界的行政学研究中都仍是极其边缘的,在今天这个因为“影响因子”的发明而让学术研究的主流与支流变得一目了然的科学世界中,《行政理论与实践》及其所刊载论文影响因子的低下足以让行政科学的研究者笑掉大牙,世界上其它地方的行政哲学研究成果就更不用说了。直到今天,行政哲学仍然是行政学研究中的“二等公民”。
行政哲学的边缘地位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任何哲学在常态社会中都是没有市场的。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也曾有过一个哲学的黄金时代,但随着90年代以来整个社会的趋稳,哲学在当今中国的学术世界与现实世界中也早已失去了话语权。事实上,我们应该感到意外的恰是,在公共行政这样一个科学精神如此根深蒂固的领域中行政哲学仍然取得了如此丰富的理论成果的事实,而这一事实又反过来证明了,即使在一个常态社会中,哲学也是一种必需品,尽管常态社会治理中的绝大多数问题都可以通过也只能通过科学而得到解决,但也有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只有在哲学思考中才能得到回答的。常态社会也需要追问“什么是最好的治理方式”,也需要对看似良好的社会治理现实保持一种警惕和批判的精神,这就是行政哲学的存在理由,就是行政哲学在常态社会中的任务与使命。只要人类仍然具有理想主义的情怀,仍然对于明天抱有一种更好的期待,那么哲学就仍将是一种有生命力的思考方式,行政哲学也将继续对人类社会治理的改善作出自己的贡献。
三、变革社会中的行政哲学
现代政治哲学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产生的,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宣言。行政学则是资本主义社会从革命社会进入常态社会之后的产物,是常态社会中的一种治理科学。作为行政学的一个分支领域,行政哲学是在常态社会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它并没有近代早期政治哲学的那种颠覆所有现存秩序的革命抱负。但作为一种哲学,它仍然是对现实中西方社会所出现的革命性躁动的一种回应,即对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所发生的如“五月风暴”、“黑人革命”等革命性事件的一种回应,因而,尽管缺乏革命的抱负,初生的行政哲学则对变革充满了兴趣。比如,弗雷德里克森就认为,“变革是新公共行政学的基础。”(14)比勒也争论说,正是对变革的关注将新公共行政运动与以往的行政学研究区别了开来:“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新公共行政’的措辞可能真的意味着什么。因为这样的观念意味着新公共行政学将成为对快速变革中的组织的研究。”(15)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拥有对于变革的浓厚兴趣,新公共行政运动才明确反对当时的政策科学研究,因为,推行这种研究的“公共政策学院不涉及、从未涉及也绝不是被用来处理大规模的社会变革的”。(16)事实上,所有以科学为名的研究都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研究社会变革的问题,因为变革充满了不确定性,而科学则必须以研究对象的确定性为前提。所以,尽管经常都会有以科学家自称的学者对未来进行预测,但这种预测却总是达不到科学应有的精确程度,甚至往往谬以千里。当然,哲学也无法预测未来,无法预测变革的结果,但正是因为它明确地认识到了未来的不可预测性,它才能够对变革作出一种更加科学的研究。具体来说,哲学并不打算预测未来,而是试图对未来加以建构,我们虽然无法准确预知变革必然会走向什么结果,却可以通过对变革的自觉建构而引导其前进的方向,从而使变革能够给人类的社会治理与社会生活带来更好的结果。这正是行政哲学力图承担的使命。
在整体上,20世纪的西方社会属于一种常态社会,但从60年代开始,在这种常态社会中,变革也已成为一种持久性的主题,或者说,变革成为了社会的常态。8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的行政改革浪潮的兴起,不仅西方社会,而且在广大的非西方社会中,变革也已经成为或正在成为一种常态。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全球化运动的飞速发展,所有社会都被卷入了一场共同的急剧变革的运动之中。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变革社会。变革社会不同于常态社会,也不同于革命社会。在某种意义上,变革社会具有本尼斯与斯拉特所说的“临时社会”的特征,在这个社会中,所有的一切都是临时性的与流动性的,因而呈现出了高度的不确定性,但另一方面,这种不确定性并不意味着所有现存的秩序都已失效,因而需要加速它们的垮台,相反,这样做只会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使我们再度陷入一个革命社会。事实上,20世纪人类政治文明的最大进步就是对行政改革的自觉运用,使社会治理矛盾可以通过主动的行政改革得到化解,而不用积累到不得不通过政治革命的方式而爆发出来。这是一种比近代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更加理性的社会变革方式,对于人类整体的福祉而言,也是一种更好的社会变革方式。因此,在我们所生活的变革社会中,行政改革应当成为社会治理体系重建的基本途径,行政哲学则应当主动承担起研究行政改革与社会变革的使命,通过对以行政改革为基本途径的社会变革的积极建构而引领人类在变革社会中朝向更好的目标正确前行,避免陷入革命社会的泥潭。
行政哲学是行政学中理论性的方面,但它不是与实践隔离的,更不应脱离实践,高高在上。纵观“新公共行政运动”以来的西方行政哲学,现象学派在“praxis”的观念下一直宣称致力于弥合理论与实践的分离,但他们在著述中则时时表现出一种哲学家式的清高,让实践者与其他学者都感到难以亲近;“黑堡宣言”发表以来的许多学者则纠缠于公共行政学自身的学科身份问题,而失去了应有的现实关怀;弗雷德里克森、登哈特等人从公民参与出发做出了一些在实践中产生了较大反响的成果,但这些成果又反映出他们缺乏理论建构的雄心,对行政哲学作为一个独立知识领域的贡献不足。一种好的行政哲学既需要从现实出发,又需要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从而引导现实的发展。所以,今天的行政哲学研究在思考行政改革的问题时,需要拥有一种前瞻性的视野,在引领社会变革的意识下把握行政改革的方向。当然,研究行政改革并不是行政哲学的专利,事实上,绝大多数微观层面的行政改革的研究任务都是由行政科学予以承担的,在这些问题上,行政科学也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比行政哲学更能解决实际的问题。但在那些更加宏观、更具根本性意义的改革问题上,行政科学则是无能为力的,因为这样的改革所要解决的是“什么是更好的治理方式”的问题,而这样的问题是科学所无法回答的。所以,在变革社会中,行政哲学应当比行政科学承担起更加紧迫和更加重大的研究课题,当它这样做了的时候,就应当得到应有的尊重,而不能因为它不符合所谓的“科学规范”而受到行政科学的排挤。
就中国的情况来说,尽管五四运动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但在持久的革命过程中,科学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也未获得充分的发展,哲学则因其之于革命运动的适用性而迎来了极大的繁荣。所以,在科学与哲学的问题上,中国学者在整体上存在“偏科”的情况,哲学思辨游刃有余,科学思考则显得力不从心。由此,在得到恢复与重建之后,中国的行政学研究也是首先从行政哲学入手的,关注的是行政体系及其过程的价值的和规范的方面,至于行政体系及其过程的事实的和工具的方面则由于行政学者科学训练的不足而没有在学术研究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在一段时期内,由于行政学者所谈论的都是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合法性、公共性等笼统的规范性价值,行政学甚至被学者们戏称为“性科学”,形象地说明了中国行政学研究哲学先行的状况。只是在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学成归国人员的增多,行政科学才在这些受过严格科学训练的学者们的努力下建立了起来,并在“与国际接轨”的学术潮流和“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教育方针的共同作用下呈现出了取代行政哲学研究的趋势。
中国行政学研究的哲学先行是由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决定的,是20世纪中国革命史的历史遗产。这场革命将哲学思维深深地刻入了中国学者的头脑之中,所以,当中国学者开始思考行政问题的时候,也自然而然地把哲学作为了他们的基本思维工具。不过,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开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初步建立,中国社会开始从革命社会进入了常态社会,住房、医疗、教育等各种各样需要由科学来加以解决的具体问题急剧增多,在这种情况下,行政科学的成长与行政哲学的相对衰落就成了势所必然之事。行政哲学与行政科学的此消彼长是我们在进入常态社会之后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要建立起适宜于常态社会的治理方式与治理机制,就必须在科学的方向上付出更多努力,让政府的每一次行为都受到科学精神的指引。然而,我们并不完全处在一种常态社会之中。如前所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整个世界都被卷入了一场变革的洪流,变革已经成了这个世界的常态,自然也成了中国社会的常态。其实,今天的中国社会兼具常态社会与变革社会的双重特征,因此,它对科学与哲学也都有着强烈的需求,既需要通过科学来解决常态社会治理中的具体问题,也需要通过哲学来把握社会变革的脉动。所以,在今天中国的行政学研究中,行政科学与行政哲学都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都应当承担起中国社会治理体系的再造与完善的历史责任。
从常态社会与变革社会的分类来看,中国政府当前面临着两大任务:一是社会治理体系的科学化,二是社会治理体系的再造。就中国从革命社会进入常态社会的过程来看,这两大任务其实是一个问题,因为从革命社会进入常态社会也需要社会治理体系的再造,而这种再造的途径就是社会治理体系的科学化。但从中国也处于一个变革社会中的现实来看,这两大任务又是不一样的,仅仅通过社会治理的科学化无法满足变革社会的治理需要,我们还需要进行符合变革社会需要的社会治理体系再造。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了这一问题,从“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提法来看,“科学发展”是我们在常态社会中应当采取的发展路径,“和谐社会”则是我们在变革社会中的前进目标。在一个常态社会中,“科学发展”可以带来人民财富的极大增长与人民生活质量的全面提高;在一个变革社会中,只有以“和谐社会”为目标,我们才不会重新陷入革命社会,才能够享受“科学发展”所带来的各项成果。可见,中国的社会再造是以“和谐社会”为目标的,这是哲学尤其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承担的研究使命。中国的社会治理体系再造则应当以“服务型政府”为目标,只有建立起了“服务型政府”,才能创造出真正的“和谐社会”。当代中国行政哲学的使命就是承担起“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建构工作。
“服务型政府”的提出是中国学者的一项原创性贡献,是中国行政哲学研究的原创性成果。尽管“服务行政”的概念最早可能是在20世纪初的德国行政法文献中出现的,(17)美国行政学家卡罗尔(James D.Carroll)也曾在1975年提出过后工业行政(post-industrial administration)的第一要素是一种服务行政(service administration)的观点,(18)但总的来说,在西方学术界,服务行政概念的出现是极其偶然的,它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程度上的流行,服务型政府的概念更是闻所未闻。在某种意义上,服务型政府的概念和理论之所以能够产生在中国,也是与中国行政学研究哲学先行的特征分不开的,由于中国行政学研究是哲学先行的,所以,学者们在思考行政问题时带有更多理论建构的意识,也拥有较强的哲学思维能力来进行这样的理论建构。因此,尽管中国行政哲学研究在起点上要晚于西方的行政哲学研究,但就研究本身而言,则反而比西方行政哲学研究具有更强的逻辑性与体系性,而不像西方学者那样只是在现象学、宪政理论或后现代主义等流行一时的学术潮流那里去寻找只言片语的帮助。
总之,出于中国同时处于常态社会和变革社会中的现实,我们需要同时开展行政科学和行政哲学研究,但在两种研究上应当采取不同的策略。就行政科学研究而言,应当虚心接纳西方成熟的科学管理观念和科学管理技术,以较少的科研成本实现最大化的科研产出,利用已经被证明对西方社会常态治理行之有效的行政方法和技术来解决中国在常态社会治理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就行政哲学研究而言,应当鼓励自主创新,给予理论创新以充分的政策支持,充分发挥中国学者在哲学思考上的遗传性优势,避免因为全面的科学化而造成中国学者哲学思维能力的退化,沦为西方话语霸权的附庸。“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缺乏独立自主的哲学话语,无论在政治上还是行政上,中国政府所取得的这些成就在国际上都广受质疑,甚至中国民众对于所谓“中国道路”也缺乏起码的自信。凡此种种,严重阻碍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中华民族的复兴绝不是对传统文明的回归,也不是对西方文明的复制,而应当是一种文明再造,即通过创造一种新的文明来引领人类社会的进步,而这种文明再造必然是以理论创新为前提的,它需要我们以创新性的理论思维来带动创新性的社会治理变革,在社会治理体系的再造中推动文明的进步。这就是时代向中国行政哲学研究者提出的使命。
注释:
①William Archibald Dunning,Essays on the Civil War and Reconstruction and Related Topics,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898,pp.364-365.
②Leslie Stephen,History of English Though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Vol.Ⅱ,London:Smith,Elder,& Co.,15 Waterloo Place,1876,p.131.
③Heinrich Meier,“Why Political Philosophy?” The Review of Metaphysics,Vol.56,No.2 (Dec.,2002),pp.385-407.
④W.W.Willoughby,“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19,No.1 (Mar.,1904),pp.107-111.
⑤Frank J.Goodnow,“The Work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Vol.1 First Annual Meeting(1900),pp.35-46.
⑥Frank J.Goodnow,“The Work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Vol.1,First Annual Meeting(1904),pp.35-46.
⑦Westel Woodbury Willoughby,“The Value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15,No.1 (Mar.,1900),pp.75-95.
⑧Paul Janet,“Political Science,” In John Joseph Lalor,(Ed.),Cyclopaedia of Political Science,Political Economy,and of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Vol.3,New York:Maynard,Merrill,& Co.,1893,p.258.
⑨Leo Strauss,“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19,No.3 (Aug.,1957),pp.343-368.
⑩Woodrow Wilson,“The Study of Administratio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2,No.2 (Jun.,1887),pp.197-222.
(11)Herbert A.Simon,Peter F.Drucker,Dwight Waldo,“‘Development of Theory of Democratic Administration’:Replies and Comment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46,No.2 (Jun.,1952),pp.494-503.
(12)Michael Harmon,“PAT-Net Turns Twenty-Five:A Short History of the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eory Network,” Administrative Theory & Praxis,Vol.25,No.2,2003,pp.157-172.
(13)Michael Harmon,“PAT-Net Turns Twenty-Five:A Short History of the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eory Network,” Administrative Theory & Praxis,Vol.25,No.2,2003,pp.157-172.
(14)H.George Frederickson,“Toward a New Public Administration,” 竺乾威等编.公共行政学经典文献:英文[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268.
(15)Robert P.Biller,“Some Implications of Adaptive Capacity for Organizational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Frank Marini,(Ed.),Toward a New Public Administration:The Minnowbrook Perspective,Scranton:Chandler Publishing Company,1971,p.126.
(16)Aaron Wildavsky,“The Once and Future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The Public Interest,Number 79,(Spring,1985),pp.25-41.
(17)程倩.“服务行政”:从概念到模式——考察当代中国“服务行政”理论的源头[J].南京社会科学,2005,(5).
(18)James D.Carroll,“Service,Knowledge,and Choice:The Future as Post-Industrial Administr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Vol.35,No.6 (Nov.-Dec.,1975),pp.578-581.
标签:政治论文; 政治科学论文; 公共行政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哲学专业论文; 科学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政治哲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