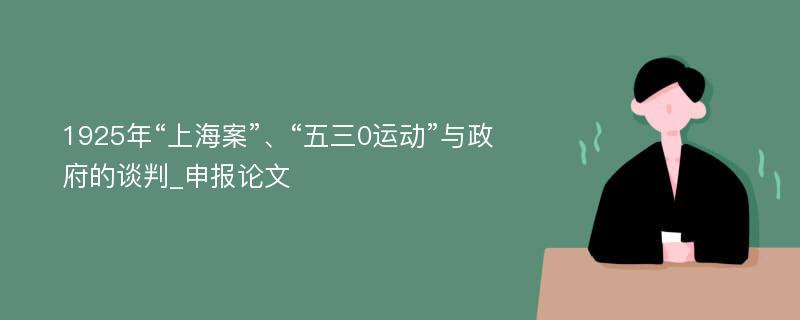
沪案交涉、五卅运动与一九二五年的执政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执政府论文,五年论文,九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前言
直奉战争结束后,在张作霖、冯玉祥支持下,1924年11月24日,段祺瑞在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就任临时执政,并随即召开善后会议,试图解决时局之纠纷,为国民会议的举行做好准备。然而,善后会议刚结束,国民会议还未及开幕,五卅惨案便突然爆发,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外交与政治事件,以及规模浩大的群众运动。以此为契机,1920年代的中国历史亦有了一个大转折。
迄今为止,学界关于五卅事件与五卅运动的研究,多将视线投射于学生、工人、商人及党派身上,强调这些力量对运动的发起及推动作用,对执政府在五卅运动的角色及表现则比较忽略。(注:主要的相关研究有傅道慧:《五卅运动》,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任建树、张铨:《五卅运动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萧超然等编著《国民革命的兴起,1923-1926》,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3-262页;尤尔根·奥斯特哈梅尔(Jürgen Osterhammel):《中国革命: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朱章才译,台北:麦田出版公司,2000年;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刘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黄逸峰:《五卅运动中的大资产阶级》,《历史研究》1965年第3期;何毅亭:《五卅运动中的上海总商会》,《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李达嘉:《上海商人与五卅运动》,《大陆杂志》第79卷第1期,1989年7月;阎平:《“五卅”运动和中共“左”倾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小杉修二:《五三○运动の—考察》,野泽丰编《中国国民革命史の研究》,东京:青木书店,1974;Thomas Creammer,Hsueh-yün:Shanghai's Students and the May Thirtieth Movement.Master thesis,Uni.of Virginia,1975;Hung-Ting Ku,Urban Mass Movement:the May Thirtieth Movement on Shanghai.Modern Asian Studies,vol.13,no.2,1979;Nicholaa R.Clifford,Spoilt Children of Empire:Westerns in Shanghai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the 1920s.Hanover:New England University Press,1991。)既有的看法也多认为执政府在五卅运动中态度软弱,迫于民意而与列强进行交涉,但不能坚持,后来则镇压群众运动。(注:李光一:《段祺瑞“执政府”在五卅运动中的卖国外交》,《史学月刊》1957年第4期;任建树、张铨:《五卅运动简史》,第172-173、205页;吴东之主编《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48-157页。)此种观点失于片面,对执政府办理沪案交涉及其与五卅运动展开之关联过程没有清楚的阐析,并不能反映史实的全部。
不过,仍有一些学者关注到执政府在五卅运动中的表现。如里格比(Richard W.Rigby)曾探讨执政府与外交团的沪案交涉过程,指出执政府希望通过运动所提供的机会加强其在国内与国际上的地位。(注:Richard W.Rigby,The May 30 Movement:Events and Themes.Canberra: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1980.pp.85-97.)丁应求从中外关系的角度论述了五卅上海谈判及对日交涉等问题,对执政府在交涉中的强硬风格颇有褒词。(注:丁应求:“一九二五年上海五卅运动的研究——以中日关系为主”,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86年,第122-178页。)施乐伯和于子桥合撰论文亦曾对执政府支持学生的行为有所论述。(注:施乐伯(Robert A.Scalapino)、于子桥:《“五卅事件”再探》,《“中华民国建国八十年”学术讨论集》,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英文部分第58页。)李健民、杨永明等人的论文对五卅时期执政府与民众运动关系稍有提及,杨指出段祺瑞“欲借外交而争取群众、借群众之力以为己助”之事实。(注: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运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年,第182页;杨永明:《五卅运动时期的外交与内政》,《社会科学研究》2001年第5期。)但由于史料的局限,(注:里格比与丁应求的研究因时间较早,故均未利用中文档案,尤其是执政府外交部档案。这些档案先后披露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五卅运动与省港罢工》,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民众运动),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上海市档案馆编《五卅运动》(共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中华民国八年至十五年)》(以下简称《排日问题》),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或论著主旨的限定,上述学者对执政府在五卅一役中的表现仍无充分阐释,尤其对执政府与运动的成因、发展及收束方面的关联性,基本上未提及。执政府主导的沪案交涉与群众运动间的互动关系及内在动因,论者更未注意到。林霨(Arthur Waldron)曾论及直奉战争与五卅运动的关联性,认为上海及其他各地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发生是由战后秩序失控所导致,将五卅运动仅视为民族主义兴起的结果是不够的,但他并未注意到战后上台的执政府在五卅运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注:Arthur Waldron,From War to Nationalism:China's Turning Point,1924-1925.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p.241-262.林氏在此书中虽然指出了将“民族主义”作为五卅运动形成之分析概念的缺陷,但是由于过分强调1924年直奉战争的后果而对战后秩序失控的程度有所夸大,也没有将“五卅事件“之成因与此后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成因作必要的区分。对于前者而言,固然与江浙战争后上海政治社会秩序的失控有关,但对于后者而言,却主要是当时各方势力尤其是执政府有意运用的结果。关于林霨此书介绍,可见马敏《林霨著〈从战争到民族主义:中国的转折点,1924-1925〉》,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事实上,1925年5月底在上海发生的顾正红案及南京路枪杀案虽有其偶发性,但是这一事件的影响所以能扩展到全国,并引发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却与执政府的政治、外交策略运用密不可分。从执政府的角度出发观察五卅运动,可能会加深对其的理解。(注:本文将执政府当成研究五卅运动的一个重要对象,并非认为五卅期间政府内部意见完全一致。不过,由于中央政府要员多与段祺瑞有密切关系,加之重要决议均经国务会议商议后做出,外交部的对外交涉亦多需要经过段的首肯,政府对事件的应付及其种种策略的出台当然可以被视为执政府的集体决定。)本文将主要依据1990年代以后公布的档案史料,对执政府与五卅运动的关系作一较为全面的考察,并透过此研究来勾勒出五卅运动的另一面。
二 事件爆发后执政府的内部应对与群众运动的形成
五卅事件发生前夕,执政府正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段祺瑞解决“金佛郎案”的办法引起外界的广泛抨击;教育总长章士钊因对北京学潮之强硬处理被全国学界攻讦而自请辞职;宣传已久、饱经挫折的关税会议,其召开又似遥遥无期。5月28日,张作霖藉对金佛郎案的处理不满,通电带兵入关,意在改造政府。舆论多认为,在“风雨飘摇”之中执政府似已无法继续其统治,其政权生命如何延长实属疑问。(注:《内外时评——临时政府的延长问题》、颂皋:《内外时评——奉张入关与北京政局》,《东方杂志》第22卷第7、13号(1925年4月10日、7月10日);《时局改造说之盛传》、《北京通信》,《申报》1925年5月29、30日;孔另境:《五卅外交史》,永祥印书馆,1946年,第16-17页;颜惠庆:《颜惠庆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142页。)然而,五卅事件的突然爆发却让形势有了转机。
5月30日,上海公共租界南京路发生公共租界巡捕枪击中国学生及民众之血案,当场打死4人,多人受伤。(注:《南京路发生惨剧后之昨日形势》,《申报》1925年6月1日;《五卅运动》第2辑,第98页;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Part Ⅱ,From the Firs to the Second World War.Series E,Asia,1914-1939,vol.29(Bethesda,Md: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97),pp.141,174。据上海学生联合会调查,因30日的南京路枪击事件,中国民众先后死亡11人。(参见国际问题研究会编印《五卅事件》,1927年,第21页)在随后的几天内,事态继续恶化。6月1日,复发生租界巡捕开枪事件,当场打死1人,17人受伤。见《五卅运动》第2辑第110页。)特派江苏交涉员陈世光急电外交部通报此突发事件。(注:《上海陈特派员五月三十日电》、《虞洽卿接上海总商会电》、《收总商会函》,1925年5月31日,《排日问题》,第426、430页。事发之际,虞氏正在京出席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第五次大会。)同时,正在北京的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亦将其接到的沪案发生电报报告执政府。执政府对事件迅速作出反应:对内安抚民众激动情绪,设法控制上海已形成的罢工局面;对外则以强硬态度表示抗议,并藉“民意”作后盾,以迫外人让步。
段祺瑞接获沪案消息后,即派许沅以外交部特派江苏交涉员身份火速南下,又派虞洽卿以“淞沪市区会办”的名义返回上海调处。(注:《国内专电》,《申报》1925年6月3日;《沪英捕杀伤学生风潮扩大》,《益世报》1925年6月2日。见季啸风、沈友益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以下简称《史料外编》。该书系由剪报汇集而成,故本文凡引自该书者,如能辨别原报纸之名称及日期,便一一注明,否则只有注明新闻标题及在该书页码)第68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00页。《政府公报》第3294号,1925年6月2日,第1-2页。许沅之任命是5月30日上午国务会议上做出,并非沪案发生后方任命,盖陈世光此前即因病恳请辞职。见《三十日之执政会议》,《申报》1925年6月4日。)为协助虞处理沪案交涉与善后,段又命令从教育部精选职员数名随其乘专车南下。(注:《公共租界罢市之二日》,《申报》1925年6月3日。上海总商会后来之所以长时间承担罢工工人经费的筹募及管理实与执政府此时的政治安排密切相关。)6月2日,执政府国务会议紧急讨论沪案,阁员对租界当局以武力摧残手段对付无辜学生,多表愤慨,认为有辱国体,要求政府应即时彻查,秉公交涉,“与全国人民一致合作,以平民气”。会议通过四项决议:1.当即向驻京使团领袖意使表示严重抗议;2.应由执政府、外交部各派大员一名驰赴上海,实地调查并妥筹临时处置;3.调查大员人选定曾宗鉴、蔡廷幹二人;4.急电该地军警长官镇抚商民,切戒越轨行动,免贻外人口实。(注:《阁议讨论沪案办法》,《申报》1925年6月6日。曾宗鉴时任外交部次长,蔡廷幹为税务处督办。)6日,段祺瑞发布执政令,宣告政府对于五卅事件之态度:
此次上海租界事变,市民激于爱国,徒手奋呼,乃垒遭枪击,伤杀累累。本执政闻之深滋痛惜。除饬由外交部提出严重抗议外,已遴派大员驰赴上海慰问被害人民,并调查经过事实,期作交涉之根据,而明责任之所属。政府视民如伤,维护有责,必当坚持正义,以慰群情。尚冀我爱国国民率循正轨,用济时艰。本执政有厚望焉。(注:《临时执政令》,《政府公报》第3299号,1925年6月7日。)
五卅前夕,上海正处于战后的“三不管”状态,(注:慎予:《三不管的上海》,《国闻周报》第2卷第17期,1925年5月10日。江浙战争收束时,段政府应上海各界团体要求宣布撤废凇沪护军使、迁移上海兵工厂、淞沪不驻兵。关于江浙战争及其收束请参考冯筱才《江浙商人与1924年的“齐卢之战”》,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第33期(2000年6月)。)华界公然贩卖鸦片,驻沪军队因此内讧开火,以致人心惶恐。(注:李振华辑《近代中国国内外大事记(民国十三年至十六年)》,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年,第4717、4719、4721页;《虞洽卿接上海总商会电》,1925年5月31日,《排日问题》,第430页。)淞沪警察厅、沪海道尹署、上海县知事署、江苏交涉公署等官方机构对民众之集会、游行及学生演讲等活动也没有采取干涉政策,执政府更未有此种命令。(注:5月30日,沪海道尹张寿镛及警察厅长常之英、交涉员陈世光曾致函总商会及各路商总联合会,望其对罢市之议加以劝导,但并无强力禁止措施。见《张寿镛等致上海总商会及上海各路商总联合会函》,《革命文献》第18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印,1978年,总第3277页。)正是在这种情势下,上海的中共及国民党党团组织得以从容发动罢市、罢工、罢课运动。(注: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上海:东方出版社,1991年)第24-28页;傅道慧《五卅运动》第91页;上海市档案馆编《五卅运动》第1辑第12-21页;黄美真、石源华、张云编《上海大学史料》(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140页;《郑超麟回忆录(1919-1931)》(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03页。6月1日,上海总工会登报通告成立,并发表告全体工友书,宣布“从六月二日起,上海全埠各业工友,全体一致罢工”。详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卅运动史料》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5页。)6月1日,上海罢市实现,2日全市总罢工实现。当虞洽卿与许沅抵沪时,罢市与罢工均已成为事实,虞洽卿此后主要的任务之一便是依政府命令安顿上海罢工工人。(注:《执政接见领衔义翟使问答》,1925年6月5日,《排日问题》,第438页。段对领袖公使意使翟禄弟(Vittorio Cerruti)表示:“上海罢工已派虞洽卿赴沪,大致无妨。”见《排日问题》第439页。)
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扩散,更与“军阀袖手旁观”有莫大关系。(注:《朱兆莘致外交部电》,1925年6月2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73页。)5月10日,段祺瑞曾为北京学生因集会受阻而冲击教育总长章士钊住宅一事,下令斥责学生,并责成教育部告诫学生嗣后“务应专心向学,勿得旁涉他务”。(注:李振华辑《近代中国国内外大事记(民国十三年至十六年)》,第4717页。)沪案发生后,全国各地出现抗议及援助浪潮,其声势尤以北京为烈,执政府对其持默许乃至支持态度,事实上已经放松了对学生运动的管制。6月1日,北京各校学生即开始筹备各校沪案后援会,政府并未表示取缔。相反,为表示对民众爱国热情的支持,北京政府一些要员参加群众游行,祭吊五卅牺牲者。(注:《沪英捕杀伤学生风潮扩大》,《益世报》1925年6月2日;《全城学生罢课讲演》,《晨报》1925年6月5日。均见《史料外编》第68册第100、141-142页。《朱兆莘为沪案与安格联辩论电》,1925年7月2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民众运动),第183-184页。)
6月3日,在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下,国民会议促进会、学生联合会等团体在北京召开国民大会。各校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并先后至执政府与外交部请愿。段祺瑞派人接收呈文。外交总长沈瑞麟则亲自接见请愿代表,表示对学生所提要求“将尽量做去”,沈甚至派部员同学生代表谒见公使团领袖公使,以协商学生整队通过东交民巷使馆区之事宜。(注:《昨日北京学生大游行》,《益世报》1925年6月4日,见《史料外编》第68册第119-120页;《国内专电》,《申报》1925年6月4日。)
4日起,北京各校学生均罢课讲演,据称有八九千人在各处讲演。军警方面未加干涉,甚至“亦加入听众”。京师警察总监朱深还特邀各校校长到警厅谈话,其要旨亦仅告诫校长们“切不要由对外一转而对内,反对政府”。朱并向学生表示“在范围内作爱国运动,警厅方面,不但不加干涉,抑且愿尽力保护”。(注:《全城学生罢课讲演》,《晨报》1925年6月5日,见《史料外编》第68册第141页;李金坡编《五卅惨案调查记》,北京民国大学,1925年,第11-14页;《国内专电》,《申报》1925年6月7日;《全城学生罢课讲演》,《晨报》1925年6月5日,见《史料外编》第68册第144页;《北京学界誓死雪耻》,见《史料外编》第68册第157页。)10日,20万人参加之雪耻大会在天安门召开,军警方面协同维持秩序,京畿警卫总司令鹿钟麟派邓萃英为代表担任大会主席之一。(注:《雷雨如注中之国民大会》,《顺天时报》1925年6月11日,见《史料外编》第68册第202页。当时北京主要在冯玉祥控制下,由国民军第一师师长鹿钟麟任京畿警卫司令。李大钊、徐谦、李石曾等人与之关系密切,这是北京发生大规模群众运动的一个重要背景。然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忽略执政府对民众运动的主动运用。)段祺瑞对来府请愿代表表示“容纳全部要求,对英力争”。(注:《空前之北京国民大会》,《民国日报》(上海)1925年6月12日。)此后北京不断出现大规模的群体抗议集会。(注:14日,长辛店京汉铁路工人5000余人到北京天安门集会,并到外交部与执政府请愿,两处均派代表接见,并加以安慰(《京各界为汉口惨变游行示威》,《晨报》1925年6月15日,见《史料外编》第68册第292页)。25日,又有各界举行30万人总示威。30日,“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国民大会”在天安门前召开,500多个团体参加。详见《国民革命的兴起,1923-1926》第173-175页。)京师宪兵司令部对北京的事态发展曾有报告给执政府,但并无压制措施。此种气氛中,雪耻大会的举办者甚至想到请求执政府航空署派飞机在京城上空散发传单。(注:《五卅运动与省港罢工》,第121、124页。段祺瑞对此仅批示“该署系公家机关,宜否酌之”,并未对大会召集及传单之散布表示任何反对。参见《五卅运动与省港罢工》第21页。)对其他各地由学生主导的五卅宣传行动,政府亦基本采取放任态度,国内似已形成官方与学界合作一致对外的态势。(注: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宣传》,第252页。)群众运动借政府放任之机蓬勃发展的同时,执政府无疑正在利用此股民气达到其政治目的。
沪案发生后,执政府也前所未有地向外界表示对民众舆论的重视。6月6日,国务会议有“根据民意负责办理此案”决议通过。8日,段祺瑞在府邸接见北大学界代表蒋梦麟、王世杰、周鲠生等,代表们对谈话结果甚表满意。(注:《政府对沪案昨晚已下明令》,《顺天时报》1925年6月7日;《京各界雪耻运动坚持猛进》。见《史料外编》第68册第150、174页。)16日,段在与英国公使白慕德(Charles Michael Palairet)会晤时表示,列强在同中国政府谈判时,以前多没有将中国全体民众考虑在内,但是现在情形不同了,民众舆论是中国任何一个政府都不能忽略的。(注:British Documents of Foreign Affairs,p.240.)尽管这种姿态或为“民意汹汹”之情势所逼迫,其中不乏故意“作秀”的成分,却也反映了执政府有意的政治运用策略。
执政府的态度似与冯玉祥、张作霖等人有关系。沪案发生后,冯玉祥的表现最为激烈,不仅在其部队中发表反帝演讲,还派人携款两万元到沪支援罢工工人。(注:James E.Sheridan,Chinese Warlord:The Career of Feng Yu-hsiang.Stanford:University Press,1966,pp.172-173.)6月8日,冯致电张作霖,请其一起致电政府,对沪案表示决心。9日,冯又致电段祺瑞,表示愿意“枕戈待命,剑及履及,为政府作后盾,为国民平积愤”。(注:朱松庐编《五卅惨史》,上海和平救国社,1925年,第70-71页;《冯张对外态度一致》,《民国日报》1925年6月12日。国民军方面的反应亦可参见《国民军起为国民后援》、《国民军积极援助国民》、《岳维峻致于右任电》、《冯玉祥述对“五卅”决心》,《民国日报》1925年6月9、10、11、13日。)其激进态度不但为国人瞩目,亦使英人高度紧张。当时执政府既然“在冯势力范围下”,(注:《收驻英宋代办(莘)电》,1925年6月9、15日,《排日问题》,第469、483页;British Documents of Foreign Affairs,p.177。)支持群众运动便也有拉近与冯关系、加强自身地位的意味。
沪案发生之际,奉张正抵达天津,其势汹汹,改造内阁之说喧嚣尘上。执政府对此甚为恐慌,段祺瑞连续派阁员到津探问张氏真意。然沪案发生后,全国民意沸腾,要求政府对外严正交涉。张作霖在此形势下,对内亦只有表示缓和,以免成为舆论靶的,对外则更多的是保持表面的沉默。(注:《张作霖入关之先声》、《国内专电二》、《奉张入关之原因》、《张作霖到津记》、《北京通信》、《奉张入关后之京政局》,《申报》1925年5月30日,6月1、2、3、4日。张在6月10日复奉天省长王永江电中指示:“沪案发生仅上政府一电,请求据理交涉,各方函概未答复。事有中央负责,无庸别有表示也。防止各校学生运动,务须妥速办理,并告以政府宗旨。力主严重,决不放松,勿令生出枝节。”(辽宁省档案馆编《中华民国资料丛稿·电稿·奉系军阀密电》第2册,中华书局,1985年,第160页)奉在对外沉默的同时,与英美等国外交官却有密切联络。参见The May 30 Movement,p.79;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运动》第174页。)张为表示在“爱国”上不落后于他人,6月4日曾发电抗议上海英人枪杀行为,要求政府“据理交涉”。9日又响应冯玉祥,率奉军将领通电执政府及各界,谓“悍卫国防,义无旁贷,请一致对待”。传说张亦有一万元捐给上海罢工工人。对执政府之处境,张则表示“非常体谅”,改造内阁一说亦暂告和缓。此举当然是张“藉以顾全自己立场”的表现。在执政府正“注力于外交问题”之际,奉张无疑意识到如有过高之要求,其效果可能适得其反。(注:《五卅惨案调查记》,第21页;《冯张对外态度一致》、《奉张亦同情于爱国运动》,《民国日报》1925年6月9、12日;《五卅运动》第2辑,第198页;The May 30 Movement,p.78;《国内专电》,《申报》1925年6月4、7日;《暂可小康之中央政局》,《顺天时报》1925年7月9日,见《史料外编》第5册第512页。)
冯玉祥与张作霖既然相继表示“爱国”之意,段祺瑞乃一面向外界宣布冯、张等要求对交涉采坚定立场的来电,一面派员赴天津邀张“共担国事”,声言“政府应付丛脞,希望疆吏原谅,则勉维暂局,若督责太严,惟有遂初”,内含威胁之意。12日又覆电冯、张,表示“决坚持到底,望内外合作”。对执政府而言,趁外交紧急时挟民意以对抗强势军人是暂保地位的一剂良方,亦是均势政治的一种运用手段。(注:《国内专电》,《申报》1925年6月8日;《段政府对沪案态度》,《民国日报》1925年6月13日。1924年底段祺瑞出山时,其幕僚所提出的主要策略之一便是“使临时政府长久站立在各派均势的三脚架上”。参见松涛《内外时评——战事形势与和平运动》,《东方杂志》第22卷第21号(1925年11月10日);《东南战起后之段方政策》,《申报》1925年11月4日。)在此情势之下,五卅运动得以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
三 初期交涉与五卅运动的展开
中外关系危机存在之际,执政府的地位无形中得到巩固。外交谈判进行时,政府的威望可能会随着民族主义情绪滋长扩散而上升。段祺瑞政府从一开始就试图通过恰当因应此一事件而增强其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地位。在1925年开始的几个月内,执政府一直在与公使团代表讨论条约义务的法理承认及废除治外法权等问题,敦促有关国家考虑条约修改问题,但并未得到列强的实质性答复。(注:The May 30 Movement,pp.87,85.)关税会议的召开也迟迟未有进展。南京路枪杀事件爆发后,政府似乎有望在外交方面获得突破性进展。
30日,南京路枪杀案发生后不久,特派交涉员陈世光即应学生要求到领袖领事馆表示口头抗议。次日,陈复奉令向领袖领事递交第一次抗议书。6月1日,因枪击案仍在继续,再次递交抗议信。2日,外交部在北京向公使团送出第一次抗议照会,认为“该学生等均青年子弟,热心爱国,并不携带武器,无论其行为之性质如何,断不能以暴徒待之。乃捕房未曾采取适当方法和平劝阻,遽用最激烈手段,实为人道及公理所不容,自应由租界官吏完全负责”。(注:《五卅外交史》,第17-18页;British Documents of Foreign Affairs,p.175.由于31日是星期日,各国驻京公使馆休息。故照会上虽书“六月一日”,但送出该照会已是第二天。见《五卅事件》第51页。)其支持学生之态度异常鲜明,以致使团认为该照会“似出愤激学生之手”。6月4日,外交部不及外国公使团之答复,又因上海公共租界继续发生枪杀案,遂提出第二次照会,谴责租界当局“蔑视人道”,应对其开枪行为及其后果完全负责。(注:《收驻英朱代办(莘)电》,1925年6月26日,《排日问题》,第492页;《五卅外交史》,第19页;《五卅事件》,第51页。)5日,段祺瑞接见领袖公使意使翟禄弟时,表示自己“至深痛苦”,“上海巡捕如此对待学生,使中国对于国际地位攸关体面。”(注:《执政接见领衔义翟使问答》,1925年6月5日,《排日问题》,第437页。)8日,外交部长沈瑞麟会晤英国代理公使,亦谓:“此次各地市民激以爱国热诚,毫无排外性质,执政日前所颁昭令,劝慰国民已有率循正轨之语,余看沪事现时最紧要者,莫过于恢复市面平时原状,即如取消戒严令,撤退海军陆战队,并解除商团巡捕之武装,释放一切被拘人等,发还被封或占据之各学校房屋,只要租界当局有所觉悟,措置公道,公愤自易平息。”(注:《总长会晤英白代使问答》,1925年6月8日,《排日问题》,第453-454页。)
沈瑞麟所提取消戒严令等四项要求,实际上是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所提“十七条”之先决条件,(注:“十七条”包括4项先决条件及13项正式条件。先决条件4项为:(一)立即取消戒严令;(二)撤退海军陆战队,并解除商团及巡捕之武装;(三)所有被捕华人一律送回;(四)恢复公共租界被封及占据之各学校原状。正式条件13项,主要内容如下:(一)惩凶;(二)赔偿;(三)道歉;(四)撤换工部局书记鲁和;(五)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绝对自由;(六)优待工人;(七)分配高级巡捕;(八)撤消印刷附律,加征码头捐交易所领照案;(九)制止越界筑路;(十)收回会审公廨;(十一)工部局投票权案;(十二)要求取消领事裁判权;(十三)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其各条之下多有细目说明。(详见胡愈之《五卅事件纪实》,《东方杂志》第22卷五卅事件临时增刊,1925年7月,第20-22页)6月7日上海工商学界联合会将“十七条”面交刚抵上海的特派交涉专员蔡廷幹、曾宗鉴等人。(详见《五卅运动史料》第2卷第279-280页;《收上海交涉员(沅)电》,1925年6月11日,《排日问题》,第470页)外交部对“十七条”,初拟分层次处理:“取消领事裁判权”及“永远撤退驻沪英日海陆军”两条因关系中外已签条约,故决定不提出;而先决条件四项,及惩凶、赔偿、道歉等项则在沪提出;撤消公共租界工部局“三提案”及制止越界筑路、收回会审公廨等由外交部催办;至于“代工部局投票权”一条决另与外人定洋泾浜章程;其余各条视情形“相机提出”。详见《发上海特派员(许沅)电》,1925年6月13日,《排日问题》,第475-477页。)10日,沈在会见法使时又重提此四点,认为如能做到,上海秩序或可恢复。使团方面则要求执政府命令学生返校,静候政府解决。沈对此屡次表示拒绝,称“政府断不能以压力禁阻学生”。11日,中方再发出第三次照会,声明对于五卅惨案及六一惨案,上海租界官吏应负责任,同时再次将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之四项先决条件全部提出。(注:《总长会晤法玛使问答》,1925年6月10日;《总长会晤义翟使问答》,1925年6月12日。见《排日问题》第464、473页。《五卅外交史》,第23-24页。)然而,6月4日,公使团在对第一次中方照会的答复中,否认上海租界捕房当局应负沪案责任,并认为中方所述并不完整。(注:所谓“不完整”,即指中方照会中“仅言英捕击伤若干华人,并未提及日本人为华人掷于沟中,及新世界枪伤美商团之事”。见《刘秘书(锡昌)赴义馆会晤义翟使问答》,1925年6月4日,《排日问题》,第434-435页。)6日,第二次覆牒仍认为中国所得报告不甚完全,同时又通知中方,公使团已组织调查委员团,并决定即派赴上海调查。(注:《五卅外交史》,第21页;《使团驳复外部第二次照会》,《顺天时报》1925年6月7日,见《史料外编》第69册第160页;《外交部致特派江苏交涉员陈世光电稿》,1925年6月8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第236页。)10日,各国委员团抵达上海,开始调查工作。中国外交部亦即令曾宗鉴对沪案中伤毙华人情形做“精确详尽”之调查,以备提出要求之依据。经政府同意,上海总商会托律师谢永森修订“十七条”,政府方面亦同意在仔细斟酌的基础上照此提出。(注:《发上海曾次长(宗鉴)函》,1925年6月16日;《发上海许交涉员(沅)电》(共三封),1925年6月13日。见《排日问题》第483、475-476页。谢永森为上海总商会之顾问,据云“精通法律”,经该会呈请,6月6日由外交部饬令委派谢氏帮同江苏交涉员办理沪案。见《外交部致特派江苏交涉员陈世光电稿》,1925年6月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第236页。)当时执政府尤其是外交部方面似有意使“上海事件地方化”,故在各方协调下,决定将“十七条”修改成“十三条”,以“完全涉及上海地方”。14日,许沅正式将“十三条”提交给领袖领事。(注:《颜惠庆日记》第2卷,上海市档案馆译,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第238、240页;《总商会修改条件已由交涉员提交领袖领事》,《晨报》1925年6月15日,见《史料外编》第68册第235页。执政府有意借民众团体提出对外交涉条件,并在暗中直接介入“十三条”之拟订过程,而学界多将“十三条”视作是由上海总商会或者虞洽卿个人擅改十七条而提出,实未明了其中内情。)15日,北京公使团电令在上海之六国委员团,组织沪案委员会,与中国委员迅速开议。执政府也特派郑谦、蔡廷幹、曾宗鉴、虞洽卿四人为谈判代表,与六国委员接洽开议。(注:《执政府外交部关于沪案交涉事即日开议电》,1925年6月15日,《五卅运动与省港罢工》,第32页。虞洽卿之任命与北京使团领袖领事翟禄弟在段祺瑞面前的建议有关(见《执政接见义翟使问答》,1925年6月14日,《排日问题》,第480页),但虞后来以其“立于商会会长地位,未便参加”,向政府辞去代表职务。(见《上海总商会五卅委员会第六次委员会会议记录》,1925年6月16日,《五卅运动》第1辑,第444页)后政府则以原定“随同办理”的许沅递补。)
为使对外交涉有所依靠,此时政府对上海罢工给予支持。6月11日执政府国务会议上,应10日天安门国民大会之所请,决先由财政部拨上海10万元,以维持罢工工人生活。(注:《国务会议议决拨上海十万元》,《顺天时报》1925年6月12日,见《史料外编》第68册第212页。)13日,在京政界及学界名流成立沪案救济会,以筹划沪案交涉与援助沪案失业工人为宗旨。从其组成即可以看出政府支持的色彩甚浓。(注:该会以熊希龄为正会长,梁士诒、许世英、李石曾、黄郛为副会长,马叙伦为干事部主任,副主任为袁良、屈映光。评议员包括薛笃弼、郑洪年、孙学仕、王正廷、胡适、汤尔和、张耀曾、孙宝琦和颜惠庆等人,鹿钟麟、庄蕴宽等亦在其中。(《昨日成立沪案救济会》,《顺天时报》1925年6月14日,见《史料外编》第68册第223页)据说,在救济会中,熊希龄与梁士诒等人均极激进。熊主张拒付债务,并写信给段要求宣战,而颜惠庆等人态度相对和缓。参见《颜惠庆日记》第2卷第241页。)在政府的授意下,上海总商会开始办理罢工工人经费之维持管理,并与中共领导下的上海学生联合会、上海总工会等团体合作。(注:《共青团上海地委学生部关于五卅期间上海学生运动情况的报告》,1925年10月,《五卅运动》第1辑,第99页。以往研究在谈及五卅运动与上海商人时,往往只注意商人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或者因其利益攸关而对运动加以支持,而多忽略政府态度对其影响。(参见何毅亭《五卅运动中的上海总商会》,载《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李达嘉《上海商人与五卅运动》,载《大陆杂志》第79卷第1期,1989年7月)1925年上海工人五卅罢工经费问题,由于牵涉面甚广,笔者拟另撰专文讨论。)后者的地位此时无疑得到政府默认。对群众运动的控制亦在努力进行之中。6月14日,因镇江、汉口、九江等地发生民众排外事件,使团方面向中国政府提出警告。(注:《使团将向中政府提出警告》,《顺天时报》1925年6月16日,见《史料外编》第68册第240页。此项警告于6月17日提交给执政府外交部,认为各地华人排外情绪正在发展中,请中国政府注意其责任。参见《使团警告昨日已送达外部》,《顺天时报》1925年6月18日,见《史料外编》第68册第259页。)执政府当即在15日召开特别会议,通过“保护外侨案”,决定由陆军部与内务部通电全国军警,一律严密保护外侨生命财产。对于学生爱国运动,“随时派军警严防匪徒从中鼓煽,危及外侨”。在北京,由执政府侍卫武官处会同警卫总司令部、警察厅等合组联合办事处,以维持京中治安秩序。(注:《执政府昨日开特别会议》,《史料外编》第68册,第241页。)政府此种举动既是为了敷衍使团之抗议,亦是因此时上海交涉正在进行之中,执政府方面恐外人因华人排外举动而退出交涉。
16日,沪案交涉会议在江苏交涉公署举行,列席使团参赞六人。中方特派员为蔡廷幹、郑谦、曾宗鉴、许沅等四人。17日,中外委员开第一次谈判,中方即以“十三条”为交涉根据,但祁毕业(Tripier)表示:“中国政府向使团抗议,仅提出四项问题为本团所知,其余均未知悉,无从商量。”六国委员似乎设想在赔偿牺牲者、同时将华界中国负责警长与租界捕头爱活生(Edward W.Everson)撤职、终止罢工与撤去外国军队几项条件基础上与中方达成初步的解决方案。(注:《特派江苏交涉员许沅检呈使团派沪调查委员与中央特派员交涉会议记录致外交部函》,1925年6月1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第257页;British Documents of Foreign Affairs,p.176。)但此方案显然与中方要求相距甚远。
18日,六国委员因奉使团训令,限三日内讨论完毕,故将其所拟往来函稿交中方代表,作为解决方案讨论之基础,其中尤其强调五卅事件由于华界警察怠于职务之故。中国委员表示不能接受,认为“十三条”中许多项均为事件之肇因。六国委员遂发表宣言,声明中国要求条件在该委员团之职权范围之外,随即返京。上海交涉遂告破裂。(注:《特派江苏交涉员许沅检呈使团派沪调查委员与中央特派员交涉会议记录致外交部函》,《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第264-265页;《京师警察厅关于交涉中断外委返京密报》,1925年6月19日,《中华民国史料汇编》第3辑(民众运动),第163页。对初期沪案交涉的失败,多有人认为是与上海总商会擅改“十三条”,与“十七条”形成两种意见,而让外人发现国人的不团结,影响其态度有关。(参见《五卅外交史》第34-35页;《五卅事件》第34-35页;方椒伯《回忆“五卅”罢市》,《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第1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192页)但丁应求的研究表明,交涉中止其实与此关系不大。关键是中外双方在条件上无法达成一致,外人只愿意将协商的范围限于纯粹的五卅事件,而中国政府代表财坚持提出“全盘性要求”。是故谈判无法继续。(参见丁应求“一九二五年上海五卅运动的研究”,第136-138页)此点亦可从英国外交官的事后报告中得到证实,见British Documents of Foreign Affairs,p.187。)
执政府之所以坚持“十三条”不让步,是欲藉此次交涉来增强政府威望。交涉成功,政府无疑取得重大外交胜利;失败,则更促使民气沸腾,而要求政府办理交涉的要求愈甚。政府亦能以此给外人压迫,迫使其在其他问题上让步。6月20日,外交总长沈瑞麟在回答北京各校沪案后援会代表时称:“十三条件,为上海工商联合会所提,换言之,即上海各界之全体意思,亦即与我国有重大关系之条项,政府当然据理力争,无论如何,非与国民一致坚持到底,非达到目的不止”。(注:《外陆两长对学界之表示》,《顺天时报》1925年6月21日,见《史料外编》第69册第13页。)对十三条件,民间倒有一些舆论表示不满,认为十三条件“毫无价值杂乱无章”、“反使各国疑虑”或者仅反映了上海租界内“少数资本者之利益”。(注:《收黄增生函》,1925年7月11日,《排日问题》,第532页;《所谓沪案之十三条件》,《益世报》1925年6月19日,见《史料外编》第68册第268-269页。)汤尔和也称“头脑最不冷静的,就是政府。自从沪案发生到现在,没有看见他们有一定的步伐,只看见他们顺着群众‘打民话’(不是打官话)。很好的机会,睁眼错过,跟着潮流,漂到那里是那里”。(注:汤尔和:《不善导的忠告》,《晨报》1925年6月27日,见《史料外编》第69册第25页。)但这种“无步伐”、“打民话”,虽有慑于强大民意的无奈,同时背后却也隐藏着策略性运用群众运动的一面。
上海交涉失败后,执政府方面开始采取长期交涉计划,将重点转向修改中外条约及催促列强同意迅速召开关税会议上。6月24日,外交部同时递送两个照会给公使团:1.沪案移京交涉,正式提出十三条为交涉根据。2.提议依公平主义修正中外条约。26日,政府复成立外交委员会,决定对五卅一案分阶段办理。(注:孙曜编《中华民国史料》,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649-652页;《外交委员会已正式产生》,《史料外编》第69册,第46页。外交委员会之设立是6月16日国务会议上通过的。见《段政府组织外交委员会》,《民国日报》1925年6月18日。)
不过,上海交涉失败后,当地的群众运动实际便开始收缩。对上海总商会而言,罢市之举既是出于被迫,而事后之维持亦有做交涉后盾之考虑。但罢市给上海商界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故上海谈判失败后,商界随即决议开市。6月19日,即上海中外委员谈判破裂的次日,上海总商会即召集76团体决议自当月21日起开市。同一天,各路商界总联合会也致电北京政府,强烈要求与英国的谈判须于24日前结束。23日,总商会与工商学联合会举行联席会议,定26日开市。(注:方椒伯:《回忆五卅惨案》,《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9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0页;《五卅运动》第2辑,第220-222、225页。关于上海“五卅”罢市的形成经过及商界的应对等,参见冯筱才《罢市与抵货运动中的江浙商人:以五四、五卅为中心》,载《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1期。)罢市虽然结束,但是抵货运动却更为热烈地在各地被发动起来,其目标则主要转向英国,这与执政府的单独对英策略密不可分。
四 单独对英策略的提出与反英运动的急进
沪案发生后,各国反应并不一致。在具体交涉过程中,各国分歧更趋明显,这一方面使中国的外交策略能获一定成功,另一方面亦迫使英国方面的对华政策发生改变。
英国在五卅事发后力图拉近与各国的关系,共同对中国施加压力,但其他列强并不配合。先是法国与美国的法官在工部局会审公廨上宣判被拘学生无罪,接着北京公使团又因发现上海公共租界当局“秘密动员令”而排斥上海领事团参与交涉。中国方面则利用“英捕射杀无辜学生”的宣传,采取有效的分离策略,使英国孤立化。(注:晨报编辑处、清华学生会编《五卅痛史》,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年,第89页;Harumi Goto-Shibata,Japan and Britain in Shanghai,1925-1931.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5,pp.19,39,30。)
到6月19日,北京使团表示愿意继续与中国政府谈判,但将英国代表排斥在谈判委员会主要负责者之外,在华英人为此深表不满。23日,六国委员将调查结果撰成报告书准备发表,但英国恐其责任将被证实,乃极力阻止。然法国公使玛太尔(Damien Comtede Mattel)仍将报告原文寄往巴黎公布。(注:British Documents of Foreign Affairs,p.176;《五卅外交史》,第38-39页。)7月6日,使团会议上意、日、美等国公使均同意对中国稍作让步,训令上海领事团饬公共租界工部局即日实行以下三条:工部局总巡麦高云(Kenith John Mceuen)应立即免职;工部局董事会应严加谴责;开枪之捕头爱活生应依法严办。但英公使表示强烈反对,力阻其实行。9日的使团会议上,英公使为工部局尽力开脱,并指责法使公布报告。法使玛太尔遂辞去交涉代表一职,使团分裂公开化。
对英国的强硬态度,执政府从一开始便有所注意,并有集中目标于英国之应付策略。6月10日,英方便发现“排外运动变为专门排英运动,日渐蔓延”。13日,外交部致英国代理公使照会亦暗含单独对英交涉的意味。(注:《黄秘书宗法接见英馆台参赞谈话记录》,1925年6月10日,《排日问题》,第465页。13日该照会称:“此次上海各校学生因学生被捕及工人受伤时事游行、演说、散布传单,既非越轨举动,且未携带武器,乃捕房总巡Everson氏遽行发令开枪,伤毙华人多名,至再至三,贵国在公共租界既处特别地位,而首先发令开枪又为捕房总巡,此案现定在上海就地商议办法,相应照请贵代理公使查照,电饬在沪贵国官吏,对于华官所提各条务以公允态度容纳,俾得早日商结,是所至盼。”见《发英白代使照会》,1925年6月13日,《排日问题》,第478页。)汉口事件与沙基事件发生后,单独对英的呼声更高。正如外交部调查汉案专员邓汉祥所称,单独对英,一可使范围缩小,易于持久;二可使英人直接感受痛苦,不难就范;三可使政府与人民亦能趋于一致,政府对外既坚持到底,不稍退让,则人民自然谅解,乐为后盾。四可利用外交生政治作用者。政府人民能沟通一气,亦无间隙之可乘。(注:《内外兼顾之政府态度》,《顺天时报》1925年6月15日,见《史料外编》第68册第233页;孙曜编《中华民国史料》,第661-662页。)
上海交涉中,中国政府又发现英政府态度强硬,并影响到六国委员团的意见。是故,有6月18日执政府及外交部给各地的训令,表示事件之责任仅在英国,与其他各国无关,国民如为一般的排外,反失各国对我之同情。上海县知事曾据此训令在华界四处张贴相似内容的告示。英使白慕德为此曾向中国政府递交照会抗议。(注:《收董康等致总长函》、《发江苏省长(郑谦)电》,1925年6月6日、7月7日,《排日问题》,第508-509、507页;《曾宗鉴致沈瑞麟电》,1925年6月1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第265-266页;《外交吃紧中之政府表示》,《顺天时报》1925年6月19日,见《史料外编》第68册第270页。)
使团分裂后,“单独对英”之主张遂由外界之呼吁正式成为执政府运用的策略。到7月中旬,形势似乎正如瞿秋白所说“完全陷于‘单独对英’的对日妥协运动之宣传里”。(注:瞿秋白:《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九二五年》,《新青年》第3号(1926年3月25日)。)为了单独对英,执政府在一开始便有意先将顾正红案及日纱厂问题设法解决。(注:《发日本芳泽公使照会》,1925年6月4日,《排日问题》,第439-440页。沪案发生后,外交部派秘密调查员朱锡麟等人到上海先解决日厂罢工问题。(见《收朱锡麟函》,1925年6月29日,《排日问题》,第496页)奉命返沪调处沪案的虞洽卿一回到上海,也再三强调要将日本纱厂问题与英租界开枪事件分开处理。参见《五卅运动史料》第2卷第1078页;亦可见虞氏给日本上海总领事的信,Harumi Goto-Shibata,Japan and Britain in Shanghai,1925-1931,p.16。)上海谈判失败后,日纱厂案单独解决加紧进行。为尽速解决此案,执政府后来甚至同意贴补工人所要求增加的3个月工资共15万元。8月12日,中日双方在解决条件上签字,上海日本纱厂先后复工。(注:《日纱厂案将先解决之倾向》,《益世报》1925年6月25日;《上海事件筹备续开谈判》,《顺天时报》1925年6月25日。见《史料外编》第69册第30页;《收江苏省长(郑谦)代电》,1925年8月11日,《排日问题》,第559页;《五卅外交史》,第87-96页。)日本从五卅运动的谴责中得以脱身。
执政府“单独对英”策略获得国内舆论及实力派的支持。事发之初,一些颇具影响力的人物即提出缩小范围的主张,如江亢虎、邵飘萍、戴季陶等人便先后提出此种意见。北京大学校方似乎也不赞成学生发起反日运动。(注:《本埠各团体之函电》,《申报》1925年6月4日;《总长会晤英白代使问答》附件一,《排日问题》,第454页;戴季陶:《中国独立运动的基点》,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海执行部,1925年,第2-3、6-7页;《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121页;Harumi Goto-Shibata,Japan and Britain in Shanghai,1925-1931,p.15。)五卅以后,冯玉祥虽然表达了对外国人强烈的敌意,但是正如谢里登(James E.Sheridan)指出的,冯的这种敌意是有选择性的。面临奉张的威胁,为巩固势力,他正在一面争取苏俄的援助,一面向日本示好。所以冯玉祥亦是“单独对英”提倡有力者,其代表在6月28日上海总商会会议上要求与会者把仇恨集中于英国人身上。7月8日,冯玉祥复通电全世界基督教徒,抨击英国对“五卅惨案”之态度。(注:《冯玉祥主张专抵制英国》,《顺天时报》1925年7月1日,见《史料外编》第69册第67页;《五卅运动》第2辑,第253页;郭廷以编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1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9年,第906页。冯在1925年7月,表示欢迎日本人来帮助他开发西北,并称准备派10000名中国学生到日本去学习。见Chinese Warlord:The Career of Feng Yu-hsiang,pp.154-155,179,290。)
为了使“单独对英”策略运用成功,执政府对群众运动给予实质性的援助。6月26日交通部电政司通令要求“交通界同人,各捐本月份薪水之三十分之一”。英使为此特照会外交部表示抗议。同日,交通部又准教育部转来之北京学生联合会呈请,发给准备赴四处串联进行“长途演讲”之学生免票,并电各地军政长官请其查照办理。(注:《英国使馆关于交通部电政司所属人员募款接济上海罢工工人事致外交部照会》,1925年10月1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第278页;《交通部致张作霖等电》,1925年6月26日,《中华民国资料丛稿·电稿·奉系军阀密电》第2册,第179-180页。)7月23日,段祺瑞、吴光新、沈瑞麟等人在北京接见来京游说之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代表俞国珍、吴芳、郭寿华、邵华等人,对代表所提要求“极表同情”。段并称已电上海总商会,先行维持罢工工人,政府即筹款汇沪,以保安宁。(注:《段执政与沪代表之谈话》,《顺天时报》1925年7月24日,见《史料外编》第69册第202页。公共租界警务处亦得到政府在7月中旬后两次汇款到沪的情报。(见《五卅运动》第2辑第306、361页)这两笔汇款加上6月11日国务会议议决之10万元拨款,总数是25万元,与李健民的统计相吻合。(参见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运动》第158页)执政府的拨款举动固然与各民间团体的催促有关,但是请愿要求兑现时机的把握也反映了政府当局的对英施压策略的实施步骤。)执政府对群众运动的支持立场为外界所洞悉。英国方面在获悉中国政府让学生免票四处串联演讲的情报后,坚信执政府与排英运动的煽动有密切关系。7月14日,日本公使在谒见段祺瑞时,也认为“中国官宪于禁阻暴行中,对于民众运动有加以保护及经费援助之情形”。而英国《泰晤士报》更坚定声称“罢工能持久,由于中国政府拨款资助”。(注:朱兆莘关于英外相谈论中国现状电》,1925年7月23日;《外交部关于日使提出八项请转达各使馆电》,1925年7月24日;《朱兆莘致外交部电》,1925年6月20日。以上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第181、271页;另见British Documents of Foreign Affairs,p.186。)
不过,在反英这一点上,张作霖与冯玉祥的态度无疑有巨大区别。冯在苏俄支持下竭力反英,(注:James E.Sheridan.Chinese Warlord:The career of Feng Yu-hsiang,pp.157,168-173.)张则对反英运动不太赞成,倾向于压抑群众运动。张到天津后,训令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对于沪案无论发生如何暴动行为,即请采取适当方法,预为禁止”,如有意外,均由其本人担负责任;并表示自己“现驻津埠,万不能使地方治安有所动摇”。是故,当地军警严禁学生与市民到租界演讲游行,并派兵在英租界工部局门前守卫。6月18日,张学良也在上海发布通告称:“公众所提各项要求已提交谈判会议,务望各位静候和平解决。凡假借某工会或联合会所赋予权力,扰乱治安或危害外侨生命财产者,均将依法惩办。”该布告似乎是应上海外人的要求所发,目标直指上海总工会与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张学良离开上海前,调徐州奉军第一旅邢士廉部来沪驻扎也与上海领事团要求有关。(注:《大公报》(天津),1925年6月7日,转引自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五卅运动在天津》(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82页;《五卅运动在天津》第163页;《五卅运动》第2辑第218、215页。)
上海交涉失败后,奉张与执政府间在沪案交涉及群众运动的态度上分歧加大。张作霖反对向列强提出修改条约一事,对交通部、教育部给学生免票待遇和鼓励其到各省演讲更不表赞成。张作霖还电令奉天省长王永江“饬就地军警一体注意监视”。王随即电奉省各县知事,表示“此种行动是使国内无一片安净土也”,下令“无论何方、何机关护照信件,由外处学生带来奉省煽惑者,一律禁止;如不服,即押送山海关内,不准境内容留一人。”王并将此意电告执政府交通总长叶恭绰,表示“沪案发生,奉省自有特见之主张,未便任外来人到此讲演。”(注:《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1册,第908页;《张作霖致王永江等电》,1925年6月27日;《奉天省长公署致各县知事电稿》,1925年6月27日;《王永江致叶恭绰电》,1925年7月4日。以上见《中华民国资料丛稿·电稿·奉系军阀密电》第2册第180、182-183页。)同时,天津警察厅亦严防各界联合会之大游行及运动罢工、罢市。直隶省长李景林下令严查“多方煽惑”之“乱党”,并取缔“共产主义者”。(注:《五卅运动在天津》,第169、225-226、244页。)
7月23日,就在段祺瑞于北京会见上海学生代表并鼓励有加的同时,驻沪奉军却突然封闭工商学界联合会与中华海员公会俱乐部、洋务工会等团体。淞沪戒严司令邢土廉布告宣称:“正义理应维护,姑息足以养奸”,“嗣后无论何种团体,务须认清题目,沪案交涉为一事,而利用机会自便私图者,又为一事。总之题目以内之事,行动不加干涉,题目以外之行动,即属越轨。”其原因似为工商学联合会有传单散发,直指“奉系军阀”与“英日帝国主义”勾结压迫爱国运动,同时也与英国驻沪领事之再三要求有关。(注:《驻沪奉军镇压罢工团》,《顺天时报》1925年7月25日;《沪七团体被封风潮和缓》,《晨报》1925年7月26日;《上海海员公会业已启封》,《益世报》1925年7月27日。以上见《史料外编》第69册第206、211、222页。)李景林亦于7月27日在天津以各界联合会“有逾越范围之事实”为由将其查封。(注:《五卅运动在天津》,第169、225-226、244页。)
执政府对邢氏此举,显然没有准备,上海三团体被查封后亦未接邢氏报告,惟有请江苏省长郑谦迅速查复。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代表邵华等人即到执政府请见段,要求惩办邢士廉,并将被封团体一律启封。邢后来因海员态度强硬,可能引起严重反弹,故将海员公会启封,对工商学界联合会,认为其并未立案,“应查明所发不稳传单,并须奉张电复核办”。(注:《上海两团体被封后》、《上海形势已渐见和缓》,《顺天时报》1925年7月27日,见《史料外编》第69册第220页。28日,邢奉令将工商学联合会启封,亦可能是受段祺瑞态度影响,或由于张寿镛、虞洽卿等人的调停。参见《上海海员公会业已启封》,《益世报》1925年7月27日,《史料外编》第69册,第222-223页。)同时,奉系并且有将沪案交涉之主动权转移其手之迹象。(注:邢士廉曾向英领表示愿意负责在沪先行磋商沪案先决各条。见《邢士廉在沪接洽沪案》,《顺天时报》1925年7月30日,《史料外编》第69册,第237页。)这自然不为执政府当局所乐见。
五 关税会议的召开与五卅运动的压抑
执政府对五卅事件之运用主要是想借外交来增强其自身凝聚力,此种政治性运用的主要落脚点则是关税会议的召开。关税会议不但能直接加强执政府,而且会议如果成功,必会因新税则或公认的附加税所造成的收入增加而延长其政治生命。(注:参见莱特(Stanley F.Wright)《中国关税沿革史》(姚曾廙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458页。)
按照1922年2月华盛顿会议所签订《九国间关于中国关税税则之条约》第2条,关税特别会议应于该条约实行后三个月内,由中国政府指定日期、地点,在中国开会。第10条又规定,该约将于1925年8月5日即该约批准文件全部交到华盛顿之日发生效力。然由于法国政府藉金法郎案而迟迟不通过华会条约。直到1925年4月执政府与法国换约承认金法郎案后,此事方提上日程。但对于关会的召开,各相关国在五卅前态度均不明朗,舆论不断有以“外债与悬案”之解决为前提的说法。(注:《国际条约集(1917-1923)》,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第769-772页;《关税会议之难开》、《关税会议九月召集讯》,《申报》1925年5月18、20日。关于华盛顿会议上对中国关税问题的讨论及决议可参见金光耀《顾维钧与华盛顿会议》,载《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第28-32页。)
沪案发生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使列强深感不安。中国政府单独对英的策略更引起英国的紧张。当时有舆论认为关税会议久延不开,是中国排英风潮兴起的重要因素。故英政府似有意以关会为条件促使执政府压抑反英群众运动,并“力催”法国政府批准华会条约。(注:《收驻英朱代办(莘)电》,1925年6月26日,《排日问题》,第492页;《朱兆莘致外交部电》,1925年6月9日;《朱兆莘报告英政府对谈判条约不表态电》,1925年7月1日。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民众运动)第123-124、176页;British Documents of Foreign Affairs,pp.186,194,240。6月16、19日,英代办曾两次警告北京外交部注意排英举动。(见《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1册第896-897页)而在中国南方,因省港大罢工及广州政府对英之经济绝交使英国利益遭受重大打击,故英政府欲在关税会议上让步,以换取执政府取缔排英运动。参见刘彦《最近三十年中国外交史》(太平洋书店,1930年)第165页。)美国政府因五卅一案的冲击亦在重新考虑对华政策,对于关会态度趋于积极。(注:《北京6月10日路透电》、《收驻美施公使(肇基)电》,《排日问题》,第467-469页;参见王立新《华盛顿体系与中国国民革命:二十年代中美关系新探》,载《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63-64页。)7月7日,法国上下两院将条约完全通过,关税会议的举行从程序上来看已无问题。
执政府催开关税会议固然是因为财政久陷困窘之境,借关会的召开达到增收“二五”附税之款项。不过其目的其实并不仅仅在此。在沪案交涉与五卅运动发生后,政府便想利用此机会扩大关税会议之讨论范围,提出关税自主案,并增加华盛顿会议所定附加税额。(注:《来源枯竭之北京财政》,《申报》1925年8月23日;武育干:《中国关税问题》,转引自中国史学会等编《北洋军阀(1923-1928)》第5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第64页;《颜惠庆日记》第2卷,第238页;凤冈及门弟子编《民国梁燕孙先生士诒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910-914页;《外交部关于日使提出八项请转达各使馆电》,1925年7月2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民众运动),第181页;《关税特别会议委员会关于会议经过概要电》,1926年5月1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财政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311页。)是故,如果说关税会议之召开是五卅案前即已预定者,那么会议之内容及中方之条件则与五卅案有密切关系。执政府实际上藉五卅交涉之机力图改变关税会议的内容。(注:梁士诒后来称,执政府对关会“欲争回主权必求达到关税自主之目的,如其不能达到关税自主则惟有决裂闭会”。(《民国梁燕孙先生士诒年谱》,第931页)颜惠庆在就任外交委员会委员长后亦有所渭“治标治本”说。“治标者,系就沪案而言,似即执政钧令内指明之交涉事宜,外交部所提出之办法十三条是也。治本者,系就修正条约而言,可以息嗣后一切纷纭之变,似即钧令内指明之善后事宜,外交部所提出之修正条约是也。”参见《颜王蔡何故为变相之辞职?》,《晨报》1925年7月3日。)
为了对列强施加压力,6月24日,北京政府在发出关税会议请柬的同日,即照会各相关国提出修改条约之要求,并动员驻外公使游说各国认可修订条约。(注:《朱兆莘报告英政府对谈判条约不表态电》,1925年7月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民众运动),第176页。当然此举亦可能为一虚招,一方面在应付民意,而另一方面则想以此促使列强在关税会议问题上做出让步。是故英公使白慕德在向本国外交部报告中曾表示,中方对所提修改不平等条约一事暗示不要太认真。参见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运动》第182页。)30日,美国国务卿凯洛格(F.Kellogg)在会见中国驻美大使施肇基时表示支持中国的修约要求,并敦促其他列强。(注:参见王立新《华盛顿体系与中国国民革命》第64页;孔华润(Warr I.Cohen)《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中美关系的历史剖析》(张静尔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98-99页)。7月17日,美政府照会华会签约各国及瑞典、丹麦、西班牙、秘鲁,建议从速召集中国关税会议,并派遣法权调查委员。见《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1册第907页。)然英政府对谈判条约一事开始并不发表态度,尽管其民间有同情中国之“十三条”要求及修改条约的呼声存在。7月中旬,英政府对中方提出扩充关税会议范围的要求似有接受之意,惟表示须以“中国排英风潮终了为条件”。(注:《朱兆莘报告与英友人密商十三条解决办法电》,1925年7月28日;《朱兆莘关于英美法日讨论对华方针》,1925年7月16日。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民众运动),第182、180页。)为应付此种要求,执政府通电各省,表示“沪案骤起,各省人民奔走呼号为政府之后援,期外交之胜利,良以爱国、爱群具有同情,举动不越范围,自不得加以抑制。”但是如有“假托名义,阴险煽惑,实行其破坏主义”,则“务应妥筹防范”。司法部亦有“严防过激办法”四条拟定,并通令各省遵行。7月24日,内务部又有“严防共产运动”的密令。(注:《五卅运动在天津》,第254-265页;任建树、张铨:《五卅运动简史》,第259页。上海交涉中止后,执政府对苏俄“赤化”问题其实已有注意。见《收上海朱锡麟等函》,1925年7月2日,《排日问题》,第521页。)这些命令的发布虽然有警惕苏俄势力的用意,但也未尝不是在敷衍各国,与执政府对群众运动的支持并不矛盾。8月5日,九国代表在华盛顿就九国公约及关于中国关税之九国公约交换文件,条约始发生效力。18日,北京政府照会各国派员参加定于10月26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关税特别会议。(注:孙曜编《中华民国史料》,第681-682页;《颜惠庆自传》,第143页。执政府在送出请柬前,曾经阁议反复讨论,决定应根据华会我国有完全主权之原则,正式向各国提议将关税会议范围扩充,俾得讨论修改条约中之恢复中国关税完全自主问题。参见《关税特别会议史》第75页。)26日,英国公使照会中方,奉其政府令赞同中国政府邀请参加关税会议,意大利、荷兰、比利时、日本等各国亦先后表示赞成。28日,国务会议通过并公布关税特别会议委员会所拟章程。9月8日,沈瑞麟、梁士诒、颜惠庆、李思浩、王正廷、叶恭绰、黄郛、莫德惠、蔡廷幹、姚国珍等人就任关税特别会议委员会委员。(注:《政府公报》第3402号,1925年9月20日,第15页。)
当关税会议的召开即将成为事实时,执政府对群众运动便开始进行实质性的压抑,与奉张之态度趋于一致。8月6日,驻京英使馆工人罢工。虽然沈瑞麟在答复英方质问照会时曾表示“工人与使馆系雇佣关系,进退为私人之自由,政府未便制止”,但英使馆华员公会准备组织游行却被警方禁止。同时,警厅发布告示,严禁工人同盟罢工及“煽惑者”,以“维持首都秩序”。(注:《驻京英使馆工人罢工》、《昨日英使馆罢工华员招待各界》,《益世报》1925年8月7、10日;《警厅禁止英使馆罢工华员示威》、《警厅严禁罢工及煽惑者》,《顺天时报》1925年8月13日。见《史料外编》第69册第262-263、273、288、289页。)8月11日,李景林在天津以强力镇压裕大纱厂工潮,12日,驻津奉军更调兵包围该厂工会,据称工人被杀者二十余人。各界联合会、天津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等均被查封,工会、学生领袖受到通缉。李景林还呈请执政府下令取缔工潮。(注:《五卅运动在天津》,第254-265页。)20日,段祺瑞批复李景林呈报镇压天津工潮电,通令保护工业,取缔煽惑罢工,“嗣后各省区遇有假借号召罢工情事,应责成各该地方长官严切制止,其行凶抗拒者即当场捕拿,尽法惩治。”(注:李振华辑《近代中国国内外大事记(《民国十三年至十六年)》,第4754页;《中华民国资料丛稿·电稿·奉系军阀密电》第2册,第186-187页。)执政府秘书厅亦饬令江苏省长郑谦,认为上海总工会为非法团体,应予立即解散,通缉李立三等人。邢士廉即以此命令,迅速查封总工会。(注:《五卅运动》第2辑,第481-482页;《沪总工会忽被解散》,《益世报》1925年9月20日,见《史料外编》第69册第347页。执政府此时的态度与以前对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及上海总工会地位的默认亦成一鲜明对照。盖团体是否“非法”,政府并不是现在才清楚。执政府不在这些团体开始活动时予以禁止,到利用已尽时才施以打压,可清楚看出其对民众运动的政治运用。)到8月底,强硬派在执政府国务会议上无疑已占据上风,(注:据《申报》消息,在天津裕大风潮发生后,政府当局有多次会议,认定为共产党在其中活动,而“某某两总长之主张,较之章行严(教育总长章士钊)尤为强硬”。其要点认为“学潮及各地爱国运动,多有人从中利用,实含有党派意味,而非单纯人民之呼号”。见《政府将严厉取缔爱国运动》,《申报》1925年8月31日。)26日,执政府发布“整饬学风令”,表示“自后无论何校,不得再行借故滋事……倘有故酿风潮,蔑视政令,则火烈水懦之喻,孰杀谁嗣之谣,前例俱存,所宜取则。”(注:孙敦恒、闻海选编《三一八运动资料》,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3页。)与此前对学生运动之支持态度形成鲜明对比。执政府对“民气”的战略运用至此实际因目的基本达到而告一段落。
9月19日,各校沪案后援会正在筹备次日召开天安门国民大会,段祺瑞饬令严厉制止,并对负责北京治安之朱深与鹿钟麟两人表示:“今后对于无论学生市民集会,一律禁止……如有反抗,依法取缔。”鹿钟麟对此表示“惟执政之命是从”。20日,北京各校及各团体门前均有军警严密防守,保安队则驻扎于中央公园等处,禁止行人通行,没收种种旗帜,在军警的全力弹压下,“震动京国之国民大会,竟同雪化矣”。(注:《明日国民大会将被干涉》,《益世报》1925年9月20日;《昨日各界示威大扫兴》,《顺天时报》1925年9月22日。见《史料外编》第69册第345、350页。《段祺瑞禁止爱国运动》,《政治生活》第52期(1925年9月23日)。不过,可能鉴于国民军的态度,此次阻止国民大会的召开,手段尚称和平,未以武力对待学生及民众。这与奉军在天津的武装镇压举动有明显的差异。)对“段政府的机智巧妙,置全国人民于掌握之上,任意玩弄”,中共方面无疑非常愤懑,表示“五卅惨杀唤起了中国民众向帝国主义猛攻的势力,因此政府藉此得著了开关税会议的好处……民众反倒是在此时是他们的眼中钉”,又称“这是段祺瑞希望在将要开的关税会议席上,多得到帝国主义的宠爱之必有的前提”。(注:士炎:《沪案解决与段祺瑞政府》,《政治生活》第54期(1925年10月7日);《仅反对沪案重查就够了吗?》、《告工农兵土学生》,《政治生活》第52期(1925年9月23日)。)
随着执政府的态度发生变化,上海罢工运动也正渐渐进入低潮,罢工经费无以为继。(注:参见《五卅运动》第2辑第362、438页。)7月底,上海总工会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已有“适时停止罢工”的倡议。俄共中央政治局乃决定“有组织地脱离罢工斗争,最大限度地巩固业已取得的成果”,并向指导中共工作的维经斯基(Voitinsky,Grigori)等人发出指令,上海罢工运动开始紧急“刹车”。(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第643-646页。)8月10日,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发表《告全国工人兵士、学生》书,正式提出改变罢工策略,以工人的经济要求和地方性质的政治要求为复工条件。(注:《向导》第125期(1925年8月18日)。)从8月25日到9月30日,上海各业罢工工人陆续实现复工,五卅运动至此基本结束。沪案交涉也因关会的即将召开而陷于冷却状态。9月15日,领袖公使荷使欧登科(W.R.Oudendijk)照会中国政府,正式提出重行司法调查,希望中国亦能予以赞同,中方即复照表示坚不承认,但使团决定司法重查仍然进行,尽管后来它几乎成为一个单方面的行动。政府既不愿意在此问题上再激动民气,而又不愿意对重查表示配合,惹起民众之反弹,所以基本上是默不作声了。
12月23日,重查报告发表,工部局致函中方,表示已核准总巡麦高云、捕头爱活生之辞职,并以75000元作为抚恤被难者家属之费。(注:参见孔另境《五卅外交史》第70-71页。)从其立场来看,似乎意味着沪案交涉到此结束。但正在关税会议上与各国讨价还价的执政府对此结果则不予承认,外交部还训令许沅将工部局之抚恤“五卅”难属的支票退回。(注:参见《五卅事件》第70页。)此后,沪案交涉便成为悬案,虽然在1926年4月执政府结束之前,还有几次催促开议的照会给使团,但最终除了会审公廨的谈判与工部局华董问题有所进展外,其余条件便多湮没于累累的外交公文之中。
五卅事件后所爆发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实际上是受到内外两股力量的牵引作用。苏俄对运动的扩散及收束有着重大的影响力,(注:关于苏俄与五卅运动的关系可参考《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550-551、628-648页;亦可参见杨雨青《五卅运动的收束与“首都革命”的发生》,载,《北京党史》2000年第3期;周利生《维经斯基与五卅运动》,载《北京党史》2002年第2期。)而执政府的力量也隐于群众运动的发起及展开之中。
五四前后中国外交似有重大变化。一方面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摆脱了“软弱外交”的窠臼;另一方面便是政府在对外交涉中更多地有意识地利用“民气”,即所谓“国民外交”勃然兴起。五卅运动中,这种趋向似乎达到一个高峰。沪案发生后,如果没有执政府的宽容与支持,不可想象,五卅事件如何能被激荡成如此规模庞大的一次群众运动。
执政府在初期交涉中对民众运动的利用,表现极为明显。一方面在上海支持工人罢工,一方面在全国造成民众抗议运动。民众运动紧松之调节与执政府之态度有密切关系。外交上,执政府则做出强硬的姿态,显示出对外不妥协的形象,并迫使强势军人在政治问题上暂作让步,政府亦得以在派系均势上保持其地位。沪案交涉移京后,执政府将重点转在单独对英策略的执行上。政府以实力支持反英运动的展开,将民众运动的压力释放出来,并与南方国民政府的反英运动相互呼应,最终亦影响了英国对华外交政策的改变。
然而,在列强答应关税会议的召开时间以及对其范围改变的认可后,执政府随即采取了与前面不同的态度,对民众运动进行严格的抑止。9月以后,不仅在上海,而且在其他地方民众运动便在强力的压制下趋于萧条。五卅运动期间,国闻周报社社长胡政之曾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大凡新政治家不贵能散动群众,而贵能节制群众。盖能发能收,乃可得群众运动之实效。否则五分钟热心本为任何群众运动普通之现象,非事过境迁,毫无效果,即意气所激,反生枝节,二者均有规律有计划之群众运动所宜有。(注:冷观(胡霖):《群众运动与节制》,《国闻周报》第2卷第23期(1925年6月21日)。)在这一点上,执政府似乎是深谙其道。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执政府政治策略运用为一面,其成效则为另一面,后人在评价时,不能因为其最后仍倒台而忽略其政治表现。至少从延缓其政府的死亡时间上来看,便是其政治运用的成功。如何在各种军事势力间踩平衡木,是需要高超的政治技巧的,这方面,执政府的表现并不算差。
以往讨论群众运动者,往往将注意力集中于党派运作与民意表达,而忽视政府运作的一面。实际上,从民初的历史来看,没有政府的容忍或者支持,群众运动往往是难以得到大规模的发展的。以往学界多认为五卅运动的形成,是由于民众的热情推动与党派力量的操作,是因为其多关注“群众运动”的表象、规模及群众自身力量的觉醒等等。除了站在前台的中共以外,对隐藏在群众背后的其他政治势力如何“运动群众”多较忽视。实际上,笔者认为政府与群众运动的关系实际上更值得研究,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同样有党派运动和民众热情,罢市、罢工等能在上海发动成功,而在许多地方则失败?五卅运动在地方层面具体模式的差异,应与政府及地方实力派的态度有较大关系。
以往研究五卅运动者之所以对执政府较为忽视,或者低估其在此事上的积极表现,可能与研究上的一些预设有关。如研究多从“革命史”的角度出发,认定群众运动必然是有强大的真实民意基础,对“军阀”的负面评价亦成为一种定式。因此,研究者可能会对五卅运动中段祺瑞及执政府支持运动的史料避而不用,以免与“军阀”惯有解释框架相悖。(注:惯常用“军阀”概念框架来叙述北洋政治,其实太过于简约而不能洞悉其丰富面貌。关于“军阀”概念及“军阀政治”框架在民初历史研究中应用及批评,参见冯筱才《“军阀政治”的个案考察:卢永祥与1920年代浙江废督裁兵运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台北)第19期(2002年5月)。)但是这样一来,研究者描述出来的历史图景与实际的情形可能便有相当大的落差了。
政府运用民气来打压外人,此例不鲜。较早的1905年抵美运动,从一开始即有清政府之暗许与支持在其中。(注:参见张存恭《光绪卅一年中美工约风潮》(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第28-72页。)到1915年二十一条交涉,袁世凯政府故意运用民意来为外交助力,手法已至为明显。(注:参见吕慎华“袁世凯政府与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台南中兴大学历史学系硕士论文,2000年;亦可参见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62、69页。)五卅运动中,执政府更是将此一策略运用得炉火纯青。所以在近代中国,群众运动从来就不是单纯的民意表达,它不仅是在野政治势力的工具,其实也经常是执政当局的工具。忽略“民众爱国运动”背后此一重大力量,就无法理解近代中国群众运动的复杂内涵。正因为群众运动往往成为政府的工具,所以当政府的利用目的达到,群众利益的被抛弃便将成为可能。这种情形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似乎屡见不鲜,甚至成为近代中国政治的一种传统与特色。
附识: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罗志田教授、汪朝光研究员的帮助,后复蒙匿名审稿人惠赐宝贵意见,谨此致谢。惟文中观点仍由作者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