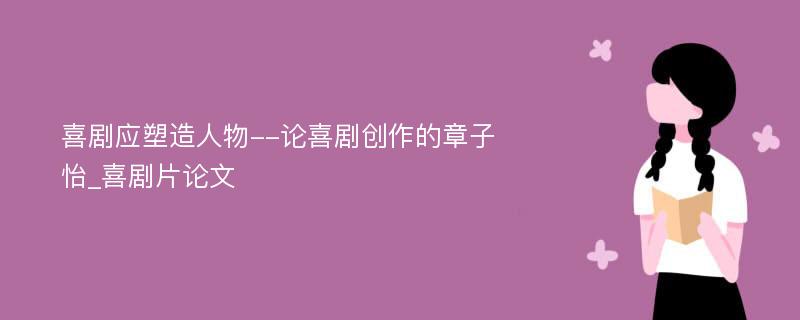
喜剧要塑造人物——张子恩谈喜剧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喜剧论文,人物论文,张子恩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受访:张子恩
访问:东耳 本刊记者
东 您的几部清朝电视喜剧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是您预料中的吗?
张 《宰相刘罗锅》的社会影响之大是我始料不及的。北京的收视率超过48%,在上海高达50%。我到新疆拍电影《白马飞飞》的时候,新疆少数民族地区一个很小的县城独山子是我们的外景地,我们在那里吃饭,旁边的人就在议论《刘罗锅》怎么好,那儿的牧民都知道刘罗锅。在深圳,那里从来不看内地电视剧,他们一般都看粤语片,但在播种《刘罗锅》时,万人空巷,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可以说东南西北的人都愿意看《刘罗锅》。美国、加拿大的华人打电话来说喜欢这部电视剧,看过好多遍,而且大家都在传看或买电视剧的录像带,当时我们国内还没有录像带,美国已经有了。法国也是这样。新、马、泰的华人也愿意看。台湾的电视台就播了5次,是空前的, 因为即使是他们自己的戏也没有连着播5次的。
《康熙微服私访》在国内的收视率高达38%,有的地区达到40%多。在台湾也火得不得了。一个台湾电视台的副导演说:张导,你现在在台湾红得不得了,虽然你没有去台湾,但你的名字在台湾的影响很大。台湾导演李行后来对我说,从《刘罗锅》以后,“张导,你该忙起来了”。
《刘罗锅》拥有这么多的观众在过去是不可能的,可以说大部分电视剧没有像《刘罗锅》拥有这么多的观众。尽管我的戏不宣传,也很少有人知道我,但我感觉观众是知道的,到哪儿只要一提《刘罗锅》,人人都知道,说明观众的数量是非常大的。而且港台和美国、加拿大、东南亚的华人地区,对这个戏入迷得不得了,这说明中国文化本身是相通的,文化传统是一样的,并不是说我们社会主义文化就不能打动人,只要你做得好看,做到雅俗共赏,就都能看。《刘罗锅》对我的启示就是这样,电影、电视剧没有很严格的国际性。
东 从您的外表看不出是搞喜剧的,可您拍了不少喜剧,都很有观众。
张 我这个人特别不苟言笑。比较喜欢中国文化,看了很多历史的书,在西安这片土地上受黄河文化的影响比较大。西安出了很多电影导演,跟我们受到的文化积淀有关。另外,我这个人比较内向,笑也得想我为什么笑,笑之后怎么样。我喜欢相声,喜欢侯宝林、刘宝瑞的相声,在幽默这点上我受他们的影响和启发。特别是侯宝林很棒,几年前曾经有人想拍侯宝林传结果没拍成,这很可惜。另外,我特别喜欢卓别林,收集了他所有的作品,经常看,每看一回,就笑一回,百看不厌。人家总觉得我们中国人没有喜剧细胞,像我似的,不苟言笑,其实,中国人是很懂喜剧的,可惜是没有人做而已。中国人本来生活中就老板着脸,对笑反而容易接受,因此喜剧的观众也更多,尤其年纪大的,再让他悲悲凄凄,是不愿意的。《刘罗锅》和《康熙》为什么有这么多观众,原因就在这里。
生活很苦,需要更多的笑,需要笑声、需要动作来刺激生活。武打片为什么兴盛一段,就是这个道理。影视是比较擅长表现动作的。另外,人都有一种想发泄的心理,由于道德和社会责任的约束,压抑心理欲望,所以只有借助动作片发泄。就像人喜欢看足球赛,一方面是足球本身的魅力,另一方面是喜欢那种氛围,到那儿可以放声地叫喊、大骂,可以哭,可以笑。这是一种调节人的心理的方式。
我一开始就比较注重雅俗共赏,寻找商业娱乐和艺术的交叉点。从《神鞭》开始到《刘》到《康》走的都是这个路子。但这两年电影没有观众了,只有做电视剧。所以在《神鞭》之后我主要探讨商业娱乐和艺术的交叉点,在电视剧上实际做的也还是寻找艺术和娱乐的交叉点。逐渐对动作、武打、血腥厌倦之后,我觉得这个路子在商业娱乐题材上只是一个方面。悲剧容易震撼人,给人很多力量,但是娱乐性比较差。人不能老看悲剧,老流眼泪,人们更喜欢笑,更喜欢动作、激烈的东西。从这点看喜剧就比较容易达到雅俗共赏,更多的城市观众喜欢看喜剧。喜剧的前途非常大,在电影和电视剧上是长盛不衰的。
东 您觉得目前中国影视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张 我觉得电影跟电视剧说到底就是个商品,是一个娱乐的东西。娱乐的形式过去有一段是武打片时髦,所以我也拍了很多武打片,后来香港人搞笑武打,就是把喜剧跟武打结合在一起,这又增加了一种新的形式。我们现在老把电影放在一个教化的位置上,是不行的。我们中国影视始终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娱乐的问题。为什么电影不卖座,因为它不好看。应该把好看放在第一位。好看只是一个包装,不是一个实质。实质还是你的思想。港台电影很注重包装,但他们忽视思想,思想是我们的长处,我就希望把这两点结合起来。美国电影做来做去,实际上讲的就是美国精神,人道主义,但它的包装始终是好看的。电视剧同样,也需要好看。《刘罗锅》这种喜剧是一种好看的形式,武打片是一种好看的形式,破案片也是。我在最近拍的《风雨一世情》里把悬念弄得很强,故事弄得很曲折,同样也是好看的一种形式。其实这些年我不断探讨的就是怎么接近观众的问题。
东 您理解的喜剧是什么样的?
张 我觉得中国的喜剧传统很好,从过去的十大喜剧直到现在的相声,这些都是喜剧延伸下来的各种各样的形式。我想,喜剧第一条件要喜,要喜得起来,能逗人乐,要让人高兴。第二个条件要成为剧,有一定的规模,有很完整的剧本,有很大的演员班子,这才能成为剧。小品也变成喜剧我觉得不合适。情景喜剧严格来讲不能算是喜剧。比如莎士比亚的戏,它得有多少幕多少场。喜剧得有一定的规模,三分钟两分钟也算喜剧?我觉得不能,不成其为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几年我拍的这些戏,比如《刘罗锅》是宫廷寓言式喜剧,《康熙微服私访》是以皇帝作为题材的喜剧。我最反对外在的那种愣是胳肢观众的喜剧。
《康熙微服私访》的喜剧核是在故事结构本身,点子出来以后,戏本身就带有喜剧的因素。比如皇帝到民间,可能变成了乞丐,变成了一个药铺掌柜,或一个买紫砂壶的商人。地位的变化,环境的变化,人物关系的变化,就会产生很多喜剧因素。故事结构本身决定了这是一个喜剧,而不是用一些表面的摔跤或逗乐的语言去解决这个问题。台词和动作只是一方面,要在故事结构本身去找喜剧因素,这样才能把喜剧做得让观众喜欢,有一定的规模。文化的这种素质也是喜剧里很重要的内层的东西,不能光看到逗笑这一点,在笑之余还要给人一些启示。
现在的喜剧大多停留在表面,在小品的基础上再发展一下,就冠上一个喜剧的头街,这个不对。喜剧首先要有一个界定,到底什么是喜剧?刻画喜剧人物是喜剧的关键。像《康熙微服私访》里不但刻画皇帝,还刻画了很多三教九流的人物。这些人的地位跟皇帝地位的悬殊,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喜剧性。
东 您的喜剧里冷幽默的东西比较多。
张 我感觉电视剧跟电影的喜剧最主要的问题还是一个冷幽默的问题。我从《神鞭》开始就是用冷幽默的办法,就是要挖掘人物内在的幽默的东西。《神鞭》是我自己根据冯骥才的小说改编的。《神鞭》就是用幽默用喜剧的形式去讲历史,讲八国联军对我们的侵略,它采取的是黑色幽默的形式,看完以后觉得很有意思,而且笑能保持长远。比如玻璃花到外国大使馆时,我用了一个长镜头,表现这个表面上非常横的混混儿,可到了洋人面前就变成了一个特无知的人,见了沙发、洋雕塑、裸体画都非常新奇的喜剧性动作,把这个人物在这个特定环境里的感觉表现出来了,传达出来的这种感觉就比单纯寻找外部动作要深刻得多,给观众留下的笑容更隽永。他可以看完戏去回味,去琢磨,闭上眼睛一想还是沉醉在一种笑的意会里,而不是哈哈一笑就拉倒。中国人很喜欢听相声,如侯宝林的相声就有这个特点,当时包袱一抖你就会笑,听完之后回去一琢磨,又能领会出更深的意思,还会再笑,这就是真正喜剧的力量。如果笑料很表面,它逗留的时间就非常短,不可能隽永。
我在《刘罗锅》之后就更多地研究这方面的事,其实《刘罗锅》是沿着《神鞭》的路子走下去的,只不过变成了一个电视剧而已。《刘罗锅》跟《神鞭》很接近,都有黑色幽默的东西。黑色幽默的东西保持的时间非常长,不是很简单的一笑了之。我在《刘罗锅》的导演处理上加进了很多喜剧的因素,剧本里不足的地方、人物欠缺的地方,我都把它们往冷幽默上做。
东 喜剧是不是从全片的结构就要开始考虑?
张 是的,有些故事本身的形式也可能会造成喜剧,比如《珍珠翡翠白玉汤》。我就是把刘宝瑞的单口相声视觉化了,搬到荧屏上去,同时表现了刘宝瑞的一生。在20集的戏里有两条线,一条是刘宝瑞的生平,另一条是他的单口相声。单口相声里用演刘生平的主要演员,不少演员都扮演多个角色,比如方子哥演刘宝瑞,一会儿他变成皇帝,一会儿变成乞丐,不同的戏里演不同的角色,这本身就带有喜剧的色彩。再加上刘宝瑞的单口相声是经过千锤百炼的一种喜剧,很多笑发人深思。《珍珠翡翠》我把它叫做冰糖葫芦或珍珠串式的结构。单口相声的喜剧性同刘宝瑞人生的悲剧性互相映衬。
东 您对带有悲剧性的喜剧怎么看?
张 喜剧一般总是跟悲的东西联在一起,所以人们常说悲喜剧。喜剧最后深刻的内涵往往是悲剧性的。卓别林很多戏都是这种情况。我们也应该学习这种东西。《刘罗锅》的幽默和《康熙》的幽默不一样。《康熙》的外表多一点,《刘罗锅》是带有悲剧的喜剧,实际上它的喜剧因素是表现很悲的东西。喜剧在整个艺术中的地位不高,悲剧才是最了不起的,但人们更愿意看喜剧,因为悲剧太沉重。喜剧和悲剧需要互补、结合,任何艺术都是在对比而已。《康熙》的喜剧是轻松的,小细节多,在人物上没有太多的喜剧,康熙这个人物本身不是喜剧人物,三德子是。康熙是用喜剧的方式解决他的问题,如解决贪官问题,重视农业问题等等。每个故事寓意都很深。但外表只是用一个轻松的喜剧方式来叙述,实际上它不是一个喜剧的内涵。
东 您对喜剧演员是怎么界定的?
张 李丁老师跟我谈喜剧表演的时候,他特别强调能够塑造喜剧人物的演员才叫喜剧演员。卓别林在没有塑造人物的时候,只是插科打诨,地位很低,到他塑造了人物以后才成为一个喜剧演员。我们中国现在比较缺少特别棒的喜剧演员。喜剧演员得塑造人物,并不是说会出个怪相就成为喜剧演员了。他必须塑造人物,这个人物要非常圆满,非常有内涵。比如刘罗锅这个人物,他有很完整的个性,跟皇帝、跟和珅有各种各样的碰撞,这些碰撞以喜剧作为包装,内涵又是非常深刻的。比如像卓别林的《摩登时代》,表面上很滑稽,但内涵很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形成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很完整的人物,这才够得上是喜剧。
东 一般导演很难想到让李保田、陈宝国去演喜剧,您挑他们是怎么想的?
张 陈宝国是一个很好的演员。他第一次跟我合作的是《默默的小理河》,演一个不苟言笑的人物,后来我发现他很善于塑造人物,而且形体动作非常好,很会模仿,于是在《神鞭》我比较大胆地决定用他来演玻璃花,后来实践证明,他演得非常好。我拍一部戏起码要有一两个特别好的专业演员,这样能把群众演员带动起来,我基本上采取这种办法,比如《刘罗锅》里,王刚从来没演过戏,而且在主持节目时有很虚假的动作,让人烦他,特别是北京人特烦他,可是我想,这些在演和珅这个人物时就成了长处,令他演这个人物特别合适。再加上头发一剃,锛儿头特大,眼睛又大又往外鼓,造型上的特别也有助于成功。另外我拍电视剧用了很多拍电影的办法,用调度、镜头去弥补演员的表演。
李保田演的喜剧跟一般胳肢人的喜剧不同,他有品位,这个品位一个是跟剧本、导演的处理有关系,另一个与演员本身的素质有关系。李保田并不是演喜剧的,但他的那种冷幽默表现得很出色。不可能让李保田去演陈佩斯那样的角色,很外部的,用动作去逗人的,他演不出来,他只能演比较冷的,带有一种文化色彩的幽默的东西。李保田是一个很有文化功底的人,他非常执著,准备角色非常充分。最好的一点是他过去演过徽剧里的丑角,走路、摔辫子、撩袍子、起坐的动作都很有功夫,这是他演清装戏一个很大的优势。所以尽量挖掘、利用他的长处。李保田跟我还算谈得来,他有些什么想法,比较好的我就采纳。比如他在剧中穿着大靴子走得很滑稽,这固然有他本人形体的因素,还有音乐的因素,是影视综合艺术的结果,并不单单是演员演得多么好。他也许在另外一个戏里就演得很不成功,比如李保田在《鸦片战争演义》里,观众就对他很有意见。说明一个戏跟演员合拍了,它就可能造就这个演员,如果跟他不合拍,很可能砸了这个演员,使大家认为他一无是处,其实他是一个很棒的演员。一个演员必须在一个非常好的剧本里,在一个非常好的导演指导配合之下,才能做得好。
大部分记者和媒体有时一窝风地吹嘘某个演员演得不得了,其实他们不明白,这里头演员表演的天分其实只占一半,另一半是由其他很多因素如造型、摄影、导演镜头调度等加在一起造就的。并不是演员一个人如何能。比如葛优,是很好的演员,但他在《寇老西儿》里就很没光彩,一看特傻,他在《秦颂》里简直就像不会演戏的人。这原因就是剧本跟导演的处理。陈凯歌在拍《黄土地》时,把演员作为一个道具,这是推到了极致。但反过来说,演员实际上也是一个道具,当然他有自己的能动性,不能完全作为一个道具对待,但很大程度上有道具的含义。实际上演员表演的结果,是导演表演观的体现。你这个导演风格细腻或粗犷,内在或外露,调教出来的演员就不一样。演员演得很差还是很好,相当大的程度取决于剧本和导演的总体把握。剧本和导演的总体把握好了,演员才能把自己最闪光的东西放在那个位置上。
东 是不是任何演员都有可能在您的喜剧中扮演喜剧角色?
张 我是比较注重形体、外部造型的,首先造型要符合我脑子里想的这个人物。外表如果接近了,而他又是很好的演员,导演就会很省劲儿,一说他就明白。你不说的他也能给你演出来,给你添彩儿。很次的演员可能就比较费劲,但是总体上如果剧本写得很合适,我们又能找到很合适的细节,也许不会演戏的人也可能成为一个很好的演员。比如《康》里卖官的长得很丑的斜眼,根本不会演戏,是个群众演员,但他符合了这个人物,就会给人演得好的印象,其实他完全是一个外行,当然这种可能性不多。不过很重要的角色不可能用一个外行演员,还是尽量要找专业的演员,像李保田、张国立、王刚,应该说素质都很好。
王刚虽然不会演戏,但他有比较好的文化底子,能理解这个人物,所以在有的时候就可以指导他去做。比如和珅正在喝茶,外面来报告,嗓门很大,他呼地一下吐出一口水,这实际上是导演给的,我说你吐,冲着镜头吐,这个镜头就很有效果。当然王刚也非常用功,他回去看剧本,经常能提出一些想法或方案:“导演,我想这段台词这么排一下……”他经常跟我商量,比如坐马桶那场戏,就是我跟他沟通以后,商量怎么表现时,他提出来的。还有和珅嗑瓜子把皮吐到盘里的动作,做出的那种姿势也是一种现场感觉。因为和珅非常善于拍马屁,阿谀奉承特别在行,我在拍这场戏时要求他做出一种媚态来,他顺便做了一种京剧里的动作,我一看这动作很好,就用上了。
李丁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他是真正的喜剧演员。他曾是苏联专家训练班里的高材生,后来被打成右派,流落到青海,在生活方面有非常多的积累,他对北京文化又了解得很深刻,所以他的六王爷演得特别好。他的戏很多东西是他自己设计的,比如“皇上圣明”这句台词,他每次说的都不一样,节奏、眼神、动作都不同,这是一般演员做不到的。他对剧本里的规定情境理解得很深,现场拍的时候就跟导演交流,他的戏虽不多,但是特别出彩儿。他在《慈禧西行》里一场最精彩的表演在播出时给剪掉了,他把一大段有两三分钟的台词说得精彩极了。在《风雨一世情》李丁演一个城府很深,很善良、很有文化功底的人,这次表演他基本上是闭眼睛,说话老不看人,这是他的另外一种设计。他琢磨人,塑造人,总是很能把握剧本里最精华的东西,即人物身上最精彩的东西。他经历复杂,艺术造诣非常深。而且经常提携别的演员。我觉得喜剧演员主要得塑造人物,并不是会插科打诨就是喜剧演员,我不认为一些很外表的东西是可以称为喜剧的,比如摔蛋糕,并不是说卓别林就这一招,他还有更内涵的东西在里面。现在很多演员只是学习他的皮毛,那是不对的。
东 张国立最早演《顽主》时不太幽默,可是在《刘罗锅》里他却特别出彩儿。
张 原剧本里乾隆写得不好,没有个性。后来我就强调这个人物城府很深,贪官、清官他都用,和稀泥搞政治平衡,是他的特点。根据这个认识给他加台词,使得他在三个人之间的分量加重了。导演对剧本写得不够的人物有时还要加细节。比如和珅用手绢接皇帝的痰然后掖起来的动作,就是我给加的,我感觉和珅为取得皇上的信任必须有超乎常人的动作,这种动作就使人物一下子出彩儿了。又如和珅用餐,拍马屁的管家把虾剥了皮递到他嘴里,这也是原本剧本没有的,剧本里只写了和珅吃饭,但怎么吃就看导演如何处理。不少细节都是导演处理时想到的。
东 您作为一个导演,是如何用镜头来挖掘喜剧因素的?
张 喜剧的细节有时是用镜头来体现的,而不是演员表演出来的。喜剧首先是结构、内涵,最重要的是人物,这个人物可不可能成为一个喜剧人物。人物要塑造得很有喜剧色彩,包括外在和内在两个方面,外在的形体动作都要带有喜剧色彩,然后再去寻找场面调度上的喜剧性,方方面面综合起来才能变成一个喜剧,而不是很简单地找点笑料就能做出来的。比如《刘罗锅》里讨论24箱金砖问题,我就用一个镜头正面拍刘墉和和珅吵架,皇上在中间,他俩在皇上的左右不停地斗嘴,皇上不知道怎么办好,这种镜头本身就带有喜剧性。
刘罗锅动耳朵原来剧本没有写,李保田对我说:“导演,我有一个绝招,我会动耳朵。”我说那你动给我看看。我看后马上想到挪到剧里用,因为它很有幽默感,很滑稽,又显示出这个人在想主意,我就把它用在这个人物最关键的几个点上,而且都给特写镜头,因为在全景里动耳朵就毫无意义。
这就跟王刚的眼睛一样。王刚的眼睛一鼓起来就特别有一种喜剧性。有时候他眼睛一瞪镜头推出特定,要是放在一个全景里,一点儿效果也没有。如果用一个全景去拍他的大脑门和眼睛,也没有多大实用性,我用一个广角镜头拍他的头,然后哗地走到远景,广角的纵深感加强了喜剧性。所以影视喜剧的感觉最终是用镜头来解决的,要靠导演去捕捉它,而不能单靠演员本身表现出来。
东 您对“戏说”历史的这种创作方法怎么看?
张 我拍《刘罗锅》时有人问这是不是戏说?我当时就有一个很明确的观点,戏说是非常必要的,如果没有戏说,就没有喜剧。但问题是戏说不能是胡说,要区分戏说是戏剧地说,还是胡说、游戏之说,不能用胡说来代替戏说,把戏说界定在一个胡说的范畴之下,有人说我这不是历史,我说这正因为不是历史,它才更胜似历史,因为有时候跳出来才能比历史更具真理性。比如莎士比亚没有写英国历史,《水浒传》没有写历史,《三国演义》没有写历史,《西游记》更没有写历史,这些都是经典之作,但是比历史更概括,更接近真理,它的内涵更深刻。没有戏说就没有戏,这是最基本的常识。
东 您怎么概括您喜剧的风格呢?
张 喜剧不一定老是一种模式,它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刘罗锅》是一种模式,它讲了一个很深刻的故事,用喜剧这种形式使人欢乐给人智慧。喜剧必须跟智慧联在一起,这个笑才有质量,如果没有智慧就很浅薄,一笑了之了。这个戏好就好在有智慧,用中国人的方式,比较冷的比较内在的这种笑来讲一些很深刻的问题。所以华人都能接受,有很强的生命力。《康熙微服私访》是另一种模式,类似单本剧、折子戏。每一个故事讲一个严肃的主题,但都具有幽默的形式。《珍珠》是一种新鲜的风格样式,是一种贴近底层的平民化的喜剧,原因是刘宝瑞的单口相声在天桥的时候就是给拉三轮的拉大车的摆地摊的人说的。变成电视剧以后,同样还是市民大众喜欢它。观众在一个电视剧里能看到十几种不一样的喜剧风格。这三个戏,实际上都不一样,我想尽量在每一个戏里追求不同的风格。我想,喜剧应该是从形式到内容都是统一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讲文化讲内涵,这样我们的喜剧才能有质量。
东 您为什么对清宫戏感兴趣?
张 清朝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是最兴盛的一个时期,版图最大,民族最多。在中国的封建社会,汉唐是一个高潮,清朝又是一个高潮,故事非常多,在时间上跟现代人最近。从《神鞭》开始就有人说你怎么老拍辫子?其实,不可避免的是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都是辫子的后代。辫子只是一种发式,就像现在人们的短头发一样,辫子本身只是在乱世的时候如明末清初或清末民国初期,才有了一种象征的意义。
东 同样是喜剧作品,您的作品的品位就很高。
张 作品是需要一个格调的,不能为迎合观众把作品做得很低俗,很没意思。因为我到底是一个文化人,我要用文化做幽默和喜剧,所以必须让喜剧具有品位,具有后面一层意思。比如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它有后面一层意思,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抨击,否则就没有生命力。虽然摔蛋糕这种手法很多人都用,但用到有后面一层意思的时候,才有品位。品位是很重要的。现在有很多人自称是喜剧大师,但拍的很多东西是没有品位的,到底成不了格调。
一个电影或电视剧的导演,应该是一个永远从零开始的工作。每当你接到一个新戏以后,就介入了一个新的领域。《刘罗锅》接触的是清朝乾隆盛世这一段,你得知道了清官、贪官是怎么回事,刘墉、和珅、乾隆是怎么回事,你就要在这一领域下花费很多功夫看很多书,你必须要比演员,比服、化、道、摄、录、美知道得多,包括音乐,你都要懂,然后你才能把他们组合到一起。导演实际上是一个指挥,演员就是一个小提琴手,摄影是一个钢琴手,还有巴松、小号、大鼓等,你得把这摊东西都调动起来。观众看的是小提琴手拉得好,其实他是在指挥的总体把握之下。同一部贝多芬的作品,一个指挥跟另一个指挥指挥出来的效果完全不同,更何况我们的剧本本身不可能达到像贝多芬那样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