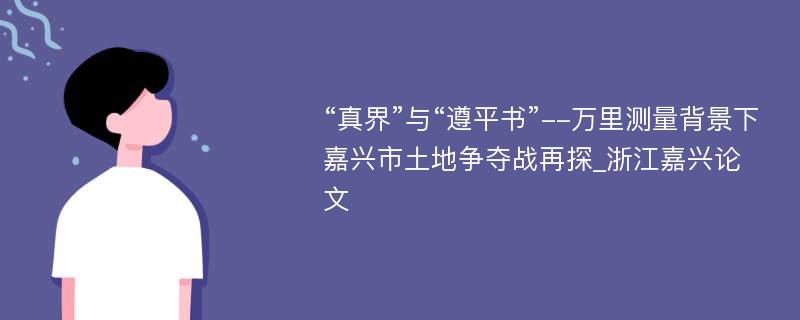
“正疆界”与“遵版籍”——对万历丈量背景下嘉兴争田的再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嘉兴论文,疆界论文,万历论文,背景下论文,遵版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2x(2012)04-0024-12
对于明末嘉兴府嘉兴、秀水、嘉善三县的所谓“争田”事件始末,现有研究已有较充分说明。根据当时各县绅民的申辩内容,将其原因归纳为三县错壤导致隔属换粮这一点:宣德五年分县时,跨都买卖的田土因分县变为两县间的错壤,人户为方便交粮,比较税则高下,相互贴银,通过私下暂时让渡产权就地纳粮当差,这种复杂的田粮关系导致丈量推收时发生混乱,遂成为争田的主要借口。①
然而,邻县互嵌田土在当时并不鲜见,里甲之内土地、人户、税粮三者之间的错位淆乱也是明后期的普遍现象,为什么其他各县没有出现如此激烈,持续时间如此之长的争执?为什么地方政府的裁决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对此,上述解释依然未予以澄清。考察引发长期争讼的各个因素,可以发现,三县丈量方法上的特殊设计和处置嵌田税粮的多种做法增加了丈量归户的难度,当地方政府必须进一步弄清人户与土地的结合关系以确知嵌田的原额归属时,遇到了无法解决的困境,它集中体现出明后期以专重田土为特色的里甲体系重建所内含的局限。
一、嘉兴府的圩田丈量办法
三县争田事件是万历土地丈量后的一个遗留问题,因此有必要先对浙江地区土地丈量的基本程序,区域差别和局限性做一交代。
栾成显先生已经指出,明后期土地丈量的一个最大特点是黄册的里甲编制与鱼鳞图册的字号划分已日趋一致。②同时丈量人役的组织以里排为单位的事实在徽州地区也已得到确认。③
浙江大多数地区也同样如此,编号田块登记在标明字号并有明确疆界的图内成为最普遍的做法。如海宁县隆庆元年的丈量,首先强调的就是以原额之里为基础的疆界划定,此后丈量即在此内进行:
本县原额三百五十六里,列六乡三十二都,分为头中末三段。东抵海盐,西接仁和,南连沿海,北至桐乡崇德。地方田土相联,必须分别明白,然后可行,此外之大界所当正也。大界正矣,然后每段立段长三名,每十里立都长一名,每里立图长一名,务择殷实老成公正知识之人使任其事。各将本图田地山荡,先分各都,次分各图,各立大标,分定各段都图界址,仍就其中分别总目,每田一邱插立大竹一片,自一都一图照依千字文,天字一号编起顺序编号,各书竹片之上,秩然不乱,此内之经理所当明也。④
再如金华府东阳县嘉靖末的丈量:“乡分为都,都分为图,图为保长一,书算、文手各一,俱择诚实晓事者充之,合一县十四乡为耆民三,以总大事”。⑤湖州府安吉县嘉靖四十三年丈量也是“逐图分号,编次鱼鳞”。⑥绍兴府会稽县嘉靖末丈量将33都共111图连同坊隅在内都按千字文编号,每图一号,顺次而下。⑦至清代,上述做法被全面继承,“民间田地卖买,国家赋税征收,历来皆以鱼鳞册为凭。其制,于都之下划分为图,每图一里,各以千字文中之字依次表之,民间约剂,所谓某字第几号者是也”。⑧
之所以会有这种“每图一里”的做法,是因为明后期以来的土地丈量是在原有里甲体系日渐废弛的背景下进行的。作为税粮分派的对象,丈量编号后的原额田土以里编派既利于催征,又便于对推收进行监管。同样出于便利征收的考虑,浙东地区多有丈量之时对图内原额田土进行简化税则的活动,以求减少因税则纷乱引起的推收混淆。⑨与此同时,借助重定丈量经界的机会,一些县份出现了所谓“履亩并图”的现象。隆庆五年,台州府临海县令周思稷赴仙居县丈田,出于均平里役的目的,他将丈量后的田土按照额定亩数重新编定,直接改变了该县的都图分布,开启了浙江地区均田均役改革的先声:
通计邑中之田若干顷,除官田一万二千亩免差不编里,寺田一万二千亩折半论差,优免役占照题准通例,各以官级论免。其额免外余田悉与民户一例编里,合该田三百亩充一里长,强有力者不加益,贫而愚者不加少焉。官户田多者尽其一图,其田不及与有余者,从其择所,相愿同充。又审第一都暨第十、十三、十五、十七、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四等都消耗太甚者九图归并之。⑩
由此可知,明后期以来以核田清税为目的的土地丈量同时也是一次对里甲体系的重新改造。原有里甲编户的内涵由此被编号的田土所取代,对田土面积、位置、推收以及经界的把握成为地方政府日益重视的问题,而鱼鳞图册与归户实征册的相互参核成为这种把握的内在机制:“鱼鳞图册百世不磨,而归户实征十年一变。凡续卖续买,其归户也,有归票以记其出,其收户也,有收票以记其入,而挪移诡寄之弊绝矣”。(11)
与上述以里为图的经界办法不同,万历以后嘉兴府嘉、秀、善三县的土地丈量则是以圩为单位组织的,而与人户、税粮的结合又必须在里甲单位中实现,两者从一开始就存在一个错位和衔接的问题。
在嘉兴县,圩长全面主持圩内丈量。在最初的总丈中特别强调与业户隔绝联系,“总丈时不许照会业主,庶无通同欺隐诸弊。且端责圩长,一圩自完一圩事,不涉业户,不容推委稽延,事不烦而告成,最速也”。(12)其后的覆丈亦强调“与业户无涉,不许挟令业户到乡,籍端科索”。(13)除防弊的目的外,这么做主要是由于土地关系的复杂,“圩长在本圩与各佃居处相习,其某号田系某业主,某业主者或所熟悉,但其中有典卖不等,亦有分拨子姓不一,更或田业系此姓此名,而完粮役册又系别姓别名者,必凭业主自具圩田单数方无差误,故总丈草册不可遽令圩长开填业户也”。(14)租佃关系中的城乡隔绝,土地典卖的复杂关系,花分子户,诡寄别名的普遍存在使在本圩耕种的佃户也难以完全知情,想全面清查土地占有状况是非常困难的,遂采取回避的办法以求按时完成。
与此同时,各圩业户以图甲为单位,由册书颁发业户田粮清供单,其田在各圩者复填圩田清供单,填明其田土坐落都圩和办粮图甲,“凡官户、儒户每户一单,民户或一户一单,或照当役分数一单,其甲户零星者听填里长单上,听从民便可也,但不得舛漏厘毫”。(15)多个业户的零星田土汇凑成一甲本名完粮之数的情况在当时非常普遍,“听从民便”则意味着丈量在有意识地放弃对黄册户名下实际人户的细化把握。此后进行的分丈就是业户以总丈后的各圩田土数为范围,以圩内号数为单位,将自己挂靠在黄册户名下的田粮凑合成一圩之数的过程,“如圩长总丈一千亩,则各业户零星分丈必算足一千亩之数,不得略有盈缩异同,如此以粮核田,又以田核粮,一一明白的确”。(16)所谓田粮互核就是区圩田土与黄册里甲原额田粮之间的相互调试,后者所包含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并不着力清理。但即使这样,在嘉兴县康熙年间的丈量中,两者之间在疆界、挨号、分爿、弓尺、积算、配粮等各个方面都出现了差缪:
……如一圩之田或分属两图,因万历九年鱼鳞底册遭毁,茫无界限,先动弓者竟将临图之田丈为己有,间有多至一二百亩者。此图既多则邻图自缺,时移世换,即有盈亏,何至相悬若是,此疆界之差也。夫册号鱼鳞如于某方起弓,逐爿挨号绘图,毫不紊乱,若鳞之擳比者。然今因圩长朋充者多,又复仓忙急遽,竟有第十号在东,而十一号又在西者,十分之中不无一二,此挨号之差也。又如业户丈田一号,圩长有分作两号者,业户丈田二三号,圩长又有并作一号者,致使私存底数与圩册毫不对同,此分爿之差也。又如业户丈为二十弓,圩长有多丈一二尺者,复有少丈一二尺者,至于分寸之间更多迥异,此弓尺之差也。算法须期画一,今弓尺既差,则积步归除俱属两样,因而业户算少而圩长算多,又或业户算多而圩长算少,此积算之差也。禾属完粮,户名凡在民图,大率零星者居多,必须配搭,如业户有田四亩一爿,其二亩在某郡某册赵甲户下办粮,其二亩在某郡某册钱乙户下办粮,填注未尝有弊,今圩长或丈为四亩一分,则亏粮一分矣,圩长或丈为三亩九分,又多粮一分矣,甚而一号之内有差至数分者,圩册纷纭难以枚举,此配粮之差也。(17)
以圩为单位的丈量经界虽然在直观上简洁明了,但却割裂了对田土、人户、税粮的综合把握,造成了三者衔接的困难。结果是嘉兴县康熙年间丈量后出现了图亏,即按照上述程序形成的各图田土数比之原额出现了缺失,对此,嘉兴士人屠延禧建议在图与图之间进行调剂,“各图有亏者,亦有溢者,俟圩册既齐,合县通盘打算,将溢补亏,与八十七万之原额相符亦可邀无事之福矣”。(18)即以图与图之间的调剂替代对缺额原因的核实,保证全县总额不失即可。
而在嘉善县,一区之内以圩为单位丈量所形成的数额称“圩总”,它与原有黄册田土数额“册总”在数量上存在着差额,需要先将两者汇总比对,“如一区十圩、五圩,圩有圩总,区有区总,以十圩总合一区总,务求无差,然后以一区所统里数,原册田地荡屯彼此相对,如有增损,明白开注,以便查考”。(19)但是在一区之内,土地买卖的频繁使圩田的里甲分配常处于混淆不明的状态,所谓“查考”根本难以进行,在区与区之间先进行此增彼减的调剂,保证总额不失才是最首要的工作:
区总分别几圩,册总分别几里,某里分隶某圩,至明白也。近来各圩业主卖买不一,里甲互更。要以大数乘之,大约一区册总田地若干,一区圩总田地若干,彼此相对,不致悬绝。某区如少若干,则某区必多若干,务使以多补少,不失开县原额之数,方可造册。(20)
此后对圩田的归属图分只是由圩内人户自报,“以田从人,以人从里,此所谓归户单也”。(21)
与嘉兴县相比,嘉善县通融的单位更大,把对圩田内人户与土地关系的清理放在了一个更次要的位置。作为实征的册总即使无法理清混乱的土地关系,也可以通过区与区之间的通融以维持一县原额的不失。但是,当涉及确认两县互嵌田土的问题时,则必须要搞清楚其业主和推收情况,以确定是否要纳入本县实征原额田土中,对此嘉善县丈量主持者方扬在已开始就顾及到了:
外县田地坐落本县者,要见何年推收,奉何明文凭据。如天宁寺庄,此未分嘉善县时已有本寺,犹可言也。至如各户三亩五亩,或一二十亩,业户三年五年,或一二十年。管业者既无常主,办粮者亦无源流,暗相兑换,彼此更名而不更县,甲乙更主而不更粮,此民间宿弊也。虽承流已久,不可以久弊冒作原额,果查有明据,即开收明白,登列册籍可也,不得仍前暗推暗收,以滋隐射之弊。(22)
土地买卖的零碎化导致管业无常,缺乏及时真实的记录,办粮之源自然难查,结合上述嘉兴县的情况,我们知道,这是该地丈量时普遍遇到的困境。正是在这一点上,嘉善县首先出现了问题。由下文可知,嘉善县丈量后所得之全县“圩总”数额比对“册总”原额后出现了缺额,由于难以确定缺额出自何处,遂将之归咎于嘉、秀二县在推收中借上述“暗相兑换”之机攘夺本县原额田土,争田之端遂由此开启。
二、寄庄与错壤
三县争田的焦点主要是围绕对上述“外县田地坐落本县”情况的处置。对人户跨县买卖田土的赋役征收,明代中央政府是通过寄庄制度来安排的:“(洪武)二十四年,令寄庄人户除里甲原籍排定应役,其杂泛差役皆随田粮应当”。(23)即规定寄庄田土的税粮和杂泛差役由寄籍县分征取,而里甲正役则按人户原籍地的里甲次序应役。也就是说,对寄庄田土的赋役征收本身就存在着属人与属地两种标准。纳粮以寄庄地为准的原则一直被强调着,如嘉靖三十九年大造,明政府就强调“十岁以下或年老、残疾、单丁、寡妇及外郡寄庄纳粮者,许作带管畸零,其十岁以上并各分析人口俱编入正图”。(24)
当县份疆界发生变动,一些都分改隶他县时,原有人户跨都买卖的田土就会变成寄庄田土,赋役征收基本也是按照上述原则安排的。我们可以举一个绍兴府会稽县和嵊县在嘉隆间丈量推收的例子来加以说明。
绍兴府会稽县因征粮争议,在成化九年将其所属二十五、二十六两都划归嵊县治下,“两都田当二万八千四百一亩五分九厘二毫,粮视其亩随之”。(25)但由于黄册重造疏忽,两县寄庄田土的纳粮归属出现了混淆:
如会稽二十五都人甲,向有田十亩在二十五都中,后来却买一都乙之田十亩,遇册岁,则甲必装所买乙田归之二十五都,以总便输役。其后二十五都忽属于嵊,则甲之田向在二十五都中之十亩得以随嵊,而续买一都中之十亩不得以随嵊,得附其输于会稽之一都,曰寄庄户而已矣。顾失检于册岁,令甲得以混一都中之十亩并二十五都中之十亩悉归之嵊,如此类者凡五千亩。而会稽民如陶宗夫者,向有田若干在九都,其后续买二十五、六等两都之田,计二十八亩有奇,册岁亦归于九都以总便输役,其后两都既属嵊,则此二十八亩有奇者亦宜随输于嵊,曰寄庄户而已矣。顾册时仍占于会稽,如此类者亦九百九十六亩七分三厘四毫。嘉靖二十六年,知县张鉴知邑田多奸,履概邑亩及嵊界,始悉其故,白于府,并度之,乃各归其额。(26)
由上可见,会稽县对本县田土疆界的划分是以“总便输役”为原则,即以税粮的征收权限为标准。坐落本县都图的寄庄田土因在本县交纳税粮,因此当归属本县原额,即“正图”,这是符合明初的相关规定的。由于在黄册十年推收时混淆了这一标准,寄庄田土常被混入田主原籍所在的县份,造成寄籍地县分纳税田土的缺额。当嘉靖二十六年知县张鉴履亩丈量时,通过申请于府,获得同时丈量二十五六两都的权限,就将上述混淆纠正了过来。嵊县民人对此亦多有争执,嘉靖二十八年浙江布政司携会稽总书及两邑民人赴后湖查册,印证了张鉴清理无误。至万历元年,上述清理被确定下来,两县互嵌田土坐落及人户籍隶遂被立碑记载以杜混淆:
收归嵊田凡五千亩,并盈出者七百一十一亩九分四厘,地凡二百五十八亩九分二厘二毫。内坐:
十二都田一十亩三分三厘一毫
十四都田三十一亩八分七厘
十六都田六亩八分三厘
十九都田六亩五分一厘
二十二都田二十四亩九分三厘三毫
二十三都田五亩七分九厘八毫
二十八都田三亩九分
二十九都田一亩二分九厘七毫
二十都田六亩七分五厘八毫
二十一都田一百亩一分
二十四都田四千二百七十一亩二分八厘,地二百一十二亩二分八厘一毫
二十七都田一千二百四十亩二分二厘三毫,地四十五亩六分四厘一毫
退归嵊田凡九百九十二亩六分八厘四毫,内:
第九都二图陶宗夫田二十八亩七分三厘八毫
二十一都二图董泮等田二十七亩六分四厘八毫
三图胡泽等田九亩七分八厘八毫
四图宋仪定等田一十一亩八分六厘九毫
二十二都二图董雷田九分五厘五毫
二十四都一图龚森等田八十亩七分一厘八毫
二图章文正等二百三十一亩七分二厘四毫
三图陆仁等田四百四十七亩八分一厘七毫
二十七都一图孙权等田六十四亩九分一厘八毫
二图郑文礼等田九亩六分七厘七毫
东南隅三图卢阿王等田一十六亩五分八毫
四图赵泽田五亩六分九厘八毫
东北隅四图传机等田三十亩八分六厘四毫
五图钱镇等田一十六亩一分四厘六毫
六图高土诚田九亩六分一厘六毫(27)
“收归嵊田”的五千余亩是籍隶嵊县,田坐会稽的田土,上引文标出了这些田土所坐之都,其税粮纳于会稽。“退归嵊田”是籍隶会稽,田坐嵊县的田土,税粮纳于嵊县,上引文标出了这些田土的人户原籍所属的都图。由于田土和人户的登记都为同一单位,清查其寄庄地的坐落和原籍地的里甲归属并不是很困难的事,两县疆界得以理清。
以上是在丈量清税中遵循寄籍地纳粮原则划分经界的情况。需要说明的是,在明后期的黄册编审中,以寄庄名义规避赋役的现象是极为普遍的,在日常推收中上述原则其实难以有效贯彻。一种规避办法是寄庄人户不在寄庄地另立户名,而是以子户的名义将税粮征收的责任诿于原卖户之下,如金华府武义县介于本府永康县和严州府宣平县之间,“民间田地转相贸易,承买既非土著之民,异籍又无推收之例,契券可易,版图难更,于是通之以寄庄,至居邑产十之一。然寄庄海内在在有之,皆立名于册,官得比征,赋无积逋,武人则异是矣,不自立户,附于原主,有通户皆寄庄,而已无升合者,有附于总户而□以避税者,种种情弊,乃为逋粮之薮”。(28)由于没有另立寄庄户名,对其田土征税就变得非常困难。
另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是优免人户通过占有邻县土地而将自己的优免范围延伸至邻县。如广东按察司佥事曾鼎在宣德八年的上奏中就指出,“今广东、浙江、江西等处寺观田地多在邻近州县,顷亩动以千计,谓之寄庄,止纳秋粮,别无科差。……又有荒废寺观土田报为寄庄,收租入己,所在贫民无田可耕,且多差徭,而僧道丰富,安坐而食”。(29)其他人户复通过诡寄将优免进一步扩大,既可免除里甲正役,又可避杂泛差役,明中期以来“以绝户为里甲,而影射田粮,以官户为寄庄,而躲避徭役”(30)是极为普遍的现象,“若殷富之家故为规避之计,或假绅袍名色,或托别县寄庄,或作义男女户,恣意花分,巧立名色,则其户虽析而产实未析”。(31)其诡寄“或以文职立寄庄,或以军职立寄庄,或以军人立寄庄,不过巧为花分,以邻国为壑耳”。(32)再如萧山县嘉靖初年的均徭之征,“有托邻县显官立户者,有将田寄于本县京宦户内者,有将户下人丁碎分者,有捏鬼名带管者……其邻县显官既免原籍差徭,岂容复免寄庄田亩”。(33)按照洪武二十四年的规定,杂泛差役本应在寄籍地征发,但通过寄籍于“邻县显官”则可成功逃避均徭银的征收。
职此之故,在明后期的赋役改革中,对于徭役编佥和里甲支应的分摊越来越注意到对寄庄田土的把握,如嘉靖间宁波府鄞县的丁田之征以田十亩折一丁,对附籍寄庄户,则每田二十亩则増一丁。(34)定海县的里甲支应将见年田土折丁后分为十二段以供应每月之需,其折丁田土中也包括了“寄附之田”。(35)海盐县在万历三十九年的摊丁过程中也将本县寄庄户丁包括其中。(36)
里甲支应之役属里长正役的范畴,应编在寄庄户原籍所在里甲应役,但上述各地做法则显示出,至嘉靖年间,以原籍里甲次序为断的原则已被打破,折丁后的里甲丁田之征包括了寄庄田土,在随后的条鞭合并中,各县丁田银两与税银合并形成的条鞭银征收范围就自然包括了本县的寄庄户。另一方面,当以编审粮里解役为主要目地的均田均役开始进行时,各县也基本取消了对乡宦寄庄田土的优免。(37)随着明后期赋役改革的进行,承担条鞭银和里役佥派的原额田土在折丁的过程中逐渐将寄庄田土包括进来,后者与原籍地的关系趋于减弱。
与寄庄做法不同,嘉兴府嘉兴、秀水、嘉善三县在分县之初对彼此互嵌的田土以“错壤”名之,其赋役征收的归属从一开始就与“寄庄”的规定反是而行之。
宣德五年,大理寺卿胡概以“政繁事冗”分嘉兴以秀水、嘉善,分海盐以平湖,分崇德以桐乡。(38)与上述会稽县在成化年间分二十五、二十六两都于嵊县一样,分县的原则大致以都为界划定田粮,但对由此形成的邻县互嵌田土的情形,并未以寄庄方式规范之,而是以“错壤”称呼。
徐必达:《国赋原平奸民酿乱乞敕严行勘结以靖地方疏》:
窃照洪永间,止嘉兴县耳。至宣德四年,始分秀水、嘉善。时承平垂六十年,人户既以籍定田地,过割从人,如赵甲本一都人户,而买坐落十都或二十都田地,值大造,彼推此收,一切坐落十都或二十都之田地总收为一都赵甲之事产,此祖制也。计宣德四年以前,大造黄册者六次矣,据册分县,自多错壤,如一都分属嘉兴县,赵甲即是嘉兴人户,其原买田地虽坐十都而分属嘉善者,不得不从赵甲为嘉善一都之事产。(原文如此,应为嘉兴一都)盖承平分县,故与草昧不同,草昧恒因疆界以定册籍,承平必因册籍以定疆界,就今嘉秀界中错有嘉善田地,是错壤原在未分县之前,而疆界岂得正于既分县以后也。(39)
岳元声:《错壤图说》:
夫嘉兴秀水始固一邑也,一邑之中,都图之内,互相券易,更相推收,有籍在一都而收坐落二十都、三十都之田者,有籍在三十都而收坐落一都、二都之田者。十年一造,以籍为定,照籍索赋,亦照籍编里,未有问及邱段坐落某处者,国制如此,何地不然。……盖自洪永以迄宣德,承平既久,券易推收,互杂自多,而分县之?时止是以户籍为定,岂其履亩割裂如鸿沟为界者哉?(40)
以上是明末清初嘉兴、秀水一方的士绅对错壤发生的解释。根据上述洪武二十四年对寄庄的规定,对于田在彼县,户在此县者,税粮的交纳与杂泛差役的征取应在田土坐落的县分,而不是人户所在的县分,上述会稽县就是按照这样的原则向嵊县嵌入本县的田土征收税粮的,而嘉兴府的“错壤”则将嵌入别县田土的税粮也归入本县征收,也即是说,宣德五年分县后,各县田土原额与税粮原额中包含了一部分坐落于外县的田土额和税粮额。由上文关于寄庄问题的梳理可知,不论在明初“人户以籍为断”,还是在以后寄庄原籍属人性质减弱的趋势下,这种“错壤”下的隔县收粮都是没有法理依据和事实基础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不同?嘉兴县士绅王儒在《三县关会田粮七辩》中作了如下解释:
……故老传闻,析县时以籍为定,故有旧籍占嘉兴,新籍占秀水,或千亩之家,或百亩数十亩之家,房屋世业在郡城内外,而祖宗坟墓,子姓住址,或一二亩或四五亩,先置在嘉善界中,常情安土重迁,又难弃多就寡,不得不告存嘉秀者。又有仕宦、世胄、军匠等户,举监、生员、吏承等项,起家本庠,出身本图,隶戍本所,发遣本甲,顶祖本役,而田地则在新析界中,一或拨籍,将不便于优免,不便于起送,不便于承袭,不便于勾补,不便于纳班,势不得不仍旧贯者。又有殷实之家,人丁繁衍,国初落户,世世合并当差,粮里极重苦役皆其应充,为齐民巨擎,如先年怀十万等,不忍又令窜名新县,复以大户编苦役而重累之者。又有既以嘉兴旧籍拨入秀水,似难以秀水新籍中有彼界零田再拨嘉善,一户骤创两籍,上必体恤调停,籍不去则田在彼中者,并存秀水矣,人情不甚相远,即析县在今时,司民牧者不当如是耶?(41)
由上可见,分县不仅涉及田土和税粮的分割,还涉及对优免和徭役承担的重新分配,在明初人户以籍为断的原则下,因分县而导致的分籍会改变过去乡宦优免和户役征调的变更,会导致粮长大户串名应役于两县,因此嵌在别县的田土不另立户名,而是将其“存”在了本县人户名下,由此形成与寄庄做法相反的错壤惯例。
嘉兴县将“以籍为定”的洪武祖制扩大到对隔县税粮的征收确实是没有根据的,只是这不合理的实施自明初即已存在,几成惯例,至嘉靖二十六年均则运动开展之时,复又得到了进一步确认:
……当未扒平之先,嘉、秀嵌嘉善之田与善田之粮额同,原比嘉秀田粮为重。至嘉靖年间,各县扒平,则嘉、秀嵌善之田仍于嘉秀通县田粮内扒平定额,所以从嘉秀而稍轻也。各县嵌田俱从本县粮额完粮,其例明矣。(42)
在扒平以前,各县田土税则庞杂纷乱,对错壤税率的核定仍以坐落县分为准,自扒平后,税率则改以原籍所在县分为准,府守赵瀛在均则时确立的所谓“不动版图”(43)的原则,是进一步确认了宣德年间对错壤田土税粮归属的划分,即确认了黄册里甲以户系田的祖制可以扩大到隔县税粮征收这一其实没有根据的做法。
使上述问题变得更多一层纠葛的是三县人户对错壤田土的税粮征收发展出一种“兑粮”与“贴银”的做法。据万历十五年嘉善县令蔡彭所述,“嘉善与秀水俱由嘉兴县分割,疆界毗连,民居错列,有籍隶嘉秀而田坐嘉善,有户分嘉善而田坐嘉秀。富豪势要之家隔属不便输粮,遂私相兑换,各认本县粮差,名为兑粮不兑田,相传年久,莫知来历,但以为田在各县而粮差在本县也,非法所当行,但彼此粮额尚照旧兑办,未为亏失”。(44)在嘉靖二十六年均则之后,各县税则划一,相互间高下有异,人户在兑粮时遂有“贴银”之举,“嘉兴粮最轻,秀水粮稍轻,而嘉善最重,故嘉善与秀水换粮,每亩贴银一钱,与嘉兴换粮每亩贴银一钱五分,其弊已久,由是嘉善东境去府悬绝,亦有嘉秀之田,甚至城中亦有嘉秀之地,然田地虽淆,粮额未亏。”(45)另据王儒《三县关会田粮七辩》所述,“此滥觞于嘉靖而沿习于万历,每于大造,照换顶收,分毫无错,此乐于轻而彼亦不嫌于重,并无后言,故隆庆造册,嘉善粮额不失”。(46)通过缴纳贴银,错壤人户暂时性让渡其田土产权以方便就地纳粮,这使得人户的土地占有状况变得更加复杂。
这样一来,嘉兴三县由于历史上分县的原因,其田土、税粮与人户的复杂关系使一县丈量时须区别以下三种不同的情况:其一,为田土坐落于本县,业户也为本县人户的土地;其二,为田土坐落于本县,业户为它县,税粮也在它县交纳的错壤土地;其三,为田土坐落于本县,业户为它县,税粮在本县交纳的寄庄土地。同为外县嵌入本县的田土,第二种是分县时形成,并在嘉靖二十六年均则时得到确认,第三种则是在分县之后复因土地隔县买卖造成的寄庄田土。当万历九年嘉兴府各县进行丈田核税的工作时,各圩圩长一方面要搞清楚错壤田土的面积和原籍,以便推出,不使混进本县原额,一方面又要确认寄庄田土的面积和原籍,以便纳入本县原额之中,不使失额。这中间还要辨明是否有兑粮行为,兑户为谁,方能辨别其田土是错壤而不是飞诡。如上引《丈量则例》可知,在嘉善县丈量之前,方扬已虑及此一困难,但从实际的丈量情况来看,对错壤田土的清查仍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各种差缪:
……查得万历九年奉文丈量,嘉善图
长有稔知田在嘉善粮在嘉秀而丈入两县者,有不知而误丈入嘉善者,有明知而故丈入嘉善者,有失报而并丈入嘉善者,有错报而误丈入嘉秀者,有妄报而故丈入嘉秀者,陆续查明改正,故有初关,有续关。(47)
由上可见,嘉善县对于本县错壤之田有不知而误入者,有明知而故入者,甚至有同时登记于两县者。嘉兴、秀水两县也有类似的情况,兹举两例:
秀水县编修黄洪宪在万历九年丈量之前有祖遗田四百六十余亩坐于嘉兴,自嘉靖三年以来就办粮于秀水,“万历九年清丈,缘田界两县,犬牙相连,以致彼此推调,失于报知,及业户自行首明,嘉兴顾候丈明,照旧归会秀水办粮”,即在嘉靖三年,黄氏家族买错在嘉兴县田四百六十余亩,遵其错壤初意,纳粮于秀水,万历九年丈量时被混入嘉兴,经人户首明退还秀水。至万历十三年,秀水里书不察,将之作为新升田开报,黄洪宪禀明县令予以纠正,由其申文可知,误报的原因是当初两县关会之时,秀水一方并无记录,因此没有登记。(48)产生于宣德五年的错壤田土在此后的漫长岁月中经历着频繁的、趋向细碎化分割的历程,在这一过程中,政府要对它的转移和分割进行准确登记实是困难,里书借此作弊很难防范,上述差错必然难免。
崇祯年间,黄洪宪之子,福建巡抚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黄承玄,同弟凤阳府推官黄承乾,都察院进士黄承昊向秀水县令揭明本户田粮来历,以驳嘉善县飞诡之责。据其申称,黄家在万历九年以前,有先世遗田坐落嘉善者共1600余亩,包括了寄庄和错壤两种情况,分属嘉善和嘉兴、秀水的原额。其中在嘉善办粮者991亩,在嘉兴、秀水办粮者646亩,“至九年丈量,各圩长不行知会,将田溷报嘉善册内,及奉两县重征,乃始令黄臣告明关回秀水,而本户在嘉善办粮原额仍不缺也”,对于这600余亩的错壤之田,据万历二十五年县令章士雅清查,“本户坐落嘉善之田向在秀水完办,原买文券税契开载甚明,除先年卖主年远无存者二百四十二亩三分四厘二毫各免关回外,查原兑杨岑等八户田共二百四十四亩一分六毫,潘继、马孙、蒋谱等九户田一百七十亩五分三厘七毫,各照原兑田粮在于本县各户下完粮等因。申府。夫此四百余亩之田既查各有兑户,彼此兑纳田粮,则又何可概谓之飞诡?即令杨岑、潘继等有无完办,本户不得而知,其或避匿不完,是弊在各兑户之隐粮,而非本户之隐田也”。(49)即先年卖主年远无存者242亩,免其关回,此外有244亩系与嘉善杨岑户兑田,又170亩与嘉善潘继、马孙、蒋谱等九户兑田,兑户有考,因此不是飞诡。至于这些兑户是否切实交粮,就与己无关了。这一自述最详细地说明了圩长丈量与归户衔接中发生错误的情形和以后清查改正的程序,这都是其他府县在丈量中不会遇到的事。
由于三县围绕着对寄庄、错壤,和衍生的兑粮、贴银等关系的清理过于复杂,实际丈量中对于田土的原额归属必然发生大量错误而又难以完全查明原因。再由上文对嘉善和嘉兴两县丈量程序的考察可知,其以圩为单位的田土疆界划定使对上述复杂关系的清理最初并未包容在图的范围内,当嘉善全县丈量总额(圩总)比黄册总额(册总)缺额甚多时,根本无法在事后查清其真实的原因,这一点王儒在《三县关会田粮七辩》中说得非常清楚:
惟万历九年应该先开收,后丈量,则原额胡由失也,惟不行开收,一概混丈,又以丈实为据造册,而弊孔百出,在在有之矣。然丈后推多者何以故?缘应推数中既有隆庆前后互换之田,又有析县时嘉秀嵌入嘉善之田,数焉得不少?若必欲关数相抵,则既欲丈量前后互换之田入册,又欲析县时嵌入嘉善之田一百五十年来不可穷诘者入册,此必不可得之数也。(50)
即在丈量之初就应该先在各图间进行推收,在这一过程中,要分别因兑粮导致的错壤田土归属的混淆以及寄庄田土的数额,将每里的田粮原额进而每区的原额确定下来不使失额,然后再进行丈量,就不会出现失额。事后再去追究则于事无补。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本县人户的诡寄隐漏问题也有可能造成缺额的发生。“当审役之时,有贫民田已转售,而粮存本户者,有奸民潜贿里胥,而漏报丁产者,嗣后大造一番即增一番隐驾,隐则匿有为无,驾则砌多于少,摊于一县谓之县亏,派于一图谓之图赔,是邑赋之烦,不烦于编载之额,而烦于县亏、图赔二者也”。(51)这种图赔、图亏的现象各地所在多有,而要比较有效地分别上述各种造成缺额因素,则有赖于丈量的圩长、圩内人户以及负责推收的册书间的有效配合。
三、围绕“疆界”与“版籍”的争讼
由上可见,造成嘉善县失额的可能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丈量程序对田土于人户关系把握的错位,有三县原额田土归属上难以理清的各种复杂关系,更有日常推收中的种种作弊行为。而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对土地关系清理的有限性根本无法使三县之间就缺额的原因达成共识。各县都从保住自身原额的动机出发,在历次会勘中不断追加着对方“以邻为壑”的欺隐证据,更以对互嵌田土属人与属地两种原则的各执一词反复拉锯,持久的纷争就此演成。
首先从嘉善县一方来看,万历九年的丈量依循着方扬的规划完成汇总后,出现了丈量总额少于八年实征额的情况。对其缺额的数量,现有研究都采纳嘉善县在第二次会勘中提出的30000多亩,而第一次会勘的直接材料都说明了呈报的缺额是5600多亩。(52)其产生的原因,据知县蔡彭所述,乃系业户对错壤田土推收的不实不尽,“业户因见嘉秀粮轻,本县粮重,各图诡避乘时,奸顽将田坐嘉善者借称粮在嘉秀,尽数报推,田坐嘉秀者不认兑粮嘉善,巧避重而不还,甚至本县田地混隐嘉秀势豪户下,以致二县丈出额田数多,本县丈亏额田五千六百八十四亩零”。(53)
直至万历二十六年三月嘉善县里老再次呈控时,亏田数额才被扩大为30000余亩,对亏额产生的解释仍是本县推去错壤田土太多,收回太少。(54)这30000多亩田土滞留嘉秀,粮额却存于嘉善,致使嘉善以低洼荡滩13000余亩抵田升科,复将余额摊赔全县,而嘉秀丈量本有余额,此30000余亩系其原额之外却并不报增,己田每亩遂得以摊减税粮,复将余田隐匿细户名下以为无粮之产,并举出此前嘉兴县金圻隐田数千亩的例子以为佐证,同时声称秀水黄洪宪户下清出隐田6000余亩。为此正式向知府提出了取消三县嵌田旧例以“正疆界”的要求:
……将额分圩田在嘉善界中者粮完嘉善,在兴秀界中者粮完兴秀,据嘉善底册上面注某区某圩某人田若干,仍旧存区办粮,下面诡注兴秀都图者宜尽削去,至于兴秀底册上面注某都某图某人田若干,仍旧存都办粮,下面诡注嘉善区圩者亦尽削除。(55)
由上文可知,嘉善县针对错壤田土提出的正疆界之议是以明后期寄庄田土属地性质的加强为其合法性基础的,当寄庄田土的税粮、徭银进而解役的佥派都在寄庄地县份完成,后者自然有将之归入本县原额的动机。此议由于张似良的去任没有实行,但上述正疆界的说法得到了当时嘉善县知县章士雅的肯定。(56)
从嘉兴县方面来看,在第二次会勘期间,从地方里老、士绅王儒等到县令郑振先都对嘉善县缺额的说法表示质疑,同时坚决否认“正疆界”的提议。
他们指出万历九年丈量以前,嘉善县额田626931亩,比之分县初额626262亩已多,至万历十二年由票开载丈实田地共629417亩,更形增多,至十五年第一次会勘结束刊定碑式,嘉善县总额(627019亩)虽有所减少,但比之前两者仍是增加的,那么该年丈量是否缺额呢?这仍是个疑问。纵使缺额,为何此前只缺5600亩,而此时却骤增至30000余亩?如果30000亩缺额确系出自嘉秀隐匿,则应细考其来历,“要见各田先年系何人户,名立于嘉善何都图,何里长,甲下何人避重就轻,关推嘉兴,逐一根究来历,如嘉善先年原额所有,今嘉善诡入嘉兴,即应改正推收,如嘉善原额所无,自系嘉兴原额所有,如一概来关,是隐田在嘉善,缺额在嘉兴也,关复者何名,关推者何据耶?”更何况其中一些要求关回的人户田土甚至连都图坐落都没有。对于本县人户金圻的隐匿,嘉兴并不避讳,但指出同样要搞清其隐田是否坐落嘉善都图,如果不是,那就是嘉兴县自己的事务,与嘉善无涉。至于黄洪宪户下隐匿的6000亩其实是嘉善县本身的寄庄田,而不是错壤田土。作为缺额不存在的反证,除嘉善县上述额田在丈量前后有增无减这一点外,奉四北区、迁中区共有1918亩圩田以二亩折一亩却未奉明文,再加前此由票内开载的隐田3400亩及第一次会勘中清出马瓒等户的田土共计13078亩均未入原额,怎能说是缺额呢?(57)
由上揭丈量程序可知,嘉兴县要求“逐一根究来历”的要求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同时针对嘉善县彻底收回本县所有嵌田,进而取消其在嘉秀的都图坐落以正疆界这一点,如上所述,嘉兴乡绅在回溯三县错壤渊源的基础上提出了针锋相对的遵版籍说法,即认为隔属收粮的惯例国初即已形成,早已归入各县原额,不将其分析清楚一概混丈入嘉善就是借正疆界为名行攘夺之实,目地乃是让邻县之人为该县豪右的隐田行为买单:
今豪右欺隱数多,碑帖颁刻难掩,恐终不免首告入额,反捏缺少额田,藉口推多回少,一经吊取,则先年脱漏之家便可隐为世业,坐享无粮之素封,永杜子孙之后累,故复仍故智,得陇望蜀,彼有一摘再摘之谋,此无已误再误之理,以是知彼中里递倡为推多回少之说者谬也。(58)
当对缺额原因的解释转移到欺隐诡寄的时候,双方都可以找到充分的证据,这让争田变得彻底无法收拾。至万历四十二年开始第四次会勘时,除重述上述内容外,嘉善县在清查嘉秀二县册籍时开始不懈地发掘着邻县欺隐的证据,发现“嘉兴二十八都,秀水一十七都各图黄册内各业户名下并无收入嘉善县田亩,明系诡隐,抄册存证。又查嘉兴县魚鳞等册隐没德化等都号字等三十三圩,约田数万亩不送查对”,将嘉兴县万历九年丈实田数加上此前金圻等人隐额共多出原额13460亩,其中12404亩隐在嘉善界内,“查无收户,隐不完粮”。此外,嘉善书手又于嘉兴册籍内搜出印信弊册八本,计隐田5490亩,又有隐匿黄册四十二本,拒不送查。在揭发个别人户欺隐方面,嘉善县查出“天宁寺僧陈元灯隐田五千三十五亩,精严寺僧唐海镜一千二百一十亩,俱坐本县界内。先年历据元灯执称,前田收入秀水县北隅二图,海镜执称前田收入秀水南隅二图完粮。万历二十八年五月内,本县批解里老吴旃,算手张昱等赴府提同本僧,并秀水县算手丁科等简出万历十一年秀水县造送贮府黄册,当堂会查。北隅二图陈元灯户下只有坐落秀水县界内一千九百七十六亩,并无坐落嘉善界内田五千余亩收户。南隅二图唐海镜户下只有坐落秀水县界内田七百二十八亩,并无坐落嘉善界内田一千二百余亩收户。……且据僧徒真禅、清渭、海航等各诉前田系嘉隆年间明中正契置买嘉善人户薛杲等之田,向充迁西区十八册里长,则田系新置,额系嘉善明甚”。同时,嘉秀里书在清查嘉善田土时,也算得嘉善确实因嘉秀飞诡而亏额33000余亩,事态至此进一步扩大。(59)
至万历四十五年四月二十九日,在分巡嘉湖道佥事王钟岱、知府庄祖诲的主持下,三县公同磨算,以确定上述亏额的来源。在这一过程中,却又发现嘉善县在三年前吊查的鱼鳞册有割补的痕迹,“内有下保东区伐字圩旧割今增八叶,迁中区收字圩旧割今增二十八叶,大桐圩旧割今增十二叶,迁北区大三往圩旧割今增一十四叶,思四区问字圩旧割今增一十叶,纸笔印记,大小新旧俱各迥异,及照前算仍与旧数不差,统算比之志额不少,即此四圩补完旧额田数已足6166亩零,尚有未完数十本,正在严查”,五月初三日,嘉善乡绅魏大中、钱继登等私约嘉善县令吴道昌出城,“乃执正疆界三字为说,又有公书议逋二纸,谓册不可凭,田尤不可丈等语”,(60)至初六日,遂发生嘉善民众冲击府堂和秀水乡绅岳元声宅第,迫使巡抚以下相关官员请辞的严重事件。其后在对此事的审理中方才知晓,原来万历四十二年两方互查之时,为了造成缺额的铁证,郭文翰、俞汝猷等人将本县魚鳞册中的嵌田部分统统割去了:
至割册一事朱思贤供称四十二年七月十一日本府查册,嘉秀两县解册在先,独嘉善册未解。十三日晚郭文翰俞汝猷禀官谓鱼鳞挨号册田原足额,难以送查,不如割去方好藉口,因抬册文翰家,文翰、汝猷将挨号册先割,十五日差俞汝猷赍解,又审鱼鳞册,供系郭文翰张郁王成祖朱思贤同割,只因未经俞汝猷算明,恐有异同,十七日本县具文申府请发汝猷回县,照前割挨号册查算,抽割念四日方着朱思贤赍解,今查卷案日期,情节一一相符。(61)
嘉善县这一拙劣的割册举动使其彻底丧失了主动,它体现出以区圩登记的田土系统难以在清查归户的基础上与里甲黄册原额的登记系统实现有效契合。在双方历次的会勘中,彼此都发现了对方黄册原额田土中有隐漏的宿弊,嘉秀两县的黄册记载也确实没有完全登录推回的错壤田土,可是由于在最初的丈量中里书混报的情况非常普遍,人户与田土的关系在错壤之上附加以兑粮的混淆,何为本县诡寄,何为隔县错壤遂难以辨别,无法像会稽县那样搞清缺额田土的都图坐落,无奈之下,嘉善县才出此下策,正疆界的要求因缺乏实现的条件而只得作罢。
四、结语
综上所述,自明代中后期开始的土地丈量因其所处赋役变革阶段的不同而在功能上各有侧重,从嘉隆年间的均则到万历年间的均役,丈量后的土地不仅是用于征粮的“税亩”,还是用于摊役的“役田”,以田土编成,以田系人的里甲运作框架逐渐形成。但嘉兴争田的事例则向我们昭示出,人户与田土的复杂关系仍是这一框架内必须要妥善解决的问题。当两者的结合关系因跨县买卖这一特殊情况而变得更加复杂时,以原额主义为旨归的丈量反而造成了一县纳税田土的失额,以恢复原额为目的的会勘却激起了相关利益群体的持久纷争。相对于不定期的土地丈量,一条鞭法后日常里役的佥发则更是时刻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正是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解决方式,决定了明后期直至清初以田土编成的里甲体系的演变形态和阶段性特征。
注释:
①参见[日]川胜守:《中国封建国家の支配构造——明清赋役制度史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年,第503-513页。冯贤亮:《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4页。
②栾成显:《明代黄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61页。
③[韩]权仁溶:《从祁门县“谢氏纷争”看明末徽州的土地丈量与里甲制》,《历史研究》,200年第1期。夏维中、王裕明:《也论明末清初徽州地区土地丈量与里甲制的关系》,《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④万历《杭州府志》卷7《国朝郡事纪下》,第22页。
⑤章懋:《核田记》,载道光《东阳县志》卷6《名宦》,第13页。
⑥万历《湖州府志》卷3《区亩》,第20页。
⑦万历《会稽县志》卷5《户书一》,第12-13页。
⑧民国《鄞县通志》·《政教志》,第318页。
⑨绍兴府税则纷乱及其简化后的形态参见万历《绍兴府志》卷14《田赋志》。
⑩吴时来:《周临海均田颂》,载万历《仙居县志》卷12《诗文》,第38页。
(11)康熙《海宁县志》卷4《赋役》,第8页。
(12)钱江:《丈量末议》,载康熙《嘉兴县志》卷9《事文中》,第12-13页。
(13)钱江:《丈量末议》,第13页。
(14)钱江:《丈量末议》,第13页。
(15)钱江:《丈量末议》,第14页。
(16)钱江:《丈量末议》,第14页。
(17)屠延禧:《复上嘉邑林父师书》,载康熙《嘉兴县志》卷9《事文中》,第18-19页。
(18)屠延禧:《复上嘉邑林父师书》,第19页。
(19)方扬:《丈量凡例》,《方初庵先生集》卷16,《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影印本,集部,第156册,第689页。
(20)方扬:《丈量凡例》,第689页。
(21)方扬:《丈量凡例》,第690页。
(22)方扬:《丈量凡例》,第689页。
(23)徐溥等编:《明会典》卷22《户部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17册,第257页。
(24)《明世宗实录》,卷489,嘉靖三十九年十月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版,第8136-8137页。
(25)万历《会稽县志》卷5《户书一》,第17页。
(26)万历《会稽县志》卷5《户书一》,第17-18页。
(27)万历《会稽县志》卷5《户书一》,第19-20页。
(28)嘉庆《武义县志》卷3《外赋》,第8页。
(29)《明宣宗实录》卷100,宣德八年三月甲寅条,第2236页。
(30)弘治《赤城新志》卷5《版籍》,第1页。
(31)康熙《嘉善县志》,卷4《食货志上》,第2-3页。
(32)《田赋书》,嘉靖《宁波府志》卷24《书三》,第17页。
(33)张选:《忠谏静思张公遗集》卷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影印版,集部第93册,第409-410页。
(34)《田赋书》,嘉靖《宁波府志》,卷24《书三》,第15-16页。
(35)嘉靖《定海县志》卷8《贡赋》,第14页。
(36)“凡业本县之产者,无论军民匠灶寄庄人户,照依前分亩数派立为丁,每丁约银七分”。(天启《海盐图经》卷5《食货篇第二之上》,第4页。)
(37)如海盐县万历二十九年编审:“外县士夫彼处自有优免,毋得混入本县缙绅一概叨免,即有田产原隶本县图籍,一体当差”。(天启《海盐县图经》卷6《役法》,第6页。)
(38)《明宣宗实录》卷64,宣德五年三月戊辰条,第1522页。
(39)光绪《嘉兴府志》卷82《艺文》,第12-13页。
(40)光绪《嘉兴县志》卷11《田赋下》,第36页。
(41)崇祯《嘉兴县志》卷9《土田》,第23-24页。
(42)王庭:《三县田粮问答》,载康熙《嘉兴县志》卷9《事文中》,第6页。
(43)嘉靖《嘉兴府图记》,卷8《田赋》,第8页。
(44)《万历十五年三院详嘉善县照旧足额田粮文卷》,载崇祯《嘉兴县志》,卷9《土田》,第18页。
(45)康熙,《嘉善县志》卷4《田土》,第4-5页。
(46)崇祯《嘉兴县志》卷9《土田》,第24页。
(47)王儒:《三县关会田粮七辩》,载崇祯《嘉兴县志》卷9《土田》,第23页。
(48)以上叙述及引文参见黄洪宪:《与秀水郭中尊论田粮积弊书》,载崇祯《嘉兴县志》卷23《遗文五》,第79页。
(49)以上叙述及引文参见《附黄乡宦辩揭》,载崇祯《嘉兴县志》,卷9《土田》,第53-56页。
(50)崇祯《嘉兴县志》卷9《土田》,第24页。
(51)康熙《嘉善县志》卷5《食货志下》,第27页。
(52)《万历十四年嘉善里老书算查清田数报单》,载崇祯《嘉兴县志》卷9《土田》,第17页。
(53)《万历十五年三院详嘉善县照旧足额田粮文卷》,载崇祯《嘉兴县志》卷9《土田》,第18页。
(54)“万历九年推收底册关推与嘉兴田一万一千九百二十九亩,有嘉兴田与嘉善换粮者止开回六百八十五亩,推与秀水田一万九千三百一十四亩,有秀水田与嘉善换粮者止关回二千六百五十四亩。万历十一年,嘉兴续关去田一千一百九十九亩亩,秀水续关去田一千六十亩,推去太多关回太少等情……”(《万历二十六年嘉善告争田地知府张似良不行查勘竟申本道转申两院批行本县知县郑振先申文》,载崇祯《嘉兴县志》卷9《土田》,第19页。)
(55)以上叙述及引文参见《知府张似良详文》,载嘉庆《嘉善县志》卷8《土田》,第38-39页。
(56)章士雅:《正疆界议》,载康熙《嘉善县志》卷10,第63页。
(57)以上所述及引文参见《万历二十六年嘉善告争田地知府张似良不行查勘竟申本道转申两院批行本县知县郑振先申文》,《三县关会田粮七辩》两文。(崇祯《嘉兴县志》卷9《土田》,第19-29页。)
(58)《三县关会田粮七辩》,载崇祯《嘉兴县志》卷9《土田》,第24页。
(59)以上叙述及引文参见《知县徐仪世申文》,载嘉庆《嘉善县志》卷8《土田》,第40-44页。
(60)崇祯《嘉兴县志》卷9《土田》,第44页。
(61)崇祯《嘉兴县志》卷9《土田》,第49页。
标签:浙江嘉兴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