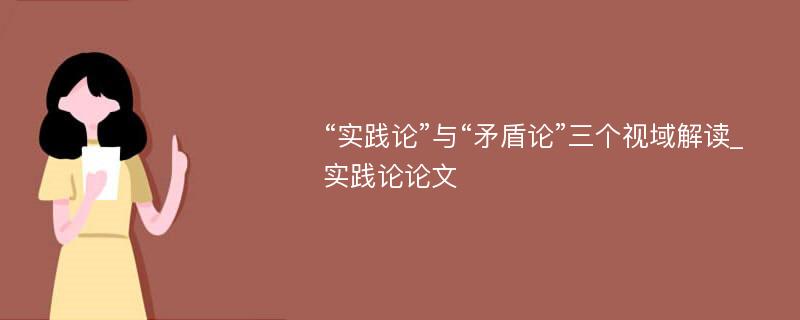
解读《实践论》、《矛盾论》的三种视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践论论文,矛盾论论文,视域论文,三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实践论》、《矛盾论》作为毛泽东哲学的经典著作,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独特的问世历程和重要的历史作用。它们自问世以来,被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解读、诠释和评价。理论哲学、实践哲学与文化哲学是人们解读《实践论》、《矛盾论》三种不同视域。在理论哲学视域中,《实践论》、《矛盾论》的理论内容被系统阐释;在实践哲学视域中,《实践论》、《矛盾论》的实践智慧品格被深刻揭示;在文化哲学视域中,《实践论》、《矛盾论》对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以及领导群体培育的价值得到彰显。分析这三种哲学视域的视界特点,阐释它们的诠释贡献并揭示其存在的问题,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实践论》、《矛盾论》的理论内涵、哲学品格和当代价值。 一、理论哲学的解读视域 对《实践论》、《矛盾论》进行系统细致的理论阐释,在我国曾经是占主导地位的解读方式。如果把这种方式称之为“理论哲学”[1]视域的话,这里所说的理论哲学,不同于哈贝马斯语境中的“意识哲学”或“思辨哲学”,因为它并不简单地与实践哲学或文化哲学对立。因此,所谓理论哲学的视域,在最确切的意义上,是指对《实践论》、《矛盾论》进行体系化解读的方式和视角。显然,理论哲学视域关注的焦点指向哲学理论的逻辑严密以及相应的学术品位。 在对《实践论》、《矛盾论》的体系化解读中,有两种并不完全一样的方式:一种是各色各样的专题解说著作或论文;另一种是中国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在理论哲学视域中解读《实践论》、《矛盾论》是中国几代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教育的熟悉而又习惯的方式。通过理论哲学的解读方式,内含在《实践论》、《矛盾论》中的基础理论成为广大民众耳熟能详的话语。正是在被系统解说的过程中,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实践论》、《矛盾论》,突破其诞生的最初形态(提高青年干部理论思维水平的演讲大纲),成为统一新中国亿万人民思想的理论体系和意识形态。 然而,相应的问题也潜伏在理论哲学的视域之中。著名的毛泽东思想研究者斯图尔特·R·施拉姆在《毛泽东的思想》中说:“自列宁的时代以来,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哲学家的声望,已被认为是共产主义领袖人物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毛泽东当初作这一系列讲演,无疑是以确立他在这方面的地位为目标的,在他之前,也力求具有这种资格。毛泽东在党内的对手都在莫斯科受过训练,在其后的五六年间,他就要同他们展开实力较量。因此,他感到自己容易受到攻击之处是人们可能说他不过是个农民游击战争的领导者,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能力分析抽象的范畴。然而事实不久就表明,毛泽东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演讲并未真正达到预期目标。这些演讲有相当大的部分,尤其是开始讲的那几章,几乎是不加掩饰地照搬苏联的材料,而毛泽东用自己语言表达的地方,结果常常不甚理想。”[2](P58) 施拉姆的上述文字触及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内第一代领导集体诞生的曲折过程,因此很有震撼力。但是,这种理解是在理论哲学视域中形成的,它捕捉到了《实践论》、《矛盾论》与西方哲学专业学者的哲学论著之间的差别,因而做出了“照搬”和“不理想”的论定。这种论定实际上提出了理论哲学对于哲学思想的学术性诉求。 正是在这样的视域下,致力于论证《实践论》、《矛盾论》在理论逻辑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与发展就成为很多哲学工作者的重要使命。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艰苦工作为人们理解《实践论》、《矛盾论》的理论创新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然而,仅仅在理论哲学视域中解读《实践论》、《矛盾论》还不能充分彰显它们的历史背景、丰富内容、实践价值和特殊品格。在这种视域下,毛泽东的革命实践家的角色及其肩负的历史重任被遮蔽了,具体说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理论哲学视域中探讨毛泽东在延安学哲学、用哲学、讲哲学的动机和历史事实不符 事实说明,毛泽东在延安读苏联哲学教科书、做哲学演讲的动机不仅仅是或者主要的不是为了锤炼和展示自己的抽象思维能力,更不是为在党内争权夺利服务。 毛泽东在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一九○八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3](P109)也就是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日战争初期特殊的实践需要激发了毛泽东的读书、演讲和写作热情,这个实践绝不能被狭隘地理解为党内争权夺利的斗争。 斯诺曾经以记者的身份描述过作为《实践论》、《矛盾论》问世“第一稿”——毛泽东延安哲学演讲的背景:“在卢沟桥事变前后的几个星期里,他(毛泽东——引者注)在延安有一段暂时空闲的时间。军队开赴前线了,毛腾出时间来收集材料,准备在(延安)抗大作关于哲学基础的讲演。这批青年学生经过三个月的短期训练,准备在今后几年做政治辅导工作,需要为他们写一些简明而基本的讲义。在党的坚持下,毛写了《矛盾论》和《实践论》,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的日常实例结合起来。”[4](P283-284)斯诺的描述表明,毛泽东学哲学、讲哲学更主要的是为了培养从事政治辅导工作的领导后备军,帮助那些即将奔赴抗日前线的青年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提高他们的理论思维水平。 如果仅仅为了展示自己的抽象思维能力,比较方便的路径是在报刊上发表经过充分修改因而在理论逻辑上比较完善甚至有理论创新的文章,而没有必要“很不合算”地花四天时间备课只讲一个上午那样地“做赔本生意”。事实上,《实践论》、《矛盾论》在抗大演讲以后,并没有立即被精细地修改,独立成篇,也没有大规模地翻印和公开发行。 (二)在理论哲学视域中解读《实践论》、《矛盾论》,不能彰显其深刻的实践意蕴 曾经担负过第五次反围剿军事指挥重任、同毛泽东相处不会很愉快的李德(奥托·布劳恩),在其回忆录《中国纪事》中讲述了他对《实践论》、《矛盾论》的印象。李德尽管很瞧不起《实践论》、《矛盾论》,视之为“庸俗唯物主义”,但是,他说:“毛学习理论的目的,主要并不在于弥补他极其缺乏的马克思主义知识,而是要寻找他能利用的合适词句,来论证他自己的,完全与马列主义背道而驰的观点,更正确地说,来装饰他自己的观点。”[5](P285) 这些否定性论断恰好表明,毛泽东解读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写作《实践论》、《矛盾论》是要阐释新观点和新见解的。这些毛泽东“自己的观点”不是毛泽东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对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哲学提问,其解答思路浸润着中国共产党十六年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是对历史经验的反思和积淀,因而具有面向现实的实践智慧品格。换言之,《实践论》、《矛盾论》采用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术语和理论所表达的即便不是新的理论观点,但在其背后也有着与这些术语和理论原来意境不同的中国革命的实践意蕴。 而在理论哲学视域中解读《实践论》、《矛盾论》,却往往将《实践论》、《矛盾论》和所关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放在同一个平台上。一方面,《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研读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成果;另一方面,《实践论》、《矛盾论》被扩展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这样一来,《实践论》、《矛盾论》与哲学教科书之间的间隔就被消除了,《实践论》、《矛盾论》不同于哲学教科书的品格就被彻底屏蔽了。 (三)在理论哲学视域中解读《实践论》、《矛盾论》往往只能呈现它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谱系中的地位,而不能说明它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变革意义和对于中国现代社会的建构价值 中国有着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诞生地西方的文化传统,中国近代的发展道路也不同于俄国,因而作为中国新文化建构和社会发展理论基础的哲学理论有着特殊的理论蕴涵。仅仅以西方理论哲学建构标准或者以苏联教科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为尺度来衡量《实践论》、《矛盾论》的价值和意义,显然脱离了《实践论》、《矛盾论》发挥作用的社会背景,其结论也必然偏离历史的真实。 二、实践哲学的解读视域 与在理论哲学视域中解读相区别,在实践哲学视域中,我们可以解读《实践论》、《矛盾论》的实践智慧品格。 日本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知名学者新岛淳良对毛泽东的风格有如下理解:“他(毛泽东——引者注)是继承近代中国思想家的传统的革命家之一,但是,他既不是一个工匠式的革命家,也不是一个学者式的革命家,而是一个技师式的革命家……所谓工匠式,是‘迷信经验’,‘受物、习惯和道具所左右’,采取‘不钻研’的态度,而且‘不相信新事物’、‘按照已知的方式行事’。与此相反,所谓技师式,是指‘以无比高超的、最适应时代要求的思想’,‘发现、反省和发明,,‘其思考的对象限于行动本身’,‘他的观念都是行动的观念’。由此可见,毛泽东无疑属于技师式的革命思想家。他与仅仅想‘努力理解’,‘解释自己的观念’,‘尽力把自己的感情作为合理的运动表现出来’的学者式态度无缘。他的作品就是中国革命。”[6](P33-34) 新岛淳良对毛泽东风格的刻画体现了日本人精细的品位,对我们理解《实践论》、《矛盾论》的哲学品格有启发作用。因为众所周知,文如其人,也就是说,一个人的风格会映现在他的文章的品格上。 然而,在实践哲学视域中解读《实践论》、《矛盾论》是伴随着中国当代实践哲学范式的建构而出现的。在实践哲学视域中,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实现了哲学品格的变革,不是具有理论哲学特点的苏联哲学教科书的中国翻版,而是当代中国实践哲学的新形态。 总结有关专家学者的论述,《实践论》、《矛盾论》的实践哲学品格主要体现在: 第一,《实践论》、《矛盾论》创作的指向是“改造世界”的实践。[7]毛泽东学哲学、讲哲学的目的不是为了成为理论家,而是指导改造世界的实践。尤为可贵的是,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对实践的理解比有关哲学教科书的解释要开阔得多、深刻得多。 第二,在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的相互关系上,毛泽东强调理论活动(认识)对于实践的依赖。在这个基础上,他阐释了认识与实践之间互动的发展过程,因而在《实践论》中,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是在实践基础上的辩证统一。 第三,在认识成果目标形态设置上,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强调经过循环往复不断上升的认识与实践互动过程而获得的理论,是以能够对实践发挥指导作用的实践智慧为模本的。在毛泽东看来,再好的理论,如果不能指导实践,或者不被用来指导实践,也是无用的。 第四,在《矛盾论》中,毛泽东通过对辩证法宇宙观的阐释,为人们呈现了一个变动不已、生生不息的世界。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强调重视特殊矛盾,呈现出对实践智慧的明显偏向。 由此可见,相对于理论哲学对于《实践论》、《矛盾论》解说的系统性,在实践哲学的解读视域中,《实践论》、《矛盾论》的哲学品格创新及其实践意蕴得以鲜明地呈现。然而,实践哲学的解读视域仍然不能全面地呈现《实践论》、《矛盾论》对于中国当代发展的深刻影响。换言之,在实践哲学视域中,促使《实践论》、《矛盾论》由延安时期的哲学演讲大纲向后来定型文本转化的社会根源不能得到历史的说明。不仅如此,《实践论》、《矛盾论》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版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之间的细微差别和不同品格,也没有得到深入解析。具体反映在这样两个方面:其一,在实践哲学的视域中,《实践论》、《矛盾论》的变革意义被局限在哲学品格和思维方法的建构上,其对于当代中国文化乃至社会建设的意义则没有得到全面反映。其二,在实践哲学的视域中,施拉姆所触及的“照搬苏联材料”的问题没有得到正面的回应和合理的解释。 三、文化哲学的解读视域 文化问题的研究在中国哲学界被持久关注,文化哲学的建构也有欣欣向荣的态势。值得关注的是,人们对于文化哲学的含义、领域和价值的定位存在歧见。因此,笔者认为,在当代中国,文化哲学视域已经形成,但是,文化哲学范式与理论的建构却还在路上。 作为视域的文化哲学具有以下内涵:第一,将文化作为哲学考察的对象。这是以承认人类精神创造呈现样式多样性和文化作为有机整体存在为前提的。在文化哲学视域中,丝丝入扣的哲学理论和体系化的科学理论固然是人类精神产品的成熟、系统、稳定和严密的形态,神话、诗歌、民俗、诗性思维等同样也是人类精神产品的珍贵表现形式。前者有前者的普遍优势,后者有后者的特殊价值。与此同时,各种文化形式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因此,人类文化在一定意义上是作为有机整体存在的。第二,在对文化做总体性研究的同时,承认在各种不同生活环境中出现的文化表现形式的地域性差异及其多样性。以“两希”文明为源头的西方文化、培育了佛教精神的印度文化和绵延五千年的中国文化之所以经常成为人们比较的样本,是因为它们之间有着不同的风格和意境。第三,文化哲学的考察视野在颠覆传统“理论哲学”精神霸权的同时,强调文化有符号化建构的特点,并不将文化等同于“人化”的活动及其过程,而是更强调人类实践活动的“章法”和“样式”,因此,文化哲学视域不仅与理论哲学视域相区别,而且也与实践哲学视域有所不同。 在文化哲学视域中解读《实践论》、《矛盾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创新对它们的认识与评价: 第一,在承认中国文化特殊性和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理解《实践论》、《矛盾论》的特殊意蕴。 其实,很多学者在这方面已经进行了卓越的研究和探讨。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中,冯友兰不仅将毛泽东与致力于中国文化变革的新文化运动联系起来,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左翼,培养出了它自己的接班人毛泽东”,而且也看出了《实践论》所阐释的认识论与西方哲学论著研究的认识论之间本质的区别。他认为:“《实践论》所谓认识,和西方传统哲学所谓认识,其意义不尽相同。西方传统哲学所谓认识,主要是就个人说的,其主体是个人;《实践论》所谓认识,不是就个人说的,其主体可能是一个社会团体,也可能是整个社会。”[8](P137、150)在《重估毛泽东辩证法中的中国传统元素》中,王南湜指出: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关于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主要矛盾方面与次要矛盾方面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论述,只能在中国的特殊的“象思维”辩证法中得到理解,在西方的“概念思维”辩证法中是不可能存在的。[9] 因此,《实践论》、《矛盾论》尽管在话语体系上有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渊源系统,但其思想内涵却有着中国特有的文化意境。 第二,在承认文化表达形式多样性和文化作为有机整体存在的前提下,关注《实践论》、《矛盾论》作为毛泽东哲学著作与毛泽东的诗文、政论文章、军事著作、重要讲话等文献之间的内在关联。因为《实践论》、《矛盾论》与苏联哲学教科书在遣词用句上有一定的关联性,有人因此提出所谓“抄袭论”的责疑。回应类似责疑的最好方式,莫过于突破《实践论》、《矛盾论》哲学理论的叙述框架,找到它们所内含的主题思想不同于苏联哲学教科书的意境以及非苏联哲学教科书的来源,并探讨它们的发生和发展的真实历程。 比如,《实践论》阐释了“问询实践”的思想法则,这种思想法则无疑不同于凡事“问天”的思维传统。追踪毛泽东的著述不难发现,“问询实践”的思想法则,早在1925年毛泽东创作《沁园春·长沙》时就以“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形式显露,在1936年12月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已经有相当完备的阐释。 由此可见,将《实践论》、《矛盾论》与毛泽东的诗文、政论文章、军事著作以及重要讲话等文献关联起来解读,无疑是将毛泽东的哲学著作看成他诸多著述中的一种,不仅可以体会其内在的发展脉络,而且哲学与非哲学文献之间在文化层面上的内在关联也会更加清晰。 第三,关注《实践论》、《矛盾论》对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的深层影响。 毛泽东的哲学演讲和《实践论》、《矛盾论》的定型文本对于中国文化建设的意义,需要在世界文化发展的平台上加以关照。具体说来,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独特的民族色彩,比如,巫史底蕴、传承悠久、中央专制、混沌合一、独立自足等。但是,伴随着全球化的脚步,中国文化遭遇到了巨大的困境。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相连的是高度集权的专制统治系统,在中国出现文化困境的同时,中国专制统治的治理(领导)系统也轰然垮塌。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并非仅仅是文化层面上的革新,而且也有新的治理模式和领导核心的培育。 毛泽东的哲学演讲以及后来定型的《实践论》、《矛盾论》文本,从文化建设和领导核心缔结角度看,发挥了穿透中国传统治理理念的神秘外壳、消弭中西文化之间的沟壑、重铸当代中国民族精神和领导力量的内在价值。 就中国传统的治理文化而言,其历史传承和文化内涵非一篇短文能够说清,本文仅选取有代表性的案例做一粗略的分析。笔者认为,至今还悬挂在太和殿皇帝座椅上方的匾额和两边的楹联典型地注解了中国专制统治的精神理念在近代的表现样态。匾额是“建极绥猷”,楹联是“帝命式于九围兹惟艰哉奈何弗敬”、“天心佑夫一德永言保之遹求厥宁”。很显然,匾额和楹联表达的精神理念不同于西方近代或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也不同于古典西方文化或中世纪西方文化,简单说来,它表达了对于皇权运作的精神指导和文化“禁忌”。从精神指导的角度看,它指明皇权运作要循道而为,不能主观任性,有理性自律的实践智慧。从文化“禁忌”的角度看,它又将“皇道”归结为“天命”的保佑,表现出神秘文化的精神蕴涵。 对于这样的文化传统,全盘否定和全盘肯定不仅是思维方式上的两个极端,在实践中也是难以做到的。毛泽东有关《实践论》、《矛盾论》的延安哲学演讲和后来定型文本的全国传播,实际上对中国传统文化既有精神穿透的作用,又有批判传承的历史态度。一方面,《实践论》、《矛盾论》揭示了实现国家稳定、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力量是民众的实践,以及面向实践凝聚民众实践智慧的方法、过程和路径。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承认矛盾、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的辩证思维方法和领导方法,从而穿透了中国传统皇权运作系统的神秘意境。另一方面,《实践论》、《矛盾论》将科学的理性精神传导给广大民众,从而提升了民族精神,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建构了当代中国的领导核心。 综上所述,在三种不同的哲学视域中,《实践论》、《矛盾论》被解读出不同的内涵、意境。这三种不同的解读各有所长,它们之间不仅难以相互取代,而且有着互补的关系。就当前现状而言,在理论哲学视域中进行解读,已经走过其历史的辉煌,处于被反思的状态;在实践哲学和文化哲学的视域中进行解读则受到更多的关注,有很多论题需要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