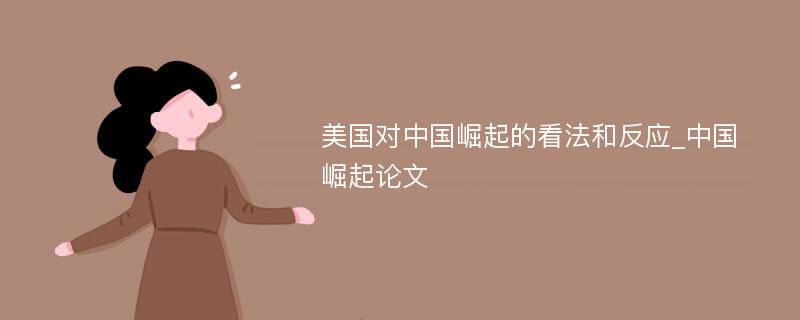
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和反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认知论文,中国崛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不断增强,尤其在某些尖端科技领域所取得的瞩目成就,中国的综合国力显著提高,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也日益扩大。作为21世纪国际政治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①在最近的几年中也获得了良好的发展。与此同时,美国国内关于中国崛起对当前国际秩序以及对美国“一超”地位的影响有着不同的认知和反应。
一、中国崛起挑战美国霸权
在美国国内,持“中国崛起是对美国现有霸权的挑战”这一观点的人不在少数,他们大都是悲观的美国衰落论的信奉者。他们认为,与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相比,中国却在不断崛起,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愈益缩小。随着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原有的国际体系必然受到来自崛起大国——中国的挑战和威胁,而这正是美国政府所特别警惕的。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最主要目标就是防止可能危及美国利益的地区霸权国的出现,竭力维护二战后所建立的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这既是美国国家利益的保障,又是美国霸权地位的象征。因此,无论是实际利益还是其象征意义,美国都不容许有任何挑战。这些人之所以有这样的认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对现实主义理论的教条理解和盲目信任。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际政治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一个国家的安全保障完全依靠这个国家本身。民族国家作为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其根本动机和最终目标就是最大限度地追逐权力。在国际政治中,一个大国的迅速崛起必然会导致现有国际体系中的权力转移(Power Transition),而在国际政治的权力转移过程中,崛起大国与霸权国之间的关系往往都是“紧张、猜疑与冲突”的。②“富强的中国不会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大国,而是一个决心要获得地区霸权的雄心勃勃的国家”,这是由国家的本性所决定的,“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使其生存几率最大化的最好办法是成为本地区的霸主”。③因此,“中国的崛起给东亚和世界带来了诸多挑战”。④
第二,从历史经验的角度出发,认定中国的崛起一定伴随着对现有国际秩序的颠覆和现有霸权国国家利益的损害。这些人通过分析近代以来各个不同时期大国之间的权力角逐得出结论,一个新兴崛起大国是不可能与现有霸权国分享权力的。它们会根据自己的利益来重新设计新的国际秩序和游戏规则,剥夺霸权国的现有权力。一战前的德国正是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它试图通过战争来强制推行符合德国利益的政策,打破了欧洲的均势格局。“在整个近代国际体系历史中,上升大国总是在挑战主导国(霸权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而这些挑战通常会导致战争。”因此,“没有理由相信中国的崛起会是一个例外”。⑤
第三,从美国现实政治和意识形态角度考虑,中国的崛起不仅在地缘政治上构成了对美国霸权地位的挑战,而且在意识形态上也对美国造成了威胁。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美国认为这不仅仅是美国在政治军事等硬权力方面的胜利,而且也是美国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胜利。因此,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推出了“参与和扩展”战略,把在全世界推广美式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作为美国外交的主要目标。但是,让美国感到不快的是,社会主义中国仍然实行着与其相悖的政治经济制度,并在不断地发展壮大。为此,美国政府在“以压促变”的“遏制”(Containment)战略失灵的情况下,实施了对华“接触”(Engagement)政策。这一政策的主要目的有两个:其一,从现实需要出发,展开与中国的对话与合作,有利于美国自身的利益;其二,通过对华接触,可以时刻掌握中国的动态,并以促使中国融入国际体系为手段来潜在地影响中国的内外政策,实现对华政治改造。但是,美国的这一做法并没有达到目标。因此,中国的崛起不仅对由其主导的国际秩序构成了挑战,而且对其所倡导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也构成了威胁,“中国的崛起威胁到美国在东亚经济和意识形态的渗透”。⑥
由此可见,建立在这一认知基础上的美国对华政策必然表现出强硬的色彩。美国有学者指出,迄今为止,美国对华提出了两种战略思想——“遏制”战略和“接触”战略,但它们都只是“理想化”(Ideal)的战略,不具有现实操作性。他们认为,如果采取“遏制”战略,“最好的情况是导致中美之间激烈的安全竞赛,最坏的情况是导致战争”,⑦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而采取“接触”战略也无法保持中美关系的长期稳定,因为“美国的政策制定者相信,与北京长期的和平关系只有在中国实行政治和经济自由化的情况下才有可能”,⑧而通过“接触”战略事实上是达不到这一目标的。华盛顿的对华政策实际上是两者的结合,即“两面下注战略”(Hedged Strategy),但是这种战略仍然存在相当大的风险,因为“美国大战略中包含了预先使用暴力手段来维护美国首要地位的逻辑(the Logic of Anticipatory Violence)”。⑨所以,如果美国继续在东亚保持大量的军事存在,中美之间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就会一直存在。为此,他们提出一个所谓的“离岸平衡战略”(Offshore Balance Strategy)。这一战略的核心是“美国仅在其重要国家利益受到直接威胁时才在海外部署军事力量”,⑩将美国军力分布由全球转向对美国国家利益至关紧要的重点地区。美国实现这一战略,需要有两个方面的前提:一是必须清晰界定美国国家利益,并排列出战略的优先次序;二是必须尽可能地利用其传统盟国,协助美国承担由于美国军队的撤离所带来的防卫真空。
根据这一战略,美国对华政策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继续保持与中国的接触。这种接触,主要是基于经济关系的战略考量。美国需要转变贸易政策,扭转对华贸易逆差,严格控制高端技术流入中国,同时放弃促使中国国内政治自由化的努力,因为美国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它所产生的结果只能是“损害中美关系”。其二,明确美国对台政策,增强台湾防卫能力,保持台海现状,使该地区不出现危及美国利益的局势。其三,利用亚太地区的其他大国制衡中国。要实现这个目的需要至少两个方面的条件,即该地区其他大国对中国崛起心存疑惧以及这些国家具备制衡中国的能力。就当前看来,这两方面的条件都已具备。因此,美国充当“离岸平衡手”(Offshore Balancer)的时机是成熟的、合适的、有益的,“通过实行离岸平衡战略,美国可以更好地保存其相对权力和战略影响力”。(11)
二、中国崛起与美国霸权并存
在美国国内,一些人从较为冷静、客观、理性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崛起给美国带来的影响。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并不必然导致美国霸权的消逝,或者说美国霸权的衰落与中国的崛起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些人认识到,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以及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中国显然会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在某些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甚至还会起到主导性作用。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具备全球主导力量的大国,也不能说明中国已经开始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他们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美国的相对实力下降但绝对实力仍远强于其他国家,尤其是其军事威慑力不容挑战。美国国务卿赖斯指出,美国国力强劲的基础在于“美国社会的动力、活力和弹力(Dynamism,Vigor and Resilience of American Society)”。(12)虽然近期由于世界金融动荡,美国经济出现了衰退的迹象,但它的基础仍然牢固,“自2001年以来,与其他主要工业国家的经济相比,美国经济保持着又快又高的增长,美国毫无疑义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13)针对对美国军费不断增长的批评,赖斯表示,虽然由于发动了两场战争,美国的军费不断膨胀,但是“当前美国防务费用占GDP的比率仍低于冷战时期的平均水平”。(14)实际上,美国在越战中的花费占到GDP的1.6%,而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军费开支还不到GDP的1%。(15)因此,当前的军费开支仍然在美国财政可承受的范围内,并没有影响到美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美国仍然具有超强的综合实力,这一点不容忽视。正因为如此,美国完全能够主导当前的国际政治格局,发挥在国际体系中的领导作用。
第二,二战后所建立的国际体系具有新的特征,是其得以长久维持的重要因素。二战后所建立的国际体系具有与以前所有国际体系不同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1、它是建立在非歧视原则和开放的市场(Market Openness)基础之上的,这为新型大国在该体系内扩大其日益增长的经济政治目标创造了条件。2、它建立了以联盟为特征的领导机制。以前的国际体系往往受制于某一个强国,而现在的体系却是由一批民主国家来主导,加强了该体系的稳定性。3、它有一系列的国际制度和规则来约束国家的行为,为各国在这一机制中加强合作和分享权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基础。总之,这一国际体系是包容的、规范的。新兴大国可以在该体系中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利益要求,而不必打破这一体系,因为新兴大国对于原有国际体系的态度取决于“崛起大国的本性和它对旧秩序不满意的程度”。(16)其中,“更为决定性的(因素)是国际秩序本身的特点——因为是国际秩序的本性决定了崛起大国的选择——挑战这个秩序还是融入其中”。(17)这里包含着两个方面的信息:1、原有秩序是否合理、规范、开放,让新兴崛起国在其中能满足并维护自身的利益;2、原有秩序是否足够的稳定和强大,使得崛起大国要打破这一体系所付出的成本无法估量而打消这个念头,“在任何体系中,如果权力过分集中在最强大国家的手中,要对其进行制衡,这样就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这样就会形成一个门槛,令其他国家望而却步”。(18)制衡尚且不易,要颠覆原有国际体系更是难上加难了。
第三,中美两国都是有核国家,核战争的毁灭性后果将严重制约两国的外交政策。霸权战争是建构、维护和变更国际秩序的有效手段。衰落的霸权国“首要的,最有吸引力的应对衰落的方法是排除问题的根源。当军事优势仍然掌握在衰落中的霸权国手中时,发动一场预防性的战争摧毁或削弱上升的挑战国”。(19)但是,在核武器时代,两个有核国家爆发战争,并非是一国所得即另一国所失的零和博弈,而是双方的同归于尽,“在核战争中,人类遭受毁灭的危险太太,以致根本无法以战争手段来实现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的目的”,(20)“战争导致人类历史变迁的进程已经被废弃”。(21)
由此可见,崛起大国颠覆现有国际体系的威胁微乎其微。因此,对于美国来说,美国的“单极时刻”(Unipolar Moment)虽然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但美国所维持的国际秩序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美国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完善这个体系,增加其包容性,给予中国更大的发言权,让中国成为现有国际体系的建设者和维护者,而不是颠覆者。这样,即使美国在其相对实力下降的情况下,也可以继续保持其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如果华盛顿希望维持其领导地位,她必须增强作为国际秩序基础的规范和制度,使这一秩序更易于加入,更难以推翻”。(22)为此,美国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1、重新确立其作为当前国际秩序支持者的角色,更多地运用多边协商机制,强化美国国际体系领导地位的“合法性”(Legitimacy);2、继续保持国际体系自身的开放性,加大促进新兴国家融入当前国际体系的力度。美国将这些国家纳入到当前国际体系中来,不仅不会影响到现有体系的性质,而且还可以规范这些国家的行为,保障美国的利益。通过上述措施,“美国的全球地位可能会有所削弱,但是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仍会是21世纪的主导秩序”。(23)
三、美国对中国崛起认知的几点共识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基本上了解了美国国内的一些政界和学界精英对于中国崛起所持有的不同态度以及相应的政策取向。超越这些认知差异,我们仍能从中发现诸多共同之处:
第一,中国崛起是一个基本事实。无论是对于中国崛起心存疑忌的悲观者,还是对美国维持其全球领导地位的乐观者,都认识到中国近些年来的巨大发展及其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并开始基本接受这一事实,“中国的崛起无疑是21世纪重大而又激动的事件之一(Great Drama)。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和积极的外交活动正使东亚处于转型中”。(24)
第二,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不可否认,尤其是软实力受到严重削弱。虽然“美国仍是当前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并且这一地位还将持续相当长时间”,(25)但是由于美国在全球反恐行动中采用了“先发制人”的单边政策,表现出穷兵黩武的好战形象,并且曝出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监狱的“虐囚”丑闻,以及在近期所采取的“越境打击”恐怖分子行动,给美国的海外形象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无可争议,美国作为民主典范的海外形象被损害了”。(26)正如美国外交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N.Haass)所言,“美国实力的现状无法掩饰美国在世界地位的相对下降,而伴随美国实力相对衰落的是美国影响力和独立性的绝对减弱”。(27)理解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反应需要同时关注两个变量:其一是中国的迅速强大;其二是美国相对实力的下降。正是由于美国相对实力不如从前,从而对控制国际局势的能力产生了怀疑。因此,美国国内才会感受到来自中国崛起的巨大压力。如果在考察美国对华认知中忽视美国实力相对下降这个变量,我们就无法理解美国对于中国崛起所表现出的那种近乎“神经质”的紧张的原因。
第三,中国仍然是一个地区性大国,与美国之间的差距依然巨大。上述两种认知的人都对此有着清晰的认识。无论是从军事、经济等硬实力方面,还是在制度、文化、价值观等软实力方面,中国都无法和美国一争高低。从中美国内生产总值(GDP)来看,中国2007年GDP达到了32801亿美元,居世界GDP总量的第四位,相当于美国的23.7%。(28)中国人均GDP为2461美元,在全球181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06位,仍为中低收入国家水平。(29)这样的差距不是短时间所能赶上的。许多观察家预计,美国GDP总量到2025年仍是中国的两倍。(30)从军费投入来讲,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表的《2008年年鉴》显示,美国在2007年的军费开支创历史最高纪录,达到5468亿美元,占全球军费开支的40%以上,增幅为6.94%,超过世界平均增幅。在2001年到2007年间,美国军费开支增幅高达59%。(31)据美国《国防新闻》周刊报道,中国2007年度的国防预算约为450亿美元,仅为美国的9%。(32)从军费数据比较来看,中国的军力与美国不可同日而语。况且,中国实行防卫性的国防政策,国防建设的主要目标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关于这一点,西方学者也有同感,“中国的(军事)战略目标、军事能力以及军力结构是相对谨慎(Consevative)的”,中国没有寻求扩张主义目标(Expansionist Goals),当前对军力的投入仍然与这一目标一致。(33)由此可见,“尽管中国正逐步成为一个地区性主导大国,但它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可能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34)中国不可能对美国构成威胁。至于美国国内对中国崛起所表现出的紧张和恐惧,只是美国一贯的心理反应而已。换句话说,美国人有着一种“无病呻吟”的悲情思维,总是喜欢把问题看得很严重,而事实远不是如此。因此,尽管国内有各种要求给中国施加压力以遏制中国的论调,但是布什政府对此权且听之,仍然与中国保持各方面的沟通与合作,使中美关系处于一个稳定、良性发展的轨道。这表明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它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正如国务卿赖斯所言:“我们与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更多植根于共同的利益,而不是共同的价值观”。(35)因此,中美双方都不愿看到中美关系出现倒退,更不愿看到中美之间出现直接的军事冲突。这种共识是中美关系长期良好发展的保障。
第四,冷战后美国政府的战略目标没有改变。上述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形式上好似根本对立,但实质上他们都是围绕着美国总体战略目标展开的,即确保在全球没有挑战其地位的地区霸权国,维持国际格局中的“一超”局面。美国国内对于美国霸权能维持多久,如何保持这种霸权地位进行了诸多研究,提出了许多“大战略”(Grand Strategy)思想。不管这些思想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区别,其总的目标都是指向保持美国在冷战后的全球领导地位,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
第五,中美关系走向的主导权掌握在美国手中。中国的发展虽然让美国在制定其外交政策时需要更多地倾听中国的声音,照顾到中国的利益关切,但是,美国在中美关系的发展中仍然居于主导地位。也就是说,未来中美关系往何处去,主要是看美方的态度和政策如何,“中美关系之间将发生什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华盛顿的对华战略”。(36)因此,中国对于未来美国政府的政策走向应保持密切关注,制定各种应急预案,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美国新政府上台后对中美关系所带来的某些不利影响。
注释:
①Kishore Mahbubani,"American's Place in the Asian Century",Current History,May,2008,p.198.
②G.John Ikenberry,"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Foreign Affairs,Jan/Feb.,2008,p.23.
③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出版,第421页。
④M.Taylor Fravel:"Power Shift and Escation",International Security,Winter 2007/08,Vol.32,No.3,p.83.
⑤Christopher Layne,"China's Challenge to U.S Hegemony",Current History,January,2008,p.13.
⑥Christopher Layne,"China's Challenge to U.S Hegemony",Current History,January,2008,p.13.
⑦同上,第16页。
⑧同上,第15页。
⑨同上,第16页。
⑩同上,第15页。
(11)同上。
(12)Condelezza Rice,"Rethink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2008,p.23.
(13)同上,第23-24页。
(14)同上,第23页。
(15)Fareed Zakaria,"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Foreign Affairs,May/June,2008,p.27.
(16)G.John Ikenberry,"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Foreign Affairs,Jan/Feb.,2008,p.27.
(17)同上。
(18)威廉·沃尔福思:“单极世界中的美国战略”,参见约翰·伊肯伯里主编、韩召颖译:《美国无敌:霸权的未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104页。
(19)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Peking University Press,March,2005,p.191.
(20)保罗·肯尼迪著,陈景彪等译:《大国的兴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出版,第494页。
(21)G.John Ikenberry,"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Foreign Affairs,Jan/Feb.,2008,p.31.
(22)G.John Ikenbeny,"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Foreign Affairs,Jan/feb,2008,p.24-25.
(23)同上,第27页。
(24)同上,第23页。
(25)丁幸豪、邓凡:“孤独的霸权能走多远”,《美国研究》,2003年第3期。
(26)Francis Fukuyama and Michael Mcfaul,"Should Democracy Be Promoted or Demoted",The Washiongton Quarterly,Winter,2007-08,Vol.31,No.1,p.35.
(27)Richard N.Haass,"The Age of Nonpolarity What Will Follow U.S Dominance",Foreign Affairs,May/June,2008,p.46.
(28)刘铮、周英峰:“国家统计局报告显示:中国经济总量已占世界6%",http://news.sohu.com/20081027/n260268849.shtml
(29)陈维松:“2007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461美元,居世界第106位”,http://www.china.com.cn/news/2008-10/29/content_16682186.htm
(30)Fareed Zakaria,"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Foreign Affairs,May/June,2008,p.27.
(31)“统计显示美国去年军费开支占全球总数的40%以上”,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6/09/content_8334957.htm
(32)“国际时评:究竟谁威胁谁”,搜狐网,http://mil.news.sohu.com/20070530/n250305402.shtml
(33)M.Taylor Fravel,"China's Search for Military Power",The Washiongton Quarterly,Summer,2008,Vol.31,No.3.
(34)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出版,第169-170页。
(35)Condelezza Rice,"Rethink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2008,p.13.
(36)Christopher Layne,"China's Challenge to U.S Hegemony",Current History,January,2008,p.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