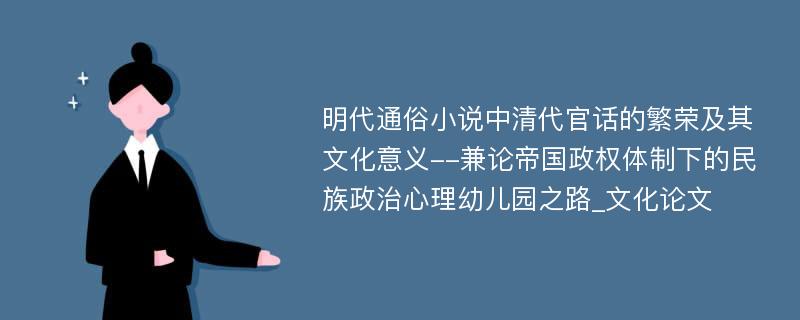
明代通俗小说中清官故事的兴盛及其文化意义——兼论皇权制度下国民政治心理幼稚化的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皇权论文,清官论文,兴盛论文,明代论文,通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代是中国皇权制度恶性蜕变的时期,因而权力体制对国民群体的压迫掠夺及其对国民心理的影响极为严酷(注:关于明代皇权高度专制化趋势所导致的一系列结果,详见拙文《中国皇权制度逆现代性的主要路径——从明代的历史教训谈起》,《开放时代》(广州)2000年第7期。)。然而也就是在明代,清官文化和通俗文艺中的清官故事高度繁荣,出现了海瑞等典型的清官和《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包公传》、《海刚峰公案》等一大批清官故事和故事集。本文认为:正是由于弱势国民群体在现实中根本无法消解专制权力的巨大压迫,所以他们才转而创造出一种广泛而“有效”的心理补偿机制,试图通过对清官的企盼、幻想、艺术张扬等神化方式,以使自己得以在心理上勉强抗衡周围无处不在的黑暗与腐败。这种机制造就了亿万下层国民心中的清官情结和通俗文艺中许许多多的清官故事;而反过来,深受皇权制度之苦的国民只有越加通过这种虚幻的方式平衡现世的不幸,这又为其政治人格和政治心理的进一步弱势化和幼稚化开通了道路。
一、明代权力制度和法律文化对国民弱势群体的压迫
简单说,明代权力制度与法律文化的关系是:高度专制的皇权体系将“权高于法”制度特征的发展到空前的程度。研究者指出:“皇帝是最高的立法者,皇帝发布的诏令敕谕是最权威的法律形式,皇帝的特权凌驾于一切法律之上,从律敕并行到以敕代律,正说明了当时当律的性质和特点。”(注:韦庆远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66-267页。)而这一特质的明代比以往更为突出,即《明史·刑法志·序》记述的:明代将自古以来“敕”(皇帝意志)重于“律”(法律规范)的准则发展到了极端,由此导致中期以后,从皇帝到各级奸吏特务都可以玩法律于股掌之上,并且使明代政治在法律完全变态、特务奸吏横行的伴随下走向极端黑暗的深渊。孟德斯鸠说:“专制国家里,法律仅仅是君主的意志而已。”(注:《论法的精神》第一卷第五章,商务印书馆(北京)1978年版。)而明代的情况显然是这一规律的典型体现。于是当时一切司法程序、法律规定,都成为专制者手中任意亵渎玩弄、最大限度地牟取私利的工具。
权力操纵下“法外法”的恣肆成为明代法律的特点,于是任何大奸巨慝、贪赃枉法者,都可以“公肆赂遗而逃籍没之律”,“密行请托而逋三载之诛”(注:《明史》卷一百九十二《张翀传》,中华书局校点本。)。嘉靖万历前后,国家监察和司法制度在横行的权势面前更成了废纸:“本朝姑息之政甚于宋代,……甚至败军之将,可以不死;赃吏巨万,仅得罢官,是吞舟之漏也!”(注:于慎行:《谷山笔麈》卷之三《国体》,中华书局(北京)1984年版。)而监察官员自己都要俯首听命于权门,亦是通例,这种对权力完全失去制约的政治和法律环境,又反过来极大地刺激了权势者倚仗皇权的纵容而横行不法:
刑法有创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末而极。举朝野命一听之武夫宦竖之手,良可叹也。(注:《明史》卷九十五《刑法志·三》。)
权势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具体例子,比如东厂奸吏专门以搜捕盗贼为名而肆意敲诈无辜——他们酷刑逼迫被害者诬陷攀扯有钱人,待将其财产轧光以后再层层呈报捏造出的罪名,三、四天之内就将其处死灭口,而这些恶行甚至连刑部也绝不敢过问(注:详见(明)李清:《三垣笔记·上·崇祯》,中华书局(北京)1982年版。)。
在这种权力制度下,下层国民的境遇当然极其可悲。张居正早就感叹当时国家司法制度放纵权贵而专门欺压贫弱:“法之所加,唯在微贱,而强梗者虽坏法干纪,而莫之谁;……何国有不伸之法,覆盆自苦,人怀不白之冤?”(注:引自(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十八,中华书局(北京)1981年版)至万历中期以后,所谓的“廉政肃贪”更成了举世的笑柄:
惩贪之法在提问,乃豺狼见遗,狐狸是问,徒有其名:或阴纵之使去,或累逮而不行,或批驳以相延,或朦胧以幸免。……苞苴或累万金,而赃止坐之铢黍;草菅或数十命,而罚不伤其毫厘。(注:《明史》卷二百二十六《丘橓传》。)
传统体制的合法性本是以君主“恤爱子民”、“下养百姓”的伦理原则为支撑,但在明代中期以后的政治环境中,情况却逆变为:
今天下之苍生贫困可知矣。自万历十年以来,无岁不灾,催科如故。臣久为外吏,见陛下赤子冻骨无兼衣,饥肠不再食,坦舍弗蔽,苫藁未完;流移日众,弃地日多;留者输去者之粮,生者承死者之役。君门万里,孰能仰诉!(注:《明史》卷二百二十六《吕坤传》。)
可见在明代权力制度下,百姓备受欺压盘剥而又哀哀无告的局面之怵目惊心;但在完全不具备现代性出路的情况下,他们又只能把“仰诉君门”作为自己超拔于苦境的唯一企盼。
二、明代清官故事的文化内涵和情节模式
明代权力制度对束手无策的国民之百般压迫,以及弱势群体“群门万里,孰能仰诉”境遇,迫使他们通过在幻想中塑造上忠天子、下爱万民的清官而重新建构出仁爱和谐的社会伦理,即如拟话本小说作者的评论: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未做官时须办有匡济之心,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一做官时,更当尽展经纶之手。即如管抚字,须要兴利除害,为百姓图生计,不要尸位素餐。管钱谷,须要为国家足帑藏,不要侵官剥众。管刑罚,须要洗冤雪枉,为百姓求生路,不要依样葫芦。……若是戴了一顶纱帽,或是作下司凭吏书,作上司凭府县,亦为准词状,退纸赎、收礼物,岂不负了幼学壮行的心?(《别本二刻拍案惊奇·奸淫汉杀李移桃 神明官追尸断鬼》)
这已把人们期望清官之心理与他们在黑暗现世中之无奈二者间的关系,展示得很清楚。
明代小说中有对当时吏治和司法制度之痼疾的大量描写,从这些故事中可归结出其四大特性:第一,在君权体制中,无数“蚁民”的卑贱地位(注:对于“子民”的这种卑微地位,明代小说中有许多直接的描写,比如《醒世恒言·两县令竞义婚孤女》:“小人是老相公的子民,这蝼蚁之命,都出老相公所赐!”)、以及由此而来的官吏对他们任意生杀的无限威严;第二,制度性的专横与腐败已经使司法完全蜕变为各级官吏搜刮聚敛的工具;第三;专制威权对于司法官吏之心理的兽性化塑造(如酷刑、滥刑在明代的恶性发展)及其对国民法律文化环境造成的巨大阴影;第四,司法暗无天日以及制度性的府溃所导致的司法昏聩无能。由于清官文化是在此背景下发展的,因而国民对清官文化的企盼和塑造也就具有了与上述性质相对应的一些基本内涵。所以尽管在表面上,明代黑暗的吏治与充满温情的清官文化是截然相反的两种文化形态,但实际上,后者的生成路径,恰恰是由前者设定的!下面具体来看通俗小说对清官文化内容的描写。这些内容包括:
第一,由元代清官故事中惩治权豪势要的模式,转变为清官对民间社会的发奸擿隐。
通过塑造不畏权贵、公正执法的清官形象,使权势者横行不法给弱势群体造成的巨大现实压迫和心理创伤这一恶性郁结得到宣泄和抚平,这曾是清官文化的基本涵,所以在元杂剧中,包公等清官的刚直不阿、为民申冤的形象已经塑造得相当完满。
皇权制度的痼疾之一,就是权势者的肆意欺凌百姓、横行不法。中国历代流治者虽出于维护体制长远利益目的而一定程度对此加以抑制,但皇权体制内部这种自我抑制的规模和效能都很有限。特别是明代中后期,当超常规地掠夺国民已经越来越成为权力体系的生存目的、并且已经完全无法自控制,同时政治权威的这种贪婪的兽性更通过权力结构而空前充分地笼盖整个社会的时候,社会弱势群体的备受压迫感当然会比以往更为强烈。在这种形势下,通过皇权赋予清官的权威而抑制贪官恶霸的势焰,仍然是抑赖于宗法制度和君权制度庇护的子民们之唯一希望;但实际上,这种希望又变得越来越渺茫。
明代清官文化这一重要特点在通俗文艺中鲜明地反映出来。我们知道,元杂剧曾塑造出了一批威势赫赫的清官人物,他们仰仗天子赐予的“势剑金牌”而先斩后奏、痛诛那些蠹政害民的贵戚衙内,并由此而使饱受荼毒的小民们如蒙甘露、重获生机。比如这些酣畅淋漓的段落:
(两淮提刑肃政廉访使窦天章唱:)从今后把金牌势剑从头摆,将滥官污吏都杀坏,与天子分忧,万民除害!(《窦娥冤》)
(包公唱:)叩金銮亲奉帝王差,到陈州与民除害。威名连地震,杀气和霜来,手持着势剑金牌,哎,你个刘衙内且休怪!(《陈州粜米》)
(府尹白:)兀那厮,你听者:圣人为你这河南府官浊吏弊,敕赐老父势剑金牌,先斩后奏。若你那文卷有半点差错,着势剑金牌,先斩你那颗驴头!(《魔合罗》)
这些都是通过清官们因势剑金牌在手而放胆诛讨惩治贪官污吏的喜剧模式,强烈体现出清官文化对已出现裂痕的君权体制加以修复和锦上添花的文化功能,即是元代著名包公戏《陈州粜米》最后的总结:“方才见无私王法,流传与万古千秋!”
与前代清官文学这种基本模式形成对照:一方面,明代的清官文化作品的数量在明代中期以后大量膨胀;而另一方面,除了《包公案》等较多承袭前代特定故事情节的作品还保留一些与元代包公戏大致相似的情节外,上述“把金牌势剑从头摆,将滥官污吏都杀坏”的模式已经大大萎缩了——所以在直接表明明代清官文化的众多小说中,已经很少能见到清官们如何不顾当朝权贵之威势而诛讨贪官、为小民申冤报仇的故事,而至多只有一些对品阶较低官吏和乡宦之劣迹的愤慨,其绝大多数事例仅涉及一般乡宦的勾结下层官府。
比这种有意回避上层权贵横行不法的现实更进一步的是,巡按大人那些诛讨贪官污吏的招牌非但不再具有昔日的感召力,反而成了世人眼中的笑柄,比如《金瓶梅》中的情节:
(巡按御史曾孝序)极是个清廉正气的官。……开了(衙门)大门,曾御史坐厅。头面牌出来,大书:“各亲王、皇亲、附马、势豪之家”。第二面牌出来,“告都、步、按并军卫有司官吏”。第三面牌出来,才是“百姓户婚田土词论之事”。
这位清官巡按如此大张旗鼓地标举自己的职责即在于究弹枉法害民的权贵势要,并向皇帝上本参劾西门庆等人的贪肆不法。没想到西门庆从内线得知奏章的内容之后便有对策:“西门庆道:‘常言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事到其间,道在人为。少不得你我打点礼物,早差人上东京,央及(蔡太师)老爷那里去。”随后有了这样的结果:
(西门庆家人回禀道):“翟爹看了爹的书,便说:‘此事不打紧,教你爹放心。……等他本上时,等我对老爷说了,随他本上参的怎么重,只批该部知道。老爷这里再拿贴儿分付兵部余尚书,只把他的本立了案,不覆上去。随他有拨天关本事也无妨!’”
于是曾巡按的参劾非但不能损西门庆等流氓贪官的毫发,反使自己大祸临头:“太师阴令(宋)盘就劾其私事,逮其家人,锻炼成狱,将(曾)孝序除名窜于岭表,以报其仇。”(注:详见《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第四十八回、第四十九回。)可见在明代,“清官惩戒权贵”这一元代清官故事中确立的模式早已成为水中之月。而正是在这种趋向下,明代清官故事的基本情节模式,才转变为清官们运用威权而对下层民间社会中各种犯罪的剖判明断,以及如何对那些心性奸诈的“顽民”责罚惩戒。
其实,明代小说中对清官文化内涵的概括就已经标举出它们的重心所在,比如《警世通言·老门生三世报恩》中的诗句:“只愁堂上无明镜,不怕民间有鬼奸”——这里的“堂上明镜”恰因与“民间鬼奸”的对立,才具有了存在的意义。又如成书于万历时的《新民公案》,其内容分为:欺昧、人命、谋害、劫盗、赖骗、伸冤、奸淫、霸占等八类。所谓“新民”,语出《尚书·康诰》“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意为人臣尽心竭力辅佐天子,使其能够克承天命。而在吴迁在万历年间为此书所写的《新民录引》中,对清官文化这一的内涵有更明晰的说明:“盖将以明者新之民,而以新者效之君”——即是说清官的职责,是将经过州县官员道德感化才变得心性一新的子民奉效与君王的面前!明代中后期,是皇权专制从上到下向社会一切角落恶性辐射蔓的时期,而恰是此时,清官文化和清官故事的基本内涵完成了上述重大修正和发展,这一现象当然值得留意。
第二,清官故事通过对清官好官们格外“慈养子民”的描写,竭力召唤“民本”政治原则所要求于官僚阶层的道德和职业禀赋(即传统儒家政治伦理中经常说的“下养百姓,以来其心”、“慈爱万民”等等),并以此为基础而重新确认君权及其官僚制度万古不变的合理性。
我们知道,海瑞等一些人在明代中期以后政治极端黑暗腐败的背景下克己行仁,这些不愿同流合污的“清官”力图通过自己的操守不坠而恢复君权社会的理想形态(注:详见《明史》卷二百二十六《海瑞传》。)。与这种自上而下的构建相比,下层国民对清官的构建和塑造更有强烈企盼和高度理想化的色彩,在小说中,清官往往完满体现着民本和仁政的一系列原则,比如借前代故事而称颂唐代崔宰相被贬定州后,“在任果然是如水之清,如秤之平,如绳之直,如镜之明。不一月之间,治得府中路不拾遗”(《警世通言·崔衙内白鹞招妖》),如此众多的高行懿德齐集一身,当然表现出平民小说对清官理想的构建方式。
与现实制度中弱势群体的处处横遭欺凌相比,小说往往通过清官对贫弱无助者的加倍体恤抚爱、格外慈善的克己施恩而表现出清官们的大仁大德。如《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故事中,金玉奴出身微贱,其夫莫稽为了另攀高门,将金玉奴从船上推入水中,意欲将其淹死。结果玉奴暗中为神佑护,脱难上岸。彷徨无计时,恰遇淮西转运使许德厚(“德厚”正是理想伦理的标志)上任行至途中,转运使夫妇得知玉奴的不幸,立刻认其为义女、收留身边。许转运使上任后又恰为莫稽的顶头上司,于是得以凭借自己的威势和善心,撮合金玉奴和莫稽重新结缡、并使金玉奴将莫稽大大教训一顿。这个故事完全没交代许德厚夫妇何以会对金玉奴这样一个地位低贱、无处依栖的女子加以无限爱怜和无私济助,只是叙述这样的义举完全出自许德厚夫妇的天性,而故事的结局更突出了这种仁爱带来的整个社会伦理的和谐:
自此莫稽与玉奴夫妇和好,比前加倍。许公夫人待玉奴如真女,待莫稽如真婿;玉奴待许公夫妇,亦与真爹妈无异。连莫稽都感动了,迎接团头金老大在任所,奉养终身。后来许公夫妇之死,金玉奴皆制重服,以报其恩。莫氏与许氏世世为通家兄弟,往来不绝。
可见,在社会伦理体系出现危机、底层社会的成员走投无路或者各种社会矛盾纷杂无序的情况下,清官及时出现、及其“其仁如天”的道德禀赋和威行无阻的政治权势,乃是克服危机并导致社会体系在更高的境界中复归于和谐完美的关键。类似的故事在拟话本小说中很多,例如《醒世恒言》中的《两县令竞义婚孤女》、《初刻拍案惊奇》中的《李克让竟达空函 刘元普双生贵子》等等。由此可以看出上述模式乃是国民心理和通俗小说的一种普遍定势。
再看《醒世恒言》中《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的例子。这篇故事具有典型性,主要是因为它通过十分复杂的情节设计,表现出以清官出现为标志,从而使平民社会中原本不可开交的矛盾豁然转机的故事模式。故事梗概是:医家出身的刘公生有一对儿女,儿子刘璞一表人材、学业已成,女儿慧娘姿容艳丽,受聘近邻裴家,尚未出嫁。刘公一心给儿子完婚以后再嫁女,所以为儿子聘下孙寡妇之女珠姨,而珠姨还有一个弟弟孙润,与姐姐生得同样美貌,且已与徐家之女定亲,珠姨姐弟“加添资性聪明,男善读书,女工针指”——总之,这些平民百姓原本的生活前景和伦理关系都十分惬意可观。不想刘璞成亲在即,突然身染重病,渐渐不起。刘公为了救治儿子,意欲给他成亲冲喜;而孙寡妇生怕刘璞果真病重,将女儿嫁他后耽误了女儿的一生,又怕自己回绝了刘家的婚事之后,刘璞康复,也是耽误女儿。情急中她令的儿子孙润乔装后代替女儿去成亲,以便观察刘璞的病情究竟如何以再做决断。而刘家因为儿子病重不能起身成亲,也是手足无措,无奈中只好令刘璞的妹妹慧娘代替哥哥迎亲成礼,并在婚礼后服待“新嫂嫂”。不想孙润乔装的新人与慧娘几日一同起居间,竟然相互爱悦而私下偷欢,最后露出马脚,并使这阴差阳错中的羞玷吵得四邻皆知。于是,刘家向孙寡妇兴师问罪;而裴家打上刘家门来,质问刘家既然将女儿慧娘许给裴家,何以又闺帷不修,出此丑事。故事发展至此,各方汹汹不已,搅成一团,眼看毫无出路,只好到乔太守衙门一求公断,由此使局面立时改观,小说写道:
这乔太守虽则关西人,又正直,又聪明,怜才爱民,断狱如神,府中都称为“乔青天”。
这位“青天”审明原委,又见孙润、慧娘郎才女貌、相互爱恋,遂当堂剖判:令刘璞、珠姨依旧成婚;孙润、慧娘将错就错,结为夫妇,且将二人各自原先所收裴家和徐家的聘礼原物退回;又见裴家之子裴政与徐家女儿“也相貌端正,是个对儿”,遂判二人结为夫妻。因为这样一大套拆东补西、颇有游戏色彩的命运安排是太守的擘划主张,所以三对新人和四家父母对之均无异词,于是所有人物的结局也就都异常完满:
裴九老道:“老爷明断,小人怎敢违逆?但恐徐雅不肯。”乔太守道:“我作了主,谁敢不肯!……”徐雅见太守作主,怎敢不依,俱各甘伏。……乔太守写毕,叫押司当堂朗诵与众人听了。众人无不心服,各各叩头称谢。乔太守在库上支取喜红六段,叫三对夫妻挂持起来,唤三起乐人,三顶花轿儿,抬了三位新人。……此事闹动了杭州府,都说好个行方便的太守。人人诵德,个个称贤。……乔太守又取刘璞、孙润同榜登科,俱任京职,仕途有名,扶持裴政亦得了官职。一门亲眷,富贵非常。
从这个家喻户晓的故事中(“乱点鸳鸯谱”已成为一句成语),可以清楚地看到,“清官模式”中三位一体的要素:清官的廉明无私、怜才爱民→子民们对清官给予自己命运一切安排指派的恭顺无违、感恩叩谢(“老爷明断,小人怎敢违逆”;“人人颂德,个个称贤”)→这种对青天大老爷的恭顺膜拜给子民们带来的宗法制度中空前的世俗利益(“仕途有名,……富贵非常”),以及用这种慷慨许诺而诱使国民沉溺其间的极其廉价的喜剧文化心理。
上述三位一体的清官模式在明代中后期这专制主义空前发展的背景下发育成熟,其原委当然更是值得留意——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中,君权是唯一能够使宇宙间万灵万物陶然而乐、熙然以生的至上力量,明代理学对于这一原则当然更为强调,如胡居仁阐释万物得以安行其道的根本原因:“惟王道能使万物各得其所。”(注:《明史》卷二百八十二《胡居仁传》。)而明代中期以后空前发达的清官文化,则显然是将君权的这种“政治超能”空前大规模传导给代表君权而统治控御子民的清官们;并由此而在“王道”日益颓败腐溃的无奈中,诱使甚至是强迫国民对这越来越像海市蜃楼般虚幻的美景,予以加倍的眷恋和憧憬。因此理学家上述头巾气的论说,在市井文学中被自然而然地转换成了最通俗、最深入下层国民文化心理的警句:“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警世通言·金令史美婢酬秀童》)
第三,与“贪墨成风”、对小民敲骨吸髓和百法欺凌的官场大潮相反,清官故事力图表现清官们的廉洁高尚人格,以及通过对这种人格神圣性的渲染而印证的君权制度和宗法伦理的永恒价值。
如果说,海瑞等人修齐治平的努力在“贪墨成风,生民涂炭”的现实中得到的都是悲剧性结果,那么同样的企盼在清官故事中,却总是以廉价喜剧的形式得以加倍兑现,并由此而在无法消解和日益致命的现实悲剧表面,抹上一层格外赏心悦目的油彩。
明代通俗小说中经常利用各种故事中的情境而彰显清官们的极端廉洁,比如《醒世恒言·一文钱小隙造奇冤》的故事中,歹人的最终败露和天理的张扬,都是因一位清官的主持审案,而这位官员的禀性是:“为官清正廉明,雪冤辨奸。又且一清如水,分文不取。”又比如《初刻拍案惊奇·李克让竟达空函 刘元普双生贵子》中描绘出一位矢志不与举世贪黩同流合污的清官形象:
裴安卿做了郎官几年,升任襄阳刺史。有人对他说道:“官人想来清苦,今得此美任,此后只悉复归不愁贫了。”安卿笑道:“富自何来?每见贫酷小人,惟利是图,不过使这几家治下百姓,卖儿贴妇,充其蠹囊。此真狼心狗行之徒!天子教我为民父母,岂是教我残害子民!我今此去,惟吃襄阳一杯水而已。贫者人之常,叨朝廷之禄,不至冻馁足矣,何求富为!”……莅任半年,治得那一府物阜民安,词清讼简。民间造成几句谣词,说道:“襄阳府前一条街,一朝到了裴公台。六房吏书去打睡,门子皂隶去吹柴。”
可见在这样的故事模式中,清官的不顾举世贪竞聚敛而忠于“天子教我为民父母”的职责,不仅成就了其个人的高风亮节,而且注定会带来一连串制度性的政绩(“物阜民安,词清讼简”),甚至使明代势苦洪水猛兽的胥吏之害(注:由于制度性原因,明代吏治的腐败和兽性化颓势发展到“若泰山之不可拔,决水之不可御”的程度(详见侯方域:《壮悔堂文集》第十一卷《额吏胥》、顾炎武《日知录》卷之八“胥吏”条,并参见拙文《明代流氓文化的恶性膨胀与专制政体的关系及其对国民心理影响》,《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2、第5期连载);而这种空前的黑暗,正是明代通俗小说中大量衙门场面和吏治黑幕情节的基本背景。)烟消云灭(“六房吏书去打睡,门子皂隶去吹柴”)——与现实中吏治和整个政治伦理的日益腐败相反,通过这个模式,宗法伦理不仅不再贬值腐溃,并且更可以通过清官而兑现出下层国民渴望的一切。如果注意到这个故事结尾处特意交代的裴安卿因为人清忠、死后被上帝“敕封为天下都城隍”,则更可以看到清官人格极大升值的实现方式。
再看《二刻拍案惊奇》中《韩侍郎婢作夫人 顾提控掾居郎署》所述一个更完整典型的故事:明代弘治年间,直隶太仓州衙门中有一吏典顾芳,平日常在卖饼的江老儿家中歇脚,老儿尊称他为“提控”。顾提控家有贤妻,江老儿有一十七岁女儿爱娘,容貌非凡,于是顾提控“便与江家内里通往来竟成了一家骨肉一般。”不想江老儿遭人嫉妒,遂有流氓唆使海贼诬他是窝主,结果平白吃了一场无头官司,被一群如狼似虎的衙役将家中抢劫一空,幸亏顾提控拿出“差使钱”打发了众衙役,次日又在知州面前力保蒋老儿乃善良人户,才使他从冤枉官司中脱身。蒋老儿挣得性命回家,一心要报答顾提控,无奈劫后家无余物,只好将好儿爱娘送与顾吏典为妾以表一片诚心。而顾提控坚辞不允,蒋老儿于是亲自将爱娘送至顾宅,以至连顾提控妻子也以为丈夫是“有意留住的,今夜必然趁好日同宿。”不想顾提控却全然是一幅大仁大德的心肠:
提控娘子问道:“你为何不到江小娘那里去宿,莫要忌我。”提控道:“他家不幸遭难,我为平日往来,出力救他,今他把女儿谢我,我若贪了女色,是乘人危处,遂我欲心,与那海贼指扳、应捕抢掳,肚肠有何两样?……我意欲就此看个中意的人家子弟,替他寻下一头亲事,成就他终身结果,也是好事。
故事以顾吏典的乐善好施、持身清正,而与当时社会论理的普遍堕落和衙门官吏的贪婪凶残加以直接的对比。在此基础上,故事通过情节的发展和结局进一步表现出清官文化的神圣意义:由于吏典的秉正无私,爱娘得以全身回家,后来有幸嫁给朝中显宦韩侍郎做了二房,并得了皇帝班赐的夫人封诰;而顾吏典又恰好升迁在韩侍郎衙门中为属官,爱娘诚心报恩,将自己的原委告诉丈夫,于是侍郎与顾吏典彼此更有一番意料不到的极大荣耀:
(侍郎)竟将其事写成一本,奏上朝廷,……孝宗见奏,大喜道:“世间那有此等人?”……侍郎道:“此皆陛下中兴之化所致,应与表扬。”孝宗到:“何止表扬,其人堪为国家所用……礼部乃风化之原,此人正好。”……提控闻报,犹如地下升天,……须叟便有礼部衙门人来侍候,伏侍去到鸿胪寺报了名,次早,午门外谢了圣恩,到衙门到任。正是:昔日箫主吏,今日叔孙通;两翅何曾异,只是锦袍红!……后来顾主事三子,皆读书登第,主事寿登九十五,无病无终。此乃上天厚报善人也。
小说塑造出顾吏典这样仁德过人的官吏形象、尤其是通过他的清正廉明如何得到“圣上”和“皇天”双重报偿,竭力证明了民本政治和清官理想崇高的终极价值;而这种努力,也正因为是在明代极端黑暗贪酷的吏治现实中产生的,而更显出直接的补偿功能。
第四,小说故事通过清官的见微知著、断狱如神,不仅表现出他们对纷繁世情的了如指掌,更表现出清官对天道奥秘的神奇把握。而这种把握对“超能政治智慧”的垄断又具有双重的意义:从明代的现实意义来说,它是下层国民在对当时“百事朦胧,天下都成瞎帐之事”的境遇中(注:《西湖二集》第六卷《姚伯子至孝受显荣》,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1981年版。),对这种空前昏聩吏治唯一可能的补偿方式;而从更长久的时段来说,它竭力凸显了君权制度中清官的神圣性及其对天道神意的体现、以及在此基础上对无知无识之“草民”群体统治的合法性。下面具体来看。
由于明代吏治的日益极端腐化和行政制度的痿痹失效、以及权势者和流氓的横行不法,所以暗如覆盆、百冤无诉就是整个下层国民的一种普遍生存状态而不再仅仅是个别的遭遇。而正是这种状况,造成哀哀无告的国民只能把走出困境的愿望寄托在清官的明察秋毫、摘奸发覆之上,明代清官故事《古今小说·陈御史巧勘金钗钿》中就有这样的铺叙:
如山巨笔难轻判,似佛慈心待细参。公案见成翻者少,覆盆何处不含冤!
可见正是因为满目“覆盆何处不含冤”的现实悲剧,所以饱受其苦的人们才殷切企盼那些执掌着自己生死的官吏们能够“似佛慈心待细参”。而这个故事的情节在明代公案小说中也有相当的代表性;故事写江西赣州的鲁廉访使,曾为其子鲁学曾与通家顾佥事之女阿秀订下婚约。不想二人还未成婚,鲁廉访使就一病身亡。因鲁廉访使在世时为官清介,所以他死后鲁公子家事日渐消乏。顾佥事见状颇有悔婚之意。阿秀母女不以顾佥事嫌贫忘义为然,所以使家仆私下传语鲁公子,令其偷偷上门,意欲瞒着佥事而赠予公子财物,使其有力迎娶阿秀。不想消息被鲁公子的表兄梁尚宾得知,他诓骗鲁公子在家痴等了两天,而自己却假冒鲁公子溜到顾家骗得财物首饰,又借机骗奸了阿秀之后,才得意扬扬地回到家中打发鲁公子出门。待真鲁公子应约到顾佥事家中,阿秀母女才知道自己为假冒者所骗,阿秀因羞自缢身亡。顾佥事得知女儿已死之后,顾忌外面声名不好,所以将一腔愤怒加在鲁公子头上,认定是他骗去了财物并杀死了女儿,故此打通官府,“必欲置鲁公子于死地”,而鲁公子在酷刑下只得自认罪名,于是被问成死罪。
这个情节的发展在清官故事中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它包含了一些基本的程序模式(无辜受害者令人同情的清白身世→他在现实社会中孤苦无助的弱者地位→忘恩负义小人的奸诈诡谲和忍心陷害→世人的懵懂无识、尽落骗局之中→官府的颟顸昏庸、酷刑定罪,等等)。而正是这种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关口,清官的出现使局面有了戏剧性转机:“(陈御史)少年聪察,专好辨冤析枉,其时正奉差巡按江西。……莅任三日,便发牌按临赣州,吓得那一府官吏尿流屁滚。”而这位御史大人破案的手段也颇有代表性:他先是重新审问当事者,于是察觉了真罪犯的蛛丝马迹。随后,御史微服到门,诱使得意忘形的梁尚宾拿出他从顾佥事家骗得的首饰,于是人赃俱获,真相大白——总之,清官的及时出现,以及他的赫然威势和细勘明察、神鉴秋毫,是冤狱发覆的唯一途径,因此这救星的一旦出现,也必然使久处绝境的子民们顿逢生路,并由此生出对大救星的无限感恩戴德(小说原文为:“奸如明镜照,恩喜覆盆开。生死俱无憾,神明御史台”)。
类似的结局在拟话本的清官故事中很多,如写某商人被人谋害之后,人命官司告到当地官府,结果不仅毫无头绪,反而使无辜者在酷刑之下顶了莫须有的罪名;幸得许尚书在山东巡按,经过百般周折查出真凶,于是受害者一家感激莫名:
……合家多感戴许公问得明白,不然几乎一命也没人偿了。……讨枝香来点了,望空叩头道:“亏得许公神明,仇既得报,银又得归。愿他福禄无疆,子孙受享!”举家顶戴不尽。有诗为证:世间经目未为真,疑似由来易枉人。寄语刑官须仔细,狱中尽有负冤人。(《二刻拍案惊奇·许察院感梦擒僧 王氏子因风获盗》)
可见正因人们无可逃遁地羁身于“狱中尽有负冤人”的司法制度之下,所以有幸遇到“明白”的清官才成为子民们唯一可以寄托微茫之希望的所在。
在了解了以上内容以后,应该注意到清官故事模式中的一项重要的内容,即通过对清官辨察力的百般神化而赋予他们超凡的政治资质,从而使他们具有对世界本质的理解和对子民统治权的双重垄断。上文指出,与明代中后期现实社会中各级官吏的昏聩懵懂,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无穷冤狱成为对照,小说中的清官们总是具有辨识秋毫的明鉴,并且能够以此为利器而手到擒来地破解各种疑难。现在尤其要注意的是,清官的这种明鉴并不仅是世俗社会中一般的聪慧多识,相反,它更多地是一种来源于天道和神明的超凡智慧,是一种能够窥破一切尘障的神圣能力。在明代小说中,这种神异特性成为了清官的专有禀赋,而对这种禀赋及其在统治子民过程中意义的描写,也成为了清官故事的一种基本情节模式。
早在元杂剧包公故事中,包公就因其是世俗正义的化身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神界的权威,比如《盆儿鬼》对包公的形容:“人人说你白日断阳间,到得晚时又把阴司理”;《生金阁》说:“千难万难得见南衙包待制,你本上天一座杀人星,除了日间剖断阳间事,到得晚间还要断阴灵。只愿老父怀中高揣轩辕镜,照察我这悲悲痛痛,酸酸楚楚,说无休,诉不尽的含冤负屈情。”
到了明代故事中,清官们的上述神异禀赋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那么,清官这种神圣和神秘的力量何以会在明代日益显著?这种超凡禀赋的文学和文化学意义又是什么呢?
从文化史来看,明代清官文化的这一性质其实是复活了十分古老的文化形态。在人类文明的初期,人们无力认清世界众多事物和现象的原因,而这些事物和原因又随时关系着人们的生死存亡,所以他们只能通过宗教崇拜的方式,把洞察万物的希望和能力集中赋予崇高的神明及其在尘世的代表。所以在氏族文化中,酋长、祭司、巫师等对世界的神奇洞察力,不仅是其神圣权威的基本要素,而且往往又是与他们政治权威和道德领袖的地位结为一体的。如在中国神话中,神帝仓颉有四只灵光四射的眼睛,所以他能够洞察天地间的一切隐秘;民间传说天宫中也有千里眼、顺风耳之类具有神奇感知力的官员,以保证玉皇大帝对世间万物的随时洞察无误。由此可以知道古代社会的一项重要的原则,即统治者政治权威的主要来源之一,就是他绝对地具有蒙昧的子民们所没有的对世界隐秘本源的神奇洞察力。马克斯·韦伯将统治者的这种神奇禀赋称为“奇里斯马”(charisma),他具体解释这种特有的统治魅力:
“魅力”应该叫做一个人的被视为非凡的品质(在预言家身上也好,精通医术的或者精通法学的智者也好,狩猎的首领或者战争英雄也好,原先都是被看作受魔力制约的)。因此,他被视为天分过人,具有超自然的或者超人的,或者特别非凡的、任何其他人无法企及的力量或素质,或者被视为神灵差遣的,或者被视为楷模,因此也被视为“领袖”。
韦伯接下来指出,在“魅力型”社会统治结构中,统治“非凡的品质”乃是其统治“合法性”的基础,而它一旦丧失了这种神奇的能力和魅力,其统治的神圣性和合法性也就会相应消失(注:详见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册,商务印书馆(北京)1998年版,第269、270页。)由此可知,对于统治权力来说,这种来源于“神的恩赐”的洞察力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般来说,上述对世界隐秘本源的神奇超凡洞察力总是极严格地为神圣的天帝所必需和独有,比如儒家经典中对帝喾和大禹明察天下万物的描写:“生而神灵,……聪以知远,明以察微”;“履四时,据四海,平九州,戴九天,明耳目,治天下。”(注:《大戴礼记·五帝德》,《大戴礼记解诂》,中华书局(北京)1983年版,第120页、125页。)又由于天子帝王等等被认为是神明在尘世代表者,所以他们也就相应地具有了这种神奇的洞察力:
天子者,与天地参(叁)。故德配天地,兼利万物。与日月并明,明照四海而不遗微小,……万事得其序。(注:《礼记·经解》,十三经注疏本第1610页。)
在这里,天子绝对的统治权威、他至高无上的道德禀赋、“明照四海而不遗微小”的超凡明察、以及唯有天子才能使时整个宇宙万物各得其序的伟大制度规范力,这些显然是彼此一体、互为支撑的。但是,当传统社会发展到各级官吏制度已经能够充分体现最高君权制度的时候,上述文化禀赋和功能,就被原封不动地向下传导给了君权最理想的体现者——清官。于是,与《礼记》中天子文化禀赋的结构完全相同,清官们的禀赋也同样是多元一体的,即:他是“号令出时霜雪凛,威风到处鬼神惊”(拟话本小说惯用语)的绝对权力之代表;是宗法道德的体现者和裁判者;是使万千原本注定要颠沛失怙的子民安居乐业的大救星;同时也必定具有明察秋毫、神鉴一切赜隐曲奥的非凡洞察力。
清官上述特质在明代的日渐凸显,当然更有切实的现世意义——如果将明代中后期的官吏阶层的实际情况与神赐的非凡能力这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加以对比,可以立刻看出:由于当时“百事朦胧,天下都成瞎帐之事”的昏聩吏治,所以不仅政治体系的权威本身受到极大的质疑,而且亦使国民对整个世道和天道秩序的信仰发生了极大的动摇,而正因为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所以人们对清官神圣超凡洞察力的企盼才表现得十分强烈。也就是说:恰恰是现实司法和吏治制度空前的昏聩和日益的沉沦,才使得越来越多沉冤到底、走投无路的百姓,那样热切渴望和想象着清官们如何一面天性爱民如子、体恤下情,同时更上层楼地具有明辨秋毫、心通神明的超凡禀赋。所以与元杂剧对包公拙朴的神化方式相比,明代对清官神奇洞察力的渲染和塑造,是一种远为完整、奇异的清官神话模式。下面来看明代清官故事中常见的两种类型及其文化意义:
其一,每当遇到无头案和现世力量无法解析的疑难时,清官们注定可以通过梦感通神、或者因为直接领受来自神灵的神秘启示,从而手到擒来地破解这些疑案。这一模式在清官故事中极为普遍,例如写包公遇无头案时于梦境中得谶语和神启,或祈拜求神而得神助的,有《警世通言·三现身包龙图断冤》、《包公案》中的《观音菩萨托梦》、《锁匙》、《龙骑龙背试梅花》、《兔戴帽》、《详情公案》中的《梦黄龙盘柱》等极多的故事;写清官梦中得神启和谶语并由此而擒得杀人盗贼的有《拍案惊奇·李公佐巧解梦中言谢小娥智擒船上盗》、《二刻拍案惊奇·许察院感梦擒僧 王氏子因风获盗》等;写清官白日得神示,则有《别本二刻拍案惊奇·奸淫汉杀李移桃 神明宫追尸断鬼》中的黄参政,他在马上时“一阵旋风在马足边刮起”,遂引导他揭破和尚杀人之命案。甚至还通过更为神秘而又五花八门的方式,随时给予清官以析难破疑所必需的神启,比如《明镜公案》上卷《舒推府判风吹“休”字》、《项理刑辨鸟叫好》、《曹察院蜘蛛食卷》,以及《西湖二集·周城隍辨冤断狱》等等,以空中平白吹来的谶语、鸟鸣、苍蝇的飞集不去、蜘蛛在纸上啃食出的痕迹之类代表天意而标示出破案线索,等等。
那么清官故事中如此普遍而一致的模式之形成,其原因和意义何在?上面指出,明代以后,原本是天神和帝王禁脔的神奇洞察力,被渴望在黑暗吏治之下获得喘息机会的大众文化向下传导给了清官(君权制度最理想的体现者)。而现在我们看到,为了实现对君权制度的这种修补,大众文化普遍采用了对之加以神化甚至是“巫魅”(马克斯·韦伯对前现代社会的定义)化的方法,所以清官们正是通过这种明显向原始巫术复归的方式,才具有了作为对现世官吏阶层之昏聩补尝的神奇能力。反过来说,弱势群体只能将自己命运的希望寄托于神异万能的清官,这种虚幻思维在国民心理中的积淀和定型,则注定使巫魅性长久而深刻地“魇魅”着我们民族的政治和法律观念、阻碍着我们走出中世纪臣民社会的进程。
其二,清官通过个人“微服私访”、以及随后的对自己政治权威的全面展示而破解疑案、解民倒悬。这一程式在《陈州粜米杂剧》等元代包公戏中已出现,及至明代的清官故事中则更为典型和普遍,比如《警世通言·李谪仙醉草吓蛮书》故事中的李白“打扮做秀才模样,身边藏了御赐金牌,……听得人言华阴县知县贪财害民,李白生计,要去治他”,他故意唐突县官,入狱之后才亮出御手调羹的身份和金牌圣旨,结果吓得县官磕头求饶等等;再如《古今小说·陈御史巧勘金钗钿》中的陈御史独自装扮成布商偷偷从衙门中出外四处打探,遂发现真正的罪犯并勘破其诈伪;又比如《西湖二集·周城隍辨冤断案》中所述:周新“每巡属县,尝微服,触县官之怒,收系狱中,与囚人说话,遂道一县疾苦。明日所属官往迎,乃自狱中出,县官恐惧伏谢,竟以罪去。因此诸郡县吏闻风股栗,莫敢贪污。”至于公案小说集中的清官,则更是经常以此类方式才得以破案除奸,比如《包公案》中的《包袱》、《厨子做酒》等许多篇什皆是如此。
微服私访(往往还因此遭受欺凌和磨难)→尽览民间下情(或勘破疑团迷雾)→回衙施威而一举使冤情大白、奸佞落网,这种模式在清官故事中的广泛存在当然不是偶然,由此而反映出的是一种普遍的诉求:就如现实中司法者的无能导致了清官只能越来越多地依靠梦境中的神启而破解疑案一样,腐溃至骨的明代官吏体系也已经完全无助于公正的司法,因此下层国民只能将希望寄托于清官个人以完全摆脱(甚至是凌驾)这套体系的独立司法行政方式。但另一方面,由于传统社会又根本无法提供除皇权体系之外的权威,于是这处超越官吏体系的幼稚愿望,其终点最终还是只能复归到对皇权和官僚体系巨大权威的依仗和炫耀之上——就像许多故事中清官微服而探得民情冤狱之后,立即亮出自己的高高在上的官阶,于是将刚才还在耀武扬威的贪官奸吏们吓得屁滚尿流。
结语:清官文化的畸形繁荣与国民政治文化心理的幼稚化
康德对“父权政治”评价可以作为明代繁荣的清官故事之对照:
一个政权可以建立在对人民的仁爱的原则上,像是父亲对自己的孩子那样,这就是父权政治(imperiumpaternale)。因此臣民在这里就像是不成熟的孩子,他们不能区别什么是对他们真正有利或有害,他们的态度不得不是纯消极的,从而他们应该怎样才会幸福便仅仅有待国家的领袖的判断,并且国家领袖之愿意这样做便仅仅有待自己的善心。这样一种政权乃是可以想像的最大的专制主义——这种体制取消了臣民的一切自由,于是臣民也就根本没有任何权利。(注: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北京)1991年版,第183页。)
被统治者们必须仰赖和感戴统治者的“仁爱”和“善心”,这种感恩戴德的真正基础乃在于庶民的政治品格永远沉论在“不成熟的孩子”的状态;而反过来,这又成为“最大专制主义”的前提,康德已经将“开明专制”的这种内在的逻辑关系阐释得很清楚。而明代以后高度繁盛的清官救世、清官除奸等等故事,正鲜明地表现出在畸形政治体制下,国民心理向“不成熟的孩子”及“最大的专制”的方向严重扭曲与贬值的趋势。
清官文化和清官故事由元代的一度流行、到明代初年的完全消歇,再到嘉靖以后的高度繁盛,这一发展经历了U字型过程,孙楷第先生说:“大概包公故事的传说,起于北宋而泛滥于南宋和金源,至元朝则名公才子都来造作包公的故事。……(元代包公剧)实在不算少。到了明朝洪武以后,以包公案故事入剧的风气似乎消歇下去了,但至嘉靖以后包公案故事又复兴起来。”(注:《包公案与包公案故事》,孙楷第著:《沧州后集》,中华书局(北京)1985年版,第78页。)他指出的明朝初年“包公戏”创作沉寂的事实,其实是当时政治气氛和法律文化之必然,因为朱元璋确立的法制理想,是普天下的臣民以充分体现他统治威权的“法外之法”(《大诰》)为最高行为准绳,既然帝王本人如此强烈地希望充当全国上下一切角落的法律教官兼终审法官,当然就根本不需要再有什么擿奸如神的“包大人”。而只是到了明代中期,明初建立的法律制度被专制权力本身的横行不法瓦解以后,民间对“包青天”的企盼才重新炽盛起来;而现实中此类企盼的随处孳生,也才造就出嘉靖万历以后,日益腐败政治环境中如海瑞那样典型的清官,以及日益贫弱的国民政治心理环境下空前繁盛的清官文化。
从更根本处看,在皇权社会之中,清官文化的产生一直有其必然的原因。而这种生成机制尤其在君权体制和官吏制度的根本性弊端恶性膨胀的明代,开始对社会文化和国民心理发生着越来越深刻的影响,由此而形成广大国民对包公、海瑞等清官的跪拜尊隆,即如孙楷第先生所说:“包老爷毕竟更有权威,在民间他的势力几乎和关老爷(照宋、元说话当称“关大王”)一样。如果世间的人真须要一位文圣和武圣配起来,那末包公是唯一之选,因为平民对于他的印象比孔圣人深多了。”(注:《包公案与包公案故事》,《沧州后集》第68页。)也由于具有上述深刻的生成机理,所以我们还可以断言:即使是在久远的年代之后,只要政治文化模式的本质没有改变、而社会弱势群体依然只能无奈地面对权力的恶性膨胀,那么不论现实中的“清官”在专制权力蔽日的阴影下沦落到多么的渺小和无奈的境地(注:比如黄仁宇先生所说:“海瑞的一生经历,就是这种制度的产物。其结果是,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第135页)),但是各式各样古典的或是新式的清官文化和清官故事,还是必须依照明代以来既有的路径而一再膨胀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