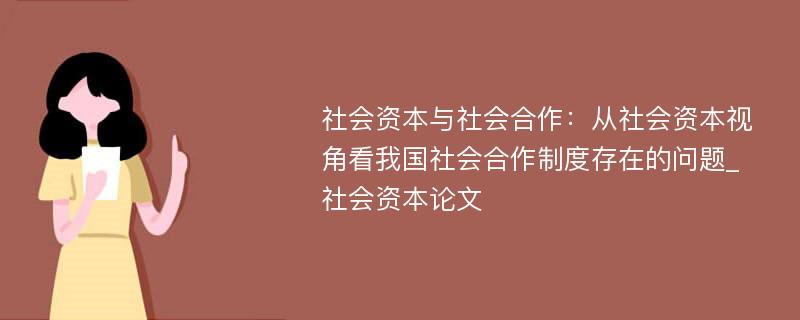
社会资本与社会合作——从社会资本的视角透视中国社会合作体系中的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论文,资本论文,中国社会论文,视角论文,透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资本由分析社会某种关系特质的一个描述性、分析性的概念不断被普遍化、规范化,在发展理论中被建构成不同于物质资本、货币资本、文化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又一重要的具有积极意义的社会内生资源。社会资本对一个社会的合作形态与互动的性质、质量显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一、社会资本与社会合作
社会资本是一种由社会结构内生的关系特质,一些学者将其视为一种公共物品、社会财富和资产,可以为一定范围内的社会成员共享。一些官方机构,如世界银行、世界经合组织,将社会资本同可持续发展的主题联系起来,并视为一种“能够促进集体行动的规范和网络”[1]。社会资本不仅是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可以提供良好合作关系、降低交易成本,而且它有利于信息传播、提供新的机会、减少贫困等。
将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积极的、对社会整体有贡献的社会资源的思想是与科尔曼、普特南、福山等人的研究分不开的。科尔曼将社会资本理解为“人们在群体和组织中为实现共同目标而一起活动的能力”。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就是“社会网络以及源于这一网络的互惠规范和信任性”。福山则将社会资本和经济繁荣直接联系起来。他认为社会经济的繁荣是相互信任的个人合作的结果,而非古典经济学所假定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结果。他区分出三种资本: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并且根据后者的性质将不同的社会区分为信任度高的和低信度的国家。
从这一角度看,社会资本之所以有着功能上的重要性,在于它提供了一种进行社会活动、社会合作的基本资源。从积极的意义上说,社会资本具有不同于其他资本的特性:第一,社会资本不同于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它是关系性的、社会性的,它更强调人们相互合作关系以及进行社会合作的可能性。第二,社会资本是社会制度、特定的结构关系内生的,它是一定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关系结构所具有的某种特质,这些特质表现为社会、团体等内生的资源,包括各种关系网络、规范,如为人处世的原则、制裁的手段等。第三,社会资本表现为一定的社会实体,如家庭、市民共同体、志愿团体及社会的其他关系网络。第四,社会资本所蕴涵的是一种比较自由的互惠关系,这种关系为更大范围的社会合作提供了条件和驱动力,也是将社会成员在更大的范围内联系起来的利益基础。在这种意义上,作为一种内生资源的社会资本为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合作提供了平台,并构成了任何集体性的社会活动的基础。
二、中国合作体系的重建:以国家为轴心的合作体系
在1949年以后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国家自上而下地对社会进行改造和重组,建立有效控制的组织实体。在农村,将基层的社会关系变为以党政为核心的集体关系;在城市,建立起了纵向的官僚等级体系单位体系。结果国家在全面垄断了各种社会资源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以国家为轴心的社会合作体系,寄附于国家机体的政治资本来代替社会资本。
第一,以政治关系替代社会关系在这种替代过程中,政治关系代替社会关系,官僚组织代替各种社会实体资源,党政伦理代替社会的日常伦理。在这一背景中,中国社会合作形式及其性质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的结果导致了一种以国家为轴心的、强制性的社会合作形态:一,在这一合作体系中,一切由国家及其各种组织作出安排,合作个体没有多少选择,一切行动听指挥是这一体系力求实现的理想状态,个人全面依附国家、单位、集体。二,合作的动力来自国家的政令和政策及其所作的制度安排。三,正是这种等级化的、以国家为轴心的制度体系为社会成员提供了合作的总体秩序,个人被趋中性地聚合到权力中心。
显然,以国家为轴心的、强制性的社会合作形态,使社会很难内生并维持某种道德规范、牢固的关系网络和团体资源,增大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使人与人之间的结合更趋近于一种暂时的、工具性的手段。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中国社会在市场化以后出现的信任危机以及“腐败”现象的普遍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市场化中合作关系面临的困境
中国市场化的过程也是社会合作性质发生变化和合作形态转换的过程。但是,在这一变化过程中,暴露出许多严重的问题,它们不仅直接影响到社会的整合、合作的质量,而且也影响到社会秩序的公正性、合法性。
第一,显性的和隐性的:两种秩序的冲突。市场化带来了各种社会关系的发展,引发了以国家为支撑力量的正式秩序和社会中自发形成的秩序之间的矛盾。正是由于正式制度的强大的力量,社会内生的资源更以一种隐性的状态出现,构成了一种由利益互惠所决定的隐性的社会秩序。这种在体制内部发展起来的关系网导致了个人利益联结,强化了将正式关系私化的倾向,使利用体制资源、组织资源进行交换成为个人资本积累的重要手段。在体制内部滋生的“关系”网往往并不表现为一种公共物品,而是利益交换利益转化的桥梁,是一种寻租的工具。这种内生的社会资源在体系内以一种畸形的、隐性的形态发展关系、关系网功利性的利益结合造就的是私人利益团伙主义,它们逐渐向国家建立起来的正式制度体系中渗透,严重威胁到普遍信任体系,影响到社会秩序的合法性。
第二,调动积极性与社会内在动力缺欠。由于以国家为轴心的合作体制的挤压,社会内生合作资源的缺乏也使调动积极性成为中国体制改革的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在国家合作体制之内,主要靠政治动员和这一制度所设定的等级体系来实现,调动积极性即人为地将处于集体中的成员自上而下地作不断的划分,而这种划分调动了一部人积极性的同时也抑制另一部分人的积极性。当金钱的激励呈边际递减时,只有通过高压手段才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促使人们去完成工作。这正说明了“积极性”不是内在的而是要靠着某种制度设计从外面来加以鼓励的。体现了社会缺乏内在动力。
第三,内生规范的不足与社会秩序的危机。作为一个外源的、晚发的现代化国家,中国在现代转型过程中缺乏内生的、有机的社会秩序,使社会缺乏自治能力,缺乏团体资源,缺乏社会合作关系的能力。结果是在中国非政治化与社会的去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秩序危机和合作伦理资源的极度欠缺。而合作伦理资源极度缺欠的结果是:社会合作的动力直接来自利益驱动,功利主义、投机主义成为为人处世的准则。建立在良好合作关系基础上的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要有充分的内生社会资源的支持。因此,培育社会资本,或者说为这种内生的社会资源的生成创造有利条件,而不是破坏它,就应当成为市场化过程中各种制度、组织改革必须加以关注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