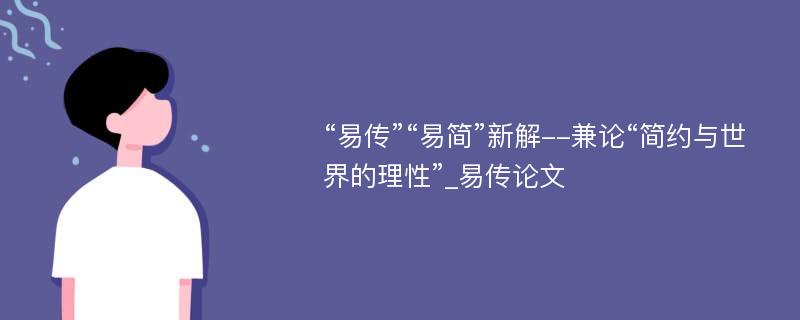
《易传》中的“易简”新释——兼谈“易简而天下之理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理论文,易传论文,天下论文,兼谈论文,易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82(2007)05-0018-08
在《易传》中,“易”“简”是一对矛盾概念,《系辞上传》凡四见,《系辞下传》亦两见。有理由认为,作者甚至将它们提到纲领地位,认为把握了二者则得天下之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存在一种简单化的理解,人们未及慎思深究,往往将“易简”等同于“简易”。
一、历来之释存在的问题
检索流传下来的古代文献,汉代一些学者对“易简”之释相对来说较为审慎,至魏晋以后的注释者才逐渐趋同于作为“简易”理解。
据孔颖达在《周易正义》卷首所引,汉代《易纬·乾凿度》即已指出“‘易’一名而含三义”,后来郑玄作《易论》依此义展开,将三义明确表述为:“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崔觐、刘贞等也如此解释。他们认为,易简之义蕴含于《易》所专致论述的生生之德中;变易则指生生之道,变而相续;不易是讲天地定位,不可相易。郑玄重点列举了易、简的例证,其四条均与乾、坤相联系,“《系辞》云:‘乾、坤其易之蘊邪?’又曰‘《易》之门户邪?’又曰‘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简矣’,‘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此言其易简之法则也。”(第4—5页)[1] 从这些例句中,我们几乎见不出将“易简”看作是简易的意旨。按唐代李鼎祚《周易集解》保留下来的资料,汉末学者虞翻可以作为汉代《易》学的代表者,他解释道:“阳见称‘易’,阴藏为‘简’,简,阅也。乾息昭物,天下文明,故‘以易知’;坤阅藏物,故‘以简能’矣。”(第545页)[2] 以乾之显现为易,坤之收敛为简,应该说这是较为接近原义的训诂。
遗憾的是,自魏晋以后的释《易》著作,大多将“易简”或明或暗地理解为简易。王弼注《周易》,在义理方面实现空前的突破,但是对于《系辞》以后诸传他并未触及。晋代韩康伯注《易传》仍然坚持撇开象数,援《老》释《易》,虽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只是他将“易”、“简”二字作了简单化的处理。他对“乾以易知,坤以简能”的解释是:“天地之道,不为而善始,不劳而善成,故曰易简。”(第259页)[1] 在“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之后仅写道:“《易》之所载配此四义。”(第273页)[1] 至“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简矣”,他竟明确解释为:“乾坤皆恒一其德,物由以成,故简易也。”(第296页)[1] 还须注意的是,对于《系辞上传》的“易则易知,简则易从”和《系辞下传》的“夫乾……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德行恒简以知阻”两则论述,韩康伯均默然跳过,未予理会,究竟是出于轻视还是出于棘手,不得而知。
由于孔颖达主修的“国定教科书”《周易正义》是以王弼、韩康伯的《周易注》为范本,奠定了韩注《易传》的官方意识形态地位,长孙无忌主修《隋书》时,即在《经籍》篇称:“郑学浸微,今殆绝矣。”汉代某些注释虽经李鼎祚辑录得以部分保存,但长期未被人们关注。因此我们看到,宋代注《周易》的名作,诸如司马光的《温公易说》、张载的《横渠易说》、程颐的《伊川易传》、苏轼的《东坡易传》、朱熹的《周易本义》和杨万里的《诚斋易传》等,都直接或间接地用“简易”释“易简”,只是具体的阐述互有出入。
尽管《易传》言“易”涉及平易、容易诸义,但不能构成把“易简”解释为简易的充足理由。《易传》中“简”字凡六见,都出现于同“易”对举的语境,并且又总是与“乾”、“坤”的对举捆绑在一起,作者显然是以之分别表示乾、坤之德;而能够见出接近于简易之义的只有“易知”、“易从”两处“易”字。诚然,先秦时代常有以“简”表示简易的用法,但在《易传》中此词凸显了深刻的哲学意味,可以肯定,其意蕴要比“简易”丰富得多。
熊十力先生在《体用论》(第七卷)[3] 与《乾坤衍》(第七卷)[4] 中对“易”与“简”所指涉的义理有较深入的阐发,李尚信先生在《〈序卦〉卦序之建构及其思想》一文中从常变性方面把握“乾以易知”(第67页)[5],均是难能可贵的。但总体上说,迄今为止,学界未曾充分注意到,将“易简”释为简易带来的一系列疑难问题,致使相关阐释趋于表浅化且缺乏自洽性。
首先,《易传》的作者果真认为简单容易是《易》的根本特点吗?应该说他们通篇的主导意旨是在赞颂《易》或易道之“神”,如“神无方而易无体”,“阴阳不测之谓神”,等等,并且明确指出,对于易道“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从总体上看,易道广大而幽微,借用柏拉图对美的说法:“易是难的。”即使简易可以看作是易道的一个特点,也不能处于根本性的地位。
其次,《系辞上传》首段依照概念的对立关系平行展开,前有天与地、乾与坤、高与卑、动与静等的对举,后有有亲与有功、可大与可久、德与业等的并列,如果“易”与“简”等同于简易,则二词的意义合为一体,并无实质的区别,这在行文中反映出作者的思维发生“短路”,是逻辑之忌。作为先秦时代极富思辨水平的学者的手笔,且很可能经过集体的润饰,该不致有如此的情况。
再次,从语法结构上看,“易则易知,简则易从”并非表达然否的判断句。按《易传》作者乃至先秦时代的言语习惯,阐释性的判断句应该表述为:“易者,易知也;简者,易从也”。文本中的“则”显然是表达一种因果关系,我们知道,因与果不能是同一概念,由此可以肯定,“易则易知”中两个“易”字不同义。
第四,也许有人会说,将“易简”中的“易”理解为平易,“简”理解为简单,就可以避免意义的重叠。可是简单与后文的“有功”又有何必然联系?须知“有功”是在呼应“坤作成物”,成物是凝定赋形而化为纷繁多样的现实世界,为何非要认定它简单?多数注家以“简”为“繁”的反义词,试问:就是追寻到本根,为何独以“简”称坤而不称乾?至于乾道,本身阳刚、健动,其实并没有平易的属性。
第五,再进一层看,单纯从简单容易这一方面考量,也许讲乾简、坤易更为合理。乾、坤固然是易道运行的两个最基本的矛盾方面,但依照“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的观点,熊十力先生等称乾为体、坤为用也是可以成立的。我们知道,体一而用殊,一即是简,伪《子夏易传》称乾“一施命而不杂”是有代表性的观点,据此以乾德为“简”岂不刚好合适?人们常称坤“从乎阳而不自作”,“不劳而善成”,既如此,称之为“易”又有何不可?
第六,《易传》推崇易、简二德,特别在于它们是开物成务的根本。而所谓开物成务,未必需要借鉴道家的无为观念,强调所谓“不烦不扰,澹泊不失”等,从而导出简易之义。虞翻的阐释较为精当:“以阳辟坤,谓之‘开物’;以阴翕乾,谓之‘成务’。”(第595页)[2] 我们不妨由此引申:乾以开物而显,坤以成务为能,所谓乾之易德主要表现于阳、辟,所谓坤之简德则主要表现于阴、翕,“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第七,如果“易简”就是简易的意思,那么,“易简而天下之理得”当作何解?简易的特点显然不能统率变易和不易诸义,怎能涵括天下之理,弥纶天地之道?也许可以说天易地简,如同乾易坤简一样,但是决不能说天地简易。必须注意的是,作者讲“易”、“简”并非直接指阴、阳二爻及其组成的卦象,而是着眼于揭示宇宙大化的根本规律。
此外,在《墨子·非命》和《荀子·富国》中已见“简易”一词,如果《易传》的作者想要表达简易的意思,直接运用此词岂不更为方便?有人会说这是出自要同乾、坤等概念对应的考虑;但是我们看到,先哲并不拘泥于此,例如他们并没有为求对应关系而勉强地采用“阳、阴”的表达,仍然遵循通常的言语习惯,如称“阴阳之义配日月”等。
基于上述,我们有理由认为,《易传》中的“易简”不应等同于简易。
二、“易”、“简”对举语句的阐释
依据许慎的《说文解字》,“易”是象形字,其本义是指蜥蜴。看来变易只是其引申义,而难易之易正如段玉裁所指出的仅属于假借义。许慎认为,《易纬》的解释可备一说,即“日月”二字合成“易”,象阴阳。如果真是如此,由阴阳的相互作用和主导地位的更替也可引申出变易之义。“简”之本义是指牒,也就是用来写字的竹简。“等”为齐简,“编”为次简,单片的竹简经编次而成书简或简札。如按《尔雅·释器》所说,简谓之篳,指的正是简札,则编次义已隐含其中,“简”因而含有广大载物、简约有序和静守恒持之义。《论语·尧曰》称“简在帝心”,其意是某人或善或恶,在天帝心目中必定尺寸明确、条绪分明、尽数知悉。① 古代在言及军备时常有“简车”、“简徒”之类说法,当是指将车、徒等聚集拢来,组织起来,展现出来。
在《易传》中,“易”、“简”二字较之“简易”的内涵要丰富得多,其中“易”主要取变易义,指乾的健而动和变化不居的势用,虽然事物的变易是在乾与坤、健与顺、刚与柔、动与静、开与合诸矛盾方面的张力之间形成,但以前者为主导,或者说前者主变,所以《易经》与《易传》的作者最重《乾》。“简”则有顺、静、直、方、大、藏诸义,主要指坤的顺而静和贞固赋形的势用。天地万物的内在变化需要相对静止,纷杂的质料在运动中走向整一而成型为物,即是简。简与翕相通,合成一物就意味着赋予该物以形式,而形式往往具有静、直、方等特点。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易主要体现于时间维度,简则主要体现为空间维度,所以在《系辞上传》中我们看到,前者联系着“可久”,后者则联系着“可大”;前者表现为具有潜在性之“德”,后者表现于具有现实性之“业”。由于变易则日新,而“日新之谓盛德”;由于简藏则富有,而“富有之谓大业”。
《系辞传》中直接引出“易”、“简”这对概念的是作者对乾、坤的论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易道具有乾道与坤道两个方面,乾道主辟“辟户谓之乾”,坤道主合“阖户谓之坤”,一辟一阖而成变。乾为天、为阳,坤为地、为阴,乾健而坤顺,乾刚而坤柔。既然男女构精而生子,那么由此类比就可推知,乾主导着事物形成之前的潜在性,坤直接孕育出事物的现实样态。朱熹以乾之“易”为知之事,以坤之“简”为行之事,虽然未必精当但可备一说。(第537页)[6]
基于上述,现在让我们将《系辞传》中“易”、“简”二词对举的语句抽取出来,采用注译形式对它们一一讨论。(为了阐释和接受的方便起见,所列语句的先后次序有所调整。)
“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
如何理解“乾以易知”和“易则易知”?我们知道,乾为乾道、天道,《乾·彖传》从宇宙观角度指出:“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乾·象传》从人生观方面补充:“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据此可以推论,前两个“易”宜理解为“变易”。事物变易源于其内在的乾健、阳刚属性的显现,虞翻称“阳见称‘易’”是可取的见解。也就是说,乾道凭借促成事物的变化而昭示自己的存在。显然,前后两个“易知”的指谓并不相同,前一“易知”之“易”与“以”组成介宾结构,后一“易知”则为偏正式的合成词,“易”直接修饰“知”。前一句介宾结构中的“易”在后一句中成为条件,“则”字表因果关系,相当于“那么,就”,其整句的意思是:正因为乾道在事物变易中显现所以就容易被人认识和掌握。也许可以说,这里所表达的是孔子的观点。据《论语·阳货》记述,孔子称自己想保持默然,弟子子贡赶忙说:“您要是不讲话,我们怎能传述您的思想呢?”孔子认为不然,于是以天(即乾)类比:“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坤以简能”和“简则易从”与上述两句语法结构相同,无须再作分析。这里的关键是把握“简”的涵义。作为坤道之德的“简”既有容纳之义,同时还有贞固赋形从而使事物有序之义。考《左传·桓公六年》的一则记述:“秋,大阅,简车马也。”这里的“简”是表示将所“藏”(拥有)的车马编队列出以供检阅的意思,由此引申,“简”含容纳、梳理、展现诸义项。此外,坤道以简为能事,常体现为凝静、宽和、柔顺诸特性。《坤·彖传》赞叹:“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大象》落实于人,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文言》对坤道作了更具体的描述,称其“至静而德方”,不仅成物而且“黄中通理”,“美在其中”。正因为坤以确定的有序的形式显现或者说有则可循,所以人易从。
“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简矣。”
“确然”是刚健貌,“隤然”是柔顺貌,为历来注家所认同。如果这句话所表达的意思是:“那乾,刚健地示人以简易;那坤,柔顺地示人以简易”,则实在是了无意义。同是在描述简易的特点,何必分别加上“确然”和“隤然”修饰?考察语境,并非巧合的是,《系辞下传》与《上传》一样,开首便论述天地、乾坤、刚柔而至易简。但又存在一个显著的不同,《下传》突出揭示了变动与恒持的矛盾。在紧接变动(“变在其中”、“动在其中”、“生乎动”)与恒持(“贞胜”、“贞观”、“贞夫一”)两个方面的分析之后申述乾易、坤简的特性,正好与前面的论述文气贯通,且具有总结前文的意味。也就是说,乾之特性是刚健而变动之易,坤之特性是柔顺而守常之简。所谓“贞夫一”应该主要是指恒持乾德与坤德,易道一以贯之地生生不息,而不是指达到了极其简易的程度。
由于是总括变动与守常两个方面,我们可以译之为:乾,刚健地向人显示了变动不居的倾向;坤,柔顺地向人展示了贞固守静的倾向。后文“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更是清楚地表明,此处的“易”、“简”不是指那看上去很简单的卦象,而是指客观的物理世界,即说明卦象和爻象是以符号形式摹拟、表示出事物的阳动与阴静、阳刚与阴柔等对立特性相摩相荡、开合成变规律。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②
为何乾的德行“恒易以知险”?《乾》卦的爻辞告诉我们:“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乾乾”是进德修业,积极进取貌,“惕若厉”为惧貌,这是说遵循乾道的君子积极从事变革,但对前途的艰险仍保持着警惕。爻辞还讲到“亢龙有悔”,反映了物极必反的规律,表明险象已显于前。《文言·乾》的结语正好可以作为权威的注释:“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同样地,坤的德行“恒简以知阻”也可以找到它立论的源头。《坤》卦的爻辞六三写道:“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文言传》发挥说:“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坤道也是所谓地道、妻道、臣道,具有内敛、凝定、有序、守静诸特点,这可以说是“恒简”,长此以往就会有阻,必然酝酿着变革,所以尤其到了《坤》卦的上六,正如《象传》所解释的:“龙战于野,其道穷也。”
基于上述,这段话可译为:那乾道是天下最为刚健的,其德行是坚持变革、开拓进取,当能意识到前途有险而不骄淫;那坤道是天下最为柔顺的,其德行是坚持秩序、收敛守静,当能意识到路途有阻且不气馁。
“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与“易简之善配至德”。
之所以将这两句话放在一起阐释,是因为我们的先人普遍倾向于将宇宙观与人生论融合为一体;之所以把这两句话放在最后,是因为它们最能说明“易简”的普遍意义和重大价值。
不管《易传》在流传中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我们仍有理由肯定,今本“十翼”的确已构成《易经》的一个完整的阐释系统。其中《彖》释卦名与卦辞,《大象》总体上描述卦象,《小象》则分别地阐释爻辞,《文言》分释乾、坤,《系辞》则合释乾、坤,《说卦》释八经卦,《序卦》则统序六十四卦,阐释面逐步展开;《杂卦》为汉宣帝时才发现,由于侧重于描述六十四卦之间的各组对立,也有存在的理由。总之,诸《传》构成一条完整的阐释链,《系辞传》是其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其主旨是阐释父母卦《乾》、《坤》。
对于《易经》的阐释,《系辞传》应该说是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十翼”中不仅篇幅最大,而且最富于哲学意味。这是因为,乾、坤对于《易经》来说居于枢纽地位。作者反复指出:“乾、坤其易之蕴乎?”“《乾》、《坤》,其《易》之门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在《系辞传》的作者看来,《周易》的纲领在《乾》、《坤》,研究易道的核心是乾、坤,而乾道与坤道各自最有代表性的特性是易、简,它们可以说是乾、坤的标帜,甚至可以说是乾、坤的代名词。因此,理解了“易、简”也就洞察了易道运行的内在二重性,从而在根本上把握天下之理。
《易传》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易经》所企求揭示的“天理”转化为伦理。按照这种一天人的逻辑,既然“易、简”二者中易为乾德,健而动,总是在开拓创生,故君子受之当自强不息;简为坤德,顺而静,总是收敛凝定,故君子受之当厚德载物。位我上者是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胸中,二者都是神圣的,且不容判分,道德修养深厚者能体天地之撰,通神明之德,或者说“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便是“易简之善配至德”之旨。所谓至德就是人对易道知之并从之,化必然为自由,概而言之是具有易、简之善,分而言之则是兼有变易、不易及简易三者而应合天地之运行。正如朱熹在《周易本义》所指出的,“至此则体道之极功,圣人之能事,可以与天地参焉。”(第368页)[7]
综上所述,“易简”具有极为丰富而深刻的涵义,绝非“简易”一词所能承担。在“易”、“简”对举的语句中,《系辞传》的作者一以贯之地以“易”指称宇宙大化中一种开拓创生的倾向,以“简”指称宇宙大化中成物赋形的倾向。依此阐释,无论在文法上还是在义理上均更为通畅。
三、“易简”新释的理论意义
退一步说,即使《系辞传》作者在撰写时就容许语词的模糊多义,我们对“易简”作如上阐释仍有重要意义,因为如此更为合乎宇宙和人生的普遍规律。
我们知道,事物的发展变化总是包含着运动与静止两个矛盾方面,其中运动是绝对的,但相对静止也必不可少。乾道健而动,是动态的、运动的;坤道顺而静,既表现为静态,也表现为相对静止。《庄子》指出,“《易》以道阴阳”(《天下》),且“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天道》),应该说是对《周易》的较为确切的把握。易道生生不息,阳动而主导着变化,在时间维度上突出表现为乾之易德;阴静而让物成形,主要在空间维度上表现出坤之简德。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乾易与坤简两种势用所形成的张力而构织起无穷的宇(空间)宙(时间)。
乾易、坤简的倾向在生物界和人类心灵世界中均得到体现。无论是生物个体还是整个有机界,其存在和演变无不包含发展倾向与亲合倾向所形成的内在张力。对于人类心灵,中西方哲人其实有着非常接近的体认。亚里士多德不赞同先辈将“灵魂”分为知、情、意三部分,认为心灵的活动存在认识和欲求两种对立趋向;我国魏晋时期的嵇康撰有《明胆论》,也认定人的精神必具明与胆两个方面;唐代柳宗元更提出人的“天爵”并非孟子所谓的道德忠信,而是志与明。可以说,所谓欲求、胆、志等是乾健之性的体现,是向外发散、要求拓展开新的倾向,所谓认识、明等是向内收敛、要求和谐整一的倾向,实即知性为自然或人生立法。
既然易、简之理昭示了宇宙与人生的普遍规律,那么切实把握它必然有利于哲学视野中的中西融合与古今会通。这里略举现代中外哲学界几位富有原创性的思想家的表述,从中可见同《易传》作者的感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熊十力先生无疑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富原创性的思想家之一,其哲学思想出入于儒、佛而归本于《大易》。他自述十八岁时读《易·系辞传》,品味“辟户谓之乾,阖户谓之坤”的论述而豁然开朗,顿悟虚灵开发者谓之辟,亦谓之心;聚凝阖敛者谓之翕,亦谓之物。这一根本性的感悟正是本文所专注的论域。在晚年撰写的《体用论》和《乾坤衍》中,熊先生无意于注释《周易》,而着眼于发挥其“翕辟成变”,“体用不二”的基本观点。他常常将易道称之为“恒转”,认为它必然包含两种“势用”;一种刚健而不物化,坚持不断开发,名之为辟;一种凝敛而成物,总是进行摄聚,名之为翕。辟为乾德,翕为坤德,宇宙大化正是立基于乾、坤推衍,翕、辟成变。在他看来,乾道“生生”,“大明”,所以乾是生命、心灵,具有刚健、升进、炤明诸特性,因而为阳;坤道“成物”,“载物”,所以是物质、能力,具有柔退、摄聚、迷暗等特性,因而为阴。辟(乾)为体,自为主宰,能转化翕(坤)而成物即成其用,乾、坤不能分离,体、用不容分界,物质与精神也不宜分割,此即体用不二。熊先生在高度赞美乾德的刚健、进取、主变的同时,还明确将“简”释为坤的“贞固”之德(第七卷,第112页)[3],称道坤让物“成型”的能力。
与熊十力先生深受东方文化的浸润不同,金岳霖先生更多接受了西方哲学的熏陶。即使如此,其本体求索的结果却是很接近的。金先生在《论道》的第一章所集中探究的问题是:道由“式—能”构成。他首先明确肯定“道是式—能”(一·一),然后分述何谓式、能,二者的基本特性和相互关系。按照金先生的理解,“能”不是一个普通名词,不过是为了行文方便而使用的“名字”,它的好处是蕴涵中国传统哲学“气”范畴的某些义项,却又避免了让人误解为“质料”,它是活的,动的。(一·三)“能”还便于同“可能”联系起来,表现出动态与多元趋向,从而可以解释现实世界的物之不齐(所谓“能不一”)。“式”可以明确地界定为“析取地无所不包的可能”(一·五)。它是逻辑的源泉,是理的源泉,但是不限于任何一个逻辑系统或某一分理,只能说是“一理”或“唯一逻辑”,简而言之,“式无二”(一·一三),“式常静”(一·一七)。在金先生的头脑里,宇宙的最基本的模式是“能”在“式”中且可以自由出入,因而既有根本性的法则,又演化出现实世界的多样性,亦即“居式由能莫不为道”(一·二六)。应该说,式与能之分非常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因与动力因、宋明哲学家的理与气之分。金先生也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认为讲形式与质料或理与气的相互依存“感觉不到这思想底必然”(第25页)[8],并且“能”决不应有质料的限制。
在西方现代哲学家中,最为接近《易传》所描述的宇宙图式的莫过于叔本华的观念了。这位西方现代思想史的开创者,自诩要揭示世界的本来面目,而不是像某些蹩脚学者那样只知道从既有的本本出发。他所看到的世界由两个层面构成:一是表象,也就是康德所谓的现象界,在这层面上需要时间、空间、因果性等根据律表出;一是意志,叔本华认为它就是康德所谓的物自身,因为在人的意识中“取消”了表象之后,“剩下”的就只有意志了。与人们通常将意志赅括于力的概念之下相反,叔本华把自然界的每一种力都设想为意志。并且,这种力是动态的,意志本质上是一种盲目的、无止境的追求。世界的表象不过是意志的客体性而已。除了这内外之分,叔本华还有一平行的二元划分,即理式与意志一样构成本体界的内容。原来,叔本华所理解的意志的客体化有不同的级别,理式就是“意志的客体化每一固定不变的级别”(第191页)[9],当然这是相对于意志没有与杂多性相涉,仍然是自在之物而言的。理式又可以说是意志的直接的恰如其分的客体性,不过最为简明的表达莫过于以之为一种基本结构,理式之于自然,“有如给自然套上一种格式”——叔本华认为只有这样理解才是恢复柏拉图的原意。(第191页)[9] 合起来说,意志乃是理式的自在本身,理式则把意志客体化了,这种客体化是完美的;但理式的展开由于在根据律的诸形态中被分散为多种或多面的,因而作为表象的世界就并不是完美的了。(第252页)[9]
尼采常常被看作是叔本华思想的传人,不过其思想首先来自于自身的感悟。正当1870~1871年普法战争期间,他独居阿尔卑斯山的一隅,潜心思索和“猜谜”,围绕希腊艺术的思考得出近似于叔本华思想的结论。尼采所描述的酒神精神近于乾,主要表现为变化不居之易,日神精神近于坤,主要表现为收敛凝定之简。在尼采看来,日神是一切造型力量之神,是光明之神,支配着人的内心幻想世界的美丽外观,赋予对象以柔和的轮廓,它要求“适度”,携有“清规戒律”(第15—16页)[10],其代表性的艺术形态是雕塑。人身上的酒神冲动是一种深沉而强大的内驱力,表现为整个情绪系统的激动亢奋,或者说是“情绪的总激发和总释放”(第320—321页)[10],它的强烈奔突似乎是“泰坦的”或“蛮夷的”,酒神状态是一种痛苦与狂喜相交织的癫狂状态,使个体向世界本体(意志)复归。醉是日常生活中的酒神状态,音乐是酒神艺术的代表。尼采认为,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协同作用,“酷似生育有赖于性的二元性”(第2页)[10],一样,生成单个的艺术品乃至整个艺术世界。
我们并不讳言上述几位哲学家之间存在巨大的思想差异,如熊先生早年是辛亥革命的参加者,由于对黑暗的政治现实深恶痛绝等原因,尤其推崇乾,推崇变与动;金先生一直是学者,对于西方的逻辑学研究颇深,所以首先推崇式,推崇恒与静;叔本华与尼采虽然都以意志为本体,但由于对意志的把握有别,一者走向消沉,一者走向强暴;熊十力先生继承《周易》的倾向,对作为本体的乾道赞美有加,叔本华则从人的生存着眼贬斥意志,等等。但显而易见的是,他们对宇宙人生本原的追问都觉察到其中蕴涵最根本的二重性:所谓乾或辟,与能、生命意志或强力意志等同义,代表一种普遍的刚健开拓的力的势用(约略相当于易),所谓坤或翕,与能式、理式、日神精神等同义,代表一种普遍的贞固有序的数的势用(约略相当于简);一方面存在变化不居的动力源泉,另一方面又存在凝定聚合的数理结构,二者协同作用于纷杂的质料,便是开物成务,形成丰富多样的现实世界。中西方哲人各自从不同角度深入开掘,居然在岩层深处相遇,真可谓是“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明确其中的基本道理,对于先哲的观点我们有可能在比较中择善而从,从实际出发扬弃某些不适当的表述。如熊十力先生以乾为精神,为体,以坤为物质,为用,未必恰当。坤既是用又是体,同样是万物的始基。“乾主变而导坤”(即易),坤承乾而赋予质料以形式(即简),才是开物成务之功。相应地,以乾为炤明、坤为迷暗也值得商榷,应该说炤明之性尤为坤道所具有,事物凝定“成型”才炤明,而人的认识也主要是对事物存在形式的把握。金岳霖先生认为式相对于能来说表现出阳刚的特性,与人们的普遍看法正好相反。如果理或原则的确定性即是阳刚,那么坤道也可如是观。正像坤虽“直以方”可是相对于永远奔突之乾来说仍属阴柔一样,静的式相对于动的能也只能算阴柔。叔本华虽然肯定意志是世界的本体,但是在人生哲学中又认为它是痛苦的源泉而持否定态度,强调人们在审美境界中达到个体意志的寂灭。其实他所着眼的是他律意志(即功利欲求),而没有考虑自由意志(心灵趋向审美境界不能没有自由意志)。中国古代哲人的观点较为公允,孟子虽然也曾主张寡欲,但那是为要立大体(意志自律)而抑小体(意志他律)。尼采的哲学观较之叔本华的更具人类学色彩,他展现的是一个诗人哲学家的视界,然而他对酒神精神的肯定演变为对强力意志的赞美和对人民大众的蔑视,日神精神逐渐淡出。借鉴心理学家荣格的观点,笔者倾向于这样的看法:乾仿佛集体无意识中的阴影原型,既是创造力同时也是破坏力的源泉;坤仿佛集体无意识中的自性原型,能让杂多转化为整一,但它也可能造成因循保守之弊。也就是说,乾与坤,易与简,相对于人类生存来说,均为利弊并存。
扩展“易简”的阐释空间,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人们常常讲,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理解易、简之理,我们很容易看出,二者实际上是人类生存的永恒主题。中华民族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复兴时代,发展与稳定构成社会全面进步的基本矛盾,其必然性也在易、简之理中。我们有理由相信,确切地把握了“易、简”,则可以从根本上说,“天下之理得矣”。
注释:
①《论语·尧曰》可能是孔子的再传弟子所记。“简”字的这种用法后来已鲜见,据此有助于推断《易传》的写作年代。张岱年先生在《论〈易传〉的著作年代与哲学思想》(《易大传》即《易传》)中认为它撰成于庄子之前,此语例亦可佐证。
②《系辞下传》的开首与末尾都特别将“易”与“简”对举描述,前后照应,可见作者非常重视易、简的二元对立。汉儒论“易”之三义而首推“易简”,其阐释较为忠实于原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