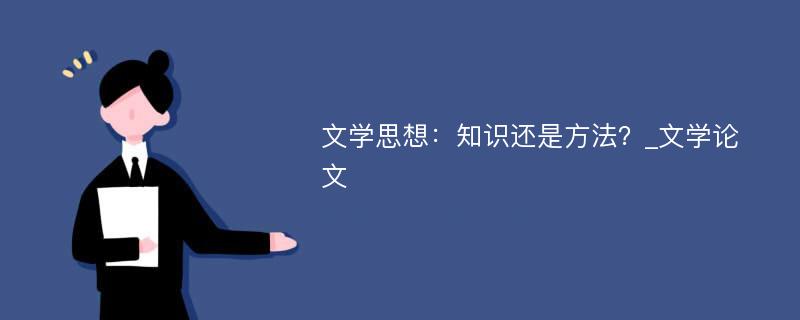
文学理念:知识还是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念论文,方法论文,知识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问题的提出
目前文学理论的研究存在着强烈的自我解释冲动,这种自我解释冲动的“潜话语”,表现的恰恰是文学理论存在的合法性以及有关文学理论的学科定位、存在形态等理论元话语问题的长期被忽视。这些问题在当前的话语背景中被置于研究视域的盲点,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不言自明的东西。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多样化,种种“文学”理论众声喧哗的背后,令人遗憾的看到,文学理论研究没有明确的自我定位认识,没有明确的问题意识,缺少内在的生机和活力,缺少进一步发展的理论空间,真正具有实际价值与意义的精神资源和思想资源实在是很有限。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有种可能,即可以从文学与文学理论的关系入手,把责任归之为与文学理论密切相关的当前的创作-欣赏、生产-消费的文学活动本身。也就是说,过于按照市场化原则操作的文学“生产-消费”这一过程的商业化味道过于浓厚,使文学创作越来越考虑如何去适应消费市场、受众人群,而甚少或不去理会文学理论话语的存在及其对文学的指导和借鉴意义;而理论话语言说对象的缺失,又在某种程度上使文学理论自身的发展可能过于超前或滞后,使文学活动难以把握文学理论内在的精神实质,从而使二者在不同的层面上各有其发展的规律,因而也难以进行有效的对话。
但是,如果转换一种视角,“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非常间接的,而且我们可以忽略它,因为我们的目的毕竟主要是对各种思想的理解。”(注:〔美〕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一卷,杨岂深、杨自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9页。)那么,分析当前文学理论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时,或许可以从文学理论自身,而非简单地从理论与创作的关系入手来分析文学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问题的原因归根到底在于文学理论元话语的缺场。元话语的缺场导致了对文学理论的学科属性在一种知识或者方法之间徘徊。这直接导致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陷入了某种危机之中,在貌似“多元化”、貌似“繁荣”的表层下掩盖不了思想的匮乏与方向的迷茫。方法论问题是理论元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了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研究方向和研究成果。所以,本文试从文学理论本身这一角度展开论述。
方法论:理论研究的自我规定性
目前的某些文学理论研究,只是一种知识性而非知识论的研究。所谓知识论的研究,其核心是“知识是什么?知识如何可能?”尝试着提出一切可能解释事物的变化的假设,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是“为知识而知识”的科学(注:〔法〕莱昂·罗斑:《希腊思想和科学精神的起源》,陈修斋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在这种方法指导下,传统的文学理论,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从“文学是什么”入手,把文学看作是一种知识的特殊形式,注重按照科学的方法对文学进行研究。正是这种研究方法,使文学理论这门科学在回答文学活动的规律时具有很强的实践性、证伪性。正如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中强调的:“文学是创造性的,是一门艺术;而文学研究,如果称为科学不太正确的话,也应该是一门知识或学问。”(注:〔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一页。)应该说,任何文学理论研究都是在一定的基础上层开的,确实需要知识的积累和消化。但是,单纯知识性的解读又容易使文学理论仅仅成为既定的原理和结论,成为一种可以复制、传播的知识,使文学理论研究只是一种现成理论的复述与挪用,缺少创造性的认识与说明,缺少批判性的理解和阐释。这种知识性的解读,其弊病有二:第一,将文学理论研究成果视为某些既定的知识,这使理论本身失去了反思、批判、创新的维度,使理论常识化。第二,将文学的原理性认识视为某些现成的结论和道理,条分缕析,使理论日渐教条化。文学理论研究中知识性的研究方法容易使专业的术语成为一种先入为主的概念程式,体系的建设成了固定的框架模式,在研究中注重的是“是什么”,而不是“为什么”,缺乏的是理论反思的深度与本体追问的勇气。所以文学理论研究在不断接受一个又一个理论研究的成果的时候,却越来越缺少内在创新的活力,某种程度上成了一种程式化的操作过程,而文学理论自身所应具有的特性却隐而不显。与此同时,这种研究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和误区,诸如:文学理论的他者化、话语的平移、学科的自我边缘化和盲目扩大化,等等。因此,文学理论存在的合法性、发展空间、价值成分及意义备受质疑。
应当怎样看待这些问题?其实这就是前人所批判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常识在日常应用的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东西,但它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碰到极为惊人的变故。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虽然在依对象的性质而展开的各个领域中是合理的,甚至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迟早都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会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记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记它们的生成和消逝;看到它们的静止忘记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注: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0页。)目前的某些文学理论研究就存在着这种现象。当各种文学理论研究成果已然成为知识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变成常识时,科学的文学理论研究需要的就是采取正确的方法,变革人们的理论“期待视野”,拓展和深化人们的理论研究视域,推动新的文学理论“范式”的产生,从而获得理论研究的超越性与穿透性。
在文学理论的研究中,似乎最不缺的就是“方法”。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新“三论”到今天的“现象学方法”、“新历史主义方法”、“解释学方法”等,各种研究方法接踵而至。但这些只是理论研究的具体的操作方法,是形而下意义的方法,是本文所说的“方法”应当考察的对象。所以,本文所说的方法应当从形而上而非形而下的层面去理解,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方法。这应是在文学理论研究过程中具有一般性、指导性并且处于哲学高度上的方法。它是文学理论研究的内在规定性,贯穿在文学理论研究的各个领域,正是因为运用这一方法,才能够把各种具体的“方法”和具体的理论成果系统地凝定成为原理性的认识,使已知变成未知,使不可能变成可能。因此,它具有一种穿透性和超越性功能,而这种穿透性和超越性又使理论研究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和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形而上的方法意识其实也就是对于文学理论自身特征的观念性认识,决定了文学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研究范围和研究方向,因此也就具有了认识论和本体论的意义。当前的文学理论研究所普遍缺乏的正是这种意义上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应当是文学理论具有发展弹性和理论个性的灵魂。
那么,如何在方法论层面认识这一问题?我们认为,唯物的辩证的方法依然是行之有效、重要的思想资源。所以这样讲,是因为“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和革命的。”(注:马克思《〈资本论〉1872年版跋》,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与此同时,作为理论思维,唯物辩证法是关于思维的科学,它也和其他各门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是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我们可以将唯物辩证法的理论特性归纳为批判性、科学性和历史性三者的有机结合。从文学理论研究来看,应该说这一方法是符合“理论”本身特性的。乔纳森·卡勒在他的《文学理论》中认为,所谓的理论,其内涵应当有四点:1、理论是跨学科的,是一种具有超出某一原始学科作用的话语;2、理论是分析的话语,它试图找出证伪性,或语言,或文字,或意义,或主体中包含了什么;3、理论是对常识的批评,是对被认定为自然的观念的批评;4、理论具有反射性,是关于思维的思维,我们用它向文学和其他话语实践中创造意义的范畴提出质疑。(注:〔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不难看出,在唯物的辩证的方法和理论特性之间理应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所以,具有批判性、科学性和历史性统一特性的方法应当成为文学理论研究的自我规定性。
对方法论的具体阐释
对于批判性、科学性和历史性这些惯用名词的常识性认识,又常常阻碍了对其真实意义的理解。所以,有必要对它们作进一步的阐释。
第一,唯物辩证法的批判性不仅仅是理论思维的一种功能,其本身就具有认识论意味,是理论思维自身的属性。思维具有既指向存在又指向自身的特性,理论是“关于思维的思维”,而“思维的思维”就是理论的自我认识,是理论的反思性、否定性,是人对自身以及所处现实的一种超越性的思维指向性。在文学理论研究中,就是要对既有文学理论以及文学理论研究的批判和反思。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理论前提的批判。理论前提是构成理论的思想支点,同时也具有对新的文学思想的形成造成一种思维的强制性。消解理论前提的强制性既是理论批判的实质内容,也是形成新的思想的先决条件。所以,它能够超越观念的内在性,赋予理论以新的指向性,从而使文学理论研究获得新的自我超越。因此,批判就不仅仅是对理论内容的批判,更是对理论前提的批判。当下的某些文学理论知识性的研究方法,往往忽略了这种文学理论自身的批判性本性,这就使得文学理论难以取得创新和发展。批判性是理论的鲜活特性,它打破了僵化和教条,是理论创新的动因,并赋予理论研究以强大的生命力。但要注意的是,批判性不等于“否定一切”的怀疑主义、否定主义。文学理论界有一种倾向,批判和创新仿佛就是“批判一切、否定一切”,这是不负责任的简单化的肤浅的理论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固然可能为我们指出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甚至也不乏新意,但从理论自身的长远发展来看,这种方法只具有一时的有效性、轰动效应,经不起理论、实践的检验,最后只能使理论创新变成空泛的标新立异,变成哗众取宠的文字游戏。批判性和反思性是在已有理论研究成果基础之上的批判性和反思性,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理论追求。要在文学理论自身的发展和个人的阐释之间、传统与现代以及东方与西方的文学理论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只有这样,文学理论研究才能不断取得进步,文学理论才会拥有内在的生机和活力。爱因斯坦说得好:“建立一种新理论不是像毁掉一个旧仓库,在那里建起一个摩天大楼。它倒是像在爬山一样,愈是往上爬愈能得到更宽广的视野,并且愈显示出我们的出发点与其周围广大地域之间的出乎意外的联系。”(注:〔美〕爱因斯坦:《物理学的进化》,周肇威译,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62年版,第109页。)
第二,唯物辩证法是关于思维的科学。文学理论研究按照可然率、必然率、或然率的要求对文学活动本身的现实性、可能性和必然性做出了应有的归纳、判断和预测。从文学活动和文学理论的发展实践来看,应该说具有内容的规律性、解释的普遍性以及实践、理论的可预见性。文学理论研究则是理论思维科学性的具体体现。文学理论研究的科学性是指其理论以系统的符号系统和概念框架去认识、理解进而解释文学世界。它的思维方式和概念体系又可以不断地进行“范式”革命。强调文学理论研究的科学性,应该能够达到这样的目的:一、学科研究对象的确定性;二、学科研究的规范性;三,学科概念术语所指的明晰性;四、学科本身的内在规定性;五、理论成果的可发展性;六、理论实践的可操作性。这里需要申明的是,首先,这不等于试图以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改造文学理论的“科学主义”,不等于文学理论研究的自然科学化。其次,强调文学理论研究的科学性,没有也不会否定它的人文社会性特征。从价值论的角度看,文学理论研究的科学性使文学理论具有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概念范畴、形态范式和理论追求,有利于维护文学理论学科的规范和独立。同时,我们不仅看到文学理论以何种方式存在,更看到了文学理论存在的意义。正是对文学理论研究意义的科学性认识,使我们获得了文学理论研究价值的评判尺度和价值规范的依据。所以,文学理论研究科学性的意义就在于它提供给我们关于文学理论的知识体系、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这一切恰恰构成了文学理论研究的意义世界。
第三,唯物辩证法还是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文学理论和其他学科一样,涉及到的是具有历史性的,处于经常变化之中的对象。因之,文学理论研究既要正视文学活动的发展情况,更要面对不断发展的文学理论的历史。
当然,文学理论研究的“历史性”不等于历史还原主义。任何一种文学理论都是在继承前人和学习他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有其具体的历史语境,特定时代的历史合理性和明确的理论指向性和针对性。但是如果因此而试图在客观化的前提下将理论进行所谓的还原,就只能是一种理论上的理想主义。此外,文学理论自身的发展构成了文学理论研究重要的对象,我们强调文学理论研究的“历史性”,但不能把文学理论发展的历史简单化。也就是说,不能将某种理论产生之前的理论都视为走向这一理论的必然。因为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对理论的任意剪裁,“六经注我”。同时也会造成了一种理论的普遍有效性的历史主义幻觉,对理论本身特性和功能的理解相反却被弱化了。
究竟应当怎样正确理解文学理论研究的“历史性”?从横向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找到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在一切时代的“共同标志”和“共同范畴”,可以找到“合理的抽象”,这“合理的抽象”就是文学理论研究为大家所接受的共性话语。从纵向角度来看,这一“合理的抽象”又是由许多部分组成的,这些不同的部分义都有着自己的规定性。这就需要文学理论研究在尊重这些不同的内在规定性的前提下,找出这些规定的“共同点”,赋予理论以更加强大的有效性和更加长久的生命力。这种将研究对象的历史展开与其所属范畴之间的互动关系的研究,以及理论共性与个性的研究,会有效地把握住学科系统的内在发展脉络。这才是文学理论研究方法“历史性”的正确态度。
小结
诚然,文学理论的学科特性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特征,所以,本文这种对文学理论研究方法的理解不是唯一的,也是可以商榷的。但至少是想直面现实,提出问题。同时,也力图从方法论的角度入手,恢复文学理论的本来面貌,使文学理论研究真正进入科学的“理论”的层面,而不是在常识的层面打转转。对于当前的文学理论研究来说,方法论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对文学理论研究方法的理解同文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至关重要。如何找到新的理论增长点,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一步。正如前面所说,批判性、科学性和历史性都具有自己特定的理论内涵,而这三者的有机结合又构成了文学理论研究方法的本质特征,所以,不能分开来做片面孤立的理解。科学的文学理论研究,应当在对已有的各种文学理论研究成果充分吸收、充分了解、充分反思,对传统充分尊重的基础上,按照批判的、科学的和历史的要求,对文学理论进行重新研究,追求“质”的飞跃而不是“量”的提高。与此同时,科学的文学理论还应该“通过独立的研究必然可以掌握它甚至创造它”(注:〔匈〕乔治·卢卡契:《审美特性》(一),徐恒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页。)。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在吸收各种思想资源的基础上,维护文学理论本身的学科独立性和规范性,才能有力地促进文学理论学科的不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