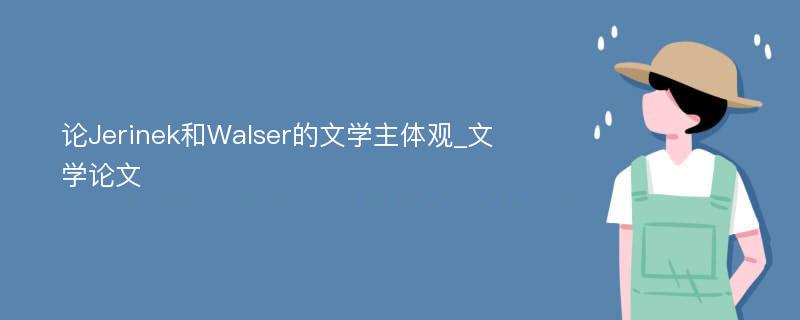
论耶利内克与瓦尔泽的文学主体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瓦尔论文,主体论文,文学论文,耶利内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08)05-0043-06
对耶利内克《他不是他》(er nicht als er)的解读本应该从标题开始,因为它像谜一样诱惑着读者。由于作品的副标题是“关于罗伯特·瓦尔泽和与他在一起”,因此我们认为在这个标题里蕴含着作家耶利内克与作家瓦尔泽的某种关系。而“他不是他”却使得作为文学主体的作家、作家所创造的文学人物在“自我”的层面上变得扑朔迷离。然而耶利内克却十分慷慨地主动揭开了自己设下的谜底,耶利内克在这部作品中的最后一段话就是:
诗人在雪地中死去,他的礼帽终于离开了他,斜卧在他的身边,但是仍在照片上。这本书的标题就是由罗伯特·瓦尔泽的名字拼凑起来的,却不完整,或者毫无意思:罗伯特不是瓦尔泽(Rob-er-t nicht als Wals-er),也就是他不是他。他什么也没有,他拥有一切。这就是他,也是这个文本的要旨所在。(Jelinek:49)
耶利内克的慷慨似乎是一种欲擒故纵,因为她的解谜却使文本更加神秘。她把主体的认同符号(名字)拆碎了是不是把主体也拆碎了?“毫无意思”是不是也是某种意思?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毫无意思”的意思究竟是什么?我们看到,在这里“他不是他”的“谜”没有彻底揭开,我们仍需要阐释“罗伯特不是瓦尔泽”以及“没有即拥有”的悖论,也许“他不是他”恰恰就是他。文学阐释的魅力大概就在这种云雾状态中寻找意义。如果说需要阐释,那就是在昭示某种被阐释的东西,即“存在着的”(das Seiende)。也就是说,“存在着的”没有全部地表明它的本质,有部分东西还没有得到揭示。因此我们的原则是:让掩蔽的东西自己来“揭示”掩蔽的事实。
一
《他不是他》这本小书写于1998年,是一部描写已故瑞士作家罗伯特·瓦尔泽的“剧本”。之所以说它是剧本,大概是因为耶利内克当年欣然接受了萨尔斯堡戏剧节的约稿,为戏剧节撰写一个剧本,因此这本小册子的封面上赫然印着“剧本”这样一行小字。同时,耶利内克在文本的扉页上写了一句类似场景提示的话:“几个心情尚好的人在一起交谈(或许躺在浴缸里,犹如过去在精神病院里那样)。”(Jelinek:7)虽然1998年夏奥地利导演威勒(Jossi Wieler)将这部作品搬上了萨尔斯堡戏剧节的舞台,然而从文本形式上看,它并不具有传统剧本的时空形式:既没有舞台人物、场景,也没有情节和对话(耶利内克的剧本大多如此),只有“我”的内心独白。这在某种意义上延续了耶利内克的戏剧作品的风格。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有理由把这部作品看成是“散文”(Prosastück),看成是某种思维碎片,或者就像耶利内克自己所说的那样,是打碎在地上的水晶瓶,“一种瓦尔泽式的万花筒,从一个小小的碎片中折射出了无限的绚丽和璀璨”,(Jelinek/Lecerf:10)或者就像一篇运用瓦尔泽的语言献给瓦尔泽的“颂词”。整篇文本由十二个意群段落组成,没有任何刻意安排内容的痕迹,而是顺着泉涌的文思而水到渠成,这点与瓦尔泽的文本异曲同工。从表面上看,叙述主体不断地阐述自我和瓦尔泽,同时,这种不断地叙述(或者恰恰是因此而不叙述自我)却只是没有逻辑和结构的梦呓。叙述主体似乎是瓦尔泽的自诉,又似乎是叙述主体与瓦尔泽的冥冥神交。
从根本上说,《他不是他》不仅反映出耶利内克作品一贯语言简练、结构简单的写作风格,而且与瓦尔泽的文学风格有一定的共通之处,那就是善于在文学语言的树林里捉迷藏,或者说是对文学意图的掩蔽。在这个问题上本雅明已经有了定论,本雅明在《罗伯特·瓦尔泽》一文中对其风格做了这样的说明:“我们现在面对……完全没有企图的、但又因此而具有魅力的、迷人的荒芜的语言。同时还是一种随波逐流式的语言,体现了优美和苦涩的所有形式。我们说这是一种表面上的无意识。”(Benjamin:349)虽然我们尚无法确定耶利内克是否在此刻意戏仿瓦尔泽,但是从她对瓦尔泽的敬仰之情来看,似乎可以作出她对瓦尔泽“马赛克”、“半睡眠半清醒”和“梦呓”风格表示首肯的假设。(瓦尔泽:239)在谈到《他不是他》的创作时耶利内克说:“罗伯特·瓦尔泽是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我没有见过跟他相似的作家和作品。当然他是让人却步的,当我开始写一些表面上看似简单的东西时,我觉得已经没什么可以写的了。”(Jelinek/Lecerf:10)如果说《他不是他》与“让人却步”的瓦尔泽有关,同时又是在写“表面上看似简单的东西,却已经没什么可写的了”,那么耶利内克究竟在写什么呢?她有什么深层的意蕴要掩蔽或者掩埋呢?她又是如何来做到这一点的呢?
首先来看耶里内克的表现手法:这是一段自我独白的第一人称作家对另一个作家关于文学的对话,从文本副标题“关于罗伯特·瓦尔泽和与他在一起”的逻辑关系来看,这里蕴含着两个叙述视角:第一是“关于”瓦尔泽的叙述,即主体对客体的叙述;第二是“与”瓦尔泽“在一起”,即叙述主客体的混合;而在文本中,我们发现这两种叙述视角常常是无法区分的。独白者的对话对象是瓦尔泽,而独白者似乎是瓦尔泽本人。这样,叙述主体和客体就变得模糊不清,“他”与“他”的关系也就处于一种叙述悖论中,整个文本也似乎成了瓦尔泽的自言自语。《他不是他》中的独白断断续续,同时采用了大量瓦尔泽的引文,这种结构给人一个印象,好像耶利内克有意让作家瓦尔泽说话,似乎瓦尔泽在述说他的生活和写作。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有人仿佛独自在大自然中散步,也许有几只小鸟在啾啾欢叫,小河发出阵阵拍击声,这时突然出现一个声音:“且慢,请您留步,您没看到灵魂从肉体中飞了出来,就像您心中的作品、像沉睡的女神那样?”(Jelinek:9)这便是文本的开头。
从叙述结构和效果上看,耶利内克(假如我们将其视为文本创作主体)、第一人称叙述者和叙述对象瓦尔泽就好像是一种叙述螺旋体,混杂、融合在一起,让人进入一种混沌的睡眠状态。在耶利内克看来,“睡眠”恰恰是文学主体的某种“生存方式”,(耶利内克:25)或者是一种梦幻状态,使叙述主体和叙述对象变得含糊不清;而“睡眠”和“梦幻”也常常是瓦尔泽文学作品中对主体、尤其是对文学创作自身的无意识显现,如《雅考伯·冯·贡腾》、《散步》、《强盗》和其他作品中都对此有很多表述。在《他不是他》中,一方面第一人称叙述者采取了与瓦尔泽对话的视角(肉体的视角或外视角):“我的先生,您的作品很另类”,等等;另一方面,却采用瓦尔泽的视角(灵魂的视角或内视角):“就连我的房间过去也只能感觉到我的存在,它们实在太熟悉我了,假如它们感觉到了,它们为什么不在我要出门去雪地里散步的时候拦住我?不过我总是很喜欢勤奋地散步,圣诞节也要去散步。”(Jelinek:36)
耶里内克通过以下几个主题词来展开十二个相互交融的片断:女神、音乐、房间、生活、食肉动物、秩序,等等。它们不断地深化、发展,形成文本“灵魂从肉体”或“自我和本我”的分离及合一的主题,大概这就是耶利内克要表达的“他不是他”。同时,通篇由独白或内白写成,读者可以感觉到词的声响和节奏。文本始终围绕灵魂是如何离开肉体这个主旨,叙述灵魂游离的状况。
二
假如我们读过卡尔·塞利希的《与罗伯特·瓦尔泽散步》,那么我们马上就会理解耶利内克的用意。耶利内克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从本质上说,瓦尔泽总是在写一个文本,他的大文本都是由许多小文本聚集起来的,也就是说,从本质上看瓦尔泽的写作是一种分裂性的、残片式的写作。”而这种“残片式”或者“马赛克式”的写作在耶里内克看来是歇斯底里的必然结果。她认为瓦尔泽的歇斯底里就是表现自我和自我丧失之间张力的破裂,其表现形式就是不断地解说自我,但却不仅仅是为了说明自我,而是“歇斯底里分裂成两半时的一种敏感,当然歇斯底里可以四分五裂,恰恰是这些分裂开来的东西成为写作的本体”。(Jelinek/Lecerf:11)耶利内克进而提出了一个观点:瓦尔泽作品中的文学主体特征即是“自我分裂”。在这个意义上,耶利内克印证了本雅明对瓦尔泽文学作品特性的认识:“因为抽泣是瓦尔泽喋喋不休的曲调,它给我们揭示了瓦尔泽至爱的源泉。它来自歇斯底里,而绝非他处。”(Benjamin:350)
歇斯底里是一种癔症性精神障碍,主要表现为发作性意识范围狭窄、具有发泄特点的急剧情感爆发、选择性遗忘、自我身份识别障碍等。弗洛伊德对歇斯底里症治疗研究的贡献主要在于提出了催眠术和语言疏导,而在催眠疗法中,在“半醒半睡”状态中达到梦游和潜意识认知尤其重要。在这里我们不难发现,瓦尔泽所至爱的文学发出“喋喋不休的曲调”恰恰与歇斯底里的病症有关,睡眠、梦游和梦呓在他的作品中是回归主体的无意识行为和文学风格的主旋律。迄今为止,我们无法确定瓦尔泽本人曾在文学中获得歇斯底里治疗的文献证明,唯一能够找到的就是本雅明关于瓦尔泽“歇斯底里”的评语。而耶利内克在《他不是他》的卷首语中所提示的“几个心情尚好的人在一起交谈(或许躺在浴缸里,犹如过去在精神病院里那样)”,给了我们同样的启示,那就是瓦尔泽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的无目的性,以及主体意识的化解。
《他不是他》文本的叙述主体是第一人称单数,文字所表达的是叙述主体对文学创作的反思和冥想。由于放弃了时空情节(生与死、现在与过去完全失去界线),耶利内克成功地绕开了读者始终喜欢问的一个问题“谁在讲述”,而是像瓦尔泽那样回归到了叙述本体,或者说是文学创作的本身。上面我们说过,《他不是他》整个文本没有故事情节,这本身并不重要,但重要的是为什么作者放弃情节和内容。我们看到,《他不是他》的作者似乎不断地在做推雪球的游戏、一种近乎梦幻的文字游戏,我们可以说这是弗洛伊德意义上的“潜意识”和“白日梦”。但不能否认的事实是,耶利内克从一个字推向下一个字,从一个句子推向下一个句子,从一个想法推向下一个想法,作者试图由此来解读写作和思考问题。这恰恰又是瓦尔泽文学写作的特点,就像本雅明所说的那样:“瓦尔泽的每一句话只有一个任务,就是忘记前一句。”对瓦尔泽来说,“如何写作绝对不是一件小事,所有他原先想说的话都在写作的自身意义面前而显得失去意义。也许可以说,写作是至高无上的。”本雅明针对瓦尔泽文学文本的情节荒芜曾经发表过这样的意见:“罗伯特·瓦尔泽身上恰恰表现为一种非常奇特的、难以描述的荒芜。这种对内容的放弃就是分量,他的漫不经心恰恰是一种耐力,这点是看待瓦尔泽作品的关键。”(Benjamin:350)
文字的荒芜并不完全意味着叙述主体的荒芜,也许叙述主体正在无意识中逃遁,或者被掩蔽起来了。而瓦尔泽的逃遁恰恰是他的“在”,也就是“我在家里却不是我”(假如我们在这里把“家”理解成海德格尔的存在之“寓所”的话)。主体的诡异性或许能从罗马大帝奥古斯都临终前问身边大臣的最后一句话来揭示:“我这一辈子喜剧表演得如何?”(Heidemann:55)这个隐喻告诉我们,文学主体常常会戴着面具出现在我们面前。这如同笛卡尔在《私人沉思》(Cogitaiones Privatae)中开宗明义所写的那样:“自我就像演员一样需要化妆登台,而自我总是戴着面具登上世界这个舞台。”(Heidemann:55)瓦尔泽的面具是什么呢?抽象地说就是“他不是他”,或者从瓦尔泽的视角出发来说“我不是我”。而这里必须说明的是“他不是他”(er nicht als er)中的als这个连词:我们看到无论是读者眼里的叙述主体“他”,还是叙述主体眼里的“我”,都与这个“als”(作为)有某种联系,它都是一种掩饰,即“派松”(Person)。从词源学上看,德语中的Person即“面具”的意思。而als源于中古德语中的alsō,意为“如同”,也就是说这里叙述主体处于一种“相互比较”的关系之中。因此在耶利内克“他不是他”这个诡异命题中,言说及被言说的对象既是一元的,也是二元的。这样我们大概可以确定,瓦尔泽和耶利内克的叙述主体就躲藏在文字之中,这就是耶利内克所说的“他不是他”,或者说“罗伯特不是瓦尔泽”。按照这个逻辑,对于瓦尔泽叙述主体的寻找最终只有在纸张中寻找,而文字却在树林里散步。文字被囚禁,就像诗人被囚禁一样。文字既是灵魂也是肉体:
所有的字行现在都成了尸体,(意义)在尸体中静静地被保存起来,假如我们想耐心地去发现我们自己,那么我们大多数人身上都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为什么您的想法不再走出躯体,而我的思想却要出来?只是为了连篇累牍地、又不那么愉快地、顽固不化地跳跃到纸张上去。(Jelinek:20)
耶利内克在与莱塞的谈话中指出:
我尝试去定义什么叫做“不断表现自我的自我丧失”,不断地解说自我,但不是为了说明自我。瓦尔泽就是一个不断地解说自我的作家,他几乎不能说别的任何事,他总是在说“我”,但指的却不是“自我”,这就是我所说的那个现象。(Jelinek/Lecerf:12)
那是什么现象呢?《他不是他》中第一人称叙述者是这样解释的:“您的作品非常怪异,我亲爱的先生,我觉得您越不愿走进自我,您就越远离自我。是的,诗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然后便远离自我。”(Jelinek:10)这个诗人就是罗伯特·瓦尔泽。在这里耶利内克说出了《他不是他》所掩蔽的要害,她对瓦尔泽的文学创作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体观:与瓦尔泽出于“歇斯底里”的主体荒芜有所不同,她明确地主张文学创作是反叛自我,而反叛自我的手段是在“写”的过程中放弃自我。
三
这种反叛反映在文学创作主体的无奈上,就如耶利内克对瓦尔泽创作的评判那样:作品就像“一个沉睡的女神,即便在睡眠中也在飘逸,……醒和死的区别就是梦”。(Jelinek:40)对耶利内克来说,我们常常死去,因为我们常常遗忘做梦。而瓦尔泽的生命却是“写作”,就是那即便在睡眠中也在飘逸的沉睡女神。我们小心翼翼地说,那也许就是写作的冲动、自我释放的冲动。越是心中的宏大或宏大的自我,在瓦尔泽的文学表述中便越是显得非常渺小以至于小到几乎消逝:“您在寻找我吗?那么您在我身上找不到我。但是只要您愿意弯下腰去,您就能看到我!我就像小草那样微不足道,它们只有在微风下才会轻轻地摆动自己的身姿。”(Jelinek:25)这其实也是耶利内克在《他不是他》中表现出来的文学主体观。在整个文本的十二个片段中,她始终与瓦尔泽在一起实践着一个约定,那就是“诗人总是走出自我,总是在激活他人,而从来不是自己”。相反诗人在写作过程中“释放着自身的人性本质,这个本质会带上别的特性,使人在这个深谷中迷失方向”。这就是说,诗人的人性本质与其作品的本质常常会混淆不清,以至于诗人心中所蕴含的宏大的东西一旦表现出来,就成了某种特别微不足道的东西了,它会小到常常不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耶利内克怀疑这个主体的“微不足道”也许是瓦尔泽故意为之,因为主体的蜷缩恰恰是“因为今天的‘宁静’过于喧哗,今天的‘人’真正在死亡”。(Jelinek:10-12)或许耶利内克在文学现代性中找到了上述悖论的解释。
本雅明曾对瓦尔泽的“自我”做过一个解释:“也许我们只要从一部《白雪公主》——瓦尔泽当代文学中具有最深刻意义的作品中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个表面上看最为扭曲的瓦尔泽是固执的弗朗茨·卡夫卡最钟爱的作家。”本雅明所说的就是瓦尔泽用无人不晓、极其平常的童话来当隐喻,以诗歌舞台剧的形式开始写作散文,从而把文学主体掩埋得最深。其手法就是本雅明所说的“最为扭曲”的文学主体。如果说本雅明的评论是以“瓦尔泽开始的形式结束”,(Benjamin:351)那么瓦尔泽的“童话”恰恰是在美好的结局之后开始:白雪公主、王子、猎人和女王在宫殿中一起对童话本身质疑,过去和现在、童话和真实情景交织在一起,“善”与“恶”完全失去了可以依附的替身。在本雅明眼里,瓦尔泽的《白雪公主》不是新瓶装旧酒,而是在本质上对文学叙事的摧毁,多义性、文学主体因此也就得到了逃遁的可能。
这也是耶利内克的企图。在《死亡和少女》的首篇《白雪公主》中,耶利内克也同样在死亡中建构了童话和现实的悖论,因为只有死亡才是绝对真理。她不仅让白雪公主在时间的隧道中穿越了真理,而且也把瓦尔泽拉进了这个时间的隧道:“我现在离开房子,假如我步伐快一点的话,我马上就会回到死亡,会准时地回到死亡中去。”在死亡中唯一做的一件事就是散步,“假如宁静最终还是宁静的话”。(Jelinek:43-44)
四
瓦尔泽的《陌生人》是一篇暗示文学主体诞生的重要散文,文中首先反思了主体的孤独与封闭:当一个从窗前路过的陌生人举头投来期望交流的友好眼神时,“我”表现出来的是习惯性的“视而不见”和“置之不理”。(瓦尔泽:239)这其实不过是现实生活中的主体的“失语”的插曲(而在弗洛伊德眼里这正是歇斯底里患者的一种症状)。在《陌生人》里,瓦尔泽从这个日常现象出发反思了“我”的“过失”,却无意地宣示了自己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代名词“托波特”(Tobold)的诞生,同时这也暗示了其文学文本诞生的过程:
我觉得自己非常没有责任心。我甚至可以说我感到很难过,感到不幸。不过我不喜欢“幸”或者“不幸”这两个字眼,它们说不清什么事情,我已经给那个陌生人取了一个名字,就是那个在我窗下要跟我打招呼的年轻人,我叫他托波特。当我想到他的时候,他就以托波特名字出现。这个名字我是在半睡眠半清醒的状况下偶然想出来的。现在他在哪里?他在想什么?我是不是能够猜出他脑子里的想法?是不是能猜出他现在正在想些什么?或者反过来,我是不是能够想象,他是否脑子里有跟我一样的问题。我的思绪久久地缠萦在他身上,在那个寻找过我的人身上。(瓦尔泽:239)
现代人常常是孤独的,他们的主体性也许习惯于封闭。瓦尔泽一辈子就是孤独的散步者,而文学正是他打开内心门闩的一个途径,就如耶利内克所看到的那样:“要打开自我就必须从内心出发。”(Jelinek:15)瓦尔泽在《陌生人》中就是这样用文学打开自己“自我”的。耶利内克对瓦尔泽上面《陌生人》的一段文字做了恰如其分的阐释:
对那些总是写自己,但又是指自己的作家我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那些认识到自我残缺的作家。他们虽然在不断地说自我,但不是在指自己,而是在说其他。这不是弗洛伊德意义上的“本我”,也不是“超我”,而是在作家身心中的所有。我自己大概也属于这类作家。那是些相对自我封闭的作家,他们在写作时处于一种不能守住自我的状态。比如我就会在写作中进入一种恍惚的状态,这是一种半醒半睡的状态,但决不是睡或是醒的状态。反过来说,瓦尔泽也是一个常常出神的作家,他的写作是为了自我在现实中的移位。(Jelinek/Lecerf:13)
瓦尔泽写过一篇著名的散文叫《散步》,他在其中写道:
您想想,假如一个诗人或作家一旦停止吮吸生育和抚养他的大自然中真善美的乳汁,那么他很快就会文思枯竭,江郎才尽,可悲地落到失败的境地。您再想想,诗人作家从外面千变万化的世界里得到的神圣金色的教诲,这大自然的课堂对他会是多么的重要。(瓦尔泽:159)
耶利内克从瓦尔泽的文学散步中汲取了精神养分,就像她自己所说的那样:
我记不起来什么时候第一次读瓦尔泽的东西,我经常不断地阅读他的东西,就像读报纸一样。他对我来说就像是内涵深厚的作家,万花筒般的世界集聚在每一个小点上,我的每一本书里都蕴涵着瓦尔泽的话,就像人们以前造大教堂时在地基里要埋只生灵那样,我写的东西里都有瓦尔泽的意蕴在里面。(Jelinek/Lecerf:13)
耶利内克这里所说的意蕴或许就是她与瓦尔泽共有的文学主体观:在放弃和消解文学主体的过程中以期实现文学主体的实质所在。至此,我们可以谨慎地说,通过上述解读,我们大概悄悄地走进了“他不是他”这个命题中所蕴含的否定之否定,而这个辩证法也许正是教堂地基下掩埋的那只生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