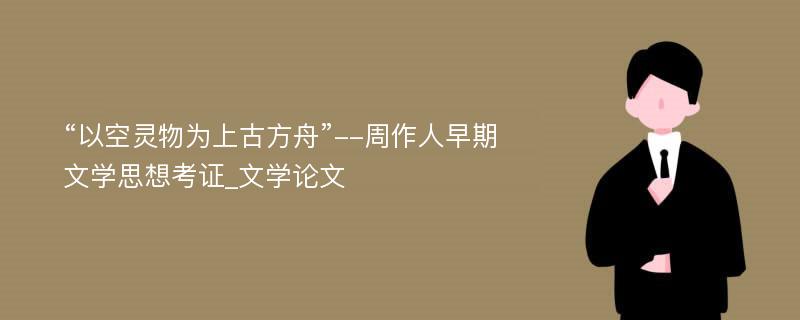
“以虚灵之物为上古之方舟”——周作人早期文学思想考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舟论文,上古论文,之物论文,思想论文,周作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0)05-0078-06
1918年,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一文中,周作人说:“新小说与旧小说的区别,思想果然重要,形式也甚重要。”[1](P.55)这事实上也构成他散文写作的两个向度,在从“美文”到“时事之文”再到30年代“笔记体散文”的写作过程中,如何实现思想与形式之间的浑然统一,正是他要思考的一个核心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周作人努力做到两者之间的平衡。一个有趣的事实是,每当因现实与思想的纷乱而心浮气躁时,他就高呼“我只希望,祈祷,我的心境不要再粗糙下去,荒芜下去”,“我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境地”,并说自己以后“大约是不想写”长篇论文,而“想只作随笔了”;然而当他写了像《苍蝇》《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等一批“平淡自然”的“美文”以后,却又在《泽泻集》的序言中宣称:“我希望在我的趣味之文里也还有叛徒活着。”①在这看似矛盾的言说中,正折射出作者为调和“思想”与“文学”所付出的努力。
周作人的文学经历起步于1901年10月到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读书以后。这恰好是中国文学观念的转折期。杨联芬认为:“晚清新小说运动大致可以1900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1900年前(实是戊戌变法失败前),维新知识分子对小说的倡导,基本上属于思想界发现和论述小说重要性的理论呼吁阶段,小说只是作为抽象概念被置于配合政治改革的思想启蒙位置,也就是说处于维新运动‘外围’之意识形态方面,还没有被视为文学,所以关于小说创作和具体形式的探讨,在那时几乎没有涉及。1900年后,维新派知识分子参与政治改革的可能性丧失,伴随着梁启超身份和事业的转移,这种情形才发生了改变。”②
维新派知识分子是在丧失了他们传统“得君行道”的政治途径以后,才转而以民间知识精英的立场,通过文学,来提倡变法救国的。变法以后,出于对文学本身的重视,中国知识界对“文学”本体的研究及其创作实践,呈现出了一种新的面貌。根据陈平原的研究,“中国小说1902年起开始呈现对传统小说叙事模式的大幅度背离”,[2](P.12)这是文学技法上的革新;更重要的是,观念上的革新也在进行之中。差不多就在同时,以王国维为代表的“纯美”的文艺思想,也在中国文艺界浮出水面。王国维认为:“美之属性,一言以蔽之曰: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已”,并认为哲学与美术是“天下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今夫人积年月之研究,而一旦豁然悟宇宙人生之真理,或以胸中惝恍不可捉摸之意境一旦表诸文字、绘画、雕刻之上,此固彼天赋之能力之发展,而此时之快乐,决非南面王所能易者也。”正是建立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他给文学下定义:“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而“个人之汲汲于争存者,决无文学家之资格也”。③在20世纪初的中国,这样一些言论的出现,无疑促进了当时文艺界对文学本体地位的思考。
然而这只是一个方面,笔者想要强调的是另一个方面。虽然已经出现了艺术无功利的审美思想,但在后维新时代,由于“文学”在一段时间里差不多充当了“得君行道”的替代之一,因此由政治的意识转化而成的文学的功利观念,仍然在当时的文学理念/创作中占有相当的地位。1902年,在刚刚创办的《新小说》第一号“论说”栏中,梁启超发表了著名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开头即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即小说具有“熏”“浸”“刺”“提”四种力量。[3](P.6)在这篇论文里,梁氏对小说文体的讨论,尤其是对后四种力量的论述,大体仍在小说的文体属性内展开,这也是20世纪初中国文艺界出现的新气象;但问题在于,这样一种讨论,其最后的思想归结,却是由小说的文体属性找到了“新民”的途径。这就从文学本体的层面,将小说从中国传统的“小说小道”,提升到了民族救亡的宏观视野中来加以考察,它一方面为中国现代小说/文学注入了超越常规的“尊严”地位,另一方面,在众多的“欲……必新小说”的论说结构中,无限放大了文学的社会功能。
在20世纪初的中国,这两个方面的探索一方面并存着,并各有沿着自身思路展开的理论探讨与创作实践;另一方面,更为普遍的现象是,出现了两者之间的调和思想,从而形成了一种有限度的文学功能理论。周作人早期的文学思想,事实上也处于这样一种调和之中,即周作人的文学思想,从一开始就面临了如何处理文学的艺术属性及其社会功能之间的关系问题。从原则上来说,他既反对一种纯美的艺术理论,同时也不主张无限度地放大文学的社会功能,而是在这两者之间,取一种“中庸”的调和态度。在这里,调和不是简单地捏合取中,而是出于对两方面立场的更为深刻的了解与吸取,其背后隐含的,则是他对知识分子社会身份及其功能的自我体认。
周作人在南京读书期间深受梁启超的影响。周氏当时的日记中有多条内容记录了这一方面的消息。如:
1902年8月6日(七月初三)条:“……借得《新民丛报》十一号(六月朔出)。阅之,内好书甚多,率皆饮冰子所著。看至半夜,不忍就枕。善哉,善哉,令我有余慕矣!”8月7日(七月初四)条:“上午抄《饮冰室诗话》《尺牍》及摘录《新罗马传奇》《新民说》等,至午竟。下午发致韵仙托买《饮冰自由书》《中国魂》二书……”8月9日(七月初六)条:“夜借得《自由书》一册,阅之,美不胜收,至四更始阅半本,即睡。”8月10日(七月初七)条:“上午《自由书》看竟,换得《新民报》二册。”
此后8月12、13、14、17日均有关于梁启超文字的阅读记录。④如此密度的阅读与评论,知堂当时对于梁氏的言论,完全称得上是入迷。直至1903年3月11日(二月十三日),周作人“接日本初五函,由韵仙交转,并《新小说》第一号、《权利竞争论》各一本,看十余页”,次日“上午看《新小说》竟”。[4](P.377)
梁启超的文学思想,至少是有助于周作人确立起一种严肃的文学观念,一种对文学尊严地位的认同。与王国维不同,从20世纪早期开始,周作人的文学思想,就不但反对将文学视为娱乐、游戏之一种,而且也还反对纯粹的“为艺术而艺术”一类的观点。在《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一文中,周作人即认为:“文章之德,固亦有娱乐一端,然其娱乐之特质,亦必至美尚而非鄙琐”,“若夫文胜质亡,独具色彩而少义旨,斯为失衡。”他强调,文学须“具神思(Ideal)能感兴(Impassioned)有美致(Artistic)”,此三者,“使其作用侧宗一解而缺调和,则有偏胜之患。主神思者入于怪幻,重美致者沿为L'art pour l'art(此言为艺术之艺术),而感情之说则又易入浅薄一流”。其中对于“美致”一端,周作人尤其联系中国传统视说部为“闲书”的观念,作了更进一步的批评:
有别说焉,其义亦正,而为众所可认者,谓著作极致在怡悦读者,令得兴趣、有美感也。理固纯定,亦为文章所当有事,第复失于偏,未能圆满。美致之说,上已及之,此仅为文章之一枝,未可即该全体。如在诗歌韵律之作,犹为副因,散文益在其次。若文章为用唯观听之娱,则其流甚易入于纯艺术派。吾国素目视说部为闲书,惟供茶余酒醒之消遣,而猥鄙之作亦即乘此而兴。轻视之渐,其品益下,则犹不如艺术末流,虽或不中,尚本学理而来,未至如是之滥恶也。[5](PP.97-101)
这里,周作人虽然认为“纯美”理论“其义亦正”、“理固纯定”,但终于“仅为文章之一枝”,而“未能圆满”。不但如此,更为周作人所担心的是,这种纯美的艺术理论假如和中国“视说部为闲书”的传统观念结合起来,就很有可能削弱小说/文学的社会功能,从而导致“其品益下”,甚至达到一种“滥恶”的境地。由此可见,周作人的文学思想,其实始终存有一个关心现实社会思想、文化的维度。有意味的是,周氏此文写于1908年,而此前从1905到1907年,王国维已在国内系统提出了无功利的文学理念,甚至直言“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这样,周作人的上述观点,纵然不是对王的直接批评,其不引后者为同调,也应该已经甚为分明了;而其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立场差异,梁启超至少是一个不应该被忽略的存在⑤——从这一个口子,周作人确立了一种严肃的文学观念。这种文学观念与他作为精英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是一致的,在它的引导下,我们无法想象周作人会认同《礼拜六》打出的“宁可不娶小老嬷,不可不看《礼拜六》”一类的文学推介;而他后来屡屡强调文学的“道德”力量,其源盖亦在于此。⑥
但周作人对梁启超文学思想的认同,恐怕也仅限于此。对于梁氏的政治小说,他始终没有表示赞赏。这就说明,周作人对于文学尊严地位的强调,并非是像梁启超那样,通过无限放大文学的社会功能来实现;恰恰相反,对于后者,他持一种严格的限定态度。正是在这样的结合点上,融入他对艺术本体的思考。在周作人,他的文学功能理论是建立在文学本体范畴之内的,受到文学艺术属性的制约。唯其如此,在留学日本以后,周作人的文学思想就不但反对一种为艺术而艺术的纯美理论,而且也还反对一种没有节制的文学功能论,一种视文学为“教训”的态度。
这里有必要就周作人的文学经历稍作回顾。事实上,在受到梁启超影响的同时,周作人还接触到了林纾翻译的西方小说⑦;与此同时,利用在江南水师学堂学到的一点英文知识,他还开始翻译爱伦·坡、雨果等人的小说。⑧1906年夏秋之际到日本留学以后,周作人的西方文学视野进一步拓展。1907年3月,并开始“与鲁迅合译英国哈葛德、安特路朗合著的小说《世界欲》(The World's Desire),译名易为《红星佚史》”。[6](P.69)这样一种文学经历,不仅仅是理论上的,而且也是实践上的(正如陆游的诗:“纸上得来总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使周作人有能力对现代/西方文学的内在肌理,作相对深入的了解,并使他有能力对一种“教训”的文学观,持批评的态度,从而超越了梁启超的文学理论与实践。1907年2月,在《〈红星佚史〉序》中,周作人说:
中国近方以说部教道德为桀,举世靡然,斯书之翻,似无益于今日之群道。顾说部曼衍自诗,泰西诗多私人制作,主美,故能出自由之意,舒其文心。而中国则以典章视诗,演至说部,亦立劝惩为臬极,文章与教训漫无畛畦,画最隘之界,使勿驰其神智,否者或群逼拶之,所意不同,成果斯异。然世之现为文辞者,实不外学与文二事,学以益智,文以移情,能移人情,文责以尽,他有所益,客而已,而说部者文之属也。读泰西之书,当并函泰西之意,以古目观新制,适自蔽耳。[7](PP.48-49)
功利的文学思想被强调到极致,就必然出现“以说部教道德为桀”的创作现象,而这正是晚清梁启超一脉文学创作的弊端。它使文学沦为“教训”的工具,从而失去其独立的地位。对此,周作人同样不能认同。在这段引文中,他从西方文艺“主美”的立场出发,认为文学的功能只在“移情”,“能移人情,文责以尽,他有所益,客而已”。这里所谓的“移情”,其在写于1907年的《文章之力》中以“其与读者交以神明,相喻于感情最深之地”[8](P.72)作解。此后在《圣书与中国文学》(1920年)一文中更借助于托尔斯泰《什么是艺术》中的观点,作进一步申述:“艺术家的目的,是将他见了自然或人生的时候所经验的感情,传给别人”,“一切艺术都有这个特性,——使人们合一。各种的艺术都使感染着艺术家的感情的人,精神上与艺术家合一,又与感受着同一印象的人合一。”[9](P.300)显然,所谓“移情”,是从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上讲的,这和“教训”的文学观有些相似。但两者之间仍有差别,“教训”的文学观是作者单向度地将自己的政治思想、道德观念灌输给读者,“开口见喉咙”,“议论多而事实少”;⑨而在“移情”的理念下,作者和读者之间必须凭借了“情感”的中介——作家将个人的情感融入到艺术品之中,而读者则从艺术品中重新感受到作者的情感,从而实现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情感“合一”——才能实现文学的感染力量。
这样一种艺术的中介,周作人在《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一文中,有更为详细的讨论。在这篇论文里,他在考察西方关于文学的多种定义以后,最终偏向于美国人宏德(Hunt)的界定:“文章者,人生思想之形现,出自意象、感情、风味(Taste),笔为文书,脱离学术,遍及都凡,皆得领解(Intelligible),又生兴趣(Interesting)者也。”为此,他敷解四义云:“其一,文章云者,必形之楮墨者也”,“其二,文章者,必非学术者也”,“其三,文章者,人生思想之现形也”,“其四,文章中有不可缺者三状,具神思(Ideal)能感兴(Impassioned)有美致(Artistic)也”。而在第四条的解释中,周氏进一步说:“思想在文,虽为宗主,顾便独在,又不能云成……夫文章思想,初既相殊而莫一,然则必有中尘(Medium)焉,为之介而后合也。中尘非他,即意象、感情、风味三事(即顷所举三状之质地)合为一质,以任其役,而文章之文否亦即以是之存否为衡。”这就很清楚,在周作人,人生思想是文学的根本内容,但表现这一内容的文字要成为文学,则必须经过艺术的中介,即须将人生思想融入到意象、感情、风味之中,锻造出一种“能感”的文学品格,否则,“使不经此,则所形现者将易于混淆,更无辨于学术哲理之文矣”。这样,通过对艺术中介的强调,周作人确立起了文学的独立地位:“文章一科,后当别为孤宗,不为他物所统。”[5](PP.96-98)
然而,正如周作人并不因为认同文学的社会功能而将这一倾向无限放大一样,他对文学独立地位的强调,同样也有其限度。这就是说,虽然是要否定一种“教训”的文学观,他却并不因此而走向王国维式的“纯美”一途。在这个问题上,周作人选用“移情”一词来表达他对文学功能的认识,颇具玄机。
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中概述西方文艺思想中的“移情”理论时说:“移情作用在德文中原为Einfühlung。最初采用它的是德国美学家费肖尔(R.Vischer)、美国心理学家蒂庆纳(Titchener),把它译为empathy。照字面看,它的意义是‘感到里面去’,这就是说,‘把我的情感移注到物里去分享物的生命。’”[10](P.236)文艺理论上的“移情说”后来由德国美学家立普斯(Theodor Lipps)发扬光大。立普斯“移情说”,首先是主体要将自己固有的情感外射到客体中去,然后再从客体读取这种感情,并最终引起自己情感上的审美反应。这样,文艺理论上的“移情”问题,其关注的焦点其实是在鉴赏主体自己的“情感”由外射到获取的心理过程上。这和王国维对艺术的认识有些接近。在王国维,“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11](P.12)在这样的前提下,他对艺术的理解是自足的,它无需借助于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而只需从作者或鉴赏者的自我情感体验中,即可实现艺术的审美价值。但周作人强调的“移情”显然不具有这样的品性。他的关注焦点是在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情感”共鸣上,即读者通过作品获取作者在这个作品中所要表达的情感。这样,在周作人,“移情”的确切含义就是作者通过作品感染读者,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互动过程。
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在这一互动的过程中,周作人希望实现的,是一种怎样的情感效果?即其所谓的“情”字,是否就是一个纯美学范畴的概念而不具有社会性?这个问题其实梁启超早就已经提出。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梁启超首先认为,小说“感人”的特性“如空气如菽粟,欲避不得避,欲屏不得屏,而日日相与呼吸之,餐嚼之矣”。这样,假如“其空气而苟含有秽质也,其菽粟而苟含有毒性也”,那么,“其人之食息于此间者,必憔悴,必萎病,必惨死,必堕落”。[3](PP.8-9)就是说,小说“感人”的属性本来是没有善、恶之别的,人们往里面填注善的内容则其所“感”者善,反之则恶。正是从这样的前提出发,为鼓荡民气,梁氏批评了中国传统小说创作中的“诲淫诲盗”现象,进而提出了“新小说”的主张。
对周作人来说,“移情”同样存在这一前提。在《人的文学》中,他认为:“莫泊三(Maupassant)的小说《一生》(UneVie),是写人间兽欲的人的文学;中国的《肉蒲团》却是非人的文学。俄国库普林(Kuprin)的小说《坑》(Jama),是写娼妓生活的人的文学;中国的《九尾龟》却是非人的文学。这区别就只在著作的态度不同。一个严肃,一个游戏。一个希望人的生活,所以对于非人的生活,怀着悲哀或愤怒;一个安于非人的生活,所以对于非人的生活,感着满足,又多带些玩弄与挑拨的形迹。”[12](PP.88-89)在这样的言说中,可以看到周作人与梁启超思想关注的近似。在一种精英知识分子的立场下,谈“移情”就不纯粹是一个文艺学上的问题,而还牵涉到价值问题,因而与所“移”之“情”的内容有关。由此,周作人所谈之“情”,恐怕就不是一个“趣味”所能够涵盖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它应该还包括了诸如国民精神、人类蛮性的批判等诸多内容。这样,周作人关于“移情”的论述,内在地,已经预埋了他对文学社会功能的认同,而并非只是对文学本体属性的强调。
因此,周作人的文学思想具有浓郁的调和倾向:一方面,虽然在精英知识分子的立场下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却反对将这种社会功能强调到极致,因而从反面强调文学的独立地位,并使文学与政治等领域保持距离;另一方面,对文学独立地位的强调又并不隔绝他对现实社会思想、文化的关注,因而在创作上强调一种严肃的文学态度,并使其文学观念与纯美的艺术理论区别开来。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立场,在《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一文中,周氏最后说:“夫文章者,国民精神之所寄也。精神而盛,文章固即以发皇,精神而衰,文章亦足以补救,故文章虽非实用,而有远功者也。”他又从埃及、希腊、波兰的历史观察中得出,一个民族或者国家,“质(按,指人、地、时三事)虽就亡,神能再造,或质已灭而神不死者矣,未有精神萎死而质体尚能孤存者也”,因此,“为今之计,窃欲以虚灵之物为上古之方舟”。[5](P.88-94)在周作人,文学既“非实用”,但亦有“远功”;虽为“虚灵之物”,却可成为救世的“上古方舟”。就在这样一种奇妙的结合中,他为“文学”与“思想”的融合,找到了自己的理解与途径。而此后他既反对“为艺术的艺术”、又反对文学“为人生”,既批判载道的文学观、又强调文学的“道德”力量,既有一种再造文明的文化冲动、又与文学救亡的诸多力量保持距离,这一系列看似矛盾的主张与选择,若从这调和的文学倾向,以及与这一倾向紧密相连的文化立场出发加以理解,也就大都能够得到切实的解释。
收稿日期:2010-08-10
注释:
①以上引文分见周作人《雨天的书·自序二》(1925年)、《艺术与生活·自序》(1926年)、《泽泻集·序》(1927年),收入《雨天的书》第4页、《艺术与生活》第2页、《泽泻集》第1页;亦见《周作人散文全集》第4卷第346-347页、第4卷第733页、第5卷第281页。
②关于晚清小说地位的演变,参阅杨联芬《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引文见该书第1章,第22页。
③参见王国维《古雅在美学上之位置》(1907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1905年)、《文学小言》(1905年),收姚淦铭、王燕编《王国维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5月第1版,下部第17页、第12-13页,上部第16页。
④参阅鲁迅博物馆藏《周作人日记》,大象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上册第344-346页,其中引文标点由引者添加。以下凡引该著文字,标点皆由引者添加,不再注。
⑤近来学人在讨论周作人的文学思想时,大多表彰其纯美的一面,而认同他与王国维之间的同调。袁进在《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之第四章《新与旧》中即认为:“鲁迅、周作人对人生的看法与王国维很不相同,但在文学观念上却与王国维一致。”杨联芬在《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第一章《在悖论与调和中建立文学的“现代”平台》中也认为:“在1908年前后,周氏兄弟的文学观念并不接近梁启超,而更接近王国维。”我的意见略有不同。周氏兄弟早期的文学思想,从总体上来看是调和了以梁启超和王国维为代表的功利与纯美两脉文艺思想,因此,从任何一脉中找到其近似或背离之处,就都有其文本上的脉络与依据。但若从思想底色,或从后来的文学创作出发分析,那么,周氏兄弟的文学观念,从根本上说,就都带有更为明显的用世意识,因而或明或显地存在一种社会功利色彩,这就使他们的文学思想更接近于梁启超,而不是王国维。袁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版,2009年4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本文引用据后者,第82页;杨文见氏著,第40页。
⑥事实上,受梁启超的影响,周作人在南京读书期间的文学观念也颇带有国家主义的立场,参阅周作人《说生死》(1904年)、《论不宜以花字为女子之代名词》(1904年)、《女猎人》(1905年)等文。甚至一些文章的用语也带有梁氏风格,如读《女猎人》中的“吾心目中固宛然有女猎人在”,不由让人想起梁氏《少年中国说》中的名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引文参见《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卷,第32页;《饮冰室合集》第1卷,文集之五,第7页。这种国家主义的影响直到留学日本期间,仍有夹杂的表现。如写于1907年的《文章之力》中,周作人还是认为:“吾窃以为,欲作民气,反莫若文章。盖文章为物,务移人情,其与读者交以神明,相喻于感情最深之地,印象所留,至为深入,莫能漶灭。”所谓“欲作民气,反莫若文章”,就仍然留有国家主义的思想影子。此后随着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加大,这种国家主义的立场才逐渐淡薄,到五四时期,乃有直接否弃的言论出现。引文见《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卷,第72页。
⑦周作人在南京读书时很喜欢林译的小说,差不多出一种买一种。林氏去世以后,在《林琴南与罗振玉》一文中,周作人还这样介绍林在翻译上的功绩:“老实说,我们几乎都因了林译才知道外国有小说,引起一点对于外国文学的兴味,我个人还曾经很模仿过他的译文。他所泽的百余种小说中当然玉石混淆,有许多是无价值的作品,但世界名著实也不少:达孚的《鲁滨孙漂流记》,司各得的《劫后英雄略》,迭更司的《块肉余生述》等,小仲马的《茶花女》,圣彼得(St.Pierre)的《离恨天》,都是英法的名作,此外欧文的《拊掌录》,斯威夫德的《海外轩渠录》,以及西万提司的《魔侠传》,虽然译的不好,也是古今有名的原本,由林先生的介绍才入中国。”见《周作人散文全集》第3卷,第524-525页。
⑧周作人于1905年翻译了爱伦·坡的小说《玉虫缘》、柯南道尔的《荒矶》(The Man From Achemgle)、取材于《天方夜谭》的《侠女奴》;1906年摘译改编了雨果的小说《孤儿记》。
⑨此两条引文分别出于公奴《金陵卖书记》(上海开明书店,1902年)和俞佩兰《〈女狱花〉叙》(收《女狱花》,泉唐罗氏藏版,1904年),本文据陈平原《小说史:理论与实践》引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3月第l版,第233页。
标签:文学论文; 周作人论文; 王国维论文; 周作人散文全集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读书论文; 梁启超论文; 新小说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