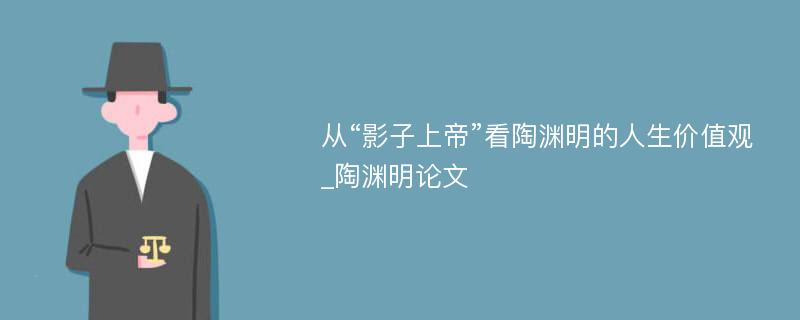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从《形影神》诗看陶渊明的生命价值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影论文,亦不论文,价值观论文,陶渊明论文,生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733(2003)04-0081-05
陶渊明为什么不享受“公田之利”而去“种豆南山”?为什么视官场为“樊笼”而要返归“自然”?从陶渊明的诗歌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与他的生命价值观有着密切关系。陶渊明现存诗歌120馀首,其中吟咏生死的作品占了一半以上。本文拟从陶渊明著名的《形影神》三首组诗的分析入手,就陶渊明的生命价值观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
《形影神》三首组诗最为集中而深刻地表现了陶渊明的生命价值观,下面是三诗并序:
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舒自然以释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
形赠影
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
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适见在世中,奄去靡归期。
奚觉无一人,亲识岂相思。但馀平生物,举目情凄湎。
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
影答形
存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
与子相遇来,未尝异悲悦。憩荫若暂乖,止日终不别。
此同既难常,黯尔俱时灭。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
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酒云能消忧,方此讵不劣。
神释
大均无私力,万物自森著。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
与君虽异物,生而相依附。结托既喜同,安得不相语?
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受永年,欲留不得住。
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
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在这一组诗里,诗人让“神”辨自然以释“形”、“影”之苦。“形”指代人企求长生的愿望,“影”指代人求善立名的愿望,“神”以自然之义化解它们的苦恼[1]。“形”认为虽然人最具灵性,最具智慧,但不仅不能像天地那样“长而不没”,像山川那样“无改时”,而且也不如“草木得常理”,经霜经露枯萎而复荣。人生苦短,惟一能做的就是“得酒莫苟辞”,肆口腹之所须,恣心意之所娱。表面看来,狂饮烂醉和纵欲无度是作践生命,是“惜生”和“求生”的反面,然而它骨子里是对惜生不得、长生不能的绝望表现。“影”则选择了另一种存在方式。“影”认为卫生养形既不可能,长生不老更是无望,登昆华,求神仙,此道久绝;既然不能使形长存就应该让名不朽,如果“身没名亦尽”,怎不使人“念之五情热”。表面上看,求名者与饮酒者有异,实质上二者相同,“不得已而托之身后之名,与托之游仙饮酒者同意”[2]。在“极陈形影之苦”之后,诗人借“神”之口抒写其生命感怀。“形”惧“奄去靡归期”因而追求口腹之所须,心意之所娱,“得酒莫苟辞”。“影”惧“身没名亦尽”因而追求“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然而在“神”看来,“形”和“影”可谓自寻烦恼,因为“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死亡是每个人生下来就得担当的宿命,不管如何“营营以惜生”,人人都要走向死亡。“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沉湎于醉乡非但不能超脱生死,反而使生更短促,使死更提前。“立善长所欣,谁当为汝誉”,立善当然是为人钦仰之举,但沽名钓誉则不可取。“形”累于养而欲饮,“影”役于名而钓誉,其弊全在于“营营以惜生”,而“惜生”的症结又在于害怕失去自我——失去自我的身体、精神、名誉、财富”[3]。
饮酒和求名是“形”和“影”面对短促的人生所作的生命价值选择,但陶渊明将两者的存在方式视之为“苦”,表明他对人生价值的选择并不以此为念。然而陶渊明在他的诗文中却常说他“性嗜酒”,“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次辄尽,期在必醉”(《五柳先生传》);求彭泽令的目的,也是因为有“公田之利,足以为酒”(《归去来兮辞》);甚至于他在临终前所写的《拟挽歌辞》中也有“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的感叹。披阅其诗,则几乎“篇篇有酒”。那么,他为什么在《形影神》诗中否定“得酒莫苟辞”呢?我们认为这是因为陶渊明之饮与“形”之饮具有本质的不同。“形”之饮,是由于恨人生太短,所以要穷当年之欢,尽一生之乐,这说明它并没有超脱生死,对死亡心怀恐惧和绝望。陶渊明之饮则不然,他是为了“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饮酒》其七),从而达到“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饮酒》其十四)的超然境界。
超然物外,“纵浪大化”,是诗人对生与死的超脱,是诗人对生命价值的惟一选择。它既可去“形”之累,又可解“影”之役:“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个体生命是大化的一部分,应当将个体融进宇宙大化的生命洪流,一方面在精神上吐纳山川,另一方面又与造化和同一气,随天地而同流,与大化而永在,天地大化的生生不息就是个体生命的永恒。
二
《形影神》这组诗大约创作于晋义熙九年(413),时为东晋末年。当时佛、道、玄思想泛滥。名僧慧远在庐山主持东林寺,写《形尽神不灭论》和《万佛影铭》,宣扬净土宗关于神不灭,信佛可以通过轮回获得来生幸福的教义;而五斗米道则宣扬符篆炼丹,升仙永生;玄学由无为的自然观趋于放诞,达官贵族则追求奢侈享乐。还有名教的流毒,鼓励士人沽名钓誉[4]。陶渊明在这组诗里,不仅是针对慧远的《形尽神不灭论》和《万佛影铭》而发,也不仅仅是批判了道教徒的“长生久视”说,而且也是对传统人生观的扬弃。
我们知道,人的生命价值始终是古代士人所关注的大问题。自孔子提出“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之后,“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曹植《与杨德祖书》),“使名挂史笔,事列朝荣”(曹植《求自试表》),一直是我国古代知识分子无法解脱的情结。同时富与贵,义与利,长生久视与尽情享乐也由于人们的取舍不同而煽炽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思潮。这种人生价值观在《古诗十九首》里就有着最为集中而鲜明的表现。《古诗十九首》产生于东汉末年,其作者们是这样表述他们对生命价值的选择的: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人生的价值在于选择高官要职,而求得权势和富贵;
“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人生的价值在于立德立功立言,而使“荣名”传于身后,以求不朽。
“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人生的价值在于扫除烦恼,摆脱羁绊,放情自娱。
“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五金石固。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丸与素。”——人生的价值莫过于“饮美酒”,穿美服,求得物质生活的满足。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人生的价值莫过于及时行乐,尽情享受有限的人生。
从上面所引的这些诗句我们可以看到,《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们对草木的枯荣,岁月的飘忽特别敏感,也就是说他们看到草木的荣枯想到岁月的飘忽,就情不自禁地产生出对死亡的恐惧,因而他们探人生之哲理,究生命之价值,唱出了一曲曲荡气回肠,动人心魄的哀怨悲歌。
实际上陶渊明对草木的枯荣,岁月的飘忽,同样具有《古诗十九首》作者那样的敏感,自然界草木的枯荣常常触发他的生死之念:“采采荣木,结根于兹。晨耀其华,夕已丧之。人生若寄,憔悴有时。静言孔念,中心怅而。”(《荣木》)在《杂诗》其三中他写道:“荣华难久居,盛衰不可量。昔为三春蕖,今作秋莲房。严霜结野草,枯悴未遽央。日月还复周,我去不再阳。眷眷往昔时,忆此断人肠。”人事的盛衰如同草木的枯荣,可是人生的老少却又不像草木“还复周”,因而诗人发出了人生不如草木的慨叹。
节序的变化更使陶渊明“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游斜川》序),常常引起他对生命终结的焦虑:“开岁倏五日,吾生行将休。”(《游斜川》)“流幻百年中,寒暑日相推。常恐大化至,气力不及衰。”(《还旧居》)“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饮酒》其三)“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岁月相催逼,鬓边早已白。”(《饮酒》其十五)“日月不肯迟,四时相催迫。”(《杂诗》其七)“明旦非今日,岁暮余何言!素颜敛光润,白发一已繁。”“民生鲜长在,矧伊愁苦缠。”“穷通靡攸虑,憔悴由化迁。抚已有深怀,屡运增慨然。”(《岁暮和张常侍》)面对短暂的人生,诗人也曾有过多种生命价值选择。他曾回忆他青少年时代的远大志向说:“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诲,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其八)这是多么有豪侠之气的壮志。在诗中他还表扬过那些廉正自守的官吏:“袁安困积雪,邈然不可干。阮公见钱入,即日弃其官。”(《咏贫士》其五)“昔在黄子廉,弹冠佐名州。一朝辞吏归,清贫略难俦。”(《咏贫士》其七)这种赞扬,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陶渊明大济苍生的志向[4]。他的多次出仕,也正是他追求这种人生价值实现的表现。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陶渊明的壮志逐渐消磨,但其用世之心并未完全消失。在《荣木》诗中,他自责废学耽饮,“总角闻道,白首无成”。最后说:“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在《杂诗》中他又说:“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同时,他也曾有过“在世无所须,惟酒与长年”(《读山海经》其五)、“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杂诗》其四)的生命价值思考。然而,陶渊明清楚地认识到,在当时的社会里,他的大济苍生的人生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沉湎于酒,不仅不可能“促龄具”,相反还可能使人生变得更短,而“斯人乐久生”,也不过是痴人说梦。在对生命价值作了再三思考后,他说:“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屡空不获年,长饥至于老。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裸葬何必恶,人当解意表。”(《饮酒》其十一)因而在“称心固为好”的思想指导下,他最终还是选择了“纵浪大化”的生命价值观而抛弃了传统的生命价值观。
三
“纵浪大化”就是返回自然。它包括外在自然与内在自然两个层面。对陶渊明来说,返回外在自然就是弃官归隐,去享受山水田园之乐。在《归去来兮辞》中,陶渊明对他的生命价值观作了这样的宣示:“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实际上,这种价值选择不只是陶渊明瞬间的审美体验和身心陶醉,而是他整个生命的沉浸和投入。史传记载,陶渊明二十九岁“起为州祭酒”,但“少日自解归”。其后又曾辞去主薄之聘。过了六七年,在三十五岁时,他又出任江州刺史桓玄的州府官吏,一二年后又因母丧退归。四十岁时他又复出为镇军将军刘裕的军府参军,明年转为江州刺史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同年八月,为彭泽令。十一月,因程氏妹之丧,弃职返里。此时陶渊明四十一岁,此后便再未出仕[4]。从陶渊明的仕宦简历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虽然多次涉足仕途,但每次出仕的时间都很短,任职不久即自行解职。从表面上看,陶渊明的自行解职似乎都是因为家中有事,但实际原因并非如此。例如陶渊明三十五岁时任职于江州刺史桓玄的州府,次年所写的《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中就有这样的诗句:“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诗中,诗人又透出这样的信息:“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由此可见,陶渊明虽然三翻五次涉足仕途,但每次出仕他都感到自己是“以心为形役”,因而身在仕途而心念山泽园田。这种时仕时隐时出时归的仕宦生涯,不仅使陶渊明认识到自己“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自己真率的本性无法改变,认识到自己本“无适俗韵”,刚而拙的本性不可能偶合世情,讨好世俗,而且更使他明白想要不失去生命的真性,就得脱弃人世的繁华,就得超脱人际的利害,“先有绝俗之特操,后乃有天然之真境”(黄文焕《陶诗析义》卷三)。一个人越耽于追逐名利,他离自己的生命真性就会越远,可能就越会失去“此生”。所以在《归去来兮辞》中,陶渊明不仅检讨自己:“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而且向世人郑重宣布:“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于是他终于回到了自己“日梦想”的田园,重归自己“质性自然”的天性。
陶渊明弃官归田并不是要否定仕宦人生观,在他看来,人生在世“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人生苦短,没有必要“以心为形役”(《归去来兮辞》),“或击壤以自欢,或大济于苍生;靡潜跃之非分,常傲然以称情”(《感士不遇赋》),潜跃仕隐的人生选择都无不可,视哪种生命方式更适合自己的本性,便选择哪种存在方式以尽自己的本分,只要自己觉得“称情”或“称心”就是了。因此可以说陶渊明的弃官归田,是基于对自我本性的深刻体认而作出的生存选择,是“质性自然”的本性呼唤。正因为如此,所以他对自己回归田园,返回自然才表现出那样的喜悦之情。《归园田居》其一写道: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馀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馀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所谓“复得返自然”不仅是指诗人回归到自己“日梦想”的田园,同时也是指回归到自己生命的本真。在这里,诗人可以摆脱一切官场应酬,仕途倾轧,人事牵绊,可以“绝尘想”,“相见无杂言”,可以披星而出,带月而归,开荒田野,种豆南山,可以享受“山涧清且浅,遇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归园田居》其五)的纯朴生活,可以陶醉在“气和天惟澄,班坐依远流;弱湍驰文鲂,闲谷矫鸣鸥;迥泽散游目,缅然睇曾丘”(《游斜川》)的大自然怀抱,这才是“纵浪大化”的真超然,这才是深契自然的真洒脱。
四
陶渊明对于人生考虑很多,在自然与人的关系中,他希望能参透生命的哲理:“大钧无私力,万理自森著”、“万化相寻异,人生岂不劳”、“既来孰不去,人理固有终”。自然按照规律运行变化,人生亦复如此[4]。因而,他认为人也应该委身自然,随自然的变化运转,将个体与天地融为一体,与自然同节律——这实际上就是返回内在自然,是“纵浪大化”的深层涵义。基于这样的认识,所以他在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能够以非常平静的心情写下了《拟挽歌辞三首》和《自祭文》。可以这样说《归去来兮辞》和《归园田居》写的是生归田园,《拟挽歌辞》和《自祭文》写的是死归黄土,但无论是生归园田还是死归黄土,所表达的主旨都是“复得返自然”——返回外在自然和内在自然。《拟挽歌辞》和《自祭文》是诗人逝世前的绝笔,标志着他生命的终结与创作的终结,而承受生命终结的方式和态度则是他的生命价值观最为真实的体现。
如前所述,陶渊明对人生短促亦有《古诗十九首》作者们的敏感,而对人生短促的感受越深,其超越人生有限性的渴望也就越切,《古诗十九首》的作者正是如此。但是,陶渊明并不以追求个人不朽来超越人生的有限。他否定了“形尽神不灭”的说教,明白了“帝乡不可期”的事实,放弃了立善求名的选择,在《自祭文》中他再次郑重地宣称“匪贵前誉,孰重后歌”,他丝毫不以生前为世人所欣慕为荣,也不以死后为别人所思慕为意,轻视世人所珍视的“前誉”和“后歌”,更不害怕失去自己“不再值”的生命,真正达到了“聊乘化以归尽”的无私境界。
当然,陶渊明并非不热爱生活,翻阅他的诗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诗充满了对亲属、朋友的真情,但对于死亡他又是如此的豁达坦然。因为他认识到人的由少至老再由老至死是一个自然的变化过程,不必把它看得过于神秘,也不必对此惊恐不安,所以他的许多诗文就常把死亡称为“化”:“常恐大化尽,气力不及衰”(《还旧居》),“余今斯化”,(《自祭文》),“翳然乘化去,终天不复形”(《悲从弟仲德》)等等。所谓“化”,就是自然变化运转的结果。因而他认为自己既然秉承生命于大化——“茫茫大块,悠悠高旻,是生万物,余得为人”(《自祭文》),那么就应该“识运知命,畴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无恨”——重新回归所自出的大化,也就不值得凄凄怨怨哭哭啼啼,也就没有什么抛舍不开割断不了的了[5]。这就是说承受死亡的态度应当是“正宜委运去”,“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因而可以这样说,《拟挽歌辞》中的所谓“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自祭文》中的“余今斯化,可以无恨”,“从老得终,奚复所恋”,正是陶渊明在生命弥留之际将早年所肯定的“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生命价值观,变为一种迎接死神的方式。总之,“纵浪大化”既是陶渊明对自己生命价值的选择,也是陶渊明超越自我的一种方式和境界,在达到了这种境界后,个体便彻底解脱了生死之累。所以他谈到死后的语气是那样的平静自然:“家为逆旅舍,我如当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杂诗》之七);想到死时的神态是那样的从容自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拟挽歌辞》);面临死的心境是那样恬淡安祥:“廓兮已灭,慨然已遐,不封不树,日月遂过”(《自祭文》)。面对死亡,处在令人不胜其哀的生命最后一息,诗人的心灵仍然如此的平静,这的确不能不令人感叹!
[收稿日期]20-03-03-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