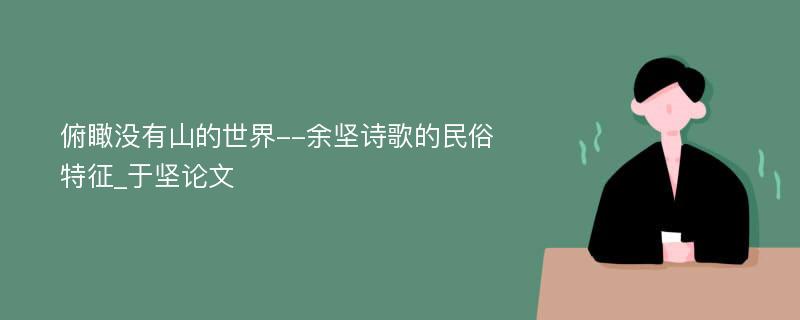
在没有山岗的地方俯视世界——于坚诗歌的民间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山岗论文,诗歌论文,特征论文,民间论文,地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降,中国诗歌在历史风云的激荡和自身裂变的阵痛中,从“精神贵族”的神坛轰然坠落,在摇曳生姿光亮炫目的“喧哗与骚动”后化解为无数碎片,旋即便归于宁静。当诗歌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退守到文化边缘的边缘,孤独地守护着寂寥的时候,于坚以其开阔恣肆、明净透彻的诗行,以远离玄学与神话的单纯,以关爱自然、向下探询的身姿走进了人们的视线;人们也随着他流动的诗行一起关注“在阴影中走过的同事”,一同“守望黎明”,一块儿“飞行”于日常生活与口语构筑的民间。所谓“民间”,我们认为应该是诗人建立在乎民百姓、芸芸众生这一实体上的立场、视角和情怀。它之于一首诗的整体面目来说,意味着日常生活的杂色性状,艺术上的本土气质与通俗性,内质上生生不息的喜乐精神,以及阅读上的亲和感。[1](p.253)2002年,于坚在瑞典奈赫国际诗歌节上的发言曾指出:“‘民间立场’,这个词不是‘大众’的意思,它在非官方的、口语和母语的、非时代性的、生活的日常性、普遍性的意义上使用。”在新生代诗人中,于坚不是倡导诗歌民间写作的第一人,他不过是以平民的身份关注经验、常识,注目“世界的常态”,跟自己“相依为命的东西,故乡、大地、生命、在场、人生”相亲和,[2](p.86)以坚持不懈的创作衍进和诗学阐释擦亮了“民间”一词,以其话语的民间性和叙说的民间感染力勾画出了具有独立品质的民间特征。
一、话语的民间性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被市场经济无情冲击,经济生活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自《诗经》以来负载着教育承、政治生活、文化消费等使命和重量,在“言志”、“载道”、“化民”的线形目标追求中扮演文化主角,重教化主情感、以精神思辨和感悟为根本特征的诗歌在远离经济的同时也被经济推至文化的边缘,面临被社会主流话语抛弃的现实困境。在此语境下,一部分诗人回归自我,构建被经济大潮冲刷得七零八落的“麦地”,一部分诗人则走向民间,沉潜到当下。从文学创作年表看,于坚的文学创作要晚于朦胧诗人,他的初期创作是受到了朦胧诗的影响并汲取了丰富养料的,只是敢于创新的于坚在朦胧诗争得一席之地时,以自己对诗歌敏锐的感受力和果敢的转折完成了对朦胧诗的转变。
在于坚看来,诗人和公民的身份于诗歌中是要截然分开的,诗歌不是高高在上的或左或右的意识形态的喧嚣,而是关于人生和世界、关于永恒的充满智慧和幽默感的日常谈话。“诗人和公民这两种身份不要混起来。作为一个公民,你可以表达你对政治事件的态度。但在诗里面,我觉得诗人不应该有什么立场。诗人唯一的立场就是诗的立场。””从这一诗学立场出发,他的创作试图挣脱政治规范和意义的束缚,卸去意识形态的重任,脱下孔乙己的“长衫”,自觉地以平民的立场和视角审视社会与人生,把诗歌的主题从国家、时代、大文化转向个人、地方、日常生活和传统。在题材形态与现实的关系上,他的诗从时代中撤退,躲避崇高,淡漠强烈的时代政治感。他消解崇高,用冷峻的目光透视崇高,以冷静的态度剖析崇高,穿越崇高的五彩斑斓抵达其背后被遮蔽的真实。在《参观纪念堂》中,诗人跨越纪念堂的雄伟和肃穆,跳过人们对领袖的景仰与崇拜,大胆挖掘潜藏于民众内心深处的一点点猎奇与诙谐:“从各地赶来”是要“看看领袖长相”;看着安睡中的领袖静静地躺在水晶棺木里,便“想搔搔他的脚底板/瞧他会不会一下子坐起来/咯咯地笑眼泪直淌。”以平民的平视的视角关注曾经叱咤风云的领袖,淡化了笼罩在一代伟人头上的光环,削减了毛泽东的神性,再现了毛泽东平凡人的喜怒哀乐,恢复了其活生生的人性。教堂在信徒们的眼里是神圣庄严的,但在异教徒的诗人看来,它的核心是“冰冷的”,“里面 像是一个储藏室 烛光希微没有电/散发着霉味 在黑暗中守旧,”就连拯救人的灵魂、净化人的心灵、大智大慧的耶酥,原来不过是一个“痛苦的男人”,“是一个被涂了金色油漆的木偶。”上帝的寓所并非金碧辉煌,它的存在无法遮蔽它光芒四射的反面——黑暗、陈旧、空虚、虚伪,所以上教堂就不是对神灵顶礼膜拜,“只为了‘到此一游’拍些照片/作为回到故乡 向迷信的乡巴佬 炫耀的资本。”至此,崇高和神圣被消解得一千二净。所以,读者在他的诗中看不到政治风云的变换,揭竿起义的英雄,为民众奔走呐喊的时代代言人,感受到的是一位与读者一起讲述关于诗歌、关于世界、关于人等实实在在事情的谈话对象。但是,这并不是说于坚的诗与政治现实的表现绝对无缘,只是他在表现政治现实时采取了一种中性的写作立场,客观写实,远离形而上话语的现实理解,以不带价值判断的话语描写个人视界中的原生现实。因为他深信在诗里面“诗人不应该有什么立场”。[3]他将现实的重大变化融于人物、事件的客观变化之中。创作于1985年的《作品49号》,题材的选取与现实紧密相连,或者还可以说叙写的主题是宏大的: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给人们带来了福音,使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然而,这一主题是通过一个“开病假逛大街”、“把裤管改细学华侨”、“向很多人借过饭菜票”的青年的神话般的变化凸现的,整首诗洋溢着轻松、调侃、诙谐的氛围,观点在读者阅读的流程中自然呈现,一定程度上削减了主题的宏大性。在《作品89号》中,作者也选取了现实题材,然而,作者将自己远远地隐藏在诗歌的背后,仅仅客观地叙说眼前目睹的现实:“……下午的玉米/是另一种金黄 辽阔只剩下一些局部 倒下的庄稼/像一捆捆缴获的枪支 它们再也不会丰富农业下个月/它们将在一份建筑合同中死亡。”他以民间的清醒和单纯让存在说话:城市化进程使农村失去了金黄的秋天,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乡村与城市在此消彼长中强烈地对峙着。
话语的民间性,还表现在主动从空间和在场上重返民间。一方面,于坚坚守对自然的体味和守护,并以此追思诘问生命与存在的本源。他写下了大量的有关自然的诗,如《作品57号》、《高山》、《河流》、《山谷》、《阳光下的棕榈树》、《我看见草原的辽阔》、《滇池》、《远方的风》等。在他的视野里,自然的一切都是美的,但他的诗传递给读者的不仅是自然美的身姿与身影,也不仅是由其构设的风俗风情画卷图景,而是一种潜在的给人以内在心灵触动与启示的人格力量的美。所以,当“我”面对群峰时,群峰“使我永远对远处怀着/初恋的激情/使我永远喜欢默默地攀登”(《作品57号》);当我置身茫茫草原时,“我”不敢喊叫“辽阔”,而“只能闭嘴 像个哑巴”,静静地感受“辽阔的草原”“为我拨开”“一只深远的牧歌”(《我看见草原的辽阔》);当“我”行走于不熟悉的山谷时,也会虔诚地顺着淙淙流水的“声音前行”。“诗人写作与人生世界是一种亲和而不是对抗的关系,它不要改造、解放这个世界,而是抚摸这个世界。在诗人写作中,世界不是各类是非的对立统一,而是各种经验和事物的阴阳互补。天马行空,然而虚怀若谷。”[4]在于坚的笔下,自然不仅仅是外部世界的对象指称,它更指向主客交流中洞开的一种境界:“要看得远 就得向高处攀登/但在山峰你看见的仍旧是山峰/无数更高的山峰/你沉默了只好又往前去”(《高山》),“泥巴把河流染红/真像是大山流出来的血液/只有在宁静中/人才看见高原鼓起的血管/住在河两岸的人/也许永远都不会见面/但你走到我故乡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听见人们谈论这些河/就像谈到他们的上帝”(《河流》)。在这里,高山、河流与人彼此相融、相亲和,自然的人格和人格的自然互为投射,于坚正是以这种对云贵高原文化的独特理解来阐释对个体生命的领悟的,他试图从叙说空间的社会主题向自然的转向中,来完成对经济社会里人们远离生命本源、遗失自我、遮蔽自然本性的批判。另一方面,于坚一直努力撩开集体意识,还原生活的日常面目,重建日常生活的尊严,重新确立日常生活在文学中的地位,恢复日常生活在“生活”中的意义,从场上重返民间。回到生存的现场,回到常识,回到事物本身,一直是他写作的一种内在愿望,他认为“真正的生活乃是无意义的生活。也就是所谓常识的生活,这种生活其实正由于它的无意义才成为生活的常态和永恒。”[5]他的这一诗学追求让他把视角转向日常生活,关注普通人的生存境遇,坦然地关注都市平民世俗的、庸常的、琐屑的日常生活和内心世界。他截取日常生活片段,描写和展示生活的细节,展示生活的原生态,呈现艺术审美图式的生活化与世俗化。“他们又吵架了瘦男人和胖女人锻工和翻砂工吵架了/冰块辣椒石头镪水刀子大粪从套间里喷出/老远也听得见/……/后来他们手挽手进城后来买回一大包东西”,像这些活生生的平民形象时常穿行于于坚的诗歌之中,我们可以不经意地在他的诗中阅读到像皮球一样脏的二十岁的青春,拥挤简陋、恩恩怨怨吵吵嚷嚷的“尚义街六号”,灌注普通人生存窘迫和悲哀的罗家生。于坚正是以这种下倾的姿态,对民间的零距离接触,化解了诗歌的形而上,重建了普通人在诗歌中的地位,张扬了琐屑、“无意义”生活在诗歌中存在的权力,表现出了朴实深厚的民间情怀。于坚认为:“诗人与世界的关系不是对象,不是主体和客体,而是在世界之中。它歌吟的是世界赖以存在的基本事物,与生俱来的事物,人和世界的不言自明的关系。这不是关于‘活着,还是死去’形而上追问,而是存在者的天真之歌。”[6]于是,他将话语深入到世界之具体的、细小的、存在的事物之中,真诚书写个体的深切感悟,则更显示出民间关怀的魅力。“那是什么坠落 在十一点二十分和二十一分这段时间/我清楚地听到它很容易被忽略的坠落/因为没有什么事物受到伤害没有什么事件和这声音有关/它的坠落并没有像一块大玻璃那样四散开去/也没有像一块陨石震动四周/那声音 相当清晰 足以被耳朵听到。”(《坠落的声音》)这是一双“听不到表、蚊子、雨滴和落叶的声音的耳朵”[7]对声音的关注,与其说他是在用耳朵倾听世界,不如说是在用心感悟世界,从点点滴滴发现美、感受美。于坚对存在的物的关怀,将人们的视线由天空、神明、麦地牵引到当下,注目于存在的意义,更让人发掘生命的底蕴和生活的意义。
二、叙说的民间性
当于坚站在日常生活的现场深情地传达他的日常关怀和民间情谊时,他还试图引领我们顺着他诗歌的流动探询诗歌的源头——从语言开始的地方开始。与话语的民间性相对应,于坚以他对诗歌的透彻理解和别具一格的感悟,在叙说方式上找到了自己独特的方位和出发点,以此构筑其诗歌的民间性。
解构象征,拒绝隐喻,消除蒙盖在词语上的文化积尘是于坚诗歌叙说民间性的第一向度。追求意象化、象征化,将生活扭曲变形,藉以表现诗人“心滤”的现实,是朦胧诗创作的一大特征。朦胧诗往往以普遍的暗示替代直接的显现,以意象的凝聚和组合取得象征的效果,运用隐喻使作品变得扑朔迷离,显示出鲜明的抽象性和超脱性。就是某些先锋诗歌,也在消融朦胧诗语言板结的同时,又被一些“大词”套住了手脚,丧失了自由和生活化的特征。于坚曾尖锐地指出:“细读某些先锋诗歌,不过是词汇的变化史。基本的构词法——‘升华’,从五十年代到今天并没有多少变化,不过是把红旗换成了麦地,把未来换成了远方而已。”[5]脱离常识的升华式写作必然依靠大词。与这种大词癖相反,于坚一度提出“拒绝隐喻”、“回到隐喻之前”的主张。他的“拒绝隐喻”就是拒绝朦胧诗那种借助现代书面化语言为世界命名的方式,“回到隐喻之前”就是回到诗作为日常生命形式的本真状态,让诗“脱离文化之舌”,通向自由之路。他试图通过对存在的去蔽显真,达到一种恢复,即“把事物恢复到属于它自己的空间里,恢复到它本然的状态中,没有文化和个人意识的干涉,它的存在完全是第一性和亲历性的。”[8](p.62)他用大胆的语言冒险实践自己的诗学主张,有意地超越语义的确定性思维,拆除表层物象背后的深度模式,消解人为赋予或积淀而成的文化内涵与象征,凭借想象的飞跃和激情的喷涌,用最平常的词把想说的话说清楚。这样,在于坚的眼里,乌鸦不是“黑夜修女熬制的硫酸”,不是“代表黑暗势力的活靶”(《对一只乌鸦的命名》),海鸥也与在“文学史上的那些已被深度抒情的益鸟无关”(《赞美海鸥》)。他以“现象学客观还原”的方式,层层剥离主观臆造加在存在之物上的种种所指意义或象征的隐喻的内涵,拂去文化积尘对词语的遮蔽,穿越传统文化对语言的重重包裹,以语言的自足抵达语言本身,使存在之物获得重新命名。于是我们看到的春雨就是“漫不经心地往下跳/纤细的长腿一触地就跌断了/它们哭着在水泥填平的地面爬行/那渗透事物的能力已经丧失”(《停车场上 春雨》),它们只是以雨的姿态跳到地上,被坚硬的地面碰得粉碎,这里,春雨不过是春天里的一场雨而已,它走向它的过程,其“润物细无声”的象征意义已被彻底解构。同样,《在云南省西部荒原上所见的两棵树》中,人们看到的是两棵充满生命力、洋溢自然美的树,它们生长于自己的空间,享受着自然的天光雨露,存在仅为存在,最多客观为鸟儿提供栖息之所,除此,一切的“伟岸”、“坚守”、“搏击”、“忠贞”与它们无关。于坚就是这样以普通的、习见的一些“旧词”构建他的诗歌,并在这种使用中使许多词语恢复了活力,恢复了它们与事物、生活的亲密关系,从而在别人看来最没有诗性的地方,重铸了诗性。
为消解词语的文化积尘,表达日常生活的平淡琐屑,于坚选择口语化叙述的叙写策略,有意规避正统诗歌语言的窠臼,以纯净鲜活、朴素通脱的世俗化、散文化、口语化的民间语言言说,以此呼应话语的民间性。首先,他淡化意象的经营,以平白、朴素、活泛的日常口语入诗。中国诗歌向来是讲究意象的营造的,朦胧诗时代,诗人们更是通过对意象的叠加与断裂的追求,构建朦胧、神秘的氛围。于坚坚持语言还原,试图让词语回到真实的生活中,或者说让真实的生活回到语言中,使语言成为对真实生活的表达或言说。于坚和舒婷都写过以思念为主旨的诗歌,但二者的表达迥然不同。在舒婷的《思念》中,作者巧妙地选用四个独立的意象,以“藏”与“剪辑”并用的方法设置四幅图画,从各个不同角度组合思念的内涵:斑斓、断续;真诚、挚着;孤寂、凄美;深长、悠远。并将这些零碎的意象叠加在一起,省略关联的过渡,使意象与意象建立同态对应,构成一幅有时空距离、有层次和深度的艺术图景,以此增加诗歌语言的审美信息量,拓展读者的审美想象空间。在于坚的《寄小杏》中,诗人以毫不掩饰的、活脱脱的生活口语叙说思念之情,每一句话都顺手拈来,自然天成。它让读者的思绪缠绕作者的笔尖,将读者的阅读最大限度地限制在诗歌语言本身的规定之中,强调诗歌的现场性和一次性,真正做到了“诗到语言为止”,有着素面朝天的清醇。在于坚看来,仅仅通过意象的淡化使语言还原还不够,还需要从词语、句子结构等最基本的方面返回口语。在具体运用上,他的诗中大量使用口语词语,如《远方的朋友》中就有“大不了”、“搓搓大腿”、“抓抓耳朵”、“不容易”、“一脚踢开”等,使诗具有亲切感;从句子结构看,他的诗句大多遵循现代汉语句子的结构特点,如“我知道有一天你会回来/抱着三部中篇一瓶白酒/坐在那把四川藤椅上/演讲两个小时”(《作品39号》),少有因省略、位移而造成的阅读与理解障碍;从表达上看,他常采用词语或句式的重复制造一种轻松、随意的口语风格,与市民白话相吻合,如“茶水是老吴的 电表是老吴的/地板是老吴的/邻居是老吴的/媳妇是老吴的胃舒平是老吴的/口痰烟头空气朋友 是老吴的”(《尚义街六号》),《作品52号》更是以15个“很多年”开头的相同句式连缀全篇,以单调的重复记录平凡人的平淡、琐屑和无奈。其次,放逐形式上的韵律,追求与生命律动谐和的语感。于坚曾说:“我是很讲究韵律的。但我押的不是像古代那种非常明显的尾韵,我的那种韵是押在诗行内部之间,在单词和句子之间进行一种韵律上的变化,营造一个语言的在场,氛围,布鲁斯那样随意,但是和谐……我注重的是让读者入场,在场,而不是记住。……我把韵变成一种内部的韵,音节传达的气氛,而不是一种外在的琅琅上口的韵。”[3]于坚所说的韵律,实际上就是一种语感。所谓语感,于坚是这样阐述的:“在诗歌中,生命被表现为语感,语感是生命有意味的形式,读者被感动的正是语感,而不是别的什么。诗人的人生观、社会意识等多种功利因素,都会在诗人的语言中显露出来。直觉会把心灵中这些活的积淀物化合成有意味的形式。”[9]于坚的诗之所以能产生平淡之中意味悠远的况味,是因为在词语的选择、节奏的构成以及韵律的流转上,都贮注着诗人内心生命节奏的有意味形式,是诗人对日常生命形式、形态的体验呈现。例如他的《避雨之树》:“寄身在一棵树下躲避一场暴雨/它用一条手臂为我挡住水……它是那样使我们永远感激信赖而无以报答的事物/我们甚至无法像报答母亲那样报答它 我们将比它先老/我们听到它在风中落叶的声音就热泪盈眶。”在这里,诗歌语言与个体生命的直觉体验相契合,呈现出晶莹剔透之美,语言与诗人的生命状态、生命经验以及形而上的感悟同构,这些口语化的语言在展示自然生命本体的同时也深刻地揭示出现代人的内心真实。
平面化的冷抒情是于坚诗歌叙说民间性的第二向度。自《诗经》创立“赋、比、兴”的诗歌语言表达以来,以情驭物、客观衬托主观的“比兴”模式一直是中国诗歌的主流表达方式,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当诗歌从那些重大的、有意义的整体事件中缓过神来,开始关注真正的、“无意义”的、常识的生活时,以抒情为第一要义的模式才受到普遍的怀疑。在于坚的诗歌中,他常常以“局外人”、“边缘人”的冷眼观察一切,直接处理审美对象,再现事物本身的关系,不做文辞夸张,不做感情评价,将主体和情绪撤离诗歌,把热烈、奔涌的情感化为平淡、冷静的平面话语进行零度抒情,以期达到真实地再现生活。在《事件:铺路》中,诗人写铺路,重点在客观描写铺路的过程——测量、挖掘、搬掉、填平、铺设等一些简单的动作和带给人们的真实感觉——“平坦安静 卫生 不再担心脚的落处”,作者全然不支出感情,不精心营造意象,只客观地录制过程的画面,当然也就消解了意义的深度所指。诗人正是以这种平面化的冷抒情方式,达到恢复事物原生性、还原真实的目的,以此反驳浪漫主义夸饰浓烈的抒情模式。然而,这种外表的客观冷静,并不表明作者只是照相式地反映现实,他是将炽热的激情以冷峻的方式呈现,而冷峻的外表下却滚动着岩浆般的情感。在《事件:棕榈之死》中,诗人这样写棕榈:“一望而知 这是一棵活着的棕榈/但要仰视。”当在众目睽睽之下,工人砍倒这棵棕榈之后,诗人更加精细地的描写被伐后的棕榈:“他的根部翘向天空叶子四散已看不出它和木料的区别/随后又锯成三段以便进一步劈成烧柴。”其实,在这一仰视一毁灭的对比中,诗人对自然的呵护,对人们发展经济的同时破坏家园的惋惜之情已经跃然纸上,只是诗人仍然克制自己的情感,不让情感喷涌而出,而让它潜流在冷静的叙述中:“图纸中列举了钢材 油漆 石料 铝合金/房间的大小 窗子的结构楼层的高度 下水道的位置/弃置废土的地点处理旧木料的办法/没有提及棕榈。”诗人巧妙地将情感掩藏到棕榈之死的具体的、现场的、可感的叙述中,不留蛛丝马迹,然而,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冷静外表下骨子里炽热心灵的燃烧。
与西川、王家新们试图“从灵魂的视野去阐述和想象当代的生存处境,以严肃的思想和语言探索回应浮浅低俗的时代潮流”不同,[10][p.83]于坚往往以调侃、游戏的方法把诗写得随意轻松,以诙谐替代严肃、幽默取代神圣,于不经意的调侃和诙谐中表现出幽默、反讽的效果。
“家庭出生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职业 天生我才必有用
工资 小菜一碟 何足挂齿/文化程度 少壮不努力 老大徒伤悲 本人成
分/肌肉30公斤 血5000cc 脂肪20公斤 骨头10公斤/毛200克眼球一对肝2叶手2只脚2只鼻子1个/婚否 说结婚也可以 说没结婚也可以
信不信由你/政治面貌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0档案》)
在人的历史被公共语言书写的年代,人丧失了作为个体存在的依据,属于具体生命形态的东西被历史一一过滤,个体特征消失得一千二净,人的存在框定、同化为一种公共的存在。诗人在调侃、玩世不恭的语调中透着对特定历史时期造成的生命荒原的辛辣讽刺,其讽刺的力度并不比朦胧诗人们的呐喊逊色。于坚还擅长戏拟其他语体或糅合各种语体,使诗歌具有戏剧性或喜剧性的特点,从而产生幽默与反讽的效果。戏拟书信体的有《给姚霏》、《小杏》,戏拟大事记的有《贝多芬纪年》,戏拟档案体的有《0档案》,戏拟荒诞派戏剧的有《事件:三乘客》。在一些诗歌中,于坚还在老老实实的大白话中插入古语词或嵌入古代诗句,将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巧妙融合,制造轻松随意的诗歌氛围。例如在《结婚》一诗中:“国家的套间 只分配给成双成对者 人生的另一本护照通向结婚的小人国/东市置家具西市照合影北市买棉被 南市配音响。”第一诗行以平静诙谐的语调对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福利分房制度的弊端进行了批判;第二诗行戏仿《木兰诗》“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的写法,既写出了结婚准备之繁忙,又使这种繁忙显得极具节奏,轻松活泛,同时,也是对结婚准备之繁琐、挑剔的有力讽刺。在《礼拜日的昆明翠湖公园》中,诗人更是大胆地、大量地插入和借用各种语言,以语言的驳杂真实诙谐地再现公园的形形色色。借用古代诗文:“大隐隐于市”、“杨柳岸小风残月”等;直接引用口语中的对话语言:“‘小姐倒几盅茶来’”等;插入公共场所警示标语牌内容:“‘不准随地吐痰”不准乱扔垃圾“小便人槽”讲文明 讲卫生’”。诗人正是以这种杂语的混合,一方面叙说生活的纷繁,一方面又卸下了生活沉重的因子,以生动形象的语言揭示出生活底层潜藏的幽默,使诗歌呈现生生不息的喜乐精神。然而,我们又不能不看到,于坚虽然借口语的运用实现了诗歌向“原在”的后退,诗歌成为与生活原在共存的“在现场”,凸显了诗歌的现代色彩和现代气息,但他对象征、隐喻等知性语言的放逐,对日常生活琐屑的过多铺陈,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诗意的流失,使诗歌远离了自己的精神家园,成为了一次性消费品,成为了读者阅读时无法排遣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