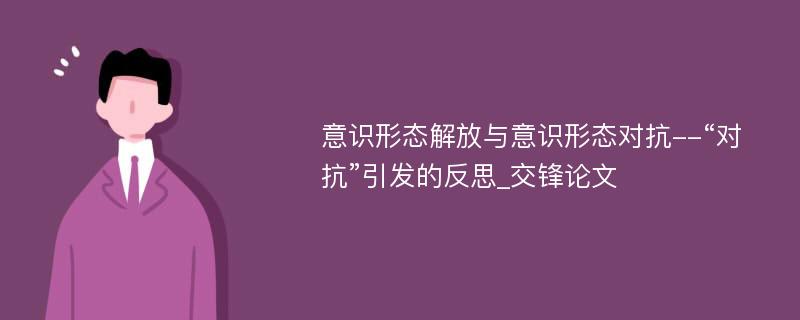
思想解放与思想交锋——由《交锋》引发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解放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交锋》出版时间不长,为什么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从著作本身考察,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其一是具有较强的实录性。这本书以大量的篇幅,比较系统、比较完整地披露了发生在“三次思想解放”过程中的各种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事实,其中又不乏鲜为人知的东西。其二是寓理于实。作者从大量史实的罗列、比较中,深刻地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哲理:改革进程中的每一步思想解放,都不是平静地、轻易地进行的,而是在激烈的思想交锋的基础上实现的,思想解放与思想交锋是推进改革不可缺少的思想动力。对于前一个方面,许多书评给予了充分肯定,笔者不拟赘述;对于后一方面,见到的书评中似乎涉论不多,笔者想借题阐发自己的一点感想。
解放思想的实质是两种对立思想的交锋
解放思想作为党的路线、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我国新的历史时期首要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作为社会生活中具有时代个性的重大口号,是在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和确定下来的。解放思想从开始提出即有其明确的政治取向:它的目的在于打破党和国家的那种“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的政治局面,改变广大党员、广大干部那种“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进而“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为实行改革创造广阔的思维空间。解放思想的这种政治取向,决定了它的实质必然是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战胜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用科学的思想战胜迷信的思想,用新的思想战胜旧的思想。简言之,所谓解放思想就是两种对立思想的交锋,就是用正确的思想战胜并代替错误的思想。
如《交锋》所说明的那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三次思想解放”,实质上是三次激烈的思想交锋。“第一次思想解放”是1978年战胜“两个凡是”;“第二次思想解放”是1992年破除姓“社”姓“资”;“第三次思想解放”是1997年冲破姓“公”姓“私”;而这三次思想解放又都贯穿一条反“左”的主线。由此我们可以说,三次思想交锋从总体上说就是马克思主义同“左”的错误思想的交锋;三次思想解放从总体上说就是从“左”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认清解放思想的实质是两种对立思想的交锋,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和正确把握解放思想这个方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解放思想作为党的一项基本方针,具有鲜明的反倾向性。就是说,它坚持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在这种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中,它同样坚持从实际出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而从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而言,始终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解放思想的方针,主要是与“左”的思想相对立的,主要是为反对“左”的思想影响服务的。作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基本方针的组成部分,解放思想非但与过去大跃进年代曾经用过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有全然不同的针对性,而且较之一般意义上的敢想、敢说有更加深刻的政治含义。当前,党之所以坚持这个基本方针和基本口号不变,就是因为“左”的影响还远远没有肃清,反对“左”的历史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
解放思想的过程,必然充满正确与错误、探索与责难、批评与反批评的矛盾与斗争。“不争论”只能是不搞过去政治运动意义上的那种所谓的“争论”,或者只能是对不同思想的交锋确立一个不干扰建设和改革大局的基本原则,而不可能在事实上消除争论,如《交锋》作者所说,“中国的事情”“不想争论也不行”。
解放思想作为党的现行方针的一个重要方面,具有不可替代性。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正式提出解放思想问题,中经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直至党的十五大,解放思想作为党的基本方针、基本口号的地位始终没有改变,而且从来也没有被其他相近的提法所代替。如“实事求是”是与解放思想有着内在联系的提法。在党的重要文件中,在邓小平、江泽民的重要讲话中,从来是把这两个提法连在一起、并列地提出的。邓小平在有的讲话中,从两者的内在联系上讲过“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而在同一次讲话中,邓小平同志紧接着就讲到,“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可见,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坚持实事求是;而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邓小平同志常常把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联系起来,但从来没有用实事求是代替解放思想。这也表明,解放思想包含着明确的反对“左”的错误思想的政治取向,意味着要在较长时间同“左”的思想进行艰难曲折的斗争。解放思想这个基本方针和基本口号的不可替代,表明了我们党同“左”的思想的斗争将长期地进行下去,不能削弱,更不能取消。
核心问题是两种社会主义观的对立和斗争
思想解放的实质是两种对立思想的交锋,而这种交锋的核心又是两种社会主义观的矛盾和对立。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对于我们究竟要建设怎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长期存在两种矛盾和对立的观点,或者说两种对立的社会主义观:其一是模式化的社会主义观,其基本特点就是把社会主义标本化。这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固定的模式,这种模式是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和各国(包括本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构筑而成的。既然是模式,就具有了不可改动性,一切试图突破模式、超越模式的理论和实践,自然被认为是离经叛道,是背离社会主义。其二是改革的发展的社会主义观,其基本特点是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不断改革和不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的体系。这种体系既缘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也缘于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但是更缘于实际生活的发展。这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不论就其理论形态还是就其社会形态来说,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模式,需要依据实际生活的发展变化而进行改革和创造。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中,一切重大的思想解放和思想交锋,都是紧紧围绕着两种社会主义观的对立和斗争这个核心问题展开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实质上是与两种社会主义观紧相关联的两种方法论之争,即在究竟应以什么作为标准来衡量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是与非问题上的“凡是”观点和“实践”观点的争论。在其后不久进行的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的讨论、党的十三大报告中阐明的生产力标准和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中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实际上是“实践”观点的引伸和进一步发展。这些观点从方法论的角度,充分肯定了改革的发展的社会主义观的科学性和现实性,尖锐地批判了模式化的社会主义观的保守性和空幻性。邓小平同志关于“三个有利于”标准的论述,吸收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以来关于评价标准问题讨论的一切积极成果,确立了科学地观察、判断与评价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是非功过的方法论体系,使我们党和国家走出了“唯上唯书”的思维窘境。这本身就是巨大的思想解放,同时它又为促进全党思想的进一步解放确立了基础和前提。
关于姓“社”姓“资”与姓“公”姓“私”的两次交锋,实质上是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现在社会主义本体问题上不同认识的争论,或者说是在社会主义应该是怎样的、不应该是怎样的问题上不同认识的争论。中心是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究竟应该继续坚持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和经验实行市场经济;一个是中国现行的所有制结构是否应当进行必要的改革和调整。应当说,这两个问题是在社会主义本体论中最敏感的问题,从理论的角度看,经典作家在这方面的论述不仅篇幅多而且取得了几乎是不容置疑的权威地位;从实践的角度看,我国已经按照经典作家的论述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而且具有了几十年的历史。在这样的问题上有所突破,真是何其难也。但是党的十四大和十五大,跨出了艰难的一步,宣布中国将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代替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将确认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创造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局面。这是改革的发展的社会主义观的巨大胜利,是思想的巨大解放。
思想解放与思想交锋需要民主的保证
20年前,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一次重要讲话中,在强调要解放思想的同时,还强调必须发扬民主,指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思想解放与思想交锋有了远比20年前更为广阔、更为宽松的政治空间。但是回顾《交锋》所展示的“三次思想解放”的历史,觉得重提邓小平的上面论述不无必要。
如前所述,解放思想主要指从“左”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思想交锋也主要指改革的思想同“左”的思想的交锋。而“左”的思想不仅年深日久,而且常常寄身于我们现行的制度、体制、法令、政策、条例之中,部分地乃至相当部分地有了合法化、权力化的载体。在这种情形下,本来是僵化的、“左”的东西,却保持着一定神圣性和不可移易性。如《交锋》作者所说,在“三次思想解放”中被推倒的“个人崇拜”、“计划经济崇拜”、“所有制崇拜”,都是“左”的思想营造物,至少是“左”的思想浇灌物。“左”的东西溶于并得到现行领导制度、现行经济制度、现行所有制结构的权威的保护,这时,反对“左”的行为,就容易被看作是违背原则、违反政策的行为,解放思想就有了自由化之嫌。事实上,在每一次已经载入史册的重大的思想解放中,这种现象都是不乏其例的。可见,进一步创造民主的条件,以保障思想解放与思想交锋能够经常地正常地进行,仍然具有现实的必要性。
对于目前党内外民主生活的状况,应当有一个恰当的实事求是的估计。一方面必须看到,不论在党内还是社会范围,敢想敢说的局面已经出现,表明民主生活在日益发展;另一方面决不应忽略的是,在关系到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问题(如实行市场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等)上的多种思考、多种声音、多种议论的局面还远没有形成。《交锋》中所说的“三次思想解放”跨越很长的时日,呈现艰难曲折的状态,这表明中国当前既需要以思想的解放促进民主的发展,同时也需要以民主的扩大保证思想的解放。
读过《交锋》之后,感到有两点小小的缺憾。一是作者在叙述“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时候,漏掉了两件不该漏掉的事实,那就是理论务虚会和关于生产力标准问题的讨论。这两件事对于实现“第一次思想解放”、促进以后两次的思想解放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应该讲到。至于这两件历史事实本身的问题以及人们对它们的不同看法,不足以成为把它们排除在“实录”之外的理由。二是《交锋》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解放划分为几次,似嫌不妥。因为这样的划分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在诸多问题上思想解放之间的联系(如“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不恰当地给一定阶段或一定问题上的思想解放打上了句号(事实上对相当一些人来说,20年前集中解决的“唯上唯书”的问题,时至今日也没有完全解决)。但是,不用“次”来划分不同时期、不同问题上的思想解放,又该用什么来划分呢?笔者现在也说不清楚,愿意就此与有识者一道探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