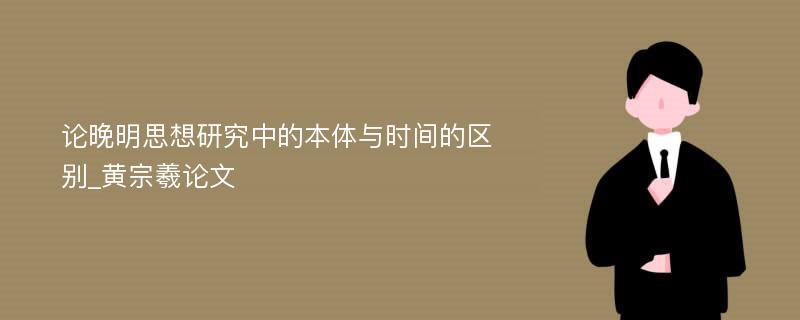
晚明心学中的本体与工夫之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体论文,工夫论文,明心论文,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先天良知(本体)与致知过程(工夫)之辨,是王阳明心学的基本论题之一。在王门后学中,王畿、泰州学派对先天本体作了多方面的分疏,但由此又将本体等同于现成之知,聂豹、罗洪先等反对以本体为见在,但同时却试图返归寂然未发之体;二者从不同方面展开了良知的先天性之维。与之相异,钱德洪、欧阳德等及明末的东林学者则以后天工夫为关注的重心,从各个侧面对致知过程作了考察。以此为前提,黄宗羲进一步从理论上对本体与工夫之辨作了深刻的转换。
一 现成良知说:工夫的消解
在天泉证道中,王阳明曾提出了利根之人的预设,并以直指本体为其特点。尽管王阳明同时强调这只是一种逻辑上的可能,但这种逻辑的设定与良知的先天规定相结合,却潜下了从先天本体到现成良知的衍化路向。在王畿那里,便不难看到这种理论的衍化。
作为王门的后学,王畿亦以良知立论。关于良知,他曾作过这样的界说:“良知原是无中生有。……虚寂原是良知之体,明觉原是良知之用。体用一源,原无先后之分。”(《滁阳会语》,《王龙溪先生全集》卷二,以下引自该书,简称《龙溪集》)此所谓虚寂是就先天性而言,明觉则指自觉的意识,王畿认为二者无先后之分,意在强调先天即明觉。先天与明觉的这种合一,决定了自我能够在现实的道德实践中触机而发:
不学不虑,乃天所为,自然之良知也。惟其自然之良,不待学虑,故爱亲敬兄,触机而发,神感神应;惟其触机而发,神感神应,然后为不学不虑,自然之良知也。(《致知义辨》,《龙溪集》卷六)
触机而发,神感神应,是基于对良知的了悟而作出的当下反应,它本身亦可视为明觉的表现。在此,先天性(天之所为)构成了主体明觉的根源,而主体的明觉反过来证实了良知的天赋性。换言之,主体的明觉完全消融于良知的先天性之中。
王畿的以上看法与王阳明显然有所不同。王阳明致良知说的前提之一,是本然之知(先天良知)与明觉之知(良知的自觉意识)的区分:先天良知最初并未为主体所自觉把握,惟有通过后天的致知过程,才能转化为自觉良知。与之相异,在王畿那里,先天与明觉的合一,开始取代了本然与自觉的区分。作为明觉与本然合一的良知,也就是所谓现成良知:“至谓世间无有现成良知,良知非万死工夫断不能生,以此校勘世间虚见附和之辈,未必非对症之药,若必以现在良知与尧舜不同,必待工夫修整而后可得,则未免于矫枉之过。”(《松源晤语》,《龙溪集》卷二)
王阳明肯定心理、本体与工夫的统一,已表现出扬弃本体超验性的趋向。王畿强调先天与明觉的合一,使良知进一步由超验之域走向现实之境。就此而言,王畿以现成说良知,又并没有完全离开王阳明的思路。良知一旦取得现成形态,则其作用方式也相应地向现实靠拢。王畿指出:
若信得良知及时,不论在此在彼,在好在病,在顺在逆,只从一念灵明,自作主宰。自去自来,不从境上生心,时时彻头彻尾,便是包裹;从一念生生不息,直达流行,常见天则,便是真为性命。(《答周居安》,《龙溪集》卷十二)彼此、顺逆等等,表现为一种外在的“境”,而灵明自作主宰,则是指良知的审察裁决。在主体与外在之“境”的关系中,主体并不是消极地接受环境作用,而是处于主宰的地位;这种主宰性的前提则是良知的见在明觉:“惟此良知精明,时时做得主宰,才动便觉,才觉便化。”(《答季彭山龙境书》,同上,卷九)正是以一念灵明为内在根据,才使主体能够对外在之“境”的行为自觉地加以省察,并据此作出判断与抉择,以避免消极地随“境”而转。在此,良知的现成性,构成了自我作为主体而在世的现实前提。
良知作为内在的主体意识,也就是本体。与肯定良知的见在作用相应,在本体与工夫的关系上,王畿反对离开本体谈工夫:“外本体而论工夫,谓之二法,二则支矣。”(同上)在本体之外论工夫,既意味着忽视德性培养的内在根据,又将导致偏离本体对成性过程的规范;由此展开工夫,往往烦琐而支漫。惟有以良知为主,才能有其定向:“此一点灵明做得主,方是归根真消息。…予夺纵横,种种无碍。才为达才,不为才使;识为真识,不为识转。”(《留都合记》,同上)所谓归根,即是将工夫置于良知的范导之下,并使主体意识的各个方面凝聚,转化为统一的内在结构,从而避免为偶然的意念所左右(不为才使,不为识转)。总起来,本体(良知)与工夫的关系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本体作为内在的明觉而直接赋予工夫以自觉的品格;其二,本体作为见在的意识结构而保证了主体意识的统一性(在不同境遇中始终保持善的向度),后者同时又使主体行为的一致性成为可能。相对于王阳明将良知的作用与过程联系起来而言,王畿更注重本体与工夫的既成关系。
自我在世,总是处于和社会(环境)的交互作用之中,就道德领域而言,这种作用乃是以主体自觉的道德意识结构为其中介:社会(环境)的诸种因素,只有通过主体在一定阶段所形成的意识结构,才能制约主体的价值评价、道德情感及具体行为,而主体对外部规范的取舍、认同,也总是以现阶段达到的道德意识为根据;正是现实的(既成的)意识结构,从一个方面担保了主体在道德判断与行为上保持恒同。如果忽视了主体意识结构的中介作用,则往往将在理论上导致双重结果:或者如极端的行为主义那样,走向环境宿命论;或者使人格的内在统一难以落实。从这方面看,王畿强调以见在的一念灵明为主宰,反对随境而转及离本体而论工夫,显然不无所见。不妨说,在现成良知的形式下,王畿试图进一步扬弃先天性所蕴含的超验趋向,将良知引向已发的经验之域,并由此突出既成道德意识结构在主体在世过程中的作用。
在王畿那里,与现成良知说相联系的是四无说。如前所述,王畿曾将王阳明的四句教引伸为四无说,《天泉证道记》载录了他关于四无的如下论述:
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意即是无善无恶之意,知即是无善无恶之知,物即是无善无恶之物。盖无心之心则藏密,无意之意则应圆,无知之知则体寂,无物之物则用神。天命之性,粹然至善,神感深应,其机自不容已。(《龙溪集》卷一)心、意、知、物皆无善无恶,意味着作为本体的良知与已发之意念均处于同一序列,无实质的差异。从逻辑上看,由此可以引出二重结论:本体与意念既无差别,则意念亦可视为本体;本体与意念皆无善无恶,则为善去恶的工夫便失去了必要性。合本体与意念为一,固然避免了本体与已发的经验之域的分离,但同时亦弱化了本体的超越性(道德意识的普遍性与崇高性),导致认当下的意念为本体,亦即本体在实质上的消解。另一方面,本体与已发之意念的界限既被模糊,对本体的自觉意识则成为多余,从而抽去了为善去恶的工夫。正是有见于此,东林学者顾宪成后来批评道:“是故无善恶之说伸,则为善去恶说必屈;为善去恶说屈,则其以亲义别信为土苴,以学问思辨为桎梏,一切藐视不事者必伸。”(《东林会约》,《顾瑞文公遗书》第五册)
作为“四无说”的逻辑展开,现成良知说同样表现出如上趋向。在强调良在的当下性、见在性、既成性的同时,王畿似乎未能完全将良知与日常意识区分开来,而道德本体的普遍性、超越性这一面亦因此而难以得到适当的定位。当良知被赋予现成形式,并被等同于其见在的作用时,本体亦相应地多少被消融于日常意识。这种思路在某种意义上已接近于禅宗的“以作用为性”,而王畿确实也常常受到“近禅”的批评。同时,本体的现成性,也使后天的工夫无从落实。王阳明的另一后学罗洪先(念庵)曾尖锐地指出了这一点:“终日谈本体,不说工夫;才拈工夫,便指为外道,此等处恐使阳明先生复生,亦当攒眉也。”(《寄王龙溪》,《念庵罗先生文集》卷三)这种批评,显然并非毫无根据。从理论的内在脉落看,良知的现成性与四无的设定相结合,确实引向了本体对工夫的消解。
现成良知说的以上发展路向在泰州学派那里得到了更具体的展现。与注重个体之意相应,泰州学派亦突出了良知的见在性。王栋便认为:“良知无时而不昧,不必加致;即明德无时而昏,不必加明也。”(《王一庵先生遗集》卷一)所谓良知无时不昧,是指良知始终以现成的形态存在于主体之中;不必加致,则意味着本体与工夫的分离。泰州学派首先将良知的见在性与日用常行联系起来:“良知天性,往古来今,人人具足,人伦日用之间举而措之耳。”(《答朱思斋明府》,《心斋集》卷二)“吾人日用间,只据见在良知,爽然应答,不作滞泥,不生迟疑,乃是健动而谓之易。”(《一庵集》卷一)见在良知向日用常行的渗入,意味着良知并不是一种超验的本体,而是体现于日常的道德实践。道德意识总是通过主体的行为而展现于外,正是这一点,使主体对道德理想的追求具有此岸的性质,并赋予内在的德性以现实的品格。泰州学派要求举措(运用)良知于日用人伦,无疑有见于此。当然,良知与日用的沟通,亦蕴含了本体向日常意识的回归。在这方面,泰州学派与王畿的思路无疑有相近之处。
由举措良知于日用,泰州学派提出了率良知之说:“故道也者,性也,天德良知也,不可须臾离也。率此良知乐与人同,便是充拓得开。”(《答刘鹿泉》,《心斋集》卷二)所谓率良知,首先是指在德性培养的过程中顺导内在的良知。按泰州学派之见,良知同时也就是天赋的见在德性,而德性的培养(道德涵养)无非是顺导这种内在德性:“宁知本性具足,率性而众善出。”(《王东崖先生遗集》卷一)德性的培养并不仅仅是一个外在强加的过程,社会的规范、理想、要求对个体的影响,与个体潜能的展开往往表现为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忽视对自我内在意识的引发,常常容易使人性扭曲。泰州学派将“众善”的形成与顺导良知联系起来,显然有见于此。
除了顺导内在良知外,率良知还具有另一重涵义。从王襞的如下论述中,便不难见其大概:“性之灵明曰良知。良知自能应感,自能约心思而酬万变,……一毫不劳勉强扭捏。”“将议论讲说之间,规矩戒严之际工焉,而心劳勤也,而动日拙。忍欲饰名而夸好善,持念藏机而谓改过,正是颜子所谓己而必克之者,而学者据此为学,何其汗漫也哉。必率性而后心安,心安而后气顺。”(《王东崖先生遗集》卷一)所谓工于规矩戒严,是指为了获得外部的赞誉或避免社会的谴责而勉强的履行某种社会规范。由此导致的,往往是人为的矫饰和虚伪化(忍欲饰名,持念藏机),后者显然不能视为真正的道德行为。与之相对的是顺乎自然并遵从良知的内在呼唤,它构成了率良知的另一内涵。道德行为既非对外在强制的屈从,亦非出于邀誉避毁而履行某种道德规范。如果仅仅考虑外在毁誉,那么即使严格地服从了某种规范,其所作所为也势必具有异己的性质,很难视为完善的道德行为。王阳明曾对“着意去好善恶恶”提出批评,认为完善的行为应当出乎自然而非有所为而为之:“出乎心体,非有所为而为之者,自然之谓也。”(《答舒国用》)这种看法已有见于道德行为的自然向度。泰州学派反对忍欲夸善,持念藏机,无疑继承了王阳明注重自然之维的伦理立场。所谓率性而后心安,则在率见在之知的形式下,对此作了发挥。
然而,在拒斥工于戒严的同时,泰州学派往往亦拒斥了理性的工夫。在泰州学派看来,率良知意味着“不假丝毫人力于其间”,它与“学”难以相容:
才提一个学字,却要起几层意思。不知原无一物,原自见成,顺明觉自然之应而已。自朝至暮,动作施为,何者非道?更要如何,便是与蛇添足。(《王东崖先生遗集》卷一)
在王阳明的心学中,自然是指理性的自觉化为人的第二天性。这一意义上的自然,已超越了单纯的自觉,近乎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不过,尽管它已超乎自觉,但这种超越本身又以理性的自觉为前提的。然而,当顺应自然与理性的自觉努力(学)相对时,自然便开始接近于自发的形态,在泰州后学周汝澄的如下议论中,可更具体地看到此点:“汝且坐饮,切莫计较;其起计较,便落知识。但忘知识,莫问真体。”(《剡中会录》,《东越证学录》卷五)在但忘知识,莫问真体的形式下,对自觉的理性本体之承诺似乎已被放弃,主体的行为亦相应地被赋于自发的性质。顺自然之导向崇自发,从理论上看乃是良知向日常的现成意识还原的逻辑结果:良知的超越性与普遍性之维在被弱化之后,它往往更易被混同于自发的意识。而在泰州学派那里,这种衍化路向又与心意关系上突出主体意识的非理性维度相一致。
二 致知过程论的展开
与王畿及泰州学派由先天本体走向现成良知不同,王门的另一些后学更多地将注重之点指向了致知工夫。其中,聂豹(双江)与罗洪先(念庵)在反对将良知视为现成(见在)之知的同时,又由强调良知与现成意识的差异而把本体形而上化,并以归寂为致知的工夫,从而或多或少地将心学引向了超验之路。从更广的视域对王阳明的致知过程作发挥的,是欧阳德(南野)、钱德洪(绪山)、邹守益(东廓)、陈九川(明水)等为代表的工夫派以及晚明的东林学者。
按工夫派的看法,良知虽是先天的本体,但其呈现却离不开后天的活动。欧阳德对此作了如下的阐释:
夫人所以为天地之心,万物之灵者,以其良知也。故随其位分日履,大之而观天察地,通神明,育万物;小之而用天因地,制节谨度,以养父母,莫非良知之用。离却天地人物,则无所谓视听思虑感应酬酢之日履,亦无所谓良知矣。(《答罗整庵先生困知记》,《欧阳南野先生文集》卷一,以下引该书,简称《南野集》)
此所谓日履,泛指主体与外部对象相互作用(感应)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产生的感知思虑等活动。在主体践履活动的展开过程中(随其位分日履),内在的良知逐渐呈露于外,离开了日履过程,良知即无从表现:所谓无日履,则亦无良知,即点出了此意。
就其肯定良知与日常践履及经验活动的联系而言,工夫派的如上看法与现成良知说无疑有相近之处。事实上,在拒斥良知的超验性这一方面,工夫派与现成良知说确乎有某些共同的语言。然而,与现成良知说由强调良知的见在性而消融道德本体于自发的经验意识不同,工夫派始终没有放弃对良知的普遍之维与自觉之维的承诺。就工夫派来说,良知呈露于日履,主要表明良知并不是寂然未发的超验本体,它并不意味着可以将良知等同于日常的偶发意念。正是本着这一立场,工夫派批评现成良知说:“使初学之士,骤观其影响者,皆欲言下了当,自立无过之境,乃徒安其偏质,便其故习而自以为率性从心。故使良知之精微紧切,知是知非所籍以明而诚之者,反蔑视不足以轻重,而逐非长过,荡然忘返,其流弊岂但旧时支离之习哉!”(陈九川:《与王龙溪》,《明儒学案》卷十九)所谓“安其偏质,便其故习”,也就是认既成的自发意识为本体,自限于偏狭的日用常行而拒斥理性的升华。与之相对,工夫派所注重的是“知是知非,明而诚之”的自觉过程。
当然,良知非自发的经验意识,便不意味着良知具有超验性质。在反对认“故习”为本体的同时,工夫派亦对归寂说提出了批评。归寂说虽然否定了良知的见在性,但却由此将其归结为一种超然于感应(现实作用)过程的寂然未发之体:“夫本原之境,要不外乎不睹不闻之寂体也。”(聂豹:《答欧阳南野》,《双江聂先生文集》卷八)对这种看法,工夫派明确提出了异议。较之归寂说将本体超验化,工夫派力图沟通形而上与形而下。从钱德洪的如下论述中,即不难看到此趋向:“未发寂然之体,未尝离家国天下之感而别有一物在其中也,即家国天下之感之中,而未发寂然之体存焉耳。”(《复周罗山》,《明儒学案》卷十一)家国天下之感,是指事亲敬兄,仁民爱物之类的践履活动;寂在感中,意味着良知虽是先天的本体,但并非隔绝于主体在后天的作用(感)过程。在工夫派看来,分离寂然之体与后天感应,往往导致本体的超验化;本体的超验化,则总是引向在已发之外去追求寂然之体。当主体沉弱于回归寂然之体时,其自身的活力也将不复存在:
离已发而求未发,必不可得,久之养成一种枯寂之病。(钱德洪:《复何吉阳》,《明儒学案》卷十一)
此所谓枯寂,即主体存在失去内在的生命力。离开了现实的实践过程,道德往往将变得抽象化、苍白化,道德主体也容易变成无生命的存在。工夫派要求扬弃本体的超验性,即试图通过道德本体向实际践履的过渡,展示道德的现实力量。
从本体呈露于日履说出发,工夫派提出了于感应变化中致其知的主张:“故致知者,致其感应变化之知。致其感应变化之知,则必于其感应变化而致之。犹之曰:“达其流之水,则必于其水之流而达之。”(欧阳德:《答聂双江》,《南野集》卷三)感应变化之知,亦即展开于道德实践过程中的良知。这里的逻辑前提是:良知尽管是先天的,但惟有在日履过程中才能取得现实的形态;作为致知对象的良知,并非如归寂说所设定的那样,是先天的寂然之体,而是在日履中获得现实形态的良知。要达到这种现实形态的良知,便必须从感应变化(现实作用)的过程入手。在此,工夫派似乎对良知的先天形式与现实形态作了区分,并更多地将良知的现实形态与践履过程联系起来:正是践履过程,赋予良知以现实的形态。这种看法,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黄宗羲“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是本体”说的理论前导。
致知之“致”有达到与推行双重含义。就达到而言,致知过程总是涉及视听思虑。工夫派认为,良知虽然并非形成于主体的认知活动,但在其后天的展开中,又离不开感知与思虑。欧阳德指出:“良知者,见闻之良知;见闻者,良知之见闻。”(《答冯州守》,《南野集》卷三)陈九川进而认为无知觉则无良知:“故见闻废,良知或几乎息矣。”(《与王龙溪》,《明儒学案》卷十九)以日履为良知的存在方式,已意味着良知并非隔绝于日常的经验意识;无见闻则良知亦成虚幻,可以视为这一观点的逻辑引伸。从德性培养的角度看,道德意识的形成,总是离不开实践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感受,这种直接的经验与感受使自我在耳濡目染之下,逐渐形成对道德原则与道德理想的向心力和认同感,并进而将其化为内在的德性。工夫派将良知与感性层面的见闻联系起来,似乎有见于此。
当然,单纯的见一善行,闻一善言,往往很难超越自发的领域。要达到对本体的自觉意识,离不开缜密的思虑:“思也者,戒慎密察之谓,精之功也,故能得其本心。”(《答王禺斋》,《南野集》卷三)经验层面的见闻感受固然能使主体扬弃道德原则的抽象性,并对其有亲切感,但惟有通过理性的反思,才能在更深入的层面理解并接受这种原则。从理论本身看,工夫派的以上看法当然很难说提供了多少新的见解,但就心学的演变而言,却又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如前所述,泰州王学在扬弃本体超验性的同时,又表现出认自发的日常意识为良知的趋向,并由此消解了学问思辨的理性工夫;聂豹、罗洪先则以良知为寂然之体,并把归寂视为致知的方式,从而在某种意义上走向了神秘的体悟。二者尽管衍化的方向不同,但在偏离理性之维上,却又有相通之处。在此背景下,工夫派强调缜密的思虑工夫,无疑表现了对理性的维护。
肯定致知工夫是达到本体的前提,主要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工夫与本体的关系。从另一方面看,致知工夫本身又必须以本体为根据:“不知良知之本体,则致知之功未有靠实可据者。”(答陈明水》,《南野集》卷一)以本体为据,也就是以良知规范致知工夫。就本体与工夫的这一方面而言,本体无疑构成了出发点,其思维趋向表现为由本体说工夫。后者在形式上与现成良知说似乎有相近之处。不过,在形式的相似之后,却蕴含着内在理论旨趣的深刻差异。在现成良知说那里,本体作为既定的、现成的形式而构成了日用常行的起点。与之相对,工夫派之肯定本体对工夫的制约,则以过程论为其理论前提。从动态的角度看,本体与工夫的关系总是展开为一个不断互动的过程,这一互动过程的具体内容表现为:通过致知工夫而达到对良知的明觉,又以对本体的明觉进一步范导工夫,邹守益曾对此作了简要的概括:“做不得工夫,不合本体;合不得本体,不是工夫。”(《再答聂双江》,《东廓邹先生文集》卷六)从正面看,做不得工夫,不合本体,也就是由工夫而得本体;合不得本体,不是工夫,则是循本体而更进于知。按工夫派之见,本体与工夫的这种动态统一过程,具有无止境的性质:“然学问之道,岂有止法哉?因其所已能,而日进其所未能。”(《又答田文学》,《张阳和文选》卷一)“知无穷尽,格致之功亦无穷。日积月累,日将月就,而自有弗能已者。”(《答罗整庵先生困知记》,《南野集》卷一)对本体与工夫关系的这种理解,可以看作是王阳明致知过程论的进一步展开。
心学所谓本体,在某种意义上表现为先验化了的主体意识系统与认识结构(包括道德认识),致知工夫则涉及德性培养及道德认识的过程。从现实的形态看,主体已有的意识结构与德性培养及道德认识本质上展开为一个交互作用的过程:德性培养及道德认识总是以已有的意识结构与认识条件为内在的根据,而并非从虚无出发;另一方面,意识结构本身亦非凝固不变,它总是随着后天工夫的展开而获得新的内容并不断深化。工夫派将致良知理解为由工夫而悟本体,循本体而更进于知的过程,无疑多少有见于内在的意识结构与道德认识、德性培养的交互作用。当然,工夫派在肯定本体与工夫动态统一的同时,始终没有放弃本体先天性的预设,从而未能在理论上超越心学的思辨。
三 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是本体
王门后学在心性、本体与工夫等问题上的辨析、衍化,为走出心学提供了逻辑与历史的双重前提。在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那里,已可以看到心学演进的这一趋向。
从心学的演进看,黄宗羲思想中值得注意的方面,首先在于对工夫与本体关系的阐释和规定。在黄宗羲那里,心性关系和本体与工夫的关系并非互不相关。由心性关系上肯定性因心而见,黄宗羲进而指出:“心不可见,见之于事。”(同上,卷二)此所谓心,泛指道德本体(心体);“事”则指事亲事兄之事,亦即道德领域的践履工夫。因事而见心,其内在的意蕴便是本体离不开工夫。黄宗羲又对真本体与想象的本体作了进一步的区分,以为工夫之外的本体只具有想象的意义:
无工夫而言本体,只是想象卜度而已,非真本体也。(《明儒学案》卷六十)类似的论述还有:“学问思辨行,正是虚灵用处;舍学问思辨行,亦无以为虚灵矣。”(同上,卷五十二)王阳明曾以先天本体与后天工夫之分作为致良知说的前提,不过,在王阳明那里,致知工夫只是达到本体的手段,而不是本体形成与存在的条件;相形之下,黄宗羲强调无工夫即无真本体,则把工夫理解为本体所以可能的必要前提。这里已表现出逸出心学的趋向。无工夫则无真本体,着重于将真实的本体与工夫联系起来。由此出发,黄宗羲进而从更普遍的意义上,对本体与工夫的关系作了规定:
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是本体。(《明儒学案·序》)
心之本体,是心学的先验预设;心无本体,意味着悬置这种先天的本体。如前所述,从内容上看,与工夫相对的本体首先是就主体的精神而言,它在广义上泛指主体意识的综合统一体,其具体的内涵则在不同的关系中展开为德性培养的根据、道德认识的内在结构、道德实践的内在规范,等等。在黄宗羲看来,精神本体并不是先天的预定,它在本质上形成于后天践履与致知过程,并以这一过程为其存在的方式。在黄宗羲以前,从王阳明到王门的后学,心学在其演进过程中始终没有放弃对本体的先天预设;归寂说将良知理解为寂然未发之体,更表现出本体神秘化的趋向。黄宗羲对心之本体的如上消解,则在扬弃本体先天性的同时,亦避免了本体的凝固化与神秘化。
就其本质而言,精神的本体总是处于不断生成的过程之中,并且惟有在精神活动与实践活动的过程中才具有现实性,离开精神活动与实践活动的过程谈本体,总是很难避免先天的虚构或超验的设定。休谟认为离开了知觉活动即无自我,从一个方面注意到了这一点;黄宗羲肯定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是本体,同样有见于此。黄宗羲的这一看法可以视为本体与工夫之辨演进的逻辑结果。强调本体与工夫的统一,是心学的基本立场。王阳明提出致良知,肯定本体原无内外,已从不同方面确认了这一原则。王门后学的工夫派认为,做不得工夫,不是本体;合不得本体,不是工夫,则对此作了具体的发挥,为黄宗羲提供了更直接的理论先导。不过,无论是王阳明,抑或其后学,在肯定由工夫而行本体的同时,都始终没有放弃对本体的先天预设,与此相应的是工夫的历史性与本体的非历史性之间的紧张。相形之下,黄宗羲将精神活动规定为精神本体的形成条件与存在方式,无疑超越了以上紧张。后者在悬置先天本体的同时,亦开始突破心学之域。
心无本体的观点体现于道德意识与道德实践的关系,便具体化为虚实之辨:“盖仁义是虚,事亲从兄是实,仁义不可见,事亲从兄始可见。”(《孟子师说》卷四)仁义在广义上既是普遍的规范,又指作为这种规范内化的道德意识及内在德性,这里主要是就后者而言;事亲从兄则是道德实践。这里的虚实之辨,首先涉及道德意识的形成问题,黄宗羲对此有如下的具体解释:
仁、义、礼、智、乐,具是虚名。人生坠地,只有父母兄弟,此一段不可解之情,与生俱来,此之谓实,于是而始有仁义之名。知斯二者而弗去,所谓知及仁守实有诸己,于是而始有智之名。当其事亲从兄之际,自有条理委曲,见之行事之实,于是而始有礼之名。不待于勉强作为,如此而安,不如此则不安,于是而始有乐之名。到得生之后,无非是孝悌之洋溢,而乾父坤母,总不离此不可解之一念也。先儒多以性中曷尝有孝悌来,于是先有仁义而后有孝悌,故孝悌为为仁之本,无乃先名而后实欤?(同上)
人来到世间,便处于一定的人伦关系(如亲子兄弟之间的家庭亲缘关系),这是一种基本的本体论事实。所谓“不可解之情”,即言其既定性;“此之谓实”,则言其现实性。在这种现实的关系之上,逐渐形成了事亲从兄等道德实践。这种道德实践最初似乎具有率性而行的形式,但它同时又包含实际的工夫:“孩提知爱知敬,率性而行,道不可离,说是无工夫,未尝无工夫;说是无戒惧,未尝无戒惧。”(同上,卷七)在道德实践的工夫由比较自发到较为自觉的衍化中,仁义礼智等道德意识也随之渐渐萌发和发展,此即所谓“有亲亲,而后有仁之名”;“有敬长,而后有义之名”(同上)。质言之,有事亲从兄之工夫,斯有仁义礼智本体;作为精神本体的道德意识,形成于道德实践的工夫。
从上述观点出发,黄宗羲对王阳明亦提出了批评:“阳明言,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不知天理从父母而发,便是仁也。”(《万公择墓志铭》,《南雷文定五集》卷三)以纯乎天理之心发于事父,是以本体的先天预设为前提的,其侧重之点在于先天本体对后天工夫的作用;天理从父母而发,则将现实的人伦(亲子关系)及由此而形成的道德实践工夫置于更本源的地位。王阳明固然并不否定后天工夫在达到本体中的作用,但这种达到(致)本身又以所致对象(本体)的既成性(先天性)为前提的,这种预设使王阳明的心学难以完全超越本体与工夫的紧张。黄宗羲对王阳明的以上批评,亦表明他已比较自觉地注意到心学内涵的问题。
通过事亲从兄的道德实践而形成仁义等道德意识,更多地着眼于个体。本体与工夫的关系并不限于个体的道德实践,广而言之,它亦指向事功等社会活动:“道无定体,学贵适用。奈何今之人执一以为道,使学道与事功判为两途。”(《姜定庵先生小传》,《南雷文定五集》卷三)道无定体,可以视为心无本体的逻辑展开,当然它同时又涉及真理的过程性;所谓事功,属经世致用的社会实践,它在本质上展开为类(社会)的历史过程;学道则泛指把握普遍的自然法则与社会规范,并进而将其化为主体内在精神本体。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黄宗羲将把握道体及化道体为本体的过程与广义的经世过程联系起来,从而使致知工夫由个体的道德践履,进而扩及类(社会)的实践活动。在黄宗羲以前,晚明的东林学者在强调“学问须躬行实践方有益”的同时,亦已开始将经世活动纳入致知工夫,东林会约之一,便是“或商经济实事”(《东林会约》,《顾瑞文公遗书》第五册),经济实事亦即经世之事。黄宗羲肯定学道与事功的统一,与东林学者的看法无疑有相通之处。不过,黄宗羲由心无本体讲道无定体,更侧重于本体的过程性:所谓学道与事功非两途,意味着将工夫广义地理解为类的历史过程,并进而从类的历史过程这一角度,来规定精神本体。
对历史过程的这种注重,在黄过羲的思想史与学术史论中得到了更深刻的体现。黄宗羲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其思想史与学术史的研究而奠立的,他对宋明思想史与学术史的系统总结与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开创的意义;他对本体与工夫关系的理解与阐释,亦以思想史的反思和总结为其背景: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是本体”,便是在其主要思想史著作《明儒学案》的自序中明确提出的。
从思想演进的历史过程看,所谓本体,便是指人类的精神发展形态的以真理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人类认识成果。这一意义上的心无本体,意味着人类精神的发展形态与作为真理的人类认识成果并不具有先天与预定的性质;工夫所至即是本体,则强调这种精神形态与认识成果即形成于类的认识发展过程之中。当然,人类精神的发展形态与认识成果并不是抽象的,它总是通过不同时代的具体探索而积累和展开。就明代而言,其文化精神的发展,便是通过思想家的探索工夫而逐渐体现出来:“诸先生深浅各得,醇疵互见,要皆功力所至,竭其心之万殊然后成家。”(《明儒学案·序》)正是思想家们的不同探索,构成了类的精神发展史。在此,工夫具体展示为类的认识演进过程。
由“工夫所至即是本体”的观点考察类的认识史,便应当特别注意不同思想家的创造性见解。在《明儒学案·凡例》中,黄宗羲指出:“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同经生之业。”自用得著者,即通过创造性探索而达到的独到见解。以此为前提,黄宗羲进一步肯定了学术探索与思想发展路向的多样性:“是以君子宁凿五丁之间道,不假邯郸之野马,故其途不得不殊。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于一途,使美其灵根者,化为焦芽绝巷。”(《明儒学案·序》)从本体与工夫的关系看,这里确认的是本体的形成与展开离不开工夫;就个体性原则与普遍性原则的关系言,它又表现了对个体性原则的注重。
当然,以自用得著者为真与肯定思想探索的多样性,并不意味着以殊途的工夫排斥对道体的把握。以类的精神发展而论,本体既体现于殊途的探索,又具有内在统一性,黄宗羲以“一本而万殊”对二者的关系作了概括:
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著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明儒学案·凡例》)
一本即以道体为内容的精神本体(表现真理的类的认识成果),万殊则是不同的思想家在不同历史时代的独特探索。一方面,类的精神本体即形成并存在于万殊的探索工夫之中,故应注重一偏之见,相反之论;另一方面,万殊又构成了普遍本体的不同方面,犹如百川之归海:“夫道犹海也,江、淮、河、汉,以至泾、渭蹄涔,莫不昼夜曲折以趋之,其各自为水者,至于海而为一水矣。”(《明儒学案·序》(改本),《南雷文定五集》卷一)质言之,统一的精神本体与多样的探索工夫之间,并不存在紧张与对峙。对人类精神现象的这种理解,在相当程度上已打通了心性之辨内含的个体性与普遍性关系和本体与工夫的关系:它既表现出统一本体与工夫的趋向,又从精神本体的形成与展开这一角度,对个体性原则与普遍性原则作了双重确认。黄宗羲思想的这一逻辑演进路向在某种意义上似乎又回到了王阳明心学的内在主题,但这种回归的背后,却又蕴含着哲学立场的深刻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