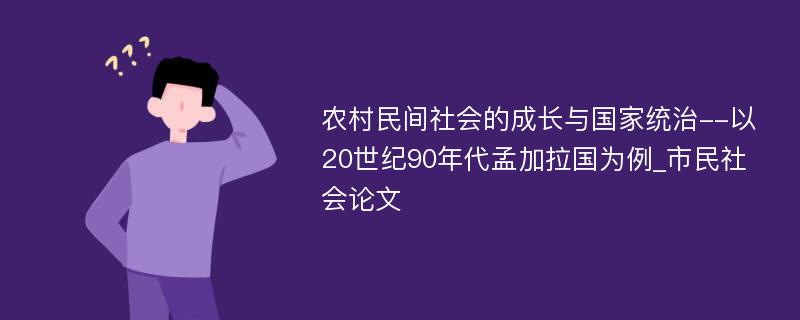
农村市民社会的成长与国家统治——以1990年代孟加拉国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孟加拉国论文,为例论文,市民论文,年代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末,随着亚洲后发国家开始步入发展·成长的轨道,也开启了东西方学者运用“市民社会理论”研究“亚细亚型国家与社会关系”①的新时代,到今天这种讨论的声音虽然有所减弱,但是上世纪末关于亚洲型市民社会的讨论,特别是关于“农村市民”的内涵正随着“弱者武器”式的讨论变得日益引人关注。总体看,20世纪末的研究归纳起来大致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对在(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东南亚国家联盟)NIES·ASEAN各国经济成长过程中中产阶层的兴起并且以集团形式登上社会舞台从而引发社会结构变动的事实及其成为民主化运动“原动力”的研究;第二,是对在后发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开发NGO”“环境NGO”“人权NGO”等一系列新兴社会组织如何领导和参与群众运动问题的研究②。这些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中产阶层的兴起以及以NGO为代表的新兴社会组织是否能够或者已经促使东亚社会走向了市民社会?其中,关于中产阶层,笔者作过专门的论述③,而从对后者的一些研究来看,一般认为在韩国、台湾的市民社会化过程中新兴社会组织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从近些年来关于孟加拉国的研究④来看,在东亚后发农业主导型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似乎确实应该考虑工业化这个催化指标⑤,因为从孟加拉国NGO组织的发生、发展及其作为来看,这种建立在脱贫背景上的NGO组织确实很难起到引导“现代化”与“市民社会”的作用。本文将从孟加拉国NGO组织的产生背景、具体作用以及其与国家统治的关系来探讨在后发农业主导型国家是不是具有实现市民社会化的可能。通过这一研究试图回答笔者多年来一直在研究和思考的一个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发展过程中的市民社会化是否可能?
一 市民社会视角下的NGO
一般来说,近年来学术界对于NGO的讨论主要围绕“第三部门”这个概念展开,即,通常认为NGO既不同于政府组织这类“公域”也不同于个人生活等的“私域”。Norman Uphoff认为,应该以契约关系的目的来区分这三个不同的领域。即,“公域”主要是以官僚机构和强制力为前提的契约关系;“私域”主要是以市场交换行为为前提而不涉及公共善行的个体利益追求行为;与此相区别,第三部门一般比较强调自发性这个特征。即,人际关系行动应该以“互助共存”为基本规范而发生,但是这种行动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个体利益而应该以公共利益的实现为目的——例如,非营利团体就是一个典型⑥。这里所说的第三部门Norman Uphoff称之为Collective action sector,这与市民社会强调“公共性”的内涵基本一致。简而言之,作为全体社会一部分的市民社会中的个体人为了实现他所认为的“公共利益”,必然自发的发生一种集合行动——这种集合行动形态我们即可称之为市民社会,而NGO组织是这种集合行动的基本表现形式。
对此,Alexis Tocqueville提出的“第三次民主浪潮”思想在上个世纪末东欧、非洲、拉丁美洲的民主化过程中再次被热炒,大多数学者认为这系列的民主化过程正是因为带有强烈NGO色彩的市民团体发挥了积极作用。对此,在上个世纪末的认识中普遍认为NGO组织一可以团结民众防止分裂,二可以为在工业社会中被孤立和弱化的个人提供心灵的栖息地。比较典型的代表应该是Robert Putnam,他认为“NGO团体通过对其成员进行内在的和广义上的政治影响来达到其对民主政府的支配效率及安定状况作贡献的目的。……内在影响一般指对成员互助、团结、公心的培养;……外在的影响主要指团体内复数的社会网络可以对利益表达起到推动作用,从而实现社会内部的有机团结”⑦。
从以上的论述来看,西方学者讨论的市民社会概念大多遵循“西方的基本思路”,即,市民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社会团体的力量功不可没,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一个基本的事实是西方市民社会形成过程中的NGO组织基本都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的表达”而自发形成,它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工业化及社会分工催化了不同利益表达群体的出现,所以他一经产生就带有戴蒙德所说的“民主的功能”⑧。与此不同,孟加拉国1990年代所产生的诸多NGO组织却具有很不相同的特征,这些组织的是通过在一种生产力比较低下的农业生产状态下的“植入”产生的,它的根本目的是“脱贫”并试图提供手段而不是意义,因此它们对市民社会形成的贡献到底有多大就成为一个十分有趣的话题。
二脱贫NGO组织的兴起
1990年代孟加拉国的NGO发展呈现了井喷状态,研究显示,在1990年代实际上是无法统计出到底有多少NGO组织的存在的,粗略估计大约是有2万左右⑨从整个NGO组织的构成结构及功能等方面来看呈现出与其他国家明显不同的“农村开发”特征,其基本功能主要是“脱贫”。在孟加拉国,NGO组织第一特征就是农村贫困阶层的组织化,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唤醒那些除了劳动力资源以外便一无所有的农民的“贫困意识”,并在自己组建的组织内部就如何评价贫困问题进行磋商。在此基础上,那些在田野工作者帮助下被组织起来的贫农们可以进入旨在增加收入的小额无息贷款的申请程序。这个增加收入的申请程序一般被认为是孟加拉国NGO组织得以存在的第二个显著特征。例如,格拉明乡村银行(Grameen Bank)的贷款程序就是一个比较经典的案例,该银行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尤诺斯认为如果贫农获得资金的权利能够得到保证,就一定能够保证经济活动的展开——穷人就可以摆脱贫困。据当时的纪录显示,当时全孟加拉国NGO总资金的50%被8个巨大的NGO组织垄断,其中尤其以格拉明乡村银行和孟加拉农村发展委员会两个NGO组织最为出名。
(一) 孟加拉农村发展委员会
孟加拉农村发展委员会⑩1971年成立,是孟加拉国乃至世界上的最大的NGO组织。这个组织应该是孟加拉国最有代表性的NGO组织,它的主要工作有两项:农村开发事业和农村信用事业。这两块的工作在孟加拉国的NGO组织活动中都具有极强的代表性。
农村开发事业是农村发展委员会整个工作的核心,它的目的是通过促进贫农阶层在村落层面的组织化从而使村民的贫困意识得以清晰化并使之增加发展的动力。具体的做法是,首先由农村发展委员会的职员进入村落访问目标家庭,确定各家庭的基本情况,并与目标家庭成员就他们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通过组织化途径解决问题的方法进行个别或者小组协商,之后这些人就会根据男女不同分组建立相应的“村组织(Village Organization)”。“村组织”通常有20--50个成员组成,在此基础上再分成若干由5--7人组成的小组,女性村组织具有结组的优先权,小组每周开会,讨论信贷的返还和增加收入的办法,同时每个人存几块钱作为储蓄金。“村组织”的大型集会一般是每个月召开一次,除了讨论小组的微观活动之外也讨论诸如社会和健康等较宏观的问题。当这种集会和“存储蓄金行动”常态化之后就要求全体成员必须参加“功能教育”课程。“功能教育”课程的教师主要由具有高中毕业水平的村民担任,主要任务是组织村民讨论自己所面临的问题,通过这些讨论使村民的“贫困意识”和“自觉能力”逐渐形成。在“功能教育”过程中,对那些贫农来说无论是讨论自己所处的环境、与精英人物的从属关系,还是讨论自己的能力及致富的可能性都是全新的体验,正是在这种方式的学习和讨论过程中,使他们的贫困意识逐渐觉醒,强化了他们对自己处境的认识。另外,这种小组的学习讨论方式也可以增加贫苦农民的自信心和小组的凝聚力。“功能教育”结束之后,由于农民的意识及小组凝聚力已经得到长足的发展,就可以进入小额信贷的程序,开始自己改善生活的实际行动。一般农村开发事业的执行时间是4年,其象征主要是“村组织”已经获得了长足发展和壮大,这个时候农村开发事业的程序基本结束,引导人们生活改善的“农村信用事业”程序启动,原来的农村开发事业机构也随之变身为农村信用事业的执行机构——乡村银行的支行,它会通过完全买断农村开发事业机构的储蓄金和贷款的方式实现功能的转变并开始实质性的金融机构市场化运作。
以上是孟加拉农村发展委员会关于农村开发的一些具体内容。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孟加拉国的农村开发是一种有组织的“集团开发”模式,在整个执行过程中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更应该是这种开发的“集体性”特征,我们姑且不论这种制度的执行状况如何(实事上有很多怀疑的声音),只是这种形式就已经与我国目前的农村发展过程中的“原子化”状况大相径庭,它堪称基层小农社会“团结”的典范。但是,从民主、自觉、发展的角度看,这种“民间到市场”的模式虽然形态上已经十分具有市民社会的特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农村发展委员会这种NGO所作的主要工作还停留在“唤醒贫困意识”(它在告知贫苦农民什么叫做富裕的生活,富裕的生活比贫困更好)——“贷款+实干致富”(它在告知贫困农民通过“钱”可以致富,而不是权利的争取)的形式上,而对意义的培养却不多见,这使该 NGO组织从产生之初就具有了较强烈的“工具化”特征。
(二) 孟加拉国NGO产生的原因
孟加拉国NGO组织的产生不是为了争夺“后发展时代”的权利,其产生过程恰恰是为了争夺“发展的权利”。这使孟加拉国的NGO组织大都带有极强的“工具性”特征,这可以从该国NGO组织产生的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得到证实。
首先,从内因来看,孟加拉国NGO的产生具有很强烈的“社会自救”特征。其主要的自救过程可以分为以国家独立的复兴救助为特征的第一代NGO和左派激进青年旨在消灭农村贫困而结成的第二代 NGO。孟加拉国1971年独立后,有1000多万难民回到国内,由于国家权威非常低小,这时候在国外 NGO组织的影响下产生了诸多本土的NGO组织,它们的主要目的是救助难民,帮助他们重建家园,在此基础上试图实现国家的复兴(11)。另外,在独立战争过程中那些为理想而战的左派激进青年的理想没有得到新政府的认同,这些人由于对腐败无能政府的失望开始把视线转到农村,而组成独立组织以消灭农村社会的贫困,这成为这批青年人施展理想的唯一手段。
其次,从外因来看,孟加拉国NGO组织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来自西方的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开发援助”。众所周知,孟加拉国的NGO组织的主要资金均来自西方发达国家,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如此热衷于对一个刚刚独立的新兴国家进行大规模“开发援助”是因为“冷战”期间对共产圈国家实施包围的策略使然。代表性事件是由美国主导下的国际机构负责推动实施的V-AID项目(Village-Agri- cultur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它的主要目的是在建立类似农民工会一类组织的基础上,通过推进援助活动以实现对社会底层民众进行“资本主义化”影响。在这一过程中,NGO组织的中立性特点被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竞争所利用,成为阻止发展中国家共产化的一个范例。随着冷战逻辑的消亡,到了1980年代,西方国家的“开发援助”也逐渐凋敝,世界银行开始成为孟加拉国发展援助的主力军,在世行看来,政府主导模式的援助带来的只是一部分既得利益者的富裕,对农村贫困的消除根本没有效果,所以世界银行在选择援助的载体时同样选择了NGO组织。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孟加拉国NGO组织的产生过程呈现出较强的“工具性”和“实用主义”特征。在这一过程中虽然能够看到诸如农村发展委员会通过“集团讨论”的模式实现团体成员现实利益的“民主化程序”,但是从市民社会形成的视角来看,其对“集团权利诉求”的行动却非常少,恰恰相反在具体过程中其更多表现的是“诉苦”行动。同时,这些组织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壮大,其“市场”倾向日趋明显,更强调“钱”对改变农民处境的作用而忽略了权利这一根本原因。
三 国家统治·NGO·市民社会
随着国外开发援助源源不断地进入,孟加拉国从独立到1990年代以来一直都没有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国家统治体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国家的资源动员能力低下。1993年—1994年中央政府的税收收入只有GDP收入的9%(12),说明该国以税收为代表的国家动员能力极其低下。在一些村落,农民的税赋非常轻,包括住宅税在内的税收估计只有农民家庭收入的2—3%,而且在农村拖欠税收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13)。这使孟加拉国的税收从中央到地方都呈现出严重的问题,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支出都严重超支。而对于政府来说与其在强化执政能力上花工夫,还不如把获得开发援助作为首要目标以提高效率(14),导致孟加拉国的政府资源动员能力逐年下降,国家统治机能也日益弱化。第二,没有建立起国家与地方(农村)之间有效的行政管理制度。孟加拉国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一直因为中央政权的变化而被任意改变,这使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演变为中央统治者通过“制度变革”争取地方支持的一种政治手段(15)。与此相对应,属于地方行政范围的地域开发、教育、社会福利、公共服务等工作被忽视,地方政府更愿意分配来自中央政府的开发援助资金给地方社会的关键人物以获得他们对政权的支持,使地方政府沦为资金分配的“事务机构”而无法建立有效的行政管理体系。第三,国家统治的支撑体系有极大的局限性。研究表明,该国独立后直到1990年代政权的支撑主要是城市里的中产阶层和农村的富农阶层(16)。即使是在军事政权的统治之下,也必须依赖这两个阶层的支持,这使得孟加拉国的国家支持体系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在社会的下层无法获得国家的各种资源的同时,国家也无法通过绝大多数下层民众的支持而完成政权的合法化过程,其直接结果就是国家政策的执行在基层社会无法顺利地贯彻执行。
我们看到,在孟加拉国呈现的是一种“弱国家一强社会”状态。但是,“在这里由于国家的政治统治力量相对较弱,对市民社会的活动几乎没有任何限制。以NGO活动为主导的市民社会活动相当活跃,并且能够影响国家的政治生活(例如菲律宾1986年的‘黄色革命’和泰国1992年的‘流血民主化事件’)”(17)的现象却没有发生。我们一般认为的国家统治的“强大”和“强力”是阻碍市民社会形成的关键因素这一路径的相反现实在孟加拉国也没有呈现出来。相反,在孟加拉国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国家统治之间呈现一种各自独立互不干涉的变异关系,之所以呈现这种状态的原因是因为脱贫NGO强烈的“功利性”使然,而这种“功利性”正与市民社会的基本思想背道而驰。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孟加拉国 NGO组织无法在市民社会的形成中发挥作用的呢?
首先,孟加拉国脱贫NGO组织的“功利性”扼杀了作为第三部门组织应有的“公共性”。如前所述,以格拉明乡村银行的运作成功作为开端,无论是诸如农村发展委员会这类巨大的NGO还是中小NGO都竞相开始了面向农村贫困阶层的小额信贷业务。这类小额信贷业务确实对农村贫困阶层(特别是女性发展获益更多)的致富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从工作的具体展开过程来看,这类“脱贫”行动更加追求“诉苦”的“激励”作用(使贫困阶层产生强烈的改善生活的欲望)对于开展此类活动的意义却很少关注,这致使此类活动被有意无意地限制在“私域”内而无法实现其对国家或者地域社会“共同体意识”培育的贡献。如丸山真男所言“无论机械团结进行到何种地步都不代表公共意识以及自由秩序的形成。对于人来说追求的不是简单的‘团块化’组织而是共同性一致的社区。如果缺少了‘公共性’就会使人堕入个人主义欲望无限膨胀的深渊”。简而言之,脱贫作为孟加拉国NGO的一种公共目标与实现这个目标而被采纳的功利性手段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以致NGO的活动无法与市民社会的“成长”建立起必然的联系。
其次,NGO组织的“商业化”运作程序遮断了市民社会活动的政治性。如前所述,以小额信贷业务作为主要工作目标的各种NGO组织都会在“信贷”这一经济程序的运作上投入大量的精力,这使得各种NGO组织的企业化特征非常明显,他们更多强调组织的运营模式、管理方法等技术目标而对作为 NGO组织所应该承担的对底层民众进行“社会化”的意义功能却往往忽视。第一,NGO组织作为社会团体,除了资金外很少提供技术和能力服务(比如培训专业人才、建立与外界互动的通道等),这使得农民可以暂时“脱贫”而无法获得“发展”的技能。对此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T.W.Schultz)认为农业可以对经济增长作出重大贡献,但前提必须是现代农业代替传统农业,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关键就在于对传统农业进行改造,改造的方式就是进行人力资源的投资,增加农业识别及有效使用较好的技术知识,引进现代农业技术和对农业进行高质量的投入,打破传统农业的内部均衡和停滞状况,以此激发农民的投资和创新活动。第二,NGO组织很少对农民进行必要的政治动员。马克思曾经用“被剥削的小农”来描述农民的社会地位——农民阶级正是因为缺少政治权力才导致了其地位的低下。如前所述,在孟加拉国政党的支持力量主要是城市的中产阶层以及农村的富裕阶层,底层贫困农民一直都没有得到政党或相关团体的重视,一直没有组织或团体代表农民表达利益诉求。而本该承担这项功能的NGO组织由于过度重视“信贷”的技术功能而使它的“政治动员及表达团体利益”的意义功能被彻底遮断。
第三,孟加拉国NGO组织与国家之间缺少良好的制度性“互动关系”,使市民社会活动的监督性功能无法发挥。众所周知,NGO组织之所以成为市民社会运动的符号,正是通过其对国家公共政策的影响来实现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孟加拉国的NGO组织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近似一种“利益交换”关系,二者之间缺少必要的信任和相互监督。这可以从开发援助项目的实施中得到证实,国家常常利用开发援助资金项目的分配来支配NGO组织,NGO组织为了获得相关的项目资金和政策保障会向国家表达忠诚和提供支持。(18)这导致国家和NGO团体之间常常围绕“项目”而进行功利计算,忽视了二者之间的制度化运作谈判,进而使NGO组织监督政府的功能无法得到发挥。
四 “工业化”与农村市民社会的可能性
1990年代孟加拉国的农村社会经历了令世界兴奋的巨大变化。以消灭贫困为目标的NGO活动显然对其社会结构的变动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众所周知,欧洲市民社会形成的“背景”主要是伴随着工业化而开启的市民社会运动,在这一运动过程中因为工业化而“产生”的城市中产阶级成为了对抗据守乡村以依托贵族和教会力量实现国王支配权力的主力军,正是在这种对抗的过程中产生的“团体利益诉求”成就了市民社会这一理论。我们看到,这种路径在亚洲的一部分国家和地区也成为了现实(比如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在这些国家或地区,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工业化”催生了市民社会运动的兴起。所以,“工业化”看来是市民社会得以实现必不可少的催化剂。简而言之,工业化带来的“文明进步”可能是民众得以进行非暴力利益诉求的先决条件,也就是市民社会运动,而东南亚的历史也证明了一个基本定律:“贫困”条件下,贫苦农民往往更多地是通过一种“暴力革命(这种方法往往有效并直接)”的方式实现其地位的改变——其结果是一部分人成为了新的权力阶层,大多数人的市民权还是没有得到有效保证。由此看来,在孟加拉国虽然出现了市民社会的组织形式,但是由于缺少工业化背景下以资本控制为目标的“利益诉求”以及“利益诉求的公共性”导致这种市民社会的“成长”更多的集中在“分配资本(解决问题)”的具体层面,而无法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
我们看到对于大多数在对抗殖民统治过程中独立的亚洲国家而言都无法适用欧洲的“城市—工商业—市民社会”的路径,他们基本还是在走“农村包围城市”式的发展道路——比如,我国就是通过农村改革的方式(农业现代化其实可以解释为工业化,亦可以解释为农民公民权的市民化)走一条既不同于欧洲也不同于南亚诸国的农村市民社会化的路径。在中国农村,从改革开放开始实际上正在走一条“工业化”的路径,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农村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在政治上在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1983年就退出了“社队体制”而不得不走上“自治”的道路,而催生这一变革的正是“独立自营农民”以个体利益为目标的市场化诉求。这种路径与美国农业社会开始的市民社会化路径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可惜的是我国的局限在于土地无法成为农民推动市民运动的“资本”。
注释:
①①Helen Hughes and Berhanu Woldekidan,“The Emergence of the Middle Class In ASEAN Countries,”ASEAN Economic Bulletin,Vol.11,No2,November 1994,pp.139—149;具海根:《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邓正来:《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岩崎育夫:《ァジアと市民社会》,东京:ァジア經濟研究所,1998年;Rich- ard Robison and David S. G. Goodman eds.. The New Rich in Asia:Mobile Phones, McDonald's and Middle-Class Revolution. London:
Routledge1996。
②③张文明:《东亚市民社会:新兴组织与中产阶层——概念·现状·发展》,《东南亚研究》2007年第5期。
④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バンゲラデシュの農業および農村開発に関する研究協力》,2001年;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バンダテデツュ農村開発実験》,2001年。
⑤日本经济学者赤松要提出的雁行理论(flying geese model)指出,当国民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美金之上(工业化是必由之路),这个国家必然自动实现“现代化(民主化)”,这种模式将在东亚诸国产生连锁反应。
⑥Norman Uphoff,“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and NGOs in Rural Development:Opportunities with Diminishing States and Expanding Mar- kets,”,Word Development,Vol.21,No.4,April 1993,pp.610---619.
⑦Robert Putnam,“Bowling Alone:America’s Decling Social Capital,”Journal of Democracy,Vol.6.No.1,January1995,pp.89--90.
⑧张文明:《东亚市民社会:新兴组织与中产阶层——概念·现状·发展》,《东南亚研究》2007年第5期。
⑨海田能宏:《saleha·begumu,バンゲラデシュ農村開発実験》,《束南アジア研究》1995年6月,第9页。
⑩关于孟加拉农村开法委员会的资料散见于以下作品。Catherine H.Lovell,Breaking the Cycle of Poverty:The BRAC Strategy,Dha- ka:University Press,1992;Aditee Nag chowdhury,Let Grassroots Sperk:People’s Partieipation,Self-help Groups NGOs Bangladesh,Dhaka:University Press,1990。
(11)大橘正明:《ょり良き協力への模索》,《もつと知りたぃバンゲラデシュ》,弘文堂,1993年,第226页。
(12)Rehman Sobhan,Bangladesh:Problems of Governance,Dhaka:University Press,1993,P.223.
(13)(14)藤田幸一:《村落公共機能の强さを目指して一バンゲラデシュ農村開発の新戦略》,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バンダテデツュの農業および農村開発に関する研究協力》2001年6月,第32--33页。
(15)佐藤宏:《バンゲラデシュ地方行政改革の政治·经济的背景》,《アジア经济》第27卷第3号,1986年3月。
(16)佐藤宏编:《バンゲラデシュの権力耩造》,ァジア经济研究所,1990年,10—15页。
(17)张文明:《东亚市民社会:新兴组织与中产阶层——概念·现状·发展》,《东南亚研究》2007年第5期。
(18)Bishwapriya Sanyal,“Antagonistic Cooperation:A Case Study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Government and Donor’s Relationships in Iacome-Generating Projects in Bangladesh,”,World Development,Vol.19,No.10,October1991,pp1373—13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