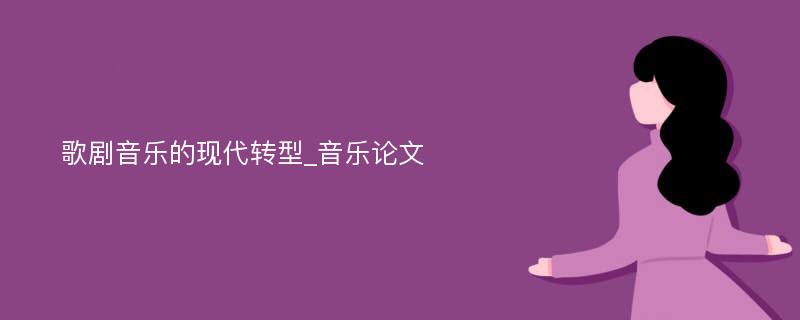
戏曲音乐的现代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戏曲论文,音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民间性向专业性的转换
古老的中国戏曲已经走过了八百余年的历史,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她积累起令人骄傲的丰富的遗产。但是,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伴随着由半殖民地、半封建走向社会主义这样最为强烈的社会变革,本来从近代以来业已显露的戏曲与时代之矛盾,便格外地突出和尖锐起来。因此,发展与变革便成为现代社会中戏曲运动的主潮。如果从艺术角度看,戏曲音乐的现代发展历程主要体现为由民间性向专业性的转换。应该说,这种转换既是出于戏曲自身发展的要求,同时也是中国音乐整体运动的潮流使然。对于这种转换,我们可以作一个粗略的历史回顾。
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底,也创造过令世界瞩目的灿烂篇章,达到曾使世界范围内同时代的音乐家仰视的艺术巅峰。但至鸦片战争前后,因腐朽黑暗的政治统治和封闭狭隘的小生产之困阻,已使其显出了某种衰颓之势:宫廷音乐已经名存实亡,宗教音乐龟缩一隅,文人音乐亦已萎顿。民间音乐则在极度贫困之中艰难挣扎。其中戏曲音乐在近代社会以后,正处于除了京剧等大戏形成外,在全同范围内各地方小戏纷纷兴起之时。这种局面的形成,与戏剧普遍由农村走向城市不无关系。它自然不同于以往伴随商贾官宦的戏曲流布,而是因农村极度贫困,破产农民艺人涌入工商经济新兴的城市谋生的戏曲潮动。如本世纪初由各地向上海流入淮簧艺人、的笃班艺人、花鼓艺人、香火戏艺人,渐次兴起沪剧、锡剧、苏剧、越剧、扬剧、淮剧等,便是典型的例证。这一局面给当时的戏曲带来了某些特点:在生产方式上,普遍由非职业化转变为职业化;在艺术上,由于诸剧种之间的强烈的生存竞争和相互吸收而加快了它们的发展和定型;在传播方式上,则由广场走向剧场。但是、就总体而言,它们在艺术上都处于并不成熟,极待提高的状态,同时也还仍然保持着传统的民间艺术品格。
历史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音乐伴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大震荡而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和发展。其贯穿的主题就是:东西方音乐文化的交流撞击和专业音乐的建设与发展。
中西音乐文化在20世纪最为醒目的撞击交流有二次。第一次是在本世纪初,那是伴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一次“西乐东渐”,当时虽有“变法维新”大背景下音乐界积极效法西乐,变革旧乐、创造新乐的主观追求,但总体上却是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独立性遭受极大破坏情况下的被动状态。第二次则全然不同,那是在八十年代前后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的一次主动选择。
而在第一次中西音乐文化撞击的宏观背景下,于学堂乐歌后期,特别是五四运动前后,我国专业音乐已经开始发展起来:涌现出萧友梅、赵元任、黎锦晖、刘天华等一批专业作曲家;也创办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科、上海专科师范学校音乐科、北京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等,直至我国第一所专业音乐高等学府——国立音乐院。(即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这样完整独立的教育机构;还组织社团、发行刊物,构成了20世纪中国音乐现代化进程的崭新局面〔1〕。然而,当时戏曲音乐的发展却与此局面并不同步。这主要因为,近代戏曲改良活动虽然开创了戏曲“从内容到形式,都以自我批判、自我改造为主的发展时代”〔2〕但不久便走入低潮,以失败告终。而且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后,把戏曲作为封建落后文化的代表加以激烈批判的基本态度,又使得戏曲长期被排斥在新文化运动之外了。因此,中西音乐文化交流、专业音乐建设真正涉入戏曲,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由戏改而始的:当时在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大批新文艺工作者投入戏曲队伍,举办了各种讲习班、进修班、成立了正规完备的戏剧学校,并很快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是,如果从创作的角度看,其高潮却是在“样板戏”时期。这可能是因为在那段不正常的时期中,“样板戏”竟成为全国政治、文化生活中非同小可的大事,一向专注于专业音乐发展的音乐界,已无其他大事可做,而被指令或主动投入到“样板戏”的创作演出或普及移植工作之中。如指挥家李德伦,作曲家吴祖强、杜鸣心、施光南、于会泳,演奏家俞丽拿、殷承宗、俞逊发等当代著名音乐家便都参加了各类“样板戏”的创作,而更多也更普遍的则是介入了“样板”作品中的戏曲类创作。当时的文化专制、“三突出”等错误理论虽然困扼着艺术,但音乐家们遵循艺术规律的艰苦探索,却仍然留下了许多极其宝贵的创造财富。另外,建国后若干年戏曲音乐发展的经验教训作为重要的基础和前提,也使得“样板戏”创作中积极进行中西音乐建设的努力,显得更加全面、深入和深刻。
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中国音乐界主动迎来了本世纪第二次重大的中西音乐文化交流和撞击,对当代中国音乐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激发起争议不断的新潮音乐之掘起、流行音乐的漫衍兴盛、学术思潮的活跃繁荣等诸多潮涌。几乎惊人地相似,如同新时期的文学在短短十年里走过了西方文学的百年历程,戏剧界则把西方戏剧近百年技法玩过一遍一样,音乐界也对19世纪以来西方音乐的各种理论、技巧摸索、研究、尝试了一番。然而,这一切在总体上却似乎与戏曲音乐的生存状态隔缘。这或许又是因为在内部,戏曲界“文革”后的拨乱反正似乎更多着力于老戏重登舞台和对传统戏的“翻箱底”;在外部则不复有五、六十年代专业音乐工作者的大规模投入,甚至“愈老愈好、愈正宗”的保守思想、排外意识也顽固地阻碍了戏曲音乐界应有的人才更新与知识更新,影响了戏曲音乐向专业性转换的前进步伐。
然而,无论如何戏曲音乐的现代进程毕竟还是表现了强烈的、向专业性转换的基本倾向,并取得了十分醒目的成就。我们不难看到,建国后的戏曲音乐的确获得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整体前进,一种不是此起彼伏、而是诸声腔剧种的全面发展。这自然是国家对戏曲事业高度重视和支持,戏改政策在全国范围贯彻落实的结果。但从艺术上说,却是得力于大批专业音乐工作者的积极投入和卓著贡献。他们大多都有一个艰苦学习和继承传统的过程,但同时却也开始打破和改变着历史上无专业的分工所导致的艺术发展那种经验性积累状态,因为这种经验性积累总是垄断性强而可传性差,甚至常常还会导致成就的中断和失传。面对着新的题材内容向传统戏曲形式提出的种种要求,在有史以来最密集的剧目生产中,他们进行了一系列远比以往更为完整、理性、自觉的创造。比如,发展成套的板式唱腔,研制行当唱腔,实行男女分腔,引进合唱、伴唱、重唱等演唱形式,吸收兄弟剧种、曲种的音乐语汇,丰富器乐手段,编创新的曲牌……,几乎对所有年轻剧种的成熟和古老剧种的新生都作出了显目的成就。专业音乐工作者的投入,很显然地加快了戏曲音乐的前进步伐。
但是,作曲专业分工地位的确立,对戏曲音乐最深刻的影响还在于向专业性转换的推动。专业作曲方式,不仅因其必然的艺术个性追求而使音乐程式沿用的变化、发展、突破中融变量急剧加大,专曲专用的意味愈见浓重;更通过专业作曲家的创作潜默地渗入了现代人的情感方式、心理结构、价值观念,从而积极地运用了若干新的观念和新的技术手段,不断改变着戏曲音乐的面貌和品格。比如在观念上,追求发展多声思维,进一步推动复调手法;注重刻画个性典型而着意突破行当、流派程式,甚至追求体现作曲家个性、剧目个性而力避程式趋同;重新认识戏与曲的辩证关系,充分调动音乐功能、发展音乐手段,力求在更高层次上解决音乐性与戏剧性关系;改变传统声乐功能与器乐极度失衡的局面,积极发挥器乐功能;克服历史上零散、不统一、乃至是失重(如不从戏剧出发的因人设戏、设腔)的创作构思。而在技术手段方面,则追求与现代音乐沟通,引进专业作曲技术,运用主题音调贯穿手法来刻画人物形象和统一作品风格、体现作品个性,充分发展转调技术,增强色彩对比,改变习用调高来推动旋律发展,吸收现代语言节奏和行为节奏以赋予音乐结构新的表现力,吸收西洋、民族管弦乐的多音色、多织体的表现手法,追求吻合于现代剧场审美需求以及新型乐队的声部平衡和音量控制。充分调动舞台音响技术以求得音乐与效果的浑然一体以及听觉艺术的完整设计……。无疑,四十余年来多少优秀戏曲音乐作品的产生正来自于上述专业化创作追求中,它们甚至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和体现了戏曲艺术的总体水平。
无法令人满足的是,这种专业性转换的进程显得过于缓慢了。现代的戏曲音乐发展在总体上却与现代文化脱节,与20世纪中国音乐发展中的东西方音乐文化交流、专业音乐建设之主题未尽合拍,苛刻地说,整体上也尚未汇入中国音乐从传统格局向现代格局的战略性转型的完成之中。建国四十余年了,且不说当前戏曲音乐优秀人才缺乏的问题日渐突出,即以戏曲作曲队伍的构成来说,也始终未能解决由特殊、专门的戏曲音乐高等教育来培养的问题。我国目前九所高等音乐学府——中央、中国、沈阳、天津、西安、武汉、上海、四川、星海音乐学院中竟没有一个具有稳定、完善的戏曲音乐专业设置,而且至今缺乏完整、权威的戏曲音乐史和戏曲音乐基本理论,缺乏对民族戏曲全面的作曲理论及主要剧种的作曲技法的系统研究。我们始终没能逐步积聚、建设起高度专业化所必需的戏曲音乐基础理论和技术理论,严格精密全面的专业训练方式,知识继承上完备的循序渐进方法,及其在操作上获得较强的可行性和应有的高效率。很显然,如果没有戏曲音乐现代转换的大踏步地前进,当代戏曲舞台艺术是很难出现长足的、面貌一新的整体改观的。因此,我们今天必须强烈呼唤戏曲音乐专业性转换的自觉意识,高度重视专业音乐工作者对戏曲的再投入,高度重视对戏曲音乐理论和音乐教育的建设,以积极有效地推动当代戏曲音乐迅猛的发展。
二、转换中的几个关系
戏曲音乐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却有着自身丰厚积累所带来的独特性;戏曲音乐也有着历史上众多的声腔更迭和今天繁复的剧种划分所构成的多样性;戏曲音乐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又始终伴随着中西音乐文化的交流撞击从而构成其背景的某种复杂性。因此,戏曲音乐由民间性向专业性的转换,便自然不可成为一种粗率简单的替代过程。这里,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关系值得戏曲界共同加以关注。
1.民间、专业关系
与西方许多国家里专业艺术兴起以后民间艺术便不断消亡的情况不同,中国戏曲音乐却作为一种高文化的民间艺术,而至今神采独具,展示着顽强的生命力。这种高文化,包括来自于知识分子的投入和贡献,但主要则是民间艺术家以口头传统(而不是书面传统),通过肉体传承的方式,世代累积艺术,并且千百年来传统不断的结果。其中,戏曲不间断的剧目生产避免了民间艺术中一般的单纯消极传递,始终面对着又继承又突破的局面而须付出创造的心智;而非专业与半专业相结合的生产、传播方式相对于一般民间艺术来说,显然也更有利于提高艺术积累的速度与质量。这样,戏曲音乐的民间性就具有一种深厚的独特传统,它与专业性之间也不是截然的分离和对立,向专业性的转换也就不是一种简单的替代,而须大大注意对原有民间性传统作出仔细的分析、扬弃、发展。
我曾把戏曲音乐的民间性特征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它的群众性,即广大民众从既是创造者又是欣赏者的两方面完整体现了作为该艺术主体的地位身份。从而赋予它极强的群众精神特征。二是创作的集体性,即创作无专业的分工、无一次终结,并总是表现为对前人成果的继承和发展。三是形态的可变性,即作品无严格意义的诞生与完成。或者说,戏曲音乐不存在永久的形式,作品总是随历史而演化、依传唱而改观”〔3〕。的确,这样的深厚民间传统也为我们留下了众多艺术珍品,积累起整套可学可用的技艺、语汇,其表现力强,形式独特,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但它始终没能形成与表演分离的创造法则,没有构成蕴涵戏曲创造规律的作曲技法的完整体系。于是创作就只能依靠有才识者凭灵气摸索体悟,在低起点上操作实施;于是它也就很难具有专业音乐那种起点高、效能好、发展快等优长。然而,当我们致力于从这种民间性向专业性转换时,又不能不注意这样的一些问题。比如:
就群众性而言,这自然是同“民间艺术的独特性主要在于创作者个人影响的微弱”〔4〕有关。而专业艺术则非常强调艺术个性,躲避重复,并也力求在继承和创新上都保持质量。然而,民间艺术更多表达群体共同情感,从而可以获得更为广泛的心灵沟通和情感共鸣,这是否在专业创作中应该引起重视呢?
又如创作的集体性,这当然是极大限制了专业艺术水准的提高的。但是,由于没有专业分工,演员和乐师兼任着作曲,一方面创作受到必然的限制,也多取沿用旧曲之法,另一方面却使他们获得了一种创作能力和素质,形成了一种传统,并使这种创作往往同舞台性生生相连,与欣赏需求息息相通。由于是兼职,二度创作与一度创作结合得也更为紧密,其中渗融的一度创作也更为丰厚、自觉。正如丰富、复杂的戏曲润腔中就不仅有演唱技巧,也还有着创腔技巧,故而戏曲演唱远比一般声乐表演对曲谱的增、减色要大得多。更可贵的在于,其中的即兴创造,往往由于置身于舞台戏剧情境之中而格外具有对情感与形式对应同构的真切体味。这种体味,构成了他们创作素质中一种非常可贵的、关于艺术的“直觉”经验,一种有价值的艺术想像力和创造力。这对于专业音乐教育中,由于主要偏重传授作曲的技术、技巧,而且技术训练相当繁难复杂,负担沉重,因而极易产生艺术创造中技术性与艺术性失衡的状态,应该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因此,当我们确立专业分工、追求专业水平的提高、充分调动专业技巧、发挥作曲家个人才智和个性风格的同时,是否也应该注意对原有民间传统中遵从戏曲综合性规律,各部分创作的相互结合、统一、互补,并重视舞台性的特殊要求,以及关注戏剧情感与戏剧形式的特殊对应,多予研究和发扬呢?是否对西方专业音乐的“尊谱观念”〔5〕不可简单横移接受,而对戏曲音乐表演中的一度创作才能、贡献、和价值给予应有的尊重和考虑呢?
再如形态的可变性,这又是同戏曲不终止的、累积性的创作状态相联系的。这种作品不固定,不断于表演中添加进一度创作的新质,并且往往是为即兴性质的流动状态,自然会有相当的随意行为加入,但是,它又总是带有智慧财富不断积累沉淀的性质,尤其这种积累还表现了创作对欣赏方面历时演变与共时流布这样双重筛选的可贵适应。可以说,戏曲特殊的“传统戏”现象,便正是由此而产生的。因此,当我们努力提高专业水准,崇尚“定腔定谱”、反对随意即兴发挥、追求把作品固定在最佳状态之时,是否也应该看到专业创作中的一次完成可能或必然存在的不完善?至少承认作品最佳状态获得的必要过程?以及关注现代戏曲发展中通过不断打磨、再创造而产生和积累起新的艺术传统和新传统的意义、价值?
2.中、西关系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中国的专业音乐建设和发展始于20世纪之初。而当时,也正值中西音乐文化的第一次大撞击。伴随着知识界参照欧美体制实施改革求新的浪潮,西方音乐文化通过基督教会歌咏、新制军乐队的建立,特别是新式学堂普遍开设“乐歌”课程(学堂乐歌之旋律则多采自欧美、日本歌曲曲调)日渐渗入我国民众的音乐生活。而专业音乐教育虽承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一面传习西洋音乐(包括理论与技术),一面保存中国古乐,发挥而广大之”的办学方针〔6〕,但大体参照欧美音乐教育体制,并以教授西洋音乐知识、技能为主要内容是基本办学格局,而且此种总体背景的影响和制约,甚至其中“以西代中”的倾向时有发生,并很鲜明。比如用西洋歌剧来改造甚至取代中国戏曲的意见从本世纪初就一直存在,然而正如刘半农在20年代就批评的那样,“我们听过采用东洋音调编成的小学唱歌,也听过硬用中国文字配合西洋音调的耶教赞美诗”,但结果是“听了要头痛”的。戏曲尽可,也必须改革,“但必须按着步骤,渐渐的改去。若要把它一脚跌翻了搬进西洋货来,恐怕还不是根本的办法”〔7〕。
戏曲音乐的确具有自己独特而深厚的传统。作为一种戏剧音乐,它在戏剧化方式上,与欧洲歌剧以男、女、高、中、低等不同的声部划分,运用咏叹调、宣叙调、多种演唱形式的交替对比,兼以贯连起伏的交响性器乐渲染来表现戏剧之基本格局不同,而采取了一种程式性的方法,即通过行当划分的性格化方式,以及一整套经过提炼、概括后的声乐和器乐上的音乐程式来表现不同的戏剧内容。在艺术形态上,于音乐和语言的紧密关系中.又因汉语语音的独特结构(声、韵、调、一字一义的单音节)而对音乐的旋律、节奏、节拍、调性、音阶等产生了全面深刻的影响〔8〕,带来了诸多的特点。其旋律发展方法又与欧州歌剧的主题发展不同,而是以民族变奏法为主,并成为了曲式结构和旋律发展包括对程式变化运用中的重要原则。节拍、节奏的独特、多样也与欧洲歌剧不同:在有拍类里板眼节奏与小节重音并非严格对应,存在着大量非强弱循环的一拍子形式,和句逗式的拍数不规整;在无拍类里则有大量的〔散板〕;还有各种节拍的频繁转换与散起上板、规整转散、慢起渐快,弹性极大的催、撤,以及演唱无拍而伴奏有拍的奇妙结合。至于打击乐的功能突出与形式多样也十分地令人瞩目……。
所有如此等等,构成了戏曲音乐独特的表现方式。它们的形成,自然得到民族传统文化滋养,体现着民族审美心理的追求,受到自身的生存状态、发展历程的规定,有些,则还与民间性质紧密相连。因此,在戏曲音乐的专业性转换中,对其独特传统应有一个周密客观的分析,严格把握继承革新的对象,克服艺术上的单线进化论观点,避免对西洋音乐专业化模式自觉或不自觉的照搬。如果联系当前的戏曲音乐教育大体还是西洋音乐作曲技术的“四大件”加上戏曲传统的专题为内容,戏曲作曲也多取戏曲旋律加上西洋传统和声等状况来看,提出上述的要求,就显得绝非是多余的了。
3.一般、特殊关系
音乐作为一种表现艺术,其形式与情感之间的对应关系既受到人类共同的生理和心理机制的相应制约,同时也会受到不同的地理、历史、社会因素的深刻影响。因此,音乐的表现便会具有人类共通的一般表现规律和不同民族的特殊表现规律。而且,格式塔心理学说已经通过某种实验阐述了一般表现规律对于形式与情感之间那种“内在关系”的普泛性意义。故而在戏曲音乐努力实现专业性转换,积极提高创作水准,力求更多获得作品动情、入戏、优美之创作自由的情况下,于深入了解戏曲内在规律的同时,积极探寻和理性把握音乐表现的一般规律,以摆脱仅仅熟悉传统程式来择调、定板、安腔的创作老套局面之限制,便是十分迫切和必要的。
的确,在欧州高度发展的、已经构成体系的专业作曲技法中,是存在着音乐创作的一些共同规律的;而在民族戏曲中,虽然剧种众多、声腔各异,但也具有某种共同艺术精神和音乐特点。因此通过对西洋作曲理论和技术的学习借鉴,以及对民族戏曲音乐共性特点的研究把握,来求得专业水准的提高,对音乐表现戏剧准确性的自觉,都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而且目前都还做得并不充分。
然而,相对于西洋音乐来说,中国音乐毕竟有着自已的民族特点:而相对于戏曲的民族性来说,则又还存在着剧种的地方性。因此、在戏曲音乐专业性转换中必须注意处理好音乐表现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关系。努力让一般溶于特殊之中,而不要以一般取代特殊,更不能以某一种特殊去取代其他所有的特殊。就剧种音乐的地方性而言,它实际体现为不同地区民众的一种特殊情感表达方式。它既有文化经验的积淀意义,但更与各地的自然地理、人文历史因素紧紧联系、深刻地表现了与各地民众之性格、气质、情感和行为方式的对应,与不同文化模式的对应,故而具有了相当稳定的特点,旺盛的生命力,和不容忽视的价值。因此,当我们看到专业性水平提高的同时,当代戏曲音乐创作中却不乏把欧州歌剧音乐主题发展手法、传统和声的配置作为先进手段划一地使用;采用大量带着似是而非的“戏曲特点”的音乐语汇而导致决不少见的“泛剧种化”现象;潜意识中希望所有剧种都走一种发展道路;要求它们都承担相同的功能、表现一样的题材……,便不能不引起我们对专业性发展的模式化、西方化的警惕,和对音乐表现特殊规律的高度重视了。
总之,现代戏曲音乐的发展、必须加快由民间性向专业性的转换步伐。但又必须高度重视既发扬传统精神,又服务于现代,并走向未来。
注释:
〔1〕参见汪毓和编著《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修订版)中第二篇之第二章“近代专业音乐的建立和发展”,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年10月出版
〔2〕《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近代戏曲”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杜1983年8月第1版,第156页
〔3〕《现代戏曲音乐的发展》,载《艺术百家》1993年第1期,第105页
〔4〕〔匈〕阿诺德·豪泽尔:《艺术社会学》,学林出版社1987年8月1版,第217页
〔5〕参见拙作《舞台表演艺术——戏曲之魂》,载《中国戏剧》1995年第4期,第25页
〔6〕转引自居其宏:《20世纪中国音乐》,青岛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14页
〔7〕刘半农:《梅兰芳歌曲谱序》,载《艺坛》1995年第2期,第54页
〔8〕参见拙作(论戏曲音乐的重字传统》,载《戏曲研究》第28辑
